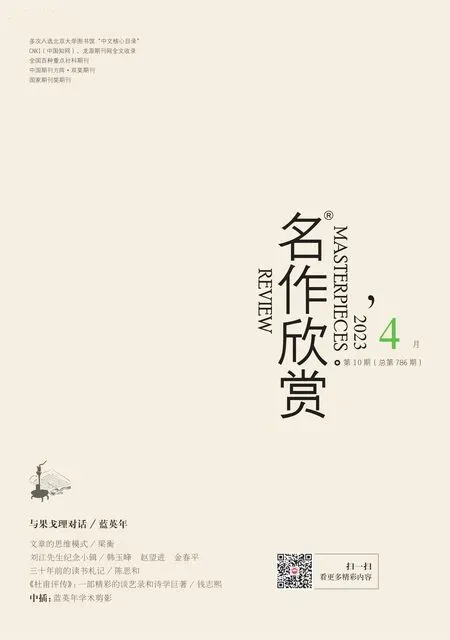口述史與互文性視野下的《戰火中的青春》
福建|徐勇
近些年來,口述史的整理與出版備受關注,其價值在被充分認可和挖掘的同時,也潛藏有一定的問題。有些口述史,在復現歷史或打撈歷史的口號下,暗地做著解構革命歷史或正史的工作。這樣的口述史,某種程度上仍舊屬于新歷史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但也有這樣的口述史,其既起到補充正史的功能,也能讓我們對歷史有更加真實豐富的認識,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初心”有更為深切的體認。應該說,《戰火中的青春》(祁向東主編,三晉出版社2021 年版)就屬于后一類。
口述史的問題域
作為一種敘事類型,口述史有其特定的問題域和敘事邏輯,要想充分有效地閱讀、認識口述史,離不開這一方面的考察。從敘事的角度看,口述史常常表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敘述上的平實粗放,第二種傾向是細節上的鮮活生動。兩種傾向往往在同一篇口述史中有癥候性的呈現。大體上看,這與口述史的回憶性結構密不可分。口述史大都是根據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事后的口述回憶整理而成,當下情境與回憶結構之間的對照關系,制約并形塑了口述史的敘事形態。具言之,印象的強弱決定了敘事的形態及其敘事結構。某些印象深刻且與口述史個人密切相關的事跡,會在口述史中以鮮活生動的細節表現出來,而那些印象模糊或印象不強烈的事件則會以快節奏或粗線條的方式呈現。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記憶的不成體系和敘述的零碎化傾向。因為是事后回憶,記憶的不成體系帶來口述史敘述上的零散化傾向。口述史中很少有貫穿始終的故事,常常只是一些散落的珍珠,甚至會出現口述史中各個情節或細節之間的抵牾矛盾關系。當然,因為是事后回憶,口述史還會出現史實或細節不準確的問題。回憶中的事件,跳躍性強,彼此不連貫,沒有一定的邏輯。因此,如何看待口述史中零散的情節,能否從零散的細節或情節構筑某一主題或主旨,就成為一個問題被提出。
這些問題如不能很好地解決,便會極大地影響口述史的閱讀和接受。從這個角度看,口述史的問題域不僅僅是方法論,更是關乎本體論的核心命題。
敘事學價值
口述史的敘事學價值,集中體現在其大量的零散的細節上。《戰火中的青春》中的細節,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充滿傳奇性和戲劇性的細節。比如說王玉金,一個入伍才三年的20 歲的司號兵,在一次完成任務趕回駐營地的路上,單槍匹馬俘虜了國民黨殘部一個排(《號聲嘹亮,耳畔長鳴》);比如說青年宋福才深入虎穴,活捉土匪頭目“四大天王”(《“獨膽英雄”宋福才》),再比如說兒童團員宋福才智勇識漢奸(《“獨膽英雄”宋福才》);還比如說大字不識的兒童團長劉文修給八路軍送信接頭的細節(《激情燃燒的歲月 戰火紛飛的青春》)。
這樣的細節,雖看似充滿戲劇性,但卻實實在在。口述史把這樣的細節展現出來,讓我們對普通戰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知。相反,在革命歷史小說中,傳奇性的細節則大多發生在赫赫有名的英雄身上。發生在英雄身上,即使是再有傳奇色彩,也并不覺得突兀,比如說《紅巖》中雙槍老太婆的傳奇故事,比如說《林海雪原》中楊子榮深入虎穴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宋福才的行為,酷似楊子榮,但這樣的傳奇故事卻發生在普普通通的小戰士身上。這就不禁讓人產生這樣的感想:普通戰士也可以成為英雄,每個戰士都可能成為英雄,英雄壯舉是廣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身上最光輝的品質。而這也更加印證了一點,即之所以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國最廣大的人民走向革命的勝利,是因為我們的黨把普通士兵身上這種英雄氣質充分激活激發了出來。這是國民黨不可能做到的。
一類是普通但不平凡的戰斗細節。這樣的細節,在這部口述史中隨處可見,但也最為感人。這樣的細節,發生在每一個普遍的士兵身上,它也使得這些普遍士兵顯得并不平凡。這樣的細節的意義在于,它凸顯了一點,即革命的勝利是由一個個普普通通但并不平凡的士兵的共同努力得來的。普通但不平凡,是這些最廣大士兵的共性。相比那些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聚焦英雄典型,這些口述史則把聚光燈聚焦到了那些普普通通的士兵身上。從這個角度看,口述史形成了對革命歷史敘述和革命正史的有力補充作用;它們之間互為補充和完善,因此可以說,缺少了哪一塊,我們的革命歷史都是不完整的或不充分的。
還有一類就是細節本身的真實可感。比如劉文修記憶中朝鮮戰場上的熟土豆:“土豆雖然是煮熟的,但嚴寒的天氣下,很快就凍得發黑,硬得像石頭,吃到嘴里會發苦。”(《激情燃燒的歲月 戰火紛飛的青春》)這一細節,突出了視覺(“發黑”)、觸覺(硬得像石頭)和味覺(“發苦”),給人一種真實感,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有這樣的細節表現。比如說還有劉文修作為偵察兵的獨有經驗的呈現:“走一段,就趴下聽一聽,聽有沒有動靜。”“借助微弱的聲音,來辨識黑暗里的情況。”(《激情燃燒的歲月 戰火紛飛的青春》)
互文性閱讀
就《戰火中的青春》而言,要想有效把握其價值和意義,需要從互文性的角度展開閱讀。即是說,作為革命戰士的口述史,有必要把它放在同紅色經典構筑的革命歷史和歷史教科書樹立的正史的對照意義上把握其價值。這樣的好處是,既能彌補口述史中史實不準確的問題,也能彌補正史的細節缺乏、革命敘事史忽略普通大眾的問題。正史或革命歷史一般不會聚焦普通士兵和普通士兵中的平凡事跡,《戰火中的青春》則大多側重于此。這是經歷過大小無數次戰斗的老兵的口述,這些口述史不是要重寫歷史,也不是為了顛覆革命史觀,而是為了豐富對革命正史的理解。比如說張興旺經歷的太原戰役(《忠魂鑄就的烈火青春》)和崔慶軒經歷的太原戰役(《不拿槍的戰士也是英雄》),就與正史中解放戰爭時期的太原戰役不同。這是由口述史的不同視角所決定的,張興旺是戰士,崔慶軒是軍醫,他們眼中和記憶中的太原戰爭自然不同。
從互文性角度展開閱讀,還可以有效建立起《戰火中的青春》同正史相互佐證的關系。比如說《忠魂鑄就的烈火青春》中張興旺眼中的巴金訪問志愿軍并寫出了《英雄兒女》一事。口述者張興旺當時并不知道那個來志愿軍陣地慰問并和陣地上的士兵交談的人是誰,后來才從團長那里得知是巴金,一個大作家。巴金根據他們的真實戰斗事跡寫成小說《團圓》,后來又被拍成電影《英雄兒女》,張興旺這里把《團圓》說成是《英雄兒女》,也與事實略有不符。這就需要互文性的閱讀加以印證。再比如說劉文修口述中的長津湖戰役(《激情燃燒的歲月 戰火紛飛的青春》),里面出現了“冰雕連”,也可以與電影《長津湖》或相關史實對照閱讀。
更重要的是,通過把口述史與正史聯系起來,可以有效建立或重構宏大敘事。僅僅從口述史所呈現的細節之間的關系,是無法建立其宏大敘事的,因為這些都不成體系和系統,彼此多是無邏輯關系的細節。我們有必要從整體的、歷史的和辯證的角度把握口述史講述的細節。其結果,這些看似零散的珍珠,就不僅僅是散落的單獨形態,而是整體秩序和歷史進程中的,與整體歷史密切相關或對應的細節,通過把它們與正史對照起來,可以有效建構起宏大敘事的口述傳統,以豐富和拓寬我們對整體歷史的深入認識。
這些口述史大都關乎平凡的士兵和平凡的事跡。但正是透過這些平凡事跡,我們看到的是普通士兵的赤子之心和革命熱忱,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意基礎。如戰士不慎打破了百姓的瓦盆,“連隊立即將五千元邊區票(解放區貨幣)連同一張寫有部隊編號的賠償字條壓在盆底下”,“借用了百姓的水桶,歸還時都要挑滿水再還”。(《不拿槍的戰士也是英雄》)這些細節,既表現了解放軍同廣大百姓的魚水情誼,更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體現,特別具有生活氣息。可以說,正是有了這些細節,我們對正史和“革命初心”的認識,就不會是理念化的和僵化的,而是具體的和生動的。
這些口述史還豐富了我們對反戰主題的新的認識。比如說如下的敘述或細節:“解放了,就不用打仗了;不用打仗了,就可以回家孝敬父母娶老婆啦。聽著戰友們你一言我一語地拉呱著,張興旺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忠魂鑄就的烈火青春》)從中我們能感覺到戰士們對和平的深切渴望,但也是這種渴望,推動著戰士們踴躍參軍,奮勇殺敵。這些口述史讓我們明白一點,所謂反戰主題是與戰爭動員聯系在一起的,沒有以戰止戰,是不可能有和平的。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在這些戰士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和平是與勝利聯系在一起的,和平是勝利后的和平。即是說,這是通過戰爭以建設一個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服務的新的中國。他們期望的和平是一個美好社會的和平環境,而不是茍且偷安,不是被壓迫下的忍耐。
綜合前面的觀點,可以認為,通過互文性的角度展開口述史的閱讀,我們能在敘事的層面確認《戰火中的青春》的意義和價值。其價值主要表現在,這些口述史,以其大量的、沒有聯系、缺乏鋪墊和鋪敘的零散細節,共同塑造和構筑了大寫的“最可愛的人”——解放軍戰士——的形象。就像口述史的整理者所說:“每一位死去的烈士,都是一座紀念碑。每一位活著的老兵,都是我們的英雄。”(《忠魂鑄就的烈火青春》)從這些口述史來看,其中的主人公們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他們對加入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說不出多少深刻的道理,也不能從階級的高度認識;但從他們樸素的道德觀和深厚的愛國主義立場,從他們看似充滿了偶然、意外或隨意的選擇,我們看到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最廣大人民自發而自覺的追求。口述史的意義就在于,它把這種樸素的感情(即樸素的道德觀和深厚的愛國情感)表達了出來,讓每一個閱讀它的人,都能真切地體會到并被深深地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