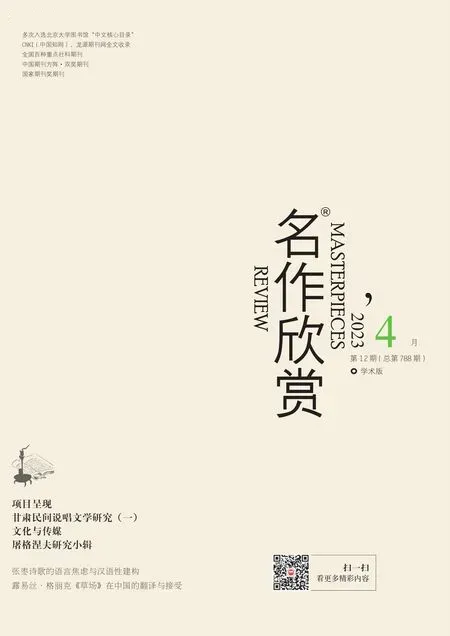曲解與濫用
——淺談唐宋詩詞名句的“變味”現(xiàn)象
⊙李冰慧[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南京 210023]
隨著傳統(tǒng)文化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比重增大、互聯(lián)網(wǎng)尤其是網(wǎng)絡(luò)文藝信息的快速發(fā)展,唐宋詩詞在各類資訊、文章以及日常交流中的出現(xiàn)頻率也有了明顯的增加。而在大眾知識儲備豐富度和細(xì)致度都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伴隨著高數(shù)值的“出鏡率”,就難以避免出現(xiàn)了一些曲解和濫用現(xiàn)象。尤其是熱度較高的唐宋詩詞名句和選入中小學(xué)階段教材、教輔的詩詞,更是“變味”現(xiàn)象的高發(fā)區(qū)。
一、斷章取義與泛濫引用
引起曲解“變味”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斷章取義。詩詞表意大多婉轉(zhuǎn)隱晦,須將詞句放入整首詩詞方能體悟其意。而許多唐宋詩詞名句在引用和再創(chuàng)作過程中被人按照字面含義取義,語境與原詩語境大相徑庭,甚至鬧出笑話。
如元稹《離思五首·其四》本是其在妻子去世多年后所寫的悼亡詩,可今人引用其中名句的表意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有人引用“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來表達(dá)對過去一段感情中對愛人的念念不忘,以顯自己的情深意重;如果這種表意與原詩還尚算有幾分契合,那么引用“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來抒發(fā)自己對某種事物的喜愛甚至向自己的心上人表白,則更加離題甚遠(yuǎn)。
而當(dāng)一句詩詞同時滿足“名句”“高大上”和“斷章取義”幾個要素,就極有可能通向“泛濫引用”的結(jié)果。這一點在中小學(xué)課本或教輔范文中出現(xiàn)的詩詞名句上體現(xiàn)得較為明顯。比較典型的有蘇軾《定風(fēng)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的末句“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本是歌頌“柔奴”隨緣自適的曠達(dá)與樂觀,是一句“蘇東坡式的警語”,寄寓著他與柔奴這一心境高度類似的人生態(tài)度和處世哲學(xué)。但因為其“高大上”的風(fēng)格,再加之各類教輔對此句的偏愛,近年來,“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伴隨著各種各樣的語境出現(xiàn)在無數(shù)的中小學(xué)生作文結(jié)尾——寫搬家轉(zhuǎn)學(xué),用之;寫考試失利,用之;寫學(xué)業(yè)壓力,用之;甚至寫業(yè)余愛好被家長反對、沉迷書海無法自拔,也可用之。層出不窮的“此心安處”,不僅造成了觀者對詩詞名句的視覺疲勞,更使詞句在紛繁的曲解中“變味”。
二、泛愛情化的營銷手段
在網(wǎng)絡(luò)文藝流行的今天,與愛情相關(guān)的網(wǎng)文似乎更能吸引讀者,帶有愛情浪漫氣息的唐宋詩詞則更是被許多網(wǎng)友認(rèn)為“有美感有意境”而成為“流量密碼”。但在營銷背景下,霸屏網(wǎng)文中的許多熱門愛情詩詞除婉轉(zhuǎn)動人的“真愛情詩詞”之外,還有許多由其他詩詞名句曲解而來的“偽愛情詩詞”。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無疑是蘇軾《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流傳最廣的經(jīng)典名句,經(jīng)常被各種營銷號引用作“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長久相伴”之意。但其實,序言就已經(jīng)點明“丙辰中秋,歡飲達(dá)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很明顯,“但愿人長久”在詞中本是對親人平安健康、能與自己相隔千里共賞明月的慰藉與期待,引申為對愛人的祝愿無可厚非,但若狹義地把此句理解成愛情詩詞,則是一種“變味”的曲解。
“一樹梨花壓海棠”被各種網(wǎng)文引用來渲染情人相處的旖旎氛圍或直接用以描寫男女歡愛的場景。其實,這句詩出自蘇軾調(diào)侃好友而作的《戲贈張先》:“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fā)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本是對老夫少妻的調(diào)侃,卻被當(dāng)作描繪情人纏綿相處的愛情詩詞而廣泛引用,不免讓人啼笑皆非。
有段時間,一句內(nèi)容為“夜深忽夢少年事,唯夢閑人不夢君”突然被很多情感博主當(dāng)作作品文案,與之相配的故事往往是懷念年少時錯過的愛人,作者則滑稽地被不同博主標(biāo)注為白居易或是元稹。事實上,上半句“夜深忽夢少年事”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描繪的是琵琶女回憶年少貌美時奢華風(fēng)光的場景;下半句“唯夢閑人不夢君”則出自元稹的《酬樂天頻夢微之》,所表現(xiàn)的則是元、白二人的知己情深,元稹病中聽聞知己夢“我”,心中牽掛又難夢對方的愁腸。上下兩句本出自兩位詩人的兩首作品,又都和愛情毫無相關(guān),卻在大眾辨析度不高和營銷手段泛愛情化的雙重影響下,成為一句“感人至深”的愛情詩詞,不得不說“變味”嚴(yán)重。
三、胡亂拼接的熱門文案
因為唐宋詩詞名句本身帶有的優(yōu)美特征,經(jīng)常有人將其剪切拼接成文案以表情達(dá)意。但在剪切拼接的過程中,往往極易出現(xiàn)詩意的曲解與“變味”。
“以夢為馬,詩酒趁年華”是網(wǎng)絡(luò)文藝青年常用的文案標(biāo)題。前半句出自海子的現(xiàn)代詩《以夢為馬》,后半句則出自蘇軾的《望江南·超然臺作》。且不論這兩句都不是“珍惜年輕時光,享受詩意生活”之意,單是這一今一古的組合用以烘托文青氣質(zhì),便使得這種文藝氣質(zhì)稍顯滑稽。
“夜闌臥聽風(fēng)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出自陸游的《十一月四日風(fēng)雨大作》。夜深雨急,詩人病臥于床,側(cè)耳聽見的風(fēng)雨之聲,如山河破碎之音化作心境。垂老志士,癡情化夢,俱是空有報國之志卻壯志難酬、僵臥孤村仍心系戍邊的悲慨。但網(wǎng)絡(luò)上竟然出現(xiàn)了“夜闌臥聽風(fēng)吹雨,鐵馬是你,冰河也是你”,而且流傳甚廣,一度成為此詩句詞條的頭條。此種胡亂拼接,表意庸俗,不僅與原意風(fēng)馬牛不相及,更是對詩人與作品的極大不尊重,馥郁芬芳的慷慨悲歌“變味”成了惡臭低俗的土味情話,情懷之淪喪令有識有情者聞之悲怒。
胡亂拼貼造成的詩詞名句“變味”,其“變味”方向與斷章取義或愛情化營銷相比,更加不可測不可控。而同理的拼接“變味”不僅在詩詞名句中有體現(xiàn),在個別古文中更是千奇百怪。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結(jié)尾有一句為“庭有枇杷樹,吾妻死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竟有惡搞網(wǎng)友續(xù)寫了一句“今伐之,為搏小娘子一笑”,后又被其他筆者強行續(xù)寫拉回“小娘子為吾妻與吾之女,今伐樹,為小娘子造出家之物”,其拼接改寫的戲劇化直接將原文之味毀之殆盡,比之詩詞名句之“變味”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流量之下,何以達(dá)詁?
早在西漢時期,董仲舒就明確提出過“《詩》無達(dá)詁”,這種觀點在后世的流傳過程中演變成了“詩無達(dá)詁”,意思是文學(xué)作品的意義是沒有確切解釋的。那么,在這種觀點之下,唐宋詩詞名句的“變味”現(xiàn)象是否也顯得無可厚非呢?
誠然,從文本角度看,詩詞本身具有豐富性和審美的多義性;從讀者角度看,接受者對作品的闡釋也往往會有個體差異。“詩無達(dá)詁”的確有其合理性。但是,“曲解”應(yīng)有度,“詩無達(dá)詁”不意味著可以任意解讀。
古典詩詞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晶,經(jīng)典厚重的詩詞文化+新潮活潑的流行熱點,這樣的融合模式原本不失為新時代文化豐富多樣化發(fā)展的優(yōu)質(zhì)范例——典雅的詩風(fēng)詞韻為流量時代的快餐文化增添了幾分含蓄深沉的韻致,打造出令觀者眼前一亮的獨特美感;流量時代的巨大舞臺也為詩詞文化吐故納新提供了新的契機(jī)。然而,光鮮舞臺下隱藏的巨大利益,也將“詩無達(dá)詁”裹挾進(jìn)了流量旋渦。
詩詞名句曲解濫用現(xiàn)象的背后,跟風(fēng)逐利的浮躁心態(tài)和迎合市場的諂媚心理不可忽視。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這種迫切牟利的心理具象成為來勢兇猛的流量追逐與流量操縱。
大數(shù)據(jù)時代,觀眾的每一次消費行為都會被保存成數(shù)據(jù),并形成市場導(dǎo)向。有著“互聯(lián)網(wǎng)原住民”之稱的年輕一代正在成為當(dāng)下影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受眾和消費主體,他們的喜好也就在極大程度上左右著文化市場前景,尤其是商品文藝的創(chuàng)作方向。而這批年輕人作為新生網(wǎng)絡(luò)小說的閱讀主力軍,審美趣味受到了近十幾年網(wǎng)文偏重“唯美夢幻”、極富“網(wǎng)感”的語言風(fēng)格的直接影響。“網(wǎng)感”的一大特點,就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時髦感”和半俗半雅的“高級感”。化用、借用古詩詞對作品加以點綴,正有助于部分商家和創(chuàng)作者營造一種虛無縹緲的“網(wǎng)感”,從而吸引年輕的受眾。
數(shù)據(jù)可視化、觀眾年輕化、審美“網(wǎng)文”化使得詩詞名句成為快餐文化時代當(dāng)之無愧的“流量密碼”。那些對經(jīng)濟(jì)效益狂熱追逐的從業(yè)者,往往秉持著“文化搭臺,流量、經(jīng)濟(jì)唱戲”的功利觀念,只顧眼前利益,無法沉下心來對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鉆研與消化,全憑一些膚淺和片面的理解,就張貼出“吟風(fēng)弄月”的活招牌,甚至打起“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旗號,生搬硬造,文義不符,以至于弄巧成拙。不僅吃相難看,還糟蹋經(jīng)典,鬧出笑話。
除了大規(guī)模的逐利熱潮導(dǎo)致的濫用曲解,部分青少年反傳統(tǒng)、反權(quán)威式或叛逆發(fā)泄式的惡搞改編也是詩詞名句“變味”的另一不可忽略的“陣地”。
部分青年人意圖通過對傳統(tǒng)文化的諷刺和娛樂來傳遞他們概念中的“后現(xiàn)代精神”,將對古詩詞的惡搞改編詮釋成一場網(wǎng)絡(luò)中的青年亞文化狂歡,以戲謔、顛覆經(jīng)典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屬于他們的流行藝術(shù),塑造出一個叛逆、自由的“理想世界”。在這個“理想世界”里,反叛權(quán)威的“經(jīng)典惡搞”釋放著他們的內(nèi)心壓力,成為他們暫且逃避繁重課業(yè)負(fù)擔(dān)、消解激烈升學(xué)競爭的“避風(fēng)港”,充當(dāng)著他們尋求獲得他人認(rèn)同、滿足青春期“虛榮心”的特殊途徑。當(dāng)然,青少年群體中這一反叛和發(fā)泄方式的流行,也和當(dāng)下社會過分娛樂化文學(xué),片面追求淺薄化的感官刺激和碎片快感,以及“越墮落越快樂”的享樂主義陷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聯(lián)。
那么,在流量裹挾之下,如何守住詩詞文化“變現(xiàn)”的底線,厘清化用借用詩詞語句的規(guī)范,使唐宋詩詞得以“達(dá)詁”呢?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市場和群眾兩個方面加以糾治。
互聯(lián)網(wǎng)消費時代,泛娛樂化市場不斷擴(kuò)大,古典詩詞的曲解與濫用和媒體平臺的經(jīng)濟(jì)利益相互交融。因此,相關(guān)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重視濫用、惡搞傳統(tǒng)文化以惡性牟利的亂象,并出臺相應(yīng)的條例規(guī)范市場。即便難以劃定對惡搞濫用古詩詞行為“一刀切”的標(biāo)準(zhǔn),至少也應(yīng)當(dāng)對平臺運營加以規(guī)范,要求各大平臺提高審核標(biāo)準(zhǔn),尤其要對自媒體平臺的流量投放方向加以審核。平臺對惡搞作品的限流和對健康向上作品的流量投放,可以引導(dǎo)個體創(chuàng)作者和商業(yè)創(chuàng)作團(tuán)體自覺創(chuàng)作優(yōu)美健康的文化新產(chǎn)品,從而使健康的文商結(jié)合理念蔚然成風(fēng),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場風(fēng)氣。
從群眾角度來看,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下信息接收的個體,我們應(yīng)當(dāng)有意識地提高自身的文藝審美。并非要求人人都去理解和喜愛“高山流水”的晦澀之作,但至少應(yīng)當(dāng)自覺抵制低俗化的不良文化信息,克服惡搞帶來的淺薄感官刺激和將曲解“變味”經(jīng)典“奉為圭臬”的平庸審美趣味。若是對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感興趣,也應(yīng)該沉下心來,正視文化“短板”,彌補文化缺失,對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了解、鉆研與消化,而不是將曲解濫用的“偽經(jīng)典”作為武裝自己認(rèn)知的鎧甲。群眾多一些理性和思考,才能避免文化精神枯萎在“因狂笑不止而抽搐的空虛”中。
關(guān)于如何對這些詩詞名句進(jìn)行科學(xué)性解讀和運用,我們也可以從孟子的言論觀點中得到一些指導(dǎo)經(jīng)驗——“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不以文害辭”,是說不要因為個別字詞而誤解了整個詞句;所謂“不以辭害志”,是說不要因為對個別詞句的片面解讀而曲解了整個作品的真正含義。應(yīng)該是以“意”(自己真切的感受)去“逆”(分析和領(lǐng)會)作者的本意,求得對作品的準(zhǔn)確理解。
“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與作品的關(guān)系。“論世”則是要了解作者所處的環(huán)境、時代,以及環(huán)境、時代對作者和作品的影響。
正如王國維說:“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有了“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結(jié)合之下的“曲解”,也就大概率能夠合情合理地豐富詩詞的內(nèi)涵。
總之,闡釋者在解讀詩歌時,有著對其進(jìn)行個性化感發(fā)與聯(lián)想的自由。但這種個性化的闡釋絕不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純粹主體性活動。“詩無達(dá)詁”雖然肯定了詩歌的意義并非唯一,但在解“詩”引句時亦不能脫離作品本身而任憑主觀意念自由演繹甚至無底線惡搞。尤其是進(jìn)行文藝作品和文化產(chǎn)品的創(chuàng)作時,更要在尊重作品的基礎(chǔ)上適當(dāng)發(fā)揮,無限類推、無中生有、張冠李戴、極度“變味”的曲解與濫用是斷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