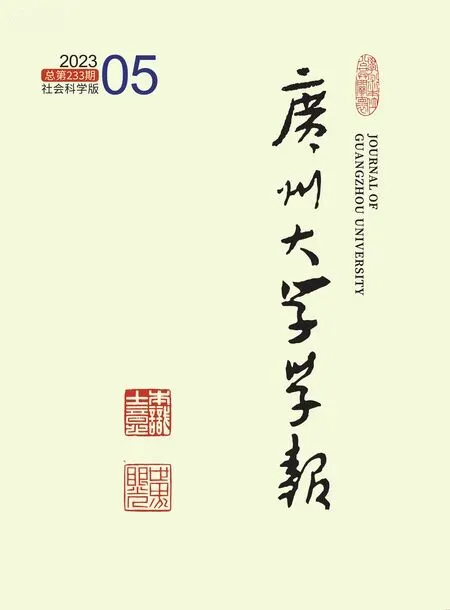幻想的經濟學初探:以虛擬化親密關系為例
傅善超
(北京市 西城區,北京 100038)
一、研究虛擬化親密關系的理論意義
網絡技術與大眾文化自身的發展為偶像粉絲文化增添了強烈的虛擬化屬性,在本身想象性親密關系的基礎上,粉絲和偶像分別呈現為“虛擬化身”與“虛擬實在”的形態——研究這種“虛擬化的親密關系”[1]的首要理論意義在于,這個現象內在地介于文化與經濟學維度之間,對相應的理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迄今為止尚沒有粉絲文化研究的理論完滿地處理這兩個維度之間的關聯,多少都有將兩者割裂的傾向。
當然,虛擬化親密關系的內在邏輯本身對于文化研究來說也具有普遍意義。雖然發端于偶像粉絲文化,但虛擬化親密關系影響實際上遠遠超出偶像粉絲文化本身。其內在的軸線,是以“角色配對”為基本前置動作的、對“親密關系烏托邦”的幻想性探索,[2]這種想象性活動并不依賴于網絡技術,而強烈地具有在“潛在”維度中探索、游戲的性質。由于“潛在”和“虛擬”是對英語“virtual”一詞在不同語境下的翻譯①,因此,可以認為,“虛擬化的親密關系”是借助網絡技術將想象性親密關系內在的虛擬化維度帶到了表面。或許正因如此,虛擬化親密關系不僅作為偶像工業的內在軸線,而且與幾乎所有“女性向”大眾文化都有密切的關聯,甚至還同樣強烈地影響著一些并沒有特別明顯的性別化色彩的大眾文化部類,尤其是近十年內才興起的角色養成類手機游戲與虛擬偶像直播領域。
另一方面,對虛擬化親密關系的商業化具有較為特別的性質,這是必須從經濟學角度進行討論的理由。如果說粉絲文化研究永遠也繞不開“消費”這個關鍵詞,粉絲文化研究永遠已經內嵌于對消費社會的分析,那么,虛擬化親密關系在商業化上的性質也恰好可以提供對消費社會的新視角。當我們采取消費社會這個更加宏觀的視角,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到文化維度與經濟學維度之間的關系為何重要。
經典的關于消費社會的理論,可以分為對文化的分析和對經濟學關系的分析。對消費社會的文化分析,按照分析的對象——也就是消費的類型,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對符號/差異消費的分析。其基本論述最早由鮑德里亞提出,也就是以對“炫耀性消費”這個現象的分析發展而來的②[3]。之后,經由布爾迪厄的發展[4]和邁克·費瑟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的總結[5],成為最廣為引述、影響最大的對消費社會的論述。
二是對敘事消費的分析,主要的代表為杰姆遜[6]與大塚英志[7]。
三是對角色消費的分析,主要的代表為東浩紀提出的“資料庫消費”的理論。[8]
對消費社會的經濟學分析,最有影響的論述則來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厄爾奈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以及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師徒。前者是較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將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征定義為在剩余價值的實現愈加困難的情況下服務部門的不斷擴張。[9]后者的論述圍繞著斯邁思提出的具有一定爭議的“受眾商品”的概念,希望改變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理論批判中偏頗的“文化主義”傾向,并嘗試將經濟學直接引入傳播學。③“受眾商品”概念之后被福克斯繼承,結合數碼資本主義的新現象,將其進一步發展為“生產-消費者的數字勞動”。[10]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文化或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消費社會,這兩個角度事實上包含激烈的理論對立: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處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對于后一種角度來說,基本的理論立場是力圖呈現文化實踐中經濟學過程的直接在場,斯邁思與福克斯的論述即非常鮮明地展現了這一立場。對他們來說,在文化分析中哪怕策略性地“懸置”經濟學維度也往往意味著實際上的“文化主義”。而對于前一種視角來說,關于消費文化的分析,無論出發點如何,最終都實際上分離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讓文化首先按照某種內在邏輯獨立地運轉,然后再與經濟學概念相連接。
當然,前一種對消費社會的文化分析也常常反對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簡單二分,鮑德里亞即對此有非常明確自覺的表述。[11]然而,他反對此二分的方式卻是,宣稱符號差異系統本身就包含一種不局限于經濟交換的廣義的經濟學規律,也即所謂的“符號經濟學”。最終,這種“符號經濟學”實際上拆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核心論述,從而不過是一種“反經濟學”。費瑟斯通對鮑德里亞與布爾迪厄的繼承和總結能夠更好地體現這種“反經濟學”的態度:他認為,是符號商品自然趨向的“通貨膨脹”導致了消費領域的擴大。這個結論完全是對曼德爾這一派觀點的顛倒,后者將消費領域的擴張首先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也即剩余價值實現困難的一種應對方式。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難辨識出虛擬化親密關系這個現象的特別意義——它剛好橫跨在上述兩種對立的視角之間。從消費的對象來說,虛擬化親密關系當然具有極其鮮明的角色消費的特點,[1]并因此獲得其相對的“文化自主性”;而另一方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以偶像工業為例,偶像經紀公司獲取利潤的絕對主要方式,正是將“受眾商品”——在這里是粉絲的熱情與忠誠——轉賣給廣告商。這一點從上市偶像經紀公司的招股說明書中不難確證。例如,在港交所上市的樂華娛樂集團的財務數據中,占收入主要份額的業務類別為“藝人管理”,在這之中份額最大的子類別“商業活動”,也就是其轉售“受眾商品”獲利的最主要渠道。按照財報中的數據,從2019年到2021年這三年中,“藝人管理—商業活動”的營收分別占總營收的50.2%、60.2%、71.4%。[12]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虛擬化親密關系來說,這兩個維度決不是割裂的。在前述所有理論中,斯邁思與福克斯師徒的“受眾商品”的概念是最有希望將兩個維度結合起來的。然而,盡管這確乎是一個讓經濟學維度直接在文化消費中在場的理論,“受眾商品”的概念卻也無法對文化分析提供多少幫助。事實上,他們選擇的具體案例本身也就缺少文化與經濟學兩個維度的有效交匯:對于斯邁思主要分析的電視媒體而言,廣告時間是對觀看時間的簡單侵占;對于福克斯主要分析的社交網絡而言,用于廣告銷售的數據是在用戶無意識的情況下被采集的。這兩類媒介消費中,文化的維度與經濟學的維度或者相互排斥,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并行不悖。而相較之下,對于以虛擬化親密關系為消費主軸的大眾文化實踐來說,這兩個維度恰恰互相促進:通常來說,不僅通過偶像代言來轉售“受眾商品”是經紀公司最主要的獲利手段,而且,粉絲消費偶像代言的產品,本身就是對偶像的角色消費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因此,盡管當前很難說以虛擬化親密關系為主軸的文化消費已經在大眾文化中占據了主流,但從上述梳理不難看出,想要對這個現象做出較為完整的理論分析,將難以避免地要求我們超越以往理論中文化與經濟學視角的割裂與對立。本文的主要目標也正在于此:希望借助對虛擬化親密關系的考察,初步搭建起一個能夠恰當地連接文化文本與經濟學機制的理論框架。為了方便起見,本文將主要以偶像工業為案例,并主要參考對偶像工業的已有研究,僅僅在需要特別辨析時才提及角色養成類手機游戲。虛擬偶像直播行業的情況與前兩者差異較大,且還在發展中,在此只好暫且不論。
二、兩個概念的澄清:剝削與數據
在正式探討虛擬化親密關系之前,我希望首先澄清兩個與之關系密切的概念,也就是“剝削”和“數據”。這兩個概念當然都已經有了非常多的討論,其中前者主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后者則在關于數碼資本主義的討論中。然而,將這兩個概念運用到大眾文化時,目前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卻帶有誤導性,因此必須做出辨析和澄清。
首先,關于“剝削”。由于西方第一代粉絲研究,尤其是受費斯克和詹金斯的深刻影響,粉絲圈獨立于“商業”或“主流”乃至與之對抗的敘事④,對粉絲研究學者來說仍是某種程度的常識。即使在營銷中征用粉絲的無酬勞動已經越來越成為常規操作,國內的粉絲文化研究學者仍然經常在討論此話題時展現出相當樂觀的態度。⑤也正是因為這種態度的深刻影響,粉絲文化研究實際上很難劃歸到對消費社會的研究中。當然,認為粉絲文化與消費社會等外在因素互動時有很強的獨立性,這樣的論述并不是簡單的盲目樂觀。其最核心的論點訴諸粉絲能動性,而這個論述對于媒體粉絲來說確實有效。換言之,希望利用媒體粉絲的商業營銷,幾乎不可能在不大量接受粉絲圈價值觀的情況下實現其目標,這一點即使以福克斯為首的、對詹金斯“參與式文化”概念的最猛烈的批評[13]也很難完全否定。
但是,當粉絲消費的主要對象——也就是粉絲與之維系強烈情動關系的客體——與按照“情動經濟學”(affective economics)[14]的原則進行營銷的產品并不高度重合的時候,粉絲能動性論述的效力就迅速地下降了,因為此時營銷利用乃至于“剝削”的主要是粉絲情動的強度(intensity)而非其質性(quality)。尹一伊關于微博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15]她指出,微博利用算法機制已經將“流量數據”(digital traffic)塑造為粉絲與其情動客體之間的“次級過渡客體”(secondary transitional object)[16]。在這個過程中,“流量數據”已經成為粉絲與情動客體(主要是偶像)之間最主要的聯系中介,而這種中介不僅是抽象化的、與粉絲消費的具體內容幾乎無關,并且還帶有文化霸權的性質。⑥
對于商業化的、以虛擬化親密關系為消費主軸的大眾文化部類來說,虛擬化親密關系的想象本身幾乎從來都不是銷售的對象,或者至少不是直接銷售的對象。這意味著,正如上一節對偶像經紀公司財報的閱讀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大眾文化部類會比較依賴以廣告盈利,故而應非常適用斯邁思-福克斯師徒的“受眾商品”理論。但是,不僅如前所述,“受眾商品”理論對文化文本本身的處理能力相當貧弱,這個概念本身也帶有爭議。所以,盡管“受眾商品”的概念確實有效地攻擊了以往粉絲文化研究的“盲點”[17],非常難得地能夠為我們提供經濟學的切入點,但是我們還是必須首先修正斯邁思與福克斯遺留的誤解,尤其是他們對“剝削”的錯誤界定。
事實上,盡管斯邁思和福克斯喜以好戰的文風慷慨激昂地擎起“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大纛,他們對《資本論》中一些基本理論的認識卻是有偏頗的。在關于“受眾商品”的論爭里,福克斯的自我辯護涉及了很多方面,[10]102-181然而,卻沒有回應真正切中要害的批評。多位批評者都正確地指出,生產“受眾商品”的勞動之所以不應當理解為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受剝削勞動,最關鍵的理由不在于它不具有經貨幣中介的雇傭勞動的形式,而在于,這些勞動服務于中介功能或流通環節。⑦換言之,這些勞動是“非生產性的”(unproductive),因為對執行中介功能或者處于流通環節的資本來說,它們并不自身生產剩余價值,而是將別的部類或環節中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移為自己的利潤。⑧將作為廣告中間商的商業電視網絡、社交媒體、乃至于偶像經紀公司征用受眾與粉絲的無酬勞動的意義,理解為提高了“廣告效率”,并因此令上述廣告中間商獲取了“相對剩余價值”[10]134,從而構成了對粉絲的剝削,這個理解是非常不準確的。“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嚴格地依附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然而,如果以“廣告效率”為使用價值的衡量標準,那么,由于廣告本身是一種競爭或博弈,其效果不僅依賴于廣告商及其目標消費者,而且還依賴于市場上所有其他行動者的決策。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非常飄忽不定的,它只能反映一時一地的競爭烈度,而幾乎不在任何意義上反映社會生產力的演進。
從宏觀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斯邁思-福克斯師徒所犯的錯誤。盡管曼德爾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的論述在一些細節上有忽視非物質性生產的傾向,但他對作為“晚期資本主義”中的一個趨勢的“消費社會”的理解至今仍是一針見血的。如前所述,曼德爾認為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剩余價值實現的愈加困難。因此,高度依賴廣告的媒體與互聯網行業,其首要的經濟學功能,是服務于在剩余價值實現領域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或者說得形象一些,是服務于資本爭奪作為消費者的無產階級的競爭。可以說,斯邁思與福克斯沒有真正理解這一點,所以才誤認為這里會產生與產業資本主義類似的剝削,并且將消費者作為第三方的資本間的競爭誤解為主要是資本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也正因如此,福克斯在辯護中將生產“受眾商品”的勞動與古典奴隸和家務工人受到剝削的情況直接類比,[10]176也是不恰當的。
故而,在分析以虛擬化親密關系為消費主軸的大眾文化時,引入“受眾商品”的概念是必要的,但也要做出一些修正。偶像工業和角色養成類手機游戲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受眾商品”獲取利潤,但因此便說用戶生產了剩余價值并受到剝削,這并不符合《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準確地說,用戶被無償征用的勞動,貢獻的不是生產力,而是掌控這些潛在消費者的資本的權力。換一個角度說,在數碼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通常認為,用戶生產出的“受眾商品”能夠體現為某種形式的數據。那么,作為“受眾商品”的體現形式的這些數據,一概都不是生產要素,而應當理解為權力要素。也就是說,這些數據給資本帶來利潤的方式,不是參與了生產并在其中作為剝削的中介,而是讓資本在剩余價值實現領域獲得了更多分配的權力。
完成了這個關于“剝削”的澄清之后,我們剛好可以接著進入關于“數據”的辨析。我們剛剛指出,作為“受眾商品”體現形式的數據并非生產要素,而是屬于資本的權力要素。然而,這是一個非常理論化的表述。究竟什么叫做“作為‘受眾商品’的體現形式”,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對于社交媒體,福克斯已經給出了解釋,[10]130但其結論不能直接套用到偶像工業。
對于偶像粉絲來說,實際運用的數據概念叫做“流量數據”(digital traffic),或簡稱“流量”(以下也以“流量”簡稱之)。尹一伊認為粉絲在微博上產生“流量”的在線活動主要包括“點擊、觀看、評論和轉發”。[15]高寒凝的界定則是,“‘流量’……指某個網站地址在一段時間內的用戶訪問量。其具體指標包括‘獨立用戶數量’(unique visitors)、‘重復用戶數量’(repeat visitors)和‘頁面瀏覽量’(page views)等”[18]70-71。這些都是可以被平臺記錄的數據。然而這些數據對偶像藝人的意義卻是可疑的。尹一伊暗示“流量”與經紀公司對偶像的支持力度和重視程度之間的關聯主要是粉絲的“描繪”“相信”和“假設”;[15]高寒凝則指出,“公開發布的藝人網絡熱度排行榜”中的數據與“影視劇制作方和廣告商制定決策”之間的關聯,并沒有證據支持。[1]另一方面,粉絲也并非完全相信“流量”。這從訪談材料中也不難窺見一斑。即便粉絲會因為沒有為偶像“做數據”而感到愧疚,她們也仍然沒有完全確信自己這種“數據勞動”的價值,而是與對“流量”的“描繪”“相信”和“假設”保持了一個或者批判性或者犬儒性的距離。[15]
在這個背景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企業一方對“流量”的態度。中國新興咖啡連鎖品牌瑞幸的前市場總監、現首席增長官楊飛在總結其互聯網營銷經驗的暢銷書《流量池》中對“流量”的態度就是不無曖昧與含混的。一方面,他開卷即斷言“流量即市場”[19]4,并提出“要獲取流量,通過流量的存續運營,再獲得更多的流量”[19]18;另一方面,又將“流量陷阱”——主要是數字廣告商的“流量欺詐”問題——列為當前“流量營銷”的三大疑難問題之一[19]12-14,并認為需要全程數據監控來防止作弊[19]223-257。在“流量欺詐”的類型學中,楊飛將廣告流量數據劃分為展現量、點擊量、注冊/留資量、潛客量、訂單量和成交量總計6個層級,認為作弊的難度依次從低到高。[19]227-228按照這個劃分,偶像粉絲視域中的“流量”類型恰恰屬于“流量作弊的重災區”[19]228。這樣來概括企業營銷部門對“流量”的態度是恰當的:他們一方面癡迷于“流量”的光暈,寄希望于“流量”能像資本一樣自我增殖;另一方面又不信任“流量”,認為“獲客成本”才是對營銷來說實際有效的實證概念。
從粉絲和企業營銷部門對待“流量”的相似態度,不難看出,“流量”更應理解為一個虛擬性的、想象性的概念。故而,對于偶像工業來說,并沒有哪些數據能夠確定地“作為‘受眾商品’的體現形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為廣告中間商的偶像工業就可以消除“流量”這個“凌虛蹈空”的概念,回歸一種“腳踏實地”的營銷。我們應當在這里辨認出“流量”的悖論性質:它確實是虛擬性的、想象性的概念,但同時,對于當下已然深刻地內在于數碼資本主義的偶像工業來說,它又是其“構成性的過度”(constitutive excess)[20]54。一旦失去了這個想象性的過度,粉絲經由偶像工業中介的消費就將失去快感的光暈。這種快感的光暈才是偶像工業掌握了“受眾商品”的真正證據,因為它與粉絲“購買意愿”之間的統計關聯更加明確。換一個角度說,這里的要點在于偶像工業與社交媒體的差異:對于后者,對用戶活動的捕捉和分析所形成的數據,就是實在的“受眾商品”的體現形式;而對于前者,這一部分數據的意義被粉絲帶有“流量欺詐”嫌疑的“主動式數據勞動”[21]稀釋,變得不確定了,導致最終只能以一個虛擬性的概念來不可靠地表征“受眾商品”的性質。不過,這不應理解為偶像工業的失敗,而恰恰是其成功之處。在對詹金斯“情動經濟學”的概念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中,馬克·安德烈耶維奇(Mark Andrejevic)非常敏銳地指出,在互聯網時代,關于用戶情感/情動狀態的“真相”(truth),遠不如可以實際對其施加影響的“關聯性要素”(correlations)重要;而“數據”的意義,也從曾經的“描述性力量”(descriptive power)轉向了“生成性潛能”(generative capacity)。[22]偶像工業中的“流量數據”正應作如是解:它主要不再描述“受眾商品”,而是以其“過度”不斷地生成、再生成“受眾商品”。
三、虛擬化親密關系中的三角關系
在上一節中,我們借助對“剝削”和“數據”這兩個概念的澄清,實際上已經基本廓清了偶像工業的經濟學關系。對于角色養成類手機游戲的分析要復雜一些,但盡管有頗為不同的機制,最后的結論仍是基本一致的,在此略去不表。⑨我們還需要繼續去完成的,是前述經濟學分析與文化維度的連接。我希望主要借助精神分析的理論來完成這個任務,因為前述“流量數據”作為“構成性過度”而發揮“生成性潛能”的機制本身,就已經很有精神分析的“韻味”。實際上,以精神分析來描述粉絲文化內在的“力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業已是相對成熟的理論路徑。⑩不僅如此,“經濟學力比多經濟的同構”也是一個拉康派的經典命題。
對這個命題的原始論述,拉康指出,之于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與之于主體的剩余快感具有相同的結構,都可以用“小客體a”(object a)來表示。拉康派的后繼者一直都嘗試在更加現實、具體的實例中建立經濟學與力比多經濟的關聯。其中最有趣的嘗試來自斯洛文尼亞精神分析學派的后起之秀薩莫·托姆希奇。他間接地回應了意大利自治主義者提出的“非物質勞動”的概念,他為對“非物質勞動”的剝削導致的工作與閑暇間界限的模糊這個論題,嘗試提出了一個精神分析的詮釋。[23]226-229
托姆希奇在此關注的論題非常切合偶像工業將虛擬化親密關系商業化的方式。他認為,受虐狂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的主體性形態,因為受虐狂“將自己奉獻于制度的凝視之下,不知羞恥地展示著享樂(jouissance),卻不知道,制度已經在他們占據的位置上建立了享樂與勞動的連續性”[23]227-228。從上一節“流量”對于偶像工業中“受眾商品”的生成作用來看,這個形式化的分析似乎抓住了一些要害。然而,這個公式除了暗示“流量”既作為快感的標記又誘導粉絲的勞動之外,卻也并沒有提供進一步展開論述的工具。不僅如此,托姆希奇的理論還面臨一定的自洽性問題。他對受虐狂與資本主義之關系的討論是對拉康話語理論的延伸,然而,“建立享樂與勞動的連續性”這一過程卻無法用拉康的話語理論來表示。
我在這里無意去解決托姆希奇理論所面臨的內在困難。在只考慮無產階級與資本的二元關系的情況下,這個理論也許就是無法成立的。幸運的是,在我們所關心的虛擬化親密關系的問題中,基本的關系是三元而非二元的——對偶像工業來說,就是粉絲、偶像、資本。我們接下來就將看到,“偶像”這個中間項,不僅對于粉絲文化研究來說本就是連接文化與經濟學維度的節點,而且也剛好就能夠讓“享樂與勞動的連續性”在拉康話語理論的框架內得到非常精密的表述。
綜合考慮粉絲、偶像、資本三元關系的分析框架已經由高寒凝提出[18]155-179,她將此關系稱為“賽博代糖的三角貿易”[18]214-218。為了適應當前的目標,我們忽略了其中關于知識產權的部分,然后用拉康話語理論中的分析師話語和主人話語連接粉絲、偶像、資本,就可以得到如圖1示。

圖1 粉絲、偶像、資本的三元關系
在圖1中,三個主要行動者都具有雙重身份,一個是顯白的身份,括號里的則是隱含的身份。我們可以將前一節中分析的結果概括為兩個過程:其一是粉絲將自己生產為“受眾商品”的過程,其二是偶像獲得“流量”或者“資源”的過程。這兩個過程都可以用拉康的主人話語來表示,也即:
主人話語是拉康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形式化表述,它表示,主人(S1)質詢奴隸(S2),使其勞動,并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快感(a)。[24]粉絲主要在意的,是三角形右邊所代表的這個主人話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偶像占據主人的位置,或者因為粉絲的數據勞動而向平臺索要其應得的“流量”,或者因為其已經獲得的“流量”向經紀公司索要其應得的“資源”。隱含的、與此過程做交換的另一個主人話語過程,則是粉絲將自己生產為“受眾商品”的過程,此過程中是資本占據了主人的位置。這兩個過程的交換對于粉絲來說合乎“公平交換”的邏輯,因為粉絲借助其對偶像的認同,可以代理性地占據主人的位置,并享有其剩余快感。換言之,在粉絲看來,這是以剩余價值交換剩余快感的過程。當然,按前一節的辨析,這里并非粉絲為資本付出的勞動直接產生剩余價值,而是這個勞動幫助非生產性的資本轉移了別處生產的剩余價值。
這里需要補充的是,我們在圖1中還為主人話語的產物——也就是代表剩余價值或剩余快感的小客體a,額外標注了另一個符號。這樣標注的意義是,和三個主要行動者都具有雙重身份類似,話語過程的產物也具有雙重性質。這里產物的第二重性質來自拉康關于三界之間轉化關系的圖示。[25]按齊澤克對此的解釋,這個圖示的含義是,象征、想象、實在三界之間的轉化關系會形成某種客體。具體來說包含三點。
第一,象征界的實在化會形成小客體a。
第二,實在界的想象化會形成Φ,它是無情動(impassive)的對象,是對實在界想象性的對象化,是原樂的具身化形象。
第三,想象界的象征化會形成S(A/),它直接具象了大他者內在的匱乏,并因此是對象征秩序有根本構成作用的不可能性。[20]209-210
在描述偶像工業三角關系的圖示中,我們讓粉絲、偶像、資本分別占據象征界、想象界、實在界的位置,進而,我們將三界之間的轉化解釋為遵循某種話語過程的一方向另一方的索取。這樣,比照著拉康的圖示,可見如下情況。
首先,資本按照主人話語對粉絲的索取得到的產物即剩余價值,它同時也是象征界的實在化,因此其客體形態“受眾商品”可以用a來表示。我們最后再解釋為什么“受眾商品”應當具有小客體a的性質。
其次,偶像按照主人話語對資本的索取得到的產物即剩余快感,它同時也是實在界的想象化,因此其客體形態“流量”可以用Φ來表示。“流量”實際上就是將“無限增長”的幻想客體化后的對象。因此,——“無情動”“想象性”“原樂的具身化形象”非常精確地描述了“流量”的性質。
最后,是我們尚未觸及的粉絲向偶像索取的過程。這個過程遵循分析師話語的規律,也即:
在這里,a表示粉絲執行的是“純粹欲望”的職能,她們質詢的對象是偶像的隱含身份——“分裂的主體”S/,其產物則是主人能指S1。這個分析師話語概括的是粉絲閱讀、分析偶像的形象的過程。按照高寒凝的論述,“偶像藝人所能產出的最重要的作品,事實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以他本人為原型創造出來的、某種可被放置于親密關系想象之中的形象”[1]。這種“可被放置于親密關系想象之中的形象”被進一步命名為“親密關系要素”。[21]在這里,偶像本身并非圓熟完滿的統一體,而恰恰是某種空洞的、可以容納相互矛盾的“親密關系要素”的容器。也正因如此,這里的偶像就適合用“分裂的主體”S/來表示。在粉絲的閱讀與分析中,并非所有的“親密關系要素”都具有同等的意義,其中最關鍵的是能夠使一組虛擬化親密關系成立的那種要素。在精神分析中,主人能指S1的意義恰恰如此:它本身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任意的能指,其功能卻是為整個意指網絡賦予意義。最終,粉絲像分析師一樣閱讀、分析作為S/的偶像,從這個過程中提取能夠執行S1功能的“親密關系要素”,和其他素材一起捏合出偶像的“虛擬形象”。這個閱讀、分析、捏合的過程是最能體現粉絲能動性的集體行動,高寒凝將其稱為“參與式勞動”。[21]
另一方面,粉絲向偶像的索取,作為想象界的象征化,其產物的客體化形態應當表示為S(A/)。S(A/)的意義必須在社會歷史背景中才能夠說明,完整的論述需要相當長的篇幅,因此請允許我在此僅稍作例證。在對后革命背景下中國女性向網絡小說的宏觀閱讀中,戴錦華指出,“真愛的到來固然是類似敘述中必須的、充滿政治無意識的裝置,或稱敘事必須的‘機械降神’,但這也間或成為某種文本邏輯的裂隙,成為其中近乎絕對的權力游戲的對立項”[26]。在這個觀察中,“真愛”對于敘事文體內部來說執行著主人能指S1的功能;但當我們將小說視為社會文本,將其置于社會集體的象征秩序當中,“真愛”就成了象征秩序的剩余,成為了大他者——“近乎絕對的權力游戲”的主角——的內在匱乏,并因此執行著S(A/)的功能,成為對象征秩序起根本構成性作用的不可能性。與此完全類似,虛擬化親密關系在偶像工業中也具有雙重的意義:它在偶像工業的“文類”內部以要素的形式執行主人能指S1的功能,為粉絲生產的文本賦予意義;在宏觀上則以S(A/)的形式,對粉絲集體想象中的象征秩序起根本構成性作用。被粉絲集體性的“參與式勞動”生產出來的虛擬化親密關系最終來說是S1與S(A/)的統一體。
四、幻想的經濟學
上一節我們運用拉康的理論,給出了偶像工業中虛擬化親密關系如何運作的完整關系,這個關系同時納入了相關的文化與經濟學的維度。不過,在上一節中,我們給出圖1仍然只是一組靜態關系:我們尚未指出其中的動力學因素。讓我們在這一節補充這部分論述。
首先要說明的是,根據拉康的話語理論,話語表達式的四個符號中,左下的項是這種話語中“隱含的真理”,亦可認為是其“驅動力”。因此,圖1本質上是從右下角開始的、順時針連接三個話語過程的驅動鏈條。這里尤其重要的驅動關系,是粉絲的分析師話語對偶像的主人話語的驅動:正是粉絲集體性的“參與式勞動”為作為S/的偶像賦予了魅力和光暈,才令其能夠占據主人S1的位置。換言之,偶像的魅力與光暈既是其能夠將“流量”兌換為“資源”的根本原因,也是粉絲最終愿意將自己生產為“受眾商品”的原因。這些魅力與光暈實際上主要是粉絲集體勞動的產品,因此當偶像工業在三角關系的完整驅動鏈條中以此牟利,這里就確實發生了一種無形的剝奪(expropriation)。
其次,在第二節中,我們指出,斯邁思-福克斯師徒將用戶將自己生產為“受眾商品”的過程與產業資本主義的剝削過程類比,這并不符合《資本論》的基本原理。盡管如此,生產“受眾商品”的勞動還是顯然像雇傭勞動那樣具有某種脅迫性。解釋這種脅迫性,才能夠解釋資本的主人話語如何能夠驅動粉絲的分析師話語。福克斯根據對社交媒體的研究提出了“社交脅迫論”[10]336,但其論據過于單薄且很難適用于偶像工業的粉絲。相較之下,高寒凝的判斷要合理得多。她指出,女性幾乎永遠是“‘情感勞動’的提供方而非獲取方”,因此日常地面臨“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的困境,而偶像工業本質上即利用此困境謀取暴利。[21]高寒凝并沒有對此進一步論述,但綜合前三節的內容,我們可以以“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為起點,牽扯出當代資本主義中更為根本的危機脈絡。
“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首先應當視為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所論述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照料危機”的一個實例。弗雷澤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越來越傾向于擠壓社會再生產,不僅威脅著家庭層面的再生產,而且還在政治制度和環境等方面制造著再生產危機。[27]然而,問題還不止于此。按上一節對偶像工業中三角關系的精神分析,粉絲對偶像的索取,最終來說是作為S1與S(A/)統一體的虛擬化親密關系。其中S(A/)的性質意味著,粉絲更為根本需求是象征秩序的構建與再生產,“制度性情感支持”應理解為其中的一個側面。不幸的是,盡管弗雷澤及與她同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所描繪的當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危機”主要聚焦于外在可感的方面,但這場“再生產危機”實際上早已開始威脅屬于“內面”的象征秩序。由于象征秩序是主體性得以構成的環境,這也意味著,主體性本身的再生產也正變得愈加困難。
這是一個彌散但籠罩性的現象,雖然尚無統攝性的研究,但可以從諸多論述中看出端倪。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杰姆遜認為后現代同時喪失了現實感與歷史感,喪失了將能指有意義地連接起來的能力,因而只能以精神分裂的方式體驗一種“永恒的現在”[28];而所謂“宏大敘事的衰落”[29]帶來的“后意識形態時代”,最終的趨勢是“以自我為代價的、超我與本我的倒錯性和解”[30]。媒介技術與權力技術的演進也在為這個趨勢火上澆油:齊澤克認為互聯網本身即有破壞象征秩序的傾向;[31]德勒茲則認為,在“控制社會”中,“個體”將被“分體”(dividual)所取代。[32]某種程度上,資本主義似乎正在拋棄象征秩序。
因此,偶像工業的女性粉絲所面臨的匱乏,不僅是缺少穩固的情感支持,而更是象征秩序本身的愈加殘破與個人主體化的愈加困難。雪上加霜的是,在普遍的“再生產危機”中,生產過程本身對勞動者造成精神傷害,也是極為常見的現象。故而,粉絲所面臨的根本匱乏——“象征秩序的殘破”與“主體性的貧困”——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總體運轉中,不僅得不到補償,還極有可能被不斷加深。與根本的匱乏直接相關的是持久的欲望,這意味著,在前一節圖1的左下角,以a表示的作為“純粹欲望”的粉絲,實際上就具有小客體a的結構——是匱乏與溢出(excess)短路般的結合。這種結構正是消費社會所需要的:為了抵消生產過剩,最為理想的消費者就應當是永不饜足的。因此,被出售給廣告商的“受眾商品”本質上就是位于三角關系左下角的那個作為“純粹欲望”的粉絲。如果說資本家對這樣的消費者還有什么不滿,那就是,這種永不饜足還缺少些方向感。以偶像與“流量”為首要工具的偶像工業,也就是一種調控和引導這個匱乏-溢出的中介裝置。至此我們發現了完美的閉環。如果說主人話語本來就可以描述資本主義剝削性的生產過程,那么我們也可以令三角關系圖2中位于下方的資本驅動粉絲的主人話語來表示兩個過程的疊合:一個是粉絲在其“正式”的雇傭勞動中受到資本驅使的過程,另一個則是在“非正式”的勞動中將自己生產為“受眾商品”的過程。將雇傭勞動加入三角關系之后,不難看出,我們之前所說的從右下開始的順時針旋轉的過程,實際上可視為資本主義基本生產過程在想象性/幻想性活動的維度中衍生出的一個“副循環”: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造成的“再生產危機”衍生出了這個“副循環”;另一方面,這個“副循環”最終又為剩余價值的實現貢獻了穩定性——也就是一群優質可控的消費者。我將這樣的“副循環”命名為“幻想的經濟學”(見圖2)。

圖2 偶像工業的文化生產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副循環”
由經濟學的內在危機衍生出的“幻想的經濟學”,恰恰能夠在相當的程度上延宕原先的經濟學危機的爆發,甚至,還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提供更加有效率的運轉模式,這是資本主義應對危機、自我揚棄的獨特方式。齊澤克和托姆希奇一直在嘗試用精神分析的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這種性質,但只能停留在形式化的理論中。我認為作為“幻想的經濟學”的虛擬化親密關系,恰恰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如果可以借用中國古典意義上的“天”來指代象征秩序,那么,偶像工業中粉絲的根本努力也就是“補天”。與神話不同的是,陷于“幻想的經濟學”中的她們,或許將無法完成女媧的使命,因為資本主義偉大的適應力已經發現了這個秘密:對人的系統的損害與侮辱,竟可以成為一樁有利可圖的生意。
【注釋】
① 尤其對德勒茲的哲學來說。
② 參見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③ 參見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Theory, no.3(1977):1-27;Dallas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MediaandCulturalStudies:Keyworks(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pp.230-256。
④ 參見John Fiske, Henry Jenkics,Theculturaleconomyoffandom.Theadoringaudience(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p.30-49;Henry Jenkins,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詹金斯:《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 鄭熙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⑤ 例如楊玲:《粉絲、情感經濟與新媒介》,《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7期;楊玲:《粉絲經濟的三重面相》,《中國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周懿瑾,白玫佳黛:《明星代言的價值共創新機制——基于多個粉絲社群的網絡民族志研究》,《外國經濟與管理》2021年第1期。
⑥ 最有力地說明這一點的現象是,粉絲會因為沒有為偶像“做數據”或“刷流量”而感到愧疚。
⑦ 參見:Edward Comor. “Value,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digital prosumption: a plea for precision,” inTheaudiencecommodityinadigitalage:revisitingacriticaltheoryofcommercialmedia(Bern: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4), pp.245-265;John Roberts, Colin Cremin. “Prosumer cul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fetishism.”JournalofConsumerCulture, no.2(2017)。
⑧ 這里不要混淆一般意義上的“生產”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生產性勞動”:前者只是常識意義上產生使用價值的過程,許多再生產勞動和自然過程都可以理解為是某種程度的“生產”;而后者嚴格地關聯于剩余價值的生產。關于馬克思理論中“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劃分和辨析,參見Ian Gough,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NewLeftReview, no.1(1972):47-72;Dimitris Paitaridis, Lefteris Tsoulfidis, “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S economy,”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 no.2(2012):213-233。
⑨ 對角色養成類手機游戲基本經濟學關系的分析,參見傅善超:《快感的治理術:關于電子游戲的文化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21,第105-122頁。
⑩ 參見Matthew Hills,Fancultures(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60-81;Cornel Sandvoss. Fans,themirrorofconsumption(Cambridge, UK: Polit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