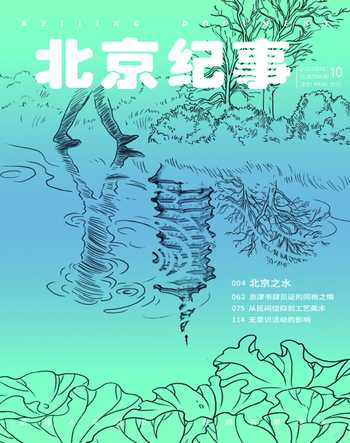無意識活動的影響
周芳凝


《唐人街》是一部由著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指導的一部在電影史上堪稱教科書級影片的驚悚懸疑片。作為一部已經過了半個世紀的電影,它為什么經久不衰,是否它所呈現的現實冷峻的社會現象、曲折幽暗的人情故事和真實復雜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觸動了每個觀眾的情感體驗,引起共鳴,可以由此有空間去想象和思考這些與人和社會息息相關的關切呢?這部電影里面幾乎跟華人沒有什么關系,只是杰克之前工作的警局是在唐人街,為何影片要以唐人街命名呢,這和華人、中華文化有什么關系?還是個巧合?并且全局結局揭開的尾聲高潮也是在唐人街,杰克在結尾的時候,絕望而迷茫地和他前同事講,盡可能什么也不做,這句他曾經在唐人街警局效力時候被教育到不屑地憤然離開的話,似乎經過了這一份血雨腥風,痛徹心扉,他有了新的領悟。每個曾經心懷理想熱血方剛的人,最終以不同的方式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去“融入”了自己,這背后有什么無意識的動力呢?
一個被平緩地娓娓道來的驚悚故事
雖然從影片性質特征上來說,《唐人街》是一部驚悚懸疑片,但是它呈現的這種驚悚的方式是十分“走心”,而不僅僅是“走視聽”的,以至于有人在電影前幾十分鐘的時段,感到情節過于拖沓遲緩看不下去。整片看下來,除了結尾的寥寥幾聲,也沒有聽到很多槍聲,沒看見接踵而至的血腥恐怖畫面。但是如果看到最后,想必沒有人能忘記在一片混亂中,惡貫滿盈的老魔鬼全身而退逍遙法外;伊芙琳在驅車逃跑過程中被槍擊中頭落在汽車鳴笛上引發的不能停止的喇叭長嘯,和她左眼被擊穿的爆頭定格;伴隨喇叭長鳴響起來的小姑娘發出無比痛苦和歇斯底里的尖叫,還有她最后被老魔鬼一把擄走的身影;一直以來都神采奕奕勇往直前的杰克最后帶著失意而痛苦的眼神對前同事盧說,做得越少越好;還有杰克的前同事,辦理本次案件的盧,經歷了這一番跌宕欺負,還是那樣表情平靜地嫻熟應對,好像這背后的一切他早就知道,并且對于這種知道他早已經習慣甚至麻木,學會熟練應對了。好似這里面每個人定格在結尾的模樣,都是現實社會中我們可以找到的一類人的畫像。
故事發生在1937年的洛杉磯唐人街,警員杰克因不滿警局內部的黑暗,辭職做了私家偵探。有一天,一個自稱是莫拉雷太太的女子出重金請杰克調查自己丈夫外遇的事情。杰克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霍利斯·莫拉雷原來是本地水利總工程師,正在為興建水壩與否的問題和當地人發生爭執。隨后杰克的助手似乎查到了莫拉雷先生外遇的證據,寄給了請他調查的“莫拉雷太太”,隨后事情便見報,成了水利局長的桃色丑聞。此后,真的莫拉雷太太伊芙琳找上門來表示自己從未雇傭杰克調查過,要起訴杰克。而后水利局長離奇死亡,杰克感到這背后一定有詭詐,于是決心查下去……幾經險阻差點被斃命封口,原來水利局長并非畏丑聞自殺,也非他的夫人伊芙琳因憤怒丈夫外遇情殺,水利局長也根本沒有外遇,所謂拍到的外遇女孩是水利局長這些年代為照顧的,他的夫人伊芙琳的女兒兼妹妹。原來這一切的元兇正式伊芙琳的父親克羅斯先生,克羅斯先生非常富有,他是前水利局局長,因為和現水利局局長莫拉雷先生關于水應該是屬于人民的還是用來賺錢利益最大化,兩人分道揚鑣。而這次克羅斯先生要把莫拉雷先生殺人滅口,也是因為他發現自己隱瞞公眾賺黑心錢的手腳會影響自己掙到這筆大錢,于是便有了這整個故事。而最終他以女兒伊芙琳的性命做了這件息事寧人的“解決方案”。一心想維護正義的杰克也在最后知道真相看到結局的時候,痛苦無力地說,做得越少越好……
小人物的理想與大時代的秩序
如果把影片中的私家偵探杰克當作是一個玩世不恭又心懷正義的英雄形象的話,那么最后暗黑的結尾,如同這個形象代表的正義和力量,被社會中的惡如同黑洞般被吞噬得無影無蹤的同時,還反噬得讓人后背發涼。不僅會讓我們捫心自問,當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面對不如意,想要堅持自己理想或者是與不滿意的現實進行對抗就那么困難嗎?面對復雜的社會網絡和其中那些權勢滔天到可以掌控一切的頂頭大佬,注定只能忍氣吞聲或者是讓自己成為他的一部分嗎?這一定程度上是私家偵探杰克在電影故事里面臨的一種心靈困境。
有的時候,即便是通過社會政治生活這種團體環境與關系體現出的心靈現象,一定程度上也與一個人個人的心靈體驗和從個體的體驗出發向大環境的投射,與繼而的交往互動形成的效果息息相關。
完美母親與全能惡人的心靈意象
克羅斯先生在整個故事里扮演了讓人感覺可以遮天蔽日的大反派的角色。他不但壞,而且壞得還很涉獵廣泛——從人倫到社會經濟,還壞得很深入——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有違人倫、可以置人命于不顧。這樣一個形象可謂一個“全能的壞人”了。這種全能的壞人形象給人心底帶來的這種絕望無助的感覺,讓人可能會聯想到另外一種在人類社會中被廣泛需要的全能形象——全能好的形象。
不難發現,人類社會似乎總是需要一種全能的完美形象作為一種信仰的支持。而對于這種全能好的心靈意象的需要和由此帶來的構建,從我們人之初和母親之間的互動就開始了,一個人在那個階段從母親那里能體驗到的全能的好,被接納、照顧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人在日后相信有像“母親”一樣好,雖然不一定全能,但是可以足夠好的愛的對象的存在。另外一面,當我們心中對于這種可以有全能般的好的意象的信念不足的時候,那種無邊的不安、失落、惶恐,便會很容易讓人導向這種想象的另外一個維度——我們終究可能很難逃脫一個無所不能的惡的對象的魔爪。
而在現實中,絕對的“完美母親”和“全能惡人”都是不存在的,只是當我們的內心有一種對于理想化的依戀形象的空缺時,那種無法消除的不安便會很容易讓我們去幻想。既然沒法被一個完美的母親愛與照顧著,那么會不會有一個全能的惡人可能一直在迫害操控著我們的生活,讓人無比絕望而無力。
孤注一擲的魚死網破與富有耐心的“持久戰”
杰克的行事方式是極致的,他那種眼里絕對不揉沙子的狀態往往把事情推向了一個極致。而有時候現實往往不是除掉一個惡人那么簡單,且在這個故事里惡人沒有被真的除掉,當真這個惡人被除掉了,“唐人街”就不是“唐人街”了嗎?這不禁讓人想到在人類心理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心態,英國的臨床心理學家克萊茵把它描繪成“偏執分裂位”的狀態,或從當代認知行為治療的視角即一種“非黑即白”的狀態。


克萊茵提出來的偏執分裂位的狀態描繪一種嬰兒在最早期,心理空間還處在非常敏感脆弱、混沌不安的狀態下,這個時候在他的體驗里,如果能夠被媽媽即時照料安撫,那么整個世界便都是好的,如果不能那么他體驗到的整個世界便都是崩塌瓦解的。但是后面隨著小嬰兒被更多地好好照料,他的心智空間開始在完美和毀滅之間發展出來一個新的空間,這個空間是一個在他受挫的時候可以容忍一時的失落和不確定的空間。在這個空間的狀態克萊茵稱之為“抑郁心位”。一個發展出抑郁心位的嬰兒開始能接受媽媽并不是所有時候都能剛剛好滿足自己的需求,生活不得不承受一些不如意和沮喪,但是這并不代表媽媽是魔鬼,也不代表生活就被摧毀了。即便是不完美,日子還是可以差不多好的,我們是可以在兼容生活的不完美和不確定中去不斷探索一種更舒適的生活狀態的。這不僅僅是一個嬰兒可以發展出的體驗和構建生活的狀態,更是一個成人可以去面對復雜而又充滿不如意,喪失,哀傷的社會現實心智狀態。
遵循“越少越好”的原則是一種華人的智慧?
不知道這是不是編劇對于華人文化的一個心中印象標簽,但是遵循越少越好的原則似乎是唐人街的行事原則。即便是一開始對此不屑一顧憤然離開的杰克,最終也不得不在絕望失落中對前同事盧重復這條原則。難道這意味著中華文化里有一種視而不見的、無所作為的“中庸”嗎?想必不應該是這樣的。這背后蘊含著一個東方思維和西方思維里面從古代思想起開始就分異的差別。西方思想里是一種更喜歡通過澄清概念的方式從“有”,從“實體”,以“由下而上”的方式來找到更真的東西的。中國文化是一種由現象的相往下向其背后看不見的意象探索的思維,所以對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中國那會便有探索老莊“道”,“無為而治”認為“大道無形大音希聲”的境界。如果放在電影故事里的情景來理解中國式文化下的“越少越好”的話,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是,做什么不一定會起到想象中的作用,而“不做什么”本身其實也是做了什么,做得少本身也是采取行動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并不是具體的做什么動作,而是通過不做什么動作,讓自己作為整個局面里面沒有被推向最直接地促進事情發展變化的元素在跟隨事情發展的進程。如果把“做”這件事情放到動機、意念,而不指示行動這個層面的話,那么東方的“無為”很多時候也只是把行動意念沒有直接付諸行動,而是放在全局更審慎地考量觀察的過程。
講故事的過程即一種對于我們在生活經驗里無法實現,實踐的內在欲求的富有美感的“升華”。它通過一種極致的理想化的形式,把生活體驗中各種狀態升華成一些可以不從結果計較,而是作為一種我們每個人內在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的楔子,擴充我們內在心靈的體驗和反思空間的起點。因而,遺憾和喪失縱然終究是遺憾和喪失,但是它們可以通過某些形式被保留,可以是永恒的、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