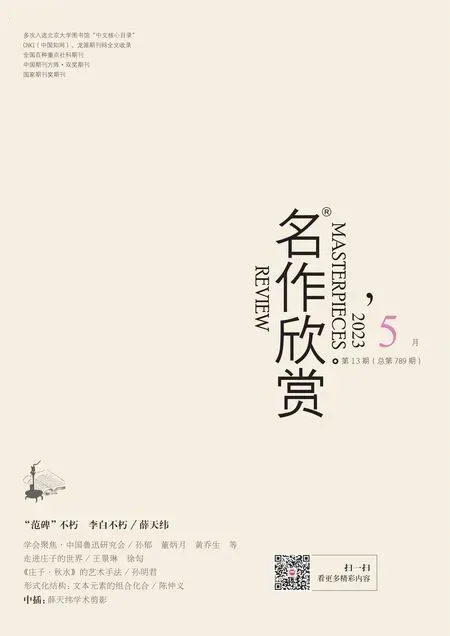形式化結構:文本元素的組合化合(上)
福建 陳仲義
化學反應與文本構成
化學反應是指在一定條件——加熱、電解、紫外線或催化劑等參與下,元素們發生不同程度的蛻變,包括經由放熱、吸熱、發光、變色、沉淀、氣化過程后而產生新的生成物。化學反應基本類型有四種:
化合反應:A+B =C(多變一)
分解反應:C =A+B(一變多)
置換反應:AB+CA =A+BC(一換一)
復分解反應:AB+CD =AD+CB(雙換雙)
遠古時代的魔法,大多都卷入化學反應,當今大千世界,同樣離不開化學變化。從緩慢滴落的石灰巖到悠悠上升的碳酸氣泡,從日常的氧化鐵銹到節日的焰火燃爆,不論是靜悄悄的水解還是激烈沖突的酸堿中和,概莫能外。“化學反應,就是這個世界的動詞。”(西奧多·格雷)經冬的銀杏,紛紛落下的葉子不怎么泛紅,可稍受秋風撫摸,同類的楓樹、槭樹、櫸樹們便漫山紅遍,秘密全在于花青素的大量生成;切開的蘋果,鮮潤的容顏立馬憔悴,原因在于多酚與酶的氧化聚合,但只要浸入檸檬水,顏面則新鮮如初,蓋因抑制被解放的結果。①
無時不在的化學反應,是萬物變化的依據。《瘋狂的化學》為我們展開魔幻節目:氯酸鉀與鎂粉有意合謀,便撒出了“天女散花”;重鉻酸銨在乙醇的點撥下,結晶出了火山的熊熊巖漿,并留下灰溜溜的“火山口”;追求無限自由的鈉在水上瞬間定格“珍珠”,卻沒有留下任何虛偽的破綻;散漫的“溴巫師”發布漫天的大霧布告,誰能讀懂它潛藏的敵意或誠意;碘化鉛在不動聲色的折射與反折射間,佯裝成一場“黃金雨”;而葡萄糖酸鎂“焚尸”之后,有可能轉世成“白馬王子”……②魔術師的演出匪夷所思,像不像詩歌文本一次次生成,各類前文本的因子,沸騰于心靈的坩堝,無法預料。實驗室的反應多數是可預設的定式可控,而詩文本的發生屬于生命場域的能量聚散,飄忽不定,它們擁有自己獨特的神經系統——溫度、心跳、呼吸、發聲、韻律、節奏,是生命氣場活的有機體。③
文本的生成,在四種化學反應范式中,更偏向于化合反應。或者直觀地說,更接近于雞尾酒的調配:伏特加+石榴糖漿+七喜,能夠改朝換代,變現為紅燦燦的“日出特基拉”;黑色的“天鵝湖”,來點藍香橙力嬌,能蕩漾成“藍色夏威夷”;威士忌、苦精、奶油、柚汁,該怎樣在新編方程下優優組合,跳出常態化雷池;白蘭地、檸檬片、橙汁和刨冰,又該在何種層次突破界面,闖出新意;琥珀的阿瑪托、褐色的瑪麗泰,強強聯袂,不一定能營造出理想的“椰風蕉雨”,很可能釀出一塌糊涂的苦果。拌攪、搖晃、兌和、漂浮,在不斷試錯中,甜酸苦辣,毫厘千里,哪怕微小的差異都可能帶來霄壤之別、無限情趣。
文本的化合反應,當然是在人腦里秘密進行的,遺憾的是,哪怕再先進的腦影像也未能窺伺其萬一,充其量人們只能從外顯的也是最終的文本,找到其“蛛絲馬跡”。無奈之下,我們最多也只能依賴單純的文本元素做點取證,借此來理解詩本結構,進而理解詩歌。我們先分揀出六種常見的元素材料,略加描述。進而推理:它們或者三五成群親密結對,或者深居簡出藏而不露,或者輕佻漂浮四處游蕩,或者有板有眼沉靜穩重。有無意識的隨機流動,有實打實的呈現,有虛無縹緲的氣化,也有刻意的喬裝扮演。高溫下蒸發,電解中異變,燃燒的灰燼,光照的萌生。各等元素、分子,各種成分、因子,精致、粗鄙也好,脫序、緊致也罷,經由主體性催化和化學鍵“張羅”,重新構成排列、組合,呈現各種化合樣態。
那么,備好我們手中的酒精燈、曲頸瓶和韋氏分餾柱,走進化合的世界。
元素組合化合舉隅
1.單質元素。單質是同種元素組成的純凈物,因“雷同”而顯得單一純粹。單質譜系中圍繞其中不管是做外圍還是圈內的電子運動,自然都帶有“純一”(專一)的特質。部分人誤以為單質詩語過于簡單明了,體現不出心靈世界的豐富性。其實單純不一定就代表簡陋,簡單也能蘊藏豐厚,請看蕭蕭的“白”:
金紫珊瑚,華貴品質 白
充滿生命活力,粉紅珊瑚 白
或五顏或六色或七彩 白
腔腸 白
動物 白
白白 白
白白 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
白白白白,白白 白
海底熱帶雨林無色無聲 白
三萬五千種生物不能孕育幼苗 白
春天靜寂 白
枯骨 白
森森 白
白白 白
白白 白
白白白白 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
(《白化的海底花圈——哀珊瑚》)
全詩146 個字,“白”字81 個,占60%的驚人股份。每一行都留下空格,且以白字收尾,制造獨到的“空白美學”④。俾使單質的白元素,雖表面單薄,但由于高度集結、大面積堆砌,森森白骨,朵朵白花,在逼人失明的耀眼白光中,詩人唱出哀傷的挽歌。橫的白色儀仗隊與豎的白色挽聯,共組不停頓的死亡抽噎。視覺沖擊力下的大白與多白,遠遠溢出單質性能。
洛夫在參觀菲律賓美軍公墓時,寫下另一種“白”:
白的 墓旁散落著花瓣
白的 玫瑰枯萎之后才想起被捧著的日子
白的 馬尼拉海灣的落日
白的 依然維持彌留時的
白的 體溫。一萬七千個異國亡魂
白的 依然維持出擊時的隊形
白的 數過來,數過去
白的 依然只是,一排排
白的 一排排石灰質的臉
…………
《白色墓園》(上半闕)
第一節實景,第二節體悟,上下兩節,用40 多顆白珠,串成往復不已的鏈條,制造無數陣亡將士的靈魂和眼睛,直勾勾盯住你。在單顏色的構圖中,一以十勝。
2016 年,大連的李皓也描寫到白,卻是從自然景物到白馬族的大回環,再到個我對于“清白”的意義認定:
白馬藏族身上的白/王朗半山腰浮云的白/奪博河里浪花的白/岷山山脈雪寶頂的白/還有我腦子里的一片空白/它們都是相互關聯的:/流云是吐故納新的白馬人呼出的/雪線是浮云撕成的布條或者碎片/而白馬人從來不這樣思考/他們干干凈凈,沒有/任何顧忌和負擔,寵辱不驚/自生自滅/只要那只救命的白公雞還在/他們就頂著白色的尾翎/清清白白地在山里走/在水里走,在寨子里走/不訴諸任何文字,不告訴任何人/他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而作一個偶然的侵入者/我只能向一杯蜂蜜酒/或者一棵鹿耳韭發誓/我從沒來過,真的
(《與白有關的一些零碎想想》)
擔任評委的我們寫下如下評語:純然白凈的語感、純然淳樸的情感、純然自在的節奏與韻律,以及經由對“白馬人”生存、生活、生命形態只眼獨到的感知與表意,和由此生成的天籟般會心會意的語境,令人頓生戀戀鄉愁而感念深深。景物事體皆有意在,以純凈成其迂回,而入幽出朗,渾成不覺。可謂近年口語詩難得之作。它出示了語感寫作一種標的,恪守“正宗”而別開生面。它與梨花體比較而勝出,在于其單質,雖透明卻不稀薄,雖簡單卻豐盈。
有趣的是,三位詩人雖然共襄“白”的盛事,卻各自在詞性上玩出自己的爽:蕭蕭的白是將形容詞當動詞用;洛夫的白是作為名詞用;李浩的白是作為名詞用,在詞性的轉品上,不可小視單質的力量。臺灣另一個超現實大師碧果,則在《靜物》的“棋盤”上安排81 個白子和81 個黑子。數學上的1+1 通常是等于2,但是,化學與詩歌的譜系——氧+氫遠遠就不是水了。
2.戲劇元素。完整的戲劇性由七種元素構成:懸念、細節、情節、場景、對白、動作、沖突。大戲劇性包含小戲劇性,小戲劇性集結成大戲劇性,這種可聚可分的“連環套”使得戲劇性神通廣大,也使得戲劇性成了詩歌文本中最古老的元素之一,最簡單的戲劇性就是觸手可及的“因果鏈”。隨便舉一例,崔護的《題都南山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兩個場景構成一個因果鏈。第一個場景,去年此時,尋春邂逅,人面桃花,款款愛意。第二個場景,今日此地,風物依舊,桃花人面,不知所蹤。這個物是人非的“故事”,外表上是今昔“對比”,實則上是因果關系。潛在的因果關聯中披露出命運的機遇與捉弄。
有因無果、有果無因、因果求因、為因求果、前因后果、后因前果、摘因折果、守果護因、因因相襲、果果連環……但凡種種,都可以制造出諸多懸念、情節、沖突。現代詩因長度拉大,現代語法“關系明確”,比古詩更有利于豐富、優化戲劇性。翟永明是現代戲劇性的超級高手(《咖啡館之歌》《小酒館的現場主題》《鄉村茶館》《時間美人之歌》《三美人之歌》《編織和行為之歌》,比比皆是)。她在《道具和場景的述說》中,借助道具的“對應”,對人生進行獨到詮釋:良辰——青春易逝/美景——痛苦的形跡/賞心——面目全非的苦頭/樂事——美的死亡加速度,這一切,毋寧看成是她對“戲劇性”的獨到理解:
一盞燈要照亮尋常百姓的生死
一個人要交融現實和往昔
一個夢重疊真景與幻覺
在獨具慧眼的“戲劇性”觀照下,她運營起來駕輕就熟,如《魚玄機賦》。
寫情境(刑場):
魚玄機著白衣
綠翹穿紅衣
手起刀落 她們的魚鱗
褪下來 成為漫天白雪
色彩、想象、浪漫,把個陰森森的刑場改造成爛漫天堂。
寫懸念:
一條魚和另一條魚
她們之間的玄機
就這樣 永遠無人知道
通過名字的借代與拆解,順便道出“謎底”。寫心理沖突:
人生一股煙 升起便是落下
也罷 短命正如長壽
又何必寫怨詩
先是看破紅塵,接著掙扎,再做自我爭辯、自我解脫。
寫對白:
魚玄機:
銀鉤、兔毫、書冊
題詠、讀詩、酬答
如果我是一個男子
理所當然 風光歸我所有
綠翹:
那就讓我們得氣于煙花
爆竹、一聲裂帛 四下歡呼
你為我搜殘詩
我為你譜新曲
對白其實也隱含著獨白。且采用古箏譜曲,“鬼魂”演奏,增加了神秘感。
寫旁白:
沒有贏得風流薄幸名
卻吃了冤枉官司
美女身份遮住了她的才華蓋世
望著那些高高在上圣賢名師
她永不服氣
借助他者“畫外音”,為“墓志銘”做翻案。
如今詩的戲劇性已經非常普及了,且加入了許多非傳統功夫:如明暗隱顯邏輯線索、蒙太奇鏡頭、多聲部復調、時空切換、身份轉換、視角改變……皆為戲劇性“添糧運草”。2015 年全球華語大學生短詩賽,有一首《等》榮膺頭獎(羅俊鵬)。只有五行,竟把戲劇性濃縮在一個“等”字上:“三歲時/你說讓我等你五分鐘/二十三歲時/你卻還沒回來/爸,我現在不要馬路對面的冰糖葫蘆了。”如此不凡的戲劇詩想,來自時空跨度的張力,讓短短五行詩飽含四種戲劇性元素:人物(父子對話)、內心獨白(貫穿一生懺悔)、場景(關鍵的馬路“閃回”場景)、沖突(漫長時空的煎熬“等待”)。就此繼續網開一面地看,但凡復調敘述、對白混合、時空穿越、多角色置換、多視角開放、偽敘述、情景蒙太奇等,都為戲劇性建筑提供了上等腳手架。筆者看好其綜合分量:舞臺寬、戲路闊、結構緊、張力大,可在詩文本世界繼續呼風喚雨。
3.知性元素。知性是浪漫詩歌向現代詩歌轉型的必經之地。為克服抒情文本的過分夸飾,現代詩學啟用感性至理性認知過程的“中介”——知性。它是詩人情愫、知解力、智慧的集合;既有智力、理智等理性化沉淀成分,又有直覺、智慧、領悟等感性的機動穿透。在詩學上,人們更愿意用智性來代名知性。
石頭作為周倫佑的個人的私立象征,伴隨從小到老的坎坷人生,他寫下一系列與石頭有關的文本:《狼谷》《不朽》《模擬啞語》《幻手之握》《石頭再現》《石頭構圖的境況》《鏡中的石頭》……書寫頻率達到驚人的程度,“扛著石頭的大鳥”(劉翔)是他再形象不過的比喻。經由這些帶有深重智性元素嵌入的深度意象,隱喻著生存中的各種負面壓力:邪惡、冰冷、嚴酷、暴虐、異化,同時也顯露出正面的持守喻指:堅硬、抗爭、強固、力量,自然也穿插了不少中性過度,顯示石頭豐厚的意蘊。
而《對石頭的語義學研究》則進一步深入詞源,擴增引申義,作為個人的終極銘文:“在黑暗中石頭被引申為火種/在火中,石頭被引申為鐵的原型/百煉成鋼;為刀鋒的冷淡/祭獻之羊與刀刃互相理解/死亡中石頭被引申為不朽……”石頭鑄造詩人的悲劇意識與強力意志,石頭成了周倫佑的脊骨。詩人用詩對石頭施以魔法,讓它們說出自己的本質,或者說,詩人采取浪漫或冒險的方式化妝成石頭,混進石頭當中進行間諜式偵查。⑤這種對石頭的“臥底”,收獲了石頭的最大秘密,也使得石頭在當代譜系中成為一段突出的亮帶。仔細揣摩石頭上的銘文,刻寫著詩人反抗的“微言大義”,充滿對苦難、自在、寫作、命運、承擔、靈魂、流浪、家園的深度掘進。石頭是一種介質,它維系著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的關系,也是兩個世界互動的橋梁,它是一個有物質重量的語詞,由于詩人以自己的生命擦亮它,成了當代詩歌的某種介入性“地標”。在隱喻、象征并沒有消失的世界里,和石頭譜系聯接在一起的還有其他深度的智性意象(麥地、鐵器、漂木等),以自身獨特的意涵與魅力,繼續擔負意義的搬運工。
有學人在理論上總結智性詩學特征:在修辭層面呈現機智、反諷和悖論等修辭的常用;在意象層面呈現出主觀情思融于客觀物象;在象征層面呈現官能感覺與抽象哲理的融通;在結構層面強調詩歌史經驗的綜合,并努力將各種對立因素組合起來而使其具有戲劇性;在態度層面則表現為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詩人對自己所處的歷史和時代的一種客觀自知的態度。⑥無不鼓倡詩人分析時代,采擷更多原創的深度審智元素,給日漸平面化、取巧的文本世界注入“思”之重量。若果說,金屬世界的舉重冠軍公推鋨元素沒錯,其密度高達22.59g/cm3,名副其實。不幸的是這位藍白色的大力士,卻有個希臘小名“臭味兒”,實在冤得很,但以如此沉甸甸的質量增強合金硬度,對于同樣推崇沉甸甸質量的文本倒是最好的鼓勵:欲強化文本的厚重之“思”、發動“審智”之舵,首先得做好磐石般的“壓艙”工作。
4.禪意元素化。與相對明晰的智性相反,禪意顯得神出鬼沒,把玩莫測,因而能成氣候者廖廖,早期有不太成熟的廢名,后來有轉向“晚期風格”的洛夫,最全面的當推臺灣苦行僧周夢蝶,而臻之佳境的該是沈奇。
趙毅衡曾道出其中的二律背反難度:“禪詩因為是寫出來的,必不是禪;禪因為拒絕被說出,因此不會進入禪詩。如果一定要形諸語言,禪要說得笨拙,詩要寫得漂亮,完全是南轅北轍:禪詩如果可能,必定是吞噬自身的意義旋渦。”⑦正是因為高難度,才繼續吸引一幫年輕人不憚險峻,嘗試新禪詩寫法。因為難度與篇幅關系,我們暫無法深勘其道,只能先于外圍,羅列相關元素,感受一二,以四川大學理工學科出身的何兮為例,他把數字化的0 與1 合成了俳句小令,在禪境、禪思、禪意、禪機里游絲飛絮。
禪境:縱然是一種無分別、無意識的現量境界,然與一般詩境還是有所區別,偏向于幽渺與虛無,以便安頓空寂、清明的人生。來讀《去年的雨》:“停下腳步,走神/一場雨就拐進巷子/而你卻忘了打傘”;還有《上鳳凰山》:“此處有山風吹來/此刻清涼和歡喜/都沒有形狀”。恍兮惚兮,境與心偕,心與景融,一片大同。
禪理:是佛學、禪宗之義理,風儀清雅,解黏去縛,直透人心。來讀《東關古渡》:“不見船來/一夏蟬聲依舊/渡我”。再讀《黃昏的光孝寺》:“有鳥雀聲在枝頭盛開,一朵,兩朵/葉落,原來也是花開。”超逸塵世,物我合一。
禪思:無論霹靂、驚雷還是清風、微嵐,皆是或輕或重的“非思量”,從固有、惰性的思路中開辟上云端、入深谷的階梯。來讀《時光》:“在我的河邊/等一杯茶蘇醒/蘇醒的還有做成了椅子的竹”;再讀《遙寄西嶺雪山》:“什么都不用想/其實我只是想念白天看見的/雪地里圍著取暖的卷白菜”。入世與出世,最需要找到思與詩的棲息地。
禪趣:以一葉一草取代世界宇宙,以輕煙淡霧撩撥泰山之物,以調侃化解沉重,以佻達維持莊穆,來讀《云鐘》:“靜靜的/行走在拉薩的風中/讓過往的風把我撞響/一下又一下”;再讀《手心里的村莊》:“把月亮藏在鳥巢里/尋找的人卻發現了太陽”。童真之意趣,傻逼之言表,都在上繳圓夢的作業。
禪機:捕捉剎那的一念動,或許就觸動了某種奧秘,古典的禪機易流落于茫茫云海,當下的“一擊”,或更接近明確的犀利?來讀《臥佛》:“佛臥下醒著/我臥下就睡著了”;再讀《焚香小集》:“不要回頭/一回頭山水就遠了”。處處充滿醍醐灌頂的機竅。
禪悟:在生死、榮辱、利害、有無的循環里,細細領教漸悟、頓悟、了悟的人生。來讀《蓋碗茶》:“門檻邊除了進出與過往,/還有什么/一只貓自得其樂”;再讀《星星》“這個夜晚,一支煙比一生還長/一支煙比一生還短”……這一切,皆由禪詩語來“打包”,而禪詩語的本質,是在不可說與可說之間婉轉,它考驗詩人如何脫逃“沉默的死海”,又從上面掀動浪花或漣漪。沈奇曾有一段文字評價洛夫的禪語:重覓漢詩本味的興頭,淡語亦濃,樸語亦華,自然呈現,邀人共悟,一時盡得禪思之別趣,且現代,且鮮活,且有味⑧。如將此說移作對現代新禪詩的寄望,亦十分切中。
禪詩之難,難在那么多艱難的要素:禪境、禪思、禪意、禪機、禪象、禪脈、禪語、禪鋒乃至禪謎,集結為“非晶相”的、無序的高分子結構。要是沒有緣分,即便眼前,也遠在天邊。這意思是說:人意不全可為,成活率太低,許多自以為是的佳作其實都是贗品。所以堅信,禪詩是詩歌化學反應中最難操控的類型,一如核糖核酸分子式,只要稍稍改變排序,立馬生成另外模樣,非超一流者,切莫輕舉妄動!一如人之染色體,僅僅在第23 對中出現XX 與XY 的一絲錯位,便導致截然不同的男女性別,同樣驚險的是,只要在第21 對中不其然多了那么一小條,便莫名其妙造出了可憐的“唐氏患者”,無可救藥。這,或許就是詩禪結合最難把握的“閃失”。
5.原型元素。原型是種族記憶、集體無意識在人類代代相傳中所形成的共識性心理積淀物。作為華夏民族特有的文化符號,如蝴蝶象征著伉儷、至愛、和美、耄耋(耋諧音蝶);蓮花象征佛界、清廉、貴子、恩愛;竹象征君子、高潔、挺拔、祝頌(祝諧音竹)等。
原型意象深受古代詩人心儀,“五四”以來的新詩沿襲了這一豐富資源。吳曉東在《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現代派的藝術母題》專著中,選擇了十幾種類型,逐一進行詳細解讀:扇是一種具有裝飾性的審美原型意象,何其芳筆下的“宮扇”,作為夢的依托,或作為“畫夢”過程,散發著對形式感的深深眷顧,為詩人自己的瑰麗的想象找到極為匹配的中介,幻想的生命形式與對象性審美獲得了高度融合。樓因其位置、結構、被賦予宏大的情景與境界,凝聚著深厚的美感積淀,同時也因其空間性被視為一種自足的心理居所,由此引發卞之琳慘淡經營《半島》——一座臨水小樓,一方面象征著詩人傾心追慕的幻美世界,另一方面又隱含著追求與理想之間無法企及的矛盾。窗是居室與外部世界的臨界點,正如橋是流水與岸的距離分界,施蟄存在《彩燕》中欲想“跨過那窗”,進而“走出那黑漆的墻門”,意味著對封閉的象牙塔生活的厭倦與突破。古城代表著人們的日常空間與生存處境,而古鎮的意象是古城的延伸,卞之琳《古鎮的夢》是通過算命鑼與梆子聲的交替起伏,喚起一種久遠的世紀意識,一種恒久不變的空寂感,一種鄉土所固有的靜止與凝滯的意緒。鏡子具有自返式的鑒照功能,在諸多詩人筆下卻各顯神通:廢名在病中《點燈》,仿佛是起床掛鏡,看見墻上的“影子”,表達自我與鏡像的關系;卞之琳的《舊元夜遐思》,傳遞了一種孤獨的“逃避心理”;牧丁的《無題》,面臨如鏡大海,諦聽到自身的寂寞。朱英誕的《曉鏡》,不僅照出容顏憔悴,還照出自身匱乏,廢名另一首費解的《亞當》,則確診了主體的虛假與空落。⑨
表面上看,原型的路子有限,因為祖宗留下的“母題”畢竟擁擠。其實,在詩人高超的聯想、想象制導下,完全可以從正宗嫡系不斷研發出亞宗、泛亞宗系列,吳曉東已成功做出分析范例。臺灣詩人陳大為在這方面也頗有心得,他書寫《再鴻門》《治洪前書》《髑髏物語》《屈程序》《曹操》《達摩》等。在他筆下,中華民族文化象征的麒麟和龍,換喻為詩歌的“圣獸”,他援取原型豪杰,思索社會現象與受教過程中的定見,捏塑理想人格的雛形,具有轉化原典、與現實對話的特色,也形成互文激蕩的多聲部特質。⑩
鄭慧如多次指出,原型“具備文化流衍過程中各種元素的匯聚,蘊含了整個民族的靈魂,成為文人取之不竭的資本。原型敘事從僵化到活化,從封閉到開放,借此詩人可由悖反傳統、回返傳統到建立新傳統,作為開涮原型、抽翻“傳統”、播弄詩意的收束。?若果我們把“原型”放入化學元素周期表里,應該屬于歷史最悠久的穩定“族群”。科學家們發現,原子核擁有特定的“魔數”序列,為2、8、14、20、28、50、82、126 排列。天造地設,鉛元素的最穩定同位素Pb—208 的質子數恰是82、中子數126,鬼使神差般均處在“魔數”系列的最佳位置上,葆有深遠的影響力。有緣于此,我們完全可以把“鉛爵士”推舉為文本“原型”的代言人,共同開發集體無意識,讓有限的原型,繁衍眾多的后裔。
6.音樂性元素。音樂教科書通常將音樂元素列為九種:節奏、旋律、和聲、音色、力度、速度,調式、織體、曲式。如若將音樂元素“移用”到詩學上——按學科不同特點加以增刪、合并——或許從整體上可分為外在節奏與內在節奏兩大類。外在節奏主要指由音節、韻腳和對稱性因素組成,典型的外在節奏是由復沓、對稱與回環形式構成;內在節奏(或稱內在律)主要是指情感邏輯起伏變化而引起的詩情流動美。故內、外在節奏的辯證是互為表里互為對應,形成詩歌理想化的音響效果。
朱湘的《采蓮曲》幾乎達到當時詩歌音樂性的“顛峰”,嚴密工整形式一直為人們稱道:全詩5 節,每節10 行,每行都固定音部,不可逾越。每節用韻的格式也相當一致,成為新月派在詩形,尤其在外在音樂節目單上的翹楚。然而到了第三本詩集《石門集》,朱湘把注重外在音樂性的詩形向詩質中心轉移,展現憂郁、病弱、頹廢的“現代詩質”,再也不管什么平上去入、抑揚頓挫、強弱長短、宮商徵羽、雙聲疊韻,只遵循“情緒的自然消漲”(郭沫若),讓人們把注意力投注到內在意義的尋思。而十四行體,也只剩下外在固定行數,所有的音樂性表示都集中在情緒節奏單位與意義節奏單位的調配上。這種詩形與詩質、外在與內在、詩與歌的“分裂”,讓百年新詩嚴格意義上的格律化步履艱難。其實相對平衡的做法是,在保證內在旋律順暢進行時,適當釋放外在音樂性能量(復沓回環、對仗對稱、排列跨行、能指滑行、疊詞疊句、韻腳交替)未嘗不可。
然而現代詩崛起,大力推行內在節奏為主的音樂性,大大消弭了因“格律化”影響而留存的外在音樂性。但奇妙的是,伴隨著外在節奏的弱勢,近年悄悄推行的語調,儼然形成一種形式化了的情緒、聲音、語義的混合。語調似乎有一種巨大的能耐,將內、外節奏進行某種巧妙的收攏、統編:她一頭牽動內在情緒體驗,一頭連接語言形式,語調似乎成為詩歌更為隱秘的“旋律”?
毫無疑問,鄭愁予的音樂性達到內、外節奏的高度統一,達到現代語調的行云流水。擬聲運用、語勢變化、句型排列、色彩變奏,充滿“美麗的騷動”,成就獨特的“愁予風”。臺灣女詩人羅任玲曾運用“音樂色彩學”窺視鄭氏的內外節奏與語調,統計出鄭愁予7 本詩集10 種色彩頻率,這構成鄭愁予詩作冷暖兩大調性,具體顏色的次數分別為:白73 次、紅52次、黑47次、藍42次、青34次、綠27次、金23次、灰14 次、紫11 次、黃10 次。?
人所共知,色彩和音符的相同處皆是由波的頻率導致的,前者是電磁波,后者是聲波,它們能產生強烈的對應,蓋因從紫到紅的七色波,頻率越來越低,而7 到1 的音符下行也呈下滑趨勢。故色彩與音符的交織轉換,擁有視覺與聽覺的“通感”優勢。可是這樣的優勢,在現代詩階段,因外在節奏削弱導致音樂元素流失,是時代使然?審美變遷?但隨著流行歌曲的興起,已有不少人士強烈呼吁詩與歌“破鏡重圓”,無論要等上一個新的“輪回”,還是停留于“一廂情愿”,現代詩的未來,無法漠視多種音樂元素。
“窯變”藝術
日本學者金森修在評價巴什拉元素詩學時寫到:物質不是精神的敵人,而是精神的朋友。世界是物質與精神這對親密伙伴交流的場所;物質將要展現逃脫近代科學描述的優美姿態,詩將要擺脫精神自我陶醉的陷阱;“我覺得:似乎尚未充分勘查到至少元素詩學能讓我們窺視到豐富世界的可能性”。?該論斷可繼續發揮的是:詩歌的豐富性取決于詩性元素的密度,也決定詩質的好壞。詩性元素組合每個具體詩本,從架構(題材、主題、布局、意義等)到肌質(語詞、聲韻、節奏等),都留下無所不在的蹤跡,而這些蹤跡又集中突出為上述所闡釋的各種元素亮點。它們密布在文本的每個角落,或緊致或稀松或隱形或顯豁或疊加或交混,形成一個有機體,有的牽一發而動全身,有的渾然不分筋肉相連,在不同崗位各盡其職,在相同位置相互競爭。仿佛遵循某種律令,既有序地排列組合,似乎又四處游蕩。
它再次叫人想到材質與冶煉工藝。各種破銅爛鐵經過高溫處理,去偽存真,最后形成合金;各式碎石礦物,幾經格式轉化,也得以最后變構成型。古人早就窺見化合冶煉的奧妙:
自有爐錘,妙歸陶冶。無堅不銷,有颣必舍。聚如郁煙散若奔馬。活活泉鳴,艷艷霞赭。汞可成丹,注焉用瓦。笑彼僻固,鑄金事賈。?
如劍冶鐵,如鏡煉銅。出自爐韛,妙入化工。光皎冰玉,氣為星虹。湅燒為云,碧色補空。初震石鼓,漸調金鏞。色滿天地,隱隱隆隆。?
文獻概述再美妙,也不足于眼見為實。2015 年杜甫1300 年誕辰儀式后,筆者特地趕往禹州神垕鎮參觀鈞陶燒制,堪稱國寶級的窯變,在在是“入窯一色,出窯萬彩”“鈞不成對,窯變無雙”。它印證每件作品都具唯一性,即使同時同爐同位,也不可能燒制出雷同產品。表面貌似相同流程,從原料到出窯幾十道工序——節氣、溫度、濕度、氣場、氛圍、材質、壓力,其中只要一個環節稍有改變,馬上成群成堆地“串色”,導致“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一過程,多么吻合詩歌文本的變幻生成。
鈞瓷區別于其他瓷種之處,是其釉層結構帶有“纖維狀”,即便恪守配方,也很難改變出乎意外的顏色與品相。原則上說,以銅為主的氧化劑衍生出的釉色有:茄皮紫、海棠紅、蔥翠青、雞血紅、孔雀綠、寶石藍,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紅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青,紅中寓白、藍中有綠,爭奇斗艷,萬紫千紅。通過拉絲、沉積、結晶等途徑,又變幻出星點、菟絲、蟹爪、龜背、雨簾、蛛網、葉脈和蚯蚓走泥等形態。沒有一次是重復的,沒有一回依樣葫蘆的。如是無窮地分解化合,豈不是現代詩寫的多重有機組合?“十窯九不成”的難度與變幻,不也是現代詩生成的“一過性”特征?
專家們曾用X 射線熒光法,測得Fe2O3、Al2O3和TiO2含量是導致色彩變異的根本原因,也測出窯變與14 種化學成分有關,進而得出胎、釉的基本配方。?還有人提醒關鍵是掌控好多種微量元素中最主要的磷、鈦、銅、錫四種。?由此配方對應到詩文本各種成分的權重,詩人應該心中有數:哪些應該強調、倚重,哪些必須削減、剔除。
而自采料、練泥,旋坯、定型,上釉到控火、鍛燒的流程,“過手七十二,方可成器”的繁復進行,顯示了窯變藝術與生命形式具有某種成長的同構性,具備有機、或然、動態、生長的特征。所以一件窯變器物就像是一個生命體,它妙造于自然,是一個圓融和諧的生命活體。?在這個意義上,不也是現代詩文本完型的形象寫照嗎?
盤點窯變藝術,追蹤“量化”指數,旨在強調從化學角度觀測詩歌,冥冥之中,何能得到天遣神助,才得以如此自由隨機、隨形賦色?現代詩文本的生成與構成,恰似鈞窯的成型變幻。許多時候,成功出品,多取決于氧化鐵、氧化鋁的獨到配置,表面上簡單的加加減減,實則隱含著難解難分的方程。由此推及并確信:無數有機配方的微妙組合,誕生絢爛多彩的窯變藝術。
①原田佐和子等:《化學變!變!變》,高遠、蔣莉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 頁。
②詳見楊帆:《瘋狂化學》,人民郵電出版社2018年版。
③樊樊:《生命氣場說中詩歌文本的發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a0b730100g4e5.html,2009.12.7。
④沈玲:《論蕭蕭詩歌中的“白色想象”》,《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2 年第1 期。
⑤二丫:《簡論周倫佑詩歌中的石頭意象》,《星星詩刊·理論》2011 年第8 期。
⑥汪云霞:《知性詩學與現代詩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7 頁。
⑦趙毅衡:《看過日落后眼睛何用?——讀沈奇〈天生麗質〉》,《天生麗質》,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年版,序文第2 頁。
⑧詳見吳曉東:《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現代派的藝術母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
⑨沈奇:《“詩魔”之“禪”——〈洛夫禪詩〉序》,《沈奇詩文選集》第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57 頁。
⑩? 鄭慧如:《原型、敘事、經典化——以大荒、羅智成、陳大為的詩為例》,《文學與文化》2012 年第2 期。
? 羅任玲:《臺灣現代詩自然美學——以楊牧鄭愁予周夢蝶為中心》,(臺)爾雅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7 頁。
? 金森修:《科學與詩》,武青艷、包國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0 頁。
? 馬榮祖:《文頌·熔煉》,道光世楷堂刊本《文頌》,張聲怡、劉九州編:《中國古代寫作理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9 頁。
? 顧翰:《補詩品·精煉》,張聲怡、劉九州編:《中國古代寫作理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8 頁。
? 吳雋等:《宜興仿鈞陶胎釉組成配方特征研究》,《中國陶瓷》2012 年第8 期。
? 苗長強:《鈞瓷窯變藝術的探索與研究》,《陶瓷科學與藝術》2014 年8 期。
? 江雪:《基于符號學理論的中國陶瓷窯變的美學分析》,景德鎮陶瓷學院碩士論文20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