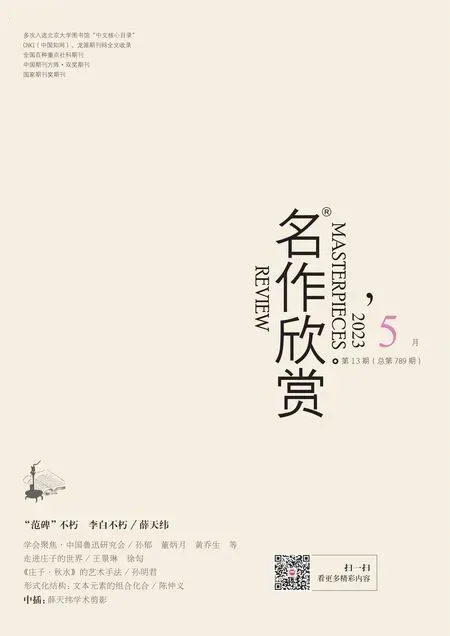有溫度與情感的節氣記錄
——《跟著節氣過日子:一個人的二十年節氣筆記》讀后
浙江 王晴飛
傳統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農業為立國的根本。關于農業、農時、農事重要性的表述隨處可見,比如孔子教育弟子“使民如承大祭”(《論語·顏淵》),便是說役使百姓的態度要慎重乃至莊重,而役使百姓的正確方式就是“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也勸誡梁惠王“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說的“時”就是孟子說的農時,指的是農業生產的時間規律。
中國人自從先秦乃至更早時期就已經開始“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尚書·堯典》),總結天象、物候規律,直到漢代逐漸形成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二十四節氣,確立了相對統一的農業歷法,也是與農事相配合的自然與時間體系,其最終目的是服務于農業生產。
節氣首先是實用的,所以隨著現代化的來臨,農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節氣也不再是所有人共同分享的基礎知識,甚至對于很多人來說,節氣已經是一種從其生長的環境中剝離出來的死去的知識,只留下與之相關的民俗、文化為人所記,而忘卻其本來意義。
現代人的時間系統也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的時間是全球大一統的時間,而節氣所代表的時間體系服務于農事,不僅僅與天象有關,更與物候相關,比如自然界的氣候變化、植物的榮枯、動物的蟄藏遷徙等,不同地域和同一地域的不同歷史時段,物候會有所不同,所以節氣代表的時間體系有其歷史性和地域性,隨著時代和地區的變化,會有各自的調整。
處于現代的我們,記錄下某一時段內各節氣的氣象物候,也就有著現實的意義。這種記錄將已經變得籠統抽象的節氣、傳統變得具體可感,使民族共同記憶通過具體個人的感受呈現出來。而我們現代人,也應當以現代精神和現代觀念,重新理解、發明傳統,使傳統在今天重新煥發生機,而不僅僅是博物館里的展品。
喬忠延先生的《跟著節氣過日子:一個人的二十年節氣筆記》(北岳文藝出版社2021 年版)就是這樣一本記錄我們時代二十四節氣的氣象物候狀況的書。本書記錄的地域主要是作者居住的山西臨汾,隨著作者探親、出差等活動,也涉及太原、北京、南京、杭州乃至廣州、臺灣等地;時間跨度上,則大約自1999 年至2019 年這二十年,雖然放在物候氣象變化的漫長歷史中,20 年不過一瞬,但對于個人來說,這已算不短。這種記錄的價值,有時同時代人因為離得太近,反而未必看得清楚,當時間距離拉得足夠遠,在與更長時段的比較中,產生差異,其意義與價值也會更顯豁。
作者喬忠延是一名散文家,以“業余”的身份而記錄氣象、物候,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我們不必諱言,若只論觀察之準確、記錄之翔實,散文家肯定不能與專業人士相比,必然會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但是,節氣本來就有其特殊性。中國自古以來的節氣記載,并非直接記錄當日溫度、天氣,而是通過自然界征候的變化,來判斷農時。
二十四節氣代表的中國傳統農時系統,固然是順天應時,是客觀的,但也總是帶有著觀察者的主觀體驗。物候觀察,不是看某一個具體指標的精確數據,而是所有指標在一個綜合性體系里發生生物、化學反應,比如“四月秀葽五月鳴啁”“八月剝棗十月獲稻”(《豳風·七月》),比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仲春之月,日在奎……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玄鳥至……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禮記·月令》一、二月)。觀察者看的是物的征候。這種“主觀”,看似不客觀,實則甚至可能更為“科學”。而我們今天的科學是否可以完全窮盡一切指標的變量的數據,是否可以研究清楚所有變量發生反應的方式,其實也還是一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上,通過物候來判斷,就有其看似非科學的“科學性”。
《跟著節氣過日子:一個人的二十年節氣筆記》也是這樣一份帶著作者主觀情感和感受的記錄。關于氣溫的紀錄,便不是具體準確的度數,而是“我”對氣溫的感覺,是氣溫(其實還包括干濕度、空氣清潔度等)作用在我的身體乃至心理上產生的反應。比如二十年的立春,作者的記錄常是“天氣不給力”“霧蒙蒙,灰茫茫”“晴亮”,或記錄節氣前后風雪的情狀,也不乏“吸一口氣,綿綿的潤肺,像是糖葫蘆的味道”這種文學化的形象描述。這些感受不能給我們一個非常精確的數字,卻能夠讓我們對該節氣時的氣候觸手可及。
這些感受還體現在作者總是將節氣當日的情況與前后若干日相比較,認識到節氣雖是一個節點,卻并非斬釘截鐵地以節氣這一天將時間分為兩段,看到“常”與“變”的辯證。比如立春雖是報告著“春”的來到,卻并沒有突然就春意盎然,而是漸漸改變,相對的時節氣候之間不是截然兩分,而是一場拉鋸戰,有時候立春反而比前幾日更陰冷。其他節氣也是如此,所以得出經驗,“雨水一到,說明春天已經站穩了腳跟,不會再讓寒流肆虐樹下的花草”。
關于物候的記載也有不少。2010 年雨水日,作者去打籃球,“看著柳樹還很枯干,伸手挽住枝條,卻是柔的了”。2000 年驚蟄日記:“田土松了。踩上去如同踩在了酵化好的面團上,好酥好軟。堰壟邊的枯葉間,似乎有了影影綽綽的綠意。細看時,間或伸出的新芽,還有些白,有些黃,或者說白里泛黃,黃中露白,并沒有完全泛綠。”這兩則觀察,非常精確也非常精彩,完全可以區分出這一時節的植物與前后兩個節氣的不同。關于動物變化的記錄,“驚蟄”一章最多,這當然是因為“春雷驚百蟲”,蟄伏的動物開始出現,易于觀察。如2003 年驚蟄前數日,家中已現蜘蛛,“提前”感受到了春意。與之匹配的,則是“田里的麥苗仰起頭”“返青了”。2013 驚蟄,再次在樓梯口發現蜘蛛,同時楊樹絮開始飄落。此外,在不同年份,驚蟄驚出了蚊子、黑蛾、蜜蜂等。驚蟄名副其實。
而記錄植物變化最多的是清明。這大約是作者每年于此日上墳,因而自然到野外去的緣故。如2000 年清明于野外見到“新葉黃茸茸滿枝”,作者以“稚綠”稱之,也是非常精確的。幾乎每年的這天,都有關于植物的記載:“窗外的桐樹爆滿了淡紫的花朵”,“大地禾苗茵綠,春嫩得能滴出水來”(2006 年清明);“酸棗刺仍舊光禿禿的,樹干上看不見一片葉子”,“好在桃花怒放,花色嬌艷”,“墳塋里栽植的柏樹株株嫩綠,生機勃勃的”(2009 年清明)。2006年芒種日,作者回農村,“滿眼是揚花的麥子,綠中泛白,白中透黑”,“麥田里白花花的,地皮是硬的,明顯是旱了”……不同節氣,有著不同動物的蟄現,也有著不同植物在開花結果。
作者因為工作關系,時常出差,也因此有機會感受不同地域的節氣。比如同為清明,2018 年作者在揚州,雖然天氣不佳,但瘦西湖內,“巖邊,路邊,花色繁多,開得像是鬧嚷嚷的一群佳人嬌娘”。又如小滿日,2004 年作者從臨汾去曲阜,途徑鄭州、洛陽,于是觀察到“臨汾的麥子尚綠,而洛陽的部分麥子已經收割過了,鄭州的麥子大部分則黃橙橙一片”。不同地域麥子的生長進度再次有著肉眼可見的差別。差異更大的是2005 年,作者在東北五大連池市,該地與臨汾不僅氣溫懸殊甚大,植物的季節也不同:“前兩個月桃花櫻花丁香就在我的家鄉喧鬧過了。但東北的花兒這會兒才怯怯地露出花蕾。”(2005 年小滿)不同緯度植物花期的差異在此得到更為直觀的呈現。
作者的主觀情感,更主要地體現在他對農事、農民的關注。我們從這份筆記中可以看出,他對農民的感情是真摯的,對農事也是內行的,他的情感與倫理都在這一邊。在日記中,他常因“節氣”的表現不夠理想、不適宜莊稼生長與收獲而焦慮,甚至怨天尤天。如2002 年,因為之前氣溫一直偏低,到了芒種時候,麥子尚是綠的,最近才熱起來,作者不禁吐槽“已經遲了”,抱怨“芒種不像芒種了”。何為“像”,或者說節氣“應該”怎樣呢?那就是完全符合我們理想中期待的節氣的樣子,使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能合乎時令,使農民勞有所得,勞有所獲。
在作者對節氣本身的理解與闡釋里,也能看出這一點。如他對小滿的贊美,“小滿時節,是一年里人心最為舒爽的日子”,“小滿時節的氣候,最一個適宜了得,用刻下時尚的話講,最為適宜人們的生活”。贊美的原因不僅僅在于氣候讓人感覺舒適,更在于小滿時麥穗開始灌漿飽滿,小滿預示著未來的豐收。關于芒種,則更能看出作者的情感傾向。在“芒種”一章開篇的“芒種忙收又忙種”里,他引用了白居易的《觀刈麥》、楊萬里的《插秧歌》,都是寫農忙的辛苦與情趣。而文章結尾處,忽然說起《紅樓夢》中女子們祭餞花神之舉,并評價為“沒事找事”。可見,沒有農事意義上的風花雪月,在作者這里是沒有價值與意義的。
節氣,以及前人關于節氣的表述,在作者這里都被倫理化了,這就使他對關心民生、將小我融入大我的詩歌表示欣賞,對傷春悲秋無益民生的詩歌表示鄙夷。比如關于“立秋”。從農事的角度看,秋是豐盛的季節,果實累累;于農夫而言,是一年的辛勞終于得到收獲。所以秋應該是愉快的,充滿喜悅的。由此,作者不僅對那些對節氣景象無功利、純審美的態度不滿(稱為“無事找事”),對于傳統文人的悲秋詩更為不屑。所以,傳統詠秋的詩歌里,他只贊賞劉禹錫的《秋詞》,便是因為詩人沒有沉浸于一己之悲歡,而是以天道(大自然)來擴大個人胸襟。“大暑”日記前的篇首一章,更是品評“暑”詩的格調境界。在作者看來,白居易《消暑》、楊萬里《暮熱游河花池上》諸詩好則好矣,但只是個人的納涼祛熱,不如王令與戴復古的境界高。“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王令:《暑旱苦熱》)與“農夫方耕耘,安坐吾敢食?”(戴復古:《大熱》),皆是表達“兼善天下”與憫農之意。“小暑”亦是如此,元稹的《詠廿四氣詩·小暑六月節》與韓翃的《贈別王侍御赴上都》,或寫出夏日生趣,或傳達對友人的思念,在作者看來,皆不夠豁達闊大,“和小暑的節氣不大對位”,因為小暑時節,正是莊稼生長拔節之時,“小暑應該是熱烈的,催人奮進的”,“小暑是一個生機盎然的節氣”,所以他更喜歡獨孤及的“不怕南風熱,能迎小暑開”與耿偉的“小暑開鵬翼,新蓂長鷺濤”,這里卻又有為“小暑”鳴不平之意,仿佛那些只著眼于景色與怨嘆的詩詞冤枉了小暑。在“雨水”一章,則更是為夸雨水而偏去罵春風,不免有“說什么就吆喝什么”之嫌。
就節氣論節氣,將節氣倫理化倒是符合節氣本身立意的——節氣本就是服務于農事,本就有其實用性,因而也就具有倫理性。不過倘若過分追求倫理性,以倫理作為唯一標準衡量所有詩詞,也不免會剪裁掉很多美好的東西,專一其美,而不能“各美其美”。尤其是將節氣人格化,過于將個人情感情緒投射到自然規律之上,有時也不免使自然淪為人事之附庸,也會在自然與人事之間建立直接聯系,反而將自然狹窄化了。如說到春分就聯想到“公平”“公正”,說到“大雪”,則于“雪”上附加程門立雪之尊師重道、臥冰求鯉之孝母至誠、孫康映雪之刻苦求學,這其實都只是人的想法,與“大雪”無干的。節氣的倫理化和人格化,也會引起過度從自然中闡發個體人生體驗的做法,使自然成為既有人事經驗的附會。比如立春而氣溫沒有明顯回升,且“天空不明凈”,作者于是稱之為“低調”,且感慨曰:“低調,是一種姿態,但不是誰也能夠做到,不是誰也有資格。不是誰也能做到,是因為有些一旦得勢,總是尾巴比頭發翹得高;不是誰也有資格,是因為低調是對于高調者而言。若是本身就是弱勢范疇,那低調是自卑,沒有人認為是低調。如此分析,今年這春天該是最具美德的春天。”(2012 年立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只是天而已。我們不宜給“天道”強行過度附加人事上的意義,尤其是這種人事意義不僅不能增加我們社會的美德,反而限制了人對天的想象力,天被人事變得小了。
服務于農事是節氣的直接目標,也是具體經驗,而在2000 余年的農事實踐中,我們的祖先也從中總結出許多抽象經驗,中華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自然也會在對節氣的理解中烙下印記。比如關于小暑之“小”,在作者看來是“炎熱的開端”,是給“大暑”留下余地。這道理,在解讀小寒時說得更清楚。小寒之“小”,是“謙和自持,一點也不放縱”,而大寒是不是就一定比小寒更寒?卻也未必。因為大寒已是極致,物極必反,寒之極便要向對立的方向轉化。所以春的溫暖恰在最寒的時候萌生。這也如我們對冬至的理解。冬至本是“陰”至盛之時,晝最短而夜最長,但是也就在這一天,“一陽來復”,“陽”已在陰最盛時萌生。順應天時,物極必反,從巔峰看到危險,從絕望看到生機,這是中國式的辯證法,也是中國一切節氣、民俗中包含的智慧。
喬忠延先生的個人二十年節氣筆記,給我們留下了第一手的節氣資料,也包含著他個人對節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所以這份資料不僅僅是客觀的、可供科學研究的無生命的素材,更是帶有著個人情感和生命的體溫,是人文與自然的交互。當然,在具體的記錄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還有一些欠缺之處,比如關于物候的記錄較少,更多的是溫度和天氣的記載,常常不能涵蓋節氣的內容,也不免有時過于偏于人事而剪裁自然。這些都不免是白璧之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的如何刷新,傳統如何再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大問題。節氣,是農業社會的遺產,但也包含著現代社會可以抽象繼承的智慧。我們固然不宜妄自尊大,以為唯我中華有節氣;卻也不必妄自菲薄,以為傳統不足道。我們不妨以新知識融匯、喚醒舊傳統,使其在今天繼續煥發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