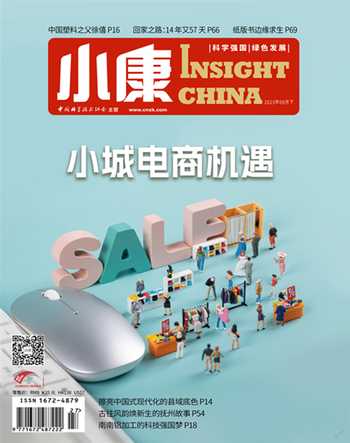“絕望之下,希望尚存”
蘇楓
“我奔跑的每一步,都是為了離你更近一步。”

由孫海洋口述,女兒孫悅執(zhí)筆的紀實隨筆集《回家:14年又57天》近日出版。這本書記錄了“懸賞二十萬尋兒子店”當(dāng)事人、電影《親愛的》原型之一孫海洋尋子路上的故事。
孫海洋曾經(jīng)在15歲就出門遠行到社會闖蕩,人到中年決定一展宏圖時,卻遭遇人生的重大危機。2007年,孫卓在深圳被拐,孫海洋踏上了尋子之路,彼時他背著一個裝滿資料的舊書包,在30多個城市奔波尋子,直到2021年12月,才終于在警方的幫助下找到了兒子孫卓并帶他回家。
孫海洋大女兒孫悅今年25歲,畢業(yè)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xué),父親尋找弟弟的旅途傾軋過她大半的生命歷程,是她成長的紋路。2007年弟弟孫卓被拐后,父親的尋子經(jīng)歷從此填滿了她的成長過程。曾經(jīng)的她是一名旁觀者、親歷者,弟弟回家后,她也終于成為了一名講述者。在寫作過程中,孫悅努力平衡真實與虛構(gòu)的關(guān)系,她真實地還原了關(guān)鍵事件和時間節(jié)點。
孫悅說:“我相信命運絕不是在壓垮人的時候才成為命運,而往往是在人奮起抵抗的時候,它才成為命運。”
絕望之下,希望尚存
2007年至2021年,14年又57天的尋找,30多個城市的奔波,5172個日夜的守望,孫海洋終于找到了兒子并帶他回家,一家人整整齊齊,圓圓滿滿,這是真正的小團圓。
2022年的大年初一,對于孫海洋一家來說,才算是真正的新年伊始。
孫海洋的半輩子都在奔跑:15歲開始,他陸續(xù)在武漢、三峽、永順和深圳為了生計東奔西跑;33歲,兒子失蹤后,他背著一個裝滿資料的舊書包繼續(xù)奔跑;47歲,他終于在警方的幫助下找到了孩子,但是他依然在奔跑……
孫海洋在歲月里搖搖晃晃終于人到中年,在決定一展宏圖的時刻,遭遇人生的重大危機。在街頭奔跑的每時每刻,他從未想到過放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我只擔(dān)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而孫海洋在苦難中,堅持繼續(xù)奔向前方。
寫《回家:14年又57天》,前后一共用了四個月,其實回過頭來,孫悅希望自己當(dāng)時再耐心一些,再多用一些時間。
她從未想過放棄,故事講述的就是“不放棄”,相比起來,記錄談不上絲毫艱難。
“破案的全過程比較難寫,就在認親前幾個月,多方都在暗自出力,許多線索都指向?qū)O卓。就像火山爆發(fā)之前的大地,看似平靜,然而敏感的動物們都能嗅到空氣中反常的氣息,并為此躁動不安。這個時刻是非常緊繃的,像一張被拉得太滿的弓,已經(jīng)無法承受分毫多余力量,可是弓上又繞滿了各處的亂麻,任何一根絲線偏移都可能使飽和的力量失衡。我不僅想拉好這張弓,還想把每根絲線都理清楚。為了盡可能客觀地還原各線索所起到的實際作用,我反復(fù)研究各種新聞材料,并采訪最直接的相關(guān)人士,多方取證。為了避免任何細節(jié)上的出入,在表述上不引起任何誤解和爭論,我也將這兩章反復(fù)修改了很多次。我還把各個版本拿給完全不了解這件事的朋友們閱讀,測試他們看完后獲得的信息是否符合事實。這確實是最考驗我筆力的部分。”
孫悅說:“有時候,我也會在寫作過程中停下來,大哭不止,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我是這個悲喜劇內(nèi)部,一粒隱痛的沙。然而,我想講述的并不僅僅是關(guān)乎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故事。時代的灰落在一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因而個人的命運也是時代的縮影。即使微不足道。”


寫《回家:14年又57天》的起因與初心是什么?
孫悅說:“《回家》的故事傾軋過我的童年和青春記憶,是我生命的深淺齒痕,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經(jīng)常看到其他記者書寫的父親的故事,而我始終有這樣隱約的念頭: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我得將爸爸的故事全部記錄下來。畢竟我在這個故事中,我是離故事最近的人之一。因此,在弟弟回家之前,我寫作的初心是為小家做長久的記錄,父親的腳步對我來說是有價值的、珍貴的,我不希望它們被遺忘和消失。在弟弟回家后,這個念頭越來越清晰地浮現(xiàn)出來,那段時間,作為幸運“上岸”的尋親人,也有了不一樣的視角和感受,我們走到了陽光下,回頭一看,那么多人還在風(fēng)雨里,我開始迫切希望這份小家的記錄能夠帶來更大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我和父親是很有默契的。我們希望一粒微塵的故事能夠照見過去十四年時代的印記,也讓更多人看到“打拐”取得的進步和其中依然存在的問題。通過這樣微小的記錄,最終,去號召正義,傳遞力量。如今《回家》出版近一年,以它收獲的閱讀面和反響而言,可以說它的意義比我寫作時想象的要大得多。”
“上世紀90年代,農(nóng)民進城務(wù)工成為熱潮,人口流動性劇增,全國各地爆發(fā)大量拐賣婦女兒童案。從內(nèi)部看,重男輕女、養(yǎng)兒防老、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后思想觀念是釀成悲劇的內(nèi)因,而從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層執(zhí)法不嚴,戶籍管理混亂,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幸運的是,我們已經(jīng)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進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后立案制度的明確變革。到今天,公眾對拐賣兒童問題的廣泛關(guān)注和深度共情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觀念正在漸漸淡出我們的視線。”孫悅說。
這種平凡何其幸福
2020年9月15日,孫悅曾在日記里寫下過這樣一段話:“打造一個全無希望的心境,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這就是我面對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這就是為什么有時候我突然很驚訝,意識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鈣質(zhì)而非某種生猛不可欺的金屬。我無法想象有一天那種力量不再像既枯又榮的野草一樣野蠻生長,脊骨也在27小時的站立中折斷了,我害怕他身邊沒人能接下他的擔(dān)子哪怕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講故事,我從頭沉默到尾,但每個細節(jié)我都記得。照理說我應(yīng)該把它們?nèi)繉懴聛恚吘鼓且才c我有關(guān)。可是在那之前我認為自己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沒有意義。”
那是孫卓被拐的第十三個年頭。就在次年,一切都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孫卓被拐的第十三個年頭,那是黎明前的黑暗。當(dāng)時也是疫情的第一個年頭,孫悅即將去新加坡讀書,父親依然奔忙在尋子路上。
在當(dāng)時,弟弟的“不在”已經(jīng)是一個十?dāng)?shù)年如一日的常態(tài):“我根本不會去幻想哪一天他會突然被找到,我想,但我不敢想。我自然蜷縮在一個全無希望的心境中,就像一個殘疾雙腿已久的人,早已忘了人是如何站在堅實的大地上。我會默默咀嚼這種境地。”
在孫悅的回憶里,“父親則相反,他始終在尋找,依然和尋親家長們密切聯(lián)系,并且尋找新的可能性。我記得,就在我去新加坡之前,抖音開始興起,且已擁有了不小的用戶群。但我并不使用,也不打算去了解,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時候并沒有我父親強。當(dāng)時我父親就下載了抖音,注冊了新賬號,并詢問我,能否幫他將《親愛的》電影中的一些片段剪輯出來,讓他發(fā)一個視頻,吸引一些關(guān)注,請這個新平臺上的人們也幫忙留意孫卓的去向。我想起十多年前,微博剛剛興起時,每篇博文還限發(fā)140個字。那時他不太會用智能手機,不了解網(wǎng)絡(luò),也并不知道微博會發(fā)展成什么樣。他并不思考這些,他只是會在一個平常的夜晚,非常艱難地摸索著注冊一個微博賬號,找到幾個基本的功能,一字一句地慢慢敲打:“我暫時還不知道微博是什么?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孩子什么時候能找回來?”然后點擊發(fā)送,讓這無比渺小的聲音落入互聯(lián)網(wǎng)的茫茫大海中。這就是我父親在第一年和第十四年的狀態(tài),區(qū)別其實并不很大。”
弟弟回家后,對這個家的改變的具體的,具象的。孫悅回憶,房間里的大象消失了,全家人頭頂那片烏云散了。逢年過節(jié),沒有那種心照不宣的“假樂”了:“具體來說,很多人都說我的父母變得比五年前、十年前更年輕了。尤其是我媽媽,身體比以前好,氣色也好,每天精力充沛、笑容滿面,以前她是三天兩頭受各種病痛折磨,吃很多藥,吃不下飯,看起來很可憐。這某種程度上也是個醫(yī)學(xué)奇跡。”
2022年春節(jié),是孫海洋一家14年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團圓年。
“我和弟弟的相處模式比較像是好朋友,畢竟算是同齡人,沒什么代溝,平時就是姐弟之間,吵吵鬧鬧的。父親和弟弟的相處有一些中國人特有的笨拙,含蓄些,但也很溫馨。”
“春節(jié),我記得大家一起準備年夜飯,孩子們一起洗蓮藕、貼春聯(lián)、放鞭炮、打雪仗,很幸福。”
第二個春節(jié),平凡和幸福都在繼續(xù)——2023年的大年初一孫悅?cè)沂窃诶霞叶冗^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我和兩個弟弟都在,還有大伯二伯、姑媽等許多親戚,非常熱鬧。從前過年其實也很熱鬧,但那種熱鬧多少有些表面,所有人心照不宣,不提團圓不團圓的,只是努力把日子過下去罷了。”
在接受《小康》·中國小康網(wǎng)專訪時,是在中秋前夕一個月,孫悅對這個傳統(tǒng)節(jié)日充滿期待:“今年的中秋節(jié),兩個孩子放假,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吃飯就好了,齊齊整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種平凡何其幸福。”
最近一年間,孫悅經(jīng)歷了蠻多有趣的事,感覺自己也長大了很多,接觸了很多以前讀書的時候接觸不到的人和事。“分享的話,我想到的是一個很不值一提的小變化。以前我的mbti人格是infp,主要特征是內(nèi)向和多愁善感,后來再測,我變成了enfp,但這一人格類型人稱“快樂小狗”。也很感慨,不僅僅是我的家庭改變了,沒想到我個人的性格和命運也改變了,或許一些看不見的齒輪也在悄悄轉(zhuǎn)動呢。”
孫海洋,尋子14年多,終得所愿。他奔走于全國各地,至今仍在堅持參與公益活動,幫助更多的人。
孫海洋在尋子路上堅持十四年多,這份父親對于兒子的愛,詮釋著勿失勿忘、帶愛回家的執(zhí)著,也揭開了許多普通人對于家庭與親情的所有堅守。而他永不放棄的力量也將帶動著我們奔赴生活的日常。正如孫海洋所言:“我奔跑的每一步,都是為了離你更近一步。”
《回家》的責(zé)任編輯程利盼認為:“將個體故事放到更為宏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能讓我們看到司法變革在時代中數(shù)次變革的步伐。在個體故事和時代變遷的交織中看到社會力量的推動:公安部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主任陳士渠、重慶市公安局的樊勁松警官、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嶸、《楚天都市報》的記者陳杏蘭、“寶貝回家”尋子網(wǎng)站創(chuàng)始人張寶艷、志愿者上官正義以及各地的公安機構(gòu)等,所有這些名字都和孫海洋等人多年的找尋之路,一起促成了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流浪兒童救助和管理制度,以及全國打擊拐賣兒童DNA數(shù)據(jù)庫等制度的完善,2016?年,“團圓系統(tǒng)”正式上線。2021?年,公安部部署持續(xù)深入推進“團圓”行動……”
《回家》由中信出版集團·無界工作室出版,既是孫海洋的漫漫尋子路,也是千千萬萬還在尋子中的普通家庭的縮影。在孫海洋一家團圓的“結(jié)局”之外,希望這個故事讓更多的人關(guān)注到仍舊在路上前行的尋找者。
現(xiàn)在,孫海洋仍在堅持參與公益活動,奔跑在幫助其他孩子回家的路上。無窮的遠方和無數(shù)的人都與我們相關(guān),這個世界也值得我們鼓起勇氣堅持對希望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