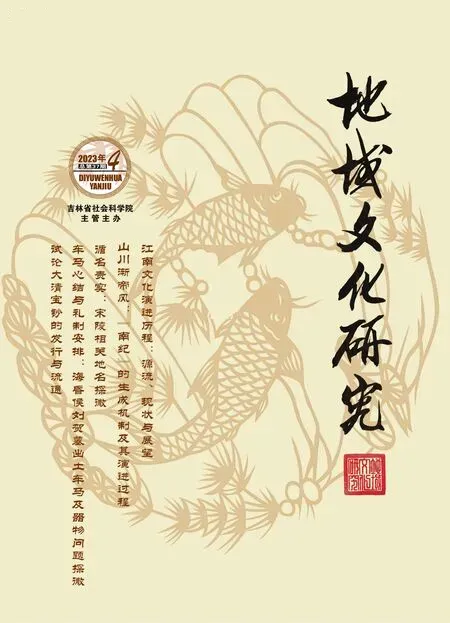車馬心結與禮制安排: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車馬及器物問題探微
王 剛
在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文物中,制作考究的車馬器備受關注。依據有關資料,相關器物分別出土于兩處,一是主墓西側的外藏車馬坑,“車馬坑為真車馬陪葬坑,出土實用高等級安車5輛,馬匹20匹。”二是主墓甬道兩側的車馬庫,對其出土器物的情況,最初認為是這樣的:“南側兩個車庫,發現了多部偶車以及隨侍木俑;甬道中發現了十分珍貴的三馬雙轅彩車和模型樂車,樂車上有實用的青銅錞于和建鼓,以及4件青銅鐃。”①江西省博物館編:《驚世大發現:南昌漢代海昏侯侯國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8 年,第20 頁、第22頁。但后來經過鑒定,其中兩件鐃應為鐲,它們與錞于,以及在甬道中新發現的一件甬鐘組合在一起,“為配套使用的樂器。”②王清雷等:《海昏侯劉賀墓青銅樂器測音報告》,《音樂研究》2022年第5期。
隨著劉賀墓車馬資料的逐漸披露,學界也對于相關問題展開了學術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大多圍繞著文物保護,以及相關器物,尤其是當盧等的歷史或藝術價值進行專門研究。③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蔡毓真等:《海昏侯墓車馬坑出土鎏金青銅當盧銅、錫元素遷移變化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黃希等:《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車馬坑出土車馬器研究性保護修復》,《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張紅燕等:《從海昏侯墓外藏槨出土車馬飾件的工藝統計看馬車類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宋姣、祝艷琴:《海昏侯墓出土的車馬器造型藝術研究》,《藝術生活》2017年第4期;章義和、陳俏巧:《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新出土當盧初探》,《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曹柯平、王小盾、徐長青:《海昏侯墓地符號世界:當盧紋飾研究》,《江漢考古》2018年第2期;江珊:《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西漢當盧研究——以三件青銅錯金當盧為例》,湖北美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等。這類研究當然有其意義,但倘要進入歷史文化的核心地帶,在以物見史中獲得新的見解,那么,一個不可繞過的層面是:禮制。質言之,漢代貴族的車馬是重要禮器,①劉增貴指出:“車作為政治社會地位的象征,在漢隋之間非常重要,尤其是古代鼎彝等器失去作用之后,其重要性更為凸顯。”見氏著《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秦漢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677頁。要考察劉賀墓的車馬隨葬問題,這一層面不可或缺。但以筆者目力所及,在相關研究中,禮制問題的討論大多散在各種片言只語之中,專題性的論文僅見2篇,②朱一、周洪:《海昏侯劉賀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禮制分析——以棺槨、隨葬車馬和琉璃席為對象》,載趙明、溫樂平主編《暢論海昏——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海昏歷史文化研究論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方良朱:《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偶樂車》,載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70輯,北京:中國書店,2019年。進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間頗大。
毫無疑問,對劉賀墓車馬器問題進行專題性的考察,對于理解西漢時代的政治文化及經濟社會的真實面貌,有著深入的意義及價值。與此同時,車馬又是劉賀極為鐘情之物。對于它們的研究,不僅可以深入到劉賀的內心世界之中,帶動墓葬考古等相關問題的研究,而且還連接著劉賀立廢前后的歷史走向及個人心路,對于昭、宣政治和劉賀的內在心理,亦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也就是說,劉賀本具車馬心結,對于車馬及相關器物有著不一樣的情愫。加之命運的跌宕起伏,在禮制安排之時,心路與往事往往交雜鼓蕩。延此理路細加觀察隨葬的車馬及器物,就可以發現,不管是出于劉賀的遺愿還是家人的安排,其間所透現的個人命運與禮制變化;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在在皆是,蘊涵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由此,以禮制的角度,歷史的眼光來展開相關研究,實為題中應有之義。下面,筆者就不揣淺陋,對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從“驅馳國中”到慨口之嘆:劉賀政治命運轉換視角下的車馬問題
劉賀墓出土的車馬及其器物屬于陪葬品。既然是陪葬,自然有著禮制要求,須遵從一定的規范。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與一般王侯不同,劉賀有著由王而帝;由帝而民,最后改封海昏的跌宕經歷。加之隨著劉賀的戴罪而歿,海昏侯國被除,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車馬及器物以何種規格下葬成為饒有趣味的問題,還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它們在劉賀生前使用過嗎?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為什么最后要將其隨葬?由于劉賀身份變化之巨,進行何等具體的處置,牽扯著種種力量的博弈,以及往昔與現實因素的交雜糾纏。
更為重要的是,劉賀在年少之時對于駕馭車馬極為癡迷。車馬,不僅伴隨著諸侯王劉賀度過了值得留戀的青春時光,甚至在立廢前后,從七乘傳赴京到在皇宮中“驅馳”游樂,既是劉賀一生的高光時刻,也是其命運轉換中極為重要的圖景。并經此轉折,墓主最終來到車馬難通的海昏侯國,郁郁地了此一生。可以說,車馬及其器物是劉賀墓葬禮制安排中的難點,它們不僅是充滿著溫暖感的重要載體,也承載著難堪的記憶,是劉賀的一大心結所在。由此,當它們隨葬之時,所寄托的意義就不是一般儀程所能限定,而應有著更為豐富的內容。也由此,對于劉賀墓出土車馬及器物的考察,就不能僅作由物及物的簡單討論,對墓主個人命運及心路歷程的考察,亦應納入視野之中。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可注意的是,當劉賀立而旋廢時,很重要的借口是違背禮制,即所謂“荒淫迷惑,失帝王禮儀,亂漢制度。”其中與車馬相關的“罪行”是:“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官、桂宮,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游戲掖庭中。”①《漢書》卷68《霍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44頁、第2940頁。這樣的罪行是否可以成立呢?劉賀所乘法駕為天子車馬,小馬車為皇太后所用器物,它們皆為宮中之物。作為新皇帝,一入宮中即以此驅馳游樂,或許在觀感上給人于不妥之感,但就禮制而言,似乎也不算太出格。
由此回到歷史的現場,可以發現,當劉賀在內宮“車九流,驅馳東西”之際,故臣龔遂曾對昌邑相安樂說道:“今哀痛未盡”,“所為悖道”,希望安樂能對劉賀的相關舉動加以規勸。②《漢書》卷89《循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38頁。然而,細繹龔說,并非是在指責劉賀違背漢制,而是認為他“悖道”,理由在于“今哀痛未盡”。也即是,此刻尚處于昭帝喪期,應表現得有所哀痛,而不應如此興高采烈地驅馳游樂。這種情形的發生,固然與劉賀的青春年少,喜好玩樂有關。加之昭帝并非親生父親,所以,雖然昭帝為先帝,但劉賀對于這位比自己稍微年長的叔輩,不僅沒有什么哀痛之情,發自內心的反倒是初登皇位的新奇與歡喜。稚嫩與不成熟使劉賀失去了自控,當然也在此后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在聽聞龔遂之言后,安樂為什么不去加以勸諫呢?或許在他看來,這也并非什么大過。在內宮之中,皇帝驅馳是一種正常之舉。至少在制度范圍之內,對其還沒有明確的法律限定。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劉賀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舉動呢?是以此來表達某種政治姿態嗎?答案是否定的。這樣的舉動,應該是個人愛好的延伸。
青年時代的劉賀是車馬游獵的愛好者,史載:“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對于這種“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以及“馳騁不止”的行為,昌邑中尉王吉曾加以力諫,并獲得了劉賀的“敬禮”,劉賀還為此表彰道:“中尉甚忠,數輔吾過。”然而,由于青年人的自控力不夠,最終結果是“其后復放從(縱)自若。”③《漢書》卷72《王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58-3061頁。
不僅如此,當漢廷以七乘傳征召劉賀入京即位之時,“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于道。”④《漢書》卷63《武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64頁。根據這段材料,王子今推算,“乘車的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45 至67.5 里”,“馳車速度可以超過騎者。”⑤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0頁。后來根據道路及尺度的實際情形,王氏又提出了幾種不同的數據,⑥參見王子今:《劉賀昌邑—長安行程考》,載趙明、溫樂平主編《暢論海昏——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海昏歷史文化研究論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4-235頁。但車馬速度之快以及御術之高超,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須知劉賀入京的隨從有200多人,這還不包括中途裁撤的50多人,昌邑王國車馬之盛、之精良由此可見一斑。
結合本論題,可注意的是,雖說劉賀因“驅馳國中”受到儒臣的勸諫,但那屬于“動作亡節”,并非實在的違制。如果劉賀在車馬問題上的“放縱”行為與禮制要求相差甚遠,他在繼承皇位時,就將失去合法性,至少受到漢廷巨大的非議,不可能這么順利地入朝。筆者曾經指出,霍光立劉賀為帝,與其年輕不更事有著巨大關系,為了繼續控制朝政,霍光不希望有一位成熟有實力的皇帝。⑦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身體與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見劉賀廢立及命運問題蠡測》,《史林》2016年第4期;拙文:《宗廟與劉賀政治命運探微》,《人文雜志》2017年第8期。或許當初立劉賀之時,這種“驅馳”反倒是霍光所看重的一面,是劉賀得以即位的加分項。所以,入京的車馬雖然繁盛,但未聞漢廷的勸諫之聲,至于皇宮中車馬游樂,或許正如王子今所指出的:“似乎是將‘馳騁’或說‘驅馳國中’的貴族游戲提升到更高的皇家消費等級了。”①王子今:《劉賀昌邑—長安行程考》,載趙明、溫樂平主編《暢論海昏——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海昏歷史文化研究論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7頁。綜合來看,以上種種本不足于構成霍光集團態度上的巨大轉換,從而對劉賀立而旋廢。也就是說,所謂的違制、違禮并非是被廢主因,而只是為了使劉賀下臺而羅織的罪名。
但是,當罪名成立之后,罷黜帝位的劉賀轉眼間已物是人非,車馬問題隨之成為一個微妙的存在。
查考史籍,劉賀被廢之后回到了昌邑王國,在長達十年有余的時間里,被軟禁于當年的王宮之中。史載:“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二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②《漢書》卷63《武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67頁。在荒草叢生的故王宮,劉賀成為身患“風痺疾”的病夫,也即所謂“疾痿”。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要與當年一樣再去驅馳車馬,自然是不可能之事,劉賀的病情,與禁足于此或許就有著某種關聯,是重要的致病之因。③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身體與政治:南昌海昏侯墓器物所見劉賀廢立及命運問題蠡測》,《史林》2016年第4期。
十余年后,獲得解禁的劉賀成為新的海昏侯,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被軟禁于王宮,看起來,他自由了。此刻,劉賀能像以往那樣再一次“驅馳國中”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查核史籍,劉賀被廢時,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財物皆與賀。”④《漢書》卷63《武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65頁。作為列侯的劉賀隨葬品如此之豐富,很大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昌邑王時期的物品被帶入了海昏。此點已為出土文物所證明,無須贅述。由本論題出發,需要提問的是,既然昌邑王國有著車馬之盛,劉賀是否將其悉數帶入了海昏呢?受限于材料,現在已無法復原全部的事實。但由劉賀墓出土的諸多車馬及器物,可以證明的是,劉賀在海昏應該有著駕馭車馬的權力及事實,這些車馬器物應大多來自于昌邑王國。關于這一問題,后面還會進一步展開,現在要解答的問題是,劉賀不再能恢復當年的車馬之盛,從而重現當年“驅馳國中”的原因何在。
揆之于史,不管劉賀帶了多少車馬及器物進入海昏,也不管他如何鐘愛這些物品,有兩大外在要素制約著車馬器物的使用。
一是身體條件。作為病夫,劉賀想一如當年“驅馳國中”,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環境的制約。與昌邑王國及京師長安不同,海昏侯國地處鄱陽湖畔,江南大片的水域環繞其間,這里的交通工具以舟船為主。尤其是在魏晉之前,江南一帶未獲得大開發,道路整治沒有大規模展開,車馬馳騁在此必然極受限制。由此,不要說劉賀,就是普通的北方人,慣于車馬驅馳之后,進入此地,因交通方式的轉換,皆會感到不便。在三國時代,著名的赤壁之戰發生時,孫、劉聯軍敢于抗衡曹操大軍,地理上的底氣所在,就是此地的舟楫之用成為北方大軍的短板,誠如周瑜所言:“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①《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61頁。
山川之變,影響著劉賀的出行。車馬之盛只能在昌邑王國起作用,在海昏侯國,它們難有用武之地。不僅如此,劉賀入居此地,大水圍城,可謂形同禁錮。
《水經注》卷三九《贛水》載:
又有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東徑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徑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②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訂:《水經注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22頁。
所謂的“慨口”,是否因劉賀之嘆而得名,非本論題所關注。但這一名稱所折射的地理狀況,形象地反映了劉賀的微妙處境。從特定視角來看,較之此前被禁錮于昌邑王宮,海昏侯國不過是擴大了的幽禁之地。這樣的情形得以發生,當然不是偶然,而應該是漢廷的有意安排,以天然形勝控制住劉賀是核心要義所在。劉賀之嘆是否發生雖不可考,但其內在的憂憤是可以想見的。
有了這樣的安排,當然也就限制住了劉賀的車馬馳騁。更重要的是,它還帶著某種政治的暗示。也即是,安分守己地待在水邊。如果劉賀不甘心于此,在海昏侯國城內大肆“驅馳”,則無疑有著示威和不滿的意蘊。智力稍微正常者,都將收斂此種行為。更何況,劉賀入居海昏之后,以避禍為基本態度。在出土的孔子衣鏡中,劉賀明確表示:“修容侍側兮辟非常”③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此后在海昏的日子里,總的來說,劉賀小心謹慎,但最終還是因為一次私人談話,而遭到削戶之懲,最終抱憾而終。④《漢書》卷63《武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69-2770頁。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要謹守禮制,以深自抑損為常態。在這樣的情勢下,當年在昌邑的車馬即便悉數運至海昏,也不過是用來滿足一般的車乘需要,由于為帝、為王的經歷,在沿用舊物時或許會有某些身份性的突破,但絕不可能招搖過市。或許它們大部分就存于庫房,成為劉賀流連追憶的物事。
在這樣的心態下,隨葬的車馬及器物就不會只反映著列侯的規格,它們應包容著此前為帝、為王時代的若干內容,在生前難以實現的夢想,也或許會通過地下的陪殉加以曲折展現。這些車馬器物可延展至昌邑王時代,成為劉賀及其家族抒發憂憤的載體。
二、車馬器物的性質、來源及相關問題
眾所周知,劉賀墓中的車馬及器物屬于陪葬品。但倘細加分析,接下來的問題則是,它們屬于什么性質的陪葬品?有哪些類型呢?又是如何來到海昏侯國,直至隨葬于地下的呢?對于這些相關問題展開有針對性的解讀,有助于出入器物之間,對其所蘊涵的歷史文化問題獲得進一步的理解。
由前已知,相關車馬及器物出土于兩處,一是車馬坑;二是主墓甬道兩側的車馬庫。其中,前者為真車馬,作為生前的實用器,依據“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入葬于地下。而后者的主體——偶車馬是專為陪葬而制作的明器,與之配套的金、鼓則是實用器。也就是說,兩處器物的性質有所不同,一是車馬坑中的生器;另一類雖有生前實物加以匹配,但總的來說為明器性質。明器問題可先置而勿論,在此所聚焦的問題是:那些在劉賀生前所擁有的車馬器物屬于什么性質?來源于何處呢?在筆者看來,它們應該是劉賀的私人物品,來自于昌邑王國。它們隨葬于地下,一方面反映了劉賀生前用具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故王與今侯的身份重疊,也造成了禮制層面的某些沖突與包容。不了解這些,在進行必要的研判時,就會造成困擾,甚至是誤判。下面,來進行具體的分析。
循著以上的問題意識來再審車馬坑的隨葬狀況時,可以注意到如下的現象,
一是:隨葬的5 輛木質彩繪車,都是生活中實用的高等級安車。陪葬的20匹馬,都是宰殺后完整埋入的,骨架已經腐朽成泥。馬車在埋入的時候經過了拆解,被拆卸下的車馬器裝入彩繪髹漆木箱內,放置在槨底板上。
二是:制作極其考究,器物上錯金銀、包金、鎏金等工藝復雜,與《后漢書·輿服志》所載“龍首銜軛”、皇太子、皇子所乘“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虡文,畫轓文辀,金涂五末”的“王青蓋車”相似。①江西省博物館編:《驚世大發現:南昌漢代海昏侯侯國考古成果展》,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8 年,第60 頁、第61頁。
將這兩種現象加以綜合考察,可以確認,隨葬車馬及器物的確是劉賀生前所用實物,而且來自于昌邑王國。理由在于:
1.現象一所反映的是葬俗中的拆車葬,它的核心寓意是,將生器的功能加以消解,完成它在世間的最后任務,從而隨侍主人于地下。
關于拆車葬問題,練春海有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這一“在西漢中期已經進入尾聲”的葬俗在先秦時期已經產生,在北方地區具有“悠久的傳統”。“拆車”的思想源頭有可能是“生器文而不功”。也即是,當生器隨葬之后,其在世間的作用已經完成,在消除其原有的實際功用的同時,凸顯喪葬禮儀的一面。不僅隨葬真車馬如此,沿此思路,甚至在漢代圖像中亦可見所謂的“無輪”之車,所反映的正是與拆車葬的關聯。在練氏看來,“‘無輪’也可視為‘拆去了輪’,是對拆車葬禮儀的圖像式繼承。”②練春海:《漢代車馬形像研究——以御禮為中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0-165頁。當劉賀下葬時,其家族沿用這一葬俗,一方面是對北方傳統的延承;另一方面,在對車馬功能的消解中,或許還有著別樣的心境與態度。
筆者注意到,在巨野紅土山西漢墓中,隨葬車馬有“木車一輛、生馬四匹和大量銅車馬飾。”③山東省菏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此墓地處漢代昌邑王國一帶,根據性質和規模,學界一般認為,這很可能是第一代昌邑王——劉賀父親劉髆的墓地。雖然它們都是真車馬陪葬,但較之劉賀墓的隨葬物,此墓中的陪葬數量及質量都不可并論。那么,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
就生器的價值功用而言,除了陪葬,遺留子孫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選擇。相較之下,紅土山漢墓的“寒酸”或許就有這樣的考量,也即是,多留些給在世的親人。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海昏侯國迷茫的未來與昌邑王國尚有期待不可同日而語。劉賀死后不久,兩個可以接位的兒子接連去世,漢廷由此廢去了海昏侯國,根據現有的資料及研究,“當年劉賀父子葬儀中,是先行葬埋了劉賀兩子,然后再埋葬劉賀的。”①張仲立:《海昏侯劉賀墓園五號墓初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4期。由于無人接續爵位,倘嚴格按照禮制要求,列侯以上的車馬及器物無人再有使用資格。毫無疑問,當給劉賀最后下葬時,國除子亡,幾乎看不到希望,處在極為絕望的氛圍之下。再說劉賀的車馬故事中所留存的并非是赫赫往事,而有著屈辱不堪的過去。既然這樣,他的家人們又何必大量地留存它們呢?將這些作為傷心載體的車馬及器物大量隨葬于地下,也就不難理解了。
2.這些車馬器物的精美及品級,不是海昏侯這一級別所應擁有的。研究者認為,這些器物與皇子所乘車馬有相似性,而我們則以為,這種品級的器物,應是在劉賀為昌邑王時代所具。就當時的政治情形來看,劉賀雖位居列侯,但依然有著罪人的標簽,甚至參與宗廟之禮的資格都被排除。②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宗廟與劉賀政治命運探微》,《人文雜志》2017年第8期。由此而觀,這些器物不可能是在劉賀成為海昏侯時所制作或賜予,只能是由昌邑帶來。也由此,我們注意到了信立祥的一個分析:
“這批車馬文物,可分為實用車馬和偶車馬兩類。實用車馬出土于外藏槨,共有五車二十匹馬,應皆為駟馬安車。同出的3000余件車馬銅飾件,相當一部分有華麗的錯金銀圖像,其精美豪華令人嘆為觀止,遠遠超過富平侯張安世墓所出的同類器物。可以斷言,這種貴族專用的高等級用車,肯定是劉賀為昌邑王時所使用的。”③信立祥:《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的價值及意義略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信氏所論,其基本依據是,器物的精美不符合海昏侯的身份,而只能匹配昌邑王的規格。這樣的推斷是可以信服的。但倘深入于劉賀家族的心態之中,又可以發現的是,將當年念茲在茲的車馬及器物隨葬于地下,并以拆車葬加以執行時,或許也是對昌邑王時代及劉賀夢想的一個消解。
前已論及,因海昏侯身份及政治限制的存在,可以推斷的是,相關器物不可能產自于海昏本地,而應該是“為昌邑王時所使用”。加之江南少有良馬,聯系到當年昌邑的車馬之盛,與相關器物一樣,馬匹很可能也都是由昌邑轉運而來。但前又論及,不僅因身份所限,以身體及地理狀況而言,并不適合劉賀在此驅馳車馬。那么,劉賀何以要將它們轉運至大澤之畔呢?除了鐘情和留戀的情感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條乃在于,他希望這些故物可以在日后派上用場。
但這些精美的車馬器物在海昏侯國具體如何使用呢?是經常使用,還是鎖在大庫之中?使用頻率有多高?這些細節都不得而知。尤為重要的是,如果依據嚴格的禮法,作為列侯,使用這些器物似乎還頗有些僭越之嫌。在這樣的思路下,有學者在對漢代相關墓葬情況作分析比較之后,認為:“比較以上考古成果,劉賀墓的車馬具裝飾級別也更與諸侯王的規格相符,明顯超過列侯。”“海昏侯劉賀在喪葬儀節的關鍵之處還是謹守禮制的,如棺槨的數量和斂服;但是在有操作空間之處如車馬飾,則有逾制之舉。這說明劉賀一方面還是在頑強地表現曾經的天子榮耀。”④朱一、周洪:《海昏侯劉賀墓部分出土文物的禮制分析——以棺槨、隨葬車馬和琉璃席為對象》,載趙明、溫樂平主編《暢論海昏——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海昏歷史文化研究論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2頁、第310頁。“與諸侯王的規格相符”云云,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些器物真的“逾制”了嗎?如果真的這樣,它們何以會存在“有操作空間之處”呢?難道棺槨、斂服等就不可以擠占出“操作空間”嗎?如果認為棺槨、斂服等聯結著“關鍵之處”,難道車馬及器物就不關鍵嗎?
事實上,車馬及器物也是禮制的關鍵依托。只不過當它們延伸到生前之禮的范疇時,與棺槨、斂服等限定在列侯的禮法系統中不同的是,車馬器物的制度安排可由列侯突破至諸侯王的規格。也就是說,在劉賀的禮制安排中,尤其是在禮器的具體使用中有兩種類型,一是成為海昏侯之后,所制作使用的匹配禮器,它們當然屬于列侯一級的物品。二是延承諸侯王時代的禮器,在使用中“王氣”依然,與現有身份之間有著某種距離。以這樣的思路來加以觀察,可以說的是,禮制并不都是硬性指標,它也有軟性之處。如果說這里面存在操作空間的話,操作空間本身其實也是禮制精神的一部分。落實到本論題則是,劉賀“故王”的身份為其提供了繼續使用“故物”的便利及權利,這的確不是常態下的情形,但嚴格說起來,它并不逾制違禮。
由前已知,當劉賀被廢時,皇太后曾下令“故王家財物皆與賀。”①《漢書》卷63《武五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65頁。這是劉賀擁有大量財物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他的很多金銀財寶都是當年昌邑王時代的留存,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他父親留下的財富,對于這些物品的擁有,使其財氣十足。不要說作為列侯的劉賀,就是在封侯之前,作為平民的他都依然享有當年諸侯王所有的種種物權。質言之,在劉賀的種種身份中,諸侯王是不可忽略的一面。因為它的存在,在廢黜之后,無論為民還是為侯,劉賀可憑借“故王”的身份擁有和使用“故物”,相應的禮器由此就屬于可享用范圍。落實于本論題中,車馬器是禮器的一種,作為“故王”之物被帶入了海昏,根據曾經的“故王”資歷及朝廷的特許,劉賀可以使用它們。倘僅僅停留于僭越層面去作單線觀察,就會失之于簡單。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畢竟屬于非常態的情形,多多少少有些名不正而言不順。而且如果一直使用這種規格的車馬器物,也容易招來猜忌及禍患,對于力求避禍的劉賀來說,在使用這些車馬器物時,必然處在尷尬和謹慎的狀態之下。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可注意的是,在劉賀墓中出土了一枚“海”字銅印,相較其他印章,它明顯大了不少,無論是形制、印文還是印紐,與一般漢代官印很不一樣。后曉榮敏銳地發現,“‘海’字印不是一般的漢代官印”,而是“一枚西漢烙馬印。”他進一步指出:“漢代烙馬印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往往冠有地名或全稱或省稱。這枚‘海’字印中‘海’字實際為‘海昏’省稱,就是一枚典型的省稱印章。”“海昏侯生前養馬不少,‘海’字印實為海昏侯實施馬政管理之物。”②后曉榮:《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研究三則》,載江西師范大學海昏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縱論海昏——“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暨秦漢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1-123頁。
對于這一結論,筆者表示贊同。但需要補充的是,烙馬印在省稱中,往往會保留完整的地名,而且還往往會將馬廄或官名補上。③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6期。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著名的漢代王侯烙馬印——“靈丘騎馬”印。陳直曾作過這樣的分析:
靈丘騎馬《雪堂藏古器物簿》金二,十一頁。“原物系烙印,按靈丘屬代郡,騎馬令屬太仆,可能系文帝為代王時,或趙隱王趙幽王所置騎馬令烙印之物。因文帝封代王,疆域的范圍不詳,靈丘在戰國時屬于趙地。以上封泥及印文,皆王國自置的屬官。”①陳直:《漢代的馬政》,氏著:《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6-327頁。
由上可知,“靈丘騎馬”印也是烙馬印,但名稱較完整,可以看出屬地與屬官。在昌邑王時代,應有著類似的情形。也即是,在昌邑王國應該有負責馬政的官員,也一定會有相關的烙馬印。但這些器物都沒有在劉賀墓中出現。它們是沒有帶入海昏,還是被劉賀所丟棄,現在已不得而知。但由“海”字印可以知道的是,劉賀重制了印章,以作為馬政管理之物。由此還可以知道的是,雖然車馬及器物可以轉運而來,但在馬政管理方面應該進行了重建,原有的規格及人員應該不再至少不能全盤保留。
甚至筆者懷疑,海昏可能沒有官家性質的馬廄及馬官。一則這里的地理條件不適合養馬,像北方那樣大量設置馬廄及管理人員,不太符合實際。二則,更重要的是,既未見官方烙馬印,“海”字印亦與官印不相符合,這其實乃是一枚私印。也即是,劉賀在對自己的私人馬匹做管理時,以此印為依憑。進一步言之,這些馬匹及器物乃是作為故王之物轉運而來,但就海昏侯的身份而言,并不具有匹配諸侯王品級的官方管理機構及人員。對于這些車馬及器物,劉賀應該是以私人財物的性質來加以管理和處置。由此,烙馬印呈現私人性質。②吳方浪也認為“海”字印為私印。但由于認定漢代的烙馬印皆為官方印信,由此在否定后曉榮主張的基礎上提出:“退一步講,如為海昏侯管理馬政之物,作為日常行政管理印信為何不留給下一代海昏侯繼續行馬政使用,而是選擇隨葬于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墓中。”(氏著:《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銅印考釋》,《文博》2019年第1期)然而,故王之物的特殊性,使得劉賀能夠以私印來進行馬政管理,這是一種特例。
而且,需要進一步注意的是,印章簡單到只有一個字,或許反映著劉賀對于海昏侯身份的不認可。對于劉賀來說,他的夢想是“南藩”身份,海昏侯只是一個過渡,在此地成為豫章王,才是最終的夢想。③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宗廟與劉賀政治命運探微》,《人文雜志》2017年第8期。從這一視角來看,這些車馬器物終究不是海昏侯所應有的用具,它們是為豫章王隆重登場而進行的準備。待到那時,禮法尷尬得以消解,才算在名正言順中完成了人生之夢。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我們就能理解“海”字烙馬印的特異。它后面所呈現的,應該是劉賀的政治期待。然而,歷史不僅沒有給劉賀這個機會,甚至最后削戶受責,直至身亡國除。當劉賀下葬之時,以拆車葬的形式加以處理,就不僅是對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是諸侯王之夢的徹底消解。破碎的希望及絕望的心境,伴隨著車馬及其器物的下葬,從官家之物到私人器物,從昌邑到海昏,掩埋了榮光和辛酸,也塵封了一段歷史……
三、“安車駟馬”與“五馬”問題
依據多年的考古成果及發掘資料,對于西漢的車馬陪葬問題,學界一般認為:1.“從目前所發掘的墓看,只有諸侯王一級的才有大型實用真車馬,列侯以下未見。可見真車馬的殉葬體現了諸侯王的身份等級。”2.“西漢諸侯王墓基本以殉葬3 輛車馬為定制。”④高崇文:《西漢諸侯王墓車馬殉葬制度探討》,《文物》1992年第2期。但劉賀墓的情形打破了以上兩個結論。前已論及,劉賀墓葬中的車馬器物來自于昌邑王國,屬于諸侯王規格。但因劉賀特殊的身份,這種對于列侯規制的突破,可視為合規的變例。白云翔在細審相關車馬器物之后,也明確提出:
制作極其考究,與《續漢書·輿服志》所載“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虡文,畫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為王,賜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中的“王青蓋車”相似。看來,劉賀是把他做昌邑王時的車馬用來陪葬了。①白云翔:《西漢王侯陵墓考古視野下海昏侯劉賀墓的觀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昌邑王時代車馬繁盛,絕非只有這些物品。那么,車馬坑中的隨葬品是出于何種目的而被挑選出來的呢?它們具體屬于何種性質的車馬呢?又何以隨葬了5輛呢?白云翔認為,由于劉賀曲折的經歷及悲劇性的結局,臨終前無疑充滿了憤懣、憂郁、無助、無望之心。也正是這樣的心結,加之劉賀死后朝中大臣“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使得劉賀去世后埋葬之時,將其生前所有幾乎全部進行陪葬,隨他而去。車馬鐘鼓如此,金銀財寶如此,奏章副本等統統如此。②白云翔:《西漢王侯陵墓考古視野下海昏侯劉賀墓的觀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這樣的分析在大體上可以成立。但落實到本論題,有些細部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討論。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幾乎全部進行陪葬”,不代表劉賀的所有物品都隨葬于地下,其間有著一定的挑選空間。而且由前可知的是,在車馬坑中“出土實用高等級安車5輛,馬匹20匹。”劉賀不可能只有20匹馬,也不可能擁有的車型如此統一規整——5輛實用高等級安車。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車馬配置,正好是一車四馬,即所謂“安車駟馬”。筆者以為,這屬于當時的一種車制安排。這一安排,也即所謂“五馬”出行——以五輛“安車駟馬”構成一組系列。
所謂安車,為坐乘之車,或因其行進中安穩之故,被稱之為安車。③《漢書·霍光傳》載:“韋絮薦輪。”顏注引晉灼曰:“御輩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并進一步解釋道:“取其行安,不動搖也。”使車安穩而行,是當時的重要考量。《禮記·曲禮上》載,當臣下年歲大了之后,君主“則必賜之幾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鄭玄注曰:“安車,所以養身體也。”又曰:“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清儒孫希旦亦云:“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④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5頁。但沿著鄭玄的解釋系統,將安車等同于小車,或許只是先秦時代的事情。在西漢,除了包括劉賀墓在內的出土實物可以對其形成反證,與本論題相關的一個文本證據是,“安車駟馬”是漢廷的重要賞賜物。例如,僅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在昭、宣時代以來,朝廷對于致仕官員的“安車駟馬”之賜就有10 次。但孫機指出:“漢代的小車并不駕四匹馬。”也就是說,作為當時的一個標配,四匹馬的“駟馬”所匹配的是大車。由此,西漢時代的安車并非就是小車,更多的或許還是高大的,配以四匹馬的車型。不僅如此,這種“安車駟馬”更代表著身份與品級。孫機進一步指出,在孝堂山石祠所刻的出行圖中,榜題所謂的“大王車”,“是自圖像中見到的漢代最豪華之車”,“應為諸侯王所乘之安車。”⑤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頁、第114頁。而現在實物對應的“大王車”,則是劉賀墓車馬坑所見之物了。也就是說,“安車駟馬”是體現諸侯王身份的重要載體。
但劉賀墓出現“安車駟馬”,不僅僅是為了凸顯曾經的諸侯王身份,或許更出于現實的選擇,以及“循禮”的政治要求。考察劉賀的過往,此種車型并非其年少時所慣乘。因為當劉賀馳騁于昌邑王國時,臣下曾有這樣的勸諫:
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①《漢書》卷72《王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59頁。
在這番話中,固然包含著禮制層面的規勸,希望劉賀的行為更符合諸侯王的身份,并為許多年后“修容侍側兮辟非常”提供了歷史的教訓。但就本論題出發,更值得注意的是“馳騁不止”所帶來的身體傷害。前已論及,劉賀患有“風痺疾”,致病之主因,固然在于政治的禁錮及身外環境的惡化,但年少時的“馳騁不止”是否也是早期病因之一呢?對于這樣的問題,罹疾之后的劉賀不可能不做出某種反思。
由此來考察安車的功能,可以發現,安車之“安”,不僅僅在于安穩,還有著抵御風寒的作用。《鹽鐵論·取下》曰:“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之危寒也。”②桓寬撰集,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63頁。質言之,保暖御寒是其重要功能。這一功能,正契合著海昏時代劉賀的身體狀況。相較之下,由“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云云,可以推知,劉賀在昌邑所乘之車,絕不是那種既安穩,且御風寒的安車。它們速度快,十分拉風,很是符合年輕人的個性。然而,事過境移之后,劉賀早就不是那個可以“冒霧露”“被塵埃”,飛揚青春于疾風快馬中的少年王,他是一名需要安養的病夫。
也就是說,來到海昏之后,防范病情的進一步加劇成為極為嚴峻的問題。如果還像年少時那樣“驅馳國中”,且不說在海昏侯國行車不便,在潮濕的環境中,“為風寒之所偃薄”的風險也是難以承受的。年少時能盡情驅馳,那時可以將“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不放在心上,但海昏侯國的病夫,豈能受得了此種折騰?更何況,通過“修容侍側”以低調避禍,是當時的言行方針。用諸侯王車馬之物、車馬之禮,雖然有著制度及政治的許可空間,也是劉賀的心結所在,但畢竟其間還有著種種沖突和尷尬,現在倘再駕駛著快馬之車,于身體;于禮制方面的避禍,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綜合以上的各種要素,可以肯定的是,以“安車駟馬”緩緩出行,而不是快馬疾馳,當成為劉賀在海昏侯國的常態。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劉賀墓為什么不以3 車加以隨葬呢?在論及3車隨葬的這一“規律”時,甚至有學者還特意對劉賀所在的宣帝時代加以強調:“皆殉葬3輛車,尤其是宣、元時期的諸侯王墓無一例外。”③高崇文:《西漢諸侯王墓車馬殉葬制度探討》,《文物》1992年第2期。由此而論,劉賀墓葬的情形會是一個特例嗎?
以3 車隨葬的事實多有出現,當然值得高度重視。但另一面的事實是,除了劉賀墓之外,紅土山漢墓以1車隨葬,文帝時代的臨淄齊王墓以4車,武帝時代的滿城漢墓以6車、4車隨葬,3車隨葬從來就沒有一統天下。限于材料,3車隨葬是否為當時的基本規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由本論題出發,更需要注意的是,3 車隨葬時,車型往往并不統一。劉尊志說:“車馬器方面,西漢早中期的車馬器組合較為復雜,特別是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階段達到鼎盛,一墓之內有多種類型的同一車馬器。”④劉尊志:《西漢諸侯王墓陪葬車馬及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13年第4期。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上,對于3車隨葬的原因,學界往往認為:“西漢諸侯王墓中的3車多是精粗不同、所配馬匹多寡各異,反映了3車有主次之分,與先秦乘、道、槁3車的情況大體相似。”⑤高崇文:《西漢諸侯王墓車馬殉葬制度探討》,《文物》1992年第2期。
但這樣的功能劃分,不符合劉賀墓的情形。與所謂的“乘、道、槁3車”不同的是,隨葬車馬坑中都是統一的駟馬安車,當這樣的車制出現時,展現的是出行時的狀況。也就是說,因目標及功能的差異,劉賀墓無須遵循3車的葬俗。更重要的是,當這樣的一支車隊出行時,“五馬”,即5輛馬車往往是重要的獨立單位。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由詩歌《陌上桑》所云的“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為切入口,來進行討論。作為樂府名篇,中國人對于《陌上桑》大多耳熟能詳。但是,為什么使君是“五馬”呢?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使君”為高級別的刺史,他所乘坐的是五匹馬所駕馭之車,與六馬駕馭的帝王車駕稍有區別。但問題是,無論是文獻還是實物,皇帝以下的諸侯王等往往是以四馬來駕車,也即所謂“駟馬”。五匹馬所駕的馬車,并沒有禮制及實物材料的佐證。閻步克經過深入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詩歌主角實際上是一個帶有出使任務的小官吏,反映的是小人得志的嘴臉,也即是:這個“五馬”非必“一車之馬”,更可能是“一隊之馬”;基于漢代使者制度和傳車制度,那位“使君”不妨推定為謁者、郎官或掾史之類的低級使者,即秩級三百石上下的官吏;不管其車隊如何構成,不管有幾輛車、幾名騎從,總之一共五馬。①閻步克:《樂府詩〈陌上桑〉中的“使君”與“五馬”——兼論兩漢南北朝車駕等級制的若干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2期。閻氏所論理據充沛,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在閻說的基礎上,可以發現的是,劉賀墓的情形正與“五馬”之論相映證。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陌上桑》的主角作為低級官吏可以趾高氣揚,乃在于“五馬”是一種高規格的車制,我們以為,它就是“安車駟馬”之制。依據有關學者的研究,這種“安車駟馬”的駕乘者主要有五類,1.封王;2.封公、列侯;3.二千石以上大吏;4.受到特殊禮遇的長者與賢者;5.使者安車。②李強:《安車與車輿制度》,《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6年第1期。前四類身份高貴,而使者無此身份,不過是因為銜王命而得以附驥其間,這正與《陌上桑》“使君”云云的譏諷語境相契合。
而且,車制以5為單位,本就具有悠久傳統。按照禮典,先秦時代王車有所謂“五路”之制,漢代沿襲和發展這一傳統,還有著所謂的“五時車,安、立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的規定。③《續漢志·輿服上》,《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44頁。依據這樣的記載,安車中有所謂的五時車,也即五色車,按照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的顏色——青、白、赤、黑、黃來對應5乘車馬。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我們注意到,車馬坑的器物在顏色上也有著一定講究,研究者指出:“海昏侯墓外藏槨出土車馬飾件雖然都疊壓混雜在一起,但是根據已有的同一輛車是同一種裝飾工藝的現象,初步推測海昏侯墓外藏槨中應有一輛錯金銀工藝馬車,有一輛黃色通體鎏金馬車,有一輛白色通體鎏金銀合金馬車,有一輛是銀質馬車。也可能還有雙色鎏金和縫隙鎏金工藝的馬車。”④張紅燕等:《從海昏侯墓外藏槨出土車馬飾件的工藝統計看馬車類型》,《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這樣的色彩配套是否有著一定的內在要求,并與“五色”有關,因材料所限,現在還不得而知。但五車或五馬之制的存在,應是不爭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一個車制現象。
四、偶樂車及相關問題
與車馬坑中的實用器不同,在劉賀墓室中,還出土了明器性質的偶車馬。
信立祥指出:“偶車馬分為偶軺車和偶樂車。”“軺車是一種級別較低的立乘小車,駕一馬,可以個人擁有,在高官貴族的車馬出行隊列中只能作為導車和從車使用。兩輛樂車中,一輛為載有實用建鼓的鼓車,另一輛為載有實用銅錞于和銅編鐃的金車。”①信立祥:《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的價值及意義略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根據這些材料,有學者將劉賀墓的車馬文物分為三類,一是車馬坑中的實用車馬器,第二類是偶軺車及相配套的隨侍木俑,“推測此處的軺車應為劉賀出行的導車或從車,隨侍木俑應象征著隨行人員。”第三類則是兩輛偶樂車,屬于珍貴的三馬雙轅彩車和模型樂車。②方良朱:《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偶樂車》,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70輯,第81-82頁。
車馬坑的問題在前面已經作了討論。當聚焦于偶車馬問題時,可以發現的是,對于偶軺車的爭議不大,但對于偶樂車問題,則往往見仁見智,后面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那么,偶樂車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器物呢?為什么會隨葬于地下?有哪些相關問題呢?
《周禮·地官·鼓人》載:“以金錞和鼓。”鄭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訓》曰:“兩軍相當,鼓錞相望。”《廣雅》則曰:“以金鐃止鼓。”根據這樣的文本,結合出土情形,信立祥認為:先秦時期,鼓與錞于、編鐃相配,用于軍旅中,在行軍作戰時,指揮軍隊進退,屬于軍禮樂器。擊鼓進軍,擊錞于和編鐃止鼓退軍。劉賀將這種軍禮樂車用于出行,顯然是借用了軍禮。劉賀墓出土的這些車馬文物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漢王侯貴族的出行車隊:王侯乘坐的主車即駟馬安車居中,最前面以數輛軺車為導車,導車之后、主車之前為鼓車和金車,主車之后為以數輛軺車為從車。擊鼓則車行,擊錞于和編鐃則車停。當然,實際的西漢王侯車馬出行隊列要復雜得多,還要加上等級較高的屬官的屬車和大量的騎卒及步卒。③信立祥:《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的價值及意義略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接續這一觀點,方良朱肯定了偶樂車為“出行的軍禮樂車”之性質,進而認為:“這兩輛偶樂車實際上代表著先秦兵車‘王之五路’中用于軍事指揮的革路。”并據此引申道:“革路隨葬,應該有著特別的意義。一方面,它象征著使用者身份的尊貴。另一方面,將本用于軍事指揮中的革路隨葬,似暗示著廢帝劉賀后半生始終郁郁不得志,希望在另一個世界稱王稱霸、征伐四方的心愿。”④方良朱:《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偶樂車》,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70輯,第81頁、第82頁。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深入于劉賀當時的處境,再結合相關出土文物細加詳考,可以發現的是,這樣的結論不易成立。偶樂車的關鍵所在是樂,或者說,它們是表現王者之樂的載體。金鼓固然可以和軍禮發生若干聯系,但落實于劉賀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它們不僅不能是,至少核心所在,不能指向于軍禮。因為劉賀的特殊身份,與軍事相關者乃是政治禁忌所在,在墓葬時是需要加以提防和回避的要素。至于說“稱王稱霸、征伐四方”云云,則不僅是極為忌憚之念,倘真如是,那簡直是不將朝廷放在眼里了。
回到歷史的現場,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劉賀作為曾經的帝王,廢居于海昏侯國,身邊都是監臨的耳目。因為這樣的緣故,一言不慎,就被削戶受懲,最終郁郁而終。在劉賀墓出土的《海昏侯國除詔書》中,漢廷對“飲酒醉歌”以及鼓瑟都嚴加切責,將其作為“無恐懼之心”,“不悔過自責”的罪狀。①楊博:《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海昏侯國除詔書〉》,《文物》2021年第12期。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劉賀的家人應該是惶惶不安的。怎么會,又怎么敢突顯軍事方面的元素呢?難道劉賀的家人們要挑戰漢廷權威,置自己于死地嗎?即便如此憨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漢廷也不可能讓他們得其所欲。可注意的是,在其他諸侯王的隨葬車馬中,往往還有著各種武器,以及狩獵的獵犬等。例如,“從劉勝墓的6 輛車可以看出,基本是其生前出門的乘輿狩獵或征戰用的車,車上配弩機、承弓器、配刀等武器。車隨從大批狩獵用犬,犬也佩戴絡頭銜鐮、頸牽鐵索隨車前后十分壯觀。”②鄭灤明:《西漢諸侯王墓所見的車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六號車旁3 匹馬中2 匹可能為戰馬,另外1匹及其他車旁的馬則基本為牽引挽乘的畜力。”③劉尊志:《西漢諸侯王墓陪葬車馬及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13年第4期。也就是說,軍事及田獵之物往往伴隨著車馬一起出土。但這些器物在劉賀墓的車馬陪葬物中未見蹤跡。
所謂事死如事生。陪葬物所反映的,其實是墓主的生活鏡像,至少以其為藍本來加以附會或拓展。那么,劉賀生前不喜這樣的勇武風格嗎?當然不是。由前已知,當他以快馬驅馳于昌邑國中,招致“動作亡節”的指責時,正是由其“好游獵”的習性所驅使。依此而論,與劉勝墓一樣,在劉賀墓中,武器、戰車、獵犬等也應一一出現于車馬之旁。但它們都消失了。為什么呢?除了海昏侯國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避禍的需求,為了生存,劉賀只能遠離它們,這是相關物品在出土物中缺席的核心原因。
要之,我們并不徹底否定金鼓相配的軍事意義。但它們的出現必須符合劉賀當時的處境,這樣的物品不能直接指向于軍事層面,否則就有了挑釁漢廷的意味,這是基本的大前提。那么,劉賀墓中何以要出現這樣的樂車呢?由前已知,按照信立祥的思路,它有著“用于出行”的寓意,并“借用了軍禮”,而且,墓室中的車馬與車馬坑中的器物可以組合為一個系列,也即是:“劉賀墓出土的這些車馬文物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漢王侯貴族的出行車隊。”依此而論,金、鼓相配,加之安車駟馬,反映了劉賀生前浩浩蕩蕩的出行場面。
但我們的問題是,如果它們原本是一個整體,為什么要分而置之?難道樂車不可以并入到車馬坑的“安車駟馬”之中嗎?
筆者以為,將這些車馬器分置于兩處,并非是隨意為之,而是因類型的不同所造就。進一步言之,作為車馬器,它們都與出行有關,但車馬坑中的安車駟馬是實際生活的寫照,而在墓室之中的器物或許只是一種寄托,并非是實際生活的反映。理由在于,墓室中的車馬是以明器模式出現,而不是真車馬,它們本來就是專用陪葬物。尤為重要的是,作為實用器的建鼓和青銅錞于及青銅鐃、鐲等,與明器性質功能有別,它們本可以在車馬坑中與安車駟馬相配。但它們移之于明器之上的情形正可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它們或許并沒有得到實際的運用。
史載,漢初名臣陸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④《史記》卷97《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由此可知,安車駟馬配之于金鼓之樂,是一個很有牌面的事情。另外,當劉賀在短暫為帝之時,曾“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官、桂宮,弄彘斗虎。”①《漢書》卷68《霍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40頁。由此亦知的是,這樣金、鼓齊鳴的場面不僅是劉賀當年的常態,由“引內昌邑樂人”云云,更可知的是,他在為昌邑王時,就有“擊鼓歌吹”“擊鐘磬”的樂人為之服務。那么,在進入海昏之后,如果劉賀要繼續維系這種排場,鐘鼓及樂人就可以一并南下,與陸賈一樣,從于安車駟馬之后,作為出行的常態。但是,它們終究移出了車馬坑,而與明器放置在了一起。這不是有些奇怪嗎?
前已論及,在海昏時期劉賀低調行事,以避禍為基本取向。筆者猜想,劉賀在實際出行時應該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至少要將聲響和動靜盡可能地降下來,安車駟馬僅作代步工具,不可太過顯擺。如此,才符合當時的境況。
還可注意的是,按照當時的習慣,即便是出行時配以樂車,一般來說,有鼓車而無金車。在山東長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車出行圖”上,就呈現出了這樣的情形。在前引信立祥之論中,已論及了這一點。由于“大王車出行圖”是東漢圖像,在比較劉賀墓中金鼓齊全的現象后,信氏認為,劉賀墓所反映的“是西漢王侯的車輿制度,到東漢時期稍有變化。”在“大王車出行圖”之上,“大王即諸侯王乘坐的駟馬安車主車前,只有鼓車而沒有金車,應是東漢時期諸侯王的車輿制度。”②信立祥:《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的價值及意義略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但驗之于史,如果認為,西漢諸侯王及高等官員出行時金、鼓齊全,至東漢時,方發生了“只有鼓車而沒有金車”的變化。那么,這樣的構想與事實并不相符。
我們先從東漢時代的情況說起,漢安二年(143),順帝在接見匈奴單于時,曾賜予他“青蓋駕駟、鼓車、安車”等器物。③《后漢書》卷89《南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962頁。這與“大王車出行圖”中有鼓車、安車,而無金車的情形正相契合。但問題是,這不是東漢的特例。史載,王莽時代也曾對于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④《漢書》卷94下《匈奴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823頁。都是有鼓車,而無金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劉賀所在的宣帝元康年間,對于龜茲王也是如此,“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⑤《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916頁。亦有鼓而無金。此外,宣、元時代的大臣韓延壽在出行時有著“鼓車、歌車”的排場,但也未見金車一類的器物。⑥《漢書》卷76下《韓延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214頁。也就是說,在兩漢時代,當出行之時,鼓車是常備物,金車則未必。兩漢之間一體承之,沒有明顯的變化。不能因為劉賀墓中金、鼓齊全,就認為,這是西漢時代的出行標準。
當然為了聲勢浩大,有些諸侯王或許也會金、鼓齊備,但這樣的做法沒有制度上的要求,對于劉賀而言,更是需要避免的一種排場。事實上,墓室中的車馬與器物搭配,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寄托,而不是實際生活的反映。這種寄托是什么呢?它當然不可能指向于軍事層面,更不可能是展現“在另一個世界稱王稱霸、征伐四方的心愿”。在筆者看來,更多的是對過去歲月的留戀。
理由在于,金、鼓作為實用器配置于車馬之上,不是在海昏時代所具有的現象,而應該是昌邑王時的舊物。或許它們就在海昏侯國的大庫之中,沒有實際運用于劉賀的生活之中,并最終隨葬于地下。那么,當年的它們又在何種情況下會配之于車馬呢?存在兩種可能。
一是應該是田獵之時,參照軍禮,金、鼓相配合以協同行動。由前已知,年輕時的劉賀“驅馳國中”與“好游獵”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當田獵之時,為了聲勢浩大以及步調一致,也即是,為了疾馳者與緩慢者不至于脫離隊伍,借用軍禮,依鼓前進,鳴金止行,實為一種常態。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的三號坑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作為兵器依仗坑,里面除了大量的武器之外,還發現了若干的依仗器,其中,“西部中間置銅錞于和甬鐘各一件。”①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而在臨近的二號坑則是殉狗坑,其中應該有不少屬于獵犬一類。由物見事,齊王墓所展現的,乃是諸侯王游獵之時,兵器與金鼓相配的情景。同樣的,昌邑王時代的劉賀亦當有這樣的場面。由于禁忌所在,不能將兵器等展現在墓葬之中。但金車的呈現,或許能對此起到一個彌補的作用。
二是作為歌舞音樂的伴奏器。在前引韓延壽的故事中,鼓車之后就是所謂的“歌車”,也就是說,擊鼓主要不是為了歌唱,而是以壯出行時的氣勢,歌車中應該另有樂器。這些樂器有些是吹奏樂,構成了所謂的歌唱與“鼓吹”,《東觀漢記·載記·劉盆子》載,劉盆子出行時,在車駕后面即有著所謂的“歌吹者”。②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98頁。但既然是“歌吹”,有“吹”亦有“歌”,單靠吹奏樂器是不夠的。回觀前引陸賈的材料,當陸氏車馬出行時,“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鼓琴瑟”,即說明有彈奏琴瑟者。但那時的樂器豈止只有琴瑟?劉賀墓金車上的錞于和鐃等是重要的樂器。在馬王堆所出的一枚簡上有“擊屯(錞)于、鐃、鐸各一人”(簡一五)的記載。后曉榮等學者指出:“這枚簡不僅記載了當時這種樂器的使用情況,還反映了當時與錞于組合使用的,還有鐃、鐸等樂器的情況。”③后曉榮、胡婷婷:《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銅錞于屬性等相關問題討論》,《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更何況,錞于與鐲以及甬鐘已被證明,“為配套使用的樂器。”④王清雷等:《海昏侯劉賀墓青銅樂器測音報告》,《音樂研究》2022年第5期。那么,劉賀金車作為“歌車”,以承擔歌吹任務,或許也是一種可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與鼓車、金車相配的,不是出行的安車駟馬,而是三馬雙轅彩車。這樣的彩車,應該不是實際生活中所用之物,它的呈現,或許也是別有情懷的安排。
與安車駟馬不同,這種車制屬于所謂的“驂駕”,在漢代,此種駕式,再配之于歌舞鼓吹,往往是王車的規格。與安車駟馬適用面廣泛不同,它為皇子、皇孫以上所擁有,為重要的身份標志物。據《后漢書·劉盆子傳》,西漢末年被赤眉軍奉為漢主的劉盆子就曾有過“乘王車,駕三馬”的經歷,李賢注引《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⑤《后漢書》卷11《劉盆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83頁、第484頁。再據《續漢志·輿服上》,這樣的王車不僅“皇子為王”時可乘,皇孫亦可乘,與公及列侯的安車之制有所區分。⑥《后漢書》卷119《續漢志·輿服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47頁。
對于劉賀而言,與皇帝相關者皆為禁忌,在隨葬品中,要盡量避免發生禮制上的正面沖撞。但劉賀曾經的諸侯王身份,也即漢廷對“故王”的承認,使得他可以使用諸侯王一級的物品。再加之劉賀同時是武帝之孫,正宗的皇孫身份,驂駕自然在其使用范圍之內。但前已反復論及,安車駟馬為劉賀的主要出行方式,此種皇子、皇孫色彩更為濃厚的驂駕,或許并沒有實際采用過。于是,當陪葬之時,以明器形式隨之于地下,并將當年田獵時的金、鼓配之于車馬之上,其間所反映的心境,應該是復雜而多維的。
結 論
劉賀墓出土的車馬及器物不僅是禮制的重要載體,也是墓主的心結所在。它們聯結著劉賀的身份及命運的變化,也體現著西漢政治文化的某些側面,是由物見史的重要材料。經考察筆者認為:
一、作為從昌邑王國轉運而來的車馬及其器物,當它們作為生前實用器來到海昏侯國之后,雖然由于故王的身份可加以使用,為劉賀所擁有,并使得可采用的禮器被分成了兩種類型,一是與海昏侯相匹配的禮器,如隨葬的棺槨、斂服等,屬于列侯一級的物品。二是延承諸侯王時代的禮器,如車馬等。在沖突和包容中,展現了漢代禮制的軟性之處,故而不存在僭越問題。但由于身份的尷尬及低調避禍的需要,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實際使用,并由此呈現出私人性的特點。而當它們以拆車葬的形式隨葬于地下之時,則不僅是對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絕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車馬之盛的諸侯王之夢。
二、作為列侯一級的墓葬,劉賀墓不僅存在車馬陪葬,而且比之一般的諸侯王,其精美程度有遠過之而無不及,并打破了3輛馬車殉葬的所謂“定制”。這固然與劉賀的特殊身份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因目標及功能的差異,劉賀墓無須遵循3 車的葬俗。隨葬車馬坑中都是統一的“駟馬安車”,當這樣的車制出現時,展現的是出行時的狀況。它的出現,由當時劉賀的身體狀況及海昏侯國地理條件所決定,也是當時政治態勢下的一種避禍選擇。劉賀墓的情形還說明,“五馬”,即5 輛馬車往往是出行時重要的獨立單位。
三、墓室中的車馬器以明器模式出現,與車馬坑中的器物有著不同的功能性質。雖然建鼓和青銅錞于及青銅鐃是實用器,但與安車駟馬的分離可以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它們或許并沒有得到實際的運用。主要原因于,由于政治禁忌的存在,墓室中的偶車馬不能直接指向于軍事層面,為了避禍的需要,劉賀在實際出行時應該撤下了金鼓等鼓吹之物。而就禮制而言,鼓車為出行的必備物,金車則未必。劉賀墓中鼓車、金車的并存,不是兩漢之間在制度上有了歷史的變化,而是或許有著游獵的目的,以及金車作為歌車功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