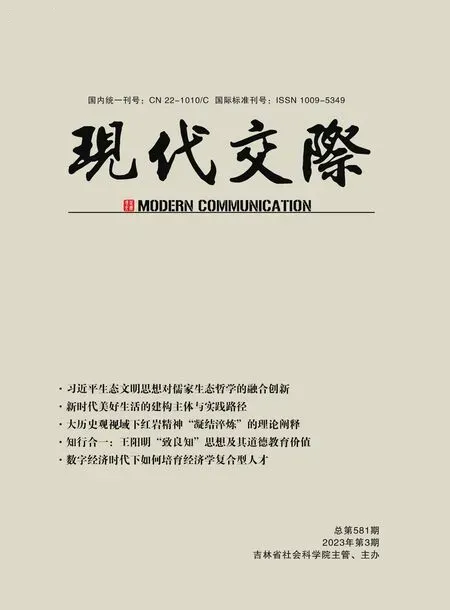《巴黎手稿》中人的發展理論及其對唯物史觀的貢獻
□馬 通 曹 晶
(1.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030;2.上海理工大學 上海 200082)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基本特征和本質要求,這些都與人的發展息息相關,“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1]22。可以看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其重要內涵的,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他方面是相互貫通的,所以以物的全面豐富為條件的人的發展滲透在整個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巴黎手稿》(以下簡稱《手稿》)是馬克思第一次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成果,人的解放和發展是《手稿》關注的核心問題。那么,《手稿》中人的發展理論的基本內容是什么?它對唯物史觀又有什么貢獻?對于這兩個問題,學界目前的研究還較為薄弱。本文擬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探討,為發揮《手稿》 中的人的發展理論在推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中的指導作用盡一份綿薄之力。
一、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馬克思認為,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這個命題的含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2]209,是現實的、肉體的、生活在地球上、與外部自然界時刻進行著物質、能量交換的人[2]209。他有眼睛、耳朵、手、腳、大腦等肉體器官,他的意識或自我意識是人的肉體的機能,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人是能動的存在物和受動存在物的統一。人的能動性是指人具有的豐富的本質力量,這是對象性的“主體能力”[2]191,也被馬克思稱為“自然力、生命力”[2]209,它們是人的肉體的機能,包括天賦、才能、需要、欲望等,如人的五官感覺、思維、直觀、情感、愿望、活動等[2]189。費爾巴哈也談“本質力”[3]33,但是就人來說,這種“生產性的本質力”[3]33是指理性、意志、愛。費爾巴哈認為,正是憑借這種本質力,人才成其為人,它是在人之內又不屬于人所有的屬神的力量[3]26-33。費爾巴哈所談的本質力是一種抽象的、普遍的原初力量和本質,而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力量則是對象性的生命力,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外延都明顯不同,這種不同是因為他們是從不同領域的異化出發來研究人的。人的受動性是指人的本質力量的表現和確證是離不開存在于他之外的、不依賴于他的對象的,這些對象在人的本質力量的發揮中起著不可缺少的制約、限制作用。人的能動方面和受動方面的統一,就是人的本質力量在客觀對象的限制下得到實現、表現或者確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有人的本質力量的發揮或者說人對對象的作用,也有對象對人的限制、制約,這一過程又被馬克思稱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或者生產,它可以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生產不可能是一個人孤立地進行的,必然處于與他人的關系中。馬克思對生產的分析已經超出了孤立的個人的視野,從對個人的研究必然地走向了對社會的研究。生產的外延非常廣泛,除了私有財產的生產和消費也就是經濟領域以外,宗教、家庭、國家、道德、法、科學、藝術等也都屬于生產的范疇。[2]186
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的生產和消費是人的各種生產的“感性展現”[2]186,也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2]186,而其他領域則是意識的領域。按照馬克思繼承自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原則,可以很自然地推論出來,前者在社會生活中就是主詞,是第一性的,其他領域則是賓詞,是派生性的。雖然馬克思在《手稿》中沒有直接地表達這一思想,但是他在談及異化的揚棄時堅持了這一原則。他認為,對私有財產的揚棄也是對一切異化的揚棄,這種揚棄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向社會的人的復歸。[2]186
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手稿》關于人的發展的理論的前提。人不僅在私有制條件下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在異化勞動和私有制的揚棄過程中以及在人成為類存在物之后,也都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手稿》中關于人的發展理論的另外兩個關鍵命題是:人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人是類存在物。前者著重強調人成為類存在物的過程,但是也無法避開談論人的發展目標,后者則闡述人的發展的目標。
二、人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
馬克思認為:“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說,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2]211這里的“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來自黑格爾《小邏輯》中的“自為存在”概念,自為存在是存在論中“質”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存在否定自身而過渡到定在,定在再一次否定自身就過渡到自為存在,因此自為存在包含“存在和定在于自身內”[4]204。黑格爾說:“自為存在作為存在,只是一單純的自身聯系……而是包含區別并揚棄區別的無限的規定性。”[4]204自為存在包含一切區別于自身,它的自身聯系是自身與自身的他物的聯系,因此它不受他物限制,也不過渡為他物,這樣自為存在就是獨立自存的,因此也是自由的。馬克思認為人是自為存在物,其第一層含義就是指,隨著人的本質力量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對象化和異化,隨著人顯示出自己的全部的本質力量,異化將被揚棄,人之外的對象將會成為人的對象,人的各種本質力量也將為人所占有,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以廣闊的、完整的對象為目的,同時也是以主體能力的發揮為目的。馬克思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將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來實現對對象的占有和對人的現實的占有。[2]189這必然涉及各種本質力量的關系,只有在每一種本質力量的發揮以其自身為目的的同時也成為其他能力發揮的條件的時候,才可能實現這一點。對于這樣的自為的人來說,他的主體能力在對象的限制、制約下的發揮已經成為他的享受。[2]189
人與自身的關系必然要通過他與他人的關系來實現和表現。當人實現了對自己的生產、對象和本質力量的占有,也必然占有他人的生產、對象和本質力量,這種占有是相互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2]187體現每個人個性的對象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存在,也是為別人的存在,又是別人為他的存在。“同樣,別人的感覺和精神也為我自己所占有。”[2]190其實,不僅僅是感覺和精神,每個人都通過社會關系占有其他人的一切本質力量,使其成為共有的財富。這樣的社會關系是屬于人的本質的社會關系,它就是個人的本質力量及其對象化活動,而不是抽象的、與個人對立的。這樣的社會關系被這時的馬克思稱為“社會”。[2]187與此相對立,私有制條件下異化的個人之間的關系則是奴役、斗爭和對抗,這是他們與自身關系的必然結果,又成為他們與自身關系的原因。自為存在不僅僅表現在人的現實存在或者類存在上,還表現在人具有普遍意識或者類意識上,類意識和類存在相互確證。總的來看,我們可以把自為存在概括為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這種發展的社會性,這里的社會性是指消滅了剝削制度后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不是一般的社會性。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有這樣的用法,他說,消滅了剝削制度后的自由的勞動的實現要有兩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勞動的“社會性”。[5]174如果把外在的自然界和他人都理解為個人的他物的話,可以明顯發現馬克思對人作為自為存在物的理解是對黑格爾的自為存在概念的吸收和利用。
黑格爾也舉出“我”作為自為存在最切近的例子,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且因而異于一般自然,即由于人知道他自己是‘我’,這無異于說,自然事物沒有達到自由的‘自為存在’而只局限于‘定在’,永遠只是為別物而存在”。[4]204可見,黑格爾認為人因為有自我意識,才成為不同于自然物的自為存在,才是自由的。馬克思說:“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2]162從這段話來看,馬克思認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也就是勞動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使得人成為有意識的存在物。黑格爾所說的區分人和動物的自我意識,并不是根本的區別,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人和動物的生命活動的區別。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人能夠達到自為存在,從根本上說不是因為他有意識,而是因為他有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或者勞動。勞動異化和揚棄的過程是人達到自為存在的最根本的途徑。當然,馬克思所說的勞動是有自我意識的因而是自由自覺的,馬克思雖然否定了黑格爾僅僅把自我意識看作人與動物的區別的觀點,但是他也沒有否認自我意識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
黑格爾講的自為存在不是一個靜態的存在,他還把自為存在作為理想性,它是從實在性發展來的。黑格爾認為“自為存在現在一般可以被認為是理想性”[4]204,并且指出,“但是真正來講,……若將實在性的潛在性加以顯明發揮,便可證明實在性本身即是理想性”[4]204。這樣能夠發展為理想性的實在性并不是孤立的定在或者自然,而是依存于精神的自然。認為自然依存于精神,這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表現,黑格爾認為精神和自然共同構成實在性,并且這一實在性經過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揚棄自然并把自然包括在其內,從而能夠成為自由的自為存在。這無疑對馬克思有重要的影響。馬克思指出,人的對象、感覺都不是直接存在著的對象、感覺,無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自然界,都不能直接歸為人的存在物。[2]211人成為人、成為自為存在或者類存在物,必須經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就是以經濟領域為其現實的、感性的存在的整個生產的異化以及這種異化的揚棄的過程。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馬克思關于人有一個辯證形成過程的思想不僅僅是對黑格爾的自為存在思想的批判吸收,它更主要的來源是整個黑格爾體系所體現的辯證法。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學者討論過,在這里不再重復。
三、人是類存在物
在《手稿》中,“類存在物”是指占有了人的類本質并具有社會性的人。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本質基本上繼承了費爾巴哈的類本質概念,費爾巴哈把理性、意志、愛當作人的類本質,類本質是以人的自然本質為基礎的,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本質則包括自然、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馬克思說:“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2]163但是,在馬克思看來,人能夠占有費爾巴哈所說的類本質,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有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這樣,馬克思把類存在物的根本規定就放在了人的生命活動上,而不是費爾巴哈理解的理性和道德。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另一個規定是人的社會性,其處在屬于人的本質的社會關系中。這種社會關系是人實現了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進而實現人的全部生產的自由的結果,但它不是獨立于人的生產之外的,它就是人的生命表現和財富,并且在它產生之后就和人的生命活動和其他生產相互作用,成為人的本質實現的條件。[2]187-188
馬克思說的人是類存在物與人是自為的存在物的意思是相通的,作為自為存在的人的自由和社會關系都適用于類存在物。除此之外,作為類存在物或者自為存在的人和異化的人的一個顯著標志在他們的需要方面。需要也是人的本質力量,馬克思認為,富有的人就是有豐富的人的本質的人,是揚棄了私有制條件下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他的需要是對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全面的需要,既包括物質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交往需要等。正是有了這樣的需要,他才能進行全面的生產從而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而異化的人的需要歸結到一點上就是對貨幣的需要。
人作為自為存在和類存在物的區別在于,人是自為的存在物包括人的異化及其揚棄的過程,其中最后的環節也即異化的揚棄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2]197,從根本上說是對發展到頂點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從整體上說是對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是向社會的人的復歸[2]185。馬克思在《手稿》中把人的發展的這一階段稱為共產主義,類存在物是人類發展的目標,這一階段被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階段。在社會主義階段,人已經通過自己生產的異化和揚棄異化而誕生,占有了自己的生產、產品和本質力量。這使得凌駕于人與自然之上的神的觀念成為不可能,因為這些觀念就是人對于外化的自己的本質力量的扭曲反映。隨著異化的揚棄,人們已經自覺地把人和自然看作世界的本質。[2]197這種感性意識也是類存在物的一個重要特征。
這也回答了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手稿》中的人的發展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理論前提、人的發展過程和人的發展目標三部分內容。理論前提是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發展過程是以勞動的異化和異化揚棄為根本的人的生產的異化和異化的揚棄,而發展目標則是作為類存在物的人。
四、《手稿》中的人的發展理論對唯物史觀的貢獻
《手稿》中的人的發展理論雖然在表達上還帶有濃厚的費爾巴哈色彩,但內容極富獨創性。可以發現,這一理論是唯物史觀的前身。那么,這一理論對唯物史觀的貢獻是什么?或者說,它的哪些思想被批判地保留在了唯物史觀中呢?只有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批判地看待《手稿》中的人的發展理論,繼承其精華內容。恩格斯曾指出,《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是“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6],所以我們對上述問題的探究是結合《提綱》及其之后的相關著作進行的。
1.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與唯物史觀的幾個基本概念
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與唯物史觀中的“現實的個人”[2]519、生產、生產關系、生產力概念都有密切關系。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第一層含義是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存在物是唯物史觀的前提也即“現實的個人” 的一個基本規定性,《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談及“現實的個人”這一概念時指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2]519
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第二層含義是,人是能動的存在物和受動的存在物的統一,這一統一體現在以經濟為其現實存在的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活動上。在這里,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或者生產的概念,這是唯物史觀的又一重要概念。“生產”概念揭示了唯物史觀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的共同形式,不僅私有財產生產和消費屬于生產,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也屬于生產。[2]186以生產概念特別是其中的勞動實踐概念為依托,馬克思還解決了舊唯物主義在環境和人的關系上最終陷入唯心主義的問題,在把人理解為歷史的主體的同時,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也摒棄了唯心主義歷史觀中歷史主體的抽象的、脫離受動性的能動性。在《形態》中,馬克思又對生命生產的社會關系這一重要的唯物史觀概念進行定義——“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2]532。馬克思在《手稿》中把活動規定為人的本質力量之一,因此社會關系的概念也是借助本質力量對象化或者生產概念來規定的。
在規定生產概念的時候,馬克思還提出了人的本質力量或者主體能力的概念,這概括了人在面對對象的時候的一切機能。后來唯物史觀中的基礎概念生產力與人的本質力量或者主體能力的概念有著明顯的聯系。馬克思在《形態》中指出:“第一,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于各個人并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580馬克思在這里區分了唯物史觀的生產力概念的兩個層次——個人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并且明確指出各個人的力量就是生產力。這里談的生產既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2]575因此,個人生產力也是一個全面的生產力概念,相應的,社會生產力也不是單純的物質生產力。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中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提到生產力的時候都在這一概念的前面加上了“物質”這個限定詞,其后的使用中由于語境本身的限定而可以省略這個限定詞,所以他沒有再加。這表明,馬克思在《序言》中也沒有直接把生產力等同于物質生產力。個人生產力以及社會生產力都是不斷發展的,正是因為這種發展,才有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唯物史觀的個人生產力與《手稿》中的人的本質力量都是個人的力量,都具有對象性、全面豐富、不斷發展的特征,其繼承發展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個人通過交往把他們各自的生產力組織成社會生產力,因而人的本質力量概念通過個人生產力而成為社會生產力概念的重要來源。
2.“人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與社會基本矛盾理論
人是自為的存在物首先是指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個人的發展的社會性質,在這一方面它與人是類存在物的含義是一致的。這兩個命題的區別在于它們所闡述的人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自為存在是人從異化到揚棄異化的自我實現過程,但不可避免地談到人的發展目標,這一目標就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為了避免重復,這一部分只探討馬克思發現的人的自我實現過程對唯物史觀的貢獻。
《手稿》對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貢獻首先在于,它發現了經濟領域的異化關系及其必然被揚棄的趨勢,從而對唯物史觀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思想有直接的貢獻。《形態》依然是把分工下的勞動、交往形式、社會生產力等作為人通過生產和交往創造出來卻獨立于人并統治人的東西,仍然認為人必然也應該在發展了的生產力基礎上占有這些自發形成的條件。[2]535-539,574可以發現,人與這些自發形成的條件的關系其實還是異化關系,而馬克思追求的還是通過對這些條件的占有來實現人的自由,也就是人成為人、自我實現。當然,在《形態》中馬克思看到了這種異化關系在歷史上的顯現出來是有一定條件的,私有制下也有具體的、有局限的“有個性的個人”[2]574-576,他不再像在《手稿》中那樣用異化及其揚棄解釋歷史發展,而是用歷史解釋異化及其揚棄。在這些條件中最根本的是生產關系或者交往形式,分工和生產關系不過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生產關系也規定著工人的勞動,把個人生產力連接起來構成社會生產力。因此,《形態》中講的人的物質生產活動與自發形成的條件的矛盾其實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手稿》中的經濟領域的異化思想是這一社會基本矛盾思想的來源之一。
《手稿》中人的自我實現過程對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貢獻,還在于它把勞動的異化作為人的異化的根源,從而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思想有重要的貢獻。馬克思說:“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2]167勞動的異化表現為勞動中工人同產品的異化,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的異化,工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的異化和私有財產。在這四個規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生產的關系是根源,它導致產品的異化和工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的異化,前三個規定是對異化的勞動本身的規定[2]164,私有財產或者資本家對工人的奴役關系是異化的勞動的結果[2]166,而資本家對工人的奴役的關系又是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奴役關系的根由。工人的勞動生產是他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與異化,在生產力關于勞動者的能力這一意義上,生產力、勞動、生產資料和蘊藏在這些自然對象性中的生產關系構成了勞動生產過程的四個要素。勞動在不斷地使勞動者的能力對象化,從而使得生產資料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者的能力。勞動者的能力的提高又使勞動過程和生產資料進一步發展。當然,在剝削社會,勞動者能力的發展是片面的,只是某些方面能力的發展和其他能力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生產力作為勞動者的能力,既可以從勞動者本身的素質來測定,也可以用勞動資料或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來指示。因為勞動者的能力本身就包括使用勞動工具改造勞動對象的能力,生產力發展必然要淘汰與其不適應的生產關系,而創造出與自己適應的關系。由此可見,馬克思把異化的勞動生產作為私有制的起源,又把勞動生產作為人的本質能力的對象化,這可以視作唯物史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理論雛形。但在《手稿》中,馬克思對勞動本身的把握更多地是從勞動對勞動者造成的肉體和心理上的影響這一角度進行的,他對勞動能力的理解還缺乏實際內容。在《形態》中,他則從勞動工具等角度來把握勞動,為勞動的社會關系找到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整個社會奴役制根源。這一思想是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所堅持的。他在1871年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一切奴役制度的基礎。[7]并且,《手稿》中的這一觀點經過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唯物史觀的另一個基本觀點,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由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經濟結構是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式的基礎。[8]這一觀點及其相關思想后來被概括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
3.“人是類存在物”與共產主義理論
人是類存在物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理論中對人的規定有密切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而迫使工人生產,從而使生產力獲得發展,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9]。因此,我們可以把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唯物史觀設想的對共產主義的人的規定。人是類存在物這一命題確立了人類的發展目標,它包括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他們的發展的社會性。從這些基本的規定來看,與《資本論》中設想的發展目標是高度一致的。不過,仔細研究馬克思表述唯物史觀的其他文本,還是可以看出《資本論》中的這一目標與《手稿》中的目標的區別,只有這樣才能夠更準確地界定《手稿》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
在《形態》中,馬克思設想的完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人是對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條件下,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以保證自己的生存進而實現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人的才能的全面發揮。[2]580由此可見,自主活動和馬克思在《手稿》中所闡述的自由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在基本內涵上是一致的。這種自主的物質生產,必須通過聯合才能成為現實。[2]581物質生產領域人的活動向自主活動的發展與其他領域中人的活動向自主活動發展是相適應的,也和人的交往由作為階級成員的交往向作為個人的交往相適應。[2]582總的來說,類存在物的人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規定和決定性的基礎(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都被繼承下來了,但是相對于《手稿》,《形態》中的馬克思明確地強調人的這一發展必須以發達的生產力和聯合起來的個人對既有的生產力、交往形式、資金等的占有為條件,這與他對社會歷史中存在統治著人的盲目力量的認識更加豐富、深刻有關。
《形態》中的實現了充分自主活動的個人不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關于人的發展目標的最終完成,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透出這樣的意思:物質生產的自由是“實在的自由”[5]174,而不是像作曲那樣真正自由的勞動。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則明確指出:“但是,這個領域(指物質生產——引者注)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10]929在這里,馬克思強調物質生產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而真正的自由王國只能在物質生產的彼岸存在。在《手稿》和《形態》中馬克思都沒有做出這樣的區分,很明顯,《手稿》要實現的人與自然的完全統一和在此基礎上物質生產為物和為人的統一只能是一種永遠指引我們前進的目標,而不可能真正達到。《形態》中提出的在物質生產領域“實現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2]581也是不可能的。雖然即使來自生產關系和其他社會結構的制約被置于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控制之下,但是物質生產本身的必要性和要達到的外在目的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它依然從外部制約著人的勞動。這就決定了這一領域的自由只能是實在的自由,這種自由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合理調節他們的物質生產,使得這種生產不再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統治人,人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在最合乎人性的條件下生產。[10]928
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本身就是唯物史觀對人的規定,生產概念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概念,生產關系概念則需要借助生產活動概念來規定,而本質力量概念則是生產力概念的前身。人是自為存在中對經濟領域的異化關系的認識是唯物史觀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思想的先聲,而關于工人對生產的關系是一切奴役的根源的思想則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理論的雛形。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基本規定被唯物史觀共產主義中的人的規定所繼承發展。這是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從整體上看,《手稿》雖然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醞釀時期的作品,但是其中關于人的發展的理論對唯物史觀的形成具有奠基意義。
面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的任務,《手稿》對人的自然性、能動性和受動性的統一的揭示,對現實的人的異化的批判,對人的發展目標的設定,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的探索以及自我實現的辯證法都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也可以為黨的最新理論、方針提供有力的學理支撐。《手稿》中關于人的發展的思想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值得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