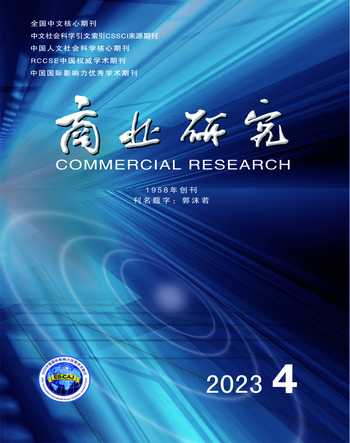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激勵中國農村居民消費嗎?
葛立宇 蔡欣榮 黃念兵



摘?要:促進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有效提升是當前我國經濟轉變增長方式、實現內生增長的核心需求。本文采用靜態和動態模型分別評估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農村消費的激勵效應,結果發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顯著促進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提升。機制檢驗發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通過“預防性儲蓄減少效應”和“擠入效應”提高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但“收入效應”并不顯著。本文的研究結論深化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拉動農村消費的理論認識,也為我國進一步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供了實證依據。
關鍵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村居民消費;預防性儲蓄;擠入效應?收入效應
中圖分類號:F3238;F8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4-0075-10
收稿日期:2022-09-26
作者簡介:葛立宇(1979-),男,江蘇興化人,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財稅理論與政策;蔡欣榮(1993-),本文通訊作者,男,廣西柳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稅理論與政策;黃念兵(1982-),男,湖北黃岡人,講師,研究方向:財稅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項目編號:71774107。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項目編號:GD21CYJ24;廣東財經大學廣東省財稅大數據重點實驗室項目,項目編號:2019B121203012。
一、引?言
當前,在經濟處于“三期疊加”的背景下,擴大內需尤其是啟動消費需求,對于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內生增長尤為重要。2020年,我國農村人口占城鎮比為5652%,但消費總量卻只占到城市的273%,城市居民人均消費量比農村居民高21倍。可見,農村消費相對滯后仍然是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癥結所在,在當前乃至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釋放農村消費潛力、有效實現農村居民消費總量擴張依然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撐點。
為應對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在中央一系列精神指導下,我國政府近年來陸續制訂、出臺了一系列促消費、振內需的政策措施,雖然和經濟水平相似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居民消費率水平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從“十二五”時期以來,居民消費總量增長速度較快,目前已經從2010年的141465億元躍升到了2020年的387176億元,年均增長1059%,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例也已經達到了38%,創歷史新高;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自2011開始,已經連續10年高于城鎮。可見,我國的基礎消費條件已經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消費需求已經逐步開始啟動。當前,我國學界有必要適時對一些成功的政策和做法進行提煉和總結,以便下一步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持續提升提供更為精準和有力的政策支持。
從公共政策方面來看,從國家“十一五”到“十三五”規劃綱要,以及《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和《“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等一系列文件精神和規劃報告中均提出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系列重磅公共經濟政策的核心經濟目標其實就是要改善民生,推進公共資源向基層、農村和弱勢群體傾斜,解決大部分民眾的看病難、上學難和養老難。在此基礎上,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盤活國內消費,促進經濟運行系統向消費主導和可持續發展轉型。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城市和農村在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還存在較大差異,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化現象較為突出。因此,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際上目前構成了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核心內容,所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政府向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不斷實現均衡化,這不僅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構成了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領域改革的核心主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因果關系上,考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否能夠真實、有效推動中國農村消費需求擴容?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消費表現為收入的函數,其由收入和平均消費傾向兩個因素共同決定,那么,在假設以上因果關系成立的基礎上,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通過哪一條因素或途徑影響到了農村消費呢?進一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農村消費結構又會產生哪些異質性影響呢?這些基本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在理論上厘清影響我國消費的深層次經濟邏輯,也有利于我國逐步找到一條擴大農村消費的公共政策路徑,推動我國經濟真正走上內需拉動、內外循環、內生增長的良性發展道路。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20世紀30年代西方大蕭條,激發了西方經濟學家研究消費規律的學術熱情。從學術發展史角度來看,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由凱恩斯開創的傳統理論階段。這一階段以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絕對收入假說為肇始,相繼產生了相對收入假說、生命周期假說、持久收入假說等經典理論,這些論證嚴謹、分析細密的理論框架至今都有啟發意義。二是由“理性預期革命”催生的現代消費理論階段。這一階段消費理論研究框架主要是從“確定性”走向了“不確定性”。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隨機游走假說、預防性儲蓄假說、流動性約束假說。筆者認為,對于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影響因素的分析,還是需要植根中國本土環境,深入了解中國農村居民自身消費行為的變化與特征,才能有助于發掘影響其消費行為的機制或效應。基于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的行為視角,目前大致有三種理論觀點或觀察視角值得重視,具體來說:
(一)預防性儲蓄效應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們將不確定性引入消費的分析框架,預防性儲蓄理論一經問世就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1]。Drèze和Modigliani[2]研究表明,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增加將使消費者增加儲蓄而減少消費。Carroll[3]利用美國的數據研究發現,當期的消費受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影響顯著,并且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越大,當期的消費就會越少。在此基礎上,國外學者相繼發展出了各種預防性儲蓄數理模型,這些理論的深化發展增強了消費理論的現實解釋能力。預防性儲蓄理論認為消費具有敏感性,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會使得人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存在強烈的不確定性預期,而該種預期使風險厭惡型消費者的消費邊際效用大于確定性條件下的邊際效用,消費的邊際效用會隨著風險的增加而增大,這使得消費者會減少當期消費,進行更多的預防性儲蓄[4]。
我國學者也積極考察了預防性儲蓄理論在中國本土情境下的適應性,考察我國改革進程中產生的各種不確定性是否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例如高夢滔[5]利用8個省的農戶微觀面板數據,基于工具變量法發現新農合減少了儲蓄(現金加上銀行存款)近12%-15%,大約為552元。劉靈芝等[6]認為支出與收入的不確定性均會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產生抑制作用,且收入不確定性的影響程度要大于支出不確定性的影響程度。張勛等[7]發現盡管由于“新農保”等政策的推廣有所提高,但絕對水平仍然落后于城鎮居民,這客觀上造成了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消費水平過低。這些實證研究證實了預防性儲蓄理論在中國農村情境下的適用性。從理論上看,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發展意味著醫療保險、教育、養老保險在農村得到推廣和普及,這些保障型的公共支出能夠有助于降低農村居民的不確定性預期,從而減少預防性儲蓄,提升農村居民消費率。
(二)擠入效應
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往往表現為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而政府的公共支出與私人消費之間,二者既可能是互補關系,也可能替代關系。一方面,如果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導致私人消費同方向增加,例如當政府增加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各項支出時,居民在食品、衣服、居住等消費也增加,這時擴大財政支出對私人消費起到了擠進的作用。反之,如果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導致私人消費反方向減少,就會產生替代關系。因此,居民消費與政府的公共支出之間應該存在著某種函數關系表達式,即政府的公共支出會產生“擠入”(crowding?in)或“擠出”(crowding?out)效應?。
從“擠入效應”來看,在現代社會,私人物品的消費往往需要相關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支持和配合,例如,沒有道路等基礎設施,居民很難增加私家車的消費數量及其所占比例,郭廣珍等?[8]構造了一個交通基礎設施同時影響生產和消費的增長模型,發現道路和道路基礎設施投資還可以通過提高居民消費中私家車數量及其所占比例(消費效應)間接推動經濟增長。政府提供農村醫療保險等公共服務,也會相應增加農村非醫療支出類的家庭消費,白重恩等?[9]利用農村引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一政策變化來研究醫療保險的獲得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新農合使得非醫療支出類的家庭消費增加了約56個百分點,新農合對消費的刺激作用即可能來源于預防性儲蓄的減少,但也可能源于醫療保險對消費的事后“擠入效應”,即醫療保險減少了參合家庭的醫療開支,因此這些家庭有了更多的可用于其他消費的收入。“擠入效應”實際上強調的是社會保障會減少家庭的保障支出,進而使得家庭有更多的留存收入來支付其他開支。
當然,政府的投資性和消費性支出也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例如方福前和孫文凱[10]運用2007—2012年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發現:我國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居民消費率和總消費率之間存在負向影響關系,說明了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和社會總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總體來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政府增加了農村的民生性財政支出比例,而相應的投資性和消費性支出比例減少,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改善理論上可以相應降低其對于農村消費的“擠出效應”,產生“擠入效應”。
(三)收入效應
凱恩斯認為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在給定消費傾向的情況下,收入越高,消費自然也會越高。在中國農村具體情境下,王健宇和徐會奇?[11]發現,收入增長性和收入永久性對農民消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收入增長性和收入永久性的提高會促進農民消費的擴大。溫濤等[12]曾對農民收入結構與消費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果表明農民的各項收入對各項消費作用強度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家庭經營收入仍然是其分項消費支出的最主要影響因素。胡日東等[13]利用2002-2011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結合混合回歸模型和SUR模型的估計方法,分別對中國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進行了影響因素分析,實證結果也驗證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具有顯著的影響。王小華和溫濤[14]還進一步發現“七五”時期和“八五”時期,城鄉居民邊際消費隨收入的增加而遞增;“九五”時期及以后,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則仍隨收入的增加而遞增,該文還深入探索了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具體變化規律和時期差異以及產生這些變化和導致這些差異的深層次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優化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對策措施。以上實證研究雖然觀察的角度不同,分析重心也略有差異,但其基本結論都能夠表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確實受到收入水平的顯著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現有文獻的研究已經足以支撐我國農村消費確實受到了“預防性儲蓄效應”“擠入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影響,這三大理論機制在中國農村具體情境下是適用的。就本文關心的核心問題而言,筆者要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要研究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能否觸發這三大機制發揮作用。消費是由平均消費傾向和收入共同決定,三者的關系表現為:c=(c/y)×y,其中,c為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y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來表示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能力;c/y為人均平均消費傾向,用以表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意愿。我國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理論上對這兩個因素都有可能產生正面作用。一方面,我國農村不僅在交通基礎設施等硬件方面,供給數量和質量上相對不足,而且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軟件方面,城鄉相比差距更大。正因如此,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意味著農村居民未來的生活保障確定性增加,相應農村居民就可以減少“預防性儲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水平、醫療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會產生公共支出的“擠入效應”。“預防性儲蓄”和“擠入效應”都有助于農村居民在收入既定條件下提高平均消費傾向。另一方面,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也有可能增加農村公共就業、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從而有助于農村居民收入的提升。當然,這些理論假說(見下圖)還有待于實證檢驗,以下章節我們將對此進一步展開實證分析。
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的機制
三、研究設計
(一)基本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中國情境下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否真實促進了農村消費的提升,我們的基本模型設定如下:
VEi,t=α+βEqui,t+γControli,t+λi+ηt+εi,t(1)
式(1)中,VEi,t為省份i在t年的農村人均消費水平;Equi,t為省份i在t年的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Control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λi為省份固定效應,η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數據說明與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本文關注的核心被解釋變量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VE)。數據來源于歷年《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所有樣本都除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剔除了價格因素的影響數據剔除價格水平影響,以2006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基期(即2006=100)對農村居民名義消費支出進行平減得到實際支出。本文涉及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變量指標都進行過類似處理。,并取對數化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現有衡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法,主要涉及兩個角度:一是地區角度,主要衡量省份內部地區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例如武力超等[15]研究設計的地區基尼系數法。二是城鄉角度。例如李丹和裴育[16]等采用公共投入產出比較的方法衡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或均等化,考慮到本文的關注領域只涉及城鄉范疇,因此,我們參考第二種方法設計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
根據國務院發布的《“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主要發展指標涉及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殘疾人服務等八個方面的內容。目前,涉及這些清單的統計數據存在較多的缺失,綜合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口徑一致性以及連續有效性的因素,本文研究并未涉及“十三五”規劃中基本公共服務的所有指標,其主要由四個方面指標構成,分別為城鄉義務教育指數(E_Com)、城鄉公共衛生指數(E_Hea)、城鄉社會保障指數(E_Sec)和城鄉基礎設施指數(E_Inf),具體的指標測度方法見表1。在方面指標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先進行標準化,然后降維處理,最后計算出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綜合指數(Equ)。
其中,城鄉義務教育指數(E_Com)的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城鄉公共衛生指數(E_Hea)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城鄉社會保障指數(E_Sec)的數據來源于《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城鄉公路公里里程數,借鑒李丹和裴育[16]的做法,按技術等級進行衡量,將高速、省道、縣道作為城鎮公路里程數,三級、四級和等外公路作為農村公路里程數,數據來源于《中國交通年鑒》。
3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P_GDP)。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表示。以收入法核算GDP時,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和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是其三大核心計算依據,這就意味著人均GDP水平越高,相應的居民消費也會逐步提升。(2)財政發展水平(FI)。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表示。財政發展水平越高,居民消費可獲得收入和消費補貼也會越高,這二者都有利于居民提升消費水平。(3)農業產業結構水平(IN)。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表示。農業占GDP比重越高,農民收入水平占居民收入水平也會越高,農村消費占居民總消費也會處于較高水平。(4)農戶固定資產投資(AS)。在收入固定的情況下,投資和消費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農戶固定資產投資越高,可能會擠占一部分的農村居民消費。(5)進出口水平(IE)。進出口水平越高,說明農村開放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可能也越高,有利于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6)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IG)。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介于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城鄉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大城鄉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城鄉收入基尼系數越小,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可能會越高,也越會接近城市消費水平。(7)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Rev)。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理論認為,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一般來說,收入越高,消費相應也會得到提升,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性影響因素。
以上控制變量數據和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中國財政年鑒》,以及中經網數據庫、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平臺等,為減弱各變量數據之間異方差的影響,對于絕對量數據取對數化處理。
本文將樣本期間確定為2006-2019年,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自2006年開始實施的“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了“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2006年實際上是我國實施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的起始時間。另外,涉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衡量的部分年鑒目前只更新至2020年版,因此將截止時間設定為2019年。考慮到我國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城市化程度較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并不明顯,實證研究中刪去了這三個直轄市的樣本;西藏自治區部分數據缺失,樣本同樣做了刪除處理。表2匯報了基本回歸涉及的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一些西方學者們認為消費行為會受到消費慣性(consumption?inertia)的影響,既當期消費要受到前期消費行為的影響。從我國農村家庭行為來看,農村消費同樣會受到過去自身消費狀況的顯著制約[17];基于這個觀察,我們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對基本回歸方程進行了分類考察,表3第(1)和(2)列我們分別采用OLS模型(最小二乘估計法)和FE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了方程(1)的基本回歸,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Equ)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3第(3)和(4)列我們將被解釋變量(VE)滯后一期,納入回歸方程,構建了動態效應模型,結果顯示,不僅核心解釋變量(Equ)顯著性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而且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lVE)也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這就說明農村人均居民消費不僅受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影響,也受到了前一期消費習慣的顯著制約。
(二)內生性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直接采用OLS方法和FE方法對(1)式進行靜態或動態回歸都面臨潛在的內生性問題,這也是本文實證分析的難點所在。可能的內生性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農村消費的提升可能也會對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產生一定的反向作用,例如,地方政府可能會優先考慮農村消費規模較多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等,以便于更好地服務當地農村的消費;二是本文雖然盡量控制了影響農村消費的相關經濟、政策變量,但仍然難以控制諸如外出務工、家庭收入內部轉移、農村自然資源稟賦效應等潛在遺漏變量的影響,這些都會導致估計偏誤。因此,有必要進行內生性處理。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避免其對基本結論產生干擾,筆者分別采用廣義矩估計(GMM)和合成工具變量法(Bartik?instrument)兩種方法進行內生性檢驗。
廣義矩估計實際上是利用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內生解釋變量的工具變量,然后將工具變量納入基本方程進行回歸檢驗,具體來說,筆者將被解釋變量(VE)和解釋變量(Equ)的滯后2-4期,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VE)和解釋變量(Equ)滯后1期的GMM式工具變量(DWH檢驗為內生變量),其余控制變量作為自身的IV式工具變量(假設它們為外生變量),運用stata非官方的xtbond2命令進行動態面板估計,表4第(1)列匯報了差分GMM(不估計水平方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解釋變量(Equ)對于被解釋變量(VE)和滯后1期的被解釋變量(VE)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差分GMM方程相比,系統GMM方程將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為一個方程系統進行GMM估計,表4第(2)列匯報了系統GMM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除了系數發生了顯微變動,顯著性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筆者對工具變量做了一系列有效性檢驗。首先,使用差分和系統GMM方法的前提是擾動項ε不存在自相關,Arellano-bond檢驗發現,擾動項的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而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故不能拒絕原假設“擾動項無自相關”,可以使用差分GMM和系統GMM。另外,Hansen過度識別檢驗統計量表明,不能拒絕“所有工具變量都聯合有效”的原假設,這表明筆者使用的工具變量具備較好的外生性,能夠滿足廣義矩方法對于工具變量的統計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Hansen過度識別檢驗雖然較為穩健,但可能會受到工具變量過多的影響。相關學者也認為GMM方法選用內生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其工具變量,可能存在兩點問題:一是在保證工具變量較優的相關性下滯后期高階數的選擇可能產生過度識別問題;二是如果內生變量各期存在較強的序列相關,將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的外生性仍然得不到改進[18]。對此,筆者進一步構造合成工具變量(Bartik?instrument),以期更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提高評估的準確性。
鑒于合成工具變量在“相關性”和“排他性”兩個標準中展現出的優良特征,本文借鑒相關文獻的研究方法,嘗試構造關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合成工具變量,具體思路如下:
假定期初的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是外生給定的,那么內生性問題主要來自期末的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如果采用全國(除去該省份)增長的總趨勢預測該省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增長水平,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原因在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國增長的總趨勢必定和該省份的增長情況緊密相關,同時該預測值由于代表全國(除去該省份)增長的總趨勢,因而又不會直接影響該省份的均等化水平。因此,該預測值能夠較好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和“排他性”的構造標準。
按照這個思路,由第t期全國除省份i以外其他所有省份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增長率的平均值可以計算出省份i預測的均等化增長水平,然后利用期初給定的省份i均等化水平,就能夠構造出省份i在t+1期(當取j=1)的合成工具變量:
BartikIVi,t+j=Equi,t×(1+g-i,t,t+j)
筆者嘗試利用此合成工具變量,構建GMM(IV+2SLS)方程進行回歸,表4第(4)列顯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對于農村人均消費水平的影響1%水平上顯著為正。為了進一步驗證合成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我們進行了兩項檢驗,第一,通過2SLS第一階段回歸,如表4第(3)列顯示,合成工具變量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Equ)在1%水平上顯著相關,可以認為合成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的要求;第二,在第二階段回歸中,如表4第(4)列所示,F統計量的值大于10,故該工具變量不存在弱相關問題,滿足外生性假定。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本文基于四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來說:
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近幾年來,網上支付、移動支付等電子消費方式長足發展,我國消費方式已經產生巨大變革,但農村的現金消費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一方面,我國農村的信息基礎設施可能還不能支持全方位運用電子支付方式,現金消費依然占據較大比例。另一方面,農村留守人員以老人、兒童居多,這部分人員可能還是以現金消費居多。在本文樣本期內,各省農村現金消費占農村總消費的比例平均為82%,這說明現金消費仍然是中國當前農村日常消費的主流方式。基于此,我們將方程(1)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農村現金消費,表5第(1)列顯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對農村現金消費的影響在1%水平上保持顯著為正。第二,增加控制變量。如前所述,方程(1)可能未控制所有影響農村消費的經濟、政策等影響因素,為了減輕遺漏變量的影響,我們盡可能擴充了方程(1)的控制變量集,具體來說,增加了如下省份控制變量:城鎮化程度、國內專利申請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農戶投資住宅房屋竣工價值、農戶轉移凈收入、農戶財產凈收入、農戶經營凈收入、農戶工資性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對于絕對量數據,我們依然采取對數化進行處理,表5第(2)列顯示,在增加控制變量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對農村人均消費水平(VE)的影響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第三,更換估計方法。極大似然估計(ML)被證明是漸進的最好的估計,隨著樣本數m的增加,會逐漸收斂,估計結果具有一致性、最小漸進方差的優點。表5第(3)列顯示,在運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ML)進行估計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對農村人均消費水平(VE)的影響的顯著性保持不變。第四,分時期檢驗。早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我國政府就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但2012年國務院制定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是我國第一份構建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綜合性、基礎性、指導性文件,較為全面系統勾勒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制度性安排,在這個文件的指導下,絕大部分省份從2013開始,出臺了本省第一份系統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性安排。實際上,《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的出臺,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次外生事件沖擊。基于此,我們將本文的樣本期分為2006-2012年、2013-2019年兩部分,并分期進行回歸,表5第(4)列和第(5)列顯示,雖然兩時期的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都對農村人均消費水平(VE)顯著為正,但后一期的系數要大于前一期的系數,而且顯著性水平也呈現同樣特征,這就說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步水平越高,對于農村人均消費的影響程度可能越大,換句話說,在本文考察的樣本期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農村人均消費的邊際影響效應是逐漸加大的。
(四)異質性分析
筆者以上論述總結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農村人均居民消費水平總體影響,但我國農村消費實際上可以細分為多個種類,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農村居民消費的細分結構會產生何種影響呢?另外,我國各省份的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等經濟發展結構也呈現較大差異化特征,這些不同的經濟特征又會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農村居民消費的因果關系產生什么作用呢?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需要進一步對本文的基本命題展開異質性分析。
1消費結構分類。筆者將農村居民消費分為基礎型消費、發展型消費和享樂型消費三類,分別計算其占農村人均總消費的占比。基礎型消費由食品煙酒、衣著、居住支出構成;發展型消費由生活用品(除食品、衣著)及服務、交通和通信支出構成;享受型消費由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以及其他消費構成。在此基礎上,筆者分別將基礎型消費占比、發展型消費占比、享受型消費占比三類消費結構類型作為被解釋變量納入方程(1)進行回歸,表6第(1)列顯示,基礎型消費占比對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有效擴大了農村居民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等生存基礎型消費在總消費中的占比;表6第(2)列顯示,發展型消費占比對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了農村居民生活用品和服務、以及交通、通信等發展型消費在總消費中的占比;表6第(3)列顯示,享受型消費占比對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了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等保障型消費在總消費中的占比。
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在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下,之所以出現如此的變動,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農村居民的收入相對還比較低,還處于全面建設小康階段,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提升的條件下,農村居民首先要改善的是食品、衣著、住房等生存型基礎消費。第二,發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絕對量不是沒有增長,而是在基礎型消費增長較快的背景下,占比相對降低了。第三,由于農村居民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支出占總消費的比例較高(2006-2019年各省份平均占比63%),農村居民的基礎消費占比的變動還是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映出農村消費的擴容升級。
2經濟結構分類。我國各省份的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平衡的,經濟結構也呈現較大的差異性,從理論上來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農村人均消費的影響,在不同經濟結構的背景下,呈現出來的因果效應,可能也具有異質性的特征。基于此,我們分別在方程(1)的基礎上,構建了三個交互項,分別是工業化程度(IN)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交互項、市場化程度(MA)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交互項、城鎮化程度(UR)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交互項,并將這些交互項依次納入方程(1)進行回歸。其中,工業化程度以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表示,市場化程度以“樊綱市場化指數”表示,城鎮化程度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表示。
從表7第(1)至(3)列可以看出,三個交互項系數都是顯著為正,這就說明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揮促進農村人均消費的正面作用。該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的背景下,加快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轉型發展步伐、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依然是我國各省份、各地區的中心工作,這些經濟關鍵變量的持續優化,不僅有利于啟動農村內需,對于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經濟內生增長也具有重要意義。
五、機制檢驗
筆者在之前的理論分析中,闡述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農村消費的三條理論機制假說,在中國農村的具體情境下,這些機制假說都有相關文獻闡明的理論依據和經驗支撐,因此本節的核心工作聚焦于實證檢驗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否引起了“預防性儲蓄減少效應”“擠入效應”和“收入效應”發揮作用。
首先,我國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率是數據衡量的難點,主要原因在于預防性儲蓄涉及農村家庭或個人的行為動機,行為動機的精確衡量需要實驗經濟學的行為實驗的研究方法進行支撐,目前,學界還未有相關的學術進展。我們認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目前還處于較低階段,應該可以認為絕大部分農戶的儲蓄動機還是應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我國農村居民目前的人均儲蓄率水平是可以近似的看做預防儲蓄率的替代數據的。基于此,我們利用《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的調查數據,計算了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儲蓄數據,并和家庭人均收入相比,得出了家庭人均儲蓄率,嘗試用其替代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預防儲蓄率。從表8第(1)列可以看出,在人均預防性儲蓄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情況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說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了農村居民家庭的預防性儲蓄率,本文前文的理論以及相關文獻的實證研究表明,預防性儲蓄率的降低能夠有效提高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這就在經驗數據上證實了我們之前提出的預防性儲蓄效應假說。
其次,“擠入效應”強調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農村民生性財政支出的擴張,會相應減少農村家庭的醫療、教育等保障型支出,進而使得農村產生更多的剩余收入進行其他類型的消費。由于農村家庭教育、養老等保障型支出數據缺失,我們根據《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的數據,運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醫療支出占總消費的比例,將其作為家庭保障型支出的代理變量,納入方程(1)進行回歸,從表8第(2)列可以看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的系數顯著為負,這就說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了農村居民家庭的保障型消費,前文理論部分表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降低了農村居民家庭的保障型消費的基礎上,能夠對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產生“擠入效應”,從而激勵農村居民消費。
從理論上看,無論是“預防性儲蓄減少效應”或者“擠入效應”,都意味著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促進農村居民在收入既定情況下的平均消費傾向。筆者將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意愿(平均消費傾向)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行了回歸,發現其系數顯著為正(表8第3列),這就經驗上證明了“預防性儲蓄減少效應”和“擠入效應”的確能夠提升農村居民總的消費意愿,這個發現對于當前究竟通過何種途徑打破制約農村消費的潛在因素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凱恩斯認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所以平均消費傾向也是遞減的。但斯密塞斯、杜森貝里、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等經濟學家的分析表明,除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外,還有其他諸多因素會對消費產生影響,這些收入以外的因素會使消費曲線隨時間延長而逐漸上移,因此,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并不是絕對的。。
再次,產生“收入效應”的前提條件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產生正面影響,也就是說,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能夠促進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為此,我們在方程(1)的基礎上,利用《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獲得數據,將方程的被解釋變量替換成了各省份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數據,表8第(4)列顯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顯著,也就是說,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并不能顯著提升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近年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主要還是由于外出務工收入,農村當地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并不對其外出務工收入水平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提升農村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的提升確實有利于其收入的提高,但發揮作用需要較長的時間積累。另外,在本文樣本期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推行時間并不長,政策效果可能還需要一定時間積累才能體現。因此,從經驗數據上觀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未能產生農村人均消費的“收入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發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并不是通過促進農村提高收入的途徑,而是主要通過擴大農村平均消費傾向的方式,提高了農村人均消費。這個發現并不意味著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對于消費的提升不起作用,事實上,筆者也嘗試運用持久收入方程評估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對于其消費的影響:
VEi,t=α+βRevi,t+VEi,t-1+γControli,t+λi+ηt+εi,t(2)
其中,將農村人均收入(Rev)作為自變量,農村人均消費(VE)為被解釋變量,t-1為滯后一期,這里的兩個變量我們未取對數,用絕對量表示。控制變量集刪去了方程(1)中的農村人均收入(Rev),結果發現農村人均收入(Rev)的系數顯著為正,滯后一期的農村人均消費(VE)的也顯著為正(表8第5列)。可見,農村收入持久提高依然是農村消費提升的有效途徑,但其并不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農村消費的作用途徑。
六、結論與建議
以上部分我們分別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動態效應模型、廣義矩模型、合成工具變量法等方法研究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我國農村人均消費的影響效應,并得出以下結論:(1)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顯著提升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這個結論在進行動態GMM、合成工具變量法等內生性處理,以及替換被解釋變量、增加控制變量、變換估計方法以及分期回歸考察后結論依然穩健的。(2)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顯著增加了食品、衣著、住房等生存型基礎消費占比,但相對卻減少了生活服務、交通通信等發展型消費和文化、娛樂等享受型消費占比。(3)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預防性儲蓄效應和擠入效應,提高了農村人均平均消費傾向,并由此帶動了農村人均消費,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收入效應并不顯著,并不是通過促進農村人均收入的渠道,相應提高農村人均消費。
基于以上結論,為了更有效地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舉措,擴大我國農村消費,彌補外部市場動蕩引起的全球需求萎縮。提出如下建議:(1)制度上要堅決打破城鄉二元壁壘,加快制定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標準,統籌預算、稅收、轉移支付、財權事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銜接,建立資金、人才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城鄉均衡配置的長效機制。(2)持續加大農村民生性財政支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盡快調整公共支出結構的城市偏好、投資偏好和速度偏好,新增財政資源要更多地向農村文教、衛生、社會保障以及基礎設施傾斜,逐步消除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減少“預防性儲蓄”,擴大“擠入效應”,強化公共資金的引致私人消費功能。(3)繼續推動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向高處發展,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調整既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賽道,也能夠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更為寬廣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參考文獻:
[1]?Leland,?H.E.Saving?and?Uncertainty:?The?Precautionary?Demand?for?Saving[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68,82(3):465-473.
[2]?Dreze,?J.H.,?&?Modigliani,?F.Consumption?Decisions?Under?Uncertainty[J].Journal?of?Economic?Theory,1972,5(3):308-335.
[3]?Carroll,?C.?D.How?Does?Future?Income?Affect?Current?Consumption?[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4,109(1):111-147.
[4]?張勛,楊桐,汪晨,等.數字金融發展與居民消費增長:理論與中國實踐[J].管理世界,2020,36(11):48-63.
[5]?高夢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農戶儲蓄:基于8省微觀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10,33(4):121-133.
[6]?劉靈芝,潘瑤,王雅鵬.不確定性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兼對湖北省農村居民的實證檢驗[J].農業技術經濟,2011(12):61-69.
[7]?張勛,劉曉,樊綱.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家戶儲蓄率上升[J].經濟研究,2014,49(4):130-142.
[8]?郭廣珍,劉瑞國,黃宗曄.交通基礎設施影響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型[J].經濟研究,2019,54(3):166-180.
[9]?白重恩,李宏彬,吳斌珍.醫療保險與消費: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2,47(2):41-53.
[10]方福前,孫文凱.政府支出結構、居民消費與社會總消費——基于中國2007-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J].經濟學家,2014(10):35-44.
[11]王健宇,徐會奇.收入性質對農民消費的影響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0(4):38-47.
[12]溫濤,田紀華,王小華.農民收入結構對消費結構的總體影響與區域差異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3(3):42-52.
[13]胡日東,錢明輝,鄭永冰.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14,40(5):75-87.
[14]王小華,溫濤.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及結構演化的差異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5,32(10):90-107.
[15]武力超,林子辰,關悅.我國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測度及影響因素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31(8):72-86.
[16]李丹,裴育.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J].財經研究,2019,45(4):111-123,139.
[17]杭斌,閆新華.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居民消費行為——基于習慣形成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3,12(4):1191-1208.
[18]周茂,陸毅,李雨濃.地區產業升級與勞動收入份額:基于合成工具變量的估計[J].經濟研究,2018,53(11):132-147.
Equalization?of?Urban?and?Rural?Basic?Public?Services?and?Rural?Residents
Consumption:?Theoretical?Hypothesis?and?Empirical?Test
GE?Li-yu1ab,CAI?Xin-rong2,HUANG?Lian-bing1a
(1.?Guang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a.School?of?Finance?and?Taxation,
b.Guangdong?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Finance?and?Tax?Big?Data,Guangzhou??510320,China;
2.?School?of?Finance?and?Taxation,?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98,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effective?improvement?of?the?consumption?level?of?rural?residents?is?the?core?demand?for?the?transformation?of?Chinas?economic?growth?mode?and?the?realization?of?endogenous?growth.?This?paper?uses?static?and?dynamic?models?to?evaluate?the?incentive?effect?of?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in?urban?and?rural?areas?on?rural?consumption,?and?finds?that?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in?urban?and?rural?areas?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per?capita?consumption?of?rural?residents.?The?mechanism?test?found?that?the?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in?urban?and?rural?areas?can?improve?the?average?consumption?tendency?of?rural?residents?through?“preventive?savings?reduction?effect”?and?“crowding?effect”,?but?the?“income?effect”?is?not?significant.?The?research?conclusions?of?this?article?deepen?th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of?promoting?rural?consumption?through?the?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and?provide?an?empirical?basis?for?further?improving?the?level?of?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in?urban?and?rural?areas?in?China.
Key?words: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consumption?of?rural?residents;?preventive?savings;?crowding?in?effect;?income?effect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