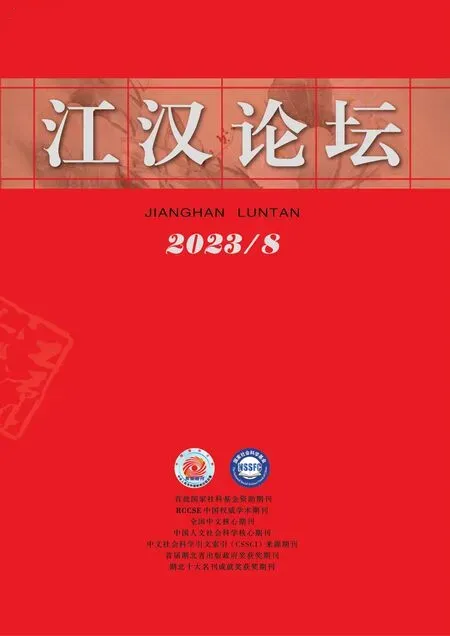新時代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誤區辨析
陳 娟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促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時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推進共同富裕打下了堅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形成思想和理論上的共識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正處于關鍵時期,必須既保持自信昂揚的奮進姿態,又保持理論上的清醒認識,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來把握共同富裕,在關于共同富裕的重大問題上認識準確、心明眼亮,做到“亂云飛渡仍從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指導和根本遵循,但是當前對共同富裕仍存在一些理論認知誤區,及時對這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進行辨析和澄清,有利于廓清是非、正本清源、統一思想,從而在實際工作中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穩步推進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世界各國面臨的世界性難題。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基本矛盾無法得到解決,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2)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3)恩格斯也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這種財產的集中是一個規律……中間階級必然越來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4)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雖然絕對貧困狀況得到緩解,但社會貧富分化更加嚴重。正如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的:“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一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5)所以,盡管一些西方國家也采取一些福利主義措施,但是貧富分化問題卻越來越嚴重。美國和歐洲前1%高收入群體占全體居民收入比重從20世紀70 年代的8.5%和7.5%持續上升到2018 年的19.8%和10.4%。(6)
社會主義制度與共同富裕是內在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一般規律,同時也科學分析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之一。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是增殖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7)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8)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指出:“我們始終堅定人民立場,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9)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我們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著力推進共同富裕,但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和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依然存在。2013 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前20%群體的平均收入是后20%群體的10 倍以上,且無明顯縮小態勢。(10)從世界各國來看,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據此,一些人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解決不了貧富差距問題,我們國家也同樣解決不了共同富裕問題。
促進共同富裕是我們黨孜孜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這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使命決定的。在對未來社會的描述中,馬克思提出“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11)恩格斯也指出未來社會“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12)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告:“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13)我們黨成立之初,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并在實踐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努力把消除貧窮、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來奮斗。1953 年12 月,由毛澤東直接主持、親自起草并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要“使農民能夠逐步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4)這是我們黨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標。“共同的富”,不是少數人的富,這就明確了我們追求的是共同的富裕,即全體人民的富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進一步傳承和弘揚以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特征的共同富裕思想,并在實踐中探索“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鄧小平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1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我們黨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礎上,堅持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共同富裕的內涵作了新的闡釋。他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6)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17)同時他強調:“讓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18)“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19)“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20)由此可見,在我們黨百年奮斗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奮斗目標從未動搖過,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為之奮斗的重要使命。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使我國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前進。有關專家測算,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是4 億人,力爭2035 年達到8 億人,到2049 年超過10 億人。如果我國絕大多數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越來越少,那么共同富裕比較好地體現了全體人民的富裕。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21)由于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存在,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始終代表的是自身利益,廣大勞動人民始終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在這樣的社會盡管可能會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富裕”,或者是少數人的富裕,但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說,千百年來,受生產力水平所限和生產關系制約,共同富裕在人類社會始終無法真正實現。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22)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不僅實現“富裕”具備相應的生產力水平,而且實現“共同富裕”也具備制度基礎。我們黨提出的“共同富裕”這一社會狀態,既是生產力發達的體現,也是生產關系和諧的反映。“富裕”對應的是生產力發展狀況,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共同”對應的是生產關系狀況,反映了社會成員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本質規定性。這里的“共同”是指全體人民,即在黨的領導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的最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個別人、少數人、一部分人,更不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團、特權階層。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不可調和,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而在社會主義中國,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實現共同富裕具備了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囿于共同富裕只是少數人富裕的理論認知是錯誤的,必須明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同時也有利于激發全體勞動人民勤奮工作、拼搏奉獻,為實現共同富裕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二、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物質生活富裕而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富裕最初是對應貧窮來說的,貧困是人類長期面臨的社會現象,是制約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因素,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食品、住房、醫療等多個方面記錄了英國無產階級的物質貧困狀況,比如,“每30 個人擠在一間屋里,空氣少到還不及需要量的1/3”,(23)“只有少數工人家庭才能達到同囚犯差不多的營養”,(24)“工人的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資本生存的一個條件”。(25)因為數千年來物質匱乏、生活貧困是困擾人類生存生活的首要難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著眼于解決人民生活困難、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就把實現生活富足作為首要目標。這時候的共同富裕的確指向物質生活富足。據此,一些人仍固守傳統觀念,認為新時代所說的共同富裕主要指向物質生活富裕。
物質生活富裕是我們黨初期提出共同富裕目標的基本內容。物質生活的滿足是從事其他活動的基礎和前提。恩格斯指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26)這就是說,從人類生活需要來說,物質生活需要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只有滿足了物質生活需要,才可能去追求精神生活需要。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當時中國的經濟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亞洲許多國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1949 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 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2/3。在人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的條件下,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足是最為迫切的,也是最現實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不變價格計算,1952 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79 億元人民幣,1976 年增長到2965 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 年的119 元增加到1976 年的319 元。盡管取得了進展,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依舊不高。1978 年全國還有2.5 億人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這一時期,大力發展生產力,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第一要務。1955 年10 月,毛澤東指出:“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一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27)可見,我們黨最初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基本上就是指向物質生活富足,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符合實際的。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內涵得到豐富和發展,不再單指經濟上的物質生活富裕,還應包括精神生活富裕。在實現物質富裕的同時,更要注重人民精神生活的豐富和充實。這是因為:第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和提升,不僅對物質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要求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方面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這就要求共同富裕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上,還要體現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層面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28)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既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又明確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實現了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有機結合,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征,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29)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綜上所述,新時代強調的共同富裕,不單指物質財富的富足,還應該包括精神方面的共同富裕。
新時代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有機統一體。物質生活富裕,要求我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有質的飛躍,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的顯著優勢”。(30)精神生活方面的富裕,要求我們在理想信念層面,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在價值理念層面,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在落細落小落實上持續用力;在道德觀念層面,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堅持社會主義道德觀,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因此,新時代的共同富裕要堅持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協調發展,不斷促進全體人民“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充裕、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31)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共同富裕的內涵還會與時俱進,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明確新時代共同富裕是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協調、相統一的科學內容,有利于我們克服單純追求物質生活富足的片面認識,同時有利于我們堅持全面系統理念,整體推進各個方面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強調共同富裕的全面性特征時,尤其要把握物質生活富裕與精神生活富裕的關系,即物質生活富裕是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條件,精神生活富裕是在物質生活需求滿足達到一定程度后的更高追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2)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階階段,盡管我國GDP 處于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 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這就要求我們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始終要把經濟建設和發展放在首位,只有在物質生活上達到富裕后,精神生活富裕才有可靠保證。
三、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先富帶后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反映了社會主義平等的價值要求,社會主義平等的實質并不是要消滅一切差別,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范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33)列寧也認為:“我們要消滅階級,從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34)由于長期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以及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年代“吃大鍋飯”和分配政策上的“平均主義”的影響,一些人誤認為共同富裕就應該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或整齊劃一的富裕。
同步富裕是指在實現富裕的時間上同步,沒有先后之分;同等富裕是指在實現富裕的程度上一致,沒有高低之分。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在理論上是有害的,在現實中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是不可實現的。由于每個人的個性稟賦、努力程度、家庭背景、機遇機會千差萬別,實現富裕的時間上必定有先有后。同時由于我國區域差別、城鄉產別、行業差別仍然存在,這就決定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人群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時間上有先有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從本質上看,其實是平均主義思想在作祟。馬克思曾經批判平均主義指出:“任何私有財產本身所產生的思想,至少對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財產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這種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的共產主義者不過是充分體現了這種忌妒和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主義。”(35)恩格斯也提出:“平均主義派和大革命時代的巴貝夫派一樣,是一批相當‘粗暴的人’。他們想把世界變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一切精致的東西,即科學、美術等等,都當作無益的、危險的東西,當作貴族式的奢侈品加以消滅”。(36)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平均主義既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成為“充滿了反動的社會空想”,(37)并力圖“在經濟方面使歷史的車輪倒轉”。(38)就其實質而言,平均主義所主張的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要把社會化大生產倒退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一種唯心主義觀念。在我國計劃經濟年代,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這種方式盡管有效控制了貧富差距,但也挫傷了那些勤勞拼搏、敢于爭先的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同時滋生了等靠要的消極觀念,從而損害了生產力的發展。低水平條件下的平均主義結果導致共同貧窮,這個教訓極其深刻。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實現14 億人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時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區同時達到一個富裕水準,不同人群不僅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時間上也會有先有后,不同地區富裕程度還會存在一定差異,不可能齊頭并進。”(39)
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也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提高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我們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找到了一條差異化、非均衡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路,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40)“先富帶后富”思路,強調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共同富裕目標下,鼓勵和支持有能力有闖勁的人和發展基礎較好的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發展起來,同時要求“先富”的地區和人群通過示范引領和幫助幫扶“后富”的地區和人群,從而促進全社會共同富裕。“先富帶后富”思路是對平均主義的否定,共同富裕承認在普遍富裕基礎上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先富帶后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不同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等于貧富懸殊甚至兩極分化,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允許有適度差異的共同富裕的新路,是適合我國國情的道路。在這一政策指引下,我國東部地區快速發展起來,同時帶動和幫助了中部、西部地區發展,但是中部、西部同東部的發展還是有差距的,即在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東部11 省市GDP 總和為550867.3 萬元,中、西部20 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為461547.9 萬元,東部人均GDP 為90767 元,中、西部為57461 元。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東部地區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指引,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步伐,取得重大戰略性成果。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在有適度差異性基礎上的普遍富裕。這種差異性,體現在時間上有先有后,在程度上有高有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盡管有先富后富之分,富裕程度有高低之別,但所有勞動者同過去相比,必須確保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都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先富帶后富”思路是在承認適度差異性基礎上的普遍富裕的新路,這有利于激發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共同富裕不是要消滅差別,而是要縮小差別,使它保持在合理、可接受的區間。必須強調,“先富帶后富”的思路,是要通過一系列制度保證,確保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共同富裕不是只需分好“蛋糕”而要把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統一起來
實現共同富裕,從表面上看,是一個社會產品公平分配問題。所有社會成員能夠公平分配到社會產品,對美好生活有幸福感、獲得感,這就可以說基本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據此,一部分人認為,促進共同富裕,只要分好“蛋糕”就可以了。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分好“蛋糕”,這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41)恩格斯論述社會主義基本特征時指出:“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42)“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43)這些重要論述揭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與前提,消費資料的分配應遵循按勞分配的原則。為了促進共同富裕,我國構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一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場主體根據國家法律和市場機制來對社會產品進行分配,應強調效率兼顧公平;二次分配主要是由政府來推行分配,比如稅收、社會保障的“五險一金”以及轉移支付等,應強調公平兼顧效率;三次分配主要是指先富起來的企業或個體自愿性質的捐贈,應強調自愿性、道德性。應該說,我國構建的三次分配機制旨在通過“擴中、提低、調高、打非”,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分好“蛋糕”,需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蛋糕”分得是否公平、是否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同;二是分到的“蛋糕”到底有多大,比之前是否有增加。“蛋糕”是否分得公平,這就要求既不能分配差距過大,也不能搞平均主義。貧富懸殊和平均主義都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不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分到的“蛋糕”到底有多大,這就涉及到原有可供“蛋糕”的分量。比如,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 萬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6 萬元的情況下進行分配,大家普遍感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6 萬元情況下分配的獲得感、幸福感強,而在較低收入水平下進行分配,即使分得再好,大家的獲得感、幸福感都不及在高收入水平下分配的感受。此外,促進共同富裕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而促進廣大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更不僅僅是個分配的問題。所以,促進共同富裕,只講分好“蛋糕”,是不全面的、不準確的。
促進共同富裕,不僅要分好“蛋糕”,還要做大“蛋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基礎和前提,是分好“蛋糕”后具有獲得感的重要條件。馬克思強調“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44)實現共同富裕“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45)“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46)生產力狀況決定著社會物質財富的豐裕狀況,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與前提條件。當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發展生產、做大“蛋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共同富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就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我們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平衡而充分發展,做大做強“蛋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因此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大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47)
毛澤東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48)促進共同富裕,內蘊著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兩件事,二者不可偏廢。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質基礎,“蛋糕”太小,分得再好,大家的獲得感也不高。如果不把“蛋糕”做大,只想把“蛋糕”分來分去,“蛋糕”只會越分越小。另一方面,分好“蛋糕”對做大“蛋糕”具有促進作用,分得不好對做大“蛋糕”具有消極作用。如何處理好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關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把‘蛋糕’做大,為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奠定更加堅實物質基礎。”(49)“‘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50)
五、共同富裕不能落后或超越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而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
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51)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實現也是一個歷史動態過程。實現共同富裕也應該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落后或超越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我們制定政策和推進事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依據。在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時,總有一些人脫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提出一些錯誤觀點,并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消極影響。比如,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還是很遙遠的事情,從而產生了不想盡力而為的消極思想。又如,既然確立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應該在現階段不計成本和無條件地實行分配公平,從而產生了不想量力而行的錯誤想法。
促進共同富裕,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既反對歷史唯心主義,也反對歷史宿命論,主張人們在認識和掌握共同富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是可以能動改造世界、創造美好未來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必須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作出更加積極有為的努力。”(52)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期盼的愿景,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既然我們黨肩負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使命,我們就要立足當下盡力而為并朝著這個目標一步步前進。我們黨當前把促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們就要盡力而為做好此事,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今天的中國具備了促進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當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1 萬美元,形成了超過4 億人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10 億人;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人民精神生活更加豐富,等等。這些偉大成就,為新發展階段推動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第二,促進共同富裕是應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客觀要求。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越來越多樣化、高端化,但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成為制約人們獲得感的短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53)第三,促進共同富裕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現實要求。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長期保持較高水平,目前基尼系數穩定在0.46,高于國際警戒線。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從城鄉差別看,2020 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834 元,而農村居民只有17131 元,城鎮居民是農村居民的2.5 倍;從區域差別來看,2020 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多的省市(上海,71121 元)約為最少省份(甘肅,20335 元)的3.5 倍;從行業差距看,2020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采礦業,147196 元)是最低行業(住宿和餐飲業,48210 元)的3 倍。如果我國對收入差距不加以有效控制,勢必會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見,促進共同富裕不僅是長遠目標,更是當前推進事業發展的現實任務。這種迫切的現實任務,必然要求我們盡力而為,朝著長遠目標一件事接著一件事干,積小勝為大勝,而不能停滯徘徊、無所作為。在制定促進共同富裕政策中,我們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促進共同富裕,還必須堅持量力而行。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制定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都要從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出發,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2021 年我國人均GDP 達到1.2 萬美元,但美國大約有6.7 萬美元,北歐發達國家平均有6 萬美元,這種距離還是很大的。在當前,如果我們好高騖遠、盲目攀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政策,不僅會增加財政負擔,還會使人民群眾陷入“福利陷阱”、滋生養懶漢的觀念。過高的標準難以兌現,即使現時兌現了,由于受財力的限制沒有可持續性。如果制定的政策實現不了、兌現不了承諾,還會使人民對黨和政府失去信心信任,帶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此,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要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始終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上,不要好高騖遠,吊高胃口,作兌現不了的承諾。”(54)
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就是要求我們在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時,既要立足當下,又要著眼未來。我們既不能因為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無所作為,也不能做出超越階段的事情而急功近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立足國情、立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思考設計共享政策,既不能裹足不前、銖錙兩較、該花的錢也不花,也不能好高騖遠、寅吃卯糧、口惠而實不至。”(55)在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穩步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六、共同富裕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而是循序漸進、逐步實現的過程
人類社會發展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各種矛盾交互作用的結果,共同富裕的歷史必然性和發展方向的確定性不是以單一線性方式實現的,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需要接續奮斗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社會理想是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6)人們不用為生存而斗爭,成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自覺的真正的主人,共同富裕與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體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57)可以說,共同富裕是人民對美好社會的向往,在這樣的社會里,公平正義的陽光普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真正得到實現。由于對共同富裕的無限憧憬,一些人幻想一夜之間就能實現共同富裕或者跑步進入共同富裕的社會。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沒有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步實現的過程。
必須充分認識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共同富裕既是我們黨的現實任務,更是長期執政的重要目標。共同富裕建立在經濟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但是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這就決定了實現共同富裕任重道遠。這種長期性可以從我們黨對新時代促進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的描繪中窺見一斑。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2020 年到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基本實現。之后,黨的十九大在明確“兩步階段性目標”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三步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到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基本實現,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三步階段性目標”比“兩步階段性目標”更加細化了前進目標內容,而且把“邁出堅實步伐”從2035 年提前到“十四五”末,反映了我們黨對促進共同富裕的明確態度和堅定決心。從“邁出堅實步伐”到“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再到“共同富裕目標基本實現”是我們黨帶領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前進路上的一個個階段性目標,這充分說明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共同富裕,其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再說,到本世紀中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后才算“基本實現共同富裕”,“真正完全實現共同富裕”還要貫穿社會主義中、高階段,我們更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和堅持不懈的奮斗。
必須充分認識實現共同富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復雜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哪一塊有短板都不可能實現。新時代,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任務艱巨繁重,道路坎坷曲折。雖然我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返貧和新的致貧風險依然存在,即使在消除絕對貧困問題后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比消除絕對貧困問題要困難得多、復雜得多。當下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任務中,無論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還是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每一項任務都不是簡簡單單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需要付出艱辛努力和克服重重障礙。此外,在促進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一些“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時有發生,增加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復雜性、曲折性。比如,臺海局勢的演變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遏制打壓、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波譎云詭,都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從而給實現共同富裕帶來了不確定性風險。
由于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我國在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并沒有采取一刀切和全面鋪開的冒進做法,而是采取先行示范、榜樣引領、逐步推廣的模式。2021 年6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頒布,賦予了浙江重要改革示范任務,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做“試驗田”。《意見》明確提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選取部分地區先行先試、做出示范。”隨后,浙江省為貫徹《意見》精神,也印發了《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 年)》。兩份文件的出臺充分說明,面對共同富裕這個艱巨任務,我們要采取循序漸進的模式來逐步推進,而不能采取畢其功于一役的急于求成的做法,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做法和有效經驗。
當前,我們初步具備了促進共同富裕的物質條件,但并不是說實現共同富裕水到渠成了。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的估計。在這一進程中,我們既不能消極等待,也不能過分急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辦好這件事,等不得,急不得。”(58)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耐心恒心,一件事一件事辦好,一步一個腳印,有序地完成分階段的目標,然后逐步完成共同富裕這個大目標。
思想是行動的指引,沒有正確思想的指引,行動就會偏離正確的航標。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正確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核心要義,澄清模糊認識,批駁錯誤觀點,為促進共同富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從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注釋:
(1)(4)(5)(35)(43)(44)(45)(46)(5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83、729、184、710、533、538、538、537 頁。
(2)(8)(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200、200 頁。
(3)(12)(22)(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1、299、299、113 頁。
(6)(10) 劉元春、宋楊、王非、周廣肅:《讀懂共同富裕》,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版,第10、15 頁。
(7)(32)(5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6、591、53 頁。
(9) 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3 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 頁。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661-662 頁。
(15)(40)《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0、374 頁。
(16)《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 頁。
(17)《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83-84 頁。
(18) 習近平:《在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 年11 月25 日。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年版,第35 頁。
(20)《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中國人民生活一定會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日報》2017 年10 月26 日。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 頁。
(23)(24)(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4、773、555 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 頁。
(27) 《毛澤東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95 頁。
(28) 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 年10 月1 日。
(29)(30)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1、271 頁。
(3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人民日報》2021 年6 月11 日
(34) 《列寧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816 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 頁。
(37)(38) 《列寧全集》第15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1、191 頁。
(39)(47)(53)(54)(58) 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20 期。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 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 頁。
(48) 《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7 頁。
(49)(5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6、97 頁。
(5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 頁。
(52) 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503 頁。
(5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5—21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