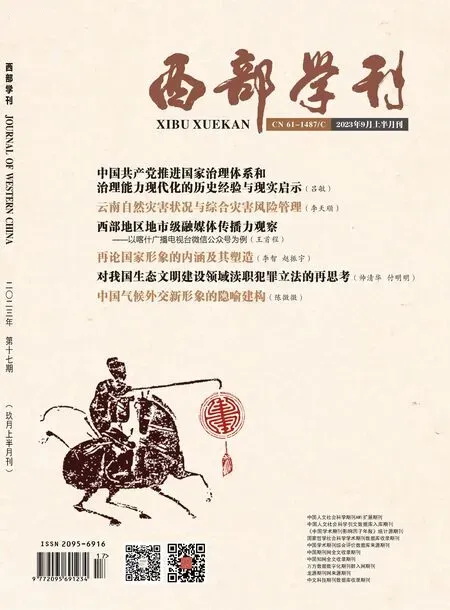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立法的再思考
帥清華 付明明
(1.南昌航空大學 文法學院,南昌 330063;2.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廈門 361005)
刑法是保障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最嚴厲的手段,通過刑法手段促使環境執法者依法執法,有利于有效規范生態文明建設的秩序,穩步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然而,由于刑事立法等原因,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執法者不依法履行職責的瀆職犯罪行為仍時有發生,嚴重妨礙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本文現就此作一探討。
一、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的立法現狀
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包括范圍很廣,從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領域,到水、森林、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領域。 相關管理部門眾多,既包括生態環境部、水利部、自然資源部、國家林草局等專門管理部門,又包括農業農村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具有部分管理職能的部門。 這些部門在履行生態文明建設管理職責時,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實施各項管理行為。
我國法律嚴格規范了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相關管理部門的管理職責,若管理部門未認真履行職責導致嚴重危害后果構成犯罪的,則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處罰。 對于瀆職犯罪行為,《刑法》規定了相關罪名,如第三百九十七條的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徇私舞弊罪,第四百零七條的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第四百零八條的環境監管失職罪,第四百一十條的非法批準征占用土地罪、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罪,合計7 個罪名。 此規定具有如下特點,(1)法條競合關系。 上述法條之間存在競合關系,屬于特別關系的法條競合,其中《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屬于一般法條,第四百零七、四百零八、四百一十條屬于特殊法條;(2)結果犯立法模式。 我國瀆職罪的立法都是以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也遵循此種立法模式。
二、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立法存在的問題
(一)傳統結果犯立法模式不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傳統結果犯要求造成特定危害后果方才構成犯罪,此種結果的衡量標準是導致“人身或者財產重大損失”[1],此種立法保護的是人類利益而忽略了生態利益,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不相符。 以《刑法》第四百零八條為例,(1)本罪與1997 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相對應,都要求出現法定的危害結果,即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判斷是否系“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標準主要是看人身傷亡與財產損失的程度。 隨著生態法益日漸受重視,《刑法修正案八》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污染環境罪”,由此本罪開始聚焦于生態法益的保護。 2013年“兩高”出臺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一條規定了符合本罪構成要件的13 種情形,其中第一至第六種情形不要求本罪出現危害后果。 因此,《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由原先的結果犯轉變成了危險犯。與此相對應,作為生態環境管理者的瀆職罪卻沒有任何變化,“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仍然是本罪的基本構成,這導致許多難以確定具體損失額的瀆職行為無法以瀆職犯罪來追究刑事責任[2]。 (2)傳統結果犯的“結果”內容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不甚相符。 傳統結果犯立法體現了傳統刑法的法益要求,即保護的是人類利益而非生態法益,故此結果是“人身或者財產的重大損失”,不直接保護生態法益,其對于生態法益的關注是將其作為人類利益所指向對象而言的。 鑒于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罪必須保護生態法益,故其應該將生態法益作為直接保護對象。 為此,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的立法應該以“生態利益損失”作為衡量犯罪成立與否的標準。
(二)法條競合處理上不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1.特殊法條立法上存在的問題。 一是法定刑偏低,該問題上文已提及,不復贅述。 二是特殊法條不是針對該領域的所有瀆職犯罪,例如《刑法》第四百零七條僅僅規定森林資源管理過程中采伐許可發放的環節。 根據《森林法》規定,森林資源管理涉及制定規劃、森林保護、造林綠化、經營管理、監督檢查等過程,采伐許可僅僅是經營管理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針對此一個環節來立法,導致法條適用性不強。 以江西省為例,其三級法院歷年來審理森林資源管理領域的瀆職犯罪案件合計98 件,但是非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案件僅為6 件①本數據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整理而成。。 再如《刑法》第四百一十條所涉及的“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罪”和“非法批準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此條僅規范了發生在土地許可環節的瀆職行為。 根據《土地管理法》,土地資源管理包含行政規劃、行政處理、行政檢查、行政許可等諸多環節,但是《刑法》第四百一十條僅針對土地資源行政許可環節立法,同樣導致法條適用性不強。 以江西省為例,其三級法院歷年來審理土地資源管理過程的瀆職犯罪案件合計111 件,但是適用《刑法》四百一十條的瀆職犯罪案件僅為1 件②同上。。 由于特殊法條適用范圍過窄,導致其基本處于閑置狀態,浪費了立法資源。
2.特殊法條適用存在的問題。 根據法條競合的適用原理,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7 個瀆職罪屬于法條競合中的特別關系,此種特別關系的競合優先適用的是特殊法條。 但是考察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具體判例,可以看出在處理本法條競合之際,絕大部分競合案件都是適用一般法條,即《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 以江西省三級法院判處的此類案件為例,自2014 年以來江西省判處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案件共計319 件,其中濫用職權罪為132 件、玩忽職守罪為157 件,加上徇私舞弊罪20 件,涉此三個罪的案件數合計為309 件。 判處的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案件為6 件、環境監管失職罪案件為3 件,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罪或非法批準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案件為1 件③同上。,合計僅10 件。
(三)對生態法益的保護未達到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1.從刑事立法角度看未直接體現生態利益。 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罪對應的是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管理行為,根據領域不同而由不同的法律規定了相應的管理職責,例如在污染防治領域,《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規定了管理部門的具體職責;在自然資源保護領域,《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等法律規定了管理部門的具體管理職責。 這些管理職責所要實現的目標大都體現為該具體法律的立法目的。 上述環境法律近年來均經過修正,其立法目的均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即兼顧人類利益與生態利益。 然而,與之相應的瀆職罪立法自1997 制定以來未曾發生變化,此種瀆職罪立法要求犯罪成立的標準是導致人類利益重大損失,即對“人身或者財產”造成重大損害。 因此,現有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罪立法不足以實現對生態利益的保護。
2.從刑事司法角度看難以實現生態利益。 刑事司法角度是否能夠直接保護生態利益的最主要手段是刑罰。 從我國《刑法分則》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刑罰來看,當前法院對于環境犯罪人基本都會判處生態修復非刑罰措施,然而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人很少判處生態修復非刑罰措施。經過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江西省僅有1 件瀆職犯罪案件適用了生態修復非刑罰措施,即南豐縣法院判處的王某玩忽職守案①(2018)贛1023 刑初88 號刑事判決書。。 從我國歷年發生的重大環境事故來看,基本每個環境事故中都包含了瀆職犯罪行為與環境犯罪行為,即絕大部分環境事故是兩種犯罪行為競合所導致的,故此類瀆職犯罪者必須承擔生態修復的責任。 鑒于我國司法機關對此類瀆職犯罪案件基本未適用生態修復非刑罰措施,此種司法現狀不利于維護生態利益,無助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四)現有瀆職罪的法定刑不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根據《刑法分則》第九章瀆職罪第三百九十七至四百一十九條的規定,30 多個瀆職罪罪名的法定刑存在巨大差別。 “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其法定刑最高為7 年有期徒刑,而與其存在競合關系的其他特殊法條所涉及的瀆職罪,刑期差別很大,例如第三百九十九、第四百條所涉及的7 個司法領域的瀆職罪,其法定刑最高都是10 年有期徒刑。 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幾個罪名法定刑都很輕,如“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環境監管失職罪”的法定最高才3 年有期徒刑。 從一般意義上考慮,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的危害性很大,尤其是在我國發生的特別重大的環境事故中,其損失一般以億元起算,加上間接損失及治理費用等,甚至達到幾十億、上百億元。 據此判斷,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所產生的危害后果未必小于司法領域的瀆職犯罪所產生的危害后果。 再比如《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了“環境監管失職罪”與“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罪”兩個罪,這兩個罪名極為不協調:(1)根據法條規定,前者屬于失職罪,后者屬于瀆職罪;(2)前者主觀上為過失,后者包括故意和過失;(3)前者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后者最高刑為十年有期徒刑。 這就隱含著環境污染防治領域的危害小于食品、藥品監管領域的危害的邏輯。 造成此種問題,原因可能在于前者是在1997 年刑法制定的,之后未曾修改,實際上該種瀆職犯罪案件極少。 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此種瀆職犯罪處于高發態勢且嚴重危及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這表明過輕的法定刑已經不適合我國的國情,不足以保護生態文明建設的管理秩序。
三、完善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立法的基本原則
(一)明確生態法益為危害結果的內容
既然瀆職罪要求特定的危害結果,在堅守此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考慮修正危害結果的具體內容,即此危害結果需放棄傳統的人類法益標準,而代之以生態法益損害作為危害結果的內容。 此種新結果犯立法模式主要體現在專屬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罪,即《刑法》第四百零七條、四百零八條、四百一十條規定的四個罪。 然而,這四個罪涉及污染防治與自然資源保護兩個領域,其瀆職犯罪要求的變化未必相同。(1)《刑法》第四百零七條應該涵蓋自然資源管理領域,并以自然資源損失的程度作為犯罪成立與否的標準。 與此瀆職罪相對應的環境犯罪是《刑法》第三百四十條至第三百四十五條,這些破壞自然資源領域的行為都需要產生特定危害后果方才構成犯罪,相應的瀆職犯罪也應該采取結果犯的立法模式。 (2)環境監管失職罪應該與污染環境罪相對應,在犯罪構成上采取相同的立法模式,以嚴重污染環境為犯罪成立與否的標準[3]。 即環境監管失職罪應該拋棄人類利益損失作為犯罪結果的衡量標準,而代之以“嚴重污染環境”作為“結果”成立的標準。
(二)理順法條競合關系的適用
考慮到瀆職罪第三百九十七條與第三百九十八至四百一十九條之間的法條競合關系,在立法過程中必須兼顧一般法條與特殊法條的關系,作為特殊關系的競合,要明確條文之間的關系及適用。 (1)考慮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犯罪的特殊法條與一般法條的均衡性,即規范某一領域的特殊法條必須包容該領域的所有瀆職犯罪行為,且刑罰設定必須重新設計,要根據生態環境損失的程度來確定相應的刑罰,通常其最高刑罰不得低于一般法條所設定的刑期。 (2)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瀆職犯罪行為可以區分為自然資源保護與環境污染防治兩個領域,針對此兩個領域設定相應的瀆職罪名。
(三)將生態法益作為直接保護對象
將生態法益作為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瀆職罪立法直接保護的對象,其實現方式主要在刑事立法中直接體現,即明確規定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理應適用此條款。 生態修復作為懲罰措施,與《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的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懲罰手段性質類似,皆屬非刑罰措施。 我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條將生態修復作為環境侵權的法律責任方式之一,與之相對應,《刑法》應該做出調整。可以考慮將生態修復作為刑罰手段之一,以彌補現行刑法難以保障生態利益的缺憾,也有利于體現刑法維護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價值取向。 因此,可以考慮增設生態修復作為非刑罰措施,具體是修正《刑法》第三十七條,在此條款中增加“生態修復”方式,使之成為法定的非刑罰措施。
(四)提高此類瀆職犯罪的法定刑
鑒于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的法定刑偏輕,應在刑事立法層面進行調整。 具體可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法定刑為衡量標準。 該法條第一款規定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的法定刑最高為7 年有期徒刑,第二款規定徇私舞弊罪的法定最高刑為10 年有期徒刑。 參考此標準,應提高自然資源破壞與污染防治兩個管理領域瀆職犯罪的法定刑,確保刑法對相應瀆職犯罪人的威懾作用。
四、完善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瀆職犯罪立法的建議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條附加一條,作為第三十七條之二:“因觸犯本法導致生態環境嚴重污染或者破壞,可以責令其采取旨在保護、養護或者改善生態環境的特殊措施。”
(二)將《刑法》第四百零七條改為:“自然資源管理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致使生態環境破壞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4]
(三)將《刑法》第四百零八條改為:“負有污染防治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導致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