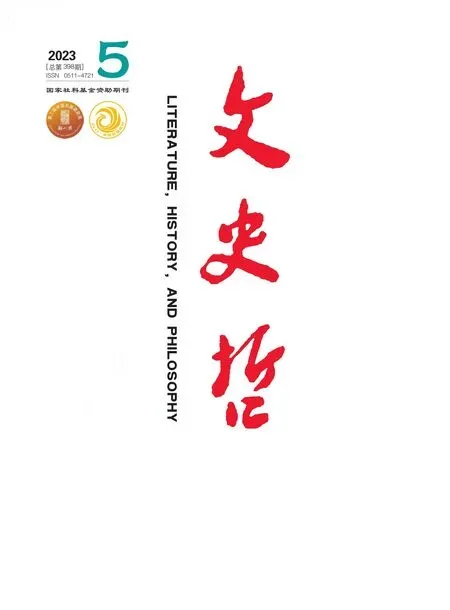戊戌維新敘述的建立:《戊戌政變記》的成書、傳播與接受
宋 雪
引 言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決意變法,然而僅僅103天之后,政變迅速撕裂了維新運動所架構的宏偉藍圖。慈禧重新聽政,新政悉皆取消,光緒被囚瀛臺,維新士人或就戮,或遠戍,或罷官,或流亡,清廷諭令通緝犯黨,查禁報刊,恢復舊制,試圖回到傳統帝制的軌道上。不過,與歷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政治斗爭的勝利者掌握話語權不同的是,戊戌維新的歷史敘述主要由失敗者一方建立。流亡海外的康梁,借助報刊輿論的鼓吹,重述變法故事,締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話。
政變后,康有為不斷申說“我歷盡艱難辛苦,變維新之大政,拼萬死舍一身出來,皆為保全中國四萬萬之人民之眾起見”(1)羅裕才筆記:《康南海在鳥喴士晚士咑埠演說》,《清議報》第17冊,1899年6月8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061頁。的經歷,以“奉詔求救”的姿態,求助于英國、日本和海外華僑,并以此建立起“戊戌變法之魁”(2)王樹枏:《南海康君墓表》,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34頁。視角下的敘述框架。不過,由于王照的揭發,康氏衣帶詔“作偽之真相盡為日人所知”(3)馮自由:《戊戌后孫康二派之關系》,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增訂本),第273頁。,各處之保皇運動,亦未取得理想成績。戊戌歲暮,旅居日本的康有為將自身經歷寫成《我史》一書,但脫稿后即出游歐美,正式刊行遲至半個多世紀以后(4)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4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康有為身為維新領袖,其發起公車上書、倡立學會、上書進呈等都是維新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事件,但在變法落幕后,整個維新敘述體系的建構主要由其弟子梁啟超完成。
與康有為相比,梁啟超在維新運動前后的經歷更具傳奇色彩。前者于1895年中進士,以工部候補主事的身份奔走政治,尚引起時人側目;而梁啟超科舉會試不售,1898年夏以舉人身份獲光緒召見,“僅賜六品頂戴”,“仍以報館主筆為本位”(5)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頁。。維新期間,梁啟超以主《時務報》撰述、主講湖南時務學堂名著于時;戊戌春入京后,為康南海的政治主張贊畫奔走,雖非政壇人物,亦由宣傳之力而聲名鵲起。政變后,“康西游而梁東渡,梁氏歷主《清》《新》兩報”(6)彬彬:《梁啟超》,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5頁。,以一支健筆,“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余地”(7)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87頁。,并以局內人身份撰成《戊戌政變記》一書,建構起維新視角下的戊戌史。作為政治上的邊緣人物,梁氏并未在實質上參預政事;然而,借助報刊的力量,時年26歲的梁啟超成為當之無愧的“輿論之驕子”(8)吳其昌:《梁啟超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5頁。。雖然“梁于康氏亦步亦趨”,“著文率皆引申其師之說”(9)彬彬:《梁啟超》,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15頁。,但將戊戌這一“政治上徹底失敗之運動”(10)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86頁。著為“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11)任公:《南海康先生傳》,《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6冊,第6305頁。,實有賴于梁啟超。
《戊戌政變記》1898年12月起先后在《東亞時論》和《清議報》連載,1899年5月出版單行本,此時距離政變發生僅有數月,在坊間輿論紛紜之時,梁啟超以局內人身份對變法做了最初的總結,也奠定了以康南海為首腦和主線的戊戌敘事框架(12)戚學民:《〈戊戌政變記〉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82頁。按,戚文對《戊戌政變記》成書的原因和過程進行了細致研究,對筆者多有啟發。本文涉及相關問題時,尊重戚文的先行研究。。不過,“此記先生作于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13)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陳美延編:《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66頁。,出于“感情作用所支配”和政治宣傳的目的,“將真跡放大”,“言之過當”(1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10頁。,并非一部信史(15)關于梁氏記述與史事之間的區隔,吳相湘、劉鳳翰、戚學民、茅海建等學者已有詳細考訂。吳相湘:《翁同龢康有為關系考實——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訂(上)》,《學術季刊》第4卷第2期,1955年,第97-108頁;吳相湘:《戊戌變政與政變之國際背景——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訂(下)》,《學術季刊》第4卷第3期,1956年,第74-83頁;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8-9頁;戚學民:《〈戊戌政變記〉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7-108頁;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1-2頁。。然而,正是這樣一部作者“不在廷臣之列,亦不在司官之列”,行文“實多巧為附會”“毀譽任情”(16)王照:《復江翊云兼謝丁文江書》,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154-155頁。的作品,問世后迅速完成了經典化,成為“敘說戊戌變法史的一個母本”(17)歐陽哲生:《從維新烈士到思想彗星——梁啟超筆下的譚嗣同》,《讀書》2018年第12期,第52頁。。考察維新視角下戊戌敘事體系的建立,《戊戌政變記》的成書發行和閱讀接受,均值得關注。
一、旅日生活與《戊戌政變記》的成書
“八月政變,六君子為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18)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11,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8頁。梁啟超《三十自述》記政變出亡僅寥寥數字,而在看似平常的字面之外,其實有壓在紙背的驚險經歷和復雜心情。
八月初六(9月21日)早朝,慈禧宣告訓政,“十時即有圍南海館之事”(19)畢永年:《詭謀直紀》,湯志鈞:《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8頁。。當時梁啟超正在瀏陽會館譚嗣同處(20)梁啟超:《譚嗣同傳》,《清議報》第4冊,1899年1月22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209頁。,消息傳來,梁氏“電上海孺博告變”(21)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康有為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4頁。,并偕譚嗣同訪李提摩太“商討辦法保護皇帝”,決定“梁啟超去見日本公使”(22)李提摩太:《中國的維新運動》,林樹惠譯,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565頁。。梁啟超赴日本使館訪代理公使林權助(23)林權助:《戊戌政變的當時》,張雁深、張綠子譯,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第571-572頁。,留宿日本使館。次日,梁氏斷發易服,在日本領事鄭永昌的陪同下乘火車前往天津(24)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804頁。,在日本領事館逗留數日,擬乘9月27日自天津港啟程的玄海丸赴日。25日晚,梁啟超在鄭永昌等人的陪同下乘船出海,途中被北洋大臣汽船追上,雙方發生爭執。26日晨抵塘沽,梁氏登上大島號(25)《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致外務次官鳩山和夫》(1898年9月30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097-1098頁。。隨后,王照亦以政治避難者身份登上大島艦。由于“在清國水域內無法將二人轉移到商船上”,乘坐玄海丸的計劃不得不改變。10月2日,林權助致電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請求“令大島艦駛往日本并相應盡快派另一艦至天津”(26)《日本駐中國公使電日本外務大臣大隈》(1898年10月2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16頁。。次日,大隈批準了這一請求,“命大島艦俟接替其位置之炮艦抵達天津,即駛返日本”(27)《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電日本駐北京公使》(1898年10月3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21頁。。10月4日,日方安排須磨艦接替(28)《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電日本駐北京公使》(1898年10月4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23頁。,因其遲遲未到,大島艦延緩起航(29)《日本駐中國公使電日本外務大臣大隈》(1898年10月6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34頁。,10月12日起碇,先往吳淞(30)《日本駐煙臺領事官電日本外務大臣大隈》(1898年10月12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64頁。,再至日本,10月17日登岸(31)據狹間直樹考察,登陸地點是吳(廣島南部的一個軍港)。狹間直樹:《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高瑩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頁。。21日,梁啟超抵達東京(32)據近衛篤麿日記,梁于20日夜半由廣島乘車,21日抵東京,下榻于麴町區平川町四丁目三番地三橋常吉的旅館。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大陸雜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第3頁。,由日本進步黨出資賃屋(33)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2頁。據日本警視廳記錄,梁啟超10月22日搬到牛込區早稻田鶴卷町四十番地高橋琢也處。《警視總監西山志澄致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函》(1898年10月24日),石云艷:《梁啟超與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5頁。。自9月26日登艦到10月17日下船,梁啟超居大島艦中凡22天。
9月27日,梁啟超和王照聯名致信伊藤博文、林權助,表達對營救出險的感激,并請日方“念兄弟之邦交,顧東方之大局”,“與英、米諸國公使商議,連署請見女后,或致書總署,揭破其欲弒寡君之陰謀”(34)梁啟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1898年9月27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9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635-637頁。,試圖借日本力量干涉中國政局。當時六君子尚在獄中,大島艦停泊在塘沽水面,梁啟超仍對營救抱有希望。此時距離政變僅僅6天,外間風聲鶴唳,謠言紛紜,“不在政局之內”(35)王照:《復江翊云兼謝丁文江書》,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153頁。的梁啟超短時間內其實難以把握局勢動向,而康有為正在赴港途中,師徒之間難以通氣,信中的立場和訴求,主要來自梁啟超的判斷,亦不排除某些材料出自王照。這封信沒有提到康有為,也未言及光緒密詔。
9月25日,康有為在吳淞口外英國輪船琶理瑞(Ballarat)上,與英國領事班德瑞(F.S.A.Bourne)談話時,首次提到光緒密詔,并說“皇上曾罵西太后只是咸豐的妃子,而不是正后,也不是他自己的母親”(梁、王信中稱慈禧“女后”,而無光緒罵慈禧之事),且斷言帝后沖突無法調和(36)《白利南致英國外交部次大臣信》(1898年9月26日),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第527頁。。隨后在赴港途中,康有為同英國領事戈頒(Henry Cockburn)談話,也闡說了相似的意見(37)Henry Cockbur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K’ang Yu-wei on Voyage from Shanghae to Hong Kong,” (September 27-29, 1898) Inclosure 2 in No.40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Presented to both House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March 1899), 308-309.。對照康有為的兩次談話記錄和梁、王的聯名信,雖都強調光緒體健無病,慈禧親俄并謀劃廢立等事,但梁、王的措辭要溫和得多。這與王照調和兩宮的立場相關,二人寄希望于“他邦干預內政”(38)梁啟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9集,第636頁。,但未有過激言辭。以維新領袖的身份宣揚“奉詔求救”,實出自康有為。
流亡中的康有為反復申說“仆受皇上密詔,令設法求救”,以光緒代言人的姿態,希望借英國力量“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權力”(39)康有為:《戊戌與李提摩太書(第一信)》,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1冊,第413-414頁。。9月29日晚,康有為抵達香港(40)《官犯抵港》,《申報》1898年10月14日,第2版。,翌日與英國海軍少將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會談。康有為稱其“誓死以救我皇上”(41)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康有為自編年譜》,第66頁。,但根據貝思福的記錄來看,此說不實(42)Lord Charles Beresford, The Break-up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Its Present Commerce, Currency, Waterways, Armies, Railways, Poli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York &London: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1899), 191-195.。10月6日,康有為接受《中國郵報》(ChinaMail)采訪,這也是其出亡以來首次公開發表意見(43)“The Crisis in China” (Hong Kong, October 7),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ober 17, 1898, 738-741.。在此前與英國領事談話的基礎上,康有為擴充了若干細節,包括慈禧挪用軍費、宦官舞弄權柄等,并著意突出自身在變法中的重要影響。不過,康氏數番說辭并未取得實際成效,英國領事認為康是“一位富于幻想而無甚魄力的人,很不適宜作一個動亂時代的領導者”(44)《白利南致英國外交部大臣信》,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第527頁。;“一個狂熱的人和空想家”(45)《亨·戈頒來函》(1898年10月19日),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895-1912)》上冊,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123頁。。康有為所篤信的“英國必會救援”(46)“The Crisis in China” (Hong Kong, October 7), 740.,只是一廂情愿。
在求救于英國未有明確結果的情況下,10月7日,康有為在與上野季三郎會面時,請求過境日本,并得到大隈重信同意(47)《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電日本駐香港領事官上野》(1898年10月9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58頁。。10月19日,康有為一行乘河內丸前往神戶(48)《日本駐香港領事館二等領事上野致外務大臣大隈》(1898年10月20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87頁。,25日晨登陸,隨即乘火車前往東京,當日夜半抵達麴町區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旅舍(49)《警視廳總監西山志澄致大隈外務大臣》(1898年10月26日),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1193頁。,后遷入牛込區加賀町一丁目三番地(50)《警視總監西山志澄致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函》(1898年10月29日),石云艷:《梁啟超與日本》,第455-45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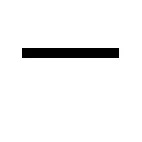
康梁抵日之后,生活方面受到大隈重信的照顧(55)林權助:《戊戌政變的當時》,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3冊,第573頁。,梁啟超在家書中亦提到“吾在此受彼國政府之保護,其為優禮,飲食起居一切安便”(56)梁啟超:《與蕙仙書》(1898年10月29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8頁。。然而,當梁啟超“舍館既定,輒欲晉謁”(57)梁啟超、王照:《致大隈重信》,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9集,第638頁。時,大隈總是避之不見;志賀重昂雖表示對“貴下今遭時之陽九,流寓異邦”(58)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3頁。的相憐之情,但未給出任何政治上的承諾。三國干涉還遼之后,日本在外交方面十分謹慎,“考慮當時日本政治情況,大隈重信作為首相接受梁啟超請求的條件,是絕不可能的”(59)狹間直樹:《初到日本的梁啟超》,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后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第223頁。。在日本使館幫助下出險的梁啟超,對日方具有好感,幻想借助日本幫助光緒帝復位。然而,在當時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僅以縱橫家的方式“作秦庭七日哭”,并不足以成此“男兒奇功”(60)梁啟超:《去國行》,《亞東時報》第4號,1898年11月15日,第28頁。。
《致大隈重信》署為梁啟超與王照合發,但很可能主要出自梁的手筆。這封信在發給大隈之外,還寄給了日本東邦協會會長副島種臣和副會長近衛篤麿(61)根據近衛篤麿日記,該信11月2日收到。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3頁。,并以《支那志士之憤悱》為題,公開發表在東邦協會機關報《東邦協會會報》上(62)《支那志士之憤悱》,《東邦協會會報》第53號,1898年12月20日,第9-18頁。按,本文所涉“支那”“清國”等語,僅出于保存歷史資料原貌之意,無其他含義,特此說明。。該文未具名,落款為10月30日。東邦協會成立于1891年,是日本重要的興亞組織。不過,這封信在《東邦協會會報》并非首發,此前數日已先行刊于《日本人》和《東亞時論》。
1898年12月5日,《日本人》刊發梁啟超的署名文章《論中國政變》,題注為“寄東亞會書”(63)梁啟超:《論中國政變(寄東亞會書)》,《日本人》第80號,1898年12月5日,第20-24頁。;五天后,該文又發表在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刊物《東亞時論》創刊號上,改題《上副島、近衛兩公書》(64)梁啟超:《上副島、近衛兩公書》,《東亞時論》第1卷第1號,1898年12月10日,第21-24頁。。《日本人》創刊于1888年,由政教社發行,志賀重昂和三宅雪嶺先后擔任主筆;東亞同文會成立于1898年11月,會長為近衛篤麿(65)《東亞同文會章程》(1899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藏本,無頁碼。。與《致大隈重信》對照,在三種雜志上刊發的文本,除首末段有所調整外,內容大致相同(《日本人》刊本首段寒暄語與另兩種版本不同,且未署日期),只是《東亞時論》隱去了聲討慈禧的93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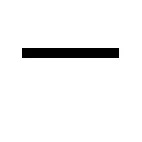
11月2日,在收到梁啟超來書的同時,近衛篤麿還收到了康有為的來信。康氏以異常急切的語氣,表達了“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的愿望,希望日本“急輔車之難,拯東方之局”,并請求同近衛見面(68)康有為:《致近衛篤麿書》,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3頁。。當時,近衛篤麿身兼多職,在日本政壇具有重要影響力。11月12日,康有為在林北泉與柏原文太郎的陪同下與近衛篤麿會面。面對康有為的求救,近衛一方面批評維新運動“改革過于急進”,同時申明“外交之事,絕非貴我兩國所能解決,如此之大事,必觀察歐美列國之態度決定之,甚難斷言可否”。隨后的11月27日,梁啟超、羅普亦往訪近衛,“梁之言,大致與日前康之語類似”。在近衛看來,康梁“總是以皇帝復位之事相談”,但此事“非如康所說的那么容易”,并且“今列國在互相監視之際,不能不采取慎重態度”(69)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7-8頁。。康梁抵日后不久,日本政局出現動蕩,1898年11月8日,憲政黨分裂,大隈重信內閣倒臺,山縣有朋內閣成立(70)《政變小史》,《太陽》第4卷第23號,1898年11月20日,第259-261頁。。隨著大隈的下野,康梁的接待方從政府變成了非執政黨。與大隈政府同情維新不同的是,新任外相青木周藏更傾向于與清政府合作。在此情形下,日方對康梁的訴求更加謹慎。
雖然康梁在書札和談話中反復強調政變系出于帝后矛盾,但在二人赴日之前,日本輿論即已注意到改革過于急進對維新失敗的影響,甚至將康有為等人稱為“急進黨”“急進派”(71)天默生:《漢土政變と支那分裂の原因》,《東邦協會會報》第51號,1898年10月20日,第72-73頁。。其實,早在維新運動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康廣仁即認為“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72)康廣仁:《致易一書》,《康幼博茂才遺稿》,《戊戌六君子遺集》下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619-620頁。;變法失敗后,貝思福也曾面責康氏領導的改革進行太急,方法不當(73)Lord Charles Beresford, The Break-up of China, 194-195.;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 MacDonald)更是認為康黨不明智的舉動,就是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74)Claude M. MacDonald, “Sir C. MacDonald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Peking, October 13, 1898), No.40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Presented to both House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March 1899), 306.。
客觀上講,維新運動缺乏規劃,急于求成,確是造成“其黨立敗,進銳速退”(75)《伊藤侯論支那》,《清議報》第1冊,1898年12月23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43頁。結果之一端;然而,流亡中的康梁若承認這一點,就等于承認維新派自身的失誤與不足,不利于以尊皇名義對外求救,亦不利于在海外華僑中建立威信。因此,聽聞日本此類輿論時,康梁均急忙辯白。11月3日,梁啟超致信品川彌二郎,力證變法之挫敗并非源自急進:
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目仆等為急激誤大事者。然仆又聞之松陰先生之言矣。曰:“觀望持重,今正義人比比皆然,是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見血久矣,一見血丹赤噴出,然后事可為也。”仆等師友共持此義,方且日自責其和緩,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數千年之疲軟澆薄,視貴邦幕末時,又復過之,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強之時也。(76)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5頁。
為了表達對日本維新志士的景仰之情,梁啟超更名吉田晉,借“新日本之創造者”(77)梁啟超:《敘》,吉田寅次著,梁啟超節鈔:《松陰文鈔》,上海:廣智書局,1906年,第1頁。吉田松陰的言論以正名。康有為在被近衛篤麿批評“改革過于急進”時,亦即提出反駁(78)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7頁。。為了證明對外求救的正當性,康有為發表《奉詔求救文》,抄送各處。該文羅列那拉氏十大罪名,痛詈其以“偽臨朝太后”身份“毒害我家邦”,“非惟亡我二萬里之大清,實以亡我四千年之中國”;同時,歌頌光緒之神武英明,變法不成全因牝朝篡政,幽廢皇上(79)康有為:《奉詔求救文》,湯志鈞:《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第52-57頁。。但其中的關鍵性文本即光緒密詔,實際經過了康有為的改竄(80)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528-562頁;湯志鈞:《關于光緒“密詔”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280-293頁。,文末譚嗣同的絕命書,亦出于杜撰(81)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第528-562頁;狹間直樹:《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第201-202頁。。
到1898年11月底梁啟超訪近衛篤麿時,康梁先后進行了兩個月的求援活動還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且近衛表示“不熟知中國之內情”,“不可冒昧從其事”(82)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8頁。,婉拒了康梁的請求。此時,面對英、日輿論有關中國變法敗于過激的批評和“奉詔求救”引起的議論,身為“羈旅遠人”的康梁,除了繼續持筆辯誣之外,已無更好的選擇: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涂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類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雖然,事有關于君父之生命,關于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83)梁啟超:《政變原因答客難》,《清議報》第3冊,1899年1月12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135頁。
由此,以“局中人”身份撰寫一部細述改革情形和政變內幕的著作,就成為康梁彼時爭取外援、應對輿論、辯白敗因以及宣傳政治主張的必要行動。《戊戌政變記》就是這樣一部應時之作。據報刊新聞,這項工作11月中旬即已開始(84)吉田薰:《梁啟超與〈太陽〉雜志》,《學術研究》2008年第12期,第142頁。。
二、輿論漩渦中的對策與戊戌神話的生成
《戊戌政變記》系為政治宣傳而作,敘事帶有鮮明的主觀色彩,客觀上并不能稱為實錄。但正是這樣一部作品,以宏闊博大的氣象、曲折詳盡的文字,締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話。作為政治流亡者的康有為,被確立為維新運動的領袖和主腦;喋血市曹的六君子,則以英雄形象青史留名。至于作者本人,也在書寫中完成了“去國忠臣”形象的自我建構。居日十年,“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85)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62頁。,開啟這一時代的,正是《戊戌政變記》一書。
1898年12月起,《戊戌政變記》先后于日本《東亞時論》(1898年12月10日至1899年1月25日,共4期)和《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共10期)連載。在兩種刊本基礎上,《清議報》館1899年4月印行的九卷本《戊戌政變記》增加了差不多兩倍的分量。新增內容多數是引文,而非適合報刊發表的時論。獨占一冊的卷一,包括康有為3篇上疏、維新期間光緒所頒61條上諭及梁氏評論;卷二引用寇連材筆記、政變前后7條諭摺,以及北京特派員來書;卷三新增的《附記保國會事》引錄《保國會章程》和康有為演說;卷七包括康有為1895年上書、《強學會序》,以及各省學會學堂報館目錄;卷八收錄梁啟超《上陳寶箴書》、黃遵憲南學會講義、譚嗣同記官紳集議保衛局事和梁啟超《南學會序》。引文涵蓋奏議、諭摺、筆記、書信、演說、序文、講義多種體裁,時間跨度較大,文字篇幅較長,不適于報刊連載。各章不斷插入的長篇引文,占據了篇幅的絕大比例,論述部分反成為附加性質的補充和說明。這一方面反映了初印本刊行前編輯時間的倉促,另一方面,所增加的內容,實際上調整了《戊戌政變記》宣傳的側重點,即轉變書寫策略,從對輿論批評的被動回應轉為對歷史話語的主動建構。
梁氏將《論支那政變后之關系》《政變前記》《政變原因答客難》《圣德記》數篇在雜志上先行刊布,并不單單是出于整部書“卷帙太繁”,更重要的現實原因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流亡的維新派既要向日本高層求援,又要對輿論澄清“急激致敗”之說。沿著這一思路,梁啟超在前期走謁上書的基礎上,系統組織文字,公開闡說政見,以期在政治困境中有所突破。
首先,梁啟超通過對彼時中外關系、日英政策的分析,敦促日方采取“先發者制人”策略,與俄國進行軍事對抗(86)梁啟超:《論支那政變後之關係》,《東亞時論》第1卷第1號,1898年12月10日,第51-53頁。。這仍是《上副島、近衛兩公書》主要觀點的重申。既然政變出于帝后之爭,“皇上之主義,在開新用漢人,聯日英以圖自立;西后之主義,在守舊用滿人,聯俄以求保護”,為了挽回局勢,就要向英日尋求支持;在這兩國中,“同洲同文同種之大日本”(87)梁啟超:《上副島、近衛兩公書》,《東亞時論》第1卷第1號,第21、24頁。又是梁氏重點求援的對象。為了喚起日方認同,梁啟超以三國干涉還遼之事,強調中日利益的一致,作為尋求同盟的文字策略。然而,身為流亡者的康梁并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這種書生論政的方式,終究無法成功。
梁啟超將帶有求援性質的《論支那政變后之關系》率先刊布在《東亞時論》上,是把主要閱讀對象設定為日本高層,但發表后卻引起了日方的反感。12月18日和20日,日本外務省書記官楢原陳政兩次上門敦請梁啟超離日,梁氏未從(88)《神奈川縣知事淺田德澤致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函(關于清國流亡者之報告)》(1898年12月22日)、《楢原陳政和清國流亡者梁啟超的對話》(1898年12月23日),石云艷:《梁啟超與日本》,第458-459頁。;12月22日,楢原拜訪近衛篤麿,“謂康有為滯留日本,將不利于日本之外交,希望勸赴他國”(89)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8頁。。同文會會員白巖龍平致信近衛,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90)《白巖龍平致近衛篤麿書》(1898年12月25日),彭澤周:《由近衛日記看康有為的滯日問題》,第9頁。。梁氏發表《上副島、近衛兩公書》《論支那政變后之關系》兩篇求援文章,非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造成外交緊張,導致日方施壓、康有為離日。這兩篇引起麻煩的作品,不再刊于《清議報》,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12月23日《清議報》創刊時,梁啟超的寄稿《政變始末》剛剛在《東亞時論》第2號發表。《清議報》第1冊將其作為《戊戌政變記》首篇刊出,文字與《東亞時論》刊本基本一致。根據首段“西后之事,既詳前篇”,其所接續的,系該冊卷首《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該篇接續《上副島、近衛兩公書》的思路,述說改革黨人“四面楚歌,所遇皆敵”(91)梁啟超:《政變始末》,《東亞時論》第1卷第2號,1898年12月25日,第30頁。之困境。梁啟超列出14條“政變之分原因”,前12條系維新舉措與舊黨沖突之事,后2條為光緒賜康有為、楊銳、袁世凱等人密詔事。這是梁啟超第一次撰文提到“衣帶密詔”,說明寫作中曾與康有為商議。康梁將密詔作為維新運動“卒以此敗事”(92)梁啟超:《政變前記》,《東亞時論》第1卷第3號,1899年1月10日,第20頁。的關鍵,一方面強調“奉詔求救”的正當性,同時也是一種自我辯護,即把變法破產的原因歸咎于舊黨阻撓,以回應外間對維新派“改革過于急進”的質疑。這一用意,在接下來的《辯誣》(《政變原因答客難》)中,表現得更加突出。
雖名為“答客難”,但除去開頭“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于急激,以自貽踡跌之憂乎”的設問外,這篇長文悉皆梁啟超獨白,文字鋪排,一氣呵成。可以說,這是康梁面對中外輿論的集中回應。首先,梁氏強調“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從練兵、開礦、通商、外交、教育等方面陳說洋務運動三十年改革之不成,全因李鴻章、張之洞等施行“溫和主義”、布新而不除舊,故提出變法“非全體并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其次,參照明治維新史,申說新政“急激”舉措的必要性:
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為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支那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于井伊、安藤諸閣老也。(93)任公:《政變原因答客難》,《清議報》第3冊,1899年1月12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140頁。
基于日本經驗,梁啟超為康氏“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等論斷進行辯護,將變法不成歸于舊黨和西后。面對“世人乃以急激責之”的情境,梁氏陳說“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反詰輿論“不審大局,徒論成敗”,以“局內人”身份進行辯白(94)任公:《政變原因答客難》,《清議報》第3冊,1899年1月12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141-142頁。。
雖然中外各界“急激之咎”并非空穴來風,梁啟超后來也承認康有為“舉動或失于急激,方略或不適于用”,而在當時的輿論壓力下,梁氏唯有持筆應戰,為維新黨人立言。變法僅持續百日即“挫跌一無所存”,但梁氏始終相信這場失敗了的運動所具有的進步意義:“然則戊戌之役,為敗乎?為成乎?君子曰成也”(95)任公:《南海康先生傳》,《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6冊,第6299、6305頁。。輿論關于變法失敗是否應歸咎于“急激”的討論,并未隨著梁文的刊出而完全退去,而梁氏“不以成敗論事”的書寫策略,確是取得了言論上的成功。
三、《戊戌政變記》的傳播、批評與接受
康梁的旅日生活和政治宣傳,很快引起日本報界關注。早在他們以政治流亡者身份抵日時,《太陽》雜志就刊出二人照片(96)《清國改革黨の領袖梁啟超 康有為》,《太陽》第4卷第21號,1898年10月20日,寫真銅版第1頁;《最近攝影の清國名士康有為氏》,《太陽》第4卷第22號,1898年11月5日,寫真銅版第1頁。,此后,《太陽》《東邦協會會報》《東亞時論》《日本人》等先后發表多篇政論文章,詳論清廷政變始末,介紹新舊雙方政策(97)小山正武:《北京の政變と露國外交術との關係》,《太陽》第4卷第21號,第26-33頁;千山萬水樓主人:《康有為氏との筆談》,《太陽》第4卷第21號,第212-215頁;某清國外交通:《清國政變の真相》,《太陽》第4卷第21號,第215-217頁;天默生:《漢土政變と支那分裂の原因》,《東邦協會會報》第51號,1898年10月20日,第66-79頁;《政變后の支那》,《東亞時論》第1卷第1號,1898年12月10日,第37-38頁;內藤虎次郎:《康有為等と如何するか》,《日本人》第18卷第80號,1898年12月5日,第14-17頁。,兼論日方應對舉措。梁啟超《上副島、近衛兩公書》發表后,其“悲壯慘淡”的血淚之語,迅速獲得了日本報界同情(98)天默生:《漢土政變の不幸——支那將來恢隆の希望》,《東邦協會會報》第53號,1898年12月20日,第100頁。;《戊戌政變記》刊布后,也很快引起了日方注意。
1899年1月1日,《太陽》雜志“海外事情”欄刊發《清國政變始末》,署名質軒,內容主要源自梁啟超《上副島、近衛兩公書》(99)質軒:《清國政變始末》,《太陽》第5卷第1號,1899年1月1日,第227-233頁。。根據該期《寄贈書目》(100)《寄贈書目》,《太陽》第5卷第1號,1899年1月1日,第253頁。,其所據底本當為《東亞時論》第1號所刊梁氏文章。隨后,該欄目連續刊發多篇相關文章(101)吉田薰和張昭軍曾提及這些篇目,吉田薰:《梁啟超與〈太陽〉雜志》,第141-142頁;張昭軍:《戊戌政變后日本〈太陽〉雜志對康、梁的報道和評論》,《史學月刊》2019年第11期,第52-53頁。:

《太陽》所刊相關文章概況
除《皇帝不豫》和《清分割問題之復燃》據自時聞外,其余數篇皆源出梁啟超詩文;據《清議報》改編而來的四篇,即為《戊戌政變記》部分篇章的編譯之作。日本大型綜合性雜志《太陽》創刊于1895年,半月刊,發行處設于東京博文館,當時編輯人為岸上操。岸上操字質軒,號僉刃,上述改編皆出自其手。根據1899年9月岸上操與梁啟超的會談,梁氏本人并未參與。表面上看,這種編譯行為具有侵權嫌疑,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此舉實有利于梁啟超政治觀點的傳播。因此,當梁啟超得知“質軒”“僉刃”的真實身份時,不僅毫無慍色,還送給岸上操一部《戊戌政變記》(102)質軒:《梁啟超氏の談片》,《太陽》第5卷第21號,1899年9月20日,第166頁。。
《清議報》創刊后,即向日本各大報館按期分送,《太陽》《東亞時論》《日本人》《東邦協會會報》等刊“寄贈書目”欄都可得見《清議報》各期贈刊,《日本人》還專門為《清議報》做了介紹(103)《清議報》,《日本人》第83號,1899年1月20日,第38頁。。隨著《清議報》的刊行,《戊戌政變記》也得以在日本傳播。1899年3月23日,在外交壓力下,康有為離日赴美(104)《康有為米國に赴く》,《東亞時論》第1卷第9號,1899年4月10日,第43頁。,《清議報》很快停止了《戊戌政變記》的連載,隨后出版單行本。當年的日本外交檔案收錄了關于《戊戌政變記》出版的報告:
《戊戌政變記》卷之一、二、三部
以上為清國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于居留地一百三十九番清議報館發行,從《清議報》中拔萃編纂成冊。專門論究清國政治之得失,國體之如何。聞知由本月二十三日始頒布于歐洲、美國、新加坡、香港等其他清國人居留地。特此報告。
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05)《神奈川縣知事淺田德則致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函(關于清國人出版書籍一件之報告)》,石云艷:《梁啟超與日本》,第463頁。感謝夏曉虹教授之提示。
結合《清議報》第14冊廣告(106)《〈戊戌政變記〉成書告白》,《清議報》第14冊,1899年5月10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第1冊,第904頁。,《戊戌政變記》的正式出版,即在5月中旬。康梁對外求救的政治主張雖未實現,但《戊戌政變記》的發行在日本并未引起太多爭議。不過,當《清議報》和《戊戌政變記》漂洋過海,轉輸國內時,則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
1899年10月21日,《申報》發布《戊戌政變記》寄售廣告:
戊戌八月之變,為中國存亡絕大關系,惟其事之本末,層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某君將事之原委編輯成書,托本館代售。全書分九卷,記載詳盡,議論精明,將中國將來之局言之了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閱之書也。全部裝訂三本,定價實洋八角。來書無多,如欲購者,請速至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107)《寄售〈戊戌政變記〉》,《申報》1899年10月21日,第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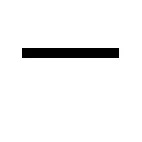
嗚呼噫嘻!去年八月十四日之變端,其機亦可謂間不容發矣。在康梁諸逆,得為漏網之魚,使其稍有人心,自當感戴鴻恩,碎身圖報。胡為而匿跡海外,依然拈弄筆墨,訕及宮廷,喪心病狂,如此其極。如近日市上所售之《戊戌變政記》,安可不及時嚴禁,而任其煽惑人心哉?是書為從逆梁啟超所著,為帙三,為卷九,大抵于逃亡之后,猶思死灰復燃,因逞其謬妄之談,謗毀我圣母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者也。客有持以見示者,端居多暇,略披數頁,種種誣蔑,幾不忍觀。……使不嚴以禁之,恐天下無識之流,皆將誤信其簧蠱,謠言之起,此后當更無已時矣,不亦深可懼哉?(109)《禁逆書議》,《申報》1899年11月13日,第1版。
這篇長文,就《戊戌政變記》言及西后虐待皇上、褫奪權柄等情形逐條駁斥,力證梁文為“自相矛盾之詞”,且就寇連材之事,問“梁逆私交內監,窺伺宮闈”之罪。文中提到“去秋康梁二逆脫逃之后,鄙人曾著為論說,謂宜著其罪狀,刊印成書,由出使大臣分給海外諸華商,使明于順逆之途,免被康梁所煽誘”,然未及成書,梁即“肆無忌憚,著此逆書”。這里指的應是一年前《申報》所刊《慎防逆黨煽惑海外華人說》(110)《慎防逆黨煽惑海外華人說》,《申報》1898年11月14日,第1版。。《禁逆書議》延續前文攻訐康梁“大逆不道”“顛覆國家”的思路,把關注點聚焦于《戊戌政變記》這部新書,聲請抵制。很快,此“逆書”就引起了朝廷注意,旋即遭到查禁:
剛子良中堂入京覆命時,呈進叛犯梁啟超所作《清議報》及《戊戌政變記》等書,歷陳康梁二逆煽惑情形,并稱近日康又遨游列國,若不使其根株盡絕,則星星之火終致燎原。皇太后覽書大怒,未幾皇上有飭拿及設法致死之旨,并遷怒某大臣。(111)《天威震怒》,《申報》1900年1月8日,第2版。
在查禁“逆書”的同時,清廷懸賞通緝康梁,且從讀者一端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加懲辦”(112)《本館接奉電音》,《申報》1900年2月16日,第1版。。
彼時清朝官方查禁的,不只是《戊戌政變記》單行本,也包括《清議報》等刊物。早在1899年4月,“梁啟超諸犯在外洋創為《清議報》,廣播蜚言,妄思勾煽”(113)《論逆犯康有為去日事》,《申報》1899年4月6日,第1版。之事,已見諸報端;《戊戌政變記》在國內發行時,由“梁啟超所為之《清議報》行銷市上已歷一年”,“無識之徒,間有出資購閱者”,守舊一方再次撰文聲討(114)《綜論〈清議報〉誣上之罪》,《申報》1899年12月28日,第1版。。《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確是實言。不過,縱使官方明令禁止,以致“書坊不敢公然出售”,但仍由何擎一轉輸國內,“己庚之間已銷流兩千部”(115)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0-111頁。,“梁啟超之《清議報》,華官亦嘗禁人閱看,亦嘗禁人代售,而至今內地仍有流傳,未見絕跡”(116)《書本報所登嚴禁國民報示后》,《申報》1903年10月28日,第1版。。為此,張之洞還曾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117)《讀鄂督張宮保所訂禁約留學日本諸生章程率抒鄙見》,《申報》1903年11月21日,第1版。。屢禁而不止,體現了梁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迨清廷覆亡,民國肇建,康梁歸國,《戊戌政變記》也摘掉了“逆書”的帽子。梁啟超去世后,林志鈞編輯出版《飲冰室合集》,并出版單行本,其中即包括《戊戌政變記》:
本書分五篇十一章,詳載《康有為向用始末》《新政詔書恭跋》《政變之原因》《推翻新政》《窮捕志士》及《殉難烈士傳》等。于《廢立始末記》中,關于西后虐待光緒情形及廢立陰謀,敘述尤為詳盡。凡欲知此次政變之始末者,不可不讀此書。(118)《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合集〉單行本》,《申報》1936年11月14日,第6版。
中華書局發售的單行本,雖稱“依據手稿,校訂最為精確”,但其實是以廣智書局本為底本的八卷本。這則廣告,陸續刊登至1939年。從晚清到民國,書商皆在強調“不可不讀此書”,但對照《申報》相隔四十年的兩則廣告,推銷的理由,已悄然由前瞻式的“將中國將來之局言之了如指掌”變為回顧式的“凡欲知此次政變之始末者”,前者重在關切未來國情,后者則旨在鉤沉前朝往事。不過,戊戌時代落幕后,康梁及其所代表的維新精神并未被世人遺忘,梁著《譚嗣同傳》《楊銳傳》《楊深秀傳》等文,先后選入多種國文教科書,成為民國教育范本(119)梁啟超:《楊深秀傳》,孫俍工編:《初級中學用國文教科書》第2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第22-26頁;梁啟超:《楊銳傳》,孫俍工編:《初級中學用國文教科書》第2冊,第27-29頁;梁啟超:《楊深秀傳》,施蟄存等注釋,柳亞子等校訂:《初中當代國文》第2冊,上海:中學生書局,1934年,第23-28頁;梁啟超:《楊銳傳》,施蟄存等注釋,柳亞子等校訂:《初中當代國文》第2冊,第28-32頁;梁啟超:《譚嗣同傳》,何炳松、孫俍工編:《師范學校教科書甲種·國文》第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6-25頁;梁啟超:《譚嗣同傳》,蔣伯潛編:《蔣氏高中新國文》第4冊,上海:世界書局,1947年,第350-363頁。。根據當時教育部課程標準,中學國文讀本選文應當“含有振起國民精神,改進社會現狀之意味”,“包含國民應具之普通知識思想,而不違背時代潮流”,且“敘事明晰,說理透切,描寫真實,抒情懇摯”,“體裁風格,堪為模范”(120)《編輯大意》,施蟄存等注釋,柳亞子等校訂:《初中當代國文》第1冊,上海:中學生書局,1934年,第1-2頁。。梁氏文字的“平易暢達”“條理明晰”(12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86頁。自不必多言,其“近代中國思想家,啟蒙運動之先驅”的地位與“倡議變法維新,鼓吹革新事業”(122)《梁啟超·作者事略》,施蟄存等注釋,柳亞子等校訂:《初中當代國文》第2冊,第1頁。的功績,也堪為時代典范。《戊戌政變記》雖為政治宣傳而作,但世事變幻幾十年后,其在文學、思想、教育諸方面,仍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
結 語
1909年,革命黨人黃世仲所著“近事小說”《大馬扁》在日本刊行,序文謂“康梁所以能招搖于海外者,全恃《戊戌政變記》一書,蓋書中極力鋪張,去事實遠甚,而外海僑民,蒙于祖國情勢,先入為主,至于耗財破家,在所不恤”(123)吾廬主人梭功氏:《序》,小配:《大馬扁》,東京:三光堂,1909年,第1頁。。該文雖系攻訐康梁之作,卻也從反面道出《戊戌政變記》的巨大影響力。
作為一部以政治宣傳為要旨的應時之作,《戊戌政變記》寫作思路依據時勢不斷調整,在結構上多有不完整之處,刊行后又根據現實需要多次改易,形成極為復雜的版本系統。梁啟超在流亡中的寫作,純為“條理細備、詞筆銳達、不必求工”的“覺世之文”(124)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合集》文集2,第2冊,第27頁。,而非圖作“傳世之書”。然而,這部細說變法原委,希圖影響國際輿論,實現救上復權的作品,終究是“俠劍無功”(125)梁啟超:《去國行》,《亞東時報》第4號,第28頁。。但另一方面,從清季到民國,梁任公“盡國民責任于萬一”“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126)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11,第4冊,第19頁。的精神,并未隨著時事更易而褪色,其明晰暢達的政論文字、委婉動人的傳記文章,也使《戊戌政變記》具有史料之外的多重意義。
戊戌維新的一百天,深刻影響了中國20世紀的一百年。“變法維新一事雖告失敗,但影響所及固極深遠”(127)張其昀:《梁任公別錄》,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第110頁。按,百日維新與百年思潮之間的關系,系王德威教授之提示,謹致謝忱。,這場歸于失敗的改革,雖未能達成效仿日俄、新國新民的期許,但其在政治體制、文化思潮、社會輿論諸方面,都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亦昭示著國家未來新的可能。借由梁啟超的書寫和建構,戊戌之秋的政治變局,成為極具悲劇色彩的時代記憶;維新派所發起的一系列求新求變之舉,則開啟了20世紀啟蒙與革命思想的先聲。在這一意義上,戊戌時代不完全是已經消逝的過去,維新的書寫和記憶,體現出轉型時代歷史的艱難演進,也關系到新舊之間的國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