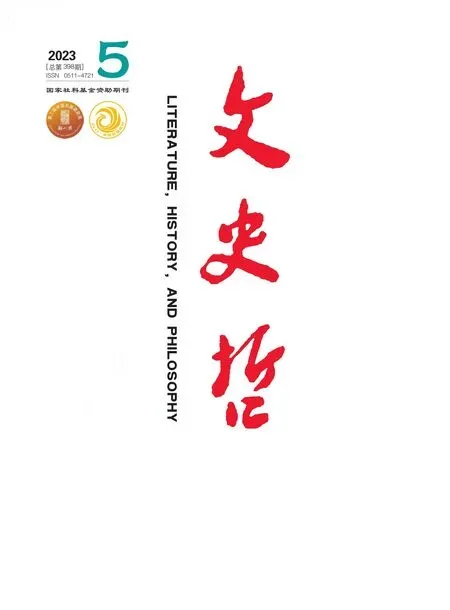從職位到官位:以魏晉南北朝的中正為例
劉 嘯
與魏晉南北朝相始終的九品中正制度,既關系到這個時期的人才選舉,也關系到這個時期的官吏選用,是士人與政府、地方與中央之間溝通的重要渠道。關于九品中正制度,學界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中文學界從較早的楊筠如、唐長孺到最近的陳長琦、張旭華(1)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年初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81-121頁。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四章,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第67-96頁。胡寶國:《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1期,第81-90頁;《關于九品中正制的幾點意見》,《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91-192頁;《九品中正制雜考》,《文史》第36輯,1992年,第289-293頁。陳長琦:《九品官人法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25頁;《魏晉九品官人法釋疑》,《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9-72頁。張旭華:《九品中正制略論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九品中正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日本學界從較早的岡崎文夫、宮川尚志、宮崎市定到最近的渡邊義浩(2)岡崎文夫:《九品中正考》(初刊于《支那學》第3卷3號,1922年),《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東京:弘文堂,1967年新裝版,第195-210頁。宮川尚志:《中正制度の研究》,《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6年,第263-338頁。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1956年初刊),《宮崎市定全集》6,東京:巖波書店,1992年。矢野主稅:《本貫地と土斷、孝秀及び中正について》,《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研究報告》第20號,1971年,第1-26頁;《門閥社會成立史》結語にかえて,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年,第537-570頁。越智重明:《九品官人法の制定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46卷2期,1963年,第36-69頁;《魏時代の九品官人法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1974年,第15-32頁;《魏晉南朝の貴族制》第二章、第三章,東京:研文出版,1982年,第44-174頁。堀敏一:《九品中正制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5,1968年,第37-75頁。川合安:《九品官人法創設の背景について》,《古代文化》第47卷第6號,1995年,第309-317頁。草野靖:《魏晉の九品官人法》,《福岡大學人文論叢》第27卷第3號,1995年,第1615-1654頁。渡邊義浩:《九品中正制度と性三品説》,《三國志研究》第1號,2006年,第61-70頁。,都有深入研究。無論是九品的性質、等級、意義,還是中正的職權、組織和與門閥社會形成之間的關系,均經前輩學者深耕熟耘,似已題無剩意。這里只擬對前輩學者關注較少或尚有疑義的幾個事例加以討論,以求能夠更加明確中正在職官制度上的性質。
前輩學者就中正在職官制度上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有兩家。唐長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試釋》一文中指出:“中正須現任官兼,而且必是中央官……因此我們相信中正必須由現任中央官兼,這樣政府才易于控制,而且也易與吏部聯系,如果由外官兼任,那只是例外。”(3)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99頁。根據唐先生的判斷,無論是常態下的由中央官兼任,還是作為例外的由外官兼任,“中正”都需要由“他官”兼任。雖然可以把它視為一種“兼官”,但在設立之初,中正并沒有官品,我們在記載魏晉南朝職官制度的正史志書中也從沒有見到“中正”一目。魏晉南朝的中正無官品、有權責,與其把這個時期的“中正”視為“官”,不如把它視為“職”,它非常符合我們過去注意到的“職位”現象(4)關于“職位”的界定,參見拙撰:《從職位到官位(一):以漢魏南北朝的校書郎為例》,《文史哲》2019年第1期,第89-90頁。。
北朝的情形和魏晉南朝不同,《隋書·百官志中》載北齊官品之制:
流內比視官十三等。……諸州大中正……視第五品。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視從第五品。……司州州都主簿……視從第七品。諸州州都督簿……清都郡中正……視第八品。……諸郡中正……視從第八品。(5)《隋書》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770頁。2019年中華書局修訂本第857頁同。按,本條有幾處標點似有誤。“司州州都主簿”未點斷,似應斷作“司州州都、主簿”。因為州都之下并未設主簿官,主簿是州的主簿。《通典》卷一四《選舉二》引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561)詔:“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于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并聽表薦。”(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1頁)點校者就斷作“州都、主簿”,因為兩者都是州的屬官。至于正文引文中的“諸州州都督簿”,也應斷作“諸州州都、督簿”,其中“督”字恐是“主”字之誤。
上引史料中的“諸州大中正”“諸州中正”與“司州州都”“諸州州都”之間,“畿郡邑中正”與“清都郡中正”“諸郡中正”之間似有重復(況且清都郡本來就是畿郡),對此現象,嚴耕望先生已經注意到并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北朝的中正“有中央地方之別,且自北魏已然”(6)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年,第639頁。嚴先生說,“復有州都,比從七品至正八品,與主簿同階”,可見他也認為“州都”與“主簿”之間應該點斷。。也就是說,北魏時期中正始分中央與地方,地方中正為新增,二者地位迥然不同。北齊承北魏制度,且無論中央與地方的中正,都是“比視官”(7)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50-651頁。。
從唐、嚴兩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中正:一種是需要中央官兼領的中正,這是一個職位,存在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齊時成為“比視官”;另一種是地方上的中正,只存在于北朝,北齊時也成為“比視官”(8)關于魏晉南北朝中正具有的“職位”性質,張旭華先生在對北朝的“比視官”制度進行系統研究時曾有所涉及,參見《北齊流內比視官分類考述(下)》,《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第124-129頁;《東魏北齊九品中正制述論》,《九品中正制略論稿》,第325-350頁。張先生通過考察北齊中央與地方的中正的職權、待遇后認為“北齊將中央和地方所置州郡中正列入流內比視官,乃是對魏晉以來中正制度的一大創革。尤其是對中央朝官兼領的州郡中正而言,雖然中正一職仍屬兼職而非流內正式品官”,更多的是將中正視為“兼職”。。因此,我們既有必要研究“職位”與“比視官”視角下的兩種中正,也有必要研究北朝地方上的中正是怎樣形成的。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職位”的中正
(一)司馬懿“州置大中正”議所見中正的職位性質
《三國志·魏書·陳群傳》載:“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9)《三國志》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34-635頁。對于這條史料的點斷,越智重明在《九品官人法の制定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46卷2期,第37-39頁)曾提出過新的見解,認為應該在“制九品”處點斷,語義上屬,作“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他的理由是“制九品”和“官人之法”是兩回事,加之“制九品官人之法”讀起來不順,官人之法應下屬,而“九品”作為一種(選舉)制的用詞,用例甚多。不過同氏在《魏時代の九品官人法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第15-16頁)一文中因發現了《北堂書鈔》引用的《魏略》記載,所以改了前文的句讀,并論證“制九品官人之法”乃魏王所制,是陳群所建言。更晚出的《魏晉南朝の貴族制》(第76-77頁)亦同后文。陳群所建的“官人之法”是一種新的選舉制度,它與漢代察舉制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于采用了“制九品”的方法。這里的“九品”只能是鄉品的九品,因為這是選人去當官的辦法,與官品毫無關系,而且當時官僚等級也還沒有開始采用九品官品進行區分(10)祝總斌先生、閻步克先生都認為魏官品的制定與頒布要到曹魏末咸熙(264-265)年間,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2-133頁;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39-252頁。。這條史料講到的是新的選舉辦法“制九品”,就是制訂按九品論人選人的選舉制度,而定九品高低的主要責任人是中正(11)仇鹿鳴先生根據《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中的“中正杜縣杜豹字子變”,考證中正在東漢初平(190-193)年間就已經出現(《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附錄《〈司馬芳殘碑〉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范兆飛先生則認為不同時代的信息由于補刻很可能累積到了一起,“中正杜縣杜豹”不能完全作為東漢的材料加以解讀,也就不能作為推斷中正確立時間的重要依據(《亦漢亦魏:〈司馬芳殘碑〉的時代及意義》,《史學月刊》2018年第1期,第29頁)。我同意范先生的意見。就目前材料所見,制九品立中正是在延康元年由陳群提出的。。據《三國郡縣表附考證》所考魏州郡總目,魏時大致有十二州、近百郡(12)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三國郡縣表附考證》,《二十五史補編》第3冊,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第2821頁。。隨著陳群提出“九品官人法”,先是在魏王國十郡實施,幾個月后隨著魏王朝的建立而推至其全境,近百郡的中正也就應運而生(13)延康元年立中正時只有郡中正,沒有州中正,州中正是到了齊王芳時期由司馬懿提議設立的。關于這一點的考辨,見下正文。。《通典·選舉二·歷代制中》“宣王辭不能改,請俟于他賢”條注曰:
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14)杜佑:《通典》卷一四,第327-328頁。按:杜佑言“州郡縣中正”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漢魏之際州中正尚未設立,縣中正在魏晉時似也沒有。
中正雖然由諸郡推選,但是擔任中正的卻是“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的中央現任官員。也就是說,只是給這些中央官再掛上一個“職位”而已,無論是對現有官僚結構,還是對現有官僚的既得利益,都沒有產生任何損害。
正因為中正是一個對現存官僚體系并無任何妨害的職位,所以才能在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地設置起來。也正因為中正只是一個職位,增減并不受既有官制的制約,所以以后到了齊王曹芳時又設立了州大中正。唐長孺先生說“州中正的設置只能是地方大族勢力擴大的結果。少數大族已經不滿足于一郡的范圍內了”(15)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96-97頁。,這是準確的判斷。我們現在試從職位的角度對州大中正的設置過程做一些分析。
《通典·職官十四·州郡上·州佐·中正》引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16)杜佑:《通典》卷三二,第892頁。《太平御覽·職官部·中正》引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本條下又引《曹羲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17)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二六五,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243頁。司馬懿建議設州大中正時,要求“除九品”“除九制”(18)對于“除九品”中“除”字的理解,還有另外一種意見。岡崎文夫在《九品中正考》(《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第204頁)一文中認為,這里的“除”是“除授”,也就是授予大中正以除授官職之權,因為賦予中正重要的權力是司馬氏的基本政策,而中正由權勢之家擔任,司馬懿的這種做法是為了結勢家之心。宮川尚志氏在《中正制度の研究》(《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第270頁)一文中也持同樣看法。。楊筠如先生早已指出,司馬懿是要廢除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罷郡中正(19)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第39-40頁。關于楊先生的觀點,下文將加以分析。張旭華先生提出“自九品中正制一建立,中正組織就分為州、郡兩級,而且是州、郡中正同時并置”,基于這種認識,他認為“廢除郡中正,同時又保留并設置州中正的建議”(《九品中正制研究》,第109、112頁)。我并不認同張先生所說九品中正制自建立時就分州、郡兩級的說法。因為按張先生的說法,司馬懿提出廢除郡中正的同時,保留并設置州中正。保留的是哪些州中正,又設置了哪些新的州中正?既然州、郡中正在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建立時都已經設立,那么就很難想象當時會單獨先設置幾個州的中正,而將剩下的幾個州的中正問題遲至齊王芳時才由司馬懿來提出。,設州大中正。州大中正設立的時間,正如唐長孺先生所說,“至遲不出嘉平二年(250),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也即是說在曹芳時”(20)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97頁。。
司馬懿要求設立州大中正的理由是“諸中正未能料究人才”,他既不用九品評定等級,也廢掉了郡中正這一層級,而由州大中正直接對本州諸郡人士“檢虛實”,這是一種新的選舉方法。問題在于郡中正對本郡人士的評定尚且力有不逮,更何況州中正要應對一州人士的評定?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難題,所以曹羲的反對意見一開始就是“一州闊遠,略不相識”,那么就勢必只能“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所謂“郡人”,就是“本郡先達”,既然是“先達”,那么就必然是大姓、名士。“訪本郡先達”就是聽取本郡大姓、名士的意見,也就是鄉里清議(21)唐長孺先生指出:“所謂鄉里清議,像汝南月旦那樣的形式并不通行,一般都是咨詢某些大姓、名士對于當地人才的評論而已。……使朝廷選舉和名士月旦統一,朝官保舉和鄉里清議統一,人士流移和核之鄉閭統一,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由吏部尚書陳群建議,制定九品官人之法,設置郡中正,品第郡人,中正由本郡推舉現任朝官的郡人充當。這樣,在野的名士月旦變作官府品第,‘核之鄉閭’變成訪之中正,也就考詳有地,問題就解決了。”見《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5、47頁。。陳群的九品官人法本來就是將名士們的鄉里清議變作在朝中正的品第,現在司馬懿又準備再來一次。郡中正不行,就置州中正;九品論人不行,就除九品。楊筠如先生說:
大概宣帝的意思,是想不用九品銓序的方法,止每州設一個大中正主持選舉的事務,是想折衷于漢代察舉和魏氏中正兩種制度。(22)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第39-40頁。
就本質上來說,州大中正主持選舉與郡中正主持選舉只有層次的不同,并沒有實質的差別。郡中正不行,可以整頓;九品之狀不盡人才,既可以整頓,也可以廢除。司馬懿為什么非要多此一舉呢?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與當時的朝局有關。眾所周知,魏明帝臨終時的托孤重臣有兩個,一個是宗室曹爽,一個是重臣司馬懿。齊王芳剛即位,曹爽就以司馬懿德高望重為由,升任太傅,剝奪了他“錄尚書事”的大權(23)《三國志》卷九,第282頁。。從此以后一直到“高平陵事變”以前,曹魏中樞政權一直控制在曹爽的手里。正如葭森健介指出的,“曹爽政權占據中樞的十三人之中,有多至七人是曹氏同族或是有姻戚關系,三人是曹氏的同鄉。也就是說,擔當曹爽政權的是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與宗室曹氏相結合的人”(24)葭森健介:《魏晉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権と州大中正設置問題》,《史學雑誌》第95編第1號,第41頁。。即使我們不考慮曹氏與司馬氏代表的統治階層有異,只要想一想司馬懿“堅忍陰毒”的性格(25)參見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48-49頁;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第1、13、14-15頁。,就知道他不會輕易放棄。司馬懿的“州置大中正議”就是他做出眾多反擊中的一個。
中正制度是一種選舉人才的制度,無論是陳群的九品官人法,還是司馬懿的州置大中正,都是為了舉人。唐長孺先生指出:“中正的任務是品第人物,以備政府用人的根據。……其實所有官職授受,除掉以皇帝特權來處理之外,都必須經過中正審查這一道手續。”(26)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02頁。這是站在中正職權的立場上來說的,以前的郡中正是如此,現在司馬懿想要設置的州大中正也是如此。不過,中正雖然有舉人大權,可用人大權卻在吏部手中,《三國志·魏書·傅嘏傳》載:
司空陳群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27)《三國志》卷二一,第622-623頁。
陳群官司空是在魏明帝時,作為九品官人法的直接制定者,他當然最清楚這套選人用人的辦法。傅嘏作為他的掾屬,在與劉劭辯難考課法時公然說“選才之職,專任吏部”,可見士人能否當官的最終決定權操在吏部之手。齊王芳即位以后,吏部完全掌握在曹爽一黨的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手里(28)葭森健介:《六朝貴族制形成期の吏部官僚》,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続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5年,第219-245頁。。司馬懿如果想要在用人上有發言權既然不可能,那么插手舉人權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法。可郡中正太多了,近百郡就有近百個中正,就涉及近百位在朝中央官員,不僅風險無法管控,就連能不能見上一面都成問題。廢掉所有郡中正,設置最多十幾位的州中正,不僅易于聯絡,而且有可能對舉人的權力結構重新洗牌,導向對司馬懿有利的一面,這也許是他“除九品,州置大中正”的初衷。胡寶國先生認為“司馬懿的本意原是想不理會‘本郡先達’的意見,改變中正品評‘決于郡人’的現狀”(29)胡寶國:《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1期,第86頁。,但我認為司馬懿的本意是要通過置州大中正掌握舉人權力,以對抗掌握在曹爽一黨手里的吏部用人之權。至于是否“決于郡人”,司馬懿似乎根本不關心,對于置州大中正之后完全可以預見的后果,反而是曹羲提出的。
司馬懿“州置大中正”的建議當時是否實行,史無明文。宮崎市定、葭森健介都認為,州置大中正是在高平陵事變之后(30)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134頁。葭森健介:《魏晉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権と州大中正設置問題》,第54頁;《六朝貴族制形成期の吏部官僚》,第239頁。,但并無確據。我認為司馬懿的“州置大中正議”是實行了的,只不過既沒有除九品,也沒有廢郡中正,而是在郡中正之上加置了州大中正,州郡中正之間是否有統屬關系,不明。《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附子玄傳》載: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31)《三國志》卷九,第295、298頁。
很多學者都認為正是由于夏侯玄的批評,司馬懿才提議設置州大中正(32)宮川尚志:《中正制度の研究》,第270-271頁。葭森健介:《魏晉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権と州大中正設置問題》,第50-51頁。。我認為可能恰恰相反,是因為這時設置了州大中正,才引起了夏侯玄的不滿。正如葭森健介氏分析的那樣,夏侯玄的這段議論是針對中正侵奪了吏部用人之權,導致“上下交侵”(33)夏侯玄議中所謂“緬緬紛紛,未聞整齊”,有可能是指司馬懿提出除郡中正設州大中正之議即曹羲所謂“明論”之時引起的各種議論。就玄議的文脈論,是指選舉中的“上之分”與“下之敘”分工混亂,也就是“參錯”。玄雖然認為要平衡二者關系,但他認為當時選人偏于“下之敘”即九品中正制。實際上,之前的曹魏三帝都是主張強化“上之分”的,具體到齊王芳初年,強化“上之分”,其實就是強化控制著吏部的曹爽一黨的權力。本條承牟發松教授提示,謹致謝。。上舉《傅嘏傳》說“選才之職,專任吏部”,說明在只有郡中正的魏明帝時期,吏部的用人權相對中正的舉人權一直處于強勢地位。齊王芳即位以后,吏部的大權一直握在曹爽一黨手里。如果沒有新的變化,夏侯玄似乎不必發表長篇大論,但情況發生了變化,那就是設置了州大中正,所以夏侯玄才會說“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他針對的是新設的州大中正,正是由于州大中正的設置,使得“專任吏部”變成了“上下交侵”,雖然我們并不清楚是州大中正獨自引起了這種變化,還是州郡中正一起促成了這種變化(34)西漢前期刺史歸御史中丞管轄,州為純粹的監察區劃。成帝綏和元年罷刺史,置州牧。“刺”“牧”二字,性質大為不同:“刺”指刺史,屬于監察;“牧”指牧民,屬于行政。罷刺史,置州牧,州牧實際具有中央監察官和地方行政官雙重身份。同樣,州也既是監察區劃,又是行政區劃。《三國志·魏書·賈逵傳》說:文帝時“以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說明直到曹魏時,州仍具監察區劃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州中正的設置,可能也含有監察郡中正的職能。本條承王素研究員提示,謹致謝。因此,州大中正與郡中正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司馬懿的回復很有意思,他贊成夏侯玄的“除重官”“改服制”的建議,卻對“朝廷考事”說“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態度曖昧不明。如果我們認為夏侯玄議中出現的“州郡中正”不是虛指地方中正的話,那么就不能排除州大中正設于齊王芳正始初年的可能性。
《太平御覽·職官部·中正》引應璩《新論》:
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踈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35)《太平御覽》卷二六五,第1243頁。逯欽立先生認為諸書所引應璩詩句,或稱《新詩》《新論》《新語》《雜詩》,大概都應歸于應璩諷諫曹爽的《百一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68-469、471頁。
據《三國志·魏書·應玚傳》注引《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36)《三國志》卷二一,第604頁。又《文選》“百一詩”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37)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5頁。應璩在當大將軍曹爽長史時,由于爽“多違法度”,所以“為詩以諷”。史稱“多切時要”“譏切時事”“風規治道”,可見主要是對曹爽秉政以后的政治人事提出意見。因此,當應璩“遍以示在事者”時,弄得“咸皆怪愕”。既然應璩的詩是寫曹爽治下現狀的,那么“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就是說的正始年間的州大中正與郡中正的實況(38)張旭華先生認為“《新論》所記,也主要是曹魏初年之事”,似乎不太準確,見《九品中正制度研究》,第108頁注1。。應璩所謂“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其實就是曹羲說的“一州闊遠,略不相識”。由此可見,雖然曹羲提出反對置州大中正的意見,理由也很有預見性,但是正始初年,州大中正還是設立了。
我認為司馬懿州置大中正議,最初的目的大概是想要通過壓縮中正的數量而將中正舉人之權集中掌控在自己手里,以對抗吏部用人之權。這是基于對上述資料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種推測。
從置州大中正這件事上很可以看出中正的職位性質。夏侯玄在回答司馬懿的提問時,曾說“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在玄看來,中正雖“不處官名”,即官令無此官名,卻有任官之實。這是當時人的看法,正指明了中正的性質。正因為它并不存在于既有的官僚體系之中,所以可以反復討論是否設置、怎樣設置、設置多少等問題。如果對郡中正不合意,可以廢除,可以保留,可以再設州大中正。
(二)選授中正與中正舉人
曹魏時期州中正與郡中正的關系,我們不是很清楚。晉代的情況,據唐長孺先生所考:
初立中正時,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在晉代照例由司徒選授。……可知大小中正例由司徒選任。……郡中正在晉代似由州中正薦舉,和以先由地方官推選不同。……這也是由大中正舉小中正的例子,但必須司徒府的通過。(39)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97-98頁。
對此,胡寶國先生概括為“曹魏,郡中正由諸郡推舉。西晉,州中正由司徒府選授,郡中正有時由州中正推舉,但最終也要由司徒府批準”(40)胡寶國先生就曹魏司徒府的問題,指出“史料中從未發現曹魏時司徒府參預品評工作……西晉‘諸郡’推舉中正的權力終于被剝奪而轉交給司徒府”;就晉代中正選授的問題指出“即使在西晉,也偶有由諸郡推舉中正的情況”。見《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1期,第85、86頁,第91頁注22。。這樣,司徒府與州郡中正、州中正與郡中正之間,由于選授、薦舉關系的存在,就有可能構成上下層級的關系。
《晉書·傅玄附子咸傳》載:
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41)《晉書》卷四七,第1323-1324頁。
魯國小中正由豫州大中正薦舉,司徒府通過。司徒府的司徒左長史可以奏免大中正,但必須司徒通過。因此,中正選授的最終決定權在司徒手中。又同書《李含傳》: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敕府符陷含于惡。”(42)《晉書》卷六○,第1641-1642頁。
李含本是隴西狄道人,但因為僑居始平,所以司徒仍可選含以秦國郎中令領始平中正。李含是秦國官,當本國秦王薨逝以后,由于“葬迄除喪”,所以被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所貶(43)李含雖然是隴西狄道人,但因僑居始平,大概就算作始平郡人,否則不會讓他擔任始平郡中正。傅祗是北地人,北地與始平同屬雍州,所以傅祗當時是雍州大中正。。當時御史中丞傅咸認為李含完全是被冤枉的。按照道理,“含有王喪”,應該“上有差代”,但是尚書敕含葬訖攝職,“不聽差代”,就是要他繼續履行官員的職責;司徒又發符屢罰訪問,“踧含攝職”,就是要他繼續履行中正的職責。結果雍州大中正傅祗剛一“議含”,司徒就“隨而擊之”,“奪其中正”,這是州大中正貶郡中正,司徒府奪郡中正的例子。
正因為州中正、司徒府有薦舉、選授郡中正的權力,所以他們也要負連帶的責任。《晉書·卞壸傳》載:
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制出母齊衰期。壸奏曰:“……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辟未有……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并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44)《晉書》卷七○,第1868-1869頁。
卞壸奏王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也就是要免王式的中正之職,而“任人”的司徒、“顯執邦論”“率禮正偽”的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都因為“不勝其任”(45)淮南郡屬揚州,當時淮南郡為何會有大小中正,仍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羅新本先生認為兩晉南北朝時,州有大中正,郡國既有大中正,也有小中正,見《郡國大中正考》,《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72-174頁。,被一并參奏。從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司徒府與州中正、郡中正之間確已構成上下關系,負有薦舉是否得當的責任。
這種更換與貶謫是在中正有病(如孔毓)或干犯清議(如李含、王式)時才會被提出。至于中正在履行本職,即舉人不當時,是否需要負責呢?《晉書·摯虞傳》載:
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46)《晉書》卷五一,第1425頁。
看來中正定品不當時,司徒也是有權參劾的,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正因舉人問題被參僅此一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認為,雖然中正必由現任中央官兼任,但它本身是一個職位。對于中央官的當官能否,有考課進行判斷,上舉劉劭的考課法就是一例。司馬懿誅曹爽之后,“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王)昶陳治略五事……因使撰百官考課事”(47)《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昶傳》,第749頁。,也是一例。這些都是對百官的考課,并不適用于作為職位的中正,所以即使如夏侯玄所說州郡中正品評人才導致的“緬緬紛紛,未聞整齊”,也沒有對中正舉人得當與否進行絕對評判的標準。正因為如此,與摯虞被參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中正在舉人這個問題上幾乎擁有絕對的權力,《晉書·何曾附子劭傳》載:
(何)劭初亡,袁粲吊(何)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48)《晉書》卷三三,第999頁。
袁粲作為中正,可以隨心所欲地調整何岐的鄉品,完全沒有“定品違法”的顧忌。《晉書·李重傳》:
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49)《晉書》卷四六,第1311頁。
在舉霍原為寒素這件事上,中正劉沈與司徒府意見不合,他可以直接抗表中書省。對比上文傅咸因在奏免夏侯駿州大中正事上單獨上奏,被司徒參奏來看,劉沈并沒有因為在舉人這件事上“抗詣中書”而遭到責難。上舉李含被奪中正一事,從傅咸的上表也可以看出中正在舉人方面的權力:
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從弟祗為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50)《晉書》卷六○,第1642-1643頁。
又《通典·禮四十八·兇禮十·斬缞三年》:
(傅)咸又言:“……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敕,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51)杜佑:《通典》卷八八,第2421-2422頁。
大概是因為雍州大中正傅祗是傅咸的從弟,對于李含被奪中正這件事,傅咸只是說“議含已過”,并沒有太大意見。傅咸反對的是,新任的“中正龐騰便割含品”(52)上揭羅新本《郡國大中正考》文認為龐騰是郡國大中正,李含是郡國小中正,但也只是疑似。我認為李含既然被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所貶,則似不太可能繼續擔任中正,龐騰應是接替李含擔任始平郡中正的。,而且據《通典》所引,龐騰是在“無所據仗”的情況下,“貶含品三等”。眾所周知,貶品等于降官,傅咸作為御史中丞,雖然“見含為騰所侮”,卻也只能“謹表以聞”,要求“朝廷以時博議”,實際上就是“乞中書見詰”,要求中書省介入。傅咸的上表里,完全沒有說到對龐騰處置失當的意見,就是因為中正在舉人這件事上擁有絕大的權力。
晉朝的舉人本是由司徒府——中正一系負責。《通典》稱:“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53)杜佑:《通典》卷一四,第328頁。這里是按內外差別來說的,如果按選舉來說,也可以分成兩個系統。一是司徒、司徒左長史、州大中正、郡國小中正構成一個舉人的系統;二是吏部單獨構成一個用人的系統。《通典·職官十四·州郡上·州佐·中正》“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條引《晉令》曰:
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54)杜佑:《通典》卷三二,第892頁。
唐長孺先生已經指出,“三”是“旦”字之誤,這里大概是說大小中正“聽取及討論臨時的升降”。這條令文說明,州郡中正之間有固定的程序討論舉人的問題,他們討論的結果需要及時通知司徒府,以更正被討論者的品第(55)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85、104、111-113頁。。司徒府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擁有發言權的,不僅僅是一個被動接受的機關。《通典·職官二·三公·晉》:
泰始三年……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56)杜佑:《通典》卷二○,第522頁。
《藝文類聚·人部十五·贈答》:
晉潘尼《答傅咸詩》序曰: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為此職,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57)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9-550頁。
由此可見,司徒左長史與州郡中正那種品評一州一郡的士人不同,它是“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實際上處于舉人的最高地位。因此,與中正的選授最終決定于司徒府一樣,中正舉人的最終決定權也在司徒府,也就是說,司徒府是舉人得當與否的最終責任人(58)閻步克先生就指出,當時名“司徒吏”者,大概就是“獲得了中正品第,因而隸名于司徒府、擁有了任官補吏資格者”(《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魏晉的“王官”“司徒吏”》,《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399頁)。周鼎先生則認為“司徒吏”與九品中正制并無關系(《曹魏正始五年〈石門銘〉所見職官釋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4期,第78-82頁)。閻先生后來在《“品位—編任結構”視角中的散吏與比秩》(《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品位結構研究[增補本]》,第494-500頁)文中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補充論證。本文采用閻先生看法。。只有當中正與司徒府在舉人問題上發生沖突,如劉沈舉霍原例,才需要第三方,如中書省介入其中,但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因為:1.正如應璩所說,“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郡中正對于所舉之人可能都不認識,更不用說州中正和司徒府了。因此,司徒府對于中正轉來的士人履歷應該很少過問。2.像傅咸這樣“性直而行”的官員并不多,潘尼就擔心他當官“或有不堪”。果然他當司徒左長史時,因為奏免夏侯駿大中正一事,被府主司徒魏舒參奏。3.司徒府是舉人得當與否的最終責任人,無論是司徒還是司徒左長史,他們都是官,都要接受官員的考課,舉人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獎懲;而中正只是一個職位,最多就是被免,并不影響擔任中正者的官位。上舉傅咸對于李含被免中正一事,其實并沒有什么意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司徒府沒有必要與中正時時發生沖突。
中正不是官,只是職,既沒有任職年限的限制,也不是被納入考課的對象。《晉書·石季龍載記上》:
下書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59)《晉書》卷一○六,第2764頁。
據此,魏晉以來有三年清定九品的制度。這里的“主者”包括司徒府與中正,主要是中正,因為品第升降登記根據的是中正的報告,然后黃紙再定,交給司徒府(60)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11-112頁。。對于中正來說,這是一個根據士人三年表現再定品的過程,與之前的定品無關,中正當然無需對過去的定品負責,因為如果所舉之人的鄉品應該被降,也是他在這三年內表現不好,而不是中正當初舉人舉錯了。至于被舉之人“在吏部選用之后,如果其人行為與品狀不符,卻從沒有以此譴責中正的”(61)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13頁。。由此可見,中正作為一個職位,超然于考課體系之外。
雖然中正的選授須由司徒通過,中正定品違法,司徒也可以參劾,雙方構成一種層級關系,但中正是一個職位,并不隸屬于司徒府,雙方之間沒有統屬關系。所以,當中正與司徒府在舉人問題上產生沖突時,中正可以抗訴。因此,在實際舉人的過程中,中正占有很大的優勢。
劉毅著名的《九品有八損疏》就指出了中正所以能夠“操人主之威福”的主要原因就是“公無考校之負”“無賞罰之防”(62)《晉書》卷四五,第1273-1277頁。。固然司徒偶爾認真一下,像摯虞那樣因為“定品違法”被參劾,結果也是“詔原之”,但如果仔細分析,摯虞的“定品違法”,實際上是指摯虞對所舉之人定品時,或是品狀不符,或是高下有誤方面出現了問題,而不是這個人該不該被舉,該不該被定品的問題(63)一種可能是摯虞與劉沈一樣,為詔舉事與司徒往復辯難。另一種可能是,司徒對所舉之人正好熟悉,愛則欲其品高,憎則欲其品低,摯虞完全沒有領會司徒的意圖。。也就是說,舉誰不舉誰的權力,完全掌握在中正手中。即使真的追究中正對所舉之人的定品問題,最差的結果也不過是免掉中正這個職位,但正如上文所說,這種概率其實很小。
袁粲想要下何岐之品,那是“高下任意”;龐騰貶李含品三等,那是“榮辱在手”。劉毅的表疏實際上直指中正制的弊端——人性、人情。有人就有恩怨,有人就有愛憎,沒有制度的約束,沒有考校的監督,擔任中正職位者要想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施恩望報。《唐語林·賢媛》載: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群,群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64)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10頁。
這雖是唐代的事情,卻很好地說明了舉人者視被舉者為私產,以求回報。這條既然放在《賢媛》篇,說明李夫人說崔群應當報陸贄舉放之恩在唐宋時期是被認可的。劉毅所謂“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的弊端,恰恰是人之常情。唐長孺先生說:
當時反對這種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都承認此一制度已為權門世族服務。我們知道當中正的人自己必須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如《霍原傳》所云幾乎全部是世族,這樣世族自然把持了選舉。(65)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15-116頁。
中正需由二品士人擔任,而二品士人幾乎全部都是世族,出任中正者即使不都是世族,世族也占有絕大多數。中正圈就是世族圈,而且這個圈子會隨著“有私于己,必得其欲”的利益授受關系越來越封閉,這是一個世族與世族之間合作共贏的時代,中正就為這種合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涂之昆弟”(66)《晉書》卷四五《劉毅傳》,第1274頁;卷四八《段灼傳》,第1347頁。胡寶國先生指出,世族并不等于勢族,見《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第83-84頁。我同意胡先生的意見,同時認為“世族”是最有資格也是最有可能成為“勢族”的。,是勢所必然。也正是在魏晉之際,士族開始形成,“九品中正制度保證了士族的世襲特權,而首先保證的是當代顯貴家族的世襲特權”(67)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第61頁。。這樣,世族變成了勢族,進而變成了士族。在這一演變的過程中,固然還有經濟上相應的保障措施(68)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第64-71頁。,但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中正制度。
“東晉以后門閥的形式已經形成,士庶以血緣區別的理論業已建立”(69)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16頁。,以后南朝關心的是士庶的血統區別,至于中正定品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周一良先生指出:
與此(筆者按:指上文所說“中正這個職位在走向衰落”)相適應,我們看到,東晉,尤其宋齊以后,根據清議來懲處官吏的,不再是中正貶降其鄉品,而是政府,特別是御史中丞出面,來處理觸犯清議的案件。(70)周一良:《兩晉南朝的清議》,《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39頁。
中正的職能,一是舉人,此時的作用僅僅是表示程序合法;二是根據清議升降鄉品,此時也由政府官員出面處理。中正實際上已無存在的必要。
十六國時期的政權大多承認士族特權,像“劉曜及石勒稱趙王以后直至滅亡大體上沿用魏晉九品官人及學校之法”,前、后燕,南燕,前秦也都有九品論人的記載(71)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163、165、171-172、173頁。。至于北魏中央的中正,嚴耕望先生非常明確地指出:
《刑法志》云:“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是為無給職,亦不在正式官品之列。……孝文時,中正在選舉用人方面尚有頗大權力,疑孝文尚承舊制。選事專歸吏部,中正不得參與,蓋宣武以后事歟?(72)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43、650頁。
是作為職位的中正,北魏一同魏晉,即“孝文尚承舊制”,而魏晉南朝重門第的弊端,北魏也重蹈覆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宣武以后,“選事專歸吏部”,這是隋廢九品中正的先聲。
二、北朝地方中正職官化的幾個問題
據上引《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載北齊官制,可知到了北齊,無論是中央中正還是地方中正,都具備了“比視官”的身份,都在流內比視官十三等之列。中正有中央、地方之別,是從北魏開始的。北魏中央的中正例由京官兼領,無品秩,選授與魏晉同。地方中正無須兼領,不知道有沒有品秩,例由地方長官辟用(73)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編第七章;張旭華:《九品中正制度研究》第五章第三節。。那么,北齊中正被納入“比視官”的行列具有怎樣的意義?
首先,既然是比視官,那就不是正員官,與《官品令》所載官員仍有區別(74)鐘盛先生認為北齊在《河清令》中對流內比視官的種類、品階等均有明確記載,這是對它們正式職官性質的確認,見《北朝州佐的“品階化”進程——以北齊〈河清令〉為中心》,《江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124-133頁。,但此時的中正已經不是無官品的“職位”,它有向官位發展的可能。
其次,比視官表示“視某品”,即等同于相應的官品,這就具有給中正定等級的意義。嚴耕望先生研究北魏中央州大中正的本官時指出,“本官高下實無定準,高者至從一品,低者至七品。其伸縮性之大可以想見”(75)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46頁。。中央的各級中正,本官官品較中正比視官品高者可以不論,較中正比視官品低者,就有可能依照比視官提高自己的等級地位。這對于地方上作為僚屬的中正尤其重要,不僅明確了其地位,還可以據此領一份俸祿。
第三,閻步克先生在研究秦漢官僚品位結構中的“比秩”問題時,曾指出“比秩”諸官的性格之一就是表示他們由府主“自辟除”(76)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增補本)》,第443-451頁。。我想這對于地方上的中正也同樣適用。
將中正定為“比視官”,對于地方上中正的意義遠大于中央的中正。中央的中正,自魏晉以來,例由中央官兼領。即使北齊將中正納入“比視官”,中央的中正也并未獨立,仍遵循魏晉以來中央官兼領的傳統(77)張旭華:《九品中正制度研究》,第450-455頁。。地方上的中正卻是個新生事物,但兩者并非全無聯系。嚴耕望先生指出:“前者掌選本州本郡人才,提供中央之選用;后者選薦本州郡縣之寮吏。”(78)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51頁。可見兩者在職能上并無不同。新生的中正只是魏晉以來中正的地方版而已,它的產生過程本就是職官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對于北朝地方中正的職官化過程,上揭諸位前輩均已有所研究,這里只擬對三個方面的問題略作闡釋。
(一)東魏“光初中正”的意義
東魏武定七年(549)《義橋石像碑》碑陰第二列有“郡光初中正李惟孝”,碑側有“□光初□正賈奴”(79)毛遠明編著:《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八冊,第一○二六號,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第94-101頁。碑陰上列文字磨損嚴重,《校注》據《金石萃編》錄文;碑側文字,因《萃編》失收,《校注》據《八瓊室金石補正》錄文。嚴耕望先生據《金石萃編》碑陰錄文,指出郡中正“有光迎之目”,見《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41頁。。今細審圖版,碑陰第二列,似可辨別“初中”二字;碑側也似可辨別“中正賈奴”四字。東魏的“光初中正”是什么意思?它與北朝的地方中正又有什么關聯?
考《隋書·百官志中》載北齊官制:
上上州刺史……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
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
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80)《隋書》卷二七,第762頁。《隋書(修訂本)》同,第848頁。原文“上上州刺史”處,“州都光迎主簿”未點斷,疑誤,州都就是地方的州中正,與光迎主簿為兩個不同官職。
可見北齊地方政府中既有光迎主簿、光迎功曹,也有功曹、主簿。我們知道,自西晉以來,中央的州大中正本有臨時委任州掾屬的權力。《通典·職官十四·州郡上·州佐·中正》引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81)《通典》卷三二,第892頁。唐長孺先生對此解釋道:“這大概在新舊刺史交替之間由于州郡掾屬,例由長官委任,而新長官尚未到任,舊長官業已卸職,舊掾屬也隨之離職,因此臨時由中正委任。”(82)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101頁。胡寶國先生對兩晉南朝的這種現象進行了舉證與分析,認為“州中正所任命的只是州郡迎吏,而非一般州郡長官的屬佐”,“諸州光迎主簿”有優先入仕權(83)胡寶國:《九品中正制雜考》,《文史》第36輯,第293頁。。應該注意的是,州大中正執行的仍是舉人的責任,“選州里才業高者”,讓他“兼主簿”,“兼”字就說明這個主簿的臨時性,史料上稱之為“迎吏”,《職官志》則冠以“光迎”,明示他們與一般僚佐的不同。“諸州光迎主簿”是否為州的屬佐,不明,但這種經過州大中正推選的人,起碼獲得了一種身份,梁陳時期甚至有優先入仕的權力,所以胡先生所舉史料中有暗示、請托中正任命這種迎吏的事例。
因此,北齊地方政府中冠以“光迎”二字的功曹、主簿,顯然是仿自魏晉南朝,由中央中正任命,在新舊長官交替之際從事迎新送故等事宜,這時已經固定為地方僚佐。北齊天保三年(552)《宋顯伯等四十余人造像記》有“河內郡光初主簿、祭酒從事宋顯”(84)毛遠明編著:《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八冊,第一○八六號,第274-278頁。。嚴耕望先生注意到這方碑刻,認為“按南朝州佐功曹主簿有迎新送故之目,此當仍從《隋志》作‘光迎’,蓋形近誤釋也”(85)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621頁。。今細審圖版,似為“初”字,不像“迎”字。上引《義橋石像碑》另有“武德郡光初功曹(闕)”(86)毛遠明編著:《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八冊,第一○二六號,第94-101頁。。本碑磨損嚴重,該處圖版無法識別,《校注》根據王昶《金石萃編》錄文,也作“光初”。但碑刻中的確有作“光迎”的,隋開皇十四年(594)《趙君志》:“君身□□錄事參軍、郡參議、縣光迎功曹,年六十七。武平五年七月二十日卒。”(87)王其祎、周曉薇編著:《隋代墓志銘匯考》第二冊,第一三八號,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第151-153頁。圖版“光迎”字樣清晰。志主趙某卒于北齊武平五年(574),考慮到他最后一任官職就是“縣光迎功曹”,那么擔任的時間很大可能應在北齊時。通過這三方碑刻的比較,說明在東魏北齊時,這種由中央中正任命的“迎吏”,最初很有可能冠以“光初”,以后才改為“光迎”,并被《百官志》記錄了下來。由此可見,東魏《義橋石像碑》出現的“光初中正”應該就像“光初主簿”“光初功曹”一樣,是由中央中正任命的迎新送故隊伍中的一員。
就目前所見的史料來看,北魏沒有“光初中正”,北齊也沒有“光初中正”,只有東魏出現了這一名稱。這的確是體現地方中正職官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因為中正在性質上已經變得和主簿、功曹一樣了。至少到了東魏時期,地方上的中正已經完全固定為地方政府中的僚屬,中央的中正已經像任命“光初主簿”“光初功曹”等迎吏那樣,開始任命“光初中正”了。可是為什么北齊保留了“光迎(初)主簿”“光迎(初)功曹”,卻沒有保留“光初中正”,的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88)如果是因為職能重復,那么光迎主簿、光迎功曹應該一并廢除。北齊官制中既有光迎主簿、光迎功曹,也有主簿、功曹,說明冠以“光迎”的主簿、功曹并不會影響地方政府中主簿、功曹的正常工作。同理,“光初(迎)中正”也不會影響到地方政府中中正的正常工作。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今本《隋書·百官志中》載北齊官制脫漏了“光初(迎)中正”一項。。
(二)地方中正產生的可能性因素:軍事
《南齊書》載建元元年十月辛巳詔:“……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捍邊役,末由旋反,聽于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為言列。”(89)《南齊書》卷二,第35頁。蕭道成即位以后,對四州士庶普降恩澤,授官定祿。其中對于“荒遠闕中正”的,允許“據軍簿奏除”。也就是說,本來是需要依據中正的品狀,現在有司可以據軍簿記錄除授官職。軍簿即軍中文簿,相對于編戶齊民的“簿籍”即戶籍等,或指記錄將士功勛的“勛簿”,以備行賞、敘階、授官(90)《漢書》卷五四《李廣傳》“吏治軍簿”條顏師古注,第2441頁。東晉南北朝時,皆行“勛簿”“勛書”“勛券”之制,勛簿為統兵將領所制作的一種登記簿之類,軍簿與軍隊選舉有關,而軍中中正,則是管選舉的專官(參見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張君義勛告〉》,《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43頁;牟發松:《六鎮起義前的北魏行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輯,1991年,第119-127頁)。。九品中正制度成立以后,不由中正品評舉薦,只能算是特例,所以是“特許”。但實際上,晉宋時期有一種說法,就認為九品論人來自軍中。
梁沈約曾經說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91)《宋書》卷九四《恩倖傳》序,第2301頁。更早的西晉李重上疏陳九品也說:“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92)《晉書》卷四六《李重傳》,第1309頁。雖然沈、李二人對于九品中正制之施行時間可能有所誤會(93)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第95頁。,但晉宋時的這種認識說明軍中立九品以論人似乎是有淵源的。所謂“權立九品”,很有可能就是據軍簿所載,立九品來區分等級。按照他們兩人的說法,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仿自軍中。為什么蕭道成可以“特許據軍簿奏除”?因為軍簿上記錄的功勞大小本就可以論人才優劣。那么軍中由誰來“論人才優劣”?魏晉南朝似與中正無關,北朝則不同。《劉賢墓志》載:
君先至營土,因遂家焉。但營州邊塞,地接六蕃。君梟雄果毅,忠勇兼施,冀陽白公,辟為中正。后為臨泉戍主、東面都督。(94)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七冊,第八七五號,第91-94頁。
劉賢所擔任的是營州治下冀陽郡的中正,是由冀陽郡守白公選任。據王金爐先生的研究,劉賢任此職的時間應在太平真君五年至八年(444-447)間(95)王金爐:《劉賢族屬之管見》,《遼海文物學刊》1995年1期,第89-91頁。。這說明北魏入主中原以后很早就設立了中正,這個中正由郡守辟任,只能是地方上的,與中央選任的中正完全不同,劉賢以后僅任戍主也可以佐證這一點。劉賢為什么會被辟為中正呢?這跟冀陽郡所在的營州有關。當時營州是邊塞,軍事行動比較頻繁,郡守設立中正的原因大概是為了對戰爭中的有功之臣進行分等。《魏書·爾朱彥伯附仲遠傳》載:
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仆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96)《魏書》卷七五,第1666頁。
這雖是魏末之事,但可見行臺權立中正的原因就在于“在軍定第,斟酌授官”。十六國北朝的行臺本就有一個地方官化的過程(97)牟發松:《北朝行臺地方官化考略》,《文史》第33輯,1990年,第75-95頁。,只是行臺更偏于軍事上的色彩。
北魏在立國的過程中,自道武帝至太武帝時期,頻繁地發生軍事行動,軍中的“斟酌授官”就顯得尤為迫切。以魏晉品人的中正適應北魏“在軍定第”的需要,這就是軍中設置中正的原因。當軍事行動結束之后,這種權置的中正是否并未消失,而是由軍府之佐一變而為地方州郡之官了呢?這些問題仍有待探討。
這兩個因素共同體現了北朝地方中正在設立過程中的臨時性(98)賴瑞和先生在討論唐代使職與職事官關系時指出,臨時性的使職可能才是官僚制度發展的源頭,見《唐代高層文官》第一章《使職的起源和職事官的相互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特別是第22-31頁。。中央的中正本來任命光初(迎)中正作為地方送故迎新中的一員,地方仿效設立中正。軍事因素則可能是地方設立中正的更早淵源。魏晉南朝作為職位的中央中正在北朝開始有了地方版,孝文帝定姓族則給了它們轉化為職官的強大動力。
(三)孝文帝定姓族后官品的重要性
在北朝,無論是中央的中正還是地方新出現的中正,將它們納入“比視官”行列都顯示出這中間有一個職官化的過程(99)本節的討論,曾經樓勁研究員、牟發松教授的提點,謹致謝。。魏晉南朝,門閥個體及姓族雖與皇權、與官位有密切關系,但并無制度方面的規定,有的是習慣,有的是社會地位,包括文化等,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明確與官位掛鉤,這是唐朝氏族志特別是淪為“勛簿”的武周姓系錄的先聲。關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這一重大舉措,唐長孺先生指出:
它具有明確、具體的官爵標準和明確的四級區分,而這在兩晉南朝至多是習慣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威權采取法律的形式來制定門閥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100)唐長孺:《論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第91頁。
孝文帝以前,北魏延續魏晉以來九品中正制的傳統以爭取中原舊族的合作,但是始終存在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鮮卑勛貴的社會地位。太武帝年間,名臣崔浩被殺,牽連頗廣。浩之被殺,原因很多,但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101)《魏書》卷四七《盧玄傳》,第1045頁。大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周一良先生就認為崔浩此舉具有“提高漢人高門的地位,抑制鮮卑人的作用在內”(102)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129頁。。如果依照漢人“經明行修”的標準,恐怕鮮卑勛貴并不會獲得多高的中正品第。孝文帝欲熔冶胡漢統治于一爐,泯滅民族的界限以求聯合統治以鞏固北魏政權,就必然要處理好這個問題。他依先世官爵判別鮮卑姓族高低,考慮先世官爵與入魏后官爵來差第漢人門閥,這樣就將胡漢統治階級重新編制于新的門閥序列之中(103)唐長孺:《論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第80-82頁。參見凌文超:《鮮卑四大中正與分定姓族》,《文史》2008年第2輯,第105-113頁。凌先生論及“宣武帝銓量鮮卑姓族過程中最大的發展就是制定了‘胡漢’高門所對應的官爵序列,從而將胡漢官僚貴族整合在北魏政權體制之下,實現了胡漢高門的合流”。這就說明宣武帝很好地繼承和貫徹了孝文帝依官爵定姓族的政策,雖然這種政策導致了新的門閥序列的產生。。既然當代官爵成為判定士族的唯一標準,中央的中正也就失業了,因為再不需要他們來“清定門冑,品藻高卑”,那么由誰來擔任中正就遠沒有那么重要。
制度的規定帶來的變化是如此迅速,可以從以下兩段史料的對比看出來。《魏書·穆崇附亮傳》載:
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104)《魏書》卷二七,第668頁。
同書《世宗紀》載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四月:
乙丑,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105)《魏書》卷八,第198頁。
據《元萇墓志》,復置司州在太和十二年(488)(106)參見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廢而復置》,《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6輯,2010年,第55-61頁。,在太和十九年定姓族前七年,當時選任司州中正仍然審慎,“必須德望兼資者”,這也正是元懌所說“高擬其人”(107)此司州中正雖然是為了審察司州僚吏而設,但必為中央所設之州大中正,非司州轄下中正,大概是因為司州新設且地位特殊的緣故,參見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第651頁附記。。然而,定姓族詔頒布以后,僅僅過了十年時間,宣武帝明詔直斥“中正所銓,但存門第”,以至于惱火地要求“審議往代貢士之方”,但是他忘了,這個門第是由他的父親一手造成的。宣武帝時期的門第是孝文帝定姓族以后形成的新的門第,是依官爵形成的門第,這種門第并不是中正所能左右的,因為中正改變不了先世和當代的官爵。
《魏書·李彪傳》載:
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時論以此譏祚。(108)《魏書》卷六二,第1398頁。
據本傳,李彪“家世寒微”,所以當孝文帝時,宋弁作為大中正,“猶以寒地處之”,李彪也并無怨言。但等到他為子求官時,郭祚“以舊第處之”,卻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據《郭祚傳》,祚為吏部尚書是在孝文帝崩后,宣武帝年間(109)《魏書》卷六四,第1422-1423頁。,這正是在孝文帝以當代官爵定姓族之后,所以李彪自以為“位經常伯,又兼尚書”,官爵頗高,所以按照新規,自應列于“貴游”,這就是他“忿怨”的原因所在。更可注意的是,“時論”也站在李彪一方,也就是說,當時人普遍認為他應該得列于“貴游”,可見孝文帝建立的新的門閥序列得到了承認。在新的秩序下,不用求中正,僅憑自身官爵就可以直接為兒子向吏部尚書求官。
既然孝文帝定姓族之后的官品如此重要,那么沒有官品、作為職位的中正就有了向職官轉化的動力,它的外在表征就是官品。因為在這之后,門閥的序列、享受的特權都與官密切相關,這也是北朝中正職官化的另一個因素。
三、結 論
從“職位”的角度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任命的中正似乎始終是一種職位,時人可以討論是否設置與廢除。凡是擔任這種中正的人,都是現任中央官,這個中央官實際上就是中正的本官。由于這種中正沒有任期,也沒有考課,所以中正選舉的結果必然朝著謀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雖然司徒府可以就中正違法問題提出劾奏,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司徒府長官與中正所選舉的人員間在數量上的嚴重不對稱,使得這種管理流于形式。這是門閥社會得以形成的制度原因。即使到了北齊時期,這種中正已經有了比視官品,但是仍然由中央官兼領,也仍然是不獨立的。
從“官位”的角度來說,北朝州郡辟除的中正雖然也是“比視官”,且地位很低,但它是獨立為官,有比視官品,有俸祿,不再依附于其他官位。這種地方中正的產生可能與北朝的軍事行為有關,且在東魏時已完全固定為地方僚屬。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北朝中正走向職官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之后,官品的重要性,即決定門閥序列高低的不再是中正品第,而是官爵高低。
無論如何,中正在從“職位”向“官位”的征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上的中正,在北齊獲得了比視官品,有向正式職官轉化的可能,但這個步伐在隋代停止了。《通典·選舉二·歷代制中》“宣王辭不能改,請俟于他賢”條注曰:“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110)杜佑:《通典》卷一四,第328頁。這是指隋開皇中廢除了魏晉南北朝中央選舉人才的中正。至于地方上的中正,依據《隋書·百官志下》載開皇三年(583)四月詔,明確“州都、郡縣正”為“鄉官”以及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111)《隋書》卷二八,第792、793頁。,可知地方上的中正在開皇年間也被廢除了,關于“罷州縣鄉官”在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重要意義,濱口重國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112)濱口重國:《所謂隋の鄉官廢止に就いて》,《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第770-786頁。。
無論中央還是地方上的中正,隋朝從制度上都加以廢除,中央的權威得到了極大加強。繼承了隋制的唐朝,在這個問題上曾有反復。據《資治通鑒》,高祖武德七年(624)“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113)《資治通鑒》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088頁。。這種“掌知州內人物”,又“無品秩”的州大中正,顯然是九品中正制下,中央州大中正的復活。《大唐故朝散大夫潞州大中正李君之墓志銘并序》載志主李楚:“拜朝散大夫,尋遷潞州大中正。”(114)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30頁。據墓志,李楚年六十七卒,葬于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卒于何時,不明。根據志文,可以知道他任潞州大中正應在唐初。不僅中央設置了州大中正,而且地方政府里也有中正。《唐故開府右尚令王君墓志銘并序》載志主王仁則:“武德初,應調為縣中正,俄除右尚令,非其好也。”(115)周紹良、趙超編著:《唐代墓志匯編》貞觀○九四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一一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8頁。這個縣中正就是北朝地方政府里中正的延續。
唐初的中正可以視為魏晉南北朝中正制度的一點余波,當時選舉上已經不再需要中正這個環節,地方僚佐也不需要中正選薦,所以《通典》稱:“隋有州都……大唐無。”又言中正“隋初有,后罷而有州都。大唐并無此官。”(116)杜佑:《通典》卷三二,第892頁;卷三三,第915頁。杜佑就干脆忽視了唐初制度,宣判中正退出了大唐的舞臺。
附記:本文曾提交2019年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的“社會史視野下的魏晉制度變遷”工作坊。與會期間,樓勁研究員曾給予重要提示。會后,牟發松教授、王素研究員、已故賴瑞和教授都曾細心審閱全稿,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對于前輩學者的無私幫助,筆者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