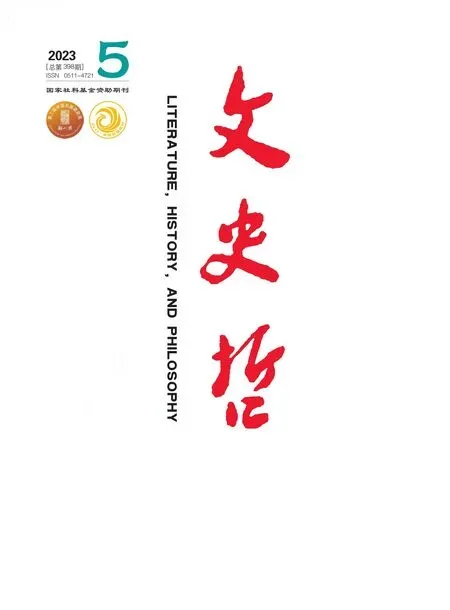論法家政治思維的角色轉(zhuǎn)換
——以西方馬基雅維利研究為參照
宋洪兵
先秦法家是一個(gè)對(duì)中國古代政治影響深遠(yuǎn)的思想流派。從胡適開始,現(xiàn)代中國學(xué)界就對(duì)何謂“法家”的問題提出了質(zhì)疑。按照司馬談、班固等人的說法,法家的突出特點(diǎn)在于:嚴(yán)而少恩,鐵面無私、一斷于法,這種觀念走向極端或者權(quán)力落在極端、殘暴之人手里,容易傷害親情,導(dǎo)致暴政、苛政;君尊臣卑,只可以作為儒家君臣倫理的一個(gè)輔助性資源。劉邵《人物志·流業(yè)》則認(rèn)為:“建法立制,強(qiáng)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1)劉邵撰,王曉毅譯注:《人物志譯注》卷上《流業(yè)第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60頁。章太炎《商鞅》則說:“法家者流,則猶通俗所謂政治家也,非膠于刑律而已。”(2)章太炎:《商鞅》,《訄書》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頁。綜合上述見解,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家”具有雙重內(nèi)涵:其一,“法家”是一個(gè)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百家爭(zhēng)鳴時(shí)代的思想流派,他們的思想以法治、富強(qiáng)、加強(qiáng)君權(quán)為根本特征;其二,“法家”又是一個(gè)政治家群體或與現(xiàn)實(shí)政治密切相關(guān)的群體,他們最為關(guān)切的并不僅僅是理論建樹,而是迫切希望運(yùn)用自己的思想去進(jìn)行政治實(shí)踐,渴望對(duì)現(xiàn)實(shí)政治產(chǎn)生影響,改造現(xiàn)實(shí)。管仲、子產(chǎn)、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李斯等,向來都被視為法家人物,他們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韓非子雖非手握大權(quán)的政治家,卻身處韓國政治中樞,與現(xiàn)實(shí)政治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實(shí)非普通士人所能比擬。即便慎到,好像沒有多大實(shí)權(quán),但是他作為稷下學(xué)宮的成員,“不治而議論”,實(shí)為齊國國君的政治顧問。
究竟誰是“法家”?清末的時(shí)候,梁?jiǎn)⒊c麥孟華等人曾編撰過一部著名的書,名叫《中國六大政治家》(3)梁?jiǎn)⒊?《中國六大政治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六大政治家包括管子、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張居正。梁?jiǎn)⒊热水?dāng)時(shí)在“國家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主張以國家主義來救亡圖存。他們將法家視為“國家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所以他們認(rèn)為六大政治家其實(shí)都有濃厚的法家色彩。民國時(shí)期的陳啟天則在這份名單上增加了漢代的晁錯(cuò)和前秦時(shí)期的王猛(4)參見陳啟天:《中國法家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由此以觀,章太炎把法家視為政治家,并不用狹隘的刑律專門人才來定義法家,這是一個(gè)深刻的洞見。問題在于,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具備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yàn)和政治智慧,這就給當(dāng)代純粹的書齋里的法家研究者提出了一個(gè)嚴(yán)峻挑戰(zhàn):不具備政治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與體會(huì)的學(xué)院派學(xué)者如何恰如其分地理解法家?同時(shí)順帶著又引出一個(gè)更為嚴(yán)峻的倫理挑戰(zhàn):當(dāng)今學(xué)者如果對(duì)法家學(xué)說所呈現(xiàn)的政治道理持認(rèn)同而非批判態(tài)度,則無異于將自己置于道德不正確的境地而面臨著法家曾經(jīng)遭遇的儒家意義上的暴政批判與民主自由意義上的專制批判,法家研究者如何回應(yīng)或如何自處?甚至有批評(píng)聲音會(huì)質(zhì)問:當(dāng)一個(gè)法家研究者認(rèn)同專門為支配者出謀劃策的法家學(xué)說時(shí),你想過自己究竟是強(qiáng)勢(shì)的支配者還是弱勢(shì)的平民百姓?形象地講,自己明明是一只待烤的鴨子,為何偏偏具有“全聚德”的思維?這將是本文要重點(diǎn)探討的話題。筆者嘗試以政治心理學(xué)的視角切入,力圖論證從“政治家”到“學(xué)者”的角色轉(zhuǎn)換,不僅不會(huì)構(gòu)成當(dāng)今法家研究者的困境,而且還是人們深入辨析人類政治特征的一個(gè)理論契機(jī),同時(shí)也是使法家政治學(xué)說理論生命力再生于當(dāng)今社會(huì)的一種有益探索。
一、“馬基雅維利困境”及其解決之道
人類之所以需要政治,乃是因?yàn)槿祟愡^著群居生活。群居必然會(huì)面臨各種利益沖突,由此就凸顯了秩序?qū)θ祟惿畹闹匾浴U蔚谋举|(zhì)在于運(yùn)用權(quán)力來分配利益并調(diào)節(jié)利益沖突。沒有權(quán)力和利益,就不會(huì)存在人類政治。人類政治的根基深植于人性,人性既善又惡的復(fù)雜情形決定了人類政治的復(fù)雜性。甚至可以說,政治就是人性。政治家每天面對(duì)的以及所要解決的,就是運(yùn)用權(quán)力和影響力去平衡沖突、裁決是非并維持整個(gè)共同體的基本秩序。如此,政治家最關(guān)心的,當(dāng)然是他的政治地位,但是為了有效維護(hù)他的統(tǒng)治,他不得不考慮個(gè)體感受,同時(shí)還要關(guān)注群體生存。當(dāng)個(gè)體利益與群體生存或他的統(tǒng)治地位發(fā)生沖突時(shí),他必須做出抉擇,由此就會(huì)面臨政治與道德的兩難:究竟按照抽象的道德原則來做事還是按照利益權(quán)衡來行動(dòng)?這是一個(gè)人類政治難以回避的困境。每一個(gè)政治家,事實(shí)上都面臨一個(gè)類似軍事統(tǒng)帥所面臨的那種困境:為了贏得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他是否愿意將部分士兵作為贏得最后勝利的手段或籌碼而犧牲之?
如何應(yīng)對(duì)政治與道德的兩難困境?馬基雅維利曾有入木三分的描述,他一方面主張君主應(yīng)該總是將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與虔敬信神等美德掛在嘴邊,另一方面君主又必須在意識(shí)到需要改弦更張維護(hù)自己統(tǒng)治利益的時(shí)候,要毫不猶豫地在行動(dòng)上做出改變:“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5)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年,第85頁。馬基雅維利事實(shí)上給出了解決政治與道德兩難困境的一個(gè)可行方案:支配者在實(shí)際的政治生活中,需要密切關(guān)心自己的統(tǒng)治利益而不要被各種類型的抽象道德原則所束縛,但是支配者永遠(yuǎn)要裝著有道德,決不能“公然”違背人們認(rèn)同或期待的各種美德。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明確主張君主在政治生活中必須學(xué)會(huì)偽裝和表演。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闡述:
你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還要這樣去做,但是你同時(shí)要有精神準(zhǔn)備作好安排:當(dāng)你需要改弦易轍的時(shí)候,你要能夠并且懂得怎樣作一百八十度的轉(zhuǎn)變。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夠?qū)嵺`那些被認(rèn)為是好人應(yīng)作的所有事情,因?yàn)樗3謬?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zhǔn)備,隨時(shí)順應(yīng)命運(yùn)的風(fēng)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轉(zhuǎn)變。(6)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第85頁。
君主必須表面上維護(hù)道德原則,甚至提倡美德,但是在實(shí)際政治生活中絕不受這些道德原則約束。這當(dāng)然對(duì)君主提出了一個(gè)很高的政治技藝要求。君主可以不受道德原則約束,但是必須講究策略,偽裝和表演就不可或缺。但是,提醒支配者應(yīng)該偽裝和表演,以及如何偽裝與表演,其實(shí)都與人們對(duì)支配者的道德期待大相徑庭,一旦公開,不但不能幫助支配者獲得并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反而會(huì)有損支配者的道德形象。“治國之道即表演之道。”(7)菲利普·博比特:《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楊立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第63頁。簡(jiǎn)單講,馬基雅維利的這些教誨應(yīng)該是有權(quán)者的“潛隱劇本”(hidden transcript)而不應(yīng)該是“公開劇本”(public transcript)(8)所謂“公開劇本”是指從屬者與支配者之間的公開互動(dòng),由于涉及各自利益的考慮,從屬者與支配者在公開場(chǎng)合都會(huì)進(jìn)行表演,說一些冠冕堂皇但卻言不由衷的話。所謂“潛隱劇本”,則是指發(fā)生在后臺(tái)(offstage)的話語,包括在后臺(tái)發(fā)生的言語、姿勢(shì)和行為,它們可能會(huì)確證、否定或扭曲公開劇本所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參閱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與抵抗藝術(shù):潛隱劇本》,王佳鵬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第2-7頁。需要指出的是,斯科特關(guān)注的是底層人民的“潛隱劇本”及“潛隱政治”,本文借用“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的概念意在表達(dá)兩個(gè)層面的內(nèi)涵:其一,政治領(lǐng)域充滿了“表演”;其二,側(cè)重論述政治領(lǐng)域當(dāng)權(quán)者的“潛隱劇本”與“潛隱政治”。。筆者認(rèn)為,政治領(lǐng)域的“公開劇本”是指支配者在公開場(chǎng)合向其統(tǒng)治范圍內(nèi)的所有人講的各種蘊(yùn)涵道德倫理與理想價(jià)值的話語;“潛隱劇本”則是支配者在私下或秘密場(chǎng)合思考和討論的不宜公開卻又直接關(guān)涉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政治利益的隱蔽話語。
按照上述比喻,政治好比一個(gè)舞臺(tái)劇,主角當(dāng)然是支配者,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配角,普羅大眾基本都是觀眾。不少學(xué)者已經(jīng)將政治視為一種舞臺(tái)表演藝術(shù),如摩根索認(rèn)為:“政治舞臺(tái)上的演員情不自禁地要‘做戲’,他們戴上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面具,隱藏起自己政治行動(dòng)的真實(shí)面目。……雖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對(duì)權(quán)力的追求,但意識(shí)形態(tài)卻把參與這種權(quán)力角逐解釋成演員和觀眾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種東西。”(9)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quán)力斗爭(zhēng)與和平》,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124頁。所謂“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其本質(zhì)就是政治家將道德作為表演的道具,根本目的在于引導(dǎo)觀眾相信他們并接受他們的統(tǒng)治,屬于“公開劇本”。政治,不僅僅是平衡利益沖突的藝術(shù),而且還是表演的藝術(shù)。以賽亞·伯林曾觀察到蘇聯(lián)時(shí)期的官員因?yàn)椤叭霊蛱睢?以至于將自己在官場(chǎng)中的表演與日常生活混為一談:“他們對(duì)他們所說的確信無疑,可以說就好像所有國家的政客都相信一套表演術(shù)一樣:自認(rèn)為善于控制這種表演,并以此來迎合觀眾,因?yàn)樗某晒εc發(fā)達(dá)取決于此。這套表演已經(jīng)明顯地與他的整個(gè)自我表達(dá)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可能對(duì)自己也如此表演,對(duì)朋友和同事更不待言。”(10)以賽亞·伯林:《蘇聯(lián)的心靈》,潘永強(qiáng)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53頁。伯林所論,當(dāng)然不止于蘇聯(lián)官員,他明確說所有國家的政客都擅長(zhǎng)表演術(shù)。意思是說,所有國家所有制度所有文明之下的政治,其實(shí)都離不開表演。荷蘭裔的美國生物學(xué)家德瓦爾走得更遠(yuǎn),他不僅聲稱“政治的根比人類更古老”,而且還從黑猩猩政治中領(lǐng)悟到人類祖先實(shí)際已經(jīng)在運(yùn)用馬基雅維利式的各種政治技巧。“政治家們會(huì)大聲嚷嚷他們的理想和承諾,但對(duì)自己私下里對(duì)于權(quán)力的熱望則會(huì)小心翼翼地掩飾著,以免暴露出來。”(11)弗朗斯·德瓦爾:《黑猩猩的政治:猿類社會(huì)中的權(quán)力與性》,趙芊里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247頁。在人類漫長(zhǎng)的政治舞臺(tái)劇中,始終存在著呈現(xiàn)給觀眾的“公開劇本”與幕后的、秘不示人的“潛隱劇本”兩個(gè)截然相反但又同時(shí)存在的行為邏輯。
雖然馬基雅維利以言行不一致的政治表演解決了道德與政治對(duì)立的困境,但是同時(shí)又產(chǎn)生了另外一個(gè)困境:越是馬基雅維利學(xué)說的信徒,就越會(huì)反對(duì)馬基雅維利及其學(xué)說。馬基雅維利解決方案必須具有所講內(nèi)容秘密性以及講述對(duì)象的專屬性,秘密性體現(xiàn)為不能公開講,專屬性體現(xiàn)為只能對(duì)君主一個(gè)人講。唯其如此,君主才能放心采納他的建議而沒有擔(dān)心被人指責(zé)的道德顧慮。德國哲學(xué)家恩斯特·卡西爾認(rèn)為,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教師的身份教誨君主要具有獅子和狐貍的雙重品格,必要時(shí)不受道德原則約束,君主要學(xué)會(huì)詭計(jì)和奸詐的藝術(shù)。“政治教師必須懂得兩件事:他必須一半是人,一半是獸。在馬基雅維利之前,沒有任何政治著作曾經(jīng)是以這種方式來說話的。……沒有人懷疑,政治生活作為存在著的事實(shí)充滿著罪行、奸詐和犯罪。但在馬基雅維利之前,沒有任何思想家去承擔(dān)教授犯罪的藝術(shù),這些事是光做不教的。馬基雅維利承諾要成為一個(gè)教授奸詐、背信棄義和殘酷藝術(shù)的教師,倒是一件聞所未聞之事。”(12)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范進(jìn)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0年,第182-183頁。卡西爾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馬基雅維利教導(dǎo)支配者如何處理道德與政治的兩難問題時(shí)的解決方案,原本其實(shí)是“光做不教的”。即使要說,也只能悄悄地跟君主耳語,并且只能對(duì)君主一個(gè)人說;即使要寫,也只能給君主一個(gè)人看,而不能以白紙黑字流傳公開,更不能流傳后世。“潛隱劇本”的突出特征在于能做不能說。
“潛隱劇本”一旦公開化,將會(huì)產(chǎn)生怎樣的道德反應(yīng)呢?首先,在觀眾那里,不會(huì)感念馬基雅維利說出了政治的真相,而是會(huì)從道德感覺角度極度厭惡其居然教唆支配者作惡;其次,在支配者那里,一旦違背秘密性與專屬性原則,馬基雅維利的方案就會(huì)面臨本意在“教誨”君主如何策略性地作惡卻不小心變成“揭露”君主虛偽治國的尷尬境地,這無異于將魔術(shù)師的魔術(shù)拆分講解,讓觀眾對(duì)魔術(shù)背后的各種伎倆了如指掌,從而造成支配者表演失靈的風(fēng)險(xiǎn)。這讓后來登上政治舞臺(tái)劇的主角情何以堪?!支配者如果認(rèn)可馬基雅維利的方案,那就無異于承認(rèn)自己在欺騙和表演,這根本就有違馬基雅維利不得公然違背道德原則的教誨。因此,真正的馬基雅維利的信徒,都會(huì)態(tài)度鮮明地反對(duì)馬基雅維利的方案,只是暗地里按照他的教誨去做。這實(shí)在是一個(gè)頗有反諷意味的悖論!
真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必然反對(duì)馬基雅維利,本質(zhì)上體現(xiàn)了權(quán)力的悖論(13)也有學(xué)者將權(quán)力悖論定義為:“所謂權(quán)力悖論,即我們憑借人性的優(yōu)點(diǎn)崛起掌權(quán),影響世界,卻因人性的缺點(diǎn)失權(quán)垮臺(tái)。我們通過改善他人的生活,而獲得影響世界的能力,然而,正是這一掌權(quán)的過程讓我們?cè)谀承╇y以自控的時(shí)刻暴露了人性的缺點(diǎn),像沖動(dòng)失控的瘋子一樣行事。”“權(quán)力悖論的關(guān)鍵之處:如何行使自己的權(quán)力?是繼續(xù)影響世界以贏得他人持久的尊重,還是像之前的許多人那樣濫用權(quán)力,最終失去權(quán)力?繼續(xù)行使權(quán)力或失去權(quán)力又取決于什么?”見達(dá)契爾·克特納:《權(quán)力的悖論》,胡曉姣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X、XVI頁。:自成目的的權(quán)力意志將導(dǎo)致權(quán)力的自我否定。以支配服從為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權(quán)力,乃是人類秩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政治的客觀存在。不排除這樣的情況,具有強(qiáng)烈權(quán)力欲的支配者,或許會(huì)通過擁有權(quán)力并維持權(quán)力來獲得心理滿足,他將權(quán)力本身作為目的。但是,自成目的的權(quán)力很難證明權(quán)力自身的自我完足性,因?yàn)闄?quán)力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類關(guān)系的體現(xiàn),赤裸裸的強(qiáng)制權(quán)力必將帶來激烈的反抗。秉持權(quán)力意志的支配者如果完全不顧道德原則,終將玩火自焚,無異于自掘墳?zāi)埂?quán)力的運(yùn)用過程始終伴隨著相應(yīng)的道德理由或宗教理由,而權(quán)力的支配本質(zhì)也必須通過非權(quán)力的面目來呈現(xiàn)。因此,權(quán)力的悖論必然導(dǎo)致政治領(lǐng)域成功運(yùn)用權(quán)力的準(zhǔn)則也即“治術(shù)”(Kratologie)的曖昧性:“它的規(guī)則如果公開的話是雙面的,因此它們最終將被那些執(zhí)迷權(quán)力者保持為秘密”。支配者試圖將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技藝保持為秘密的想法一旦失敗而公開化,這種政治技藝就將呈現(xiàn)為一種雙面性:支配者會(huì)知曉不受道德原則約束的政治技藝,服從者也會(huì)明白支配者在玩弄伎倆。由于支配者向來都以心照不宣的方式運(yùn)用該政治技藝,而政治技藝公開的結(jié)果,對(duì)服從者來說,相當(dāng)于一次“政治啟蒙”,其結(jié)果顯然對(duì)服從者更為有利。支配者當(dāng)然最不愿意看到這種既有損自己形象又為自己維持權(quán)力增加難度的結(jié)果,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滿口仁義道德,并像腓特烈大帝的《反馬基雅維利》那樣,激烈批判和反對(duì)馬基雅維利,“如果馬基雅維利真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要寫的就不是《君主論》,而是一本令人感動(dòng)和充滿規(guī)誡意味的書了”(14)參閱維托里奧·赫斯勒:《道德與政治:二十一世紀(jì)的政治倫理基礎(chǔ)》第二卷,鄭琪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1年,第288-290頁。。簡(jiǎn)言之,公開的馬基雅維利學(xué)說,其實(shí)是一個(gè)令支配者頭疼的負(fù)資產(chǎn)。
問題是,馬基雅維利不但說了,而且寫下來了,從其內(nèi)心意愿來說也非常渴望將其政治理論公開化。沙爾夫斯坦曾去探究人類歷史上的權(quán)謀之士們?yōu)槭裁丛敢夤_主張政治詐騙的問題。他設(shè)問:“盡管與自身利益相悖,為何一些權(quán)謀之士仍然愿意公開主張政治詐騙?”他認(rèn)為,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有些權(quán)謀之士并沒有意識(shí)到自己的理論會(huì)在日后出版”;另外一種情況是他們敢于說真話,骨子里存在一種基于真理或真相的自負(fù)。顯然,對(duì)比兩種情況,他更傾向于討論后一種情況,因?yàn)槟軌蛴懻摰?基本都是公開并流傳于世的。于是他推測(cè):“我覺得(但我并不肯定),所有這些權(quán)謀之士生前都希望自己的著作得以出版,盡管他們考慮過自己服務(wù)的對(duì)象是潛在的敵人;或者說他們至少希望當(dāng)自己不再是政壇上的演員或顧問時(shí),能夠?qū)⒆约旱闹鞴谑馈N抑赃@么說,是因?yàn)樗麄兠總€(gè)人都對(duì)自己在政治程序中覺察到的真理深感自豪,希望這種自豪感通過得到廣大讀者的認(rèn)同(作者想象他們會(huì)產(chǎn)生共鳴)獲得承認(rèn)。”(15)本-艾米·沙爾夫斯坦:《非道德的政治:永不過時(sh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韻竹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第256-259頁。因此,馬基雅維利式的權(quán)謀之士愿意公開自己的觀點(diǎn),根本原因在于他足夠自信,深信自己發(fā)現(xiàn)了人類政治生活的真相。他們既希望現(xiàn)實(shí)的支配者能夠懂得政治真相并做出正確的應(yīng)對(duì),同時(shí)也希望后世的支配者能夠按照他們的眼光去看待政治生活,去從事政治活動(dòng)。作為思想家,他們內(nèi)心都有一個(gè)真實(shí)的意圖,希望他們所諫言的支配者按照他們揭示的真相去從政;作為政治家,他們希望獲得支配者的重用,能與支配者一起積極參與政治事務(wù)并取得成功。
當(dāng)然,還有一個(gè)重要理由就是馬基雅維利及馬基雅維利式的權(quán)謀之士,根本就不認(rèn)為自己道德有缺,相反,他們心中都認(rèn)定自己是一個(gè)懷揣崇高理想與高貴道德的人。簡(jiǎn)單地講,他們會(huì)以一個(gè)更高的道德立場(chǎng)來為其政治可以作惡的觀念辯護(hù)。卡西爾提出一個(gè)非常深刻的問題:“在人類的文明史中還留有一個(gè)極大的難題:一個(gè)像馬基雅維利這樣的人,一個(gè)偉大的高貴的心靈,如何會(huì)變成‘昭著的惡’的鼓吹者呢?而且,如果我們將《君主論》與馬基雅維利的其他著作相比,這個(gè)難題就變得更使人迷惑不解了。”(16)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第176頁。顯然,馬基雅維利會(huì)認(rèn)為自己追求的價(jià)值是正當(dāng)而高尚的。事實(shí)上,西方學(xué)者為馬基雅維利辯護(hù)時(shí)常常把《君主論》與《李維史論》結(jié)合起來,并將其塑造成一個(gè)共和主義者,甚至是一個(gè)憲政論者(17)這方面的著作很多,代表性的著作有昆廷·斯金納:《馬基雅維里》,李永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J.G.A.波考克:《馬基亞維里時(shí)刻》,馮克利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菲利普·博比特:《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楊立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即便如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依然涉及一個(gè)根本的倫理難題:當(dāng)動(dòng)機(jī)與目標(biāo)符合某種道德原則時(shí),過程與手段可以不必受其他道德原則束縛嗎?這恐怕并不僅僅是依據(jù)一種道德原則(如公共美德)來否定另外一種道德原則(如個(gè)人美德)的問題,道德原則的相對(duì)性可以解釋部分問題,但不是全部。若按照政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原則來說,回答則是肯定的。沙爾夫斯坦甚至認(rèn)為:“馬基雅維利式的行為并不是人類的一個(gè)問題,而是人類的一種特征。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詐騙并不是一個(gè)可以先在理論上揭示,然后解決,最后通過立法或教育使之絕跡的問題。”(18)本-艾米·沙爾夫斯坦:《非道德的政治:永不過時(sh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第239頁。這是人類政治的特征,而非一個(gè)有待于解決的“問題”。換言之,馬基雅維利困境,揭示的其實(shí)是一個(gè)人類政治本質(zhì)的問題。如果沒有了謊言、欺騙及各種陰謀權(quán)術(shù),就意味著人類政治之消失。
綜上所述,馬基雅維利政治理論實(shí)際面臨著雙重困境:其一,認(rèn)定政治生活必然存在非道德的手段將面臨倫理困境,這是大多數(shù)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者看到并極力批判的;其二,馬基雅維利及馬基雅維利式的思想家面臨著政治家越是認(rèn)同他們的理論就越是要努力與他們拉開距離的困境。馬基雅維利式的思想家們要么堅(jiān)持自己對(duì)政治真相的把握甘愿承擔(dān)來自社會(huì)各方面的道德責(zé)難,要么努力證明自己的理論在動(dòng)機(jī)與目標(biāo)層面具有強(qiáng)烈的道德屬性從而自證清白。但這終究無法改變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除了特別真誠到說大實(shí)話或者自負(fù)到不顧及道德輿論影響的政治家會(huì)認(rèn)同馬基雅維利式的思想家外,絕大多數(shù)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不會(huì)輕易公開贊同自己的統(tǒng)治不受道德原則的束縛,盡管他們每天都在參與著“潛隱劇本”的幕后排練。馬基雅維利想做政治舞臺(tái)劇的“導(dǎo)演”,“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都為君主準(zhǔn)備好了,但這給他帶來的并非思想家的榮光,而是“邪惡導(dǎo)師”這樣的罵名。這完全可以解釋馬基雅維利的著作自出版之后,為何在西方歷史上持續(xù)不斷地承受著無盡的批判。越罵馬基雅維利,就越可能證明馬基雅維利的學(xué)說觸及了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否則,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何必那么在意他呢?“馬基雅維利困境”實(shí)質(zhì)就是政治心理學(xué)視域中政治與道德的兩難困境。
二、法家話語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
從政治與道德的關(guān)系看,馬基雅維利困境也是法家困境。真正謀劃政治舞臺(tái)劇的“導(dǎo)演”,不僅僅是馬基雅維利。遠(yuǎn)比馬基雅維利早一千多年的先秦法家,其實(shí)已經(jīng)把很多本來屬于“潛隱劇本”的內(nèi)容公開化了,把一部本來應(yīng)該在后臺(tái)悄悄進(jìn)行的舞臺(tái)劇導(dǎo)演到了臺(tái)上。卡西爾可能沒有讀過中國先秦時(shí)期的《商君書》《韓非子》,要不然他不會(huì)那么態(tài)度堅(jiān)定地說馬基雅維利之前沒有任何政治著作教誨支配者處理政治事務(wù)時(shí)不必顧及道德原則的束縛。沙爾夫斯坦比卡西爾多了一層比較政治學(xué)的視野,他認(rèn)為,中國的商鞅、韓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與印度的考底利耶,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圭恰迪尼等人,都是所謂“馬基雅維利式”的思想家,他們的共同點(diǎn)在于他們的理論都體現(xiàn)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特征。所謂“馬基雅維利主義指的是在政治活動(dòng)中摒棄道德的羈絆。換言之,就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達(dá)到政治目的而施以任何形式的騙術(shù)和手段”(19)本-艾米·沙爾夫斯坦:《非道德的政治:永不過時(sh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第12頁。。這就意味著,先秦法家同樣會(huì)遭遇馬基雅維利所面臨的公開揭示政治生活不必顧及道德原則的第一層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第二層困境。
如前所述,先秦法家基本都是雙重身份,他們既是政治家又是與政治實(shí)踐關(guān)系密切的思想家。法家的本意是教誨君主如何治國、如何應(yīng)對(duì)政治現(xiàn)實(shí)問題,這其中當(dāng)然也涉及如何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這一核心政治問題。作為政治家,他們對(duì)政治真相有著非同尋常的深刻把握;作為思想家,他們把政治真相的揭示與具體的應(yīng)對(duì)之策非常詳實(shí)地記錄下來。他們的思想文本,有“公開劇本”,也有“潛隱劇本”。由于他們講了許多以君主為特定閱讀對(duì)象的“潛隱劇本”,這與其他諸子如老莊、孔孟荀、墨子等,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思想面貌,在先秦時(shí)期百家爭(zhēng)鳴語境中可謂獨(dú)樹一幟。他們的“公開劇本”實(shí)與其他諸子共享著相同或相似的價(jià)值,但是他們的“潛隱劇本”公開之后太過刺眼,以至于后世論及他們的思想時(shí),大多不承認(rèn)或刻意忽視他們的“公開劇本”而專注于批判其“潛隱劇本”(20)比如郭沫若就認(rèn)為韓非子有關(guān)理想社會(huì)的描繪是虛假的:“韓非是文章的妙手,他的權(quán)謀的深刻,有時(shí)也盡有可能用美妙的畫皮來掩飾。像《奸劫弒臣》里下列的一段話便是很可能使人迷戀的。……這儼然是理想的救世主的態(tài)度。但從全盤的思想體系來考察,這不外是偶一使用的幌子而已。”見郭沫若:《十批判書》,《中國古代史研究(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74頁。。可以說,自漢代以降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法家批判史,各種政治學(xué)說基本都以法家思想為潛在批判對(duì)象。
法家政治思維的“公開劇本”依托先秦時(shí)期的共同價(jià)值,體現(xiàn)為一種“治”的秩序與“利民”的理想。法家深入論證了君主制有助于恢復(fù)春秋以來的混亂秩序,《商君書·開塞》說:“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21)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二《開塞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8頁。《韓非子·難一》也說:“國無君不可以為治。”(22)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五《難一第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58頁。法家強(qiáng)調(diào)君主制之下的君尊臣卑倫理,與儒家的君臣禮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司馬談才說:“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23)《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91頁。法家強(qiáng)調(diào)加強(qiáng)君主權(quán)力以重建社會(huì)秩序,根本目的不是君主個(gè)人的私利,而是結(jié)束戰(zhàn)亂以讓天下百姓安居樂業(yè)。因此,君主制的政治正當(dāng)性建立在天下人的公共利益這一倫理基礎(chǔ)之上。《商君書·修權(quán)》說:“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2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修權(quán)第十四》,第84頁。《慎子·威德》亦云:“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25)慎到著,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6頁。《韓非子·奸劫弒臣》說:“圣人者,審于是非之實(shí),察于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yán)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qiáng)不凌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zhǎng),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此亦功之厚也!”(26)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四《奸劫弒臣第十四》,第102頁。這些觀點(diǎn)以及《韓非子·大體》“萬民不失命于寇戎”(27)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八《大體第二十九》,第210頁。的理想表達(dá),都彰顯了韓非子思想深處的利民傾向,也即“立君為民”“天下為公”的政治原則(28)宋洪兵:《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138-139頁。。法家學(xué)說的政治正當(dāng)性體現(xiàn)為順應(yīng)時(shí)代特征有效解決關(guān)涉民生的重大問題并最終使百姓獲利,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天下百姓心悅誠服的擁護(hù)和支持(29)宋洪兵:《先秦法家政治正當(dāng)性的理論建構(gòu)》,《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6期,第68-85頁。。
法家獨(dú)特的“公開劇本”體現(xiàn)為他們主張以法治國,上下尊卑貴賤一斷于法,提倡一種公正價(jià)值,以滿足天下人基本的正義訴求。法家是在中央集權(quán)的君主制之下承認(rèn)等級(jí)尊卑制度,但其“公開劇本”卻是各社會(huì)等級(jí)在處理利益糾紛和矛盾沖突時(shí),都應(yīng)該采用一視同仁的普遍規(guī)則,也即法家主張的“法治”。法家之法,具有雙重內(nèi)涵,一層內(nèi)涵是政策性的法,順應(yīng)時(shí)代的客觀情況變化而變化,服務(wù)于支配者對(duì)當(dāng)前最為急迫事務(wù)的準(zhǔn)確判斷,如“利出一孔”的農(nóng)戰(zhàn)政策(30)參閱黎翔鳳撰,梁運(yùn)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國蓄第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59-1281頁;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弱民第二十》,第121-127頁;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2-456頁。;另一層內(nèi)涵則是帶有普適性的法,要求必須根植于人類最為基本的、最為樸素的正義感情,建設(shè)一個(gè)“無怨”的和諧社會(huì)(31)宋洪兵:《法家正義論初探》,《管子學(xué)刊》2022年第1期,第25-41頁。。無論是政策性的法還是普適性的法,都必須公正落實(shí),不得出現(xiàn)有法不依的例外情況。政策性的法雖然具有隨時(shí)而變、隨勢(shì)而變的特征,但其具體執(zhí)行過程,也必須考慮天下百姓的承受限度,不得公然違背人類的正義情感而搞得民不聊生,而其最終指向,也必須蘊(yùn)涵公共價(jià)值。“任何法和法律都無法回避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它們所表現(xiàn)的統(tǒng)治意志在客觀上必然有一個(gè)限度,這個(gè)限度就是被治者所能忍受的程度,也就是說,它必須取得被治者的事實(shí)上的認(rèn)可,才有可能存在,在這個(gè)意義上,法仍然是一種約定,只不過這個(gè)約定并非人們主觀意識(shí)內(nèi)的事情,也就是說,它不是契約論者所謂的約定,我們姑且稱之為無意識(shí)的約定,或必然的約定。”(32)蔣重躍:《論法家思想中的變法與定法》,《中國哲學(xué)史》2002年第1期,第60-66頁。韓非子之所以特別強(qiáng)調(diào)“明主立可為之賞,設(shè)可避之罰”(33)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八《用人第二十七》,第205頁。,原因亦正在于此。法家以法治國的觀念及其對(duì)公正價(jià)值的提倡、對(duì)正義情感的維護(hù),都是可以公開講給天下百姓聽的。盡管他們的主張與儒家、道家、墨家的政治觀念存在很大不同,但他們終究在人類的多元價(jià)值中尋求到了屬于自己的基本立足點(diǎn)。
法家獨(dú)特的“公開劇本”還有變法主張以及富國強(qiáng)兵觀念,由此凸顯基于整體視角的群體生存與發(fā)展的價(jià)值訴求。法家不愿意墨守成規(guī),而是主張要因時(shí)變法,以此應(yīng)對(duì)戰(zhàn)國時(shí)期因列國爭(zhēng)戰(zhàn)而日益加劇的生存危機(jī)。《商君書·更法》說得非常清楚:“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qiáng)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3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更法第一》,第3頁。法與禮,本質(zhì)上皆為人類治理國家的手段和工具,為了應(yīng)對(duì)國家的生存危機(jī),圣人認(rèn)為必須根據(jù)客觀事實(shí)調(diào)整策略變法圖強(qiáng),而不必拘泥于傳統(tǒng)觀念與制度的束縛。《韓非子·五蠹》也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35)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5頁。。時(shí)代在變化,客觀情況也在變化,不能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一切從現(xiàn)實(shí)的客觀情況出發(fā),解決最為急迫的生存問題,是法家變法理論的基本邏輯。
法家獨(dú)特的“公開劇本”還體現(xiàn)在他們依托舊價(jià)值系統(tǒng),重新定義并賦予其新的價(jià)值內(nèi)涵。典型者如《韓非子·六反》所列的世俗普遍贊譽(yù)的六種“奸偽無益之民”,而真正為國家富強(qiáng)做貢獻(xiàn)的六種“耕戰(zhàn)有益之民”(36)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六反第四十六》,第416頁。,卻遭到世俗價(jià)值的嘲諷和詆毀。這樣的社會(huì)氛圍勢(shì)必造成“所養(yǎng)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yǎng)”(37)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顯學(xué)第五十》,第459頁。的局面。因此,法家欲根據(jù)國家的生存需求重新定義社會(huì)價(jià)值,改變世俗價(jià)值與國家公共利益相背離的現(xiàn)狀,移風(fēng)易俗,將社會(huì)觀念與國家利益結(jié)合起來,“譽(yù)輔其賞,毀隨其罰”(38)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8頁。。國家生存與發(fā)展需要農(nóng)民與戰(zhàn)士,那就應(yīng)該給他們應(yīng)有的榮譽(yù)和利益,徹底改變舊有的不利于鼓勵(lì)農(nóng)戰(zhàn)階層的價(jià)值觀念。具體來說,就是改革春秋以來貴族體制之下的各種價(jià)值觀念,使之符合現(xiàn)實(shí)的農(nóng)戰(zhàn)需求。《商君書·靳令》以及《商君書·弱民》對(duì)“六虱”的批判,即是在改造舊價(jià)值系統(tǒng)的前提之下進(jìn)行的。蔣重躍發(fā)現(xiàn),法家改革舊有價(jià)值系統(tǒng)的方式,往往是在舊字中注入新的含義,這樣就出現(xiàn)了同一個(gè)漢字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不同內(nèi)涵的現(xiàn)象,如“忠”“賢”與“仁”,韓非子的理解截然不同于儒家的理解:
“忠”字的“以愛為我”、“賢”字的“名譽(yù)”和“所愛”“所賢”、“仁”字的“孝悌慈惠”等,都散發(fā)著濃郁的脈脈溫情,究其實(shí)質(zhì),是把政治關(guān)系建立在維系情感的傳統(tǒng)道德之上,更多地表現(xiàn)了舊時(shí)代宗法政治的血緣關(guān)系。而“不得不愛我”,“論之于任,試之于事,課之于功”,“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云云,則分別對(duì)應(yīng)于君臣之間的利益交換關(guān)系、因能授官和循名責(zé)實(shí)的官吏選用和考核制度、以地域國家為原則的行政倫理。忠、賢、仁的這些新含義,反映了君主集權(quán)和官僚政治的必然要求,煥發(fā)著新時(shí)代新型國家的法治精神。(39)蔣重躍:《關(guān)于〈韓非子〉中三組概念的矛盾:例說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國學(xué)學(xué)刊》2019年第1期,第90-103、143頁。
可見,法家不是不講價(jià)值,只不過他們講的價(jià)值不同于舊有的價(jià)值系統(tǒng),而具有新的時(shí)代內(nèi)涵。他們完全可以公開對(duì)全天下人講這些道理,這些新的價(jià)值本身具有倫理正當(dāng)性,亦無損于法家人物的道德形象。
因此,法家的“公開劇本”既有與先秦諸子共享的“立君為民”“天下為公”的價(jià)值觀念,又有一套應(yīng)對(duì)現(xiàn)實(shí)需求的新價(jià)值系統(tǒng),這套價(jià)值系統(tǒng)與舊有的價(jià)值系統(tǒng)之間,存在著強(qiáng)烈的對(duì)抗色彩,凸顯體現(xiàn)為公共價(jià)值與私人價(jià)值之間的沖突。法家這套新價(jià)值系統(tǒng),除了受到擁護(hù)舊有價(jià)值人士的批駁與責(zé)難外,還需要面臨一個(gè)天下百姓是否接受的考驗(yàn)。簡(jiǎn)言之,法家的“公開劇本”存在價(jià)值合理性,但他們面臨的困難在于如何讓社會(huì)認(rèn)同他們的價(jià)值并將之社會(huì)化的問題,涉及多種價(jià)值如何進(jìn)行競(jìng)爭(zhēng)的問題。如果法家只講上述“公開劇本”,他們即使不被其他學(xué)者認(rèn)可,不被天下百姓認(rèn)可,也不會(huì)遭受太大的道德批判。但是,法家學(xué)說遠(yuǎn)不止這些,他們深入政治內(nèi)核之后,根據(jù)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特征,提出了一個(gè)讓世人難以接受的“潛隱劇本”。這個(gè)“潛隱劇本”與其說是法家人物道德敗壞的產(chǎn)物,毋寧說是人類政治本質(zhì)的必然呈現(xiàn)。法家面臨的最大道德危機(jī)在于,他們將政治實(shí)踐中的“潛隱劇本”詳細(xì)記錄了下來。
法家的“潛隱劇本”,顧名思義,就是專門為君主如何治國出謀劃策而不適合公開講的秘密話語,其內(nèi)容具有秘密性,其言說對(duì)象也具有專屬性,屬于高度敏感的政治秘術(shù)。具體而言,這些政治秘術(shù)包含三個(gè)層面的內(nèi)容:
其一,法家對(duì)民的態(tài)度,屬于“潛隱劇本”。法家基于精英政治思維,認(rèn)為君主的政治決策與權(quán)力運(yùn)用具有高度專業(yè)性,應(yīng)該獨(dú)立于普通百姓的認(rèn)知與感受。政治家考慮整體利益、公共利益和長(zhǎng)遠(yuǎn)利益,百姓考慮的都是自己切身的小范圍的私利,他們對(duì)公共利益與長(zhǎng)遠(yuǎn)利益并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思考。因此,君主治國不必考慮百姓的感受,即使他們反對(duì),也要堅(jiān)決執(zhí)行。戰(zhàn)國時(shí)期,儒家始終高唱一個(gè)“得民心”并尊重民意的“公開劇本”,但是法家卻反對(duì)政治決策迎合“民心”。有學(xué)者發(fā)現(xiàn),儒家認(rèn)定“君主對(duì)權(quán)力的運(yùn)用必須是正當(dāng)?shù)?必須合乎公眾的意愿,服務(wù)于公眾的利益”,“回答政治權(quán)力的運(yùn)用與民意、民心的關(guān)系,儒家有誰提過類似于馬基雅維利對(duì)君主權(quán)力的那種辯護(hù)?法家個(gè)別人物批評(píng)儒家要求支配者合乎民心,這使他同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40)王中江:《權(quán)力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早期儒家“民意論”的形態(tài)和構(gòu)成》,《學(xué)術(shù)月刊》2021年第3期,第5-16頁。這個(gè)“法家個(gè)別人物”,應(yīng)該是指韓非子,也可能指商鞅。《商君書·更法》直截了當(dāng)?shù)貙?duì)秦孝公說出了一個(gè)“潛隱劇本”,即“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不必與老百姓去商量如何做事情,他們只是對(duì)事情的結(jié)果感興趣;所以政治家只需要從政治的角度去考慮長(zhǎng)遠(yuǎn)利益與公共利益,不必理會(huì)百姓的感受:“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fù)于世;有獨(dú)知之慮者,必見訾于民。”(41)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更法第一》,第2頁。后來,韓非子還真誠地將此“潛隱劇本”進(jìn)一步公開化:“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42)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顯學(xué)第五十》,第463頁。公開貶低百姓的能力,公開反對(duì)得民之心,這樣赤裸裸的“理論真誠”一旦公開,勢(shì)必得罪天下百姓,也會(huì)傷害很多對(duì)政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的感情。
法家基于先秦政治語境,與各家共享著民本立場(chǎng),主張“愛民”,但是,法家強(qiáng)調(diào)的是結(jié)果或效果意義上的“愛民”,在具體過程之中,百姓因欠缺理解政策措施的能力與智慧,事實(shí)上就淪為實(shí)現(xiàn)富國強(qiáng)兵戰(zhàn)略的工具和手段。法家希望百姓都能老實(shí)聽話,積極配合國家政策,為國效力。同時(shí),他們也意識(shí)到,由于人性都趨利避害,都想著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指望百姓心甘情愿為國效力是不太可能的。法家于是告誡君主,治國一定要想辦法讓百姓克服貪生怕死、好逸惡勞的本性去做他們本不樂意做的事情。《商君書·弱民》說得很清楚:“民弱國強(qiáng),民強(qiáng)國弱,故有道之國,務(wù)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qiáng)。”(43)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弱民第二十》,第121-125頁。君主治國應(yīng)該以國家為本位來思考問題,不能總是順應(yīng)百姓的私人感受和私人利益,因?yàn)檫@樣無法凝聚民力來實(shí)現(xiàn)國家利益。君主必然會(huì)采取百姓不喜歡的政策,如農(nóng)戰(zhàn)政策是非常艱苦、非常危險(xiǎn)的事情,百姓不一定喜歡,但是君主必須獎(jiǎng)勵(lì)耕戰(zhàn),才能真正富國強(qiáng)兵。富國強(qiáng)兵才能維護(hù)群體生存與發(fā)展,群體利益得到保障,才能保障百姓利益,“愛民”才有根基。《韓非子·六反》表達(dá)了同樣的意思:“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故不養(yǎng)恩愛之心而增威嚴(yán)之勢(shì)。”(44)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六反第四十六》,第418頁。《管子·牧民》曾主張“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45)黎翔鳳撰,梁運(yùn)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牧民第一》,第13頁。,但即便如此,《管子·法法》也還是指出政治之于百姓的真相在于如何利用百姓為國家效力:“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46)黎翔鳳撰,梁運(yùn)華整理:《管子校注》卷六《法法第十六》,第302頁。關(guān)于這點(diǎn),梁?jiǎn)⒊陉U述《管子》存在將人民視為統(tǒng)治工具的觀念時(shí)有一個(gè)很好的概括:“夫《管子》全書之宗旨,在順民心,為民興利除害。……非以民為芻狗也,亦非與平昔所持之宗旨相矛盾也,蓋為國家之生存發(fā)展起見,往往不得不犧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而其犧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實(shí)亦間接以增進(jìn)人民全體之利益而已。治國家者,茍不能使人民忻然愿犧牲其一部分之利益而無所怨,則其去致治之道遠(yuǎn)矣。”(47)梁?jiǎn)⒊?《中國六大政治家》,第33頁。法家此等秘密的用民之術(shù),說得非常露骨,倘若公開,勢(shì)必遭到百姓的極度反感。
其二,法家尤其是韓非子對(duì)群臣百官的態(tài)度,屬于“潛隱劇本”。法家希望群臣百官都能恪盡職守,各盡其責(zé),公正廉潔,但是,防范群臣百官以權(quán)謀私又是一個(gè)不得不認(rèn)真面對(duì)的事情,甚至在韓非子那里,還面臨著一個(gè)如何化解以當(dāng)權(quán)重臣為核心的小利益集團(tuán)時(shí)刻想著侵奪君權(quán)的政治危機(jī)的問題。先秦法家,從《商君書》《管子》到《韓非子》,吏治觀念經(jīng)歷了一個(gè)明顯的變化:由《商君書》《管子》重點(diǎn)論述官吏的職能及素質(zhì)要求,到極為關(guān)注君臣權(quán)力斗爭(zhēng),以及如何防范篡弒之臣的轉(zhuǎn)變。法家的吏治觀念與儒家吏治觀念之間的最大差別,在于法家更強(qiáng)調(diào)能力及監(jiān)督、考核的重要性,而不再像儒家那樣注重個(gè)人的德性修養(yǎng)。這本屬價(jià)值層面的競(jìng)爭(zhēng),可以公開闡述,法家的官僚制思想屬于政治領(lǐng)域的“公開劇本”。在此,需要對(duì)《商君書》的“任奸治善”問題做一簡(jiǎn)要辨析。《商君書·去強(qiáng)》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qiáng)。”(48)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去強(qiáng)第四》,第30頁。《商君書·說民》也稱“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qiáng)”(49)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二《說民第五》,第36頁。。此處所謂“善民”“奸民”并非提倡什么“流氓政治”,而是針對(duì)儒家意義上的所謂“善民”“奸民”在《商君書》那里進(jìn)行了新的價(jià)值定義,愿意犧牲個(gè)人利益及血緣親情的人會(huì)被儒家認(rèn)定為“奸民”,相反,則是“良民”(50)葉自成:《治道:商鞅治秦與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緣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245-248頁。。《商君書》在此則反其道而用之,與之展開價(jià)值競(jìng)爭(zhēng),通觀《商君書》全書,其對(duì)“奸”與“奸民”的批判和反對(duì)是非常明確的。因此,《商君書》的此處表述,不應(yīng)該被理解為一種“流氓政治”的秘密治術(shù),當(dāng)今學(xué)者對(duì)此進(jìn)行批判,實(shí)因沒有理解《商君書》的語境和整體思想。簡(jiǎn)言之,《管》《商》涉及的吏治思想,雖與儒家吏治觀念不同而存在招致儒家批判的可能,但均在價(jià)值競(jìng)爭(zhēng)與觀念競(jìng)爭(zhēng)之列,視為“公開話語”并不會(huì)帶來太大的輿論指責(zé)。
然而,情況到了韓非子那里,法家的吏治觀念就更多呈現(xiàn)出秘密色彩。韓非子認(rèn)為,君臣之間不存在親情那樣的利他因素,本質(zhì)上是一種基于利益交換的買賣關(guān)系:君賣爵祿,臣賣智力。在這種利益交換過程中,各自都試圖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博弈出來的結(jié)果就是不再依靠任何情感關(guān)系來維護(hù),所謂“君不仁,臣不忠”,而是君追求國家治理的“大利”,臣實(shí)現(xiàn)富貴與爵祿的“大利”(51)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六反第四十六》,第417頁。,實(shí)現(xiàn)君臣關(guān)系和諧的關(guān)鍵在于君主牢牢掌控權(quán)力和公正的法治。然而,從內(nèi)心來說,臣之于君,時(shí)刻存在奪權(quán)的野心,君臣上下一日百戰(zhàn),君主稍微懈怠,手握大權(quán)的重臣就會(huì)趁虛而入取而代之。君主此時(shí)就要用法術(shù)勢(shì)來駕馭群臣百官,以免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受到威脅。“所謂‘君人南面之術(shù)’的另一種秘訣,也就是要把一切的人看成壞蛋。所以一切的人都不可信,‘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備內(nèi)》)。臣下無骨肉之親固不足信,就是有骨肉之親的自己的妻室、兒女、父老、兄弟,也同樣不可信。……韓非子的本領(lǐng)本來就在這些地方見長(zhǎng),他能夠以極普通的常識(shí)為根據(jù),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52)郭沫若:《十批判書》,《中國古代史研究(外二種)》,第762頁。。摒除郭沫若對(duì)韓非子的情緒化因素,他對(duì)韓非子君臣關(guān)系的闡述是有說服力的。
韓非子將古代政治領(lǐng)域權(quán)力斗爭(zhēng)的殘酷性充分呈現(xiàn)出來。“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奸也。”對(duì)于那些活著總是找麻煩、礙手礙腳的人,如果直接把他們殺死又有傷君主名聲,那么這時(shí)候就可以在他們吃的喝的東西里放毒藥,神不知鬼不覺地解除絆腳石。要不然,就想辦法推給他的仇人,借刀殺人。總之,用陰謀詭計(jì)的辦法來“除陰奸”。“曰質(zhì)、曰鎮(zhèn)、曰固。親戚妻子,質(zhì)也。爵祿厚而必,鎮(zhèn)也。參伍貴帑,固也。”(53)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八經(jīng)第四十八》,第434頁。對(duì)于手下那些大臣,要把他們的親戚妻子作為人質(zhì),要用豐厚的爵祿來籠絡(luò),要用嚴(yán)格的監(jiān)督考核來防范。為了防止群臣結(jié)黨營私,就要想辦法讓他們互相爭(zhēng)斗,然后君主以超然的地位輕松掌握各方,所謂“作斗以散朋黨”(54)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八經(jīng)第四十八》,第437頁。。韓非子還苦心孤詣地為君主剖析“六微”(六種君臣關(guān)系的實(shí)質(zhì)),以及如何有效應(yīng)對(duì)的“七術(shù)”,其中不乏“倒言反事”“挾智而問”等不能公開的統(tǒng)治秘術(shù)(55)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九《內(nèi)儲(chǔ)說上第三十》,第211頁。。
為了幫助君主鞏固自己的權(quán)力,韓非子還從老子那里得到啟發(fā),教誨君主如何掌握“自神之術(shù)”。所謂“自神之術(shù)”,就是君主應(yīng)該像無所不在而又不可見聞的“道”一樣,努力營造一種無所不能、神秘莫測(cè)的形象,讓群臣百官無法猜透君主內(nèi)心的真實(shí)想法,從而產(chǎn)生震懾作用,覬覦君主權(quán)勢(shì)的權(quán)臣不得不收斂自己的權(quán)力野心:“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56)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八經(jīng)第四十八》,第431頁。此處的“天”與“鬼”皆體現(xiàn)了神秘莫測(cè)的意味。韓非子深知,世襲制之下的君主,絕大多數(shù)都是“中主”和“庸主”,能力和德性都很一般(57)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七《難勢(shì)第四十》,第389-393頁。。這樣的君主如何在充滿激烈權(quán)力斗爭(zhēng)的政治領(lǐng)域生存下來?韓非子對(duì)君主講出了一番“私房話”:故弄玄虛,努力藏拙,采取超然立場(chǎng),避免在群臣面前出現(xiàn)君主無能的場(chǎng)景。《韓非子·揚(yáng)權(quán)》教誨君主如何聽取臣下的言論:“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gòu)。”(58)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二《揚(yáng)權(quán)第八》,第47頁。意思是說,當(dāng)群臣發(fā)表意見的時(shí)候,君主就像喝醉酒了狀態(tài),群臣七嘴八舌說話,君主始終不先開口,一副稀里糊涂、昏昏欲睡的樣子。此時(shí),群臣就無法從君主的表情來判斷君主的好惡,也無法借此來討好君主,只好硬著頭皮把自己內(nèi)心真實(shí)的想法說出來,君主從而獲知群臣的各種意見和立場(chǎng)。是非對(duì)錯(cuò)的觀念,都集中在君主那里,但是君主始終保持超然狀態(tài),不輕易下判斷,以免出錯(cuò)影響君主的威信。因此,韓非子教誨君主的“自神之術(shù)”還有明顯的藏拙意圖。君主藏拙的法寶,就是虛靜無為,像道一樣神秘莫測(cè)。如此,就會(huì)產(chǎn)生一種“天下英雄皆入彀中”的政治效果:集中群臣智慧以為君主的智慧,集中群臣賢能以為君主的賢能,君主超然于具體政治事務(wù)的是非功過,讓自己最終成為是非功過的判斷者而非責(zé)任者。群臣若有功,最終表明君主任人賢能而有功;若有過,則可歸咎于臣下的能力。長(zhǎng)此以往,作為“中主”“庸主”的君主就能指揮和駕馭一幫能力和智慧超群的臣下來成就和維持他的政治地位,此即《韓非子·主道》所說的“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jīng)也”(59)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主道第五》,第27-28頁。。
當(dāng)韓非子撕毀君臣之間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而將君臣關(guān)系還原為圍繞利益和權(quán)力的激烈博弈時(shí),當(dāng)他告誡君主所有的親人包括妻兒父兄都需要防范時(shí),當(dāng)他提醒君主以各種陰險(xiǎn)惡毒的陰謀權(quán)術(shù)來對(duì)付群臣百官時(shí),當(dāng)他斷定君主世襲制下的君主是中主、庸主需要“自神之術(shù)”來藏拙時(shí),韓非子幾乎將當(dāng)時(shí)君主政治的所有秘密都以“教誨”的形式呈現(xiàn)了出來。問題在于,韓非子對(duì)君主如此真切的秘密教誨,一旦公開,君主作何感想?君主會(huì)不會(huì)有被當(dāng)面“揭露”與羞辱的感覺?群臣百官作何感想?他們會(huì)不會(huì)有怒不可遏、切齒痛恨的感覺?君主的妻兒父兄又作何感想?他們會(huì)不會(huì)有美好親情被褻瀆、覬覦權(quán)力的玲瓏心思被拆穿的惱羞成怒?總之,不公開時(shí),只有君主是讀者,他會(huì)看得心驚肉跳,既佩服韓非子入木三分,又有自己權(quán)力博弈底牌被看穿的隱憂,若機(jī)緣巧合,他或許會(huì)重用韓非子這樣的謀臣,并倚為心腹;然后,一旦公開,眾人皆曉時(shí),毫無疑問,韓非子會(huì)成為眾矢之的,就連君主也會(huì)毫不猶豫地拋棄他、批判他。
其三,法家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及士人的態(tài)度,屬于“潛隱劇本”。法家之于傳統(tǒng)文化具有強(qiáng)烈的批判和否定意識(shí),他們認(rèn)為,傳統(tǒng)文化熏陶出來的百姓與當(dāng)下富國強(qiáng)兵政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商鞅變法,將儒家信奉的經(jīng)典及其道德價(jià)值,貶斥為“六虱”,“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zhàn)”。“六虱成群,則民不用”(60)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靳令第十三》,第80-81頁。,“六虱成俗,兵必大敗”(61)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弱民第二十》,第125頁。。《商君書》認(rèn)為,君主治國若以“六虱”為標(biāo)準(zhǔn),耕戰(zhàn)政策就無法得到落實(shí),必將導(dǎo)致國家混亂和貧弱。《商君書》試圖以嚴(yán)刑峻法切斷舊有價(jià)值觀念對(duì)百姓的影響,使“褊急之民”“很剛之民”“怠惰之民”“費(fèi)資之民”“巧諛惡心之民”都能成為耕戰(zhàn)之民(62)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墾令第二》,第13頁。。韓非子更明顯,他將無益于國家富強(qiáng)的從業(yè)者,視為五種蠹蟲(學(xué)者、言古者、其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認(rèn)為都應(yīng)該受到嚴(yán)格的限制與嚴(yán)厲的打壓,明主之國,不需要書簡(jiǎn)之文與先王之語,一切都以法為教、以吏為師(63)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2-456頁。。豫讓感念于“士為知己者死”而為智伯復(fù)仇,最終獻(xiàn)出生命,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他們都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不貪名利、不畏懲罰甚至不怕死,這樣的一類人,韓非子認(rèn)為他們對(duì)國家的富強(qiáng)沒有做出什么實(shí)質(zhì)貢獻(xiàn),是無益之臣。他盛贊伊尹、管仲、商鞅才是真正的“忠臣”,他的忠臣標(biāo)準(zhǔn)是:“外無敵國之患,內(nèi)無亂臣之憂,長(zhǎng)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謂忠臣也。”(64)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四《奸劫弒臣第十四》,第106頁。總之,商韓對(duì)于傳統(tǒng)士人的個(gè)人道德操守觀念,以是否有功于國家的功用主義思想來加以批判,具有強(qiáng)烈的顛覆性。如果沒有更好、更高明的一套意識(shí)形態(tài)來加以替換而貿(mào)然否定之,極易招致社會(huì)輿論的強(qiáng)烈反彈。不僅如此,韓非子進(jìn)一步為君主導(dǎo)演了一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潛隱劇本”:將那些具有節(jié)操的不為法家政策服務(wù)的士人除掉。“賞之譽(yù)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65)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三《外儲(chǔ)說右上第三十四》,第311頁。韓非子認(rèn)為,君主治國時(shí),對(duì)于那些不為名利所動(dòng)同時(shí)又不怕死的人,應(yīng)該將他們除掉。這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可以公開討論的范疇,只能是非常秘密的話題。一旦公開,勢(shì)必引起軒然大波。
法家對(duì)民的態(tài)度、對(duì)群臣百官的態(tài)度以及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及士人的態(tài)度,大多數(shù)都應(yīng)該屬于“潛隱劇本”,應(yīng)該是法家告誡君主如何治國并應(yīng)對(duì)殘酷的權(quán)力斗爭(zhēng)的,基本上都涉及政治的本質(zhì)與真相,具有鮮明的非道德屬性。法家人物,尤其是商韓,講了很多上不得臺(tái)面的政治實(shí)情,他們講的本來是不適合公開的。盡管他們說的是真話、實(shí)話,但是在情感上讓純真的有道德感的人難以接受。他們希望通過法家學(xué)說直接影響君主、影響政治實(shí)踐,他們對(duì)君主講的很多“政治智慧”其實(shí)都應(yīng)該屬于政治領(lǐng)域不宜公開的“潛隱劇本”,只適合私下里講并在政治后臺(tái)運(yùn)作的。
問題在于,法家是否覺得他們?yōu)榫髟O(shè)計(jì)的“潛隱劇本”不適合公開呢?這需要有所區(qū)分。首先,法家“潛隱劇本”的閱讀對(duì)象具有專屬性,是那些能夠重視他們政策諫言并可能因此重用他們的特定君主。如此,他們就可以暢所欲言而無絲毫顧及。其次,他們思想家的身份使他們將言論著之竹帛、傳之后世,在“公開劇本”的價(jià)值框架里并不忌諱公開他們的某些“潛隱劇本”。簡(jiǎn)言之,他們的“潛隱劇本”的初衷并非為公開而寫,就算公開,他們也有一套理論來為自己辯護(hù)。
法家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之間是一個(gè)有機(jī)整體,他們能夠以“公開劇本”的價(jià)值正當(dāng)性來論證“潛隱劇本”的合理性。法家對(duì)于公開他們的某些“潛隱劇本”并不存在道德顧慮,因?yàn)樗麄儾⒉徽J(rèn)為他們的思想存在道德瑕疵。相反,他們始終認(rèn)為自己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情,為了高尚的目的,之前上不得臺(tái)面的只能做不能說的各種手段,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道德層面的高尚特質(zhì),體現(xiàn)為他們認(rèn)定自己在關(guān)懷有利于天下百姓的公共利益和長(zhǎng)遠(yuǎn)利益。法家思想由此體現(xiàn)出了道德感,并最終促使他們將“潛隱劇本”以毫無道德負(fù)疚感的方式與“公開劇本”連為一體。法家的用民之術(shù)、御官之道、反對(duì)“六虱”“五蠹”等,大多都可以納入到總體的“公開劇本”框架之下得到合理說明。
盡管如此,法家思想還是因此而體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非道德屬性,他們已經(jīng)明確地呈現(xiàn)了一種只要目的正當(dāng)就應(yīng)該根據(jù)政治真相去做而不必計(jì)較手段是否合乎道德的政治理念。郭沫若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法家的上述理論特點(diǎn):“殺人都不擇手段,做事也當(dāng)然不擇手段。”(66)郭沫若:《十批判書》,《中國古代史研究(外二種)》,第768頁。法家已經(jīng)意識(shí)到,政治生活充滿了道德與政治的悖論、眼前利益與長(zhǎng)遠(yuǎn)利益的沖突、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以及權(quán)力斗爭(zhēng)的緊迫性與殘酷性,使得政治領(lǐng)域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唯有權(quán)衡利弊之后的最優(yōu)方案。《韓非子·八說》清楚地表達(dá)了這個(gè)意思:“法有立而有難,權(quán)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quán)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67)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八《八說第四十七》,第426-427頁。顯然,法家認(rèn)為,政治領(lǐng)域的最優(yōu)方案,就是以群體的公共利益、長(zhǎng)遠(yuǎn)利益為基本著眼點(diǎn),最終有利于整個(gè)政治共同體的和諧與利益。法家唯才是用的觀念,更強(qiáng)化了法家有關(guān)政治與道德二分的觀念:政治是一個(gè)獨(dú)立于道德的專門領(lǐng)域,不能依靠道德原則來指導(dǎo)政治。法家沒有否定道德本身,他們的政治理想已經(jīng)蘊(yùn)含了道德價(jià)值,但是他們反對(duì)在具體治國過程中受道德原則束縛,而強(qiáng)調(diào)依據(jù)政治自身邏輯來展開。法家政治思維,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政治現(xiàn)實(shí)主義。
法家尤其是韓非子的“潛隱劇本”必然涉及君主如何進(jìn)行政治表演以掩蓋其秘密政治的問題。至少在韓非子那里,他明白政治領(lǐng)域的有些事情需要保密,不能公開。他說:“事以秘成,語以泄敗。”即使不小心說出君主內(nèi)心在意而又希望刻意保密的事情,都是非常危險(xiǎn)的。他舉例說,鄭國大夫關(guān)其思傻乎乎建議鄭武公攻打胡國,而這正是鄭武公一直想做的,但是機(jī)會(huì)還不成熟。鄭武公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shí)意圖,決定犧牲關(guān)其思以麻痹胡君,最終成功把胡給滅了(68)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四《說難第十二》,第87-93頁。。關(guān)其思死了,死在秘密政治的巨大旋渦之中。毫無疑問,人類的政治生活確實(shí)存在著一個(gè)秘密的“潛隱劇本”。“試想一下,人們可能會(huì)問,如果一名領(lǐng)導(dǎo)不加任何掩飾或夸大,將他所知道的事實(shí)赤裸裸地和盤托出,將會(huì)引起什么樣的混亂。”(69)本-艾米·沙爾夫斯坦:《非道德的政治:永不過時(sh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第257頁。韓非子提醒君主如何用群臣妻兒老小作為人質(zhì)來控制他們,如何用暗殺或借刀殺人來解決不斷制造麻煩的士人,教誨君主如何藏拙,如何防范自己的親人奪權(quán)等,這些內(nèi)容只能針對(duì)君主這一特定閱讀對(duì)象并且能“做”不能說,屬于絕對(duì)保密的“潛隱劇本”,必須通過政治表演來加以掩飾。總體來說,法家希望君主通過政治表演來維持法治形象、公正形象、權(quán)威形象以及神秘莫測(cè)的形象,但在實(shí)際政治生活中又必須以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為重心。權(quán)謀政治的領(lǐng)域歸權(quán)謀政治,公正法治的領(lǐng)域歸公正法治(70)宋洪兵:《一種新解讀:論法家學(xué)說的政治視角與法治視角》,《中國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第1期,第67-81頁。。法家認(rèn)為,唯有如此去理解政治并從事政治實(shí)踐,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公開劇本”體現(xiàn)的各種價(jià)值和理想。法家其實(shí)隱含著一層意味:君主最好按照“公開劇本”去說,但必須按照“潛隱劇本”去做。“潛隱劇本”在政治表演中被巧妙地掩蓋起來,從而避免君主陷入道德困境。
然而,韓非子極端的秘密政治,隨著他洋洋灑灑十萬余言的論述公開了。法家的“潛隱劇本”,在價(jià)值競(jìng)爭(zhēng)序列中能自圓其說的以及不能自圓其說的極端政治秘密,都公開了。法家的“潛隱劇本”最終變成“公開劇本”,并不違背他們的意愿,他們有一種理論自信,會(huì)認(rèn)為自己在闡述一種治國理論,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君主作為閱讀對(duì)象。在現(xiàn)存各種文獻(xiàn)記載之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資料來佐證法家著述具有秘密性。《韓非子·五蠹》曾說:“今境內(nèi)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71)王先慎撰,鐘哲點(diǎn)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51頁。這說明,管商的觀點(diǎn)在戰(zhàn)國時(shí)期已經(jīng)廣為人知了。至于韓非子,更是名動(dòng)天下。在他尚活著的時(shí)候,盡管當(dāng)時(shí)還是簡(jiǎn)牘時(shí)代,他的文章就得以廣泛傳播,以至于《孤憤》《五蠹》等名篇落到了秦王嬴政的案幾之上(72)《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第2155頁。。問題是,假如秦王嬴政讀到的不是《孤憤》《五蠹》,而是《八經(jīng)》里的秘密政治,他又會(huì)作何感想呢?現(xiàn)在人們能夠看到的,秦國歷代君主公開認(rèn)同的法家觀念,基本上都體現(xiàn)在富國強(qiáng)兵以及以法治國的層面,罕有君主公開認(rèn)同“潛隱劇本”。
問題是,難道他們對(duì)“潛隱劇本”變?yōu)椤肮_劇本”沒有任何道德顧慮嗎?可以肯定的一點(diǎn)是,他們有過道德顧慮,但他們覺得說出政治真相并尋求到真正的治國之道更重要。法家實(shí)際上是在戰(zhàn)國時(shí)期這一時(shí)代巨變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大潮中,以“戰(zhàn)斗者”或“革命者”的姿態(tài)道出了政治的真相,他們希望以此真相為基礎(chǔ)去實(shí)現(xiàn)他們重新定義的道德價(jià)值和政治理想。法家在中國歷史上長(zhǎng)期面臨著種種道德批判,原因正在于此,法家困境亦由此凸顯。法家困境的第一層內(nèi)涵,就是他們?cè)凇肮_劇本”框架之下揭示了原本屬于“秘密劇本”的內(nèi)容,賦予政治以強(qiáng)烈的非道德色彩。法家困境的第二層內(nèi)涵在于:他們的信徒終將拋棄他們!他們公開的“潛隱劇本”,給作為他們特定閱讀對(duì)象的君主帶來的不僅僅是智慧啟迪,還有更深的權(quán)力真相的揭露。如此帶來的后果是,法家“秘密劇本”的內(nèi)容持續(xù)受到關(guān)注和批判,而其基于公共利益、長(zhǎng)遠(yuǎn)利益的道德感,常常被人刻意忽視或否認(rèn)。后人在道德義憤驅(qū)使之下,已無暇去同情理解法家“公開劇本”的道德理由,而法家對(duì)政治真相的深刻揭示,也因此被刻意掩蓋起來,致使中華文明對(duì)人類政治的認(rèn)識(shí)始終停留在倫理政治的淺近層次。
總之,按照“政治家”如何治國的視角,法家始終面臨著雙重困境。這無異于宣告了他們的人格及其學(xué)說再無可能在政治實(shí)踐領(lǐng)域得到公開承認(rèn)。因?yàn)椤皾撾[劇本”的突出特征在于能做不能說,說出來就容易面臨道德批判,從而存在教唆支配者作惡的嫌疑。“潛隱劇本”公開化的結(jié)果,必然產(chǎn)生系列道德化反應(yīng)。理想主義者或道德主義者,會(huì)將其視為政治生活的洪水猛獸加以猛烈批判;政治領(lǐng)域的掌權(quán)者或現(xiàn)實(shí)主義者更清醒地意識(shí)到,哪怕他們覺得法家說出的政治真相是政治領(lǐng)域顛撲不破的真理,他們也不會(huì)公開贊賞法家人物及其思想。身負(fù)道德污名的法家,已經(jīng)成為支配者實(shí)現(xiàn)統(tǒng)治的一種負(fù)資產(chǎn)。
三、“學(xué)者”視角下的法家政治思維
法家政治思想的非道德屬性是“政治家”或與政治關(guān)系密切的作為謀士的政治思想家提供的一個(gè)認(rèn)識(shí)和實(shí)踐政治生活的理論視角。“政治家”視角的突出特征在于,國家的公共利益、整體利益與長(zhǎng)遠(yuǎn)利益需要通過政治家來統(tǒng)籌規(guī)劃并最終實(shí)現(xiàn),天下百姓的利益也必須通過政治家的統(tǒng)治來實(shí)現(xiàn)。法家政治學(xué)說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基本都是說給他們時(shí)代及未來的政治家聽的。在此過程之中,政治家是政治主體,而天下百姓只是政治家治國的客體。天下百姓的整體利益是政治家成功統(tǒng)治的結(jié)果,而非天下百姓主動(dòng)爭(zhēng)取而來的結(jié)果。總體來說,政治家視角下的法家思維,主要是面向支配者講述政治真相的。
政治家的素質(zhì)能否保障政治實(shí)踐最終有利于天下百姓?法家在此問題上陷入了困境,他們除了像儒家那樣告誡君主必須審慎地進(jìn)行統(tǒng)治之外,并無切實(shí)辦法來確保政治的最終目的有利于天下百姓。法家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單靠能力與德性皆屬中流的君主一人一己之力,無法治理好國家,所以他們?cè)O(shè)想由法家理想中的“法術(shù)之士”來輔佐君主治國,依靠法術(shù)勢(shì)的制度建構(gòu)來確保“中主”政治得以實(shí)現(xiàn)。然而,法家學(xué)說內(nèi)在地蘊(yùn)含著一個(gè)難以避免的邏輯困境,即:法家既反對(duì)傳統(tǒng)士人同時(shí)又提倡法術(shù)之士,法術(shù)之士如何可能成為現(xiàn)實(shí)?法家并無一套完整的學(xué)說體系來培養(yǎng)“法術(shù)之士”。以色列漢學(xué)家尤銳(Yuri Pines)敏銳地發(fā)現(xiàn),法家的“六虱”“五蠹”批判,等于背叛了他們所屬的士人階層,從而遭到后世士人的激烈抨擊(73)Yuri Pines, “Class Traitors? The Book of Lord Shang and Han Feizi’s assault on the Intellectuals,”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 Global Dialogue beyond ‘Orientalism’”, January 20, 2022, online.。中國古代士人眼中的法家,基本上都是殘暴和陰險(xiǎn)的代名詞,現(xiàn)代學(xué)者則將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觀念定性為文化專制主義。在此意義上,古代“士人”與現(xiàn)代“學(xué)者”對(duì)法家觀很難有積極的評(píng)價(jià),因?yàn)槿粽J(rèn)同法家的觀念,站在“政治家”的立場(chǎng)提倡富國強(qiáng)兵,無異于“士人”或“學(xué)者”進(jìn)行自我否定,誰愿意承認(rèn)自己是“六虱”“五蠹”呢?!這就給當(dāng)代學(xué)者同情理解法家學(xué)說帶來了困境。
法家排斥傳統(tǒng)文化的“潛隱劇本”,歷史地理解,乃是應(yīng)對(duì)戰(zhàn)國時(shí)期列國相爭(zhēng)局面而專注于富國強(qiáng)兵的實(shí)用路線而將無用職業(yè)、無用人士加以否定的產(chǎn)物。若從一般政治學(xué)意義來理解,則表明法家不喜歡價(jià)值競(jìng)爭(zhēng),他們主張以政治強(qiáng)權(quán)來壓制其他與統(tǒng)治政策不符的價(jià)值觀念。這是內(nèi)在于法家學(xué)說的一層重要理論內(nèi)涵,是法家學(xué)說非道德屬性的一個(gè)重要表征,也是當(dāng)代法家研究者必須認(rèn)真面對(duì)的問題。當(dāng)然,當(dāng)代學(xué)者也可以從法家學(xué)理發(fā)展的視角,置入價(jià)值多元的內(nèi)涵,將戰(zhàn)國時(shí)期的法家理論改造成符合現(xiàn)代價(jià)值觀念的政治學(xué)說體系,但是這種理論改造的結(jié)果,究竟還能保留多少法家特質(zhì),就很難說了。簡(jiǎn)言之,法家學(xué)說的非道德特質(zhì),必然蘊(yùn)含著排斥價(jià)值多元而傾向有利于支配者利益的一元價(jià)值的意味。倘若當(dāng)代學(xué)者依然循著政治家視角去為支配者如何治國考慮,亦勢(shì)必面臨著一個(gè)倫理難題:現(xiàn)代普通學(xué)者,在不再具有古代法家的政治家身份或與政治密切相關(guān)的謀士身份的情況下,若認(rèn)同法家的非道德觀念,就必須考慮自己身處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的服從者身份,那么,他們難道不擔(dān)心法家式非道德行為落到自己身上而使自己成為一個(gè)犧牲品嗎?
正因上述困境,當(dāng)代法家研究者主張?jiān)跉v史語境中同情地理解法家及其學(xué)說,并呼吁盡可能地給予法家更為公允的評(píng)價(jià)(74)宋洪兵這些年所做的研究,其實(shí)也可歸結(jié)為將法家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結(jié)合起來強(qiáng)調(diào)法家公開宣示的公共價(jià)值不可忽視,從而為法家爭(zhēng)取一個(gè)公允的評(píng)價(jià)。參閱宋洪兵:《韓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第101-190頁。。然而,即使認(rèn)同法家學(xué)說的學(xué)者,也是零散地將其容易為現(xiàn)代社會(huì)接受的法治資源和富強(qiáng)學(xué)說等從法家整體政治學(xué)說體系中摘錄出來(75)宋洪兵:《法家的富強(qiáng)理論及其思想遺產(chǎn)》,《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8年第10期,第45-57頁。。法家學(xué)說的非道德屬性,要么被刻意回避,要么他們就是像其他道德主義或理想主義者一樣,對(duì)其持批判態(tài)度。對(duì)法家政治理論進(jìn)行片面贊賞、刻意回避或一味批判其非道德屬性本質(zhì)上是一種逃避,無助于深化對(duì)傳統(tǒng)中國政治思想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
如何從“學(xué)者”視角將法家學(xué)說在當(dāng)代做一個(gè)完整的有意義的理解?要回答這個(gè)問題,必須實(shí)現(xiàn)法家思維從“政治家”視角向“學(xué)者”視角的轉(zhuǎn)換。“政治家”視角下的法家思維是提供給政治家的治國寶典,“學(xué)者”視角下的法家思維是依據(jù)法家學(xué)說面向全體社會(huì)成員講述政治的本質(zhì),其中包括統(tǒng)治階層,也包括被統(tǒng)治階層。不同的言說對(duì)象,導(dǎo)致二者的理論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法家政治思維的角色轉(zhuǎn)換可以用一個(gè)設(shè)問來體現(xiàn):假如法家人物如商鞅、韓非子以一個(gè)“學(xué)者”身份生活在當(dāng)代社會(huì),他們依然講述那套法家理論而不再單純尋求謀士身份,他們的講述會(huì)呈現(xiàn)怎樣的理論效果?
西方學(xué)界的馬基雅維利研究,能夠?yàn)槲覀兩钊肜斫夂驼J(rèn)識(shí)法家學(xué)說以及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提供一個(gè)有益參考。馬基雅維利在西方歷史上的命運(yùn),與法家在中國歷史語境中的命運(yùn)一樣,長(zhǎng)期遭受道德批判,但是,在西方學(xué)界,始終存在一派為馬基雅維利及其學(xué)說辯護(hù)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他們?yōu)轳R基雅維利辯護(hù)的基本思路是:馬基雅維利不只是甚至不是向支配者諫言的“鑒書”,而是客觀闡述人類政治本質(zhì)及深刻洞察人類政治技巧的學(xué)術(shù)著作。“馬基雅維利還不足以天真到這一步,即設(shè)想‘新君主國’的支配者,像博爾賈這樣的人,是‘教育’的適宜的主體。……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含有不少危險(xiǎn)的有毒的東西,但他是用科學(xué)家的清醒和冷漠來看待這些東西。他開出了他的政治方劑。他開的這些方劑將被使用,但這些方劑是用作善的還是被用作惡的目的,與他的方劑卻不相關(guān)。”(76)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第185-187頁。赫斯勒甚至發(fā)現(xiàn),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對(duì)支配者來說并不新鮮,但是公開化之后,卻有利于服從者:“一個(gè)本質(zhì)的真理在于,對(duì)某些準(zhǔn)則的揭露構(gòu)成了對(duì)稱性的視域,它并不與在權(quán)力斗爭(zhēng)中的站隊(duì)相沖突;同樣正確的是,馬基雅維利所討論的大部分策略在他的書之前就已經(jīng)為支配者所知曉;至少他們要比服從者更好地知曉這些策略。就此而言,人們當(dāng)然可以承認(rèn)馬基雅維利事實(shí)上加強(qiáng)了服從者的一方。”(77)維托里奧·赫斯勒:《道德與政治:二十一世紀(jì)的政治倫理基礎(chǔ)》(第二卷),第289-290頁。也有學(xué)者援引斯賓諾莎和盧梭對(duì)馬基雅維利的看法為證據(jù),認(rèn)為“《君主論》的意圖就在于警告人民一個(gè)篡權(quán)的君主所具有的種種危險(xiǎn)。……馬基雅維利暗中站在人民的一邊,反對(duì)貴族”(78)史蒂芬·B·斯密什:《耶魯大學(xué)公開課:政治哲學(xué)》,賀晴川譯,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41頁。。他們都在以“學(xué)者”的身份為馬基雅維利辯護(hù),將其非道德的政治理論視為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特征,而通過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來揭示這種本質(zhì)特征,將有助于服從者的利益。因?yàn)榭赐噶苏伪举|(zhì)的弱勢(shì)的服從者,將對(duì)支配者的政治表演更為警惕并對(duì)他們提出更高要求,從而推動(dòng)人類政治文明的進(jìn)步與發(fā)展。這為我們以“學(xué)者”身份思考法家政治學(xué)說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學(xué)術(shù)參照。
法家政治思維之所以能夠而且必然轉(zhuǎn)換的邏輯前提,離不開兩個(gè)基本事實(shí):其一,法家學(xué)說所揭示的“潛隱劇本”已經(jīng)徹底公開化而成為法家的特有理論屬性;其二,法家著作的讀者群體已由主要面向政治家而演變?yōu)榘ㄕ渭摇W(xué)者及社會(huì)大眾在內(nèi)的廣泛人群。法家政治思維由“政治家”視角向“學(xué)者”視角的轉(zhuǎn)換,將為法家政治理論帶來新的理論生命力。“學(xué)者”身份,具有更為廣泛的公共屬性,他們的研究,不僅可以對(duì)政治家提出建議,而且還面向整個(gè)社會(huì)發(fā)聲,讓更多的人尤其是更多的普通百姓知道他們的法家觀念,包括法家試圖運(yùn)用政治權(quán)力否定傳播不同價(jià)值觀念的學(xué)者這一觀點(diǎn),也如實(shí)地傳遞給全體社會(huì)成員。“學(xué)者”視野中的法家政治思維,將以呈現(xiàn)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特征為首要理論目的,并在人類社會(huì)的整體結(jié)構(gòu)狀態(tài)之下考察因法家政治思維介入之后支配者與服從者之間的博弈效果。
首先,法家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充分揭示了人類政治黑白一體、善惡混同的曖昧性。人類政治既蘊(yùn)含著政治理想、政治價(jià)值,同時(shí)也必然蘊(yùn)含著各種不受道德原則和客觀規(guī)則約束與限制的領(lǐng)域,呈現(xiàn)出難以剔除的“非道德”特質(zhì)。法家是在先秦時(shí)期以君主與封建貴族的權(quán)力斗爭(zhēng)為時(shí)代背景,探索君主如何綜合運(yùn)用法術(shù)勢(shì)來實(shí)現(xiàn)并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思考如何獲得底層百姓支持和服從以保障國家的生存與發(fā)展。法家通過中央集權(quán)君主政治的權(quán)力運(yùn)作模式,不僅揭示了戰(zhàn)國時(shí)代人類政治的曖昧性,而且超越時(shí)代特征揭示了人類政治的曖昧性。馬基雅維利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獲得的理論呼應(yīng),足以證明法家政治學(xué)說的深刻洞察力。
其次,法家政治理論的超時(shí)空意義及其“潛隱劇本”的公開化,對(duì)于支配者而言,具有雙重政治屬性:啟發(fā)性與警示性。啟發(fā)性又有正負(fù)兩個(gè)方面,正面啟發(fā)在于法家的政治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的資政功能照樣存在。比如,支配者應(yīng)該審時(shí)度勢(shì)地根據(jù)客觀情況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始終牢記為老百姓帶去實(shí)際利益以換取百姓的擁護(hù)和支持,利用客觀公正的制度遠(yuǎn)比靠人的德性來統(tǒng)治更為理性務(wù)實(shí),國家的生存與發(fā)展需要以自身國力為基礎(chǔ)等。負(fù)面啟發(fā)在于,支配者將充分利用政治的曖昧性毫無心理負(fù)擔(dān)地進(jìn)行政治表演,并在暗地里心安理得地從事道德上骯臟的活動(dòng)。他會(huì)從法家的“潛隱劇本”以及人類政治的曖昧特征中尋求理論支持,會(huì)在心里安慰自己:所有人都在這么做,自己不必有絲毫道德負(fù)罪感。如此,勢(shì)必會(huì)導(dǎo)致政治領(lǐng)域充滿更為濃郁的非道德色彩。而這,正是諸多道德主義者最為擔(dān)憂的地方,所以他們會(huì)極力對(duì)政治生活中的陰謀權(quán)術(shù)進(jìn)行道德批判。道德主義者的擔(dān)憂不無道理,但是,他們一方面沒有意識(shí)到政治的曖昧本質(zhì)是一直存在而非法家的教唆的結(jié)果,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真正懂得“學(xué)者”視野下的法家政治思維,蘊(yùn)含著強(qiáng)烈的警示色彩:公開化的法家“潛隱劇本”無異于將政治領(lǐng)域存在的政治表演悉數(shù)呈現(xiàn),而且還指出支配者隨時(shí)會(huì)為達(dá)成他們的目的而干違背道德原則的事情,會(huì)犧牲某些無辜的人的利益甚至生命。這種露骨的“揭露”,無異于警示支配者深刻注意自己的表演技能不能太拙劣,否則將會(huì)有損政治形象并最終不利于自己的統(tǒng)治。法家政治思維所蘊(yùn)含的警示性,使得支配者的政治表演被拆穿,而支配者欲通過種種道德說教或意識(shí)形態(tài)宣傳來掩蓋政治本質(zhì)則因此變得越發(fā)困難。因此,支配者就必須要有所收斂,并尋求更為高明的政治表演。
再次,法家“潛隱劇本”的公開化,對(duì)生活于社會(huì)底層的天下百姓而言,具有真正的“政治啟蒙”功能。底層百姓的思維方式多是感性的,具有道德樸素感,同時(shí)也有著圍繞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精打細(xì)算的工具理性。因此,當(dāng)他們初步接觸法家的“潛隱劇本”時(shí),第一反應(yīng)一定是批判和痛恨,他們更容易接受道德主義學(xué)者主導(dǎo)的輿論,從而對(duì)法家產(chǎn)生厭惡感。然而,深入理解法家政治思維的“學(xué)者”通過詳細(xì)剖析法家學(xué)說的“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會(huì)讓更多人對(duì)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有一清晰認(rèn)識(shí)并對(duì)政治祛魅,真正意識(shí)到天下百姓的利益必須依靠他們時(shí)刻保持對(duì)政治權(quán)力的高度警惕來加以維護(hù),意識(shí)到唯有多數(shù)人的強(qiáng)大監(jiān)督才能真正讓支配者切實(shí)重視他們的權(quán)益。面對(duì)公開化的法家學(xué)說,天下百姓不應(yīng)該只是單純?cè)诘赖律蠀拹?而是應(yīng)該從中獲得更多的對(duì)政治本質(zhì)的理性認(rèn)識(shí)。
最后,法家“潛隱劇本”的公開化,將使支配者的政治表演難度增加,支配者與服從者之間將呈現(xiàn)為圍繞利益的“明牌”博弈。在服從者不了解政治本質(zhì)時(shí),支配者還可以通過各種意識(shí)形態(tài)說教來進(jìn)行道德粉飾,以此讓服從者迷惑并取得他們的擁護(hù)和支持。然而,一旦廣大服從者都了解到政治的真相,支配者的“底牌”就被揭穿,雙方因而處于一種彼此密切觀察對(duì)方的“明牌”階段。此時(shí),支配者將受到更多的輿論監(jiān)督和權(quán)力監(jiān)督,他們的政治表演也得面臨更高的要求。人類政治文明的進(jìn)步,奠基于服從者迫使支配者讓步并最終制度化的歷史進(jìn)程。
法家政治思維由“政治家”的支配者視角向“學(xué)者”的服從者視角轉(zhuǎn)變,將使法家學(xué)說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重新煥發(fā)其理論生命力,并因其有利于弱勢(shì)的服從者權(quán)益的特征而具有某種革命色彩。當(dāng)然,“學(xué)者”視角下的法家政治思維,同樣具有“政治家”視角下的理論功能,支配者隨時(shí)都可以從法家那里獲得智慧啟迪。只不過,這種啟迪不再是專屬于支配者的,同時(shí)也屬于服從者。懂得了法家的政治思維,當(dāng)國家遇到外部威脅時(shí),支配者與服從者往往更為容易達(dá)成利益聯(lián)盟,團(tuán)結(jié)起來,共同維護(hù)政治共同體的生存與發(fā)展。當(dāng)懂得政治表演是人類政治的根本特質(zhì)時(shí),服從者也將更理性地看待支配者,從而具有更多的包容與理解。正如馬基雅維利在給洛倫佐·梅迪奇的獻(xiàn)詞中所說:“深深地認(rèn)識(shí)人民的性質(zhì)的人應(yīng)該是君主,而深深地認(rèn)識(shí)君主的性質(zhì)的人應(yīng)屬于人民。”(79)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第2頁。客觀上作為服從者的人民如何深深地認(rèn)識(shí)君主的性質(zhì)?馬基雅維利的潛在意思,就是通過《君主論》來呈現(xiàn)君主的性質(zhì),同樣,法家也通過他們的著作來呈現(xiàn)了君主的性質(zhì),并通過這些著作的公開化而使人民了解君主的性質(zhì)。說到底,支配者與服從者之間是一種互為目的與手段的共生關(guān)系,在支配者與服從者互相深刻認(rèn)識(shí)對(duì)方的前提下,本著互利共生的原則,才有可能真正促進(jìn)社會(huì)的和諧與進(jìn)步。
先秦法家如果穿越至當(dāng)代社會(huì),他們樂意見到法家政治思維由“政治家”立場(chǎng)向“學(xué)者”立場(chǎng)轉(zhuǎn)換嗎?答案應(yīng)該是肯定的。原因有二:其一,創(chuàng)作于先秦時(shí)期的法家著作,雖然在當(dāng)時(shí)歷史背景之下,極力主張加強(qiáng)君權(quán)并強(qiáng)調(diào)運(yùn)用各種手段來維護(hù)權(quán)力,但是在通讀法家著作的過程中,我們時(shí)刻能夠感受到一種強(qiáng)烈的權(quán)力批判意識(shí),《韓非子》的《孤憤》《說難》《備內(nèi)》《和氏》諸篇可謂這方面的經(jīng)典著作。法家的悖論在于,他們既深刻批判權(quán)力,卻又無奈地承認(rèn)人類離不開權(quán)力這一客觀事實(shí)。其二,法家公天下的政治情懷和公正的法治追求,注定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在于實(shí)現(xiàn)天下百姓的利益而非君主一家一姓之利。他們寄希望于強(qiáng)大的君權(quán)打壓貴族專權(quán)的封建政治,聯(lián)合底層百姓的力量來完成新的君主制國家,但是,新的中央集權(quán)的君主制國家并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他們的政治理想,一旦轉(zhuǎn)換社會(huì)語境,他們一定會(huì)愿意以“學(xué)者”立場(chǎng)來闡述他們的觀點(diǎn),做真正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情。
結(jié) 語
人類社會(huì)的秩序離不開權(quán)力,權(quán)力具有強(qiáng)烈的支配色彩但又必須依賴非權(quán)力的形式來掩飾。自成目的的權(quán)力將導(dǎo)致權(quán)力的自我否定。權(quán)力的悖論決定了人類政治的曖昧性,政治表演不可或缺;人類政治的曖昧性與政治表演又決定了非道德屬性是人類政治的本質(zhì)而非有待于解決的問題。馬基雅維利與先秦法家諸子,都因?yàn)楣_了人類政治的非道德特質(zhì)而陷入雙重困境:倫理困境以及自我實(shí)現(xiàn)的困境。他們以“政治家”立場(chǎng)而提出的各種應(yīng)對(duì)政治生活復(fù)雜情況的諫言,因其著作的流傳而公開化,喪失了單獨(dú)為支配者秘密掌握的治術(shù)資格,將人類政治的秘密屬性公開揭露出來。他們以及他們的政治理論既要承受道德批判,又要面臨被他們寄予希望的支配者拋棄與否定的命運(yùn)。
中國學(xué)者對(duì)法家的研究,缺乏西方學(xué)界對(duì)馬基雅維利研究那樣的理論深度。借助西方學(xué)界馬基雅維利研究,可以為中國的法家研究提供一個(gè)有益的方法與理論借鑒。馬基雅維利與法家諸子的歷史命運(yùn),給后世同情理解他們學(xué)說的“學(xué)者”帶來困擾,同時(shí)也帶來一種角色轉(zhuǎn)換的契機(jī)。“學(xué)者”的困擾在于,倘若認(rèn)同他們的學(xué)說,勢(shì)必在政治的曖昧性中面臨一個(gè)認(rèn)可自己成為支配者作惡對(duì)象的可能;“學(xué)者”的契機(jī)在于,可以從服從者的立場(chǎng)將他們的學(xué)說視為人類政治無法消除更無法回避的特性,既不失其原有的資政功能,又在支配者與服從者的權(quán)力博弈與利益消長(zhǎng)格局中注入警示功能,進(jìn)一步對(duì)人類政治進(jìn)行祛魅,在深刻洞察人類政治本質(zhì)的基礎(chǔ)上推動(dòng)人類政治文明的進(jìn)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