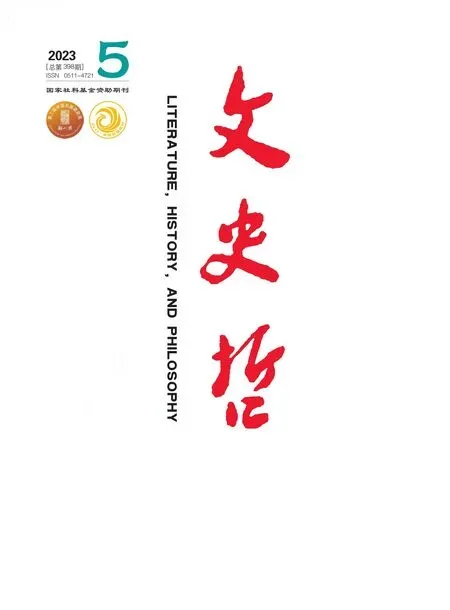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與《墨子》城守諸篇關系再議
——兼論戰國東方墨學的學術地位
張 偉
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多部抄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包括論述守御之事且與傳世《墨子》城守諸篇(以下簡稱“城守諸篇”)內容相近的《守法》《守令》二篇。簡文甫一出土,羅福頤即根據其中存在大量可與城守諸篇對讀的內容,而認為其“可能是《墨子》的佚文,或者是與《墨子》文辭相近的其他古書”(1)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第34頁。。隨著整理、研究工作的展開,學界對簡文與城守諸篇的關系展開了更為深入的討論。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守法》《守令》中存在“伍人”“去署”“守”等具有秦人色彩的詞語以及嚴苛的法制主義原則,所以此二篇當是齊人襲用秦墨所撰城守諸篇而編成的(2)關于學界對《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關系的討論,參見李學勤:《論銀雀山簡〈守法〉〈守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1-349頁;史黨社:《〈墨子〉城守諸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29-243頁。。
近年來學界根據新出簡帛古書而提出的“古書佚失觀”“族本”等文本理念,為我們重新思考簡帛古書與傳世文獻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與觀察視角,而基于這些新文本理念,《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戰國墨學流變情況實有可繼續探討的空間。有鑒于此,筆者擬從簡帛古書流傳特點入手,對二者的關系以及戰國墨學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古書佚失觀”下的《守法》《守令》與《墨子》城守諸篇
清中期以來,《墨子》先后得到畢沅、盧文弨、孫詒讓等人的校理。在此基礎上,城守諸篇的成書年代、所屬地域等問題亦開始受到學界關注。孫詒讓認為,城守諸篇乃“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于墨學為別傳”(3)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頁。。蘇時學則根據《號令》中多有“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男子”等“秦時官”以及“其號令亦秦時法”,而推斷城守諸篇出自秦人之手;不過,蘇時學囿于所聞,認為城守諸篇“蓋出于商鞅輩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4)蘇時學:《墨子刊誤》卷二,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368頁。。在民國以來諸子學研究日漸興盛的背景下,關于城守諸篇成書、流傳問題的研究日趨深入,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將其與秦墨聯系起來的觀點:
自《備城門》以下諸篇,備見秦人獨有之制,何以謂其不為秦人之書?是二說(引者注:指上引蘇時學、孫詒讓之說)者,皆不可洽人意。推而明之,其為秦墨之書無惑也。(5)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215頁。
因1975年出土的云夢睡虎地秦簡中多有可與城守諸篇相對應的內容,故城守諸篇為秦墨所作這一觀點目前基本已為學界所接受(6)關于云夢睡虎地秦簡與《墨子》城守諸篇的關系,參見李學勤:《秦簡與〈墨子〉城守諸篇》,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云夢秦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24-335頁。。

表一 《守法》與城守諸篇對照表
據表一可知,城守諸篇中與《守法》簡文相對應的內容集中在《備城門》《號令》二篇之中。李學勤認為二者大段文字相重“不會是文句偶爾相類,只能是襲用的關系”(9)李學勤:《論銀雀山簡〈守法〉〈守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345頁。。在此基礎上,李學勤又根據《守法》中存在“伍人”“去其署”等具有秦人色彩的詞語而進一步斷定《守法》雖出自齊人之手,但也襲用了秦墨的著作。史黨社也根據《守法》簡文中的秦國官名“守”而認為《守法》是“齊人抄錄了秦人作品《號令》,夾雜齊墨的資料‘合編’而成的”(10)史黨社:《〈墨子〉城守諸篇研究》,第236頁。按因史黨社認為簡767-792為《守令》篇,故其文中凡稱“《守令》”者,均為本篇中的“《守法》”。。在此需要加以指出的是,李學勤在提出《守法》篇因襲自秦墨作品之后,又提出了一種與前說略顯矛盾的觀點,即認為二者也可能擁有共同的來源(11)參見李學勤:《論銀雀山簡〈守法〉〈守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346頁。。
《守法》之外,《守令》中亦有可與城守諸篇對讀的內容,但多為守城器械設施的名稱,屬于整段文字相似的情況僅有1處:

表二 《守令》與城守諸篇對照表
在這一段可以對讀的文字乃至《守令》整篇中,并無明確顯示本篇地域屬性的證據,所以對《守令》成書及其與城守諸篇關系的探討只能借助于《守法》及同出文獻等其他證據來進行。
由表一、表二可知,《守法》《守令》與出自秦墨的城守諸篇間存在“同文”(12)所謂“同文”,指兩個不同文本之間存在的內容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學界或稱之為“異文”,或稱之為“重文”,或稱之為“對文”。本文采納李銳之說,稱之為“同文”。。李學勤、史黨社等學者正是根據這種“同文”推斷簡本乃因襲城守諸篇而成的。然而,在寫本文獻研究中,單純根據“同文”現象來判斷文本先后關系的做法并不合適,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古人多“言公”(13)“言公”一詞出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史通義·言公上》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二《言公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9頁)之論,“于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為善”(14)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三《辯證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48頁。;另一方面,則與未能在早期文本研究中樹立“古書佚失觀”而將不完全歸納視為完全歸納這一邏輯謬誤有關。
所謂“古書佚失觀”指在面對流傳至今的先秦傳世文獻及新出簡帛古書時,不能忽視雖已亡佚但卻與其相關的同時代文獻這一文本觀念。盡管《守法》《守令》中存在可與城守諸篇對讀的大量內容,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據此判定二者間具有因襲關系。因為二者間除存在前者在先或后者在先兩類情況外,還可能存在二者共同源自一個已經亡佚的文本或二者各自源出于一個已經亡佚的文本兩種可能性。在我們引入“古書佚失觀”去分析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古書間關系之后,存在“以不見為無有”邏輯謬誤的線性文獻發展觀對此類問題的解釋力便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喪失了對具有“同文”的兩個或多個文本間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的可能,因為“同文”雖不能證明文本之間必然具有先后因襲關系,但某些存在相似內容和共同本質特征的文本仍足以構成一個類似于家族的自在文本系統,亦即“族本”系統(15)關于“族本”這一概念,參見李銳:《從出土文獻談古書形成過程中的“族本”》,《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第223頁。。屬于同一個族本系統的文本可能源自同一個祖本并構成先后關系,也可能源自同一個祖本但卻是同源異流關系,還有可能共同源自師說而非具體、實在的文本。
具體到《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的關系上,因二者存在大段文字相重的情況,特別是在“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丈夫千人”(16)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一四《備城門》,第530頁。按“術”,銀雀山漢簡作“遂”。等具體數據以及“出樓”“進行樓”等守城器械名稱上亦完全相同,故可排除二者各有源頭、互不相干這種可能性,而將其劃入同一個“族本”系統。在上述可能存在于“族本”系統內的三種文本關系中,不存在具體祖本而源自口頭師說的情況,多適用于諸子學派傳習的思想性文本,《守法》《守令》這類涉及具體實用技術和精密尺寸度數的文本則不具備僅憑口說傳習的條件。職此之故,《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的關系僅可能存在同源異流或先后相襲兩種情況。至于這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是《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間的真實關系,則需結合簡文內容、同出文獻以及戰國墨學發展情況加以具體考辨、論說。
二、論《守法》《守令》非出自秦墨
在僅憑“同文”無法證明《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間必然存在因襲關系的情況下,李學勤、史黨社等學者復以《守法》中存在“伍人”“去署”“守”等所謂具有秦人特征的詞語為論據,推斷《守法》篇因襲自秦墨的觀點能否成立呢?欲回答此問題,需先對上述詞語本身加以深入、細致的分析。
李學勤認為《守法》篇“百人以下之吏及與□及伍人下城從”(1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8頁。中的“伍人”一詞,與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中的“伍人”均指“同伍之人”,加之“伍”字的此種用法不見于其他先秦文獻,故“伍人”一詞的存在可作為《守法》因襲秦墨作品的證據之一。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加強對民力的控制與利用,普遍建立了以什伍組織為代表的戶籍制度。在銀雀山漢簡出土的齊地,“伍”這一組織也出現頗早。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推行“作內政而寄軍令”時,即有“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18)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24頁。的記載。此外,《守法》簡文中“伍人”之上的闕文右側從“車”,可能是“連”字的闕文,讀為“聯”(19)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30頁。,而齊地文獻《管子》中多有“連(聯)”“伍”并用之例,如“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20)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乘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9頁。按《周禮》中亦有與《管子》類似的記載,即“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周禮注疏》卷一二《地官·族師》,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19頁)。雖然《周禮》中多有與《管子》等齊地文獻近似的記載,但鑒于《周禮》的成書時代和地域目前尚無法確指,故本文不以《周禮》中的相關記載作為論證《守法》《守令》出自齊地的主要證據,而僅在注釋中提及以供讀者參考。等。因此所謂“伍人”不僅不能作為《守法》出自秦墨的證據,反而表明其可能是齊地作品。
除“伍人”外,“去署”“守”等詞語亦不能構成斷定《守法》出自秦墨的充分條件。在李學勤看來,“去署”或“離署”一詞乃“秦人習語”,“在戰國時期其他國的文獻中不曾出現”(21)李學勤:《論銀雀山簡〈守法〉〈守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347頁。,故可據《守法》簡文中“去其署者身斬”(22)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28頁。一語而斷定《守法》乃因襲秦墨而成的作品。“去署”“去其署”或“離署”一詞中的“署”均指官署。盡管在戰國其他文獻中不曾有“去署”“離署”等表達,但以“署”指官署卻數見不鮮,如《國語·魯語上》有“署,位之表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23)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第162-163頁。的記載。既然官署之“署”不為秦地文獻所獨有,那么以此作為判斷《守法》所屬地域的證據便顯得較為牽強了。至于“守”這一官名,雖不見于戰國齊地文獻,但卻屢見于記載三晉、燕、楚等國史事的文獻中(24)魏國之“守”如“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66頁)。趙國之“守”如“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59頁)。韓國之“守”如“后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第1825頁)。燕國之“守”如“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何建章:《戰國策注釋》,第784頁)楚國之“守”如“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一五《指武》,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67頁)。,可能也非秦所獨有。總之,部分官職名稱相同并不足以證明《守法》必因襲自秦墨作品或成于秦人之手。
不僅上述諸語詞的使用不足以證明《守法》出自秦墨,與《守法》同出的其余10篇文獻以及《守法》簡文本身反而提供了諸多證明《守法》非出自秦墨的證據。據銀雀山1號漢墓所出篇題木牘可知,與《守法》《守令》同屬一組的文獻還有10篇:《要言》《庫法》《王兵》《市法》《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篇》《兵令下篇》(25)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根據1號漢墓所出篇題木牘確定這一組文獻共有13篇:《守法》《要言》《庫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篇》《下篇》,但根據簡文內容可知,篇題木牘中的《上篇》《下篇》其實均屬于《兵令》,故所謂“十三篇”當為12篇。關于篇題數量的區分,參見史黨社:《〈墨子〉城守諸篇研究》,第210-211頁。。由于以上12篇文獻在竹簡形制、書寫字體乃至語匯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且篇名出現在同一方篇題木牘上,各篇之間應有較密切的關系。對其余各篇的來源加以分析,也將有助于我們認識《守法》《守令》的源出。
雖然在《要言》等10篇文獻中,《委法》僅存篇題,《市法》《李法》殘斷嚴重,《庫法》所言為軍事裝備的庫藏規定,多涉及具體器械名稱,而無法根據簡文內容判斷上述4篇的來源,但其余6篇中可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的內容則提供了關于這組文獻來源的重要信息。《王兵》篇多有與《管子·參患》《七法》《地圖》《幼官》《兵法》諸篇相一致之處,而《管子》一書為戰國齊人所撰(26)關于《王兵》中可與《管子》諸篇相對讀的內容,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王兵〉與〈管子〉相關各篇對照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55-158頁。;《田法》中的“三歲而壹更賦田,十歲而民畢易田”(2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46頁。與《管子·乘馬》“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28)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乘馬》,第90頁。按除與《管子》內容接近外,《王法》對上田、中田、下田畝數的劃分又與《周禮》相同。因《周禮》一書的成書時代與地域遽難確定,故僅將此點注于此處以供讀者參考。的記載相近;《王法》中的“富國豤(墾)草仁(仞)邑”(29)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42頁。與《管子·小匡》所載管仲之語相近(30)《管子·小匡》:“管仲曰:‘……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447頁)《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呂氏春秋·勿躬》《新序·雜事》等文獻中亦載有此語,且均以其為管子之言。。綜上所論,《王兵》《田法》《王法》均與齊國存在密切關系,其均屬于齊地文獻系統殆無疑義。
簡本《兵令》與今本《尉繚子·兵令》間文字多同,二者可劃入同一個“族本”系統。因此盡管整理小組鑒于前者的簡式、字體及標題簡形制與《守法》等篇相似而未將其收入簡本《尉繚子》中,但我們仍可根據《尉繚子》的成書與流傳過程,推斷《兵令》篇的來源。《漢書·藝文志》于雜家類、兵形勢類分別著錄了一部《尉繚》;《隋書·經籍志》則僅于子部雜家類著錄《尉繚子》五卷,并自注:“尉繚,梁惠王時人。”(31)《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06頁。后人或據《隋書·經籍志》及《尉繚子·天官》中的“梁惠王問尉繚子曰”(32)鐘兆華:《尉繚子校注》,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1頁。而以是書為戰國中期尉繚所作,或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33)《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0頁。的記載而以為是書出自戰國末年尉繚之手(34)關于對《尉繚子》成書時代的討論,參見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第28-34頁;張烈:《關于〈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文史》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37頁。。由于先秦古書多非成于一人、一時,因此欲認清《兵令》篇的源出,需從討論尉繚其人的活動地域與《尉繚子》其書的成書過程入手,而非單純爭論尉繚其人所屬時代。
今本《尉繚子》以刑法治軍的思想主張,頗與商君之學接近,而商鞅所習之刑名法術來自魏國,又《漢志·諸子略》雜家類所著錄之《尉繚》二十九篇后,有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之文曰“繚為商君學”(35)《漢書》卷三○《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2頁。,故尉繚當為魏人或曾長期活動于魏地,尉繚之學當可劃歸三晉學術之列。由于周秦古書多不題撰人,今本所題寫之某子,往往為西漢人整理先秦舊籍過程中所增加。那么《尉繚子》一書所反映的思想來自尉繚其人嗎?先秦古書多單篇別行,至秦漢時期特別是經由西漢末年劉向、歆父子等人整理后,以單篇形式流傳的先秦典籍始得以定著為含有較固定篇目的形式。劉向、歆等人在將零散篇章匯聚成書時,并非草率為之,而是在“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學,出于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的基礎上,“刪除重復,別行編次,定著為若干篇”的,至于那些不能明確出自某家之學者,則不題具體名氏,即所謂“六略中凡書名不著姓氏者,皆不可考者也”(36)余嘉錫:《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75、208頁。。換言之,凡可考出自某學派者,均著錄姓氏以明其所自出。那么《尉繚子》其書既然題有尉繚之名,則其當源出自尉繚或尉繚后學。前已述及尉繚習商君刑名法術之學,其人、其學均與魏國關系密切,因此與《尉繚子》一書有大量“同文”的《兵令》篇也當源出自三晉之學。
《要言》乃匯集諸家格言而成,是此組文獻中體式較為特殊的一篇。其中對“大國”“中國”“小國”各自職任的劃分與出自齊地的《王法》篇接近,而“良馬有乘,遠道可長也。賢材有合,大道可明也”(3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33頁。的議論又與《尉繚子·武議》中的“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38)鐘兆華:《尉繚子校注》,第37頁。一語基本相合。是故《要言》篇與齊地文獻及《尉繚子》也有密切關系。
綜合以上所論,除因竹簡殘斷嚴重不能詳悉其內容的4篇外,其余6篇文獻或為齊地文獻,或與出自三晉的《尉繚子》關系密切。然而,相比于李學勤、史黨社等學者以“伍人”“署”“守”等內證證明《守法》《守令》出自秦墨,同出文獻的來源僅為推斷《守法》《守令》源出的外證,在《守法》或《守令》簡文本身尋出證明其非出自秦墨的內證,是確立此二篇非出于秦墨一說的關鍵。
《守法》簡文在論述所防守城郭規制時,有“郭方七里,城方九〔里〕”一語。整理者認為作為外城的“郭”應大于作為內城的“城”,因此,“郭方七里”當作“郭方十七里”(39)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27、129頁。。然而,驗之考古所見先秦城邑遺址,我們發現“郭方七里,城方九里”一語不僅未曾脫文,反而是證明《守法》篇非出自秦地的重要內證。在一般城市建設中,郭城要大于內城,呈現出“內城外郭”的城市格局。然而在戰國時期部分關東諸侯國的城邑建設中,卻出現了“城郭并立”的城市形態。所謂“城郭并立”,即郭城與內城分別建立,內城不嵌套于郭城之中(40)關于戰國時期關東諸侯國城邑建設中城郭并立的情況,參見梁云:《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考古學的視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4-198頁;許宏:《先秦城邑考古》,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285頁。。在內城既不嵌套于外城之中且與外城不相聯屬的情況下,內城的面積便有可能大于郭城。同時考古所見多數秦國城邑卻僅有一道城垣甚至無城垣設施(41)秦早期都城雍城遺址僅發現一道城垣,秦晚期都城咸陽則未修建城垣,一度為秦都的櫟陽遺址中也未發現城墻遺跡。,因此若《守法》出自秦墨,則其中便不必有論述外郭、內城如何防御的內容,而“郭方七里,城方九里”一句恰恰不見于城守諸篇。因此,涉及外郭、內城防御之法的《守法》篇必非秦墨針對秦國“非城郭制”的城市形態設計的守城方案,而只可能出自多采用“城郭并立”制的關東諸侯國。《守法》中的“郭方七里,城方九里”一語因與戰國時期關東諸侯國的城邑建設特點相符,足以成為《守法》篇非出自秦墨而與三晉或齊國關系密切的內證。
根據以上從內、外證兩方面所作論述,可基本確定《守法》篇非出自秦墨,換言之,其與城守諸篇間并不存在先后因襲關系。至于《守令》一篇,因簡文中缺乏明確反映其所屬地域與學派的語詞,故難以通過尋求內證來證明其非出自秦墨,但結合同出文獻,尤其是性質、內容與其接近的《守法》篇非出自秦墨這一外證,可推知其亦非源出自秦地的文獻。
三、《守法》《守令》與東方墨學
辨明《守法》《守令》非出于秦墨所傳,不僅解決了戰國時期兩篇墨家城守文獻的流傳問題,而且為我們突破關于戰國墨學發展、流變的固有認識提供了契機與可能。
戰國時期,墨學號稱“顯學”,時人有“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42)《孟子注疏》卷六《滕文公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714頁。之說。墨家創始人墨翟為魯人,一生中曾居魯、仕宋、東至齊、北使衛、南游楚(43)參見孫詒讓:《墨子傳略》,《墨子間詁》,第682-693頁。按墨子還曾使其弟子公尚過仕于越(參見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一三《魯問》,第474頁)。。墨子死后,墨學的流傳范圍進一步擴大,“南暨楚越,北及燕趙,東盛齊魯,西被秦國,四方莫不有墨者”(44)方授楚:《墨學源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55頁。。在廣泛流播的同時,墨家學說自墨子死后也發生了分裂,即所謂“墨離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45)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顯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56-457頁。。
與“墨離為三”相類似的是,墨家弟子還因所從事工作性質的不同而分為“談辯”“說書”“從事”三類(46)《墨子·耕柱》:“治徒娛、縣子碩問于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一一《耕柱》,第426-427頁)。談辯類弟子主要以墨家學說游說諸侯;說書類弟子負責記錄、整理墨子言行,并在墨家后學中教授;從事類弟子則主要從事守城技術的研究與應用(47)關于墨家三類弟子工作性質的劃分,參見鄭杰文:《中國墨學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6頁。。正因為墨家內部分派與墨家弟子分工均以“三”為紀,故部分學者嘗試在二者之間建立某種聯系,即在將墨家三派按地域分為東墨、南墨與秦墨的基礎上,提出了秦墨從事、東墨說書、南墨談辯的觀點(48)參見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古學甄微》,第212頁。。然而揆諸關于墨家弟子從事三類不同工作的記載,我們發現不能將“墨離為三”這一學派層面的問題與對墨家弟子工作類型所作劃分等同起來。
墨子曾以筑墻工作中的“筑”“實壤”“欣”三道工序為例,向治徒娛、縣子碩介紹墨家弟子的三類分工。所謂“筑”即夯土筑搗;“實壤”即以箕畚等工具往返運輸筑城所需建筑材料;“欣”同“睎”,指建筑工程中的測繪工作。若欲筑成一段堅固的墻體,“筑”“實壤”“欣”三道工序需同時并舉,那么若想實現墨家的社會理想,從事談辯、說書、從事三類工作的弟子亦缺一不可。因此,墨家學派雖在墨子死后分裂為三派,但此三派應各自同時涵蓋了談辯、說書、從事三類工作,而非各有側重,否則便不能很好地推行墨家的各項政治主張,實現墨家學派的社會價值。這一點還可從墨家學派在戰國時期的流傳演變中窺見一斑。在蒙文通等學者看來,因城守諸篇出自秦墨之手,故其認為秦墨乃“從事”派之墨,然而秦墨在講習墨家城守戰術與技術的同時,還記錄、整理了大量墨家事跡,亦即同時從事著“說書”類工作。秦相呂不韋組織門客撰成的《呂氏春秋》一書,是除《墨子》外記載墨家事跡最為詳盡的先秦文獻,墨家巨子孟勝為魯陽文君守城、墨者巨子腹殺子等事均載于此書。《呂氏春秋》中之所以保留有大量墨家事跡,當與秦墨之徒曾利用其所掌握的墨家文獻參與《呂氏春秋》一書的編纂工作不無關系。因此以墨家三派僅承擔一至兩類工作的觀點有欠妥當,墨家三派應同時兼擅談辯、從事、說書三類工作。
在明確從事類工作非秦墨所獨擅之后,《守法》《守令》出自秦墨之外其他墨家學派的傳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么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守法》《守令》若非秦墨所傳,則其是出自楚墨還是東方之墨呢?
據《墨子》“后五篇”(49)今本《墨子》共五十三篇,可分為五組:自《親士》至《三辯》七篇為第一組,習稱“前七篇”;自《尚賢上》至《非儒下》二十四篇為第二組;自《經上》至《小取》六篇為第三組;自《耕柱》至《公輸》五篇為第四組,習稱“后五篇”;自《備城門》至《雜守》為第五組(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06-107頁)。其中后五篇的體例類似《論語》《孟子》,多載墨子與時人、弟子問答之語,且篇中稱墨子均為“子墨子”,故當出于墨子弟子的記錄,為研究早期墨學史較為可靠之資料。可知,墨子在世時,不僅于壯年之時自齊之楚以止楚攻宋,而且在其晚年還曾居于楚國北部的魯陽,與魯陽文君相善。關于墨子死后墨家在楚的活動情況,文獻所載甚少,較著者僅有二事:其一為墨家巨子孟勝曾為楚陽城君承擔守御封邑之事,并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集體殉義自殺;其二為《莊子·天下》曾提及“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50)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一○《天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073頁。。由第一事可知,楚墨之中亦有擅長守御之事的墨家弟子,但由于孟勝率180余名為陽城君守城的弟子集體殉義,楚墨的守御文獻及守御技術可能就此失傳。至于作為戰國中后期南方墨者代表的苦獲、己齒、鄧陵子等人究竟擅長墨家三類工作中的哪一類,也因文獻闕如而不能得知了。或以南方之墨所誦習之《墨經》為今本“墨經”六篇,進而認為南方之墨擅長談辯(51)如蒙文通認為:“《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此鄧陵之屬所誦《墨經》,堅白、同異之辯,屬于南方之墨。”(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古學甄微》,第212-213頁),但《天下》所言之《墨經》當非今本“墨經”六篇,而應指能反映墨家核心政治思想且為墨家學派所共同尊奉的經典,否則楚墨便不具備稱其他墨家學派為“別墨”的資格了。綜合來看,楚墨雖曾講習守御技術、傳承守御文獻,但因擅長守御之墨家弟子共同殉義于楚之陽城,故楚墨在戰國中后期的代表苦獲、己齒、鄧陵子諸人僅以傳承墨家政治思想為務而不以城守聞名。因此,《守法》《守令》出自楚墨傳習的可能性極小。
在排除了秦墨與南方之墨傳習《守法》《守令》的可能性之后,此二篇只可能出自東方之墨了。所謂“東方”,特指戰國時期江淮以北的關東地區,包括齊、魯、宋、衛以及三晉、中山等諸侯國。前已述及,齊、魯、宋、衛一帶為墨子在世時墨家學派活躍的地區。墨子死后,其弟子禽滑釐成為東方墨家的代表人物。禽滑釐在墨子在世時即受墨子重視,如墨子自齊至楚游說楚王停止攻打宋國時,即命禽滑釐等弟子在宋國擔負守御工作。墨子死后,禽滑釐亦曾于東方招生授徒以傳播墨家學說,索盧參、許犯均曾從其問學。除齊、魯、宋、衛所處的黃河下游外,位于黃河中上游的三晉亦有墨家活動。據《呂氏春秋·去宥》,東方墨者謝子曾于秦惠王時西行入秦(52)《呂氏春秋·去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于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一六《去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23頁);此事亦見載于《說苑·雜言》,唯“謝子”作“祁射子”(53)參見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第412-413頁。按“射”“謝”二字互通。。“祁射子”中之“祁”為地名,《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下有祁縣(54)參見《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1-1552頁。,地當今山西省祁縣東南,于戰國時期為三晉之一的趙國屬地,謝子可能即活動于此。此外,某位不知名的墨者曾與司馬喜在中山王前討論墨家“非攻”主張(55)《呂氏春秋·應言》:“司馬喜難墨者師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一八《應言》,第1220-1221頁),可見在文化面貌上與三晉接近的中山國也是墨家活動的重要區域之一(56)關于考古所見中山國文化遺存及其與三晉文化的關系,參見井中偉、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320-324頁。。盡管傳世文獻中關于三晉墨家的記載較少,而僅能根據有限的史料作出上述粗淺的分析,但由上述謝子入秦及戰國時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可知,三晉地區為東方之墨與秦墨這兩大墨家派別聯系的紐帶。換言之,東方之墨正是以三晉為跳板而西入秦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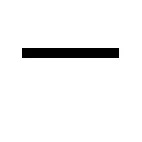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59)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一四《首時》,第773頁。按田鳩,高誘注以為“齊人,學墨子術”,是田鳩亦為東方之墨。
盡管田鳩以楚國為跳板方得見秦惠王,但因其為齊人且在楚時間很短,故當歸屬于東方之墨而非楚墨。
如上文所述,東方之墨兼事談辯、說書、從事三方面工作,故傳至秦地的東方墨家學派亦當兼擅此三方面工作。今本《墨子》城守諸篇雖由秦墨傳習、整理,但其源出自東方之墨的痕跡仍保存于文本之中,如《備梯》開篇即為墨子于泰山之下與禽滑釐討論守御之術的內容: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60)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一四《備梯》,第541頁。
“大山”即泰山。根據先秦時期山川祭祀體系中“祭不越望”的禮制規定,泰山為東方諸侯國國君登封、祭祀的對象,秦人在統一六國之前,僅以雍地諸畤和陳寶祠等為國家最高祭祀,并無禮敬、祭祀泰山之舉。因此以泰山這一“神圣空間”作為墨子與禽滑釐討論城守問題的空間背景,恰足以說明秦墨所傳城守諸篇當源出自東方之墨。
走筆至此,城守諸篇與《守法》《守令》二者共同源自東墨所傳守御之術及所撰守御文獻這一結論似乎已是呼之欲出了。然而仍有一個問題有待作出解答與說明,那就是源出自東墨守御文獻的城守諸篇有無可能自秦回傳東方并對《守法》《守令》的成書產生影響呢?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在戰國中后期關東六國與秦尖銳對立的情況下,秦國頒布了多項禁止秦人逃亡、越境以及將貴重物品私自運送出境的法令,如見于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的“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偕邦亡,出徼,得,論各可(何)殹(也)?當城旦黥之,各畀主”(61)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4頁。。雖然該條文的處罰對象是“人臣”與“人妾”,即歸私人所有之奴婢,但睡虎地秦簡中另一條關于懲處越境者的法令卻非專針對奴婢而設,其文曰:“告人曰邦亡,未出徼闌亡,告不審,論可(何)殹(也)?為告黥城旦不審。”(6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04頁因此,對私自逃亡出境者處以黥刑當是帶有普遍性的秦國法律。同樣據睡虎地秦簡,秦法令對于“盜出朱(珠)玉邦關及買(賣)于客者”(6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26頁。,則規定處以耐刑或罰款。前兩條法令杜絕了掌握守御之術的墨家弟子私自出關的可能性;而據后一條法令推測,墨家守御類文獻雖不屬于“珠玉”等貴重物品,但卻事關秦國國家安全,因此亦當在禁止攜帶出境之列。其次,在戰國中后期墨家三派互相指摘對方非墨家正統的情況下,即便秦墨的相關文獻流傳至東方,也不會被東方之墨所傳習。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如本文第二小節所言,《守法》《守令》中針對東方諸侯國城邑特點而設計的防御技術,并不適用于秦地的城守戰術。同樣,秦墨針對秦國城邑設計的守御技術與戰術,亦難以在東方城邑攻防戰中發揮作用。因此,《守法》《守令》當是兩篇出自東墨之手且在東方流傳有緒的墨家城守文獻,而非由秦國回傳東方形成的。既然出于秦墨之手的城守諸篇源自東方之墨,《守法》《守令》亦非回傳東方的秦墨作品,因此東方之墨最初傳習的守御文獻當為二者共同的源頭,換言之,二者間具有同源異流而非先后相襲的關系。
辨明《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的關系,不僅使我們認識到作為秦墨學術源頭的東方墨家亦擅長守御之術,還為重新認識墨學史上的“墨學中絕”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載墨子傳記僅有24字,且《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墨家之書無托名秦漢以后人所著者,故學界有“墨學中絕”一說。持此說者認為墨家學派在以法家學說為治國指導思想的秦國處于從屬地位,加之擁有獨立組織和內部法紀的墨家學團也與君主高度集權的秦國政治體制相矛盾,故秦朝建立后,墨家遂歸于消亡(64)關于學界對“墨學中絕”問題的討論,參見楊俊光:《墨子新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9-320頁。。然而《守法》《守令》的出土卻表明直至西漢武帝初年(65)出土《守法》《守令》的銀雀山M1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晚于元狩五年(前118),因此《守法》《守令》的抄寫年代不晚于武帝建元初年(參見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第2期,第19-20頁)。,東方墨學仍在傳承并具有一定影響力,這也正與《鹽鐵論·晁錯》所言“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66)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二《晁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13頁。的記載相吻合。總之,在戰國“墨離為三”的情況下,秦墨的消亡并不意味著東方之墨也隨之泯滅,“墨學中絕”說仍有結合新出文獻加以重新審視的必要。
結 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大量簡帛典籍實物的面世,學界開始改變持研究刻本典籍的理論、方法去看待簡帛寫本時代典籍傳承、流變關系的做法,尤其是逐漸認識到在西漢末年劉向、歆等人校書之前,典籍的狀態極不穩定,因而難以在具有“同文”的各版本之間建立某種確定無疑的聯系。近年來,學界針對簡帛典籍的流傳特點,提出了“古書佚失觀”“族本”等新的文本研究視角與理論。這些新視角與新理論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新出簡帛文獻的生成方式、書寫特征與流傳規律,而且對于我們重審學界已有的關于簡帛古書成書、流傳的成說也不無啟發與指導意義。
自1972年出土以來,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始終被認為是承襲秦墨城守諸篇而成的守御文獻。然而若將其置于上述新文本理念的觀照下,我們發現無論從使用語匯的地域性還是從其他同出文獻的來源看,《守法》《守令》與城守諸篇之間并不必然具有先后承襲關系。特別是在《守法》《守令》所載守御之術僅適用于東方諸國城郭分立的城邑布局而不適用于秦地城邑的情況下,其非出自秦墨便是顯而易見的了。《守法》《守令》不出自秦墨不僅事關墨家守御文獻的流傳問題,其背后所隱藏的戰國墨學發展格局更值得我們關注。因文獻不足征,東方之墨雖然產生較早,但在戰國墨學史書寫中的地位始終不及產生較晚但事跡卻屢見于相關文獻記載的秦墨。《守法》《守令》的出土表明作為秦墨源頭的戰國東方墨家不僅亦擅長守御之術,而且其掌握的守御之術直至西漢前中期仍在東方齊地流傳,從而為我們更深入地反思、理解“墨離為三”及“墨學中絕”等墨學史上的重大關節問題提供了新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