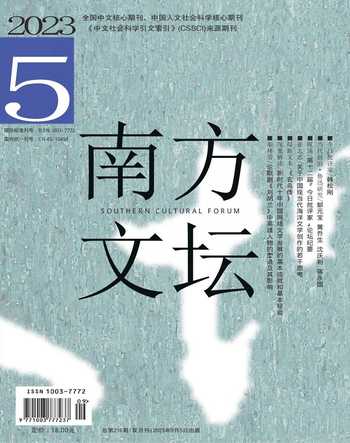如何長成一棵樹
1984年,劉醒龍開始發表文學作品。這一年,我大學畢業,分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做文學編輯。一個寫作品的人和一個編作品的人,遲早會遇上。
時間似乎長了些。與劉醒龍的交集,要等到1991年的初春,起因是劉醒龍把一篇七萬來字的中篇小說《威風凜凜》寄到了《青年文學》雜志。征得編輯部同意,我專程到湖北黃岡(那時為黃岡地區)找劉醒龍談修改意見。那個時候,劉醒龍從英山縣調到黃岡地區群眾文化館做創作輔導員才一個來月。據他后來說:在黃州城里,當時能認識他的不到十個人。而我從武漢坐長途汽車風塵仆仆前來,問到的第一個人,居然說認識劉醒龍。這一湊巧,如今看來,也是我和劉醒龍的緣分注定。
經過修改后,《威風凜凜》就在《青年文學》第7期上發表了。緊接著,我編發了他的中篇小說《村支書》《鳳凰琴》。一個全國性的刊物,在十個月之內連續發表一位并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三部中篇小說,在今天也是罕事。但《青年文學》就這么做了。
當時我們上馮牧先生家,請馮牧先生撰寫《村支書》同期評論的情形,仍歷歷在目。《青年文學》1982年創刊后,就有一個慣例,編輯部看中的、要發頭題的作品,會去請一位在文壇上有影響的評論家撰寫同期評論。為了《村支書》,主編陳浩增、副主編黃賓堂和責任編輯我,在1991年10月初,拜訪了馮牧。馮牧先生年事已高,思路很清晰,精神也很好。他了解來意后,有些無奈地說:“我現在握筆都費勁,你們看我這手。”馮牧的手在不聽使喚地顫抖著,就像手里攥著一個活物。“等我看完作品再說。”五天后,我收到了他顫顫巍巍親筆寫下的關于《村支書》的四千字評論《動人心魄和發人深省之作》。馮牧先生提攜文學后進的真摯和誠懇,讓人動容。
給劉醒龍帶來廣泛聲譽的是發表在《青年文學》1992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小說一發表,就好評如潮,很快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鳳凰琴》的推出,不僅使民辦教師群體受到關注,對當時全國兩百萬民辦教師轉正工作更是起到推動作用。民辦教師的處境和待遇,因為《鳳凰琴》而得到國家政策上的調整和改善,劉醒龍是有功之臣。這自然也是一部優秀文學作品所應有的社會價值。
后來,我還陸續編發過劉醒龍的其他作品,包括他榮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還有他很看重的長詩《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
劉醒龍的其他作品,我大體也熟悉。通過對劉醒龍作品的理解,梳理劉醒龍的創作脈絡,是一個值得琢磨的話題。
現在的劉醒龍,無疑是中國文壇上的一棵樹,一棵枝繁葉茂、果實豐碩的大樹。面對這樣一棵樹,人們往往想要了解這是一棵什么樣的樹。但是,這棵樹在文學叢林里生長了這么多年,它的紋理結構,它的姿勢形態,它的來龍去脈,不是靠簡單的評斷就能完成的。我在想,我們與其要說他是一棵什么樣的樹,不如去打量這棵樹為何長成如今的樣子。
一
劉醒龍開始發表作品的1984年,正值中國社會撥亂反正方興未艾之時,思想解放借助文學的社會影響力正如火如荼。新時期文學深孚眾望,突破一個又一個題材禁區,有力拓展著文學的表現疆域;各種國外的文學思潮,因應改革開放的情勢被翻譯介紹到國內,文壇正滿腔熱情掀起此伏彼起的喧嘩與騷動。劉醒龍創作一開始,就感受到了社會與文學桴鼓相應的這一濃烈氛圍。在創作題材不斷開拓和表現方式花樣翻新的前提下,隨之而來的是“尋根文學”的提出和深化,以及年輕的先鋒作家在敘述語言、文體革新上的試驗和探索。所有這些,無疑啟發了劉醒龍對生活本土的文化探尋,撩撥了他用直觀感受力彰顯文學才情的創作沖動。對生活本土的文化觀照和詩意化的文學感知,給劉醒龍早期的創作打上了本土情懷和先鋒姿態的烙印。而這兩者,從劉醒龍的創作軌跡和未來走向上看,可以說是理解劉醒龍創作發端的兩把鑰匙。本土的情懷和先鋒的姿態,是劉醒龍創作的兩條路徑,我們會在劉醒龍今后的創作中反復體味到它們的裊裊余音。
這一時期,劉醒龍創作的主要作品收在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異香》里。這部副題為“大別山之謎系列”的小說集,是劉醒龍20世紀80年代寫作的主要成果。在感染中、在感召中、在感應中,劉醒龍完成了自己的80年代寫作。這是劉醒龍的起步期、摸索期,也是他的先鋒期,準確地說,是他的文學初戀期。在這一時期里,劉醒龍感應的“本土”和“先鋒”,更多是情懷和姿態上的,是時代所裹挾,也是時代所點醒的。他順應著時代的文化潮流,但還沒來得及在潮流中識別自己。
很顯然,劉醒龍的創作實力還遠遠沒有被證實。
二
跨進20世紀90年代,劉醒龍的創作進入重要收獲期。以《鳳凰琴》《分享艱難》《挑擔茶葉上北京》等為代表的一批中篇小說受到廣泛好評,也因此奠定了劉醒龍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地位。這些作品以其堅固的現實質地,在一個時期被冠以“現實主義沖擊波”的說法。其實,這些作品最明顯的特征,也就是寫實。劉醒龍是90年代“底層寫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這些作品貼近大地,講述底層人民的生活,寫他們在貧困之中的人生努力和對新生活的向往,有一些貧寒中的幽怨,有一些困境中的自憐,但更多的是面對人生的堅韌不拔和意志上的執著堅定。這些作品雄辯地昭示我們:這是大地的力量,更是生命的底力。劉醒龍也因此步入了創作的井噴時期。除發表三十余部中篇小說之外,劉醒龍更是完成了《威風凜凜》《至愛無情》《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寂寞歌唱》《愛到永遠》《往事溫柔》等多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在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底層人物、小人物,是弱勢群體,是卑微者。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劉醒龍根植于大地、面向著現實的本土情懷和平民本色。這一時期,劉醒龍創作中堅固的寫實質地是那樣地醒目,人們被他筆下的現實所牽引,為他塑造的卑微者所牽掛,從而認定他是體驗型的作家,在地地道道地“寫實”,在寫“現實國情”。
其實,劉醒龍還有一副筆墨,這就是他的“寫意”。只不過這寫意是隱忍的、潛沉的,那是在寫實的內核深處沁出的、飽含悲憫而又苦澀的一份詩意和柔情。人們會依稀記得,在劉醒龍的成名作《鳳凰琴》里:清晨,在山村小學里,鄉村教師用笛子吹奏著《國歌》,學生們光著腳丫,在天寒地凍中升起國旗。貧寒之中的堅忍,幼小生命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躍然紙上,感人至深。劉醒龍把他的柔情和詩意,體現在他對物象的選擇和細節與細節之間的組織中,哀而不傷,含而不露。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他榮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中。小說中“冬茶”的寓意,無人細究。一年四季,到了冬天,生命的光亮就嶄露在那一抹茶尖上,它們凝聚了生命的能量,同時也是來年農家生計的指望。這樣的“冬茶”要被采摘,要被縣上的領導送上北京去,讓農人們翹首期盼著辦成公事后能帶來好日子。我在編發這篇作品時,直覺到作品里充盈著復雜豐富、一言難盡的內容。劉醒龍在物象上、在細節里,寄寓了深重的現實關懷和欲言又止的無限悲情。我們不能不嘆服劉醒龍對底層生活的實際擁有。只有曾經赤著腳走在寒冷的大別山山地上的人,才會生發出如此苦澀的詩意和如此悲憫的柔情。
現實的風骨和詩意的柔情,在劉醒龍20世紀90年代的寫作中,內化了、深化了他80年代的本土情懷和先鋒姿態。在這樣的轉寰中,劉醒龍確立了自己的創作重心,也為人們用文學的眼光打量社會現實平添了底力,找到了支點,調動了感受,引發了感動。這無疑是劉醒龍個人的文學發現,也因此感染了處境不一的其他人。所以我說,從本質上看,劉醒龍更是一位詩人,一位悲天憫地的詩人。
回首劉醒龍的90年代,我們還發現,90年代的中國一門心思搞經濟建設,抓市場經濟;劉醒龍則憋足勁,在全力寫實,在堅固的現實筋骨和詩意的個人柔情中寫實。
這是劉醒龍的“寫實期”。
三
進入21世紀,國家的經濟建設走上了快車道。第一個十年過去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而這一時期的劉醒龍在忙什么呢?他在用大部分的時間,寫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就是《圣天門口》。書名很歐化。“圣天門口”,實為“圣·天門口”。劉醒龍要把“天門口”這個地方“史化”“詩化”“圣化”。他在“天門口”上要凝聚起20世紀初以來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社會風云和世間煙雨。為此,他花了足足六年的時間邊琢磨邊寫作。我個人以為,《圣天門口》是劉醒龍迄今為止最用心、最得力的作品。在劉醒龍以往的作品中,他特別擅長抓住一個一個的現實物象和生活細節來體現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領悟。如今,在《圣天門口》里,現實物象變成了一個地域的所在,而生活細節變成了近一個世紀的風云煙雨。劉醒龍開始了屬于他自己的宏大敘事。
面對一個他以為“圣”的地域上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革和人生命運,劉醒龍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和組織。他選擇了兩個家族的興衰存敗,組織了一干人等的悲歡離合。他在選擇和組織中,展現自己對歷史、對人生的理解,包括他所認識的社會和政治。在展示這些剛性的社會存在和命運走向時,他還盡情綻放他以前內隱的詩意和柔情。比如書中大段大段的、一片一片的主觀性駐留和舒緩式吟唱,比如他對純樸勞動的禮贊,對愛情的抒懷,對生命的吟誦,等等。而意味深長的是,小說的主體部分放在了中國現代的鄂東,我們知道從這里走出了無數的革命者;小說的副線,則是20世紀70年代才在中國鄂西發現的漢民族文化史詩《黑暗傳》。《黑暗傳》在小說中的穿插和呼應,是要讓現代的“鄂東”具備更為開闊、更為深邃的時空。劉醒龍的確是在寫一部史詩。《圣天門口》獲得了廣泛的反響,“風骨與柔情”更加鮮明、完整地體現在劉醒龍的創作中,成為劉醒龍的個性化標識。
吊詭的是,這樣一部自己以為、他人也認為的史詩性作品,最終還是與當期的茅盾文學獎失之交臂,據說只為一票之失。而在中篇小說《鳳凰琴》基礎上續寫的長篇小說《天行者》,則在下一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榜上有名。看來,劉醒龍的“史詩”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來解讀。而眼下,人們對劉醒龍最鮮明的印象,還是以《鳳凰琴》為代表的“寫實期”里的“寫實”。作為當年《鳳凰琴》的責任編輯,竊以為,《天行者》能榮獲茅盾文學獎,這是對劉醒龍20世紀90年代寫實功績的一次反哺。
這是劉醒龍的“史詩期”。
四
臨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劉醒龍的個人文化生活里,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事是,他由一位專業寫作者,成了《芳草》文學雜志的主編;一件事是,他寫起了毛筆字。他辦刊物,辦得很有特點和個性。打開《芳草》,有這樣八個字:“漢語神韻,華文風骨。”這是劉醒龍定下的辦刊宗旨。而劉醒龍的書法,圓潤墩實,自有法度。筆畫結構上不求規矩,而通體看來卻心力充盈,氣韻貫注。劉醒龍的生活顯然在“人文化”。劉醒龍的創作也步入了“人文期”。
“蟠虺”是一個不常見的詞匯。讀音要正確,得查字典,而了解它的含義,要上百度。“蟠,音盤;虺,音毀。蟠虺,意為屈曲的小蛇,是青銅器飾物形象之一。”劉醒龍自己是這樣介紹的。“蟠虺”這兩個字是劉醒龍新長篇小說的書名。從現實物象和生活細節,到現代地域上的社會變遷和個人命運,再到遠古與當今從物質到精神上的關聯,劉醒龍的創作走出了一條從表及里、由淺入深、從今到古層層掘進、不斷深化的創新之路。
選擇“蟠虺”兩個很生僻的字作為長篇小說的名稱,自有劉醒龍的用意在。“蟠虺”是國之重器“曾侯乙尊盤”上的飾物,小說圍繞著這一重器在當今的遭遇展開。一件古老的器物,能與今天發生聯系,在于今天人們欲望的過度膨脹。正因為是國之重器,權重者就想據為己有,護佑自己飛黃騰達;而謀利者,則不擇手段,變本加厲。于是,圍繞著對“曾侯乙尊盤”的爭奪,就上演了一出多方勢力參與、各種利益糾纏的鬧劇。如何仿制,如何以假亂真、以真亂假,又如何護住神物,引出了盜墓者、仿制者、不法商人、青銅器鑒定專家和大小官員的好一番你爭我斗。直到青銅器權威曾本之把真正的“曾侯乙尊盤”放進了省博物館,這場戲方才謝幕。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情節性很強的小說。劉醒龍沒想寫出一部關于知識分子的小說,他有意回避了有關青銅器的一些專業問題,而是著力呈現道德滑坡、欲望橫行的現實情形,從而提出了人如何自持和把守的話題。《蟠虺》的扉頁上印著這樣兩行字:“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與“蟠虺”相較,“時務”更能讓人耳熟能詳。而“時務”出現在這部小說中,恰恰是“蟠虺”的反義詞。在今天,我們的現實是太過于“時務”了。這個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劉醒龍為什么要用“蟠虺”做書名,是因為這兩個字我們太陌生了,就如同我們心目中的正義感、道德感已然生疏一樣。劉醒龍無疑是在借這兩個生僻的字警醒世人,同時也是在喚醒我們心目中對神圣、對崇高的敬畏和尊崇。
《蟠虺》有很好的立意,這是劉醒龍的現實思考所得。我個人不大滿足的是,作品的重心是用說事來彰顯立意,而沒有更在意去如何塑造人物。讀《蟠虺》,我總感覺劉醒龍與他筆下的人物存在著一些隔膜,如果我們能適意地走進這些人物的內心,就會產生更多的共情。
五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劉醒龍的寫作,像是在精心制作一架風箏,并在傾心放飛著。這架風箏隨著天空中的氣流和風力在上下騰挪、左右抖動。他把它放出去收回來,收回來再放出去,含辛茹苦,樂此不疲。直到有一天,他陡然意識到在收放之中,還有扯動線繩的那么一雙手的存在。正是這雙手在不動聲色的牽引中,源源不斷地傳遞出秉性和風采、風骨和柔情。這雙手其實就是故土。
很多年前,同樣出生在鄂東這塊土地上的著名詩人聞一多曾經這樣評價先賢莊子:莊子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在尋求真理,毋寧說是在眺望故鄉。聞一多說莊子時,不知道有沒有夫子自道的成分,而此時的劉醒龍著實是開始了對故鄉本土的深情回望。在回望之中,他感受到了刻骨銘心的痛楚和牽扯,他寫出了《抱著父親回故鄉》的著名散文。隨后,他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黃岡秘卷》。
劉醒龍回望故鄉、重返故土,開始了他文學創作的“重寫期”。
重寫,是對作家在現有創作前提下獲得全身心觸動后的形象表述。它不是顛覆、推倒重來,事實上不同的年齡階段、不同的生活處境,都有其他時段不可替代的感受內容。它也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深化和升華,需要有不斷增厚的人生積累和生命感觸,更要等到一個特定的觸點,找到一個難得的契機,過去已有的一切才會被喚醒、被洞穿,才會有深入骨髓的牽扯和撕裂,才會有靈魂出竅般的回瞻和反顧。這就是創作意義上的重寫。我們從大量的創作經驗中發現,盡管文學作品的外在表現深淺不一、形態各異,但作家每一次明顯的創作進步,往往是基于新的經驗和認知上的回望,其實更多是重寫之功。
劉醒龍也不例外。按我個人的理解,劉醒龍的創作,至少經歷過兩次的重寫。起步時期,他從故鄉本土出發,受到時代文化潮流的觸動,隱隱感應到自己生長生活的土地有一種“異香”的奇特存在。他沒有來得及給這種“異香”找到更多的生活實感,但它是劉醒龍對生活本土認知在個人情懷上的最初發動。這里有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的成分,可謂是氣血之作。在寫實時期,劉醒龍直接面對生活本土中的社會現實,從現實物象和生活細節著眼去呈現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這是他的第一次重寫,意在感應、感召的前提下寫出真相和事實。劉醒龍的文學功績由此生成。在史詩時期,他的著眼點是歷史與現實的血脈關系,這是他的第二次重寫,是對生活本土的來龍去脈進行重新體認。而到了目前的回望和重返時期,劉醒龍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重寫。他結合了感應、感受和感念之上的層層遞進,在氣血相應、血肉相連、血脈相系的基礎上,用切身的感思感懷去寫與本土的血緣親情,寫出一塊土地的血質和血性。一路走來,劉醒龍真正開始審視安身立命的故鄉本土,探究它的本真和秉性。
在長篇小說《黃岡秘卷》里,劉醒龍依舊在使用自己的獨門絕技:他把現實物象推到前臺,做出特寫效果,這便是人所共知的“黃岡秘卷”;他把生活細節推向歷史縱深,要寫出充溢在故鄉本土上的人的品格和精神,這是另一部為人所不聞的“黃岡秘卷”。
現實中的“黃岡秘卷”太有名,這么多年參加過高考的很多學生都做過“黃岡秘卷”。提到黃岡這個地方,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它是“黃岡秘卷”的出生地。可以說,“黃岡秘卷”是當下人們認知黃岡的最鮮明的標識。小說從“黃岡秘卷”寫起,很容易拉近讀者與敘述本體的關聯。這是劉醒龍在敘述策略上的考慮。而劉醒龍想讓人們真正認識的卻是藏在這張名片身后的另一部博大精深的“黃岡秘卷”。
在我看來,《黃岡秘卷》的最大價值,在于對父輩祖輩人生經歷的回望,和在回望中對一方土地氣質品格的揭示。一個人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生活積累和人生閱歷,才有可能通透地理解他人的人生價值和生命意味。作品寫到了劉家大塆、林家大塆在社會變遷中的命運遭際,寫到了“我們的父親”“王朤伯伯”等的滄桑經歷和堅定不移的信念操守。與劉醒龍的其他作品所不同的是,《黃岡秘卷》是從血緣親情上切入,其所流露出的情感也就更為貼切、深摯。歷史的外在呈現總是變動不居的,而潛藏在歷史心靈深處的基因、血脈,從來都在生生不息。家國民族也從來如此。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更為包容、更為通脫地去看待、去發掘。從這個意義上說,劉醒龍對故鄉本土的重寫,實際上是對一方土地上的人生努力的重新發現和闡釋,是對專屬于一方土地的性格秉性和精神氣質的張舉和重塑。因此,《黃岡秘卷》中對“我們的父親”等的形象塑造,可謂是我們理解歷史認知傳承的一個典型文學范本。就劉醒龍的創作而言,《抱著父親回故鄉》完全可以與《黃岡秘卷》互讀,前者可視為后者的導讀和索引。
六
經過三十多年的創作實踐,劉醒龍讓自己長成了一棵樹。這棵樹露出地表后,輕盈自在地沐浴著陽光雨露,感受著文學森林的微風細浪。這棵樹長得真是地方,那里山清水秀,文脈綿長,而且由于地處偏僻,生活貧困,它得以不受侵擾,自然生長,機敏早熟,自有風骨。路過森林的人,很容易辨識出這樣一棵樹。這棵樹應運而生,與勢俱動,漸漸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在這一天地里,有山村,有大塆,有天門口,有界嶺小學,有茶園,有鄉村教師,有村支書,有五駝子,有貧寒和清苦,有塵世煙火氣。出現在情景之中的,都是些生活在底層的普通人,他們身份低微,生活困窘,卻執拗不屈,剛直不折。這一方天地,呈現出一個不發達地區百姓生活的現實圖景。這樣一個現實圖景,引發了不同生活處境的人們的內心觸動。在展現這些現實的生活場景和生命內容之后,這棵樹把根須探入更深的泥土里,要去領略歷史的厚重,探尋一方天地的生存秘密。它用功甚勤,用力甚猛,讓不明究里的人多少有些詫異。它當然也感受到了身邊涌動的浮塵躁氣,它甚至索性要翻出一件久遠的藏品,看看它在今天現實中的成色模樣和相較之下的世道人心。等到把這些都做好了,它發現有一件細小微弱的物什在不經意扯動自己的心臟肺腑,它用自己特有的靈敏感觸知曉了那是故土伸出的一雙手。這雙手綿柔無力,且斷且續,似有若無,但從來沒有在某一天里顯得這么強橫剛硬,直把人逼迫到生命的出處。從本土出發的風箏飄得再高遠,總有會伏在地上憩息的時候。用劉醒龍自己的話說:再偉大的人回到故鄉都是孫子。故鄉不僅是故鄉,鄉土不單是鄉土,這是人生出發地,更是精神再生處。與其說劉醒龍在長成一棵樹,不如說他在不斷鍛造、提煉一棵樹所應擁有的魂魄和精神。
三十多年來,這棵樹隨著生活場景的不斷變化,用感知和覺悟去迎候著新的生活內容。它從來沒有放下跟隨時代和生活的腳步,并且在不斷刻下清晰可辨的年輪。它接納著一方天地的萬千氣象,因應著浮塵俗世的煙火氣息,傳遞著生命綿綿不斷、生生不息的那一束束星火光亮。
劉醒龍用一棵樹的站立姿勢,見證著風過雨去、人來人往。
他就是這樣的一棵樹。
(李師東,中國青年出版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