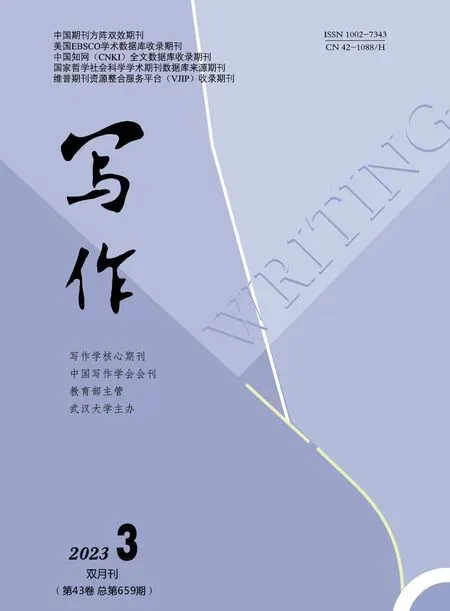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挑戰
覃 才
人工智能的文本化是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之一。2017年,會寫詩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小冰”的誕生及其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的出版,引發了人們對機器寫作的關注和對機器寫作與人的寫作的倫理思考。2023 年初,會寫詩、寫論文、寫方案及編程等更先進的人工智能機器人ChatGPT 火爆全球,大有以“ChatGPT 時代”的趨勢,構成對傳統寫作的顛覆。不能否認,在人工智能正當其時的技術共同體時代,人工智能“文本化”呈現了人的寫作之外的另一種寫作形態與可能,并“在文藝觀念、創作格局等方面,對人類的傳統創作提出了挑戰”①楊守森:《人工智能與文藝創作》,《河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作為相對于人(作家)的寫作和相對于人的文學之外的寫作類型,人工智能寫作顯然既給文學寫作帶來相應的幫助或改變,又可能成為引發文學寫作危機的導火索。從主體上看,人工智能依附的是技術,少數民族文學依附的是民族,這是兩者存在根源性的區別。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雖然在受到相應的人為設定和控制之后,能夠呈現具有民族元素、民族特征的作品,但其寫作主體、寫作語言及寫作情感都異于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它巨大的文本生成量和存在的問題、爭議,似乎反過來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合法性、經典性及價值性的挑戰。人工智能對少數民族文學(或者說是中國文學)的影響,總體上表現為技術構成的文學對作家文學的否定。這個存在可控性但又有技術自主性生成的文學類型,實際上能夠快速地生成“像但不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品,它的出現及構成的技術性文學空間,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的沖擊與挑戰。
一、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合法性”的挑戰
人工智能是“用人工的方法和技術在計算機上實現智能,以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的智能”①佘玉梅、段鵬編:《人工智能原理及應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該領域的研究與運用主要展現為“機器人、語言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專家系統等”②曾凌靜、黃金鳳主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導論》,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7頁。。“文本化”(即人工智能寫作)是人工智能不算非常復雜的應用領域。在國外,計算機程序“雷克特”1984生成的《警察的胡子是半成品》一書開啟了人工智能文本化的首次試驗,2008年俄羅斯圣彼得堡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部人工智能長篇小說《真愛》預示著人工智能寫作合法性的建立③陳奇佳、徐陽:《AI藝術創作的理論構想——以文字敘事算法研究為例》,《藝術學研究》2022年第2期。。在中國,微軟人工智能框架“小冰”(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2014 年發布)在學習20 世紀20 年代以來519 位中國現代漢語詩人的詩歌作品的基礎上,出版了自己創作、自己起名的現代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年版),成為中國第一個人工智能詩人。在“小冰”之后,人工智能“小封”“九歌”“秘塔寫作貓”“一葉·故事薈”等寫作機器人、程序及平臺繼續拓展著人工智能“文本化”(即人工智能寫作、機器人寫作、程序寫作、軟件寫作等)的進程。從寫作的主體性身份上看,這些能夠自己寫作甚至是替人類寫作的人工智能機器人、程序,它們明顯有人類作家身份意義上的人工智能作家身份,但它們在“文本化”過程中表現出的主體兼容性和不確定性又構成了對人的文學寫作的最大解構。在多民族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屬性及其特征具有明確的界定,那就是作家的少數民族身份是決定少數民族文學屬性的本質要求,這是少數民族文學“合法性”的本質決定因素。當下及未來的人工智能寫作無論怎么設置成少數民族文學,但它在本質上不是有民族主體性的少數民族文學。這顯然構成了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挑戰,引發了新思考。
從本質上看,表現為機器人、程序的人工智能寫作,其最大特點是寫作主體的不確定性或兼容性。這與強調寫作者是少數民族身份的少數民族文學的確定性、必然性是矛盾的。因為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無論多么像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的作品,寫作主體都不可能是那個人或那個民族。人工智能寫作的主體可以是任何一個人和物種,甚至也可以是地球之外的某一物種的一員。這是人工智能寫作主體不確定(或者說是缺失主體)但又可以是任何一物或對象的最大優點和問題。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寫作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寫作主體性諸多方面的挑戰,大致表現為:“一、人工智能寫作必然會沖擊作家的寫作主體性,這個判斷會愈發地被技術的不斷發展所驗證;二、人工智能不會具有寫作主體性,只會作為人的寫作主體性能力的延伸;三、人工智能技術為寫作主體性賦能,并使得主體之間的寫作能力邊界發生‘內爆’。”④張強、王超:《人工智能時代的寫作主體性位移》,《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5期。基于少數民族文學界定標準,當下及未來的人工智能寫作,無論人類怎么將它的數據、算法及語言設置成符合少數民族特點,它表現出的技術主體兼容性和不確定性都會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及其創作的否定與挑戰,即“從文學傳統、文學本體以及文學所表達人心隱微曲折的心理活動等方面來看,人工智能尚不能置換人的主體意識,故而人工智能之創作有其不可跨越的鐵門檻”⑤汪春泓:《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三思》,《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首先,人工智能寫作導致了少數民族文學族裔身份的模糊。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人工智能與人類合作的‘人一機’間性主體初現,給人類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①畢日生、宋時磊:《人工智能文學寫作“作者”問題之思》,《寫作》2020年第3期。,然而,在我們當下所處的技術共同體時代,我們已經慢慢感受到人類寫作“已無法以‘限度’之名逃避與人工智能‘作者’的競爭,寫作的主體性問題進入反思領域”②劉欣:《人工智能寫作“主體性”的再思考》,《中州學刊》2019年第10期。,因為人工智能的本質是無法量化的數據及其無限迭代的算法。在人工智能文本化過程中,人工智能數據和算法的無限迭代結果,雖然“文本化”生成了文學寫作的語言,并且能夠在一定關鍵詞或主題的設定下形成相應的作品。然而,人工智能文本化表達和作品本身存在著一個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形成的表達或作品是“誰”的?如果人工智能接受的數據是相應量的少數民族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其文本化的結果可能像其中的某個人,也可能像所有人,抑或是誰也不像。在此,我們看到了人工智能文本化后寫作者不確定的大問題,即傳統意義上的“作者之死”(羅蘭·巴特語)和“什么是作者”(米歇爾·福柯語)等寫作主體問題。如前文所述,少數民族文學最本質的屬性是作家具有少數民族的身份。設置為少數民族的人工智能寫作,其主體性的缺失,對少數民族文學所構成的最大挑戰顯然就是對其族裔身份的模糊。
其次,人工智能寫作會對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關于民族與地方的文化書寫產生混淆。無論是從空間還是從地域(地理)知識上看,少數民族文學的寫作無疑表現出明顯的關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特征。透過這種文化書寫的外衣,我們能夠剖析出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在寫作過程中是處于個體的作家身份、民族身份及其地域的一體性關系中的。每個少數民族作家的文本寫作和情感(思想)表現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關于民族和地方的一體性關系。人工智能寫作可以輸入某個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所有作品或某個少數民族的所有資料,然而,也應該看到:“從人工智能生成文學作品的方式可以看出,人類文學是目前人工智能文學的摹仿對象與學習材料,因此評判人工智能文學好壞的參考標準也來自人類文學。以人類文學的標準對目前的人工智能文學進行評價,后者仍是不成熟甚至失敗的。”③陶鋒、劉嘉敏:《文心與機芯:中國古代文論視閾下的人工智能文學》,《文藝爭鳴》2020年第7期。這就是說,人工智能像所有人但又不是所有人(像某個民族但又不是某個民族)的主體不確定性,決定了它最終呈現的文本化結果不可能是某個人或某個少數民族的。因而,它關于某個民族與地方的文化書寫,自然也不能完成等同于我們所設定的某個民族和地方。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看到了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關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的混淆。
最后,人工智能寫作導致對少數民族文學與國家的共同體關系的解構。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指出:“語言既是國家事務(民族語言也是一種政治目標),也是文學‘物質’,文學的資源必須在民族的籬笆內產生,至少在創立階段是如此”。④[法]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文學世界共和國》,羅國祥、陳新麗、趙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在多民族中國,文學與國家有著非常深的共同體關聯(歷史、政治等)。近代以來,表現為詩界革命、文學革命的白話文學運動以語言(與傳統斷裂的白話文)的形式表征了文學與國家的共同體關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文學寫作格局(主要指書面文學)的確立主要得益于漢語和漢字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普及。在掌握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之后,少數民族作家表達了他們自身及上一輩對新中國的共同體想象與關聯。這就是少數民族作家及其文學寫作非常明顯的國家特征和政治特征。對于當下及未來的人工智能寫作,雖然我們可以將某個少數民族和所有少數民族的情感(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數據輸入其中,并進行相應的迭代計算,但在文本化過程中,誰也不能保證它得出的作品能夠合宜、恰當地反映某個少數民族和所有少數民族所認為的文學與國家的共同體關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但又不能真正地反映”某個少數民族和所有少數民族的共同體表達,顯然解構了少數民族文學與國家原本真摯的共同體關系。
其實,無論我們怎么強調人種、國別、地域及族裔的差異,寫作或者說作品都是由“作者”這一主體來完成的。然而,從遠古時代到當下技術共同體時代,我們熟知的“作者”這一主體不僅有其歷史性的發展過程,而且它還發展到了我們想不到的一個新的階段。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一書中,凱瑟琳·海勒對這個“作者”(或者說是文本的敘述者)有非常清晰且新奇的解釋。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文本“作者”(敘述者)無論是在哪個時代都是存在的,但在人類從遠古時代到當下技術時代的發展過程中,這個“作者”(敘述者)是一直在變化的。按海勒的觀點,自人類誕生以來,我們現在理解的“作者”(敘述者)或是寫作主體實際上經歷了“講述者”“書寫者”及“電子人”三個歷史性的變化。“講述者”是人類在沒有書寫文字的時代的“作者”形式,在這個時代,所有作品都由講述者口頭創作,并由其家族或徒子徒孫以“人傳人”形式傳承。“書寫者”是人類進入書寫文字時代之后的“作者”形式,作品是由那些會書寫的“作者”完成的。“電子人”就是技術共同體時代中,作品由人工智能這個“電子人”創造和完成的①②[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0頁。。其實,作為技術共同體或是海勒所強調的“后人類”時代中的一員,我們所理解的“作者”無疑是在慢慢經歷著“作為一系列推動新型主體性的裂變和位移而存在”②。在當下(也可能在未來非常長的時間內),這種主體的裂變或位移實際上就構成了人工智能寫作主體的缺失問題。因而,公允而言,相對于擁有少數民族身份的“講述者”與“書寫者”,身份未知的“電子人”,它的少數民族文學生成顯然就不是一種“合法化”的少數民族寫作。
質言之,作為具有中國民族特征的文體類型,民族身份、語言、題材是少數民族文學文學屬性及其特殊性的三項基本標準。這三項標準中,民族身份是少數民族文學合法性的本質屬性,民族語言和題材可能二者都有、二者有一或二者都無。當下及未來的人工智能寫作,無論怎么將寫作目標設置為少數民族文學,它自身展現出的主體不確定性和兼容性,決定了它不可能是某個少數民族或所有少數民族。這決定了“像少數民族”但又“不是少數民族”的人工智能寫作,存在對少數民族文學族裔身份的模糊、對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關于民族與地方的文化書寫的混淆,及對少數民族文學與國家的共同體關系的解構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是當下及未來人工智能寫作“對人類作者在文學創作中的主體地位發起挑戰”③周建瓊:《人工智能寫作背景下作者主體性的消解與重構——以陳楸帆人機交互寫作實驗為中心》,《當代文壇》2021年第4期。,也是其對少數民族文學“合法性”的挑戰。
二、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經典性”的挑戰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學界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編寫各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對這個相對年輕且沒有得到很好挖掘的文體類型,中國學界產生了諸如“某個少數民族沒有代表性的作品”,或是“少數民族文學沒有代表性作品”(主要指書面文學,不包括經典化的民間口頭文學)等爭議論斷④董迎春、覃才:《論少數民族詩歌的族性本體、文化書寫及共同體價值》,《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這些爭議論斷,實際上指向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在自身民族文學空間、少數民族文學空間及中國文學空間中“經典性”缺失的問題。就文學的本質而言,“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意味著在一定空間內某個作家及其作品足夠優秀、足夠突出,一定程度上具有我們公認超出其他作品的獨一無二屬性和開拓性。這種“獨一性”和“開拓性”是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之所以被稱為經典的倫理依據。而基于算法和語言處理水平的人工智能寫作,實際上是“一種基于龐大數據庫和海量范式樣本,依據人所給定的主題詞匯或圖片信息,進行文字重新拼接組合的寄生性繁衍和組裝型生產”①錢念孫:《文學的淺涉與深耕——對人工智能寫作的認識》,《群言》2020年第7期。的寫作,它無論學習多少體量,其最終呈現的是所學習體量的“平均水平”作品。換言之,人工智能生成的“平均水平”作品明顯與少數民族文學急需建構自身“獨一性”和“開拓性”的經典之作愿望相背離,它的出現構成了對少數民族文學在不同文學空間中“經典性”的挑戰。
文學寫作于作家而言是一項有抱負的事業,創作能夠躋身世界文學殿堂的經典作品(傳世之作)是每一個作家夢寐以求的事情。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在民族地域和整個國家文學空間的經典化過程,雖然受政治、現實、際遇等影響,但本質上離不開作家本人對寫作這門手藝持之以恒的摸索。這種摸索是決定少數民族作家獨特風格和開拓意識形成的關鍵,也是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經典化的基石。人工智能寫作的特征是快速生成和輔助性,但無論它怎樣建構這種速度和輔助性,它自身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即它不管怎樣“試圖最大化地模仿、接近人類,但仍然與人之間有著根本性差異。受到操縱的人工智能寫作就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特定的寫作意圖,而寫作的主動性、主體性、獨特性自然無法得到保障,而后者卻是文學最能體現作為主體的人的意志和力量的根本性所在”②李保森、張靜超:《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契約的重建》,《藝術評論》2019年第10期。,這種真實矛盾在本質上決定了它及其生成作品基本上是“平均水平”的作品。顯然,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本質上表現為它所輸入(學習)的經典作品、一般作品及差的作品的“平均化”處理,這種“平均水平”作品在本質上很難反映作家寫作的精英性和對作品的經典性追求。也就是說,無論是少數民族作家借助人工智能寫成的作品,還是純粹由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少數民族文學文本,它一經出現,傳統少數民族作家群就表現出不接受的態度,這種情況就從最底層的某個少數民族文學空間之內,阻隔了其“經典化”的路徑。就此而言,在技術的自主性和可能的控制性之間,創造“平均水平”少數民族題材文本的人工智能寫作破壞了作家與自身民族地域和國家文學空間的經典化契約。
在技術共同體時代,人工智能寫作網站或平臺的文本生成很簡單,只要在操作界面輸入相應的限定要求,作為結果的文本很快就會產生。對于這個模式化地快速生成的文本,是很難從中找到人類文學寫作所保有的文學性的。這種沒有文學性的寫作,自然就難具備成為經典的可能。其實,就人工智能寫作而言,無論對它進行怎樣的少數民族性設定,它所呈現的具有少數民族元素但不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文本,在本質上決定了這種寫作不是真正的少數民族文學寫作。它所生成的文本,要么只能作為少數民族作家寫作的輔助性文本,要么與現實中漢族作家的少數民族題材作品相近,只是一種民族性表達但本質上不是少數民族文學。就此而言,對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像但不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文本,無論它的總量多大,也無論它對少數民族作家的寫作有多大的輔助,都無法經典化。在技術共同體時代,人工智能“這種崇尚‘技術’的寫作方式在改變文學精英屬性的同時,也使文學走向‘非經典’的窠臼”③楊丹丹:《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新變》,《藝術評論》2019年第10期。。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人工智能寫作(特別是最新的ChatGPT)的確有輔助作家和與作家“融合共進”的可能,但當作家“將他們自身的生命力——移動、體驗、勞動和思考的能力——輸入到他們制造的裝置中,他們體驗到的這種生命力,就成為某種無關的、疏離的、從別的地方返回自身的某種東西。以此方式,“人們的生命體驗就完全變成間接性的了。它還常常令人感到非常詫異”④[美]蘭登·溫納:《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楊海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頁。。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它的確是可以很快地生成近乎無限的關于少數民族題材文本,但它的特征只是有少數民族文學的一些元素、只是像少數民族文學,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文學。這個巨大的“像但不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文本體量,不僅自身能夠構成一個人工智能的文學空間,并且這個空間還可以與其他文學空間交集。這個可以靠近其他文學空間的技術文學空間(即人工智能文學空間),在“合法性”(不是少數民族作家完成)缺失的情況下,顯然無法推進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化”。
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米蘭·昆德拉順著波蘭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我的重量取決于地球上的人口數量”的玩笑,說出了一個非常符合當下技術時代的觀點。他說,從人口數量來看,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前460—前370)的重量是人類的4億分之一;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約翰內斯·勃拉姆斯(1833—1897)是10 億分之一;20 世紀的貢布羅維奇(1904—1969)就只有20 億分之一:作為個體的人(即我)變得越來越“輕”①[法]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尉遲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頁。。這是對當代文學非常有預見性和與眾不同的判斷。他從人口數量層面說明了文學(也包括其他人文藝術門類)在人類延續過程中越來越“式微”的原因。以前,我們總是懷念某個文學或藝術的黃金時代,并探討它形成與衰落的原因(經濟、物質及社會的發展等多個方面),但少有考慮人口數量的問題。然而,在當下的技術共同體時代,80 億的世界人口不僅明顯地讓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輕盈”的個體,還在另一個層面上回答了文學衰敗的原因。簡而言之,我們號稱進入到了全民寫作的時代,但人的寫作與機器的寫作顯然不在一個量級上。人工智能寫作無限量級的文本化,顯然會減少只有80 億分之一的“少數民族作家”的重量,還會在文學空間中將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化的可能降到更低。
如歷史所示,文學的演進是沒有齊頭并進的,它在整體的進步與上升過程中,總是表現出邊緣與中心的參差不齊狀態。有些地方或民族發展迅速,有些地方和民族落在后面。對那些自古以來文學傳統弱、文學資源少,并且當下特別需要代表性作家或作品來實現文學進步和文學突圍的民族而言,人工智能創造的“平均水平”作品,不僅很難助推這些民族之內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產生,也很難推動這些民族的文學進步、文學突圍及自身文學空間之內的“經典化”。劉忠波指出:“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寫作以超速、大量、不停歇為基本特征,可以實現便捷化、大眾化、低廉化的寫作生產。”②劉忠波:《人工智能寫作意味著什么?——人工智能時代的寫作主體問題》,《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現實證明其論斷是中肯的,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生成顯然是一種“平均水平”的寫作,這與精英寫作及其最終構成的經典性文本有本質的差異。這就是說,人工智能寫作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起到增殖少數民族文學文本的作用,但它的出現也在破壞少數民族作家及其作品的精英意識和認可度。在少數民族作家及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這種民族屬性的非精英意識和認可度的“稀釋”顯然構成了作家群體和批評界對少數民族文學新的批評與否定。在少數民族文學急需建構經典性的階段,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生成明顯無法擔負這項使命。
三、人工智能寫作對少數民族文學“價值性”的挑戰
在當下最大的技術共同體現實加持之下,人工智能無疑正當其時。特別是在與所有人相關的后人類時代,我們頭頂的衛星與手中的二維碼使政府實現了對個體的網格化定位。在這個陸地、天空及太空的技術一體化世界中,技術仿佛去掉了人的身份、民族及國家的屬性,我們的存在只是地圖上的一個“點”。在技術共同體的現實中,人類對人工智能文本化的好奇與探索,本質是想看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文學樣態,它所生成的作品能給人文學帶來怎樣的改變。時至當下,這種改變還未見定論,但它引起的對文學寫作倫理與價值的思考卻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一層面,人工智能寫作構成了對文學固有價值的挑戰。
只要在人工智能機器或程序上嘗試一下,就會發現人工智能文本化給寫作帶來的好處與便利。可以說,只要數據足夠豐富,無論想得到哪個民族、哪個國家題材的作品,人工智能多少都不會令人失望。換言之,在技術共同體的時代,人工智能在文本化方面是無限的。然而,這個無限、全能的人工智能到底給人類寫作會帶來什么。基于人類文學從傳統寫作到創意寫作的發展趨勢,我們似乎在人工智能身份/去身份、民族/去民族、國家/去國家的文本化過程中發現,它似乎只具有商業化價值。人工智能文本化過程表現出的兼容性、快速生成性、輔助性,催生了它具有的參與和協助所有類型寫作的特性。這就是說,從機器倫理和合法性上看,人工智能最大的價值是它的商業應用前景。在民族層面上,只要給人工智能輸入足夠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在需要相應的民族性表達時,人工智能就會呈現相應的文本。這個像但不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文本,顯然能夠幫助少數民族作家進行相應的寫作,特別是那些具有商業性、應用性的寫作,但它也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價值性的挑戰。
第一,人工智能對少數民族文學具有的文學性價值構成了挑戰。文學是人的文學,同時也是語言的藝術。它的文學性價值,既表現為人的情感抒發、存在追問及世界本質思考,又近乎不變地表現為讓人看了就覺得是文學的語言。作為一種文本類型,少數民族文學是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對個人、民族、國家及世界之本質的思考,語言是其抵達這種思考、呈現這種思考,并引起他者共鳴的方式。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學性價值就縈繞在作家、語言及他者之間。在技術共同體時代,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像一個“游戲”,誰都能很輕易地獲取,但卻難以感受到想要的那種文學情感、文學語言。“從文學創作的理論層面來說,人工智能寫作缺乏人類所特有的語言邏輯思維和情感投射功能;從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來看,其拼貼性、雜糅性、模仿性較強,而邏輯性、情感性、空間層次感大多較差。”①雷成佳:《人工智能寫作與文學體認的含混》,《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20年第4期。也就是說,這個數據與算法性的民族元素文本,缺少了人的文學具有的文學性,即“人工智能的運行機理決定了其只能以形式邏輯的方式把握世界,只能從現有人類文學創作的素材樣本中進行模仿學習,所謂‘創作’只是文字符號的篩選與排列組合”②趙耀:《論人工智能寫作的可能與限度》,《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7期。。在技術共同體時代,時時離不開技術(如在哪里都可掃碼支付)的人類已經患上技術便利之“癮”。人工智能的少數題材文本化作為寫作的便利(輔助),對可能面臨文學想象疲憊期、文學探索瓶頸的少數民族作家顯然是有吸引力的。然而,這種仿真的文學性和文學語言表達的危害也是作家需要提防的,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人工智能寫作具有的“在倒逼人類寫作,人類除非寫出更好更有原創性的作品,否則被取代和淘汰是遲早之事”③楊慶祥:《AI寫的詩可以成為標準嗎?》,《南方文壇》2019年第6期。的可能趨勢。
第二,人工智能對少數民族文學民族性價值構成了挑戰。對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而言,無論身在何地、具有怎樣的世界性身份與影響,無疑依然認同自身出生的那個小地方和所屬的民族。這是由少數民族的身份和民族的共同體催生的一種先驗性情感認同,在文學寫作過程中,這種特殊的情感認同會作為文學創作的資源潛意識蘊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間。少數民族文學具有的民族性價值就橫亙在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民族共同體情感認同之間。在約瑟夫·C.皮特所說的“技術是人類在工作”①[美]約瑟夫·C.皮特:《技術思考:技術哲學的基礎》,馬會端、陳凡譯,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前提下,人工智能寫作或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生成,雖然字里行間也有民族的元素,但在民族身份、民族共同體情感認同的缺失中,這些文本并不能切中少數民族文學民族性價值的內核。人工智能能夠看到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也能夠向其靠近,但始終無法抵達民族性的本質。就此而言,少數民族文學依附的是民族,人工智能依附的是技術與數據,這是一種無法逾越的溝壑。這種溝壑其實對應著學界一直存在的人工智能寫作有朝一日將取代作家的擔憂:“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一旦機器掌握了人類情感的大數據,并能夠解讀和表達人類情感的時候,作家這個群體,也將被機器人取代。”②陳建華:《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命運》,《長江文藝評論》2020年第1期。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以民族為本的少數民族作家及其文學似乎也無法改變這一命運。這種矛盾與未來可能構成人工智能寫作和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對少數民族文學民族性價值的本質挑戰。
第三,人工智能對少數民族文學整體價值構成了挑戰。在多民族中國,民族與國家的形成、發展有很大的政治性、歷史性關聯。在文學寫作中,出于對地域和未來的想象,少數民族作家很容易會將他們傳統、先驗的關于家庭血緣、鄰里地緣及精神文化的民族共同體情感上升到國家層面。這種民族認同情感與國家認同情感的命運關聯,構成了少數民族文學具有的整體價值。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創造性的集體合作大生產和聲勢浩大的新民歌個體創作過程中,少數民族人民將自身傳統的民族話語、地方話語及鄉土話語與新中國的國家話語相統一的新民歌創作,既讓他們實現了從傳統的‘民眾’到新中國的‘人民’的發現,也鑄造了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實體”③董迎春、覃才:《少數民族“新民歌”創作與現代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生成》,《廣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少數民族文學在歷史和現實中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對國家認同的生成是其整體價值的顯現。雖然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工智能寫作實施控制和設定,但相對于有明確情感表達和意義指向的作家(人類),誰也無法明確這種技術自主性的文本化表達了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當然,誰也不能對此予以否定),這無疑呈現了技術在主體上的去整體屬性。換言之,這個可以“誰都是”又“誰都不是”的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文本,說它表達的是對某個國家的情感認同顯然經不起推敲,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寫作與人類寫作的本質是迥異的,前者看似自由轉換大數據,實質上只是編程規定內的仿制”④楊俊蕾:《機器,技術與AI寫作的自反性》,《學術論壇》2018年第2期。,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不具有多民族中國的整體價值。它生成的無限性,在本質上構成了對少數民族文學整體價值的挑戰。
綜上所述,作為具有中國民族特征的文學類型,少數民族文學在歷史發展中逐漸創造了自身具有的文學性、民族性及整體價值。這些價值體現少數民族作家個人對民族和國家的文學思考、文學認同。就技術本質而言,當下的人工智能寫作的思維“是程序控制下的思維模式,它具有識別性和最優選擇性,卻很難具有人的情感性和主動創造性”⑤安曉東:《人工智能寫作:何以可能與何以不可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月29日第4版。。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雖然能夠給予少數民族作家寫作的相應“便利”,但它很難定義人工智能寫作主體、寫作語言及寫作情感的確切情況,構成少數民族文學固有價值的潛在威脅。
結語
隨著人工智能寫作的到來,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類型之一,它顯然是能夠進行人工智能寫作探索的。人工智能依附于技術,少數民族文學依附于民族,這決定了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與少數民族文學有本質上的矛盾與區別。少數民族文學的合法性是由作家的民族身份來界定的,人工智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的技術主體性,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族裔身份的模糊,對少數民族文學表現的關于民族與地方的文化書寫的混淆,對少數民族文學與國家的共同體關系的解構。少數民族文學一直在尋求建構自身經典性的可能,人工智能表現為快速生成和輔助性的少數民族題材文本化,雖然能夠為少數民族文學生成無限的文本,但它最終呈現的“平均水平”的寫作,不僅很難在少數民族文學空間、國家文學空間及世界文學空間中建構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性,還在很大程度上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經典性的解構。人工智能寫作數據與算法性的民族元素文本,在文學性、民族性及整體價值層面上構成對少數民族文學價值的挑戰,這是當前技術共同體時代中人工智能寫作給少數民族文學繪制未來藍圖的同時,對少數民族文學寫作與發展構成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