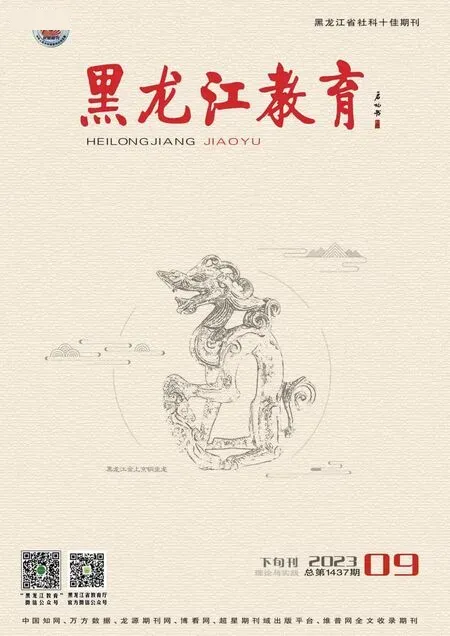新文科視域下高校“文學概論”課程探索
周 飛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一、引言
新文科作為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中文科教育的前進方向和變革要求,集中展現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創新性發展。2019年8月26 日,教育部在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年會上明確倡導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優化學科的專業結構,凸顯學科的中國特色,努力建設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本科專業[1]。新文科之“新”,是相對于當下專業日益細化的現有文科教育而言,其具體的內涵、定位與邊界尚在不斷發展之中。隨著教育實踐進程的不斷推進,一些基本的脈絡特點顯現出來:一是強調文科的交叉與拓展屬性,重視文科內部的大文科建設和文理之間的現代融合;二是平衡文科的理論性和實踐性,重視文科知識的創新與發展,實現文科知識的經濟轉化效益,激發其社會生產力;三是要展現學科建設的中國特色和中國話語,積極進入世界學科競爭之中,爭奪世界學科分類的話語權。
新文科觀念為中國文科的大發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長時段的要求。就實操層面而言,自上而下的新文科觀念轉化為文科教育中的具體改革措施需要更多的實踐抓手與“實驗田”。其中,“文學概論”作為傳統文科核心專業——中國語言文學中研究文學基本原理、基本規律和基本范疇的基礎課程,在實踐教學過程中需要整合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西方文論、古代文論、語言學等專業知識內容及新近的社會流行文藝與文化現象,因此,其也是一門在眾多學科領域間交叉與融通的綜合性課程。它的跨學科、跨文化、跨語言屬性與新文科融合發展的方向基本一致,是踐行新文科教學改革、激發傳統文科活力的前哨站之一。因此,新文科既是文章的研究背景,也是新時代對“文學概論”課程提出的新要求、新標準和新方法。
二、現狀與問題:“文學概論”課程的基本情況
現有“文學概論”屬于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必修課程,其重在對文學的基礎原理和基本規律進行概要式的講授,讓學生掌握基本文學理論知識,能夠對一般性的文學作品及文學現象進行理論化的分析與闡釋。它不僅是現行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同時也是其下屬二級專業——文藝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因其理論門檻較高,與學生的日常閱讀及生活距離相距較遠,該課程幾乎成為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中最難教和最難學的一門基礎課程。有學者集中列舉了該門課程的三大難點,即課程內容的理論性、課程思維的抽象性及話語體系的陌生性[2]。課程自身的知識壁壘與話語體系需要學生將原有的形象思維和日常思維逐步轉換為理論思維和問題意識,因此,學習的難度和要求也相對較高。為了克服這一長期存在的教學難題,教師首先需要具備較為全面的學科視野,從國內外的教學實踐中直面其現狀和問題。
國外的文學理論課程主要分為專題性文論和文學原理兩類,前者較為有代表性的是耶魯大學P.H.弗萊(P.H.Fry)教授的“文學理論導論”課程,其主要內容均為專題性文論,一次或兩次課講一個文論專題,內容涉及闡釋學理論、新批評理論、形式主義文論、符號學和結構主義文論,以及新近的各種文化研究理論,其落腳點為當代的理論講述與理論闡釋,基本打通了文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知識壁壘,其教學內容比較像國內的“西方文論”(現代部分)課程[3]。文學原理類課程最有影響力的當屬美國學者R.韋勒克(R.Wellek)的相關課程。他和O.沃倫(O.Warren)合著的《文學理論》著作在美國高校影響力很大,是各個高校文學理論課程的教材或參考書目,在國內也影響深遠。R.韋勒克(R.Wellek)在耶魯大學任教期間長期開設“Literary Scholarship”課程,《文學理論》著作就是在這門課的基礎上寫成的。R.韋勒克(R.Wellek)的《文學理論》有著完整的理論脈絡與結構體系,不是專題拼盤式的,對國內“文學概論”課程教材的編寫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國內,童慶炳教授的學術影響最大,其編著的《文學理論教程》曾是各大高校“文學概論”課程的參考教材,影響了一代學生。《文學理論教程》試圖打通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傳統文學理論之間的壁壘,試圖在馬克思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理論及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融合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文學“四要素說”,形成了一套理論邏輯嚴密、理論術語豐富的完整體系。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則加重了文學自主性層面的內容,并加入了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部分,補充了現代傳媒和全球化對文學理論的影響,體現了新文科的發展方向。
除此之外,國內還有一些高校出版了自己的文學理論教材,其使用的參考教材也多是各個學者思想體系與講課內容的總結與升華,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魯樞元《文學理論》、董學文《文學原理》、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等,各種教材都打上各個學者自身的特色烙印。
無論國內國外的“文學概論”課程,其基本知識點都落腳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不同的是有的學者堅守文學本位立場,以狹義的文學觀念編撰授課內容,有的則照顧到文學文化的大趨勢,開始向“大文科”和“跨學科”的趨勢靠攏。作者認為任何極端的做法都不可取,應該在現有文學本位基礎上,刪除掉一些過于細致的枝蔓,參照新文科的發展趨勢和時代發展要求,適當增添和調整新的授課標準和授課內容,豐富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概論”課程內容,才能使得文學理論課程更加貼近學生的閱讀和生活,符合新時代的要求。
三、試驗與目標:“文學概論”課程的改革需求
隨著新文科理念的倡導與深化,“文學概論”課程的改革和發展迫在眉睫。在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文學概論”課程本身與新文科關系最為密切,也最適合成為新文科改革的試驗田,為文科的大發展提供經驗和方法。
首先,“文學概論”課程本身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屬性,符合國家新文科的發展趨勢。2020年11月3 日,教育部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做出了全面部署,要求文科教育“緊扣國家軟實力建設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積極發展文科類新興專業,推動原有文科專業改造升級,實現文科與理工農醫的深度交叉融合”[4]。要實現這一發展,離不開現有文科教育的升級與融合。高校“文學概論”課程作為文學教育中最具綜合性和交叉性的課程,剛好能夠承擔起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轉型的“橋頭堡”責任,它通過理論講述與理論實踐的方式,將文、工、農、醫等領域的文學書寫、人文關懷與理論批判系統整合,最終實現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范式的轉型與升級。
其次,“文學概論”課程作為傳統文科的基礎課程,其對學生的理論視野與知識系統有著基礎性的構建作用,強調學生對理論的運用能力。新文科要求學生不僅要具備文學理論素養,更要對新生文化事物保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熟練的分析能力,這樣才能突出理論知識的實踐屬性,提高學生的核心素養。“文學概論”作為研究文學基本規律的主要課程,隨著“文學”自身的不斷拓展與連接,獲得了更為廣闊的應用領域與闡釋空間。一方面,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文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文學與歷史、政治、經濟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就西方文學而言,自《荷馬史詩》起便有藏往知來的文學傳統,以“詩性知識”(Della Sapienza Poetica)的形態承擔寓教于樂的功用[5]。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發展,今天的文學與流行文藝、網絡與新媒體的關系也日益密切,文學理論已經不止于傳統文學的研究,而進入到文化研究領域,從而生發出更多與學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理論場景與理論問題。
最后,在新文科視域下,新的“文學概論”課程需要新的教學目標以適應新的課程要求。一要進行文學理論知識的整體升級:由被動的知識講述轉向主動的知識生產,在教學過程中注重拆解理論知識的結構脈絡與知識譜系,提高學生理論理解力。二要實現文學理論的實踐導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理解的基礎上轉向理論的實踐運用,突出文學理論知識的實踐屬性,讓學生能夠將文學理論知識與自身的閱讀和日常生活相結合,提高自身的核心技能。三要進行學科視野的拓展:在堅持文學本位的基礎上,引入“大文科”(文史哲等社會學科融合)與“邊緣文藝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結合),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
總之,“文學概論”課程改革離不開新文科觀念的理論指導,需要在自身內在的知識結構和外在的教學形式、目標等方面多管齊下,實現自身的華麗變身,最終成為新時代的文科課程。
四、路徑與展望:面向時代和世界的“文學概論”課程
任何課程的改革目標都要落實到具體的教學實踐之中,從而將新的理念實體化和具象化。具體而言,在新文科背景下,新的“文學概論”課程應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把握文學概念的時代新變。新的課程教學應在堅持文學本位的基礎上,重視文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聯系,打造立體多維的“大文科”。除了傳統的詩、小說、散文和戲劇外,文學實踐在當代逐步走向傳媒和大眾文化。傳媒時代,文學的存在方式及文學的文化研究屬性日益受到人們重視[6]。這就需要教師對文學理論知識的整理突破現有界限,注重其對流行文藝與新近文化現象的闡釋與分析,讓文學理論知識進入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中,激活其多維的應用場景與問題情境,最終使得學生對文學理論知識有著“深而精”的理論把握。
第二,實現文科與理科的交融。在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文學地理學、文學與腦神經的關系研究,進化文藝學、量子力學與共同感研究,復雜性、隨機性與文學理論研究,后人類與文學理論研究等“邊緣文藝學”知識日益沖破傳統文理分野的教學體系[7]。法國著名哲學家、后現代文論家B.拉圖爾(B.Latour)在學理層面主張現代學術應該超越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平衡二者之間的不對稱性[8]。事實上,B.拉圖爾(B.Latour)自身的研究正是實現文理融合,從社會史和人文科學的視角介入自然科學的實踐。因此,適當引入這些前沿的文藝理論專題,有利于學生開闊視野,最終達到一個“寬而廣”的理論認知。
第三,重視文學理論與文化產業的結合。傳統文學理論知識局限于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與理論玄思,側重于提升學生內在的文學理論素養,缺乏與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強實踐性學科的融合。在國內部分高校,新興文化產業曾一度歸類于中國語言文學二級專業文藝學下屬的學科,是文學藝術與經濟產業結合的實驗地。例如,暨南大學的文藝學碩士研究生招生就長期設置文化產業與文化管理方向[9]。適當引入文學理論與文化產業的互動,提高文學理論的影響力,有利于提升文化產業的軟實力,使得學生走向更“高而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開拓文學理論的世界視野。新時代,中國文學及其文科教育正在世界文學場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對中國文學理論的教學離不開世界性的視野,需要挖掘更多的教學形式和內容。在形式方面,有條件地逐步開展多語種的互動教學,充分利用現有的開放式的世界公開課資源,將語言學習與文學理論學習相融合,培養具有國際理論視野的學生。在內容方面,一方面,在古代中國與世界的貿易交往中,中國的瓷器、絲綢和其他工藝產品為西方各國的文化藝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留下了豐富的文學藝術互動軌跡[10];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正在積極構建一種面向世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話語體系。這些都是“文學概論”課程涉及的內容,有利于學生在提高民族文學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時,放眼世界,走向世界,進而獲得更為全面的發展。
五、結束語
無論是文學理論的新發展,還是新文科的新要求,都是為了應對當下中國文科教育與研究面臨的新問題,是從中國實踐與中國發展中生發的新策略與新導向,有利于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科、新理論,培養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綜合型與創新型人才,從而在世界文科教育與理論教育中獲得更多的話語空間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