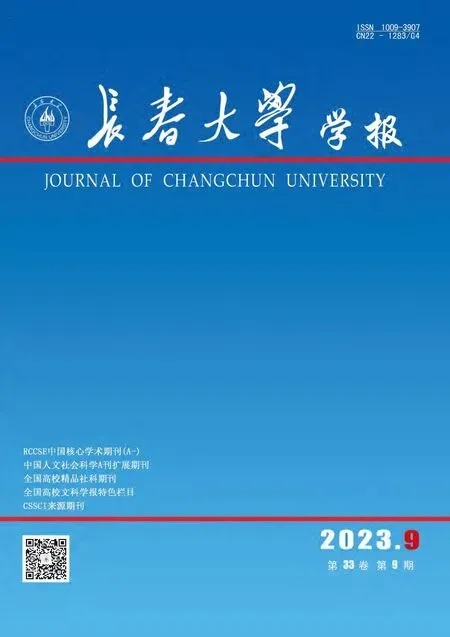外宣翻譯內在意義的再生與變異
湯玲玲
(巢湖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巢湖 238024)
外宣翻譯在國內最早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漢譯英是其最顯著的特點。學界普遍認同黃友義和張健兩位學者關于外宣翻譯的闡釋。黃友義認為,外宣翻譯是“把大量有關中國的各種信息從中文翻譯成外文,通過圖書、期刊、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以及國際會議,對外發表和傳播的過程”[1]。在此基礎上,張健教授進一步將其細化為廣義之“大外宣”和狹義之“小外宣”。前者幾乎涵蓋所有的翻譯活動,而后者包括各種媒體報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業單位的介紹、公示語、信息資料等實用文體的翻譯[2]。
據CNKI統計,自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以“外宣翻譯”為主題發表的期刊論文總數3167篇,其中博士論文14篇,碩士論文590篇,CSSCI期刊(含北大核心期刊)論文發表總數185 篇。從研究數量看,“外宣翻譯”相關發文總量占近十年來翻譯總發文量的0.98%。從研究層次看,相關高水平論文發文量占近十年來翻譯高水平論文總量的0.78%。顯然,外宣翻譯的研究節奏跟不上時代語境下翻譯發展的步伐。從研究內容看,既涵蓋經濟發展、民族傳承、歷史演變等內容的宏觀領域,又包括鄉村建設、景區旅游、企業發展等中觀層面的嘗試,也有政治文本、文獻典籍、旅游文本等微觀文本層面的解讀,充分體現了大到國家建設、小到個體發展都離不開外宣翻譯研究。從研究視角看,有以各學科理論探究為視角的研究,如傳播學、哲學、敘事學等;亦有以前沿政策為指導的創見,如“一帶一路”、“互聯網+”、鄉村振興等;還有以研究方法為視角的綜括,如CiteSpace、語料庫等。可見,外宣翻譯研究已迎來了百花齊放的發展階段。然而,現有研究散見于各領域,缺乏文化系統性和連貫性,較強的學科寄生性隨時會引起“泛學科”的潛在危機。進而言之,當前外宣翻譯對文化旨趣研究不濃,對文化意義本身關切不夠,缺乏基于自身文化體系元素的價值詮釋與意涵表達,文化元素攝入過少致使外宣文化本質和內涵出現“流失”現象,外宣翻譯“走出去”卻難以“走進去”。從洛特曼文化符號學視角出發,重新審視符號學理論框架下的外宣翻譯意義問題,深挖外宣翻譯內在意義變異與再生等問題,以期有效避免外宣翻譯單一學科視角存在的學術盲點和解釋偏頗問題,為填補外宣翻譯文化流失的溝壑提供助益。
一、文化符號學理論回溯
20世紀50年代,“符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產生,它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控制論和信息論結合在一起”[3],運用系統的結構分析法描述各種符號體系,力圖擺脫傳統主觀印象式的方法在以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20世紀60年代,文化符號學在經歷了符號學的蓬勃發展之后,從中衍生而出,成為一門獨立的理論體系。
(一)“合金化”:莫斯科-塔爾圖符號學派的共生之本
莫斯科-塔爾圖(Moscow-Tartu)符號學派的形成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解凍思潮所帶來的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以及遠離政治中心的地緣位置不無關系。學派由兩種不同類型的流派組建而成,兩者兼以文化意義的生成為研究共相。源于彼得堡文學派的塔爾圖學派在烏斯賓斯基的帶領下以詩學文學研究為主,莫斯科學派在尤里·洛特曼(1)洛特曼全名為尤里·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1922—1993),出生在俄羅斯猶太精英家庭。(Juri Lotman)的引領下以語言學研究為主。兩個流派“在塔爾圖暑期研討會這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和特定的學術環境中進行了‘學術接觸’,發生了‘共生現象’,產生了‘合金化’,形成了新的流派——莫斯科-塔爾圖符號學派”[4]。學派文化研究集中在俄羅斯本土領域,但對法國、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符號學研究頗感興趣。20世紀60年代,學派以文學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探索文本符號的結構規律、文學交際參與者的關系、意義闡釋等問題。20世紀70—80年代,把結構主義方法擴展到其他符號領域如圖像、電影、繪畫直至文化整體[5]。20世紀90年代,開始圍繞文化符號活動的類型和普通文化類型學等問題展開研究[6]。
(二)“集合體”:文本內在嬗變的二度考察
作為莫斯科-塔爾圖符號學派中最核心的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其文化符號學更是學派長期的學理指導。洛特曼文化符號學是對結構主義、形式主義和布拉格語言學派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它以文化為研究對象,將文本作為解讀文化現象的基本單位。從早期關注文學方法論的革新問題,到一般理論文學的建立問題,再到后期的文化史領域的研究,洛特曼文化符號學就像一顆磁力極強的吸鐵石,在問題研究中吸附著優秀文化理論的精髓,不斷推演著對文化現象的闡釋功能。
洛特曼對文本的研究是文化符號學獲得強大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洛特曼早期的文本強調意義集結,是一種意義型的符碼載體。誠如洛特曼所言,“文本是以特殊形式構成的、能夠包括大量濃縮信息的綜合體”[7]。隨著研究的深入,洛特曼求真的科學態度打破了先前對文本研究的認知局限,他在《文化與爆炸》中對文本進行了二度考察:“文本不再被理解為有著穩定特征的某種靜止的客體,而是作為一種功能。”[8]文本被重新定義為“完整意義和完整功能的攜帶者”[9]5,文本是擁有類似飛機“黑匣子”一樣強大功能的信息收集器和發射器。簡言之,文本不再是一種語言寫就的表述或單一符碼的轉換,而是由多語共構和多碼交互形成的集合體。文本不僅可以引發讀者與文本、讀者與讀者之間的內部交流,也能夠促進與作者、文化、社會環境之間的外部交流。因而,洛特曼后期的文本研究在吸收早期意義型概念的基礎上轉向了功能型,內涵和交際功能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文本既是文化符號學研究的基礎性元素,也被視為該理論核心中的核心。
(三)“三元性”:跨學科闡釋的循理依據
受索緒爾語言和言語二分法觀點的影響,就“語言是在文本產生之前就存在”的問題,洛特曼認為,很多情況下并非語言在文本之前,而恰恰是文本在語言之前[10]43。他通過揭示語言符號和藝術文本之間的關系,挖掘文本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洛特曼關于文本的研究克服了俄羅斯美學界盛行的純認識論和西方結構主義符號學脫離內容的純結構主義分析法的片面性,文本變成了更加開放的符碼集結。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指出:“文本被視為整個人文思維和語言學思維的第一性實體,而對‘文本’問題的探討,是以‘表現為話語的文本問題’的面貌出現的。”[11]洛特曼認為,對話是各種編碼系統之間傳遞信息的方法,通過文本進行溝通交流。這與巴赫金的觀點不謀而合。巴赫金強調,發出者和接受者的指向與回應,在主體間的關系中文本意義得以產生和形成。這與洛特曼文化符號學對話機制中的“我—她/他(I-S/HE)”模式相吻合。與巴赫金不同的是,洛特曼在對話理論中更加關注“我—我(I-I)”這種自我交際對話模式所生成的文化內在新意。在自我交際對話中,信息的發出者既是發話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文本是動態多變的,多層次信息代碼的交織不斷通過文本的多語本質傳遞給另一個自己,形成新的意義,從而重塑自我認知,加速文化增加機制和縮減機制的形成。
雅克布森在六要素及其六功能理論中指出,任何信息發出者和接受者間的交際行為都離不開語境、信息傳達、接觸交流和文本代碼,新信息和新意義將在這些要素交際過程中不斷形成。在批評性吸收雅克布森觀點的基礎上,洛特曼指出文本是傳遞多元信息、喚醒多元記憶和生成多元意義的有機體,進一步優化了文本信息傳遞功能、文本信息記憶功能和文本信息創造功能。
洛特曼文化符號學關于文本和語言關系的重新考察是對索緒爾語言學新的繼承,文本與對話關系的動態解讀是對巴赫金對話理論的新突破,對雅克布森六要素及其六功能理論合理成分的充分吸收極大地優化了文本三大功能,三者融匯貫通形成了文化符號學“開放、動態、多元”的“三元性”特質,為跨學科闡釋理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外宣翻譯與文化符號學的契合邏輯
洛特曼文化符號學認為,文化的全部新意與活力產生于不同編碼之間的翻譯中[10]42。同樣,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外宣翻譯文化的活力也源于不同編碼和符碼之間的互動,這點與洛特曼文化符號學頗有共通之處。援引洛特曼的話:“文化符號學旨在透過紛繁蕪雜、千姿百態的文化現象,抓住文化的本質和共相,構建人類文化的結構模式,這一模式具有普適性。”[9]162文化符號學普適性的文化闡釋功能依舊適用于外宣翻譯研究,主要體現在元語認知、文本載體和對話釋義三個方面。
其一,在元語同源的認知維度,兩者都以符號為元語言。文化人類學家L.A.懷特認為,“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賴于符號”[9]162,符號是文化的元語言。外宣翻譯作為人類文化傳播的一種方式,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自然離不開符號。而文化符號學認為,文化是用特定方式組織起來的符號學系統,是最復雜、最完善、最高級的符號系統,符號是其生存和發展的首要因素。因而,兩者是有共通之處的。
其二,在文本載體的闡釋維度,兩者都以文本為載體。文化符號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化,而洛特曼認為“文化本身就是文本”[12]。在這里,文化已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文本,文化符號學通過觀察文化這一完整“文本”的發展和變化歷程來挖掘其內在意義。外宣翻譯作為人類研究文化發展的一種方式,通過對文本的翻譯和解讀,借助對外宣傳媒介完成對文化的認知。顯然,文本是實現文化認知的載體,這一點與文化符號學頗為同理。
其三,在對話釋義的功能維度,兩者皆是一種對話交流行為。文化符號學的對話理論是多語和開放的,并且對話中的“文本”具有創造性和動態性。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在動態的語境中不斷突破“我—我(I-I)”、“我—她/他(I-S/HE)”原有的對話模式與認知,創造出大量新內容,產生新意義,激發新文化,這個過程就是文化符號學的“對話”交流行為。而如前所述,外宣翻譯是通過各種媒體渠道向國外受眾傳達的一種跨國界、跨語言、跨文化的對外傳播活動。可見,這也是一種交流行為。交流中必然離不開“對話”,這種“對話”既可以是獨白式的,也可以是互動式的,故兩者不謀而合。
綜上,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與外宣翻譯的契合邏輯條理清晰。文化符號學不僅是外宣翻譯研究可借鑒的理論,也可以成為一種系統闡釋外宣翻譯內涵和外延的學科工具。對于我們思索外宣文化的走向,探索外宣文化建設的途徑,尋求不同文化間有效交流與對話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外宣翻譯內在意義生成之管窺
“對外宣傳以語言為紐帶,以傳播效果為宗旨,在話語實踐的過程中完成文化與價值觀的闡釋及國家形象的建構,其形式以外宣翻譯為主”[13]。作為講好中國故事、讀懂中國內涵、建好對外話語體系的重要橋梁,外宣翻譯服務對于國家形象塑造、國家利益維護和國家話語權的提升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成為使命化的國家行為。從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符號學理論框架下的翻譯意義問題,指出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和文本的信息創造功能對外宣翻譯內在意義變異與再生所產生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對外宣翻譯文化元素的觀照和解析,激發外宣不同符號和編碼之間的文化活力,加強文化認同的符號功能,讓中華文化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從而助力文化“走進去”。
(一)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文化不勻質與信息不等值現象的消解
基于化學家維爾納茨基“生物圈”的概念,洛特曼將“符號圈”定義為文化與符號賴以生存的空間。不勻質性是“符號圈”最本質的特征,也是文化在“符號圈”表現極為活躍又異常繁雜的主要誘因,催生了不等值信息。從符號到“符號圈”衍生的過程中,文本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而這一切有賴于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是通過發出者將信息傳達給接受者的過程。在傳遞過程中,受主客體不同語言經驗、標準和記憶貯量等因素的影響,文本對異質文化的解碼難以實現全覆蓋、零偏差的理想范式,只能是近乎原編碼的信息解讀,文本也無法達到絕對意義上的信息對等傳輸狀態。盡管如此,依舊不影響文本作為文化內在意義生成的基本路徑和主要渠道所發揮的學理功用。文本中的偏差與謬誤也是新意生成的重要源頭,正是由于內部的不勻質與信息的不等值加速了新意的產生,文本不再是一個僵死的符碼結構,文本使信息“文化化”,信息又加速了文本“降噪”的進程。
如將外宣文化圈與“符號圈”相類比,不難發現兩者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對“文本”的依賴是殊途同歸的。誠如前言,文本與文化是一對密不可分的關聯詞。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一種擁有完整意義的文本組合,文化即完整的文本集合。外宣翻譯作為文化發展的一部分,自然被視為一個擁有完整意義的文本組合體,譯界、譯者、譯文等便是外宣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外宣翻譯中,由于主客體雙方受經驗理解、教育程度、認知結構、接受取向、期待視野等多重影響,致使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產生了不對稱的符碼效應和非等值的信息接收效果。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是消解文化不勻質現象和解除信息不等值困境的重要工具,文本使信息“文化化”,信息又加速了文本“降噪”的進程,因而文本在解決文化的信息不等值上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這種現象在外宣翻譯中比比皆是。“新聞外交官”的翻譯常用statesman而摒棄使用在西方語境中具有貶義色彩的單詞politician;龍”選用中國漢字“龍”的音譯Loong,卻避免使用引誘夏娃偷吃禁果的靈獸dragon這一具有原罪性質的詞匯。
針對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的問題,俄羅斯稱之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特殊軍事行動),認為這是一種反壓迫性的軍事行動;以美國為首的大部分西方國家冠以Russia-Ukrain War[14](俄烏戰爭)、Russia invasion[15](俄羅斯入侵)之名。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對于以Russia invasion和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烏沖突)主題關聯的新聞報道總數比例懸殊,前者約為后者的15倍。相同的情況見諸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管窺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局勢的主流態度,通過翻譯發揮符號表意功能在外宣中留下“噪音”痕跡,人為引導意義發展方向,使意義持續單向,從而為政治陣營的重新劃分埋下伏筆。對此,中國使用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烏沖突),亮明客觀態度和中立立場,有效避開了卷入國際政治爭端的亂圈。文本以政治考量的身份匡正了固有認識的誤區,消除文化壁壘,避免了政治事故。文本使信息“文化化”,文化通過文本層面的信息傳遞在強化政治意識的同時,也淡化了政治色彩,避免了話語沖突,展現出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和開放性,促成了外宣翻譯內在意義的變異與再生。文本在外宣中潤物細無聲地對翻譯進行鑲補、減肥和重組,達到對異質文化迂回婉約的處理效果,有助于解除文化在文本傳播過程中受信息不均勻性、不對稱性雙重影響而造成的信息不等值困境,促進了文化的異質共生。
(二)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歷史記憶與文化聯想的喚醒與重構
洛特曼將文化定義為“所有非遺信息的總和及組織和貯存這種信息的各種方式的總和”[16]。他在《論文化的符號機制》中進一步精辟地指出,文化是“表達在禁忌和指令系統中的非遺傳性集體記憶”[17]。在文化概念的內在演變過程中,文化從擁有組織和貯存功能的信息演變成非遺傳性的集體記憶。正如洛特曼認同新歷史學主義持有“歷史是文本”、“文化是記憶”等觀點一樣,文化作為一種集體記憶機制,根植于文化符號系統中,擁有復雜的記憶運行機制。作為文化第一要素的“文本”是文化記憶符號論最重要的理論基石,歷史事件的“文本化”和“去文本化”是形成和創造文化記憶的過程[18]。文化記憶的保存需要經歷“文本化”,而文化記憶的釋放和遺忘則需要經歷“去文本化”的過程。一言以蔽之,文化集體記憶機制中保存、釋放和遺忘都有賴于“文本”。文本是文化記憶的儲藏器,是文化記憶機制的理論基石,而所有過程的實現都有賴于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
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是指“文本有保存自己過去語境的能力”[10]44。文本擁有喚醒恢復歷史語境和還原文化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聯想功能,可以引發歷時和共時語境中讀者的共鳴,喚醒讀者沉寂已久的歷史記憶,這點也是對雅克布森六要素及其六功能理論中語境功能的進一步升華。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具有重現性的特質,文本可以模擬現實生活圖景,令沉寂的文化得以復蘇,人類認知得以重構和再生。正如我們看到博物館展示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時腦海會重現文藝復興、達芬奇、主人公真實身份之謎、笑容魅力等信息,無論是喚醒讀者的審美意識,還是對生活的時代感知,藝術文本承載的歷史記憶始終抹不去,記憶的重現也將繼續影響人類的多元認知。此外,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具有還原性的特質。文化作為一個文本整體,攜有還原歷史信息和保存歷史語境的特殊功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功能被階段性地“封存”,倘若遇到特定的語境和對象,它們又會重新“蘇醒”,展現強大的復蘇力。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圖書館是研學的藝術文本,理論價值頗豐。然而,當它出現在二手書店,對于賣家而言,它是獲取利益的媒介,理論價值變得無關緊要。一旦被充滿藝術構想的導演選中,將它重新搬回舞臺,依舊能上演無可比擬的經典橋段。此刻,這種被“封存”了的文本價值又一次被“喚醒”,文本的記憶功能還原了人類對歷史文化的認知,引起讀者在歷時和共時語境中的共鳴。
在文本信息的記憶功能中,文本可以引發讀者的共鳴,喚醒讀者沉寂已久的歷史記憶,揭示文本背后的文化訴求。在文學藝術創作和文化元素的外宣推介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紅樓夢》是一部擁有豐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經典著作,至今仍是外宣推介的重要文學作品之一。在譯界存有的諸多英譯本中,楊憲益與其夫人合譯的版本ADreamofRedMansions和戴維·霍克斯的版本TheStoryoftheStone頗受認同。然而,民間譯本TheDreamoftheRedChamber卻爭議頗多。霍克斯針對該譯本對文化聯想產生的影響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一譯法會引起誤解。因為‘紅樓夢’這個意思在歐美讀者頭腦中引起的聯想與在中國讀者頭腦中引起的聯想完全不一樣。在歐美讀者的頭腦中,‘紅樓夢’的意思是‘一個人睡在一間紅顏色的房間里——這一書名也頗能引起他們優美神秘的聯想。遺憾的是這不是中文書名的意思’”[19]。顯然,文本并未引發歷時和共時語境中讀者的共鳴,也未喚醒讀者沉寂已久的歷史記憶。相同的案例見于《水滸傳》譯本。賽珍珠見證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的中國遭遇到了西方各國的侵略與掠奪,見證了不平等的社會與國際關系帶來的人類文明破壞力,她希望通過小說的翻譯來重構心中儒家的“忠、義”思想,以期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20]。賽珍珠將《水滸傳》譯為AllMenAreBrothers,文本是對梁山108位小說人物的集體再現,將讀者帶入每一個人物背后的文化故事和歷史情節當中,聆聽文本背后譯者對社會文化追求和社會公平訴求的心聲。外宣推介如果采用民間粗糙直譯的WaterMargin,文本背后的文化記憶將消失殆盡,外宣效果也將大打折扣。
綜上,文本是文化記憶的儲藏器,是文化信息記憶功能最重要的理論基石,是不同文化意義生成的聚合體。文本帶有源自過去的清晰印記,對信息發生的語境具有保存能力。當文本再現信息時,它可以恢復歷史文化語境,重現和還原信息之間相互依存的聯想關系。文本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文化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調整,重構舊的文化,形成新的歷史觀和文化觀。因而,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是文化內在意義生成的又一通道,利用記憶關系把握時間和空間的抽象文化范疇是人類高度智慧的反映,催生文化內在意義的變異與再生,引發歷時和共時語境中讀者的共鳴,揭示文本背后的文化訴求,影響歷史文化的重構。
(三)文本的信息創造功能:多語場域與異質文化藩籬的跨越
洛特曼強調,文本不是由一種語言而是由多種語言同時在表述。從原則上講,任何文本都是多語的,是由許多不同等級的子系統疊加而成的符號整體[10]43。文本內部存在復雜的多語性,使內部的各子系統進行“游戲”和“對話”,所以,“文本能建立某種新信息,形成新的意義”[10]44,即文本的創造性功能。多語性是洛特曼文化符號學“文本觀”的核心。在文本交流的過程中,多語特質促使信息準確性和完整性變得異常復雜,文化意義的生成也變得更加多元。洛特曼曾用經典圖例(2)通過對洛特曼文化符號學文本創造功能的兩個圖例進行整合,深入認知文化符號學中文本的信息生成過程。原圖參見Jury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載于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Umberto Eco,I.B. Tauris &Co Ltd.,1990版,14-15頁.展示了文本多語性在交際過程對編碼和解碼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唯有統一的代碼才能使文本解碼無偏差。但在現實交際中,文本解讀是由多重且不規則的代碼合作完成的,每個子代碼都擁有不同的子系統,各類子系統交叉、疊加、融匯在一起又再次產生新的解碼內容,從而促使了新意義的生成,文本被賦予了多元的創造性(見圖1)。

圖1 文本多語性在信息生成中的編碼和解碼過程示意圖
據圖1,同一個編碼文本T1在兩中不同的解碼情境下會產生多語的信息。當編碼文本T1遇到第一種較為理想的解碼文本C時,無論是從T1到T2,還是從T2到T1,兩個文本產生的信息數量和質量都是完全一致的,T1和T2可以進行雙向轉換。而另一種情境,當編碼文本T1遇到多種不同的解碼文本C1、C2、C3……Cn時,受解碼群體不同層次的理解能力和解讀水平的影響,文本解碼會相應地出現T2′、T2″、T2?……T2n等代碼。此外,在現實生活中,解碼文本C1、C2、C3……Cn總會不同程度地交叉和重疊,此時出現的解碼結果便是T2′、T2″、T2?……T2n代碼的總和。事實上,C1、C2、C3……Cn每一個代碼內部都擁有復雜的多級結構,它們相互交融形成了一個源自T1的新文本集合,創造了新內容,形成了新意義。
“一種文化可以用只和文本創建者所用代碼部分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代碼來理解。這種編碼與解碼的不對稱性使得翻譯成為產生新信息的過程與行為,它實現了文本的信息創造功能。”[10]44洛特曼這句話依舊適用于外宣翻譯的文本交流過程。若將外宣文本視為T1,在第一種情境下,文本T1和T2的解碼為統一翻譯文本C,解碼結果T2幾乎與T1無異。在第二種情境下,遇到諸如C1、C2、C3……Cn等翻譯文本,每個文本內部都有其復雜的結構性,所產生的文本也不再是第一種情境下的T2。但無論如何,T1始終是所有解碼文本的源文本,T2′、T2″、T2?……T2n等代碼則是T1不同程度上的新變體。因此,文本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創造了新的意義,實現了文本的創造性功能。外宣翻譯作為一個多語場域,囿于多語文化的限制和海外大眾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職業特征、認知結構、期待視野等方面的差異,文化的解碼只能是近乎或近似同等意義的轉化。多語的文化保障了外宣翻譯動態性和多樣性,形成了文化的創新機制。文化的創新機制又不間斷地產生新信息和新意義,這個過程循環往復,文化新意的變異和再生永不停息。文化生成的新意義在跨越他文化與母文化之間的藩籬以實現與非符號及外符號空間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推動作用,典型案例常見于外宣中新詞新語的翻譯。
新詞新語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特色,如中國宇航員(taikonaut)、佛系青年(Generation Zen)、裸官(family-and-assets-abroad officials)、元宇宙(Metaverse)、偽娘(a cross dresser)、剩男剩女(left-over singles)、中國網民(Chinese netizen)、香菇藍瘦(under the weather)等,適度填補了文化空缺和概念空缺的情形。然而,新詞新語背后隱匿的社會變遷和文化內涵很容易形成他文化與母文化之間的藩籬,例如“甜野男孩”的譯文。隨著藏族小伙丁真為家鄉四川拍攝的視頻大火后,又一網絡熱詞“甜野男孩”橫空出世。“甜野男孩”,“顧名思義,就是長相又甜又野的男孩,第一眼看過去,撲面而來的野性讓你感覺他像狼一樣,然后人家笑了,你心想完了完了這狼怎么這么甜……”[21]外媒《南華早報》(SouthChinaMorningPost)曾以標題“China’s most handsome man right now?Tibetan herder wows Chinese social media with rugged good looks”介紹了中國的“甜野男孩”丁真。“甜野男孩”被譯為herder wows。查閱韋氏詞典,wow作為感嘆詞有“由音調緩慢上升和下降而再現的聲音失真效果”(a distortion in reproduced sound consisting of a slow rise and fall of pitch caused by speed variation in the reproducing system)之意;作為名詞可引申為“驚人的成功”(a striking success)。這里通過兩種詞性的轉換使用實現了文本創造性的功能,不失為借鑒之舉。然而,Tibetan一詞的使用卻有誤導嫌疑。丁真作為中國四川省藏族人,因爆紅后被西藏、云南等省份“歸為私有”,以致丁真本人不得不在新浪微博作了“家在四川”的澄清。然而,外媒依舊將“藏族”和“西藏藏民”混為一談。Tibetan多指西藏藏民、藏語等概念,在這里復制使用會引起海外受眾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錯誤認知,形成“四川屬于西藏、西藏就是藏族”等錯誤認知,從而影響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有破壞國家內部團結和穩定的隱患。因此,可改譯為“Tibetan-nationality herder wows”以規避問題焦點。而反觀中國外宣,華春瑩連發三次推特為丁真“打call”——The channel of Sichuan TV has a new “anchor”. Tamdrin#DingZhen,who broadcasts news in his native language Tibetan as a guest[21],同樣也使用了Tibetan一詞。但由于文字營造的前后語境,Tibetan被清晰地理解為“藏語”,規避了受眾認知的誤區。
在外宣中,多語之間的相互干擾、交雜不僅保證了文化信息的傳遞與保存,同時也產生了不可預見的新意義,文本翻越了多語場域過濾已有的認知框架,爭奪和創造了文化生存空間。在跨越他文化與母文化之間的藩籬以實現與非符號及外符號空間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外宣翻譯需要正視每一個文本代碼內部復雜的多級結構,借助文本介質對文化史和思想史進行強勁的塑形和重構。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文本中的偏差與謬誤也是新意生成的重要源頭。所以,文本具有強大的信息創造功能,它是跨越異質文化多語場域藩籬的主推力,它是識別外宣翻譯內在意義變異與再生的動力,依靠人類的想象力、創造力和預測力不斷更新受眾的記憶庫,“激發對原有認知模式的重新思考并促使知識譜系的擴容和思想變化”[22],衍生獨特的文化創造功能,再生新意。
四、結語
在文化自信的時代語境下,外宣翻譯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尤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其文化交往功能愈發彰顯。從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的視角研究外宣翻譯,是對外宣自身文化體系元素的價值詮釋與文化互動的意涵表達。通過對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理論發展的回溯,從元語認知、文本載體和對話釋義三個維度分析洛特曼文化符號學與外宣翻譯的契合邏輯,以此驗證洛特曼文化符號學對外宣翻譯的指導意義。深挖洛特曼文化符號學文本的三大功能,為外宣翻譯內在意義的再生和變異提供新思路。作為窺見人類文化全景的文本認知共通機制,文本的信息傳遞功能有助于解除文化在文本傳播過程中受信息不均勻性、不對稱性雙重影響而造成的信息不等值困境,促進文化的異質共生。文本的信息記憶功能利用記憶關系把握時間和空間的抽象文化范疇是人類高度智慧的反映,引發了歷時和共時語境中讀者的共鳴,揭示文本背后的文化訴求。文本的創造功能在多語場域里跨越他文化與母文化之間的藩籬,為實現與非符號及外符號空間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動作用。以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為方法論指導,重新審視符號學理論框架下的翻譯意義問題,有助于對外宣翻譯的意義再生與變異問題進行跨學科理論反思,避免了單一學科視角存在的學術盲點和解釋偏頗,延展了外宣翻譯跨學科研究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