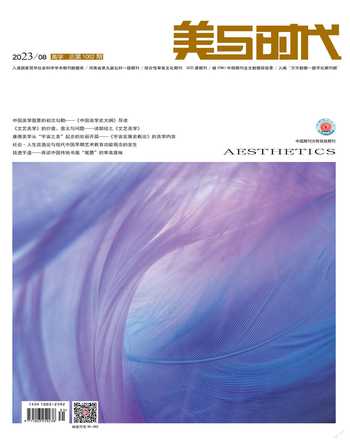普遍人性論的迷失:也論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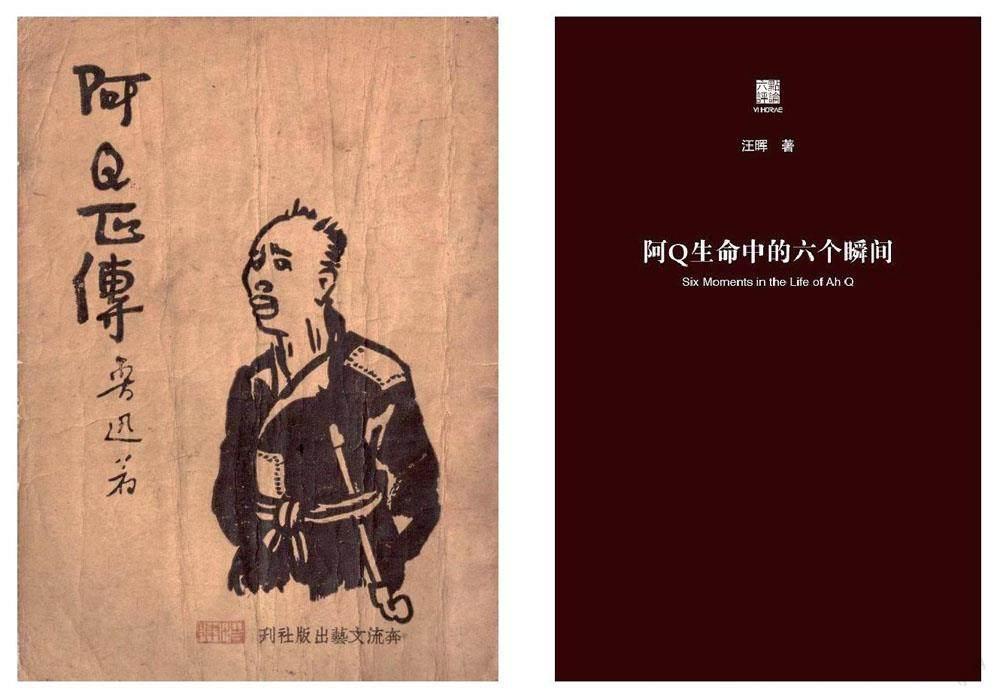
摘? 要:汪暉對阿Q生命中“六個瞬間”的揭示,對“鬼”與“國民性”兩重性的揭示,是為了替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發達工業社會重新構建一種革命理論。這個意圖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讓人們相互隔絕的等級制”等自我“外部”現實秩序(“鬼”)進行的整體批判;二是拆解“國民性”批判中普遍人性論和本質主義的傾向,指出精神勝利法失效瞬間的先進性和革命性;三是試圖指出一種終結發達工業社會異化邏輯的有效革命方式——“向下超越”的本能革命,個中思路頗類似于馬爾庫塞的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
關鍵詞:阿Q正傳;汪暉;發達工業社會;馬爾庫塞
《阿Q正傳》與阿Q,從周作人、茅盾等早期讀者那里就已經獲得了豐富的闡釋,其后更作為“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靈魂”[1]的國民性批判典型,不斷在各種意義層面被問題化,不斷被編織起新的闡釋網絡。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以下簡稱《瞬間》)以“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為副題,在21世紀重新走進這片閱讀場域,不單是要做一場魯迅研究,更切切關心“一系列事關中國革命的歷史解釋和文學敘述”[2]4。汪暉引入一種“關于身體的政治視野”[2]22,力圖證明阿Q的本能、潛意識和直覺能夠賦予其一種“革命動力和可能性”;而陶東風指斥這一本能革命不過是“獸性的大爆發”,根本不可能“促發真正意義上的革命”[3],與汪暉的判斷形成了巨大偏差。陶東風的回應很有道理,但實際偏離了問題核心,即汪暉真正想要論述的不是“辛亥”的革命,而是“當下”的革命;不是對革命“開端”的敘述重演,而是對革命“機制”的重新界定。為此他著意對國民性批判這一對國族中普遍人性的批判進行祛魅,取消了其本質主義傾向。
一、本能革命的理論來源
自從王富仁等學者在新時期跳出以唐弢為代表的政治化魯迅的研究范式以來,對阿Q的論述就從“落后農民的典型”等階級成分的強調①,走向了對以精神勝利法這一病態的社會精神現象為落腳點的國民性弱點的批判。精神勝利法消解了阿Q的革命動力,使阿Q成了國民性弱點的“藝術標本”;如果要實現政治革命的成功,精神勝利法式的國民精神弱點就必須被改造。而《瞬間》卻避開了阿Q的消極面,試圖重新開掘阿Q身上“潛藏著的趨向革命的基因”[2]10,分析重心集中在精神勝利法的偶爾失效。也即,此間的論述關鍵并非精神勝利法等精神痼疾如何沉疴難愈,而是能突破精神勝利法禁錮的本能/直覺/潛意識有多么蓬勃頑強、生生不息。哪怕這種突破只有一瞬間,也應當被珍而重之地視為革命的根本契機。
(一)本能革命的合理性:精神勝利法的荒謬內核系身體與精神的割裂
汪暉在阿Q身上發現的六個瞬間分別是:因打架被人拿走了贏來的賭錢,“感到失敗的苦痛”;一向受阿Q奚落的王胡竟然把他給打了,一瞬間感覺“無所適從”;調戲小尼姑而“飄飄然”之后,竟敢去調戲趙太爺家的傭人吳媽的“造反”;丑事發生后,阿Q遲鈍地接連意識到失去衣服的寒冷、女人們對他的躲避態度、沒有短工可做的饑餓,“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走投無路之后,阿Q想要投降革命黨,假洋鬼子卻舉起哭喪棒不準他革命,他因此在沮喪和失落中感到“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無聊”;最后是阿Q被綁縛法場,在面對死亡的極端恐懼中感受到自身“皮肉”與“靈魂”的分離,精神勝利法徹底失效,阿Q在兩眼發黑中經受著靈魂被嚙咬的巨大痛楚。這六個瞬間,阿Q覺醒的六個契機,往往只出現了幾秒鐘,就被復蘇的精神勝利法迅速壓制了;但它們的確存在,并以其短暫呈現指出了突破精神勝利法的可能。汪暉認為,這一可能來源于“對生命本身及其需求的尊重”[2]22。如果身體沒有飽受剝削、任人宰割而呈現為病態,精神勝利法就不會顯得如此可悲可笑;因此,精神勝利法真正的荒謬內核是身體與心靈的割裂,現實與精神的分離,在這個意義上,身體已經獲得了超出其本身的意義,而讓身體的本能獲得解放,也就成了救治身體—現實、改變社會秩序當仁不讓的必備動力。汪暉通過生命主義思想將他的這一發現與魯迅的本意聯系在一起:生命主義的核心是將生命置于一切物質、關系之上,生存本能因此得到肯定;在這本能之中,就暗含了對不合理的現實秩序的顛覆偉力。魯迅心中存在兩個“辛亥革命”,一是真正作為新的歷史開端的革命,它對實現消除等級隔膜與擺脫根本貧乏的自由莊嚴承諾;二是帶著革命的名頭、實際是奴隸與奴隸主地位置換的重復性社會變化。精神勝利法是讓舊秩序重組登臺、革命淪為重復的重要原因,只有突破精神勝利法,才能讓革命不再“回轉”內耗,而突破的契機,如前所述,正存在于本能的欲望、直覺和潛意識當中。既然如此,“向下超越”,向著身體和本能的世界深入,就成了把握不同于被社會歷史所壓抑的現實世界譜系的唯一可能。
照直說來,這一推論過程是堪稱順暢的。陶東風最大的疑難也不是針對這一分析的過程,而是那看起來大事不妙的結論:“阿Q革命的目標不過是身體翻身(食色性的滿足),這樣的‘革命的確是離不開本能和直覺的,是以本能為契機和動力的,它一旦突破意識或思想的防線,結果就是生命本能乃至獸性的大爆發。”[3]如果不能像汪暉所抱怨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那樣執著于為阿Q注入“新的政治意識”[2]9和“革命覺悟”,阿Q停留在“革命就是造反”水平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與精神勝利法形成正面對抗,只會導致奴隸“翻身做主人”的鬧劇,如同歷史上每一場讓統治制度循環往復的農民革命一樣。
(二)本能革命的可能性:馬爾庫塞對文明與愛欲相對立的推理鏈條的打破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命是20世紀的歷史舞臺上最耀眼的劇目,21世紀的學者仍然為之牽腸掛肚。汪暉從阿Q的六個瞬間中提煉的身體/本能革命話語體系以及陶東風對之的不以為然,正類似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學以及人們對其的批判。
弗洛伊德從俄狄浦斯情結出發,將人類的歷史定義為被壓抑的歷史:原始部落的暴君—父親壟斷著權力與快樂,強壓著兒子們克制自身的(以亂倫為代表的)愛欲本能,而兒子們反抗成功后,也效仿著父親來統治,壓制個體本能結構的現實原則由此延續下來了。顯然,這種壓制恰恰是文明進步的前提。人的本能結構具有破壞力量,因為它常常向文明索求后者所不能給予的滿足。文明社會的現實原則因此將本能得到滿足的快樂標準做了修正與轉變:直接滿足變為延遲滿足,沒有壓抑變為規律與安全感,本能消遣變為苦役工作。個體在這個過程中痛苦地意識到,他的本能結構和快樂需求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滿足,其獸性的破壞力量已經被現實調和并引入正途。因此,在快樂原則被現實原則取代后,人類發展了文明的理性功能,即學會依照現實原則權衡利弊,檢驗行為,主動與外部強加于他的“合理性”秩序保持一致。在弗洛伊德看來,出于本能結構的快樂原則為現實原則所代替,是人類文明史上巨大的創傷事件。但這種“代替”絕非一勞永逸,充滿破壞力量的愛欲本能仍然在文明的控制與壓抑下蠢蠢欲動,這種被壓抑物的回歸,構成了文明的禁忌史。汪暉引入身體本能/直覺來突破作為封建等級秩序內化于心典型表征的精神勝利法,與弗洛伊德對性本能寄予沖破現實原則壓抑的期望實在如出一轍;身體本能的受壓抑在這里不再由于精神的“高尚”而被視作合理,“倒退”“向下”被認為具有了進步的功能。而陶東風對汪暉的質疑,也同樣是弗洛伊德元心理學的可質疑之處:既然對人的本能結構進行壓抑性轉變是文明的必要條件,若要實現文明社會最大的合理性進步——實現人的本能的真正滿足、力比多的充分釋放,現實原則的壓抑就必須被全部推翻,文明豈非應當立刻爆炸回歸前歷史的原始狀態?放縱本能、病態革命的下場,難道不是回歸最原始的“獸性大發”嗎?
在這一意義上,對弗洛伊德元心理學的補救,也可作為對汪暉所發現的“六個瞬間”的革命意義的補救。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自由的力比多本質上與工作(苦役)相沖突,為了建立工作關系,就應當壓抑力比多,從中提取轉化能量,只有力比多得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滿足,工作關系才能維持下去;無論多么富庶的社會,只要人類需要勞動,這對本能的壓抑與轉化就永遠存在。文明越發展進步,對愛欲本能的壓抑就越堅決,這壓抑造就了個體的社會生存,也對個體下達了自我破壞的指令;因為越是抑制本能結構對文明的破壞傾向,本能結構對自我的攻擊力就越強烈。這是一個前途灰暗、充滿悲觀的文明辯證法:正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導致了破壞傾向的強烈釋放。對此,馬爾庫塞在“基本壓抑”“現實原則”的基礎上,引入了“額外壓抑”“操作原則”等概念,將弗洛伊德的“本能壓抑——于社會有用的勞動——文明”三者間的互動轉變為“本能解放——于社會有用的工作——文明”的基本關系[4]138-139,指出了文明與本能結構之間不一定絕對對立。文明帶給人的愛欲本能的壓抑,除了來源于文明自身的現實必然,還有“產生于特定統治機構的附加控制”[4]27,比如為了維持勞動分工而實行的等級制等,是為“額外壓抑”。“消除額外壓抑本身將導致消除使生存為勞動工具的社會組織,而非消除勞動。那么,一種非壓抑性的現實原則的出現就將改變而不是破壞勞動的社會組織,因為愛欲的解放可以創造新的、持久的工作關系。”[4]139如此一來,弗洛伊德關于“人的歷史就是被壓抑的歷史”“文明與愛欲相對立,不是壓抑愛欲就是毀滅文明”的推理鏈條也就被打破了。本能結構的破壞性暴動的矛頭所指,系特定統治機構、社會組織的額外壓抑,而非文明為保存自身而必需的基本壓抑。那么阿Q身上的“生存本能”即可逃脫毀滅文明的苛責,而變為一種內生的動力,“一種積極的能量”[2]29,六個瞬間的的確確展現出了值得珍視的革命潛能。
(三)本能革命的必要性:精神的覺醒只能通過內在的契機
在文明的進程中,快樂原則屢屢為現實原則所取代,但弗洛伊德指出,唯有一種思想活動仍然能夠超越現實原則的支配,繼續依循自己的快樂原則,那就是“幻想”。這頑固的不受現實原則規訓的“幻想”,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頗為類似。然而精神勝利法的“幻想”,顯然是封建社會的現實原則充分內化之后的想入非非,它不能超越現實原則,不具備激發本能結構破壞性的革命潛能,反而成為現實原則修正快樂原則的典型部分。它抑制了阿Q身體本能對世界的感知,將痛苦麻痹,使暴戾屈膝,讓“革命的‘產生性的原因只是在直覺、本能的瞬間生成,卻無從轉化為一種持久的政治能量”[2]26,讓阿Q在思想和行動中根本不能獨立地、自主地順從及運用自己的本能傾向和能力。“相對于阿Q的持續的精神勝利,他的羸弱而病態的身體,由于其社會地位而來的饑餓、寒冷和性匱乏才是現實的或真實的。”[2]23在精神意識已經異化、連幻想也被現實原則轉變時,被剝削、被奴役的身體因具有動物性破壞力的本能結構而具有了革命的期望,這就是汪暉所謂“身上潛藏著的趨向革命的基因”[2]10。而這革命的對象,在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時期正是森嚴的封建等級秩序,在21世紀的當下,盡管革命的外在變遷已經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依類化別的等級名目消失不見,但無形的等級隔膜“卻像鬼一樣滲透在我們的靈魂中”[2]8,仍然在革命后的現代中國的土地上游蕩。傳統等級制度由有形變為無形,成為最真實、最本質也最無跡可尋的存在(鬼),成為壓迫本能結構、亟待革命消除的額外壓抑。革命本應是一場“社會的基本規則和體制的劇烈的變化”[2]25,但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并沒有將這劇烈變化真正貫徹、延續下去。汪暉頗有洞見地指出,魯迅熱烈地為孫中山及民國初年的革命者辯護,認為他們的確曾經在事實上觸動了舊秩序,在那個開端上,像阿Q這樣的人也在懵懂中展現了自身革命的潛能(六個瞬間);也正因如此,他才會痛心“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2]25,開端已經令人齒冷地轉變為循環。然而,魯迅對民國開端的呼喚,正是一種對“重復”的呼喚,“循環”與“重復”由此顯出了對立的意義。呼喚突破精神勝利法的開端的“重復”、打斷歷史秩序的“循環”恢復機制,成為了探索的重心。在汪暉看來,“對于魯迅而言,人的精神的改變是無法從外面強加的,它只能通過某些契機,開出反省的道路”[2]26,由外到內地給阿Q注入階級自覺、革命覺悟,在此根本就不受信任。
二、“時代錯置”的史述策略
《瞬間》的歷史敘事,盡管明面上論述的是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的時代,但真正著眼所在是21世紀發達工業社會的革命應當如何“重復”這一革命的開端而非陷入歷史的“循環”。汪暉試圖在發達工業社會揭示一種新的革命機制,為當今社會新的革命主體重新命名。
(一)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整體性批判
《瞬間》的附記被命名為《阿Q時代的“死去”與“活來”》,汪暉在其中鄭重地論述經典化過程對作品生命力的限制與遮蔽的問題,希望能夠重新打開這一文本活的場域,再次獲得貼合當今世界的新鮮生命力;而他所希望“復活”的話語,正是1930年魯迅對左翼作家們的提醒:革命伴隨著污穢(身體性本能的暴動),以及這一句話的潛臺詞:污穢不能作為對革命的否定。在附記中,汪暉引入了發達工業社會的典型意象:富士康的工人。流水線上的工人意象所揭示的工業社會的內在否定性,已經由哲學充分論述過了,如席勒《審美教育書簡》:“享受與勞動相分離,手段與目的相分離,工作與報償相分離。由于人自始至終被束縛在構成整體的某個很小的部件上,所以也只能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部件。由于他聽到的一直是機器的單調轟鳴聲,所以永遠不能發展自己存在的和聲。他不是去塑造存在于其本性中的人性,而是成了他的職業、他的科學的純粹印記。”[5]在發達工業社會,勞動已經完全異化:流水線上的機械組裝技巧、機關單位的日常辦公事務,都與人的本能、潛能無關,統治變得越來越有效、合理而且多產;而在文明社會的表象背后,人的工作(苦役)世界和快樂世界同成為一系列甘受管理的消極物。“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部件”之后,人原本暴動的本能也變為靜止、凝滯的了。人的主體意識因此越來越僵硬:它的用途不再是發展自身的個性,而是要使個體與整體相協調。隨著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的進步,這樣的統治畢竟是有效減少而非增加了總的不幸,那鬼魂一般的等級秩序因此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個體意識對所受壓抑的認識已經模糊不清了;因為此時不再有一個強有力的暴君可以作為統治的整個化身,對本能的壓抑、對快樂的管制變得像是社會分工的自然結果。這非人格化的統治大大加強了個體本能暴動與反抗的“罪惡”,因為它對苦役的要求似乎并不出于一己私利,而是為了維護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極權主義理論在這里顯出相當大的合理性:人的確受到無法理解而又無處不在的龐大異己機制的擺布,個性將被泯滅,選擇失去自由,意識受到異化,卻完全赴訴無門。既然主宰社會的已經并非某個具有超凡力量的人物,而是誰也無法掌舵的巨型國家權力機器,所有統治與壓抑的罪惡就都失去了寄主與憎恨目標:“控制一般由政府機關實施,但在機關中,無論雇主或雇工都是被控制者。個體的痛苦、挫折和無能都導源于某種多產和高效的制度,盡管在這制度之中他們過著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攻擊性沖動失去了攻擊的對象,或說仇恨所遇到的都是笑容可掬的同事、忙碌奔波的對手、唯唯諾諾的官吏和樂于助人的工人。”[4]85-87無論東條英機或者希特勒,都只是國家權力頂端一個可以隨時被替代的象征物,失去寄主的罪責虛無縹緲,落不到任何人頭上,正如深受極權主義理論影響的迪倫馬特所說:“在我們這個世紀的鬧劇中,在這個白種人最后一輪的輪舞中沒有罪人,也不再有責任承擔者了。所有的人都說自己對發生的事情無能為力,所有的人都說自己并不愿意看到有這類事情發生。好像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存在所發生的事情同樣也仍然會這樣發生一樣。所有的人都是被吸卷而停掛在了某個柵籬上。我們是集體負罪,集體躺在父輩和祖輩的罪狀上。”[6]當個體對現行壓抑的認識已經模糊不清,本能的破壞傾向也只能四處碰壁,這股攻擊力因此怪異而順理成章地投向了自身:有罪的似乎不是遏制,而是被遏制者。
(二)對“國民性”概念的拆解
汪暉將《阿Q正傳》作為“中國革命開端時代的寓言”[2]27,并在這個意義上指出“阿Q就是現代中國國民性的表達——是中國現代性的面影,而不是傳統中國的表征。”[2]8從1911年到《瞬間》寫作的2011年,兩個相隔一百年的時間節點無論是延伸向封建社會的晚清還是發達工業社會的未來,等級制度及其隔膜的鬼魂都在其間游蕩不息。辛亥革命之后,額外壓抑依然存在,歷史又陷入了“循環”。于是重新造訪開端的寓言來隱喻當今、預想未來,在學思層面就具有了合理性。這是汪暉隱藏在所謂“寓言”“中國現代性的面影”等措辭之后的“時代錯置”的史述策略。在汪暉所矚目的發達工業社會,本能的攻擊力被內投,被遏制者自身的主體意識問題就似乎成為了革命的真正攔路虎,革命問題因此與啟蒙問題再次勾勾纏纏,繼續發生歷史性的關聯。當學者在當下仍然依循汪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思路,要求造反革命的主體必須首先獲得“新的政治領導和新的政治意識”[2]9,要求以“啟蒙了的新主體意識和革命意識”[3]去超越本能和精神勝利法,其所期盼的革命顯然還是倚重民眾啟蒙的思路模式。在這樣的啟蒙視野里,“流行了一個世紀的批判國民性這個命題將國民性對象化,從而也完全負面化”[2]8,但就“國民性”這一概念來說,它其實是一種針對國族的、普遍而抽象的人性論。
在革命視域中,“國民性”(Nationality/National Character)與政治息息相關,是國民在某種政治、文化的長期影響下形成的比較穩定的倫理習慣、精神態度和心理素質的總特征。只要將這個概念放到真實的社會公共領域,放到人際關系(主體間性)的維度進行考察,不難發現其中的本質主義傾向。國民性概念的實質是對某一國族的普遍人性的概括,但它依照虛假的平均主義將現實群體中不同的社會階層的特性混同一體,忽視不同階層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截然不同的歷史性質,根本上是一個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只是在啟蒙式的革命話語體系中被把玩得完整光滑。汪暉用“兩個國民性”的辯證將這一概念拆解:“《阿Q正傳》的敘述中包含著兩個國民性的對話:一個是魯迅的敘述本身體現出的國民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反思性的或能動地再現國民性的國民性,另一個是作為反思和再現對象的國民性。”[2]6也即如劉禾所說:“魯迅的小說不僅創造了阿Q,也創造了一個有能力分析批評和否定阿Q的中國敘事人。”[7]
啟蒙并改造國民性,呼喚理想人格,在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時期顯然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在快樂原則已經異化、本能破壞傾向內投于自身的當下,仍堅持只有徹底改變了“國民性”,或說國族中普遍化、本質化的人性弱點,才能讓社會實現徹底的根本的變革,難免有一種歷史倒錯、靜態史觀的缺漏;在發達工業社會,有問題的不是被遏制者的精神深度,而是遏制本身。將《阿Q正傳》解釋為啟蒙知識分子力圖改造國民性以造就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考,實際是將“農民”(大眾?)置于被知識分子俯瞰的地位,盡管知識分子也在精神勝利法的鏡像中堪稱精深地憂心自省。照直說來,無論是否具備精神意識的主體性,發達工業社會的所有個體都受著同一種壓抑,知識分子同樣不再身處社會啟蒙的中心地位,而是走向了日益邊緣化的境地。羅崗將《阿Q正傳》視為對傳統“士大夫支配民眾”構圖的反思與突破,認為魯迅試圖重新構建新型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也即啟蒙—革命群眾的關系,這一闡釋顯然不足以(或許也無意于)像汪暉的發現一樣對發達工業社會產生意義;因為當今的知識分子作為邊緣人的隱喻,同樣在現行壓抑中困惑而不能自拔,如同布迪厄所說:“藝術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識分子,都是‘支配階級中的被支配集團。”[8]無論如何顛倒變換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圖譜,都沒有在實質上走出啟蒙的思想視野。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想起張旭東所說的話:“在現代中國批評史和思想史上,恐怕再沒有比‘《阿Q正傳》代表了啟蒙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民階級的同情的批判更自負的誤讀了。”[9]而這種深陷于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論辯的誤讀和迷失,正是與作為國族中普遍人性論的“國民性”息息相關的。
三、結語
在發達工業社會,快樂原則已被修正,個體在極其強大、無往不在的規訓和異化勞動(苦役)當中與其他個體同化,一起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本能結構的暴動在日益擴大的“罪惡”面前背上了沉重的枷鎖。對于當下的文明而言,認識現行秩序的真正壓抑并不利于個體的幸福,這種麻木不仁的狀態反而更適于滿足個體被異化的快樂原則,即安全感、規律感。因此,精神勝利法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就像額外壓抑的“鬼”仍然在飄蕩一樣。這一在現實原則之下無奈地“幻想”,是身體與心靈割裂的典型表征,表現出令人絕望的僵化和麻木;如何真正解放“身體”,以本能沖破現實原則和異化精神的拘禁,就成為突破遏制的關鍵。汪暉在阿Q身上發現的六個瞬間,正是對如此一種革命機制的探索與揭示,也是對啟蒙邏輯的一種突破,與馬爾庫塞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引入政治范疇的努力異曲同工。那些仍然包蘊著徹底否定現實原則、渴望徹底解放自身的強力的本能/直覺/潛意識,永遠期待一個暴烈的釋放,它的能量一旦沖破現實原則所設置的閥門,就會理所當然地投奔到革命的旗下。這一在封建社會末期猶有奴隸式“造反”循環的嫌疑的革命機制,經過汪暉的論述,已于發達工業社會獲得了犀利的正當性。因為尤其是在這個時代,“革命的主體并不能通過從本能到意識的過程而產生,而只能通過對于這一壓抑和轉化機制的持續的抵抗才能被重新塑造。正由于此,即便是本能的抵抗也蘊含了革命的可能性,而革命的可能性也因此與破壞性、重復性、盲目性共存。”[2]10阿Q身上那些卑微而鮮活的生命瞬間,是他突破異化精神意識的希望的剎那萌芽。救治身體,解放本能,彌合身體與心靈的異化分裂,也即改變現實秩序、消除額外壓抑,真正實現精神與現實的統一。《阿Q正傳》的確是中國革命開端時代的寓言,而汪暉將它的指向引入當下,希望我們能鄭重地品嘗它所揭露的“一直就那樣存在著”的“咬嚙靈魂的痛楚”,不要嘩然而麻木地凝視著異化的勞動與痛苦,“就像水消失在水中”[2]30。
注釋:
①從政治角度分析《阿Q正傳》,典型的表現即突出阿Q的階級成分,以此反映農民在封建社會所受到的壓迫及其在新社會所接受的改造。這方面典型的評論家如周揚、周立波、蔡儀、李桑牧等。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 編年版(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173.
[2]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J].現代中文學刊,2011(3):4-32.
[3]陶東風.本能、革命、精神勝利法——評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J].文藝研究,2015(3):147-160.
[4]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張玉能,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22.
[6]迪倫馬特.戲劇問題[C]//任蠡甫,童道明,主編.現代西方藝術美學文選 戲劇美學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66.
[7]劉禾.跨語際實踐[M].宋偉杰,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103.
[8]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43.
[9]張旭東.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J].魯迅研究月刊,2009(1):4-20.
作者簡介:汪一帆,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編輯: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