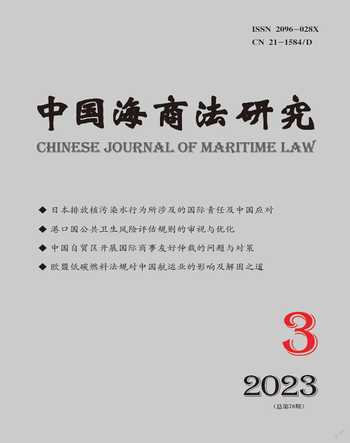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平衡路徑的重構(gòu)
摘要: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應(yīng)與國際投資仲裁程序改革并行不悖。文本改革的關(guān)鍵在于合理平衡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作為代表世界三大重要經(jīng)濟體近年改革立場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通過細化實體待遇條款、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增設(shè)程序透明度要求的方式試圖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的利益平衡。雖然兩協(xié)定在關(guān)注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問題上的側(cè)重點不同,但都同樣體現(xiàn)著強化東道國話語權(quán)的“國家回歸”趨勢。中國兼具資本輸入大國和資本輸出大國的雙重身份,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應(yīng)合理構(gòu)建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平衡,并應(yīng)改革國內(nèi)立法,統(tǒng)籌推進國內(nèi)法治與涉外法治。
關(guān)鍵詞:《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規(guī)制權(quán);投資者;國際投資協(xié)定
中圖分類號:D996.4文獻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3)03-0092-11
Reconstruction of Approaches to the Balance of Interest Between Investors an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ZHANG Qianwe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should go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One of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text reform is to rebalance investors interest and the host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A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which represents the US, China and the EUs recent standpoints of reform, the investment chapter of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and 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 make an effort to rebalance investors interest and the host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through clarifying substantive treatment clauses, extending right to regulate and adding procedural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Though CPTPP and CAI focus differently in rebalancing foreign investors interest and the host states right, both the treaties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return of the state”. As a major inward and outbound investment country, Chinas IIAs should reasonably rebalance investors interest and the host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Domestic reforms are also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t home and abroad in a coordinated way.
Key words:CPTPP;CAI;right to regulate;investor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伴隨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正當(dāng)性危機的持續(xù)發(fā)酵,國際投資仲裁機制進入多邊改革時期。針對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的現(xiàn)有研究多從程序法角度著眼,針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司法化和規(guī)范化趨勢,①提出完善投資仲裁庭設(shè)置、加強仲裁員選拔程序公正性、提高仲裁程序透明度等改進對策;②或從投資法內(nèi)部治理機制的角度,提出應(yīng)加強投資者的社會責(zé)任、促進國家間的合作;(參見彭德雷:《論國際投資秩序中投資者保護與國家規(guī)制的二元結(jié)構(gòu)——基于中國的實證考察與理論解釋》,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17年第4期,第95-98頁。)以及從外部借鑒視角,探討世界貿(mào)易組織上訴機構(gòu)、商事仲裁制度等對投資仲裁設(shè)計的借鑒價值。(Zachary Douglas,Joost Pauwelyn & Jorge E. Vinuales eds.,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Bringing Theory into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除了對原有的程序機制進行改革,對國際投資協(xié)定實體條款進行改革也是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的應(yīng)有之義,更是程序機制發(fā)揮良好作用的基礎(chǔ)。現(xiàn)有從國際投資協(xié)定實體條款角度開展的研究多基于公平與公正待遇、履行要求和征收條款,(參見余勁松:《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投資者與東道國權(quán)益保護平衡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11年第2期,第137-138頁;莫漫漫:《論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履行要求的問題及對策》,載《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8年第6期,第82-88頁;Benedict Kingsbury & Stephan W. Schill,Public Law Concepts to Balance Investors Rights with State Regulatory Action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in Stephan Schill e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89-98;Abba Kolo,Investor Protection vs Host State Regulatory Autonomy During Economic Crisis:Treatment of Capital Transfers and Restrictions Under Modern Investment Treaties,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8:457,p.485-499(2007)。)對于新近達成的國際經(jīng)貿(mào)條約在投資者利益保護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平衡上的做法關(guān)注較少。
鑒于中國近期已提交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的申請,筆者以代表美國、中國和歐盟三大世界主要經(jīng)濟體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立場的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簡稱《中歐CAI》)為研究對象,對上述文本中實現(xiàn)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平衡的路徑進行研究,助力中國把握國際經(jīng)貿(mào)規(guī)則發(fā)展趨勢,在統(tǒng)籌國內(nèi)法治與涉外法治的視角下參與和引領(lǐng)國際經(jīng)貿(mào)規(guī)則的制定。
一、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失衡的現(xiàn)象及其根源考察
國際投資協(xié)定調(diào)整的是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關(guān)系,其核心在于協(xié)調(diào)公私?jīng)_突。在公私?jīng)_突中,條約設(shè)計的關(guān)鍵在于如何平衡東道國讓渡的主權(quán)權(quán)力與給予外國投資者的權(quán)利。(參見張倩雯:《國際貿(mào)易法與國際投資法國民待遇互動關(guān)系比較研究》,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17年第6期,第58頁。)根據(jù)聯(lián)合國貿(mào)易和發(fā)展會議發(fā)布的《2022年世界投資報告》,截至2021年末,全球已締結(jié)并生效共2 558個國際投資協(xié)定,但這些協(xié)定絕大多數(shù)締結(jié)于2010年之前,對核心概念和實體條款的規(guī)定都很寬泛,且保障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安全閥”較少。(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United Nations,2017,p.127.)協(xié)定實體條款模糊和寬泛的規(guī)定給予了仲裁庭擴大解釋條約的機會,有利于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而“安全閥”較少是因為這些老一代協(xié)定締結(jié)于早年的時代環(huán)境中,對公共健康、環(huán)境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東道國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biāo)考量不足。這兩方面因素導(dǎo)致老一代協(xié)定中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失衡,當(dāng)下絕大多數(shù)國際投資仲裁案件也是基于這些協(xié)定提起。(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form Accelerator,United Nations,2020,p.2-3.)下文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考察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失衡的根源。
(一)宏觀視角
1.投資協(xié)定源于資本輸出
從歷史的視角考察,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興起與資本輸出國鞏固其領(lǐng)導(dǎo)地位的需求密切相關(guān)。在殖民主義時代,西方的強權(quán)國家將國際法作為其統(tǒng)治和征服的工具。(參見[意]安東尼奧主·卡塞斯:《國際法》,蔡從燕等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頁。)國際投資法的產(chǎn)生亦是如此,即作為資本輸出國保護其利益的工具。(Charles Lipson,Standing Guard: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4,8,37-38;Nico Schrijver,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73-174;Peter Malanczuk,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Routledge,1997,p.91-100.)自17世紀(jì)開始,一些發(fā)達國家建立了海外貿(mào)易公司,例如著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表面上從事跨國貿(mào)易活動,實際上行使著國家職能,通過簽訂協(xié)議、軍事征服、建立堡壘等方式進行殖民掠奪。(Claudia Schnurmann,The VOC,the WIC,and Dutch Method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enaissance Studies,Vol.17:474,p.477-480(2003).)到18世紀(jì)末期,這些海外貿(mào)易公司的主要職責(zé)已然變成為帝國的擴張和管理服務(wù)。(C. H. 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1784-183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1,p.23.)由于這些海外貿(mào)易公司從事活動需要尋求法律依據(jù),故一系列國際法理論應(yīng)運而生。(Kate Mile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Origins, Imperialism and Conceptualizing the Environment,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Vol.21:1,p.13(2010).)由此,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起源在于為資本輸出國論證其行為合法性,并為保護其輸出資本提供法律工具。
2.投資自由化強調(diào)投資保護
由于許多國家信奉經(jīng)濟自由化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自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開始,諸多國家出于經(jīng)濟發(fā)展和政治考慮,開放其外商直接投資市場,推動了國家間的投資自由化,(Thomas L. Brewer & Stephen Young,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System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56;UNCTAD,Trend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An Overview,United Nations,1999.)各國開始將投資自由化納入外商直接投資政策之中。(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Trends and Determinants,United Nations,1998,p.94.)在國際社會積極推動投資自由化的宏觀背景下,投資保護備受強調(diào)。
投資自由化的措施主要包括消除市場扭曲、提高外國投資者待遇和加強市場監(jiān)督三方面內(nèi)容,(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Trends and Determinants,United Nations,1998,p.94.)這些內(nèi)容均有利于投資保護。投資自由化的表現(xiàn)之一便是將國民待遇、公平與公正待遇、最惠國待遇等提高外國投資者待遇的條款納入國際投資協(xié)定。進入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大量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開始納入這些投資者待遇條款,這本身就是投資自由化相較于保護東道國幼稚產(chǎn)業(yè)已占上風(fēng)的表現(xiàn)。(John K. Galbraith,A History of Economics:The Past as the Present,Penguin,1987,p.92-95.)受國際環(huán)境影響,中國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對待國民待遇條款的態(tài)度也于1990年后開始發(fā)生變化,自此中國開始接受有限的準(zhǔn)入后國民待遇,(關(guān)于中國在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對待國民待遇條款態(tài)度的歷史變遷,可參見ZHANG Qianwen,Opening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An Emerging ‘New Normal in China?,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Vol.11:437,p.437-476(2016).)這同樣可視作大浪淘沙的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側(cè)面映證。
(二)微觀視角
1.投資仲裁關(guān)注私法功能
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本質(zhì)兼具公法和私法功能。和傳統(tǒng)的國際商事仲裁不同,國際投資仲裁既具有解決個體爭議的私法功能,又具有實現(xiàn)東道國更廣泛的政策目標(biāo)的公共功能。(William W. Burke-White & Andreas von Staden,Private Litigation in a Public Law Sphere: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5:283,p.285(2010).)投資仲裁中屬于公法性質(zhì)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即為東道國為其公共利益而采取管制措施的法定權(quán)力。(Abram Chayes,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Harvard Law Review,Vol.59:1281,p.1302(1976);L. Harold Levinson,The Public Law/Private Law Distinction in the Courts,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Vol.57:1579,p.1593(1989).)近年來,雖然國際法學(xué)界更強調(diào)國際投資仲裁的公法性質(zhì),(Gus V. Harten,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Gus V. Harten & Martin Loughlin,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s a Specie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121,p.121(2006).)國際投資仲裁實踐卻更多地關(guān)注其私法性質(zhì),因此在案件中采取的解釋進路也源于私法的解釋標(biāo)準(zhǔn)。(William W. Burke-White & Andreas von Staden,Private Litigation in a Public Law Sphere: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5:283,p.285(2010).)
強調(diào)國際投資仲裁私法性質(zhì)的解釋進路導(dǎo)致仲裁庭更多著眼于保護爭端雙方的個體權(quán)利,而忽視了和東道國主權(quán)權(quán)力及執(zhí)行其政府職能相關(guān)的公共權(quán)力。
2.投資者法理上的弱勢地位
在東道國和外國投資者的二元關(guān)系中,投資者是自然人或法人,與東道國相比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以救濟途徑為例,根據(jù)《外交保護條款草案》的規(guī)定,投資者應(yīng)在用盡當(dāng)?shù)鼐葷蠓娇蓪で笸饨槐Wo。若投資者尋求當(dāng)?shù)鼐葷瑹o論是行政復(fù)議還是行政訴訟的結(jié)果均由東道國決定,這對于投資者而言往往難以保證公正性。東道國處于法理上強勢的一方,而投資者救濟途徑有限、物力財力貧乏,似乎應(yīng)當(dāng)?shù)玫街俨猛ジ嗟年P(guān)注。
國際投資協(xié)定源于海外貿(mào)易公司的資本輸出需求,因此設(shè)計各類實體待遇條款時著重于保護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在投資自由化的宏觀經(jīng)濟背景下,各國紛紛提高外國投資者待遇以促進投資的跨國流動。在國際投資仲裁中,仲裁庭關(guān)注投資仲裁的私法功能和投資者的弱勢地位,故在解釋所采標(biāo)準(zhǔn)、舉證責(zé)任分配等問題上都更傾向于保護投資者。上述原因?qū)е聦嵺`中仲裁庭常常選擇更有利于外國投資者的條約解釋路徑。
面對既有國際投資仲裁機制在協(xié)調(diào)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沖突問題上的失衡,新近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在文本設(shè)計上進行了大量改革。考察這些條約文本可見:一方面,文本并不脫離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初衷,即投資者利益保護;另一方面,文本中強化了東道國的規(guī)制權(quán),并限縮了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在這些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
2018年底生效的CPTPP和2020年達成的《中歐CAI》因其廣泛的成員覆蓋面、高水平的制度開放、與時俱進的規(guī)則創(chuàng)新而具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也代表了美國、中國和歐盟三大世界重要經(jīng)濟體參與國際投資協(xié)定改革的立場。下文以這兩項投資協(xié)定作為研究對象,詳細考察新近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對投資者利益保護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平衡路徑。
二、CPTPP和《中歐CAI》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
(一)CPTPP和《中歐CAI》概述
在世界貿(mào)易組織多邊貿(mào)易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區(qū)域貿(mào)易談判日漸活躍。2005年,智利、新西蘭、新加坡和文萊四國談判達成了“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jīng)濟伙伴關(guān)系協(xié)議”,此為《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的前身。2009年,美國宣布加入TPP談判,并主導(dǎo)了后續(xù)談判。2016年,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12個國家正式簽署TPP。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退出TPP,2017年11月TPP更名為CPTPP,后者于2019年初生效。CPTPP以附件形式凍結(jié)了部分TPP的條款,(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Ministerial Statement,Annex II—List of Suspended Provisions,Australia Government,http://dfat.gov.au/trade/agreements/tpp/news/Pag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ministerial-statement.aspx.)但TPP絕大部分規(guī)定得以保留。雖然美國目前未簽署CPTPP,但由于該條約體現(xiàn)了美國的主要利益訴求,美國在其后主導(dǎo)的雙邊或多邊經(jīng)貿(mào)協(xié)定中很可能延續(xù)此前的立場。
CPTPP的投資章節(jié)主要代表了美國對于國際投資協(xié)定改革的態(tài)度,《中歐CAI》則展示了世界另外兩大主要經(jīng)濟體——中國和歐盟對于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重構(gòu)的立場。2013年11月,中歐雙方共同宣布啟動中歐雙邊投資協(xié)定談判。在歷時七年多的艱苦談判后,2020年12月底中歐雙方共同宣布如期達成《中歐CAI》。《中歐CAI》的達成將對中歐投資關(guān)系良性發(fā)展注入一陣“強心劑”。一方面,歐盟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20年中國已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mào)易伙伴。
另一方面,歐盟也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
可見,達成一個兼顧開放與安全、平衡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外資規(guī)制權(quán)的中歐投資協(xié)定對于中國保護對外投資和吸引外商投資都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中歐投資協(xié)定談判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發(fā)達經(jīng)濟體之間的談判。《中歐CAI》中對于投資者和東道國的利益平衡路徑代表著中歐兩大世界主要經(jīng)濟體對于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的共識,或許意味著“全球雙邊投資協(xié)定2.0”時代的到來,(SHAN Wenhua & WANG Lu,The China-EU BIT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BIT 2.0,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30:260,p.260-267(2015).)將對于整個國際投資法體系的改革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縱觀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中對重構(gòu)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規(guī)定,可將其概括為細化實體待遇條款、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增設(shè)程序透明度要求三方面內(nèi)容。
(二)澄清實體待遇條款
CPTPP投資章節(jié)的一大特點是其對實體待遇條款進行了細化,尤其是進一步明確了投資待遇的適用范圍。
1.以附注解釋國民待遇
約四分之一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都涉及國民待遇條款。(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form Accelerator,United Nations,2020,p.15.)國民待遇條款是國際投資仲裁的核心爭議條款,但國際投資協(xié)定對其規(guī)定往往十分簡單,通常僅表述為“東道國有義務(wù)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外國投資以不低于在相似情形下給予本國投資者以及本國投資的待遇”,(Rudolf Dolzer & Margrete Steven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Martinus Nijhoff,1995,p.15.)針對條款中的“相似情形”“不低于”等關(guān)鍵詞缺乏進一步釋義,而將解釋權(quán)交予仲裁庭,但仲裁庭對這些核心概念的解釋并不一致。例如,關(guān)于競爭關(guān)系與認定外國投資者和本國投資者是否處于“相似情形”具有何種聯(lián)系這一問題,不同的仲裁庭曾作出不同的解釋。在“S.D Myers訴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曾采和國際貿(mào)易法認定“同類產(chǎn)品”相似的路徑,(例如日本酒稅案(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WT/DS8/R,6.23),韓國酒稅案(Korea-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WT/DS75/AB/R,para.114),智利酒稅案(Chile-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WT/DS110/R,paras.7.3-8.1)和歐盟石棉案(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WT/DS135/AB/R,paras.99-114。)即通過外國投資者和本國投資者是否具備競爭性來認定二者是否處于相似情形。(S.D. Myers,Inc. v. Canada,NAFTA(UNCITRAL),Partial Award,para.251.)但以“Methanex訴美國案”為代表的仲裁庭在其后案件中都未采納國際貿(mào)易法認定“同類產(chǎn)品”的路徑。(Occidental Exploration & Prod. Co. v. Republic of Ecuador,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Case No. Un 3647,Award,para.176;
Pope & Talbot,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NAFTA(UNCITRAL),Award on the Merits of Phase 2,para.57.)鑒于此,國際投資協(xié)定對國民待遇條款文本改革的重點應(yīng)在于確立“相似情形”的標(biāo)準(zhǔn)。(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form Accelerator,United Nations,2020,p.15.)
CPTPP的投資章節(jié)對此作出了回應(yīng)。該協(xié)定在國民待遇條款上最大的特點就是輔之以附注的形式,對文本條款提供進一步解釋。鑒于投資仲裁實踐對國民待遇的解釋進路不盡相同,各締約國在擬定CPTPP文本的同時,也達成了對文本第9條第4款國民待遇中“相似情形”的解釋附注,以增強文本的可預(yù)見性。
附注首先明確了舉證責(zé)任。第2條規(guī)定適用國民待遇條款時,由投資者承擔(dān)證明外國投資和本國投資處于“相似情形”的舉證責(zé)任,并強調(diào)了國民待遇的宗旨在于防止基于國籍的歧視。第3條指出實踐中認定“相似情形”應(yīng)當(dāng)具體分析,綜合考量,并特地點明應(yīng)當(dāng)考慮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競爭性、法律和調(diào)控環(huán)境以及合法的公共利益目標(biāo)這三個關(guān)鍵要素,(Drafters Note on Interpretation of ‘In Like Circumstances Under Article
9.4(National Treatment) and Article 9.5(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Article 2,3,F(xiàn)oreign Affairs & Trade of New Zealand(05 November 2015),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de-agreements/CPTPP/Interpretation-of-In-Like-Circumstances.pdf.)表現(xiàn)出締約國對公共利益這一價值的關(guān)注。(參見石靜霞、馬蘭:《〈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TPP)投資章節(jié)核心規(guī)則解析》,載《國家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1期,第79頁。)
針對仲裁庭對國民待遇認定路徑的不一致,CPTPP投資章節(jié)的國民待遇條款通過附注解釋將文本解釋與仲裁實踐相結(jié)合,起到了對仲裁實踐的指引作用。一方面,在文本中對仲裁實踐中基本達成一致的解釋路徑加以明確。例如,在“Archer Daniels Midland訴墨西哥案”“Pope & Talbot訴加拿大案”和“UPS訴加拿大案”中,仲裁庭均指出,仲裁庭在考察國民待遇中“相似情形”時應(yīng)當(dāng)通盤考慮并全面評估。(Archer Daniels Midland,et al. v.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 ARB(AF)/04/05,Award,para.197;Pope & Talbot,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NAFTA(UNCITRAL),Award on the Merits of Phase 2,para.75;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 v. Government of Canada,NAFTA(UNCITRAL),Award on the Merits,para.86.)CPTPP附注第3條也對此進行了確認,認為對“相似情形”的判斷應(yīng)該具體案件具體分析,且對案件所有相關(guān)情況通盤考量。(Drafters Note on Interpretation of ‘In Like Circumstances Under Article 9.4(National Treatment) and Article 9.5(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Article 3,F(xiàn)oreign Affairs & Trade of New Zealand(05 November 2015),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de-agreements/CPTPP/Interpretation-of-In-Like-Circumstances.pdf. )另一方面,在文本中對仲裁案件中爭議較大的問題予以澄清。例如CPTPP附注第3條明確了競爭關(guān)系對于認定外國投資者和本國投資者是否處于“相似情形”的必要性。此外,CPTPP附注第4條和第5條還輔之以《北美自由貿(mào)易協(xié)議》涉及國民待遇條款中“相似情形”問題認定的典型案例。(Drafters Note on Interpretation of ‘In Like Circumstances Under Article 9.4(National Treatment) and Article 9.5(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Article 3,4,5,F(xiàn)oreign Affairs & Trade of New Zealand(05 November 2015),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de-agreements/CPTPP/Interpretation-of-In-Like-Circumstances.pdf.)
中國的大多數(shù)國際投資協(xié)定都未對國民待遇條款作進一步解釋。但是,《中歐CAI》借鑒了CPTPP的部分做法,在第一部分第4條“國民待遇”的規(guī)定中也通過腳注明確了對“相似情形”的理解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個案審查。或許因為中國和歐盟中的部分國家均非判例法國家,《中歐CAI》并未如CPTPP附注第4條運用具體的案例指引中國和歐盟認可的相關(guān)國際投資仲裁案例。所以,在具體的仲裁實踐中,仲裁庭在適用《中歐CAI》國民待遇條款時對于案例的選擇仍然具有相較于適用CPTPP國民待遇條款更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
2.限制最惠國待遇適用條件
最惠國待遇是非歧視待遇的重要內(nèi)容,約五分之一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涉及該條款的適用。(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form Accelerator,United Nations,2020,p.18.)老一代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對最惠國待遇通常以“定義+例外”的形式界定,例如規(guī)定締約國給予締約另一方投資者的投資和與該投資有關(guān)的待遇“應(yīng)不低于給予任何第三國投資者的投資和與投資有關(guān)的活動的待遇”,并附之以自由貿(mào)易區(qū)
、關(guān)稅或經(jīng)濟同盟,稅收和邊境貿(mào)易等常見例外。(例如1992年《中國與亞美尼亞雙邊投資協(xié)定》第3條第2款和第3款。)但這些例外基本未涉及程序性事項,這就導(dǎo)致仲裁庭可能通過條約解釋將締約雙方承諾的利益多邊化,進而擴大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范圍。最惠國待遇是否適用于投資爭端解決的程序事項這一問題曾在國際投資仲裁實踐中引發(fā)不小的爭議。(參見徐崇利:《從實體到程序:最惠國待遇適用范圍之爭》,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50頁。)仲裁庭對此作出的矛盾裁決也是國際投資仲裁機制被質(zhì)疑“正當(dāng)性危機”的原因之一。(國際投資條約解釋的現(xiàn)狀過于強調(diào)投資者利益保護,而忽視了東道國的正當(dāng)利益,這正是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的缺陷在實體條款方面的重要表現(xiàn)。鑒于此,有學(xué)者提出國際投資法體系正遭遇“正當(dāng)性危機”。M. Sornarajah,A Coming Crisis:Expansionary Trend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in Karl P. Sauvant ed.,Appeals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9-45;Susan D. Franck,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F(xiàn)ordham Law Review,Vol.73:1521,p.1523(2005).)針對最惠國待遇是否適用于投資爭端解決的程序事項這一問題,CPTPP予以明確規(guī)定,即最惠國待遇中的“待遇”不包括其他國際投資協(xié)定和其他貿(mào)易協(xié)定中的爭端解決機制。
《中歐CAI》對于最惠國待遇是否適用于投資爭端解決的程序事項這一問題的明確有些許不同。一方面,《中歐CAI》在第5條第2款說明“締約國與第三國締結(jié)的其他國際條約中的實體條款并不本身構(gòu)成本條中所指的‘待遇”;另一方面,該條第3款專門排除了“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程序與其他任何爭端解決程序”被視為最惠國待遇中的“待遇”。
3.細化公平與公正待遇內(nèi)涵
國際投資協(xié)定納入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的初衷意在提升東道國的良法善治,(UNCTAD,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United Nations,2015,p.97.)但協(xié)定文本中的表述通常僅為籠統(tǒng)地要求“締約一方的投資者在締約另一方的領(lǐng)土內(nèi)的投資和與投資有關(guān)的活動應(yīng)享受公平與公正的待遇”,(例如2001年《中國與塞浦路斯雙邊投資協(xié)定》第3條第1款。)缺乏針對何為公平、何為公正的進一步闡釋。公平與公正待遇因其內(nèi)涵的模糊性給予了仲裁庭極大的解釋空間,因此被一些學(xué)者稱為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的“帝王條款”。(參見徐崇利:《公平與公正待遇標(biāo)準(zhǔn):國際投資法中的“帝王條款”?》,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08年第5期,第123-134頁;Tanya Gupta,Exploring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FET) Principle and Balancing Investor-State Righ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Management & Humanities,Vol.4:1398,p.1402(2021)。)正因該條款給予了投資者拓展對其保護范圍的可能性,它成為了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最常被訴至仲裁庭的條款,在超過80%的案件中投資者都會主張東道國的行為違反了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UNCTA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form Accelerator,United Nations,2020,p.20.)
鑒于此,細化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內(nèi)涵是近年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的改革趨勢,有助于提升該條款適用的可預(yù)見性。中國的應(yīng)對之策是通過習(xí)慣國際法之最低待遇標(biāo)準(zhǔn)對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加以約束,例如《中國與加拿大雙邊投資協(xié)定》規(guī)定“公平與公正待遇”的概念并不要求給予由被接受為法律的一般國家實踐所確立之國際法要求給予外國人的最低待遇標(biāo)準(zhǔn)之外或額外的待遇。也有一些國際投資協(xié)定在運用習(xí)慣國際法之最低待遇標(biāo)準(zhǔn)限定公平與公正待遇的內(nèi)涵之外,還通過明確公平與公正待遇的構(gòu)成要素對仲裁庭適用該條款加以限制。CPTPP在運用習(xí)慣國際法最低待遇標(biāo)準(zhǔn)約束公平與公正待遇標(biāo)準(zhǔn)之外,更進一步細化了公平與公正待遇的內(nèi)涵,規(guī)定“公平與公正待遇包括依照世界主要法律體系中的正當(dāng)程序原則,不在刑事、民事、行政司法程序中拒絕司法”,即“正當(dāng)程序原則”和“不得拒絕司法”。此外,CPTPP進一步明確“為提高確定性,僅僅是一締約方采取或未采取可能不符合投資者期待的行動,并不構(gòu)成對本條的違反,即使所涉投資因此而遭受損失”。(參見CPTPP第九章第9.6條第2款、第4款。)
(三)擴張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
正如前文所述,國際投資協(xié)定產(chǎn)生的初衷是資本輸出國意在加強對海外投資的保護,因此老一代協(xié)定的主體內(nèi)容是投資保護條款,對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關(guān)注不足。例如許多協(xié)定都在序言中將“為投資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鼓勵、促進和保護投資者”納入締約目標(biāo),但對保障東道國的規(guī)制權(quán)只字未提。在協(xié)定文本中常見的保障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條款僅限于部分實體條款的例外,例如規(guī)定保護東道國的公共利益可作為征收、國有化措施的例外,但協(xié)定中往往缺乏一般例外和根本安全例外條款,或?qū)iT的規(guī)制權(quán)條款。
近年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發(fā)展存在人本化趨勢,即日趨關(guān)注跨國投資活動中伴隨而生的環(huán)境保護和人權(quán)保護問題。(參見劉筍:《國際法的人本化趨勢與國際投資法的革新》,載《法學(xué)研究》2011年第4期,第196-208頁。)歐盟是推動國際投資協(xié)定人本化發(fā)展的重要實踐者。早期歐盟締結(jié)的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多通過一般例外條款保障締約國對于公共安全、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動植物生命健康等公共利益的規(guī)制權(quán),例如2012年《哥倫比亞—厄瓜多爾—歐盟—秘魯貿(mào)易協(xié)定》。而晚近歐盟締結(jié)的條約不僅通過例外條款保障締約國的規(guī)制權(quán),還傾向于通過單獨的規(guī)制權(quán)章節(jié)強調(diào)締約國有權(quán)追求與投資相關(guān)的公共利益。例如,2016年《歐盟與加拿大綜合性經(jīng)濟貿(mào)易協(xié)議》就以第二十一章“規(guī)制合作”專門規(guī)定了東道國行使規(guī)制權(quán)的原則、目標(biāo)、程序等內(nèi)容。2018年《歐盟與新加坡投資保護協(xié)定》在“投資與規(guī)制措施”條款中規(guī)定了締約國有權(quán)為達成合法的公共利益而行使規(guī)制權(quán),這些公共利益就包括“保護公共健康、社會設(shè)施、公共教育、安全、環(huán)境或公共道德,社會或消費者隱私保護和促進與保護文化多元”。(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of the Other Part,2018,Article 2.2.)2019年《歐盟與越南投資保護協(xié)定》也有類似規(guī)定。可見,歐盟對于通過投資協(xié)定保障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追求已從單一運用一般例外條款轉(zhuǎn)向了綜合運用“一般例外+規(guī)制權(quán)章節(jié)”,更加細致、清晰地界定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這在《中歐CAI》中也得以體現(xiàn)。
根據(jù)已公布的《中歐CAI》文本,協(xié)定第一章開篇即在“目標(biāo)”部分重申了締約國為達成合法的公共目的有權(quán)行使規(guī)制權(quán)。針對規(guī)制權(quán)的內(nèi)容,第四章“投資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分別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三個方面——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針對“投資與環(huán)境”“投資與勞工”的相關(guān)問題細化了締約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內(nèi)涵。相較于早期通過一般例外條款規(guī)定締約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做法,《中歐CAI》對規(guī)制權(quán)的規(guī)定更加細致。例如在“投資與環(huán)境”部分,《中歐CAI》就分別從環(huán)境保護的程度,構(gòu)建與投資有關(guān)的環(huán)境問題的對話和合作機制,推動多邊環(huán)境條約,投資有利于綠色增長,投資和氣候變化五個部分詳細規(guī)定了締約國在投資過程中保護環(huán)境利益的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容,相比一般例外條款中籠統(tǒng)地規(guī)定締約國有權(quán)為“保護環(huán)境”行使規(guī)制權(quán)詳細了許多。
相較《中歐CAI》,CPTPP投資章節(jié)對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規(guī)定就簡略了很多。CPTPP沿襲了近年美式雙邊投資協(xié)定的做法,在第9.16條中籠統(tǒng)地規(guī)定了東道國有權(quán)針對與環(huán)境、健康或其他規(guī)制目標(biāo)相關(guān)的外國投資活動采取任何規(guī)制措施。
(四)增設(shè)程序透明度要求
透明度是國際貿(mào)易法的基本原則,可見于1947年的《關(guān)稅與貿(mào)易總協(xié)定》中。但是許多老一代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未納入專門的透明度條款,即使納入了透明度章節(jié)或條款,相關(guān)規(guī)定也較為簡單,主要是“締約方應(yīng)確保與本協(xié)議涵蓋事項相關(guān)的東道國法律、法規(guī)、程序和行政裁決及時公布”此類。(例如2007年《巴拿馬與美國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第十八章。UNCTAD,Transparency: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United Nations,2012,p.16.)相較于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國際投資仲裁實踐更多在裁判中涉及透明度要求,例如仲裁庭在釋義公平與公正待遇時認為其中的正當(dāng)程序原則包含東道國行為應(yīng)具備透明度的內(nèi)涵。(Murphy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mpany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Ecuador II,PCA Case No. 2012-16 (formerly AA 434),Partial Final Award,6 May 2016,para.206. )投資者應(yīng)當(dāng)期待東道國行為具備一致性,盡量不存在模糊地帶,與投資者的關(guān)系保持透明度。此外,投資者應(yīng)提前充分得知與其投資相關(guān)的規(guī)則和政策,以及相關(guān)政策的目的,以便其按照這些政策規(guī)劃其投資。(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 ARB/02/8,Award,6 February 2007,para.298.)
作為新一代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歐CAI》的一大重要特點是在文本中強調(diào)并細化了投資監(jiān)管透明度的要求。在《中歐CAI》(已公布文本)中,共有二十余處提到透明度(transparency/transparent)要求,對透明度的具體要求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對設(shè)置執(zhí)照和許可條件的透明度要求。(參見《中歐CAI》第三章第一節(jié)、第二節(jié)。
)
第三章“監(jiān)管框架”首先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提出締約國設(shè)置執(zhí)照和許可的條件應(yīng)當(dāng)客觀、透明。該章第二節(jié)進一步從透明度的一般要求、法律法規(guī)公開的程序及范圍、建立咨詢聯(lián)絡(luò)點、行政程序、審查和上訴、標(biāo)準(zhǔn)制定等方面具體細化了透明度要求。
第二是對國有企業(yè)的透明度要求。(參見《中歐CAI》第二章、第三章。)《中歐CAI》第二章第3條通過“涵蓋實體”規(guī)則為中國國有企業(yè)進行了量體裁衣式的規(guī)定。該部分通過規(guī)定國有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提供關(guān)鍵信息、自我解釋行為無害、遵守國際良治實踐保障外國投資者在投資活動中與締約國國有企業(yè)競爭時的透明度。此外,第三章“監(jiān)管框架”下第二節(jié)第8條規(guī)定了“補貼的透明度”,這指向了中國在國際上較為敏感的國有企業(yè)補貼問題。該條要求締約國每年公開其給與補貼的目的、法律依據(jù)、形式、數(shù)量、對象,并規(guī)定了外國投資者對締約國補貼提出異議的機制。
第三是引入了金融服務(wù)監(jiān)管國際標(biāo)準(zhǔn)。(參見《中歐CAI》第三章第三節(jié)。)在金融服務(wù)監(jiān)管方面,《中歐CAI》鼓勵雙方盡可能地適用監(jiān)管方面的國際公認標(biāo)準(zhǔn),尤其是G20、金融穩(wěn)定委員會、巴塞爾銀行監(jiān)管委員會、國際保險監(jiān)管者協(xié)會、國際證監(jiān)會組織、反洗錢金融特別行動工作組以及稅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換全球論壇等組織采納的標(biāo)準(zhǔn)。
第四是透明度可適用爭端解決機制。(參見《中歐CAI》附件一。)在多數(shù)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中,執(zhí)法的透明度被置于專門的競爭章節(jié)中,并不適用爭端解決機制。但《中歐CAI》在爭端解決機制章節(jié)規(guī)定執(zhí)法的透明度本身可以適用爭端解決機制,這相當(dāng)于給透明度要求裝上了“牙齒”,促使國內(nèi)法對此落實。歐盟近年非常重視在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加入透明度要求,《中歐CAI》也反映了歐盟這一關(guān)切。
與《中歐CAI》貫穿始終的透明度規(guī)定不同,CPTPP投資章節(jié)僅在第9.23條“仲裁的開展”和第9.24條“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兩項程序性條款中提到了透明度要求。
三、CPTPP和《中歐CAI》中的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平衡路徑評析
(一)限縮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
由于國際投資仲裁案件缺乏先例效力,加之仲裁庭的組成具有隨機性,故投資仲裁實踐存在碎片化特征。投資仲裁庭面對同樣的事實作出全然不同的認定這一現(xiàn)象已多為主權(quán)國家詬病,自相矛盾的裁判損害了投資仲裁機制的確定性及投資者和東道國的合理期待,這也是導(dǎo)致國際投資仲裁“正當(dāng)性危機”的成因之一。(Susan D. Franck,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F(xiàn)ordham Law Review,Vol.73:1521,p.1558(2005).)究其根源,實體法規(guī)則的模糊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參見郭玉軍:《論國際投資條約仲裁的正當(dāng)性缺失及其矯正》,載《法學(xué)家》2011年第3期,第146頁。)當(dāng)條款內(nèi)涵模糊時,締約國在事實上將條約的解釋權(quán)交給了仲裁庭。缺乏明確的實體法規(guī)則指引會導(dǎo)致不同的仲裁員運用全然不同的解釋思路,對同一事實作出大相徑庭的認定結(jié)果。正如前文所述,仲裁庭基于平衡投資者法理上的弱勢地位等原因常采取更加有利于投資者利益保護的解釋路徑,導(dǎo)致了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失衡。以公平與公正待遇為例,“公平”與“公正”本是模糊的詞語,缺乏對其進一步的釋明導(dǎo)致該條款存在濫用的可能性,例如在多起案件中仲裁庭對其進行擴大解釋,尤其是涉及投資者合法期待保護的問題,仲裁庭常常過度保護投資者利益而無視東道國的公共利益,同時也嚴重損害了該條款適用的可預(yù)見性。(UNCTAD,F(xiàn)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United Nations,2012,p.11.)因此,新一代國際投資協(xié)定在文本改革中注重澄清實體待遇條款,這將限縮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有利于對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的平衡。
CPTPP投資章節(jié)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正是部分限縮投資者權(quán)利和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鑒于仲裁庭存在沖突裁決的現(xiàn)狀,該章節(jié)澄清了國民待遇中“相似情形”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明確最惠國待遇條款不適用于爭端解決機制,闡明公平與公正待遇的內(nèi)涵包括“正當(dāng)程序原則”和“不得拒絕司法”,尤其是CPTPP文本及附注在對條約的解釋中與仲裁案件結(jié)合,相當(dāng)于對既有的仲裁案件進行了符合本國立場的篩選,有助于形成對該條約解釋的統(tǒng)一仲裁實踐,增強締約雙方和外國投資者的可預(yù)見性,提升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正當(dāng)性。
(二)“國家回歸”
CPTPP投資章節(jié)對老一代協(xié)定文本進行小修小補,但不對投資協(xié)定進行根本性的改變。這與美國在CPTPP的前身——TPP談判中的主導(dǎo)作用密切相關(guān)。申言之,TPP投資章節(jié)的諸多條款與2012年美國投資協(xié)定范本具有高度相似性。(參見石靜霞、馬蘭:《〈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TPP)投資章節(jié)核心規(guī)則解析》,載《國家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1期,第82頁。)因此,CPTPP的文本改革模式也代表著美國對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的立場。
從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到國際投資協(xié)定,美國作為對外投資大國,一直都是致力于保護海外投資企業(yè)的先驅(qū)者。CPTPP雖然部分限縮了外國投資者的權(quán)利,但并沒有改變投資協(xié)定產(chǎn)生的初衷,即吸引外國投資與保護外國投資者,這也契合美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本輸出國的利益需求。CPTPP對于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適用于美國這樣的海外投資者眾多的對外投資強國,有利于在適當(dāng)退讓投資者權(quán)利的同時促使締約國達成協(xié)議,但不一定適用于其他國家。
《中歐CAI》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關(guān)注東道國利益,重在從拓寬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和增設(shè)程序透明度要求的角度強化東道國的規(guī)制權(quán),這與歐盟晚近在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的做法也是一脈相承的。《中歐CAI》增加了專門的“規(guī)制權(quán)”章節(jié),對傳統(tǒng)的投資協(xié)定文本修改幅度較大,盡力拓展東道國的規(guī)制權(quán)空間。《中歐CAI》對透明度的強調(diào)突破了以往多數(shù)協(xié)定將透明度僅作為東道國義務(wù)的做法,通過規(guī)定國有企業(yè)的透明度要求等方式對企業(yè)的社會責(zé)任提出要求,投資者也應(yīng)承擔(dān)透明度義務(wù)。此外,老一代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通常將透明度義務(wù)寬泛地界定為“締約方應(yīng)確保與本協(xié)議涵蓋事項相關(guān)的東道國法律、法規(guī)、程序和行政裁決及時公布”,內(nèi)容涵蓋廣泛,這對東道國的積極作為提出了較高的要求。(UNCTAD,Transparency: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United Nations,2012,p.70.)相較之下,《中歐CAI》澄清透明度的做法限定了國家承擔(dān)的透明度義務(wù)范圍,使國家在公布信息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和控制本國的公布成本之間得以達到平衡。正如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國際貿(mào)易委員會在近期交流討論《中歐CAI》時所強調(diào)的,歐盟認為《中歐CAI》的一大特點就是“再平衡”,尤其是重新平衡歐盟和中國在市場準(zhǔn)入和投資問題上的不對稱,(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 Publishes Market Access Offers of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European Commission(12 March 2021),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news/commission-publishes-market-access-offers-eu-china-investment-agreement-2021-03-12_en.)故該協(xié)定是協(xié)調(diào)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的重要工具。
筆者認為,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采取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雖然側(cè)重點不同,但都增加了東道國在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的話語權(quán)比重,同樣體現(xiàn)了“國家回歸”,只是程度不同。2011年,美國學(xué)者José E. Alvarez提出國際投資法中正出現(xiàn)“國家回歸”的現(xiàn)象,(José E. Alvarez,The Return of the State,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223,p.223(2011).)即國家正尋求弱化對其主權(quán)限制的路徑。這是由國際社會面臨日益復(fù)雜的安全問題、國際條約日益顯露出對主權(quán)的制約、國際組織日漸脫離國家約束、私人實力增強制約國家主權(quán)等因素共同導(dǎo)致的。(參見蔡從燕:《國家的“離開”“回歸”與國際法的未來》,載《國際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9頁;楊希:《國際投資法中的國家“回歸”趨勢——兼評我國〈外商投資法〉中的規(guī)制權(quán)》,載《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21年第1期,第129-138頁。)國際投資法領(lǐng)域“國家回歸”不僅表現(xiàn)在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程序性改革方面,(例如歐盟關(guān)于投資法院的改革倡議便是一例,詳見朱明新:《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革新與國家的“回歸”》,載《國際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頁。)還體現(xiàn)在投資協(xié)定文本的實體條款中。以CPTPP為例,其中的國民待遇條款實為各國為建立更加平衡的國際投資法體系進行的探索,展現(xiàn)出國際社會,尤其是主要的發(fā)達國家在制定國際投資協(xié)定、改革國際投資法體系過程中為平衡外國投資者私人權(quán)利和投資東道國主權(quán)權(quán)力所作出的努力。和CPTPP相比,《中歐CAI》中“國家回歸”的表現(xiàn)更明顯、力度更大。
國際投資協(xié)定本文中的“國家回歸”與國際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變化密切相關(guān),可分別從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兩個視角追溯其緣由。伴隨國際格局變遷,如中國、印度一類新興經(jīng)濟體崛起,發(fā)達國家不再僅僅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資本輸出國。以“加拿大橫加公司訴美國案”為例,越來越多的發(fā)達國家被訴至國際投資仲裁庭,導(dǎo)致其開始意識到國際投資協(xié)定不再完全充當(dāng)保護輸出資本國利益的工具。因此,發(fā)達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作用,反思自己兼具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的雙重身份,重新設(shè)計更為平衡的投資協(xié)定以彌補早前自由主義占主導(dǎo)地位的投資體制帶來的不利因素。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如阿根廷等國家頻繁地被外國投資者提起國際投資仲裁,疲于應(yīng)對的同時也要承擔(dān)極高的風(fēng)險,面臨坐等國內(nèi)經(jīng)濟崩潰或給予外國投資者巨額賠償?shù)膬呻y困境。(轉(zhuǎn)引自單文華:《從“南北矛盾”到“公私?jīng)_突”:卡爾沃主義的復(fù)蘇與國際投資法的新視野》,載《西安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8年第4期,第12頁。 )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現(xiàn)有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從條款設(shè)計上平衡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建立更具有可持續(xù)發(fā)展力的國際投資法體系,成為了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共同訴求。
當(dāng)José E. Alvarez指出國際投資法中正出現(xiàn)“國家回歸”的現(xiàn)象時,逆全球化思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抬頭。此后,2016年的英國脫歐、2017年美國政府換屆后的頻頻“退群”、2020年的新冠疫情蔓延、2022年的俄烏沖突等國際事件都進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的態(tài)勢。在此情形下,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國家回歸”的趨勢很可能在未來得到進一步加強,國家可能在協(xié)定中通過更多的條款設(shè)置強化東道國對外國投資的規(guī)制權(quán)。
(三)與國際投資仲裁改革立場一致的文本改革
CPTPP的投資章節(jié)部分限縮了外國投資者的權(quán)利,但沒有改變國際投資協(xié)定保護外國投資的宗旨,這與美國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的改革立場相一致。美國依靠其政府和企業(yè)強大的議價能力,以及在國際投資仲裁庭中眾多仲裁員的優(yōu)勢,成為了現(xiàn)行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最主要受益方,因此對于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持保守態(tài)度。(參見王鵬:《中立、責(zé)任與參與:國際投資仲裁的多邊改革與中國對策》,載《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1-122頁。)
《中歐CAI》折射出歐盟對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的積極態(tài)度,重在拓展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空間。歐盟在投資協(xié)定中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與其對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的態(tài)度也是一致的。2015年起,歐盟提出多邊投資法院改革,其關(guān)鍵之處在于將設(shè)置上訴法庭,并獨立選任全職法官。(European Commission,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Project,European Commission,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nforcement-and-protection/multilateral-investment-court-project_en.)考慮到平衡東道國和外國投資者利益的必要性,投資仲裁庭需要更多公正裁決的仲裁員。因此,《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第6條的重要性得以凸顯。第6條規(guī)定仲裁員需要提交一份報告,說明其與仲裁案件中的原被告在過去和現(xiàn)在的專業(yè)上、經(jīng)濟上及其他方面一切的聯(lián)系。該條在保障公正裁決的問題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其他仲裁庭并沒有沿襲《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第6條的規(guī)定。考慮到政治因素,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中建立一個綜合性的、永久的上訴機制仍然任重而道遠。整體而言,歐盟對投資仲裁改革的倡議較為激進,主張設(shè)置具有上訴機制的國際投資法庭,從根本上改革現(xiàn)行國際投資仲裁機制,與美國小修小補的保守倡議形成鮮明反差。(參見王鵬:《中立、責(zé)任與參與:國際投資仲裁的多邊改革與中國對策》,載《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0頁;鄧婷婷:《歐盟多邊投資法院:動因、可行性及挑戰(zhàn)》,載《中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年第4期,第62-72頁。)
CPTPP投資章節(jié)與《中歐CAI》構(gòu)建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的路徑均是國家通過優(yōu)化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對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改革作出回應(yīng)。在“正當(dāng)性危機”下,雖然確有部分國家徹底放棄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或退出國際投資協(xié)定,但更多國家仍然努力通過國際投資仲裁的多邊改革路徑和重新設(shè)計適合自己的投資協(xié)定文本尋求構(gòu)建更加平衡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在近年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中,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以各自的方式重新構(gòu)建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平衡。合理平衡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也成為了國際投資協(xié)定可持續(xù)發(fā)展改革的核心要義之一。
四、對中國構(gòu)建利益平衡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啟示
作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舉措,中國正積極參與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多邊改革。如何選擇有利于中國的國際投資仲裁改革路徑是當(dāng)前國際投資法學(xué)界重點關(guān)注的問題。由于兼具資本輸入大國和資本輸出大國的雙重身份,構(gòu)建合理平衡外國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是中國積極保護海外投資同時有效吸引外商投資的優(yōu)先選擇。在參與投資仲裁機制改革的過程中,對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條款的設(shè)置十分重要。通過澄清協(xié)定中的實體待遇條款有助于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此外,國際投資協(xié)定需因應(yīng)時代需求,對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環(huán)境保護等時代議題作出回應(yīng),故有必要合理拓展協(xié)定的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對于協(xié)定中的未盡事宜,仲裁庭可能會指引至東道國國內(nèi)法,這就要求中國夯實國際投資協(xié)定相關(guān)條款的國內(nèi)法基礎(chǔ)。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中提供的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平衡路徑在中國未來締結(jié)國際投資協(xié)定時或可借鑒。國際投資協(xié)定改革也促使中國國內(nèi)外商投資立法進一步完善,這也是統(tǒng)籌推進國內(nèi)法治與涉外法治的必然要求。具體而言,中國可在完善國際投資協(xié)定和國內(nèi)相關(guān)立法時采取以下措施。
(一)澄清協(xié)定的實體待遇條款
中國近年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針對最惠國待遇程序適用問題和公平與公正待遇內(nèi)涵的模糊性問題,已作出類似于CPTPP和《中歐CAI》的限制和澄清,例如《中國與加拿大雙邊投資協(xié)定》第5條第3款明確規(guī)定
最惠國待遇中的“待遇”不包括國際投資協(xié)定和其他貿(mào)易協(xié)定中的爭端解決機制。這既有助于保障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期待,又可以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中國限定公平與公正待遇內(nèi)涵的做法是通過習(xí)慣國際法之最低待遇標(biāo)準(zhǔn)對其加以約束。相較之下,CPTPP對公平與公正待遇構(gòu)成要件的細化方式有助于限制仲裁庭的寬泛解釋,對于該條約的適用具有更強的可預(yù)見性。采用列舉式清單的方式改革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也成為了近年國際投資協(xié)定文本改革的新趨勢,(參見王彥志:《國際投資法上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改革的列舉式清單進路》,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15年第6期,第149-153頁。)中國可以加入CPTPP為契機嘗試此種改革進路。
此外,中國過往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多缺乏對國民待遇“相似情形”構(gòu)成要件的進一步解釋,而該要件正是適用國民待遇條款的關(guān)鍵。針對國際投資仲裁實踐不一致的現(xiàn)實,尚未見中國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表明對仲裁實踐的立場。當(dāng)前仲裁庭在認定國民待遇的“相似情形”要件時存在不同的裁判路徑,(參見張倩雯:《國際投資仲裁中國民待遇條款的“相似情形”問題研究》,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15年第2期,第292-296頁。)CPTPP國民待遇條款附注將文本與實踐結(jié)合,有助于引導(dǎo)仲裁庭采納己方認可的裁判路徑,該做法可為中國借鑒,中國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可在設(shè)置國民待遇條款時表明對仲裁實踐的立場。
(二)在協(xié)定中合理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
《中歐CAI》表明,東道國在運用傳統(tǒng)的國家安全例外、一般例外條款之外,亦可借用可持續(xù)發(fā)展條款維護其合理規(guī)制權(quán)。《中歐CAI》從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三方面細化東道國的規(guī)制權(quán),回應(yīng)了聯(lián)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將社會、經(jīng)濟和環(huán)境確立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三個層面。(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21 October 2015),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291/89/PDF/N1529189.pdf?OpenElement.)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思潮再次抬頭。在未來締結(jié)國際投資協(xié)定時,各國可能更加重視拓展本國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
中國早年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多關(guān)注投資保護條款,對規(guī)制權(quán)的關(guān)注不足,老一代協(xié)定納入規(guī)制權(quán)規(guī)則的比例低于全球協(xié)定的平均水平。(參見曾建知:《國際投資法中的規(guī)制權(quán)研究》,廈門大學(xué)2018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184頁。)晚近因應(yīng)維護公共秩序、保障國家安全、應(yīng)對數(shù)字經(jīng)濟挑戰(zhàn)等需求,中國的協(xié)定開始納入例外條款,(參見張倩雯:《數(shù)據(jù)跨境流動之國際投資協(xié)定例外條款的規(guī)制》,載《法學(xué)》2021年第5期,第100頁。)主要通過一般例外條款、根本安全例外或國家安全例外、金融審慎例外等條款保障本國對外資的規(guī)制權(quán)。中國的協(xié)定在未來改革時可進一步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回應(yīng)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等新的時代需求。
(三)夯實協(xié)定條款的國內(nèi)法基礎(chǔ)
依據(jù)《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第42條的規(guī)定,在仲裁庭釋義國際投資協(xié)定時,東道國的國內(nèi)法可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jù)。事實上,仲裁庭在釋義公平與公正待遇、征收和救濟條款時,確實頻頻指引到東道國國內(nèi)法之中。(Jarrod Hepburn,Domestic La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3-102.)尤其是針對協(xié)定條款的“建設(shè)性模糊”,夯實條款的國內(nèi)法基礎(chǔ)對于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權(quán)和仲裁庭準(zhǔn)確適用中國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具有重要作用。
在“投資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一章,《中歐CAI》針對“投資與環(huán)境”“投資與勞工”等問題拓展了規(guī)制權(quán)的內(nèi)涵,其中多處內(nèi)容涉及國內(nèi)立法。以“投資與環(huán)境”一節(jié)為例,該節(jié)第2條對中國環(huán)境立法和執(zhí)法均提出了要求,需要中國在環(huán)境立法中明確環(huán)境保護的水平以及與外商投資的關(guān)系,并以非歧視的方式善意適用和執(zhí)行國內(nèi)環(huán)境法。由此,有必要梳理國內(nèi)與投資有關(guān)的環(huán)境法律和政策,夯實《中歐CAI》規(guī)制權(quán)的國內(nèi)法基礎(chǔ),助力中國后續(xù)締約時納入可持續(xù)發(fā)展條款。
《中歐CAI》對透明度的要求也需要在國內(nèi)立法中具體落實。整體而言,《中歐CAI》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簡稱《外商投資法》)要求在對外開放中提高投資監(jiān)管透明度的精神相符。《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對于透明度作出的是較為原則性的規(guī)定,例如《外商投資法》第19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guān)部門應(yīng)當(dāng)按照便利、高效、透明的原則提供外商投資服務(wù)。相較而言,《中歐CAI》規(guī)則更為細化,強調(diào)從信息公開、異議機制、救濟途徑各方面落實透明度要求。這對中國政府信息公開、司法和行政救濟程序、競爭執(zhí)法、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制定等工作都將帶來較大挑戰(zhàn)。締結(jié)高水平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也是以開放促改革,對此中國可在自貿(mào)區(qū)率先試點部分高水平的國際投資規(guī)則,逐步落實《中歐CAI》的透明度要求,統(tǒng)籌推進國內(nèi)法治與涉外法治。
五、結(jié)語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作為世界三大重要經(jīng)濟體近年締結(jié)的代表性國際投資協(xié)定,通過細化實體待遇條款、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增設(shè)程序透明度要求的方式試圖重構(gòu)投資者和東道國利益平衡。雖然CPTPP和《中歐CAI》在關(guān)注投資者利益和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問題上的側(cè)重點不同,但都同樣體現(xiàn)著強化東道國話語權(quán)的“國家回歸”趨勢,這或許代表著下一代國際投資協(xié)定的發(fā)展方向,即相對弱化對東道國規(guī)制權(quán)的限制。中國正處于由資本凈輸入國向資本凈輸出國的身份轉(zhuǎn)型時期,中國締結(jié)的國際投資協(xié)定實體條款設(shè)計應(yīng)契合中國同時作為資本輸出和輸入大國的雙重身份。CPTPP投資章節(jié)和《中歐CAI》在利益平衡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其中澄清協(xié)定的實體待遇條款和拓展規(guī)制權(quán)內(nèi)涵等做法可為中國部分借鑒,但其中有關(guān)監(jiān)管透明度等要求也將給中國國內(nèi)法改革帶來一定的挑戰(zhàn)。
收稿日期:2023-05-04
基金項目:2021年度國家法治與法學(xué)理論研究項目“我國外資法與國際投資條約的互動及銜接機制研究”(21SFB3025)
作者簡介:張倩雯,女,法學(xué)博士,西南交通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
① 參見陶立峰:《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變革發(fā)展及中國的選擇》,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19年第6期,第37-49頁;王鵬:《中立、責(zé)任與參與:國際投資仲裁的多邊改革與中國對策》,載《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7-128頁。
② 參見余勁松:《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投資者與東道國權(quán)益保護平衡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11年第2期,第141-142頁;郭玉軍:《論國際投資條約仲裁的正當(dāng)性缺失及其矯正》,載《法學(xué)家》2011年第3期,第147-151頁;曹興國:《裁判者信任困境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信任塑造》,載《政法論叢》2021年第3期,第137-1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