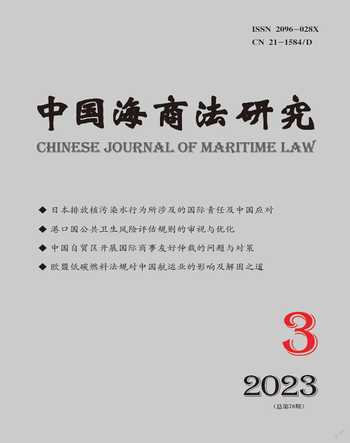港口國公共衛生風險評估規則的審視與優化
李雯雯 胡正良


摘要:新冠疫情暴發期間,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科學證據不足,風險應對工作尚未達到法治化。在風險評估視域下,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應當基于風險評估的基本框架,按照“收集信息—確定最佳證據—綜合研判”的路徑評估風險。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對中國風險評估規則的挑戰主要在于其沖擊了現行公共衛生法治理念,體現為對國家主權、風險預防、航運特殊性的關注不夠。理念沖擊凸顯出中國風險評估規則存在適用情形不明、行政主體職權交叉、義務履行的審查和監督機制空白的制度缺陷。將口岸公共衛生風險評估工作納入法治軌道,應當從理念提升和制度優化兩方面完善中國風險評估規則。
關鍵詞:風險評估;港口國;疫情防控;公共衛生風險
中圖分類號:D993.5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3)03-0035-14
Review and Optimization of Rules for Port States Public Health Risk Assessment
LI Wenwen,HU Zhengliang
(School of law,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 prominent issue was the failure of some port States in fulfilling their obligations of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when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risks from foreign ships. Port States should fulfill this obligation by using risk assessment
by following the basic logic of “information-evidence-decision”.The challenges of public health risks from foreign ships to rules for public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mainly appeared to be lack of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risk prevention an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hipping. These challenges highligh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rules, overlap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lack of review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the fulfillment of obligations. To integrate port public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to the rules of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need to be improved by upgrading the theory and optimizing the legal regimes.
Key words:risk assessment; port Stat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s; public health risk
一、問題的提出
2021年9月16日,海關總署發布的《國家“十四五”口岸發展規劃》中提出“全面排查口岸現場疫情防控弱項和短板”“鞏固和提升口岸公共衛生核心能力建設水平”。風險評估是口岸公共衛生風險應對的首要工作。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是指“用于將某一事件歸入對人類健康的特定風險的收集、評估和記錄信息的系統過程”。①
港口國口岸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旨在為有效的風險應對提供基于證據的信息和分析,有利于促進港口國正確認識風險,提高風險應對能力,優化應對措施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參見劉志欣:《風險規制視域下我國政府應急管理回應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頁。)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應對埃博拉疫情時強調,各締約國實施衛生措施應當以證據為基礎。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在宣布新冠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后,又一次強調證據在公共衛生風險應對中的重要作用。(WHO,Updated WHO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Relation to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WHO(27 January 2020),https://www.who.int/news-room/articles-detail/updated-who-advice-for-international-traffic-in-relation-to-the-outbreak-of-the-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然而,在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科學證據在風險評估中的作用沒有被重視。(SUN Siqi & ZHAO Lijun,Leg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ddress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on Large Cruise Ships: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ort State Measures,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Vol.217:1,p.3(2022). )例如,新冠疫情暴發期間,“威士特丹”號郵輪載有1 455名乘客和802名船員,自2020年2月1日從中國香港啟航后,盡管船上沒有人感染病毒,卻仍被菲律賓馬尼拉港、中國臺灣高雄港、日本石垣港、美國屬地關島港、泰國林查班港拒絕掛靠,導致在海上漂泊了13天。沒有科學證據而僅基于決策者經驗知識作出的評估缺乏科學性。對此,16位公共衛生和法律專家聯合在《柳葉刀》雜志上發文,認為一些國家和地區采取的衛生措施沒有科學證據,違反了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簡稱《條例》)的規定。(Roojin Habibi,Gian Luca Burci,et al.,Do not Violate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The Lancet,Vol.395:664,p.664(2020).)中國也有研究認為,在口岸疫情防控中采取的額外衛生措施常缺乏科學證據、(參見韓永紅、梁佩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過度限制性措施的國際法規制》,載《國際經貿探索》2020年第7期,第92頁。)超出必要限度、不符合科學原則和比例原則的要求。(參見張麗英:《新冠疫情下額外衛生措施的適用及其局限性研判》,載《清華法學》2021年第2期,第189頁。)然而,現有研究局限于在理念和原則層面為《條例》中額外衛生措施的實施提供指引,(參見郭中元、鄒立剛:《全球衛生治理視域下〈國際衛生條例〉中額外衛生措施之適用》,載《江淮論壇》2020年第5期,第135-138頁。)抑或從事后規制層面提出增強《條例》的強制力以促進履約的建議。(參見劉雁冰、馬林:《〈國際衛生條例〉》在新冠疫情應對中的困境與完善》,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122頁。)現有關于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評估的研究多集中于醫學領域,法學相關研究較少。(參見劉曉菲、張晏瑲:《論郵輪防疫應急機制的完善——以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為參照》,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0年第1期,第16-18頁;何田田:《“現有科學證據”規則與全球衛生法的完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20年第6期,第61頁。)
風險評估作為口岸公共衛生核心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港口國的國家公共衛生安全緊密聯系。風險評估是一種證據驅動的公共衛生方法,(Nosyk Bohdan,Zang Xiao,et al.,Ending the HIV Epidemic in the USA:An Economic Modelling Study in Six Cities,The Lancet HIV,Vol.7:e491,p.e496(2020).)缺乏科學證據的經驗決策,合法性與合理性均存在缺陷,導致港口國應對不力。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需要提升中國口岸公共衛生核心能力建設水平。筆者針對新冠疫情期間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實踐中暴露出的不足,擬圍繞港口國運用風險評估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這一主題,從規范依據與理論成因、運作流程與評估標準、國內規則的檢視與完善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二、港口國風險評估的規范依據與理論成因
全球化背景下,公共衛生風險及其應對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在國際法層面,《條例》明確規定港口國應當運用風險評估方法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WHO,Handbook for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on Board Ships,WHO(1 January 2014),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handbook-for-management-of-public-health-events-on-board-ships. )這一規定實質體現為合理行政原則的要求。
(一)國際法依據
《條例》作為專門規范主權國家應對公共衛生風險的國際條約,十分重視證據在風險評估中的作用。(參見《條例》第7條、第8條、第9條第2款、第11條第2款、第17條、第22條第2款、第23條第2款、第24條第1款、第27條第1款和第2款、第28條第4款、第31條第2款、第36條第2款、第39條、第43條第2款。)首先,《條例》確立了風險評估在口岸公共衛生核心能力建設中的關鍵地位,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根據《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各締約國應該根據本條例附件一的具體規定,在不遲于本條例在該締約國生效后五年內,盡快發展、加強和保持其評估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二是根據《條例》第6條第1款規定,各締約國應該評估本國領土內發生的公共衛生事件;三是根據《條例》附件一第2部分“指定港口的核心能力要求”規定,締約國對于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應當具備對嫌疑旅行者進行評估的能力。據此,港口國應當加強口岸風險評估能力建設,對于申請掛靠的船舶,評估其潛在的公共衛生風險。其次,港口國評估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應當基于科學證據。《條例》第43條第2款和第3款規定,締約國實施各項額外衛生措施均應基于現有科學證據和科學原則,并將其實施額外衛生措施的公共衛生依據和有關科學信息提供給世界衛生組織。上述規定分別從具備評估能力、實施評估行為、依據科學證據三個方面,構建出風險評估規則的基本架構。港口國應當基于現有科學證據并采用適當的過程和標準,識別和評估風險。(Daniel Krewski,Patrick Saunders-Hastings,et al.,Development of an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Alternatives to Animal Experimentation,Vol.39:667,p.667-669(2022).)
依據《條例》的規定,針對外國籍船舶給港口國帶來的公共衛生風險,風險評估與額外衛生措施聯系密切。
一方面,港口國有權依據其國內法,對掛靠本國港口的外國籍船舶及船上人員采取額外衛生措施。對此,《條例》第27條和第31條分別規定港口國在有證據證明存在公共衛生危害的情形有權對受染交通工具和入境旅行者采取衛生措施。第28條又規定,港口國為應對特定公共衛生風險或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因公共衛生原因阻止船舶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或拒絕授予船舶“無疫通行”。因而,港口國首先應當通過風險評估以確定船舶是否存在“特定公共衛生危害”或“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如果船舶上暴發新冠疫情,則適用《條例》第43條關于額外衛生措施的規定。
另一方面,依據《條例》第43條第2款的規定,港口國實施額外衛生措施應當符合科學原則的要求,遵循現有科學證據,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政府間組織和國際機構的信息或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或建議。“遵循”是指將科學證據嵌入決策制定、決策執行和決策評估中。(參見高鵬飛、吳瓊:《科學與決策的協同:新型政府循證決策模式構建與邏輯延伸》,載《領導科學》2021年第6期,第97頁。)新冠疫情期間,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建議不要采取旅行限制措施。(WHO,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Travel Advice,WHO(30 November 2021),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travel-advice.)即使對于傳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病毒,世界衛生組織仍建議優先考慮允許必要的人員旅行、撤僑行動以及食品、藥品、燃料等基本物資的貨物運輸,而不要實施旅行限制措施。(WHO,WHO Advice for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Relation to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B.1.1.529),WHO(30 November 2021),https://www.who.int/news-room/articles-detail/who-advice-for-international-traffic-in-relation-to-the-sars-cov-2-omicron-variant.)依據《條例》第43條第1款第1項的規定,港口國可以拒絕參考世界衛生組織關于不要采取旅行限制措施的建議,前提是此種拒絕“能夠產生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相比同樣或更大程度的健康保護”。一些締約國曾于2004年10月要求在《條例》的修訂中保持額外衛生措施的靈活性,妥協的結果是由締約國確定外國籍船舶是否存在公共衛生威脅,并且港口國可以靈活采取額外衛生措施,但締約國采取此類措施應當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科學證據,用于證實其已經履行風險評估義務。(WHO,Review and Approval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Explanatory Notes,WHO(7 October 2004),https://apps.who.int/gb/ghs/pdf/A_IHR_IGWG_4-en.pdf.)據此,以證據為依據是風險評估的應有之義。
(二)理論基礎:合理行政原則
公共衛生是一門以證據為基礎的學科。公共衛生法認為,科學證據構成衛生措施的合理性基礎,以科學證據為依據在醫學領域被稱為“循證”思維。(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68.)這種基于科學證據評估公共衛生風險并將評估結果作為制定公共衛生決策依據的過程,稱為“循證風險評估”(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簡稱EBRA),由此制定的決策稱為“循證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簡稱EBP)。2016年,已經有學者使用EBRA方法開展旅行醫學研究。(Emily S. Jentes,R. Ryan Lash,et al.,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and Communication:A New Global Dengue-Risk Map for Travellers and Clinicians,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Vol.23:1,p.2(2016).)
港口國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主要涉及對船舶及船上人員實施衛生措施,應當確保其實施的衛生措施有科學證據作為支撐。(Jonathan E. Suk,Sound Science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Global Health Governance,Vol.I:1,p.2-3(2007).)
風險評估的制度價值在于以客觀證據限制公權力的主觀濫用,避免不科學的公共衛生措施對私主體權益造成不合理侵害。(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432-433.)這一價值追求與合理行政原則高度契合。合理行政原則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應當貫徹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裁量權應當符合合理性價值要求。(參見胡建淼主編:《行政法學概要》,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頁。)基于衛生措施對行政相對人的影響,該原則要求港口國在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避免對船上船員和旅客個人權利以及船公司利益在內的私主體權益造成過度侵害。
首先,港口國負有保障船上人員生命權和健康權的國際法義務。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和1978年《阿拉木圖宣言》承認每個人都享有能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這項權利產生一國確保所有人不受歧視地利用衛生系統的國際法義務,尤其是為處境不利的個人提供平等和不歧視的國際人權保護。(Paul Hunt & Gunilla Backman,Health Systems and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Health Hum Rights,Vol.10:81,p.86-88(2008).)此外,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和第2條也將健康權的權利主體設定為一國公民和一國境內的外國人。《條例》第43條第1款更加針對性地規定,額外衛生措施造成的限制和侵擾不應超過能適度保護人員健康的其他合理可行措施。據此,港口國當局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既要保護港口國公共衛生利益,又要盡可能避免對船上人員的尊嚴、人權和自由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從而使衛生措施所維護的公共利益與船上人員的生命健康等權利保持適當的均衡關系。(參見胡正良、李雯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際海員換班難的法律問題與應對》,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88-89頁。)
其次,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還應當避免對船公司利益造成過度侵害。港口國為了防范疫情境外輸入風險,十分重視通過檢疫措施限制人員或貨物流動。(Maria Zambon & Karl G. Nicholson,Sudden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326:669,p.669-670(2003).)《條例》將檢疫作為一種額外衛生措施,一方面承認檢疫措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求港口國實施檢疫措施應當符合《條例》第2條規定的目的,即“避免對國際交通和貿易造成不必要干擾”。除《條例》外,1965年《便利國際海上運輸公約》第1條規定:“防止對船舶及船上人員和財產造成不必要的延誤。”這兩個條約都要求港口國在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考慮衛生措施對國際交通的影響。過長時間的船舶檢疫會導致船公司遭受不合理的損失,包括因船舶檢疫造成的船期損失以及船舶維持成本的上升,后者具體表現為因長時間檢疫導致的燃油和淡水消耗、額外的船員工資、過度消殺費用等。因而,港口國在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應當通過風險評估避免應對不當導致的船公司利益的損失。
綜上,合理行政原則在理論層面限制港口國政府實施不合理的衛生措施,而風險評估作為港口國實施衛生措施的手段,可以提供科學證據用于決策,以保障衛生措施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避免私主體遭受過度侵害應當以國家安全為底線,并遵循行政效能原則。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保障人民健康,而國家公共衛生安全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底線。港口國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如果反復斟酌和權衡應急措施和管控手段的合理性,將嚴重削弱應急效率和管控能力。(參見彭錞:《再論行政應急性原則:內涵、證立與展開》,載《中國法學》2021年第6期,第70頁。)高效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根據行政效能原則,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應當減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參見周佑勇:《行政法總則中基本原則體系的立法構建》,載《行政法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24頁。)行政效能原則對于應急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涉及國家安全這一底線問題,應當嚴格遵循行政效能原則,而不得借合理行政原則要求個人權利凌駕于國家安全之上。據此,港口國在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應當將保護港口國公共衛生利益作為優先事項,優先于對船上人員的尊嚴、人權和自由的保護。
三、港口國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的制度引入
現有關于風險評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證據在風險評估中的重要地位,而對于證據如何在風險評估中發揮作用的研究不夠深入,(Kathryn Oliver,Simon Innvar,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Barriers to and Facilitators of the Use of Evidence by Policymakers,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Vol.14:1,p.8(2014).)導致風險評估的理論與實踐存在隔閡。下文引入風險評估制度,論述港口國應當以何種信息作為評估證據,以及如何分析這些證據以評估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將風險評估理論運用至港口國口岸公共衛生風險應對實踐中。
(一)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的基本框架
為了將風險評估理論運用于實踐中,有學者設計了風險評估的基本框架(見圖1),(Daniel Krewski,Patrick Saunders-Hastings,et al.,Development of an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Alternatives to Animal Experimentation,Vol.39:667,p.692(2022).)闡明如何收集、整合、評估與特定風險決策有關的所有相關證據,為風險評估各步驟提供詳細指導。
在該框架中,第一步是收集整合與口岸公共衛生風險相關的證據。根據證據數量的不同,評估環境可以分為證據匱乏、證據有限、證據充足三種不同情形。證據匱乏是指沒有證據支持有意義的評估,證據有限是指現有證據不足以支持有意義的評估。在這兩種情形中,都需要在評估前繼續收集證據。一旦證據充足,下一步是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及半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現有證據,以評估外國籍船舶的公共衛生風險。其中,定性分析是將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確定為中、低、高不同等級;定量分析是以具體數值表示風險的發生概率和風險等級。
(二)港口國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的具體路徑
將風險評估理論轉化為實踐,還應當對基本框架進行填補,確定評估的具體路徑。根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風險評估技術》(GB-T 27921-2011)規則4.1的規定,風險評估流程分為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價三個步驟。在港口國公共衛生風險語境下,風險識別即確定風險來源,口岸公共衛生風險基本來源于外國籍船舶及船上人員;風險分析是指分析風險后果、社會可接受度、口岸核心能力,以確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級;風險評價是根據風險分析過程中獲取的信息確定風險等級,并預判即將采取何種衛生措施。口岸公共衛生風險來源確定后,需要特別關注風險分析與風險評價。風險的分析與評價之間具有手段與目的的天然邏輯關聯,是一個緊密聯系的過程。這一過程可細分為收集信息、確定最佳證據、綜合研判三個不同階段。
1.收集信息
《21世紀的專業政策制定》中指出:“證據的原始成分是信息,高質量的決策制定必須依賴高質量的信息。”(Strategic Policy Making Team Cabinet Office,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 Archive(September 1999),https://dera.ioe.ac.uk/6320/1/profpolicymaking.pdf.)因而,獲取信息是風險分析的前提。
良好的風險評估應當基于足夠的信息。行政決策的質量取決于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參見孫麗巖:《行政決策運用大數據的法治化》,載《現代法學》2019年第1期,第84頁。)風險評估應當考慮到所有可用和相關的信息來源。港口國運用風險評估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風險時,應當確保信息收集的全面、準確。《21世紀的專業政策制定》第7.1部分指出,行政決策的信息來源包括專家知識、國內外研究成果、現有統計數據、利益相關者咨詢、對先前決策的評估、新研究成果等,也包括來自互聯網的二手資料等。制定公共衛生決策需要關于健康問題的嚴重程度及其可能趨勢的獨立、客觀的公共衛生信息。(Christopher J. Murray & Alan D. Lopez,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Lesson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Science,Vol.274:740,p.740-743(1996).)
2020年12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出臺了《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背景下對國際旅行采取基于風險的方法的考慮因素》。(參見世界衛生組織:《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背景下對國際旅行采取基于風險的方法的考慮因素》,載世界衛生組織網站2020年12月16日,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7858/WHO-2019-nCoV-Risk-based_international_travel-2020.1-chi.pdf。四、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中國風險評估規則的檢視與完善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維護國家安全應當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其中,傳統安全主要指軍事安全,而非傳統安全主要指環境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等非軍事安全。(參見朱鋒:《“非傳統安全”解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第139頁。)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與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密切相關,其應對是國家安全風險防范法治領域的重點問題。新冠疫情暴發期間,中國口岸公共衛生治理遭遇挑戰。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意味著口岸公共衛生治理工作應當被納入法治軌道。(參見張文顯:《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年第6期,第2頁。)風險評估是循證科學在公共衛生治理中的重要實踐,推進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應當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完善中國風險評估規則。
(一)中國風險評估規則的立法現狀
目前中國公共衛生治理的法律法規主要有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簡稱《國境衛生檢疫法》)及其2019年實施細則、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簡稱《傳染病防治法》)及其1991年實施辦法、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簡稱《突發事件應對法》)、2011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2006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簡稱《應急預案》)、2006年《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簡稱《總體應急預案》)。其中,《突發事件應對法》第5條規定“國家建立重大突發事件風險評估體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26條規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專家對突發事件進行綜合評估”;《總體應急預案》第3.3.2條規定“要對特別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起因、性質、影響、責任、經驗教訓和恢復重建等問題進行調查評估”。在此基礎上,《應急預案》構建起一套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主導的“定級評估—綜合評估—后期評估”的專家評估體系。(參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規則4.2.2(2)、規則4.2.2(8)、規則5.1。)
此外,風險評估的具體規則散見于2012年《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管理辦法》(簡稱《風險評估辦法》)、2006年《國家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在上述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的支撐下,中國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風險評估制度。
(二)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對中國風險評估規則的挑戰
2021年7月30日,巴拿馬籍“弘進”輪從菲律賓出發,所有船員為中國籍國際海員。因船上多名船員出現發熱癥狀,該輪被原定目的港江蘇如皋港拒絕停靠,致使該輪身體不適的船員滯留在海上,9日后才在浙江舟山港獲準下船。(參見《“弘進輪”獲救背后:國際航運船員“下船難”困局》,載新京報2021年8月14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886676114509.html。)按照風險評估的要求,原定目的港如皋港在拒絕該輪掛靠前,應當對該輪上具有發熱癥狀船員的健康情況、該輪正常配員水平可能受到影響的程度,以及如皋港當地可能對該輪船員實施檢疫、隔離和治療所需要的醫療條件進行科學評估,再作出是否允許該輪掛靠的決定。(參見胡正良、李雯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際海員換班難的法律問題與應對》,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87-91頁。)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僅因為外國籍船舶可能對當地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就決定拒絕該輪掛靠的行為,合法性基礎闕如。
2012年《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技術方案(試行)》指出,風險評估是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重要環節,對有效防范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重要意義。在新冠疫情這場大考中,中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的實踐做法暴露出風險評估法律規范不完善和實施效果不佳的問題,中國風險評估規則有待完善。
1.理念沖擊
一是現行公共衛生法治強調以人為中心,(參見陳云良:《高質量發展的公共衛生法之道》,載《求索》2023年第2期,第150-151頁。)缺乏對國家主權的關注,沒有區分涉外性公共衛生事件與非涉外性公共衛生事件。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事件具有明顯的涉外性。然而,除《國境衛生檢疫法》外,《突發事件應對法》和《傳染病防治法》等國內主要公共衛生法律法規在立法價值層面對國家安全的考慮不夠,在制度設計上沒有體現出對涉外公共衛生事件的特別關注。
二是中國應急管理理念對事前預防的重視程度不夠。研究公共衛生治理應當從社會和經濟兩個層面展開。(參見張守文:《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發展法學的視角》,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3期,第591頁。)在社會層面,事前預防有利于保障公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經濟層面,必要和合理地預防疫情暴發相比于事后實施隔離、治療等衛生措施的治理成本更低,且疫情暴發會對當地經濟發展造成打擊。因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相較于應對其他突發事件更加需要事前預防。然而,以《突發事件應對法》為代表的國家應急法治總體上對風險預防的重視程度不夠,應急管理在制度設計上輕事前預防。(參見鐘雯彬:《〈突發事件應對法〉面臨的新挑戰與修改著力點》,載《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4期,第29-30頁。)正因如此,風險評估在船舶公共衛生風險應對中的作用沒有被充分發揮。
三是公共衛生法治對航運領域特殊性的關注不夠。應對船舶公共衛生風險,一方面要盡可能降低此種風險,另一方面要考慮疫情可能導致的供應鏈緊張問題,因而行政主體在風險評估時,既要注重保障公共衛生安全,也要保障航運供應鏈暢通,兼顧國家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
2.制度缺陷
一是風險評估制度與口岸公共衛生風險分級治理制度的契合程度不夠。《突發事件應對法》第3條將公共衛生事件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級。應對口岸公共衛生風險應當分級管理。然而,根據《總體應急預案》第3.3.2條、《突發事件應對法》第5條、《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26條和《風險評估辦法》第8條的規定,風險評估的適用情形至少存在以下三種不同規定:風險評估在特別重大情形中適用、
風險評估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適用,以及風險評估在各級公共衛生事件中均應當適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等級確認會在客觀上影響公眾對事件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應對措施。(參見劉志欣:《風險規制視域下我國政府應急管理回應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頁。)此種適用情形的法律規范沖突,是完善中國風險評估規則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前述“弘進”輪在江蘇如皋港被拒絕掛靠,而后掛靠于浙江舟山港,表明中國港口對于口岸公共衛生風險等級沒有明確清晰的判定標準,導致風險評估在實踐中踐行效果不佳。
二是行政主體的職權和職責存在交叉。在中國,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由掛靠港口所在地各口岸監管單位共同負責,具體包括海關、邊檢、衛健委、港口,以及所在港口的區疫情防控指揮辦等。現行法律法規關于風險評估義務的履行主體,至少存在以下三種不同規定:《突發事件應對法》第5條規定的是各級人民政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26條規定的是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國境衛生檢疫法》第15條規定的是國境衛生檢疫機關。實踐中,口岸公共衛生應對通常由衛健委、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移民管理局、民航局等部門合作完成。此外,海事、海關、邊檢等直屬查驗機構聯合地方政府部門建立聯合防控工作機制。(參見《國家“十四五”口岸發展規劃》,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21年9月23日,http://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3896488/index.html。)可見,中國公共衛生治理實踐采用整體性治理路徑,即不同職能部門共同治理、中央和地方共同治理。整體性治理本意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參見王敬波:《面向整體政府的改革與行政主體理論的重塑》,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第105-106頁。)然而,上述規范沖突導致多頭執法,可能導致不同主體分別對船舶公共衛生風險進行評估,各自決策意見不統一,進而導致治理碎片化,無法體現整體性治理的優勢。
三是信息獲取渠道單一。港口國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尤其是新型傳染病的暴發,通常需要對疫情的發展態勢作預判,而證據的充分性、可靠性和科學性直接影響預判的準確性。既有實踐是檢疫人員在船舶靠港期間登船檢測。僅僅依靠這一種途徑收集證據,效率不高。
四是風險評估義務履行的審查和監督機制空白。由于衛生措施可能侵害私主體權益,而保障私主體權益是風險評估的重要作用之一。建立審查與監督機制對于保障行政相對人權益十分重要。但是,中國目前并沒有關于行政主體履行風險評估義務的審查與監督機制。
(三)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評估規則之完善
風險評估是公共衛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風險評估規則是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事關總體國家安全。下文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針對前述理念沖擊和制度缺陷,分析中國風險評估規則的完善路徑。
1.理念提升
一是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治理具有涉外性。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參見《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載《人民日報》2014年4月16日,第1版。)因而,中國行政主體運用風險評估制定EBP,應當強化內外有別的底線思維,以維護國家主權、保障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
二是堅持科學的事前預防。提高口岸公共衛生安全治理水平,應當推動公共衛生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
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應當堅決貫徹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事前預防存在損害預防與風險預防兩種不同理論。二者都堅持以預防為主,前者指運用既有知識和經驗提前采取措施以避免可預見的損害,而非事后補救;后者針對損害結果難以確定的情形,強調“安全好過后悔”,認為對于一旦發生將嚴重危害民眾健康和生命、造成社會經濟巨大損失的衛生事件,如果能夠合理懷疑相關行為存在風險,應當立刻將風險扼殺在萌芽狀態。(參見金自寧:《風險視角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制度》,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3期,第65-67頁。)損害預防和風險預防適用于不同類型的船舶公共衛生風險。例如,對于船上經常發生的群體性急性腸胃炎,應當適用損害預防理論,運用已經形成標準化的檢疫流程和規范的風險評估方法進行預防。但對于新發傳染病,由于情況緊急,港口國檢測水平受限,此時風險預防原則更加符合保障國家公共衛生主權的要求。根據該原則,如果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風險產生合理懷疑,即可采取相應的公共衛生措施。另一方面,風險預防原則的確立使得風險評估與公共衛生事件分級的關系得以明確,即通過風險評估判定事件等級,并啟動相應級別的相應行動,而非僅針對重大或特別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適用風險評估。
三是堅持科學原則。科學性是確保衛生措施合法性的前提,科學證據是風險評估的依據。(參見李筱永:《公共衛生法治的制度邏輯》,載《醫學與哲學》2021年第11期,第69頁。)科學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評估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運用科學方法、依據科學證據。(ZHANG Xiaohan & WANG Chao,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s:The Legal Controversies,Healthcare,Vol.9:281,p.281(2021).)在此種評估時,科學性貫穿于以下三個步驟:一是判斷船舶是否產生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的風險,二是評估衛生措施對降低風險的效用,三是判斷實施衛生措施帶來的收益是否足以使限制個人權利的措施具備合法性。科學原則要求目的與手段、成本與收益之間應當合比例,與前述國家主權原則和風險預防原則的價值目標存在一定差異。《條例》第43條第2款提出的科學原則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得到充分貫徹。(《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6條明確“公共衛生治理應當開展科學研究”,第15條要求“科學分析、綜合評價監測數據”,第31條提出要“發揮科學研究機構在突發事件應對中的作用,集中力量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此外,《風險評估辦法》第1條提出“科學研判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第4條明確“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應當遵循科學循證的原則”。)行政主體進行風險評估時,應當以科學證據為依據,既要履行國際法義務,也要保障國家公共衛生主權,平衡好科學原則與國家主權原則、風險預防原則之間的關系。
2.制度優化
一是提升風險評估與公共衛生風險分級治理的契合度。首先,應當注重外國籍船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其他突發事件的差異,區分損害預防和風險預防。其次,應當注重口岸公共衛生與境內公共衛生在治理方式上的差異,前者應當在公共衛生治理中關注航運特殊性,考慮船員保護問題。根據科學原則的要求,應當參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15條關于分類應對的規定,設立專門適用于船舶公共衛生事件的分級標準,解決不同法律規范間的分級沖突問題。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WHO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Office)的事件管理支持小組為船舶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提供了可供參考的風險等級判定標準(見表1)。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理解《國家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第2條規定的醫療衛生救援事件分級與《突發事件應對法》第3條規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分級之間的關系?與《突發事件應對法》的規定一樣,《國家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第2條將醫療衛生救援事件分為四個等級,但分級標準有所不同,后者在考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級的同時,還將傷亡人員數量和事故輻射區域作為重要考慮因素。
風險評估理論認為,突發事件等級是風險發生概率和損害程度二者的函數,同一等級所對應的影響區域和損害程度大致相同;但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事件表明,等級較低的突發事件也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參見劉志欣:《風險規制視域下我國政府應急管理回應模式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頁。)在船舶暴發疫情的情形中,貨輪上傷亡人數通常不會超過船員總人數,事故輻射區域也基本固定,因而即使船舶已經嚴重暴發疫情,仍可能適用較低的響應標準,從而不利于對船員的救治。由于船上存在較多公共區域,且船上人員在封閉或半封閉環境中共用空調系統,環境特殊,從風險預防原則出發,一旦船上有確診病例,船上其他所有人員均宜視為陽性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同理,如果船上有人員出現發熱等感染癥狀,宜將其視為疑似病例。
二是解決行政主體的職權和職責交叉問題。口岸公共衛生風險涉及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具有高度復雜性,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職權和職責。根據現行立法,各級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國境衛生檢疫機關均負有風險評估義務。有觀點認為,中國公共衛生風險評估各項矛盾的源頭在于管理體制錯綜復雜導致的職權沖突和多頭執法問題。(參見鐘開斌:《“一案三制”:中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基本框架》,載《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11期,第78頁。)確立綜合協調型的口岸公共衛生風險評估體制,應當強化領導體制,確立牽頭抓總的行政主體。依據《突發事件應對法》第8條的規定,突發事件應急指揮機構負責組織、協調、指揮突發事件應對工作。實踐中,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的指揮、協調工作通常由聯防聯控機制負責。據此,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確立由聯防聯控機制負責風險評估的領導與指揮工作。在聯防聯控機制的領導下,海事、海關、邊檢按照職權法定原則的要求,分別主抓船員管理、入境監管和健康檢查工作。具體而言,海事局負責維護船員換班秩序,邊檢負責收集船舶途經掛靠港信息以及船上人員最近一段時間內的旅居史信息,海關負責評估船舶衛生狀況,包括船上有無人員出現發熱癥狀。
三是提高獲取最佳證據的能力。為促進締約國開展風險評估,世界衛生組織曾在2012年發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快速風險評估》(Rapid Risk Assessment of Acute Public Health Events),其中指出證據將直接影響風險評估的可信度。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中,如何獲得全面信息并從大量信息中提取到最佳證據成為信息獲取的一大難題。規范行政主體開展風險評估,應當從信息獲取的技術和渠道兩方面提高信息獲取能力。
在最佳證據獲取技術方面,應當科學運用大數據技術。大數據技術作為一種科學手段,其核心優勢在對數據的收集與分析上,即篩選出有價值的信息為EBP提供高質量證據。(參見高鵬飛、吳瓊:《科學與決策的協同:新型政府循證決策模式構建與邏輯延伸》,載《領導科學》2021年第6期,第98頁。)通過大數據技術對信息的即時捕捉,可以保障信息收集的及時性和信息本身的真實性;對于群體性問題,大數據技術還可以快速發現證據中蘊含的規律,預測事件的發展態勢。(參見孫麗巖:《行政決策運用大數據的法治化》,載《現代法學》2019年第1期,第87頁。)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于2021年12月印發的《“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中明確將“公共衛生應急數字化建設”列為國家信息化優先建設項目。面對航運數字化轉型和公共衛生信息化發展,中國應當推進船舶公共衛生領域的數字場景建設,將船上人員的行程軌跡和身體健康情況等信息載入機器學習模型,科學識別感染風險,發揮大數據技術在證據收集中的作用。
同時,應當拓寬信息獲取渠道。科學的風險評估基于科學證據,并要求專業人員使用科學方法分析證據。然而,病毒在檢測、感染和傳播方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不確定性。(ZHANG Xiaohan & WANG Chao,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s:The Legal Controversies,Healthcare,Vol.9:281,p.281(2021).)尤其對于新型傳染病,其潛伏期、感染率、致死率、傳播方式往往短期內屬于未知。公共衛生信息是風險評估的基礎。制定循證衛生決策需要定期更新全球和區域衛生信息。(Christopher J. Murray & Alan D. Lopez,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Lesson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Science,Vol.274:740,p.740-743(1996).)《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7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開展突發事件監測、預警、反應處理有關技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自2010年以來,國際社會愈加關注公共衛生信息在公共衛生決策中的作用。(Margaret Chan,Michel Kazatchkine,et al.,Meeting the Demand for Results and Accountability:A Call for Action on Health Data from Eight Global Health Agencies,PLOS Medicine,Vol.7:1,p.2(2010).)“鉆石公主”號郵輪疫情的應對實踐暴露出國際合作不足的問題。國際合作在公共衛生信息的收集方面同樣重要,港口國與外國籍船舶的船籍國、船員和旅客的國籍國,以及國際組織合作有利于實現信息共享。(參見胡正良、李雯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際海員換班難的法律問題與應對》,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86頁。)中國在拓寬證據獲取渠道方面,應當充分發揮世界衛生組織、其他國家和非國際行為體的作用。
首先,世界衛生組織的信息來源較廣,包括國家政府機構、《條例》國家歸口單位、世界衛生組織辦事處、新聞媒體和其他組織或伙伴。世界衛生組織在港口國獲取信息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幫助打擊錯誤信息。世界衛生組織在《2022—2023年規劃預算方案》中提出,打擊虛假和錯誤信息,支持進一步開發和促進采用具有成本效益的循證干預措施。其次,與其他國家進行信息共享的常用方法是設置數據可視化面板,對外發布經過整理的實時衛生監測數據。2020年3月25日,110個國家發布了有關新冠疫情的信息,而83個國家沒有發布。但截至2020年4月8日,167個國家已在其門戶網站中納入有關新冠疫情的信息和指導。(United Nations,Digital Technologies Critical in Facing COVID-19 Pandemic,United Nations(14 April 2020),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licy/digital-technologies-critical-in-facing-covid-19-pandemic.html.)最后,應對公共衛生安全挑戰涉及廣泛的公共和私人行為者,除政府間組織外,還有民間社會組織、慈善基金會、私營企業等。世界衛生大會在2016年5月通過的《非國家行為者交往的框架》將此類主體定義為“非國家行為者”。這些非國家行為者可以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發揮國際聯合監管作用,其提供證據的能力甚至超越主權國家。(參見何田田:《“現有科學證據”規則與全球衛生法的完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20年第6期,第63頁。)中國應當與這些非國家行為者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獲得非國家行為者在提供證據方面的支持,從而擴寬中國公共衛生信息網絡。
四是確立風險評估義務履行的審查與監督機制。《條例》關于風險評估義務履行的審查規則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締約國自我審查,即依據《條例》第43條第6款的規定,締約國執行衛生措施后,應當在三個月內對已經采取的措施復查。二是世界衛生組織審查,即依據《條例》第54條第2款的規定,由世界衛生大會定期對《條例》的實施情況進行審查。根據《條例》和《締約國自評年度報告工具指導文件》,港口國風險評估義務的履行情況應當接受審查。
在中國,為了促進行政主體履行風險評估義務,應當確立風險評估義務的審查規則。審查內容主要包括口岸公共衛生風險定級和衛生措施預判的合理性。在審查模式上,可以將風險評估義務履行情況的審查劃分為即時審查和事后審查兩類。一旦發生重大或特別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應當就行政主體是否基于證據評估風險進行即時審查。同時,考慮到風險應對的迫切性,即時審查可以采取形式審查的方式,即僅要求行政主體提供制定決策的現有科學證據或現有信息,例如外國籍船舶的《航海健康申報單》《寄港清單》《醫療日志》等文件的副本,而不對這些證據的確定性和完整性進行審查。由此,基本足以應對世界衛生組織的事后審查。
在確定審查模式后,還應確定審查標準和審查主體。依據《條例》第43條第2款的規定,現有科學證據應當符合充分性要求。為保證審查標準的一致性,中國行政主體制定EBP依據的證據也應當滿足這一標準。審查風險評估是否合理,可以參考國際公共衛生法學者戈斯廷(Gostin)提出的評估衛生措施應當考慮的7項標準:(1)傳播風險是否顯著?(2)對行動自由的限制有多嚴格?(3)強制程度如何?(4)受限制人群的規模?(5)可能產生哪些社會、政治和經濟影響?(6)衛生行政部門如何監控被隔離人員的健康狀況并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7)利益和負擔是否公平分配?(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417.)
在傳播風險方面,流行病按照不同流行程度可以劃分為地方性流行病、流行病、全球性流行病三種類型,傳播風險依次增高。(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347.)新冠疫情作為全球性流行病,傳播風險顯著。船上人員如果感染病毒,下船可能導致病毒跨境傳播。(ZHANG Xiaohan & WANG Chao,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s:The Legal Controversies,Healthcare,Vol.9:281,p.281(2021).)《條例》附件二提出了“為評估和通報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適用決策文件的實例”,為港口國評估公共衛生風險提供指導。該附件提出評估時應當考慮的四項標準:(1)事件的公共衛生影響是否嚴重?(2)事件是否不尋常或意外?(3)是否有國際傳播的嚴重危險?(4)是否有限制國際旅行或貿易的嚴重危險?如果滿足其中兩項標準,則說明傳播風險較大,港口國應當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在對行動自由的限制方面,檢疫期間、檢疫地點、檢疫條件的差異均會影響限制程度。例如,岸上檢疫較船上檢疫限制更小,單人單艙較多人同艙限制更小,房間有窗較無窗限制更小。港口國應當盡可能選擇對行動自由限制較少的方式實施檢疫。在受限制人群的規模方面,對郵輪旅客實施檢疫,受限制人群的規模較大。在社會影響方面,疫情暴發會導致醫療需求的激增,醫院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員、床位和設備。(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417-419.)此外,患有慢性疾病的船上人員可能缺乏藥物,或受傷需要急救。因而,港口國對船上人員實施檢疫等衛生措施,應當結合疫情傳播風險、措施對船上人員的限制和強制程度、船上旅客和船員的數量及其健康狀況、掛靠港所在地的醫療資源、措施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等因素進行綜合研判。
至于審查主體,《應急預案》第6.1.4條規定由國家建立統一的衛生執法監督體系,第4.2.5條規定由衛生監督機構承擔衛生監督和執法稽查職責。問題在于,風險評估工作由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實施,而衛生監督機構受衛生行政部門領導。這種行政主體間下級對上級的內部監督容易導致監督流于形式。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由國家監察機制介入,由監察部門作為審查主體可以保證審查中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11條第1款的規定,監察委員會應當對公職人員依法履職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在2013年11月15日發布的《進一步加強生產安全事故應急處置工作的通知》(安委〔2013〕8號)中指出,監察部門對應急處置工作負有指導義務。可見,監察部門應當介入應急處置工作,應當強化監察權在公共衛生應急處置領域的積極作用。
此外,為了促進行政主體履行風險評估義務還應當建立外部監督機制。風險具備雙重屬性,包括客觀的技術性風險和主觀的構建性風險。技術性風險評估面對客觀事實,依靠專家理性;構建性風險評估涉及價值和認識論,體現公眾的價值觀。(參見林鴻潮、彭浩:《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法律機制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頁。)在風險評估的外部監督機制中,科學性和民主性是兩項重要的評價標準。(Lawrence O. Gostin,Public Health Law:Power,Duty,Restrai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189. )
不同港口對證據科學性和有效性的認定存在較大差異。(Jonathan E. Suk,Sound Science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Global Health Governance,Vol. I:1,p.1(2007).)新冠疫情期間,一些港口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意愿較低,無視《航海健康申報單》《寄港清單》《醫療日志》等船舶衛生證明。(HU Zhengliang & LI Wenwen,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on Cruise Tourism:A Lesson Learned from COVID-19,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Vol.9:1,p.9(2022).)基于此,應當邀請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審查風險評估的科學性,弱化不同港口對于證據科學性和有效性的認定差異,避免經驗導向型決策。通過專家意見實現外部監督還體現在司法審查中。一般認為,行政主體承擔對于措施合法性的初步證明責任,包括提供公共衛生威脅的證據,例如病毒的感染率和致死率等,以及措施對于降低公共衛生風險的好處等,通常超過其負擔。(Ann L. Abbott,A Summary of Floridas Law of Quarantine of Persons and Public Health Law Reform Issues,Florida Public Health Review,Vol.2:10,p.12(2005).)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可以為循證醫學的證據質量提供專業鑒定。
除專家意見外,公眾參與也是強化外部監督機制的重要途徑。常見的公眾參與方式如將重要的公共衛生信息向公眾公開、邀請港口所在地公眾參與評估、為船上人員建立意見交流渠道。公眾信任是公共衛生措施發揮效果的關鍵,缺乏信任可能會導致公眾抗拒衛生措施,從而加劇疾病傳播的風險。(Michael R. Ulrich,Law and Politics,an Emerging Epidemic:A Call for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Law,American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Vol.42:256,p.275(2016).)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同樣應當獲得公眾、尤其是行政相對人的信任。當行政主體的行為、做法或決策不符合一般道德標準時,他們有義務為決策提供公共理由,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向權利受侵犯者解釋和辯護其侵權行為。(James F. Childress,Ruth R. Faden,et al.,Public Health Ethics:Mapping the Terrain,Journal of Law,Medicine & Ethics,Vol.30:170,p.174(2002).)
風險評估依賴于科學證據、良好的溝通和公眾對行政主體的信任。(Wendy K. Mariner,George J. Annas & Leonard H. Glantz,Jacobson v Massachusetts:Its not Your Great-Great-Grandfathers Public Health Law,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95:581,p.588(2005).)綜上,中國應當確立由監察部門參與的風險評估義務履行審查規則,建立以專家意見和公眾參與為核心的外部監督機制,保證行政主體在證據使用和綜合研判中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五、結語
世界衛生組織于2023年5月5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持續存在,港口國如何應對外國籍船舶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加強風險評估在公共衛生風險應對中的運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防范和應對公共衛生風險的趨勢。《條例》第5條第1款、第6條第1款、第43條第2款規定了風險評估的一般性義務,第27條第1款、第28條第1款和第2款、第31條第2款規定了港口國運用風險評估應對口岸公共衛生風險的具體義務。風險評估實質體現為合理行政原則的要求。風險評估中“收集信息—確定最佳證據—綜合研判”的運作流程和科學的評估標準,將公共衛生風險的應對方式從傳統的經驗導向型轉變為更加科學的證據導向型。港口國應對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時,應當基于公共衛生依據和科學信息評估風險。
實踐表明,中國風險評估規則仍然存在不足。口岸公共衛生輸入風險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循證醫學的科學方法有利于完善口岸公共衛生法治建設。完善中國口岸公共衛生風險評估規則,應當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在治理理念方面,注重外國籍船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涉外性和航運特性,堅持國家主權原則、風險預防原則、科學原則;在具體制度方面,加強突發事件分類治理、強化領導體制、提高獲取信息的能力、確立風險評估義務履行的審查與監督機制。提高中國在口岸公共衛生風險評估方面的核心能力,有利于實現公共衛生治理手段的進步,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收稿日期:2023-04-29
基金項目: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海上公共衛生法律治理研究”(21CFX019)
作者簡介:李雯雯,女,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講師;胡正良,男,法學博士,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研究中心主任。
① WHO,Handbook for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on Board Ships,WHO(1 January 2014),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handbook-for-management-of-public-health-events-on-board-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