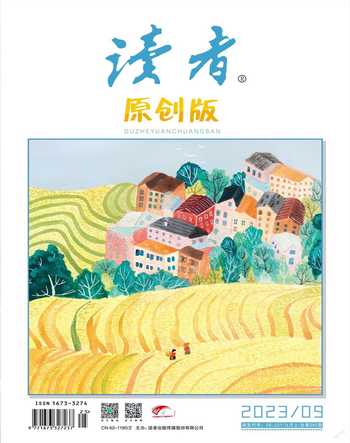青春期的饑餓
秦月溶

我們這代人出生于祖國經濟騰飛的年代,饑餓已經化作一個遙遠的幻影,只存在于長輩們憶苦思甜的回想中。明明小時候,我還是那種坐在飯桌上挑三揀四、端起飯碗就開始數米粒的人,可為了攢錢買書也可以三天兩頭不吃早飯。我一直以為自己不知道“餓”,可是進入青春期之后,飯量突飛猛進,仿佛一夜之間胃里憑空連接了一個名叫“饑餓”的黑洞,食欲變得空前旺盛,把吃東西當成了人生第一大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下是沒有鮮牛奶的,偶爾家里買一罐奶粉,沖開了也是一股奶腥味。據母親說,我小時候就不喝奶粉,只愿意吃點兒嬰兒米粉。可是,等我上了衛校之后,嘗了一次學校小賣鋪里的鮮奶,我震驚了,實在是太好喝了!鮮奶不僅沒有奶腥味,還帶著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很清爽。這種鮮奶是本地品牌,除了鮮牛奶,這家還有酸奶和各種味道的調味奶。我一頭扎進牛奶的新世界里,來者不拒,只要是沒有喝過的口味,一定要買來試試;喝過的口味,那當然是繼續喝。我甚至創下了一天喝10袋牛奶的紀錄,小賣鋪的老板看到我笑得眼睛都瞇起來了。
只要是開在學校里的小賣鋪,都是日進斗金。不管是面包、牛奶,還是辣條、餅干,對饑腸轆轆的學生來說,那都是人間美味。我們學校小賣鋪的老板頗有些小聰明,開啟了獨家創意—按季節供應冰地瓜(豆薯)和烤紅薯。原本放在菜市場里論斤賣的地瓜和紅薯,搖身一變,成為柜臺上按個算錢的珍饈。夏天,他們將地瓜洗干凈、剝皮,裝進塑料袋放進冰箱里冷凍,那地瓜看起來如玉石般晶瑩剔透,吃起來涼絲絲、水津津、脆生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冬天的夜晚,他們架起鐵皮爐子,烤紅薯的香味順著山坡往下翻滾,等到我們下了晚自習往宿舍樓走,正好聞到這甜絲絲的香味,肚子里的饞蟲全被勾了出來。在冰地瓜和烤紅薯之間,時間就這么流水般淌走,一起淌走的,還有口袋里的錢。
母親一個月給我200塊錢生活費,完全不夠用。食堂的菜油水少,就算花4塊錢點幾樣葷菜,也只能聊以自慰。說是紅燒雞塊,扒開青椒片和土豆塊,不過零星兩塊雞腳、雞肋;點一道青椒肉絲,綠瑩瑩的青椒絲上只有幾條慘白的肥肉。我總是吃不飽,總是肚子餓。食堂的正經飯菜不管飽,只能在幾個小賣鋪買吃食,早上喝奶,晚上吃夜宵,一個月的生活費只夠花半個月。
這也不能怪我貪吃,主要是受到的管教太嚴,從小沒有下過館子,吃一塊糖果就會被父母批為“貪吃”,這一下脫離了管束,可不得放開肚皮吃嘛!那時的我,身材矮小,如豇豆條一般,頂著一頭黃蓬蓬亂草一樣分叉、打結的長頭發,也沒人笑話我—大家能進衛校,家境和生活環境都差不多。大家都和我一樣,每月只有200塊錢的生活費,也不知道這個標準是誰定的,但這只是最低標準—哪怕在食堂吃飯,早上不喝牛奶,只是中午、晚上打兩頓帶葷的肉菜,200塊錢也不夠用30天,何況我們還要買生活用品和學習用具。而我們都是十四五歲的少女,正是抽條長個子的時候。而學校里,光食堂就有兩個,小賣鋪有9家,另外還有5家小炒店和兩家燒烤店,只要舍得花錢,就沒有你想吃而吃不到的東西,這讓我們如何抵御食物的誘惑?同學里,除了少數幾個以攢錢為樂的女生,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前半個月就在吃食上把生活費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在學校里,饑餓是永恒的主調。
要說幫助我們抵抗饑餓的第一法寶,我提名方便面,應該沒有任何人會反駁。為了省錢,我們往往不買有名氣的大品牌,而是整箱批發一些雜牌方便面,算下來一包才四五毛錢。一天早、中、晚各泡一包,花費也才一塊多錢。也有幾個同學合買一箱,抱回寢室再分的。有時候我們買了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還會互相交換,提升一下伙食的豐富性。那時候的方便面遠不如現在的好吃,聞起來香,吃起來其實寡淡無味,里面既無菜,也無肉,開水沖泡的面條也不怎么入味。偶爾吃一頓還好,頓頓都吃,真能把人吃得生無可戀。
我是極討厭吃方便面的,可惜每個月至少要吃上一星期。為了讓方便面變得好吃一點兒,我也做過努力,比如加一根烤腸,或者放兩根辣條,但都于事無補,什么東西放進去,都會變得和面條一個味兒。我索性懶得泡面了,一天打幾次開水也費勁,便直接將方便面干嚼了吃,不再考慮口感,只為填飽肚子。
睡前的臥談會上,大家聊到“方便面有防腐劑”,說它如何如何不健康。方便面這么難吃,還對身體不好,可是我們依然維持著每個月批發一箱的習慣,畢竟,再壞也壞不過餓肚子呀!
白天的時候,饑餓感沒有那么明顯,因為上課與各種活動吸引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當感覺到一點點餓,很快就會將其拋到腦后,一旦忘記,饑餓就不再是威脅,這就是俗稱的“餓過了”。但是到了晚上,人閑下來,饑餓感就會被無限放大,越想越餓,越餓越睡不著。經常能聽到室友晚上窩在上鋪吃餅干,“咔嚓,咔嚓”,像只小老鼠一般。
有錢的時候,晚上我會繞過整個操場,跑去校門口旁邊的燒烤店吃燒烤。燒烤店很小,店面只有3米寬,外面攔了張條桌,里面灶臺上架著一口油鍋,老板和老板娘一個炸串一個收錢,人都轉不過身來。菜品很簡單,炸火腿腸、炸豆腐干1塊錢,炸雞腿、炸香腸5塊錢,但架不住青春期學生對肉食的渴望,這里的顧客是全校最多的,等著吃炸串的學生里三層外三層,圍得密不透風。我最喜歡吃他們家的炸雞腿,腌制過的雞腿劃上3道口子,丟進油鍋炸得外焦里嫩,再放進條桌上的鐵盤,刷上厚厚一層油辣子,簡直是人間美味。炸香腸也一樣好吃,香腸是老板自家灌的,瘦肉多肥肉少,炸過后肥肉化成渣,油渣香、臘肉香和陳皮香味摻和在一起,讓人吃完還想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價格太貴,不能每天都吃。
考上大專后,我終于找到了擺脫饑餓的辦法。學校里最火的小吃店,除了燒烤店,就是小炒店。小炒店就設在大食堂后面,是一溜兒的矮小平房,每一間和上衛校時那間燒烤店的面積差不多大。考慮到學生的消費水平,小炒店只炒素菜,不賣葷菜,所有蔬菜都被切好放在筐里,旁邊放著一疊盤子,學生挑好后,老板混在一起炒,兩塊錢一份。
人一多,老板就忙不過來,我見到有學生在店里幫忙,就厚著臉皮去和沒請人的老板搭訕,也謀得了一份幫工的兼職。我的工作很簡單,中午放學后立刻趕到小炒店,一手拿夾子,一手拿盤子,學生來了,我就負責點菜。他們要什么菜,我就夾什么菜,裝滿一盤,按照順序擺在灶臺上,菜出鍋后再端給學生。做這份兼職沒有工資,報酬是店鋪打烊后獲得一份免費小炒。工作雖然不算累,但十分難熬—別人吃飯的時候,我餓著肚子站在那里點菜,聞著菜香,肚子饞得咕咕叫。一點過后,來吃飯的學生才會變少。我給自己夾菜有秘訣,先夾綠葉蔬菜,再夾菌菇和海帶絲,最后把藕片、魔芋蓋在最上頭,同樣裝一盤子菜,我的菜炒出來分量只多不少。除了要忍著餓,這份工作的另一個壞處是要忍受羞恥。碰到班上的同學來點菜,他們免不了要東問西問,問我為什么想到來夾菜,是不是和老板認識?問完了還要加一句:“你給我多夾點兒菜呀!”夾菜是有規矩的,盤子堆太滿,一是老板不高興,二是上面的菜會滑掉。我在小炒店干了3個月后,找到了新的兼職,就向老板提出了辭職,老板也沒挽留,畢竟,想要吃一頓免費小炒的學生多得是。
新兼職是在勤工儉學平臺找到的,給游戲公司做問卷調查,一份問卷十幾頁,只要受訪者認真填完,我交上去就能得到10塊錢的報酬。我耍了點兒小聰明,批發了許多圓珠筆和香味橡皮,把目標瞄準了學生群體。平常我就在大學城轉悠,專門挑一些看上去好說話的學生,先送圓珠筆,再請他們幫忙,基本不會被拒絕。周末和節假日,我就去市中心的商城,那里的中學生和小學生可愿意幫我的忙了,為了得到圓珠筆和橡皮,他們不僅自己填表,還會拉上他們的父母叔伯幫我多填一份。運氣最好的時候,我一天做了150份問卷,每個受訪者和電話都是真的,順利拿到報酬。有了錢,我吃得更好了。大學城的美食街,20塊錢可以點一小份的干鍋雞,40塊錢能夠吃牛肉火鍋吃到撐,吃完主食還有各種飲料、水果撈。我經常吃得肚皮滾圓,走不動路,可只要桌上還有食物,我就一定要吃完,不能有丁點兒浪費。大家都驚訝,我這么瘦小的身體,怎么能吃下這么多東西?
多年以后,青春期的饑餓已經完全遠離我的生活,可是留下的后遺癥還在,就是見不得剩菜。每次親友去吃自助餐,都要帶上我,理由無可辯駁—有我在才能回本。這是深刻的青春期饑餓記憶的遙遠回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