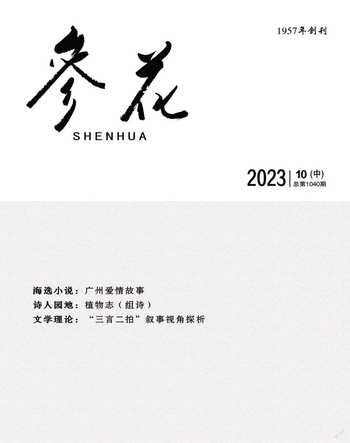清代木刻鼓詞小說的程式研究
“口頭程式理論”是美國(guó)學(xué)者米爾曼·帕里及其合作者艾伯特·洛德通過對(duì)史詩的實(shí)證研究和運(yùn)用比較方法而創(chuàng)立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出現(xiàn)決定性地改變了傳統(tǒng)的以書寫和文本理解為主的方式,而“激活了去重新發(fā)現(xiàn)那最縱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類表達(dá)之根”,[1]為其他民間口承樣式提供了具有啟示意義的研究方法。[2]本文以《蛟趾羅》等鼓詞小說的程式性現(xiàn)象為研究個(gè)案,運(yùn)用口頭程式理論的方法,分析其中具有程式意義的情節(jié),并對(duì)部分程式性的句式敘事單元及文本結(jié)構(gòu)給以總結(jié),分析和揭示木刻鼓詞小說的基本構(gòu)成規(guī)則。
一、程式理論概述及運(yùn)用分析
為了代替“套語”“陳詞濫調(diào)”“慣用的詞語”“重復(fù)”等這樣一些模糊、過于限定并且不夠精確的詞語及語句,米爾曼·帕里提出了程式概念:“在相同的格律條件下為表達(dá)一種特定的基本觀念而經(jīng)常使用的一組詞。”帕里認(rèn)為,“程式”不僅僅對(duì)觀眾有用,更對(duì)歌手快速創(chuàng)作故事有用,也就是對(duì)演述人現(xiàn)場(chǎng)說書更有用。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大量練習(xí),歌手也就是演述人會(huì)不斷產(chǎn)生對(duì)一些具體詞語的需要,一個(gè)短語、詞語,無論是被演述人聽見,還是自行創(chuàng)新,都會(huì)被其經(jīng)常使用,這個(gè)時(shí)候,程式就誕生了。當(dāng)演述人經(jīng)常使用某些程式時(shí),這些程式也就變成了他自己的程式。
表現(xiàn)常見意義的程式如名字、行為、時(shí)間、地點(diǎn)、動(dòng)作,等等,這些常見的、穩(wěn)定的程式是演述人必須牢牢記住的。當(dāng)然,程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將新的詞語放進(jìn)舊有的模式中,新的程式便產(chǎn)生了,但這個(gè)新的程式能否成為常見的、穩(wěn)定的程式,還需要看它們之間是否協(xié)調(diào),而這個(gè)過程是緩慢的。明清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大量筆錄即興作品并稍加整理后刊行于世的木刻說唱鼓詞小說。像鼓詞說唱這樣的口頭文學(xué),須被記住才能生存,而韻律對(duì)于口頭文學(xué)十分重要,因此,在傳統(tǒng)的鼓詞說唱小說中,同樣存在大量的程式。
二、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的程式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常見的引導(dǎo)性詞組或短句就是程式,是文本的基本組成要素,這些程式是演述人長(zhǎng)期形成的固定表達(dá)習(xí)慣,會(huì)隨著主題的變化而有所變動(dòng)。這些程式一般出現(xiàn)在人物出場(chǎng)后的自我介紹、人物情節(jié)、人物行動(dòng)和情緒描述上,是演述人最常見和常用的語句。木刻鼓詞小說中常出現(xiàn)的程式有以下幾類。
(一)開場(chǎng)詩程式
開場(chǎng)詩也就是定場(chǎng)詩,其功能是使全場(chǎng)安靜,便于說唱順利開始。開場(chǎng)詩作為最常見的說唱程式,通常以五言、七言詩進(jìn)入正題,但內(nèi)容不一定與正書內(nèi)容有關(guān)。開場(chǎng)詩通常會(huì)說明整個(gè)故事的發(fā)生背景,或引出故事的發(fā)生走向。這些開場(chǎng)詩有意引導(dǎo)觀眾進(jìn)入故事,展現(xiàn)鼓詞現(xiàn)場(chǎng)演述的口頭性特征。以下三段木刻鼓詞的開場(chǎng)詩都各具特色。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bào),只爭(zhēng)來早與來遲。(《汗衫記》)[3]
才子遠(yuǎn)年天命,金榜早會(huì)連登,幼年婚姻多不利,枉送佳人性命。先冠兩房妻子,不是婚姻難成,有緣千里來相會(huì),月老暗地造定。(《蛟趾羅》)
光陰遞嬗似輕云,不朽還須建大勛。壯略欲扶天日墜,雄心豈入駑駘群。卻緣否運(yùn)姑埋跡,會(huì)遇昌期早致君。為是史書收不盡,故將彩筆譜奇文。(《粉妝樓》)
這三段開場(chǎng)詩用短短幾句話就概括了整個(gè)鼓詞的發(fā)展趨勢(shì),再用“提綱勾開,閑言少敘”引出下文。比如《蛟趾羅》描寫男主人公于幼年定親之人都早早喪生,無奈之下,獨(dú)自闖蕩江湖,卻一路得到佳人相助,冥冥之中,自己的命數(shù)自有上天安排,自己的婚姻自有月老牽線,一句“有緣千里來相會(huì)”,就完美地概括了這種定數(shù)與緣分。這些開場(chǎng)詩都朗朗上口、句式自由,有助于演述人吸收、記憶,甚至創(chuàng)作新的開場(chǎng)詩。
(二)省略性程式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言簡(jiǎn)意賅、不多言說的程式,因此,鼓詞演述人往往會(huì)把不重要的情節(jié)或細(xì)節(jié)省略。當(dāng)鼓詞演述人把故事從一個(gè)邏輯或者時(shí)間的層面轉(zhuǎn)入另一個(gè)層面,從一個(gè)人物轉(zhuǎn)到另一個(gè)人物,再或是從一個(gè)情節(jié)轉(zhuǎn)入另一個(gè)情節(jié)的時(shí)候,使用的就是這些省略語引導(dǎo)性程式。如“不可多重?cái)ⅰ薄安豢啥嗌顢ⅰ薄把詺w正傳”,等等。鼓詞演述人運(yùn)用這些程式語詞,規(guī)避了那些無關(guān)緊要的情節(jié)。如下。
羅爺父子書房講話不提,單說文華閣大學(xué)士丞相之職……(《汗衫記》)
這卻不提,卻說晉爺拆出一觀,上寫忠君二字……(《蛟趾羅》)
單說胡奎帶領(lǐng)祁子富車輛,從山下經(jīng)過,只聽得鑼鼓一響,生就不好了。(《粉妝樓》)
閑言不必多說,單道侯登見祁巧云向后邊去了,無奈帶領(lǐng)家丁……(《粉妝樓》)
從樣例看,清代木刻鼓詞小說常用的省略性程式就是“XX不提”“閑言少敘”“閑言不必多說”“單說”,這些省略性程式在鼓詞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非常多,且有效地規(guī)避了一些不重要的冗長(zhǎng)情節(jié),使觀眾能夠一直沉浸故事之中不出戲。
(三)說唱交替處的引導(dǎo)性程式
在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演述人常在說唱交替處使用“話說”“卻說”等交替處的引導(dǎo)性程式,從而順利轉(zhuǎn)換故事的邏輯或說唱的角色。例如:
話說上部書說的是柏小姐在松林玩月,遇見侯登由王家吃酒回家……(《粉妝樓》)
卻言羅焜見程爺送黃金二錠,又蒙相留之恩,遂施禮謝道……(《粉妝樓》)
話說公子拜師以后,不過出些力做些活。卻說那年臘月是個(gè)小,盡到三十上日……(《蛟趾羅》)
單說二賊把玉童四馬措蹄捆住,丟在茅井以內(nèi)……(《汗衫記》)
從以上的樣例看,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出現(xiàn)了頻率較高的“話說”“卻言”等引導(dǎo)性程式,能夠讓觀眾更加明白鼓詞的演述內(nèi)容和進(jìn)程。此外,鼓詞中還常常出現(xiàn)“列位”“諸位”“眾明公”等引導(dǎo)性程式,可以有效地引起觀眾的注意力,讓觀眾更加專注于演述人的演述。
(四)時(shí)間程式
在演述內(nèi)容豐富、情節(jié)較為復(fù)雜的情況下,演述人常用“昨日”到“次日”、“方才”到“現(xiàn)在”程式化地表示時(shí)間轉(zhuǎn)換,提醒觀眾演述進(jìn)度,這些重復(fù)出現(xiàn)的語詞可稱為時(shí)間程式。例如:
話說沈廷芳在滿春園飲酒,被羅公子打了個(gè)不亦樂乎,回到相府,又不敢作聲。悶在書房,過了一夜,次日清晨,錦上天呈上賬來,說:“昨日打壞店家的傢[家]伙物件,并受傷的人,一一開發(fā)銀子了。”沈廷芳說道:“人財(cái)兩空,這也到[倒]還罷了,只是昨日這一口氣,咽不下去。”錦上天說:“且將羅家擱在一邊,等慢慢地尋他不遲,如今之計(jì),大爺叫十?dāng)?shù)個(gè)人,到張二娘店里,訪訪消息,先將祁巧云搶來再作道理。”沈廷芳說:“若再撞見他們,如何是好?”錦上天說:“那[哪]有這等巧事,聞聽人說,羅太太家法更緊,平日不許他們出門,昨日放一天,今日必不能出來,此事管包到手。”沈廷芳說:“倘若我們搶他女兒,他要喊起冤來,地方官耳目要緊。”錦上天說:“這個(gè)事不怕,大爺做一婚書,就寫上我錦上天為媒,備下花紅彩禮,叫家人抬轎將彩禮拋下,搶了人來就走,任他喊冤告狀,咱有婚書為憑,怕他怎甚?”(《粉妝樓》)
鼓詞所使用的“正在”“到了”“昨日”等時(shí)間程式非常頻繁,從樣例上看,單是這一小段內(nèi)容,使用的時(shí)間程式就很多,如“昨日”“次日”“今日”這些日常的口頭表述。在演述鼓詞時(shí),這些詞就成了故事發(fā)生順序中的邏輯關(guān)鍵詞,推動(dòng)著一個(gè)情節(jié)向另一個(gè)情節(jié)發(fā)展,在時(shí)間上進(jìn)行轉(zhuǎn)換,既可以承前啟后,又可以推進(jìn)故事本來的發(fā)展。
(五)描寫人物形象的程式
描寫人物形象和景物的程式屬于一種修飾性程式,鼓詞在描寫人物形象和景物時(shí),采用了相對(duì)固定的句式表達(dá),運(yùn)用夸張、反復(fù)、排比等手法來設(shè)景造境、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個(gè)性。于是就可以將這一類反復(fù)出現(xiàn)的修飾性語句、詞語作為程式來看待。先看描寫人物形象的程式。例如:
公子聞言出茅庵,停足站立用眼觀。三位幼女院中站,打扮形容不一般。前頭好像一仆女,少婦后隨女嬋娟。青絲如墨兩鬢秀,鬢旁斜插鳳頭簪。挽個(gè)巴角時(shí)新樣,雙紅頭繩顏色鮮。柳眉杏眼櫻桃口,桃腮粉面似銀盤。(《蛟趾羅》)
俺小姐偷眼仔細(xì)看,學(xué)生果然甚標(biāo)直,眉彎黑如香墨染,鼻子長(zhǎng)得偏相趁,臉白賽過難蛋皮,兩行銀牙如碎玉,唇紅好似血滴珠,兩耳垂肩是貴相,小子家也受過那樣屈,他爺娘必為兒難養(yǎng),把耳朵扎個(gè)窟窿當(dāng)閨女,一頂儒巾雙飄帶,身穿藍(lán)衫靛染的,腰東絲絳露著穗,粉底皂靴不沾泥,只為他人才生的俊。(《汗衫記》)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對(duì)男女主人公的描寫程式化非常明顯,凡是女性,外貌上必然柳葉眉、杏核眼、桃紅臉、櫻桃嘴、纖纖細(xì)手,十指不沾陽春水;凡是男兒,必定唇紅齒白、眉黑如墨、鮮衣怒馬少年郎、天生聰明富貴相。這些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之所以能夠成為程式,是因?yàn)槟究坦脑~小說的內(nèi)容通常都與世家忠臣子弟的男女情有關(guān),于是在塑造形象時(shí)就形成了統(tǒng)一的樣式。并且這些鼓詞里的其他女性也是如此,不論是閨閣女子,還是風(fēng)塵女子,她們?cè)谙嗝采系拿枋鰩缀跻粯樱皇窃诖┮麓虬缟喜灰粯印4送猓瑢?duì)于不同類人的程式化描述也不一樣,但同類人必定是一種程式,比如清官就是面如古月、相貌非凡又威風(fēng),匪徒就是黑臉胡茬亂蓬蓬。總之,鼓詞通過描述人物相貌、穿著、身體部位的特點(diǎn),為人物形象塑造和描述提供了一個(gè)固定法則,演述人通過這一程式化的法則,就能熟練描述人物形象。
(六)描寫景物的程式
清代木刻鼓詞中對(duì)于景物描寫的程式也比較多。例如小姐勒馬細(xì)觀真,滿坡松柏黑森森。山嶺層層接云煙,疊疊深澗數(shù)丈深。四下盡是黃柏草,梅鹿猿猴接成郡。秋波閃閃行細(xì)看,觀見高山大寨門。威威迷切石頭人,滾木磊石亂紛紛。(《蛟趾羅》)
從上述樣例可以看出,鼓詞中對(duì)于景物的描寫不像書面描寫那樣精煉與優(yōu)美,往往需要通過疊詞與朗朗上口的韻腳和數(shù)詞來達(dá)到修飾景物的目的。如森林就是“黑森森”,下雨就是“一絲絲”,河溝溪澗就是“數(shù)丈深”,河邊石頭就是“亂紛紛”,這些固定的修飾性程式搭配,同樣讓演述人能夠快速在場(chǎng)上描述景物。
(七)人物常見行動(dòng)的程式
在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可以反復(fù)看到關(guān)于人物行為動(dòng)作的語詞,它們都有著某種固定的組合方式,如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的“XX地流平”常常用來形容人物摔倒在地,還有“樸咚坐在地流平”“咕咚摔至地流平”“反身跪倒地流平”“嚇得跌在地流平”“打死猛虎地流平”“巧云也跪地流平”等。
三、清代木刻鼓詞小說結(jié)構(gòu)的程式性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中的這些程式在結(jié)構(gòu)順序方面也具有程式性,就《粉妝樓》《蛟趾羅》《汗衫記》而言,其中常見的結(jié)構(gòu)模式可為兩種。第一種,交錯(cuò)式結(jié)構(gòu)。兩個(gè)相同或相似的敘述單元同時(shí)展開,交錯(cuò)敘述,隨劇情的推進(jìn),兩條線索逐漸歸并,然后進(jìn)入新的敘事單元。如《蛟趾羅》中男主人公晉公子與恩玉蘭小姐在山中失散之后,晉公子被拐到了大寨里,恩小姐逃到了尼姑庵,此時(shí),演述人在說這兩段時(shí),采用的就是交錯(cuò)式結(jié)構(gòu),恩小姐在尼姑庵的故事情節(jié)與晉公子在山寨里的情節(jié)交錯(cuò)展開,并交錯(cuò)講述,這樣的結(jié)構(gòu)能夠讓觀眾牢記故事情節(jié),不遺忘前情。第二種,重復(fù)式結(jié)構(gòu)。即相同的程式性敘事單元重復(fù)出現(xiàn),木刻鼓詞的重復(fù)式結(jié)構(gòu)也比較多,比如《蛟趾羅》中恩小姐遇見晉相公所救的兩位女子,女扮男裝被識(shí)破,在此前恩小姐與晉公子初次相遇時(shí)也出現(xiàn)過。《汗衫記》中也多次出現(xiàn)男女主人公從誤會(huì)到認(rèn)識(shí),再到分開的情節(jié),同樣的,這幾部鼓詞中都有舅舅、母親天各一方,最后彼此的兒女在江湖中相識(shí),最后在一起的情節(jié)。這兩種結(jié)構(gòu)程式是鼓詞中最常見,也是最簡(jiǎn)單的,是演述人須牢牢掌握的基本結(jié)構(gòu)程式。
清代木刻鼓詞小說的演述人在學(xué)習(xí)基本的程式之后,可以根據(jù)經(jīng)驗(yàn)以及要演述的內(nèi)容對(duì)一些基本程式進(jìn)行改編,再形成自己的程式,如此,鼓詞中的程式會(huì)變得越來越多,這樣對(duì)于演述人而言,現(xiàn)場(chǎng)即興創(chuàng)作或改編民間小說才能信手拈來。程式太多,似乎會(huì)讓鼓詞變得類似、失去趣味性,但不難看出,縱然是相當(dāng)程序化的演述內(nèi)容,也不會(huì)使觀眾乏味。這些滿含程式性語句、由程式性結(jié)構(gòu)構(gòu)建的清代木刻鼓詞小說,其實(shí)際是人們認(rèn)識(shí)、了解、記憶和創(chuàng)作程式的產(chǎn)物。
參考文獻(xiàn):
[1][美]約翰·邁爾斯·弗里,著.口頭詩學(xué):帕里—洛德理論[M].朝戈金,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5.
[2]朝戈金.口傳史詩詩學(xué):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3]李豫,主編.清末上海石印說唱鼓詞小說集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簡(jiǎn)介:朱玲玲,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延安大學(xué),研究方向:文獻(xiàn)學(xué))
(責(zé)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