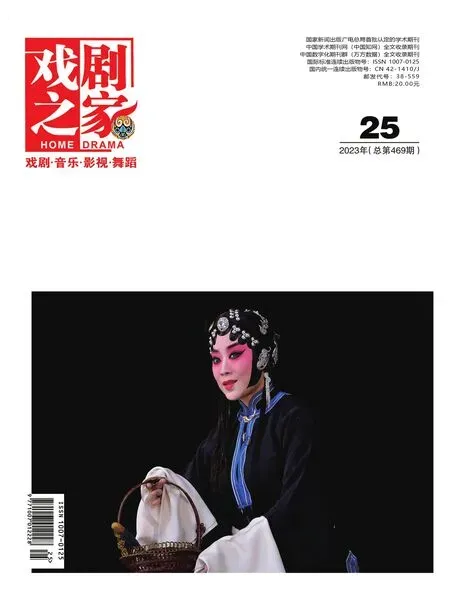關于自我與夢想的拷問
——《忒修斯之船》述評
賀 喜
(江蘇師范大學 江蘇 徐州 221000)
一、抽象的概念與舞蹈語言
忒休斯之船是西方哲學中最古老的思想實驗之一,它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個物體的所有組成部分都被替換了,那它還是原來那個物體嗎?在這個哲學概念下,編導聚焦在身份更替的變遷中,用現代舞的語言和方式,講述了一個人在彌留之際,翻越記憶圍墻,發現曾擱淺之夢,于是穿越不同時空,尋找夢的碎片與信念的故事。
從戲劇結構上來說,《忒休斯之船》有人物(老人)有情節(穿越時空尋夢)也有矛盾,但是三者并沒有戲劇邏輯上的關聯,而是以一種拼貼式,碎片化的呈現,著重于讓觀眾安靜下來,以一種近乎卓別林啞劇的形式——只交代演員當下行為,通過對道具和舞美的使用來提醒觀眾,劇情發展到“這里”就應該轉折了,極具內容的抽象感。再來是形式的抽象感,舞蹈拙于敘事而長于抒情是舞蹈永恒的議題,獨舞的敘事恐怕更是是局限重重,于是《忒休斯之船》從道具中找尋能觸發觀眾共情的因素,使得觀眾霧里看花的同時又從這些道具和氛圍中體會探索人生、追逐夢想和審視自我的孤獨感。綜上所述,舞劇具有抽象感的兩點,一是形式所致,二是內容所需,《忒休斯之船》并沒有低估觀眾的理解能力,而是以編導的想法為內核,以舞者的身體為外殼,表達編導和演員的初心,不迎合大眾,任憑觀眾自由理解,如果為了使觀眾看懂而看懂,就失去了作為現代舞關注舞者個人生存狀況(王玫)的特點,有時讓觀眾自己體會甚至會得出更加“高深”的見解。
二、作為舞蹈劇場的《忒休斯之船》
《忒休斯之船》是一個典型的舞蹈劇場作品,那么何謂舞蹈劇場?舞蹈劇場這一概念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著名舞蹈家皮娜·鮑什提出,舞蹈劇場,德文Tanz the Clter,英文Dance theatre,這是一種手段高度綜合的劇場演出形式,它摒棄了古典芭蕾意義上的美學。區別于舞劇,它很少去講述一個連貫的故事,甚至可以完全沒有故事情節,是用一種近乎蒙太奇的手法將一些碎片化的場景拼貼在一起,它又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舞蹈詩,不去刻意尋求意境和美感,而是注重舞蹈本身和演員的肢體,打破音樂的桎梏,一切聲音皆可以用作音樂。簡而言之,即劇場中包含的所有事物都可以利用起來為舞蹈本身服務,包括舞蹈影像的使用、文字和獨白的使用、音樂的使用甚至是觀眾本身。
《忒休斯之船》作為舞蹈劇場作品,有其獨特的魅力與亮點,欣賞舞蹈藝術就應該走進劇場里,因為觀眾的隨機性會給表演增加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胡沈員一開始采用的出場方式是從觀眾席中戴著面具出現,并以互動的形式隨機挑選觀眾在純白的面具上涂上顏料,南寧站巡演中胡沈員挑選了一個小孩為其面具上色,但是女孩年齡太小,看見近似于人臉的白色面具受驚大哭,并且愈演愈烈,這時觀眾們都覺得可愛,哄堂大笑,這個與觀眾的互動環節也成為了演出的一部分,觀眾也參與了這場表演。開頭已經引人入勝,結尾也給人以一種情懷的感動,胡沈員斜掛在旋轉舞臺的爬梯上,隨著舞臺的旋轉而蹁躚起舞,配合著大樹和小白船像極了童話中的小王子,接著地陷舞臺緩緩升起,舞蹈中音樂作曲人李星宇在一束白光下彈著小白船,原來音樂是現場的即興伴奏,不禁讓人心里懷念起夢中兒時的小白船,圓滿結束的背后是主創人員們精心打磨的汗水。
三、時空中“自我對話”的純舞段
這里所謂的純舞段指不依靠道具與演繹,而是將演繹的成分完全融入舞蹈動作中,即便將這個舞蹈單拿出來也可以作為一個小的舞蹈作品。純舞段的安排并不是單純的身體展示,而是身體作為舞蹈的媒介能夠展現不同時空里的人物狀態,可以拋開諸多的輔助,比如道具和舞美,回歸舞蹈的本真——用身體敘事。
整個作品有兩個關于“年輕自己”的純舞段:一個是老年時記憶中年輕的自己,一個是已經通過穿越時空之門,變得年輕的自己,這樣一說來好像都是年輕時的自己,但其實不然。前者是彌留之際的老人在被AI 智能要求輸入密碼時,精神混亂下記憶中的自己,這時的身體還是老年的,只是懷念起來自己年輕時的“角兒”夢。這個舞段可以說是整個作品前半段的華彩部分,胡沈員老師的肢體形成了自己的胡氏絲滑,融合了古典舞的身韻和京劇的一板一眼,他身著黑衣,模樣尤其像武僧,但是他又在其中反串(映射十面埋伏中的虞姬),打破了這一點,暗示了主人公可以是任何人,他當然也是“胡沈員本人”,并且在其中還融入了川劇的變臉,增加了主人公身份的不確定性,突出他的精神可能是混亂且天馬行空的,同時也增加了舞蹈的可看性。
后者是穿越時空后,已經完全變成年輕人的自己,胡沈員在“變身”之后身著白衣,而下身只有一條肉色的短褲,只是起到了遮羞的作用而已,這里也就完成了從老者到年輕人的轉變,可以理解為人的降生和離去都是孑然一身,一絲不掛的,舞者從橫向調度到曲線調度再到舞臺旋轉起來原地翻騰,像極了一顆水珠在光滑的白色盤子上滑動、跳躍、滾落。這時的純舞段已經接近尾聲,給作品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預示著和解、圓滿、歸一,所以在這里胡沈員身著一襲白衣,象征著內心世界的不加粉飾、潔白無瑕。
四、“機關算盡”的舞臺設置
舞臺對于舞蹈來說絕不僅僅只是承載的作用,相反如今的舞蹈更加依賴舞臺,好的舞臺設計和舞美更加能表達出舞蹈的情節和情感,同時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新鮮體驗。《忒休斯之船》采用的是黑匣子的舞臺包裝,搭配有多重變化的超現實純白舞臺,就如同潔白的畫紙,任憑演員的肢體在上面流動作畫,一閃而過的行動軌跡和舞蹈路線因為白色的舞臺顯得尤為明顯,仿佛一幀連著一幀定格起來。小型劇場并不等同于實驗小劇場或者黑匣子劇場。一般認為,實驗小劇場指演出的戲劇形式帶有實驗性、先鋒性,舞臺與觀眾席之間沒有明顯的間隔或區分,座椅排布相對靈活的小型劇場。這種劇場會制造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胡沈員老師開場時并未走上舞臺,而是架起扶梯爬上舞臺,又在要預示著身份轉變的時候隨著一束追光站在舞臺邊伸出雙臂,墜落入深不見底的樂池,不禁讓人捏把冷汗,在這種快速消失中完成了人生一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忒修斯之船》的舞臺恰恰滿足了實驗性與先鋒性的黑匣子劇場的要求,為舞蹈內容服務的同時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
同樣令人出其不意的的還有“舞臺地窖”,這是舞美中的一個小機關,在舞臺上的正中央有一塊能夠活動的地板,拉開后里面是空心的,演員可以鉆進去,當胡沈員將自己倒立置于地窖之中時像是被吞噬,被蠶食,被吸入了時空隧道里,被扔進了垃圾堆里,這種不尋常的舞臺設計下產生的怪誕的舞蹈造型一下子沖擊到觀眾的心靈。如此多樣化、創新化的舞蹈語言與舞蹈造型與舞臺設計是息息相關的,《忒休斯之船》能夠巧妙的運用舞臺來為舞蹈動作、舞蹈語言服務,是主創人員努力調適和打磨的成果,同時也是技術進步與審美多樣性的最好證明。
五、“別具一格”的道具使用
關于道具的使用在作品中尤其出彩:只有框架的小船、拼湊框架小船的碎片、舞臺地窖、爬梯、框架人模型群像、手執的擊劍、小木偶和面具。起初擔心道具過分華麗會搶演員風頭,但是隨著故事的發展每一個道具都被賦予了生命,同時發現道具之精致可以填補獨舞形式的空白與舞臺的單調。
尤其兩個部分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處是主人公試圖從人群框架中抽出爬梯,用來將碎片拼湊出懸吊在高處的忒休斯之船,但是始終無法抽出爬梯,于是他與模型人物重合,加入它們與它們比耶合影,表情諂媚,試圖成為他們的一員,不禁引人唏噓,若想實現自己的價值就必須隨大流?最后他抽出了爬梯,搖搖晃晃的拼湊出了不完整的忒休斯之船,預示著人類永遠無法拼湊出一個過去的自己,也無力改變過去。第二處是主角戴著厚重的多重面具,他想擺脫這個面具,顯得焦躁恐懼,但是他扯掉一張還有無數張,最后他的臉上居然吊著一個彈簧面具,詭異至極,主人公將一個個面具摘下戴在環形站立著的框架人模型上,最終,在環形舞臺上的框架人模型中間,留出來了一個空位,那個空位就是留給他自己的,這是否意味著人類在社會的洪流中始終以不同的面具示人,最終也變成了虛偽人群中的一員,過程雖然掙扎,結局卻無法逃避——每個人都會擁有自己的一副面具。
另外,同一道具以不同功能出現也顯得十分巧妙,主角手執的擊劍,在老年時是他的拐杖,青年時又化成忒休斯之船的船槳,有時又幻化成“加勒比海盜的義肢”,替演員延長自己的手臂。小木偶則負責充當推進情節的引子,它與過去的主人公對話,但也可能木偶本身就是過去的主人公的化身。
六、中國傳統元素的注入
胡沈員作為中央民族大學科班出身的演員,接觸到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與古典舞都成為了他舞蹈身體中的養分,也形成了他特有的肢體風格,在古典舞訓練下形成了柔軟的身體質感和圓潤的動作質感,在民族民間舞的訓練中形成了豐富的造型質感和多變的律動質感,于是胡沈員的現代舞具有了中國舞的美感,而在觀念上,胡沈員始終認為要把中國的元素帶到世界去,不管是在取材、編排甚至是取名上,他都努力的將中國元素放大。于是《忒修斯之船》中便有了熟悉的中國元素——川劇變臉和京劇中的“舞”。面具可以很直觀體現“人性的偽裝”,但是川劇變臉更能夠體現在同一個客體上發生的變化,并且是動態的,從物理形態變化上象征物是人非,單純比起面具的使用,變臉更具有辨識性與獨創性,更能表達意蘊。
作為國粹,京劇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象征,胡沈員在《十面埋伏》中飾演的虞姬以舞蹈和京劇的融合作為舞蹈語言,而京劇也從此融入了胡沈員的血液,虞姬這一角色仿佛量身為其定做,于是在《忒休斯之船》之中觀眾能清晰的看見虞姬的影子,在老人推開時空之門之前,西裝革履的舞起來一段具有京劇韻味的現代舞,是如此不搭,但是又令人備受震撼,也許是由戲劇到生活,也許生活就是戲劇,京劇是《忒休斯之船》中彌留之際的老人的記憶,也是胡沈員心里的虞姬的回聲。
七、從胡沈員《忒休斯之船》窺見舞蹈劇場的現狀
看完作品之后留下的是感動,回歸理性后審視這個舞蹈市場的環境,一場舞劇或者是舞蹈劇場的呈現所付出的心力不止是臺前更是幕后,胡沈員擔任出品和制作人的同時,身兼導演、舞蹈戲劇構作、編舞、舞臺概念設計、演員七職,甚至舞臺的旋轉角度都一一把控確認,所以成功來之不易但也名副其實。但是不得不說《忒修斯之船》也是幸運的,因為胡沈員擁有著頂尖的舞蹈水平的同時,參加綜藝帶給他了人氣與資源,得到了各方的幫助支持,使得這場演出更加美輪美奐,然而在這一狀況的反面不禁讓人惋惜,許多沒有被大眾注意到的,但也在潛心搞創作的現代舞團和舞者們(包括之前紅極一時,如今卻缺失市場的舞者們)已經面臨或者正在面臨著解散、失業,這些舞者也不乏優秀的作品想要走進劇場被人們看見,他們僅僅是缺乏一個的機會而已,更加悲觀的是,也許在后疫情時代下有且只有通過舞者的明星效應才能使自己嘔心瀝血創作的作品走進劇院。所以如果要改善這一狀況,舞蹈電視與互聯網平臺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希望今后的舞蹈節目組建專業團隊,精心挑選出能夠代表舞蹈藝術本身的作品,而不是一味迎合觀眾的快餐式舞蹈或者是被資本裹挾,從內而外形成一個較好的觀舞風氣——這就得靠社會把關好大方向:普及舞蹈文化,營造出多元的舞蹈文化氛圍。靠編導的頭腦風暴:創作出形式與內容并重,具有業界較高水準同時大眾喜聞樂見的舞蹈作品。靠專業演員的生動詮釋:業務能力永遠是檢驗舞蹈演員的首要條件。靠舞蹈評論引導良好的輿論風向:做到實事求是,不過分褒貶某一舞蹈作品誘導輿論風向,做到扎根學術,不故意引戰舞蹈實踐與理論兩派使得互相抵觸。如此一來舞蹈圈上下齊心只為了好的作品,便能營造出良好的舞蹈市場和觀舞環境。
我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