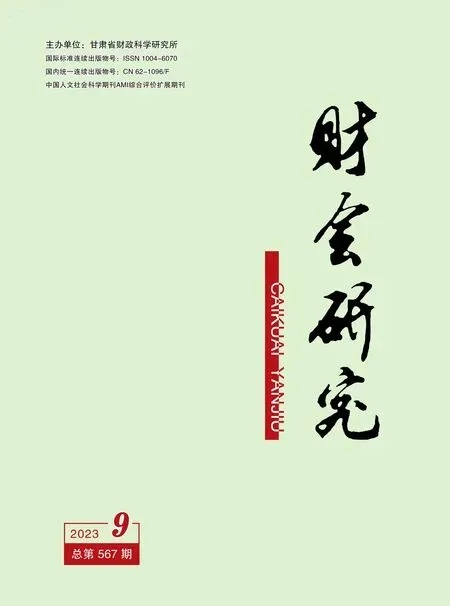高管背景特征與公司違規研究進展
——基于高管人格特質視角的拓展
■/ 付金微 齊祥芹
一、引言
近年來,上市公司違規事件頻發,嚴重損害了公司價值,給中小投資者以及市場健康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證監會官網通報2021年20起證監稽查典型違法案例,案件涉及財務造假、欺詐發行、虛假陳述、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介機構未勤勉盡責、私募違法違規以及對抗執法等;違法違規主體涉及個人、上市公司、券商、私募、審計機構等,亞太藥業、瑞華所、海通證券等被點名。根據萬得平臺關于上市公司違規的數據,2022年A股監管機構共有1114個公司違規案例、3324個個人違規案例,其中公司案例涉及609家上市公司,涉及信息披露違規的公司占所有違規公司的81.24%。截至2023年7月,已有48家上市公司或公司相關責任人被立案調查,其中超過6成涉嫌信息披露違規。公司違規行為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影響資本市場誠信基礎,備受政府關注。
2020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明確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文件指出要加強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減少信息披露違規的發生,并加大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違法、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強調要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基于高質量信息發展的要求,國家監管部門不斷加強對公司違規行為的打擊,加強執法力度,進一步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監管體系,推動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
基于此,公司違規行為的影響因素以及違規治理研究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其中,高管作為公司決策的主體,其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行為有著重要影響。
根據高層梯隊理論(Hambrick &Mason,1984),高管背景特征影響高管的認知方式、行為決策,從而影響企業行為。同時,高管以往經歷烙印也會影響其決策,并進一步影響企業行為。學術界關于公司違規行為與治理研究,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影響研究等方面學術成果不斷涌現,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心理學研究中“大五”人格等人格特質理論的發展,高管人格特質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漸入視野。因此,有必要對上述研究進行梳理,以為日后研究提供可能的思路與方向。
本文主要從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研究兩部分展開,進一步引入人格心理學中的“大五”人格特質理論,回顧梳理了高管人格特質與企業行為相關研究,希冀從高管人格特質視角,拓展對公司違規行為的研究。
二、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
從高管個人特征角度來看,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研究發現組織戰略結果和績效水平等,部分可由高管背景特征預測(Hambrick &Mason,1984)。背景特征的異質性會使管理者做出不同的決策,這些特征涵蓋如年齡、性別、教育背景、工作背景、經驗、任期等。參考Milliken &Martins(1996)的研究將高管個人背景特征劃分為顯而易見的特征,包含年齡、性別等;潛在特征,包含任期、教育背景、職業背景、行業經驗等。本部分主要梳理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從“高管的易觀察特征”和“高管潛在特征”兩方面展開。
(一)高管的易觀察特征
1.性別。由于男女觀察事物的細心程度有所差異,所以不同性別的高管在溝通協調、風險承擔、決策制定上有明顯差異。在公司績效方面,賀新聞等(2020)認為女性有更好的溝通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在提升組織績效方面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企業應該提升女性高管的比例。Klevak et al(2021)研究發現,女性高管更保守的投資風格可以為公司帶來更好的業績。在風險承擔方面,Knight(2002)研究發現女性高管風險偏好程度低于男性,也更加厭惡具有較高違規風險的行為。Amore et al(2014)指出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男性高管能提高財務績效,但也加劇了風險承擔。歐陽辰星等(2017)認為女性高管在公司經營中更加謹慎、厭惡風險,從而減少研發投入。在社會責任方面,Zou et al(2016)認為,與有男性高管的公司相比,有女性高管的公司更有可能報告企業社會責任聲明,還會鼓勵企業加強其企業社會責任聲明的內容。淦未宇和肖金萍(2019)認為女性有更強的社會道德感,相比于男性高管,在面對道德選擇時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在并購投資方面,Huang &Kisgen(2013)認為,男性可能由于過度自信,做出不利于公司發展的財務和收購決策。Levi et al(2014)認為女性不像男性會過于自信,因此有女性董事的公司不太可能進行收購,或即使進行收購,也會支付較低的溢價。李衛民和黃旭(2014)指出女性比例較高的高管團隊更加和諧民主,所以有利于抑制高管過度自信與激進投資,因而并購行為相對減少。
2.年齡。年齡差異會造成高管社會閱歷和對風險喜好程度的不同,從而影響高管在經營管理中的行為決策。本文從組織戰略決策、會計信息質量和公司績效三個方面進行回顧梳理。組織戰略決策方面,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戰略制定的靈活度會下降,而剛性和對變化的抗拒程度上升,年齡越大的管理者更難接受新信息,對企業經營戰略的風險厭惡程度也更高(Wiersema &Bantel,1992)。尹律等(2020)認為年齡較大尤其是臨近退休的高管追求簡單的管理模式,對公司的經營評價標準相對寬松,傾向于選擇寬松的內控缺陷評價體系。會計信息質量方面,現有學者認為高管年齡與會計信息質量正相關,萬宇洵等(2012)發現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年齡大的高管會減少盈余操縱,從而提高盈余質量。盧馨等(2015)發現高管團隊的平均年齡與上市公司發生舞弊的可能性呈負相關。林萍等(2020)認為年齡越大的高管越謹慎,披露的會計信息質量越高。公司績效方面,盧馨等(2017)研究發現高管的平均年齡與企業投資效率正相關。陳素琴等(2021)發現高管年齡越大,積累的經驗越豐富,對財務困境的應對能力越強,有利于公司績效提升。
(二)高管的潛在特征
1.任期。隨著任期時間的增長,高管對企業經營的實際控制權力更大,從而會對公司經營和信息披露產生重要影響。在公司經營方面,有學者認為長期任職的高管擁有公司與特定行業的業務經驗,熟知業務風險,很可能做出更好的戰略決策(Carpenter et al,2003;Dokko et al,2009;許曉明和李金早,2007)。宋鐵波等(2020)研究發現,隨著任期的增長,CEO對于公司的經營情況和內部信息掌握的更全面,且對于風險的承擔能力更強,有利于企業的研發投入。Angela et al(2021)認為高管長期任職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使得企業有更多的資源渠道,能有效地把資源轉化用來企業創新。張新昌(2021)指出長期任職的高管可以積累更多經驗,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對于企業績效的提升有積極作用。與之相反,也有學者認為長期擔任首席執行官的高管很可能固步自封,對商業環境看法短視,因而可能會導致糟糕的并購決策并有損股東價值(Audia et al,2000)。Liu et al(2012)提出高管團隊任期過長有損企業價值。鄭鈺佳和呂沙(2015)認為隨著任期時間的增長,高管更依賴原有的管理模式,安于現狀從而減少R&D投資。
在信息披露方面,有學者認為高管任期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吳雅琴和王梅(2018)研究發現,任期時間長的高管更注重公司的利益,從長遠的視角為企業績效考慮,從而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劉娜(2019)研究發現,高管任期時間越長,越能及時發現公司內部治理存在的缺陷并有效應對,從而減少信息披露中可能存在的不合規情況的發生。另一種觀點認為任期與信息披露質量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岑維和童娜瓊(2015)指出高管任職初期會通過盈余管理維護自己的聲譽;隨著任期時間的增長,高管擁有更大的權力并且受到的監督變少,盈余程度會提高,信息披露質量下降。許言等(2017)認為高管在不同的任期階段對公司信息披露的程度有所不同,為了建立良好的市場聲譽,CEO在任職初期和離職前一年有更強的動機隱藏壞消息。
2.職業背景。具有不同職業背景的高管在技能、態度以及認知能力和方式上會有所差異,而高管的認知方式又體現于公司的經營決策。本文從公司績效、信息披露、審計費用和社會責任四個方面梳理高管職業背景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公司績效方面,Dimitrios &Hang(2018)認為財務專才型CEO有助于IPO企業的績效,并提高了企業的存活率。湯倩等(2021)認為,多職業背景CEO可以積累更豐富、更全面的工作經驗,思維更加敏捷并具有長期視角,為做出正確的決策提供了支撐,有利于企業資本的積累。趙馨燕等(2022)發現復合型高管除了從事本職工作,也接受過其他崗位的培訓從而擁有更多技能,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但也有學者認為高管的職業經歷也可能會為企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劉繼紅和章麗珠(2014)認為具有財務工作經歷的高管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會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因其并未充分發揮專業技能和經驗,反而會助長公司的盈余管理。尚航標等(2018)認為熱認知職業背景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而冷認知職業背景則會降低企業技術創新。
信息披露方面,有學者認為高管的職業背景會提高信息披露質量。Agrawal &Chadha(2005)發現,具有會計師事務所經歷的高管會降低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的可能性。羅蓉曦和陳超(2019)研究發現,出于對研發的需求和興趣以及對財報披露要求的了解,具有研發背景和財務背景的高管傾向于在年報中披露研發支出。張川等(2020)也發現具有審計背景的高管所在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相對較低。但有學者持相反觀點,如蔡春等(2015)從高管審計背景出發,分析檢驗認為高管審計背景可能會降低公司的財務報告信息質量,提高審計風險。
審計費用方面,胡雪婷(2017)指出具有審計背景的高管人數越多,審計收費會更低。與之相反,蔡春等(2015)研究發現具有審計背景的高管更可能實施真實盈余管理,增加審計收費。王麗娟和耿怡雯(2018)認為有財務經歷的高管會因為專長而實施更隱蔽的盈余管理,加大審計風險并且提高審計收費。
社會責任方面,現有研究認為高管的職業背景有利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基于“認知烙印”和“能力烙印”,李心裴等(2020)指出具有海外工作經歷的高管在決策時容易受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影響,從而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吳衛星等(2020)從管理人員研究經歷視角研究,發現高管研究經歷有助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曹越和郭天梟(2020)也指出有高校任職經歷的高管更加重視社會責任的履行。李毅等(2022)研究發現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更能認識到環境保護的迫切性,從而促進企業履行環境責任。
3.教育背景。高管的教育背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高管的教育背景可以從學歷背景和學術背景兩個角度考慮。從學歷背景角度而言,部分學者認為平均學歷與多樣化程度更高的高管在企業績效方面表現得更為出色(Hambrick &Chen,1996)。Wang &Yin(2018)研究高管學歷背景與并購所在地的關系發現,出于信息優勢高管們更可能選擇本科或碩士就讀所在地進行并購。史晉川和劉萌(2019)認為高教育水平使高管看待問題更加全面,在公司治理中重視長期發展,受到媒體輿論對于研發的壓力較小。從學術背景角度而言,何任等(2019)發現,高管能將自己的科研專業特長和掌握的前沿知識運用于決策過程,同時其聲譽資源與人脈資源等“軟實力”也有助于公司治理。何旭和馬如飛(2020)從地位感知角度分析高管對創新挫折的容忍度,認為有學術背景的高管與創新投入正相關。俞靜和王運棟(2021)認為基于學術背景烙印,高管對創新的理解更深刻,獲取創新信息和創新融資渠道的機會更多,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投入。魯桂華和潘柳蕓(2021)基于信息質量假說和代理成本假說,檢驗發現高管學術背景會降低企業股價崩盤風險。但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高管們的教育背景與其薪酬、企業績效沒有必然的聯系(Jalbert et al,2011;Gottesman &Morey,2015)。
綜上所述,本部分從“高管易的觀察特征”和“高管的潛在特征”兩個角度梳理了國內外關于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影響的研究,現有研究關于高管不同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成果豐富,為未來研究開展提供了有益借鑒與啟示。
三、高管背景特征與公司違規
現階段基于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公司違規行為受到廣泛關注,公司違規的影響因素與治理受到日益豐富。在外部視角方面,已有研究發現文化和法律環境、產品市場競爭、媒體以及中介機構可以顯著抑制公司違規(潘子成等,2022;滕飛,2016;周開國,2016;陳峻等,2022;卜君和孫光國,2020)。內部視角方面,學者研究發現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管理層結構和薪酬激勵對公司違規行為有顯著影響(張棟等,2007;曾月明等,2011;喬菲等,2021;Johnson et al,2006)。高管作為公司決策的制定者,其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也受到廣泛關注,本部分對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并基于高管個人特質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
(一)高管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
1.性別與年齡。男女高管在人際關系處理、風險承擔、決策制定上存在明顯差異(Adams &Ferreira,2009;Tate &Yang,2015),女性更加厭惡具有較高違規風險的行為。這一差異也體現在男女性格方面,相比于男性高管,女性高管更加誠實,也更少地發生通過違規行為謀取私利的現象(Dreber &Johannesson,2008)。女性高管在行事中趨于保守,更看重自身的聲譽(Amore &Garofalo,2016),更愿意踐行穩健和誠信的經營原則,盡量減少公司違規行為以避免法律責任的承擔。路軍(2015)認為,女性高管通過傳染效應改變男性高管對風險的認識,由于其低風險、低自信的特點,在經營過程中注重信息的收集,加快信息在內部的流動,從而抑制公司違規。Cumming et al(2015)認為女性高管的強道德感會抑制公司證券違規。淦未宇等(2015)研究發現,為了避免違規后的懲罰和聲譽受損,女性高管一般采取穩健的經營原則,進而減少公司違規操作。魚乃夫和楊樂(2019)研究發現,由于女性較保守,女性高管比例與公司違規負相關,且高管年齡越大越沉穩,公司違規的可能性越小。陳丹和李紅軍(2020)也指出女性董事的占比與公司違規顯著負相關。顧亮和劉振杰(2013)研究發現,年齡大的高管做出的決策更加理性,企業不容易出現違規行為。孫文靜(2017)認為,董事會的平均年齡與違規行為也呈現負相關關系,同時,平均年齡越小發生的違規程度越嚴重。
2.任期、職業與教育背景。隨著任期時間的增長,高管對企業經營的實際控制權力更大,從而對公司的戰略決策產生影響。有學者認為高管任期與公司違規負相關(尹飄揚和任柏坤,2019)。Wang et al(2018)認為高管任期越長,對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作用越大,從而減少公司違規的發生率。與之相反,楊薇和姚濤(2006)發現總經理的任期與董事會獨立性負相關,高管任期越長,董事會獨立性越低,不利于內控質量的提高,從而發生財務舞弊。
具有不同職業背景的高管在技能、態度以及認知能力和方式方面均有所差異,對公司違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有學者認為過往任職經歷會抑制公司違規的發生。Lawrence &Susan(2000)研究發現董事擁有財務會計知識能夠顯著提高公司的財務信息質量,具有財務背景的董事比例和公司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具有負相關關系。王霞等(2011)認為具有財會專長的CFO會減少會計差錯的概率。俞雪蓮和傅元略(2017)也指出CFO財務專長抑制公司財務違規。周博(2019)發現董事會成員的財會和法律背景異質性對上市公司違規存在著顯著影響,具有財會和法律背景的執行董事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具有抑制作用。與之相反,車響午和彭正銀(2018)指出,執行董事的獨立性較低,具有法律和財會背景的執行董事更容易被高管要求參與公司違規。
高管教育背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從而影響公司決策和違規行為。顧亮和劉振杰(2013)指出,高管受教育水平與公司違規負相關。尹飄揚和任柏坤(2019)認為教育會帶來認知的差異,高管教育背景與公司違規顯著負相關。魚乃夫和楊樂(2019)研究發現,高管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辯證思維能力越強,違規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越小。
綜上所述,本部分從性別、年齡(高管的易觀察特質)和任期、職業與教育背景(高管的潛在特質)兩個方面考察高管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隨著人格心理學中人格特質理論的發展,學者在研究高管對公司決策影響時,人格特質的影響逐漸進入研究視野,并取得了階段性研究成果。下文將對高管人格特質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并希冀從此視角對公司違規行為影響研究嘗試進一步拓展。
(二)進一步拓展:高管人格特質與公司違規
1.高管人格特質研究。20世紀2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Allport(1937)將人格特質分為個人特質和共同特質,個人特質是指每個個體所具備的特質,共同特質指一個群體所表現出的相似、共同的特征,隨后逐漸發展形成了人格特質論。“大五”人格理論由Tupes &Christal(1992)提出并完善,他們將個體人格特質分為五類因素,分別是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宜人性、盡責性。這五類因素和特點分別是:
(1)神經質(N)——情緒穩定性:焦慮、對抗、沖動、脆弱、壓抑、自我意識
(2)外傾性(E)——外向性:熱情、社交、果斷、活躍、冒險、樂觀
(3)開放性(O)——開放性:抽象、審美、充沛情感、求異心理
(4)宜人性(A)——隨和性:信任、直率、利他、依從、謙虛、移情
(5)盡責性(C)——謹慎性:勝任、條理、盡職、成就、自律、謹慎
隨著人格心理學的不斷發展,“大五”人格模型日益受到關注。人格特質是個體穩定的、一致的心理特征,作為心理學、管理學等學科的重要交叉研究內容,高管人格特質受到了學者的關注。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逐漸認識到人格特質可以影響個體決策行為,人格特質對高管團隊個體成員的行為有強烈影響,從而影響公司業績、戰略決策和信息披露。

表1 “大五”因素及特征
公司業績方面,學者認為外傾型CEO能提高企業盈利能力。Malhotra et al(2017)研究發現CEO外傾性與公司達成交易的可能性、此類交易的頻率和交易的規模正相關。Green et al(2018)發現CEO外傾性可以提高投資者認可度和銷售額,從而提高公司績效。Wang &Chen(2019)通過CEO在社交媒體發布的語言線索分析他們的個性,結果表明CEO外傾性、情緒穩定性和隨和性有效提高了企業的成本效率和盈利能力,而CEO責任心則降低了成本效率和盈利能力。但也有學者指出外傾型人格特征會增加資本成本從而對公司業績產生不利影響,Adebambo et al(2019)通過CEO在電話會議期間的講話模式進行外傾度測量,發現CEO外傾度與公司的預期資本成本存在正相關關系。Liao et al(2022)認為在金融危機期間,外傾型CEO的過度冒險對公司業績會產生負面影響。
戰略決策方面,高管外傾性特質與風險偏好顯著正相關,即高管外傾性越強,公司對外投資規模越大(姜小祥,2017;肖峰雷等,2011;)。Aktas et al(2010)研究發現,收購方CEO自戀程度越高,收購公司發起交易的可能性越大,并指出目標公司CEO自戀程度越高,出價溢價越高。Malhotra et al(2017)認為,由于外傾型CEO傾向于尋求和享受大規模增長機會,發現獲得性增長機會,并將這些機會轉化為集體行動,外傾型CEO更有可能參與收購,并進行更大規模的收購。Arena et al(2018)發現CEO自傲有利于企業綠色創新,其對環境創新的影響隨著組織松弛度的增加而增加,但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程度而減弱。孟祥梅(2020)研究發現高管團隊的外傾性越強,企業越可能采取擴張型戰略。Hrazdil et al(2021)研究發現,外傾型CEO更樂于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進行互動,并且會考慮企業的長遠利益和發展,從而促進其參與社會活動,履行社會責任。
另一方面,高管人格特質也會對企業決策產生不利影響。Capalbo et al(2017)認為自戀的高管通常會夸大自身的重要性,強調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從而會通過盈余管理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投資者的肯定。Zhang et al(2020)發現自傲的CEO無視法律、法規和道德要求,并賦予自己實現業務目標的獨特使命,導致他們在從事項目時忽視環境損害,基于此指出CEO自傲與公司污染正相關。
信息披露方面,Liao et al(2021)指出,外傾型CFO會發布更多的盈利預測,但由于CFO過于樂觀,導致收益預測的質量較低。與之相反,Yue(2019)發現CEO外傾性與公司發布盈利預測的可能性正相關,但與發布預測的偏差負相關。Liu(2019)研究發現高管的宜人性和神經質特質與股價暴跌風險正相關,而認真性與股價暴跌風險負相關,并指出宜人性和神經質特質與壞消息隱瞞呈負相關,責任心與壞消息隱瞞呈正相關。
2.高管人格特質與公司違規。高管人格特質影響其行為決策從而可能對公司違規產生影響。Magnan et al(2010)認為自傲的高管代表其非理性的特點,容易產生公司違規行為。Cohen et al.2010)提出,專制型人格的高管不利于公司健康文化的營造,也會加劇違規的可能性。Rijsenbilt &Commandeur(2013)發現自戀的CEO會采取有挑戰性的行動獲取外界的認可和贊賞,從而導致違規行為。還有學者發現具有性格魯莽(Davidson et al,2015)、違規駕駛行為(Mironov,2015)等特點的高管更容易導致公司違規行為。
綜上所述,具有不同人格特質的高管其風險偏好程度和冒險精神有所不同,從而對企業業績、戰略決策和信息披露產生不同影響。現有關于高管人格特質與企業行為研究正處于新興發展階段,研究內容相對集中于外傾型高管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不同人格特質的影響分析以及對公司違規行為影響的研究尚待進一步探究。
四、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詳細回顧了高管背景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梳理了高管背景特征對公司違規的影響研究,進一步基于高管“大五”人格特質視角梳理人格特質的相關研究。本文為學術界和實務界系統理解已有成果提供了一定借鑒,希望拓展不同學科的交叉研究,拓展公司違規治理的研究視角。
(一)積極探索人格特質視角對公司違規的影響研究
縱觀已有研究,一方面,現有關于高管人格特質與公司違規的研究相對較少,考慮到高管對公司違規的重要影響以及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這一研究方向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另一方面,目前關于人格特質對企業行為影響的研究已取得階段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研究主要圍繞外傾性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展開,其他四種特質的研究尚待探討,宜人性、盡責性、開放性和神經質對于企業行為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積極探索人格特質的研究方法與度量
現有人格特質的研究中,對于高管人格特質的定義界限不清晰,不同學者對于同一特質有不同的解釋,使得對于相同特質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現有研究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兩種,包括測量支配-順從關系調查表(A-S反應研究)和測量興趣的相對強度調查表(價值研究),前者用來測量個體在日常關系中支配或服從的行為傾向,后者測量個體的價值傾向。也有學者使用社交平臺發表的語言、會議中的講話模式等度量人格特質程度。不同研究方法以及度量過程中存在的主觀偏差都會影響對人格特質的評估。因此,在未來研究中,可以積極探索人格特質的研究方法,明確人格特質概念,并且構建相對有效的度量方法,減少人格特質度量的偏差。
(三)積極拓展相關研究方法
現有研究多以高層梯隊理論為基礎,探究經歷烙印對高管的行為決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對于高管本身心性對其行為決策的影響有所忽視。比如高管話語的語速、聲調都能反映出高管性格,從而影響高管的行為決策。在未來研究中,可以考慮結合心理學、行為學等學科方法來考察高管背景特征探究對公司違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