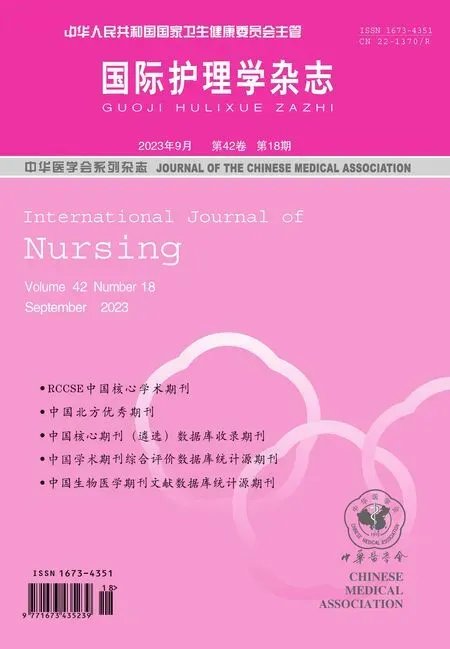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家庭教養、情緒調節效能的相關性
王寧寧 馬麗麗 張玉
1聊城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康復科 252000;2聊城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科 252000
物質依賴是指長期濫用某種物質而在軀體、心理上產生強烈且難以克制的尋覓該物質的狀態,以期體驗該物質的心理快感。隨著社會水平的不斷提高,物質依賴問題范圍有所擴大,其對個人與家庭均造成嚴重危害,逐漸成為社會關心的重點問題。相關報道指出,物質依賴患者可經過治療擺脫生理依賴,但其產生的強迫性心理依賴難以解除〔1〕。物質依賴患者產生的心理依賴會影響患者應對方式,具體表現為以消極應對方式,若未加以重視,可導致物質依賴復發。因此,提高對物質依賴患者心理治療具有重要意義。目前臨床對物質依賴患者的相關研究主要以運動干預、藥物治療等為主,對患者與相關研究因素研究較少,缺乏相關數據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在臨床實踐及查閱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自我效能的關系,為臨床心理干預提供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聊城市第四人民醫院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182例為研究組,另選取同期健康人群175例為對照組。其中研究組男98例、女84例;年齡29~62歲,平均(46.71±7.90)歲;其他精神病家族史10例。文化程度:小學11例,初中44例,高中27例,中專8例,大專8例。對照組男94例、女81例;年齡31~63歲,平均(47.01±7.51)歲;其他精神病家族史9例。文化程度小學10例,初中42例,高中25例,中專7例,大專7例。
1.2 選取標準
1.2.1研究組 ①納入標準:有明確藥物依賴史;符合ICD-11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診斷〔2〕;問卷調查時精神病性癥狀如妄想、幻聽等得到控制;父母健在。②排除標準:目前存在妄想、幻聽等精神病性癥狀;合并心境障礙、精神分裂癥等嚴重精神障礙性疾病;合并嚴重軀體疾病、遺傳疾病或神經系統疾病。
1.2.2對照組 ①納入標準:無藥物濫用史、吸毒史、物質依賴史: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文化程度、月收入狀況等方面與研究組相匹配,無統計學差異;父母健在。②排除標準:存在妄想、幻聽等精神病性癥狀;合并心境障礙、精神分裂癥等嚴重精神障礙性疾病;合并嚴重軀體疾病、遺傳疾病或神經系統疾病。
1.3 方法
應對方式調查:采用醫學應對問卷(MCMQ)〔3〕進行評估(經預試驗,本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為0.83,效度系數為0.84),共20項,分為面對、回避、屈服3個維度,以4級評分法進行評估,分值越高表明越常用該種方式。②自我效能調查:以中文版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量表(RESE)〔4〕評估(經預試驗,本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為0.80,效度系數為0.79),包括表達積極情緒、調節痛苦情緒、調節憤怒情緒3個方面,共17項,每項采用5級評分法計分,即每項1~5分,分值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好。③家庭教養:以中文版簡式父母教養自陳式量表(S-EMBU)〔5〕評估(經預試驗,本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為0.82,效度系數為0.81),共42項,每項采用4級評分法計分,即每項1~4分,包括拒絕、過度保護、情感溫暖3個方面,其中拒絕及過度保護評分越高、情感溫暖評分越低表明家庭教養越差。
1.4 觀察指標
①比較兩組應對方式、家庭教養方式及自我效能。②分析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家庭教養、自我效能的相關性。③分析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影響因素。
1.5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等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患者的應對方式比較
研究組MCMQ評分中面對評分低于對照組,回避、屈服評分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的應對方式比較分)
2.3 兩組父母家庭教養方式比較
研究組父親、母親EMBU評分中拒絕、過度保護評分均高于對照組,情感溫暖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父母家庭教養方式比較分)
2.4 兩組患者的自我效能比較
研究組RESE評分較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的自我效能比較分)
2.5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家庭教養、自我效能的相關性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EMBU評分中拒絕、過度保護與MCMQ評分中面對評分呈負相關關系,EMBU評分中情感溫暖、RESE評分與MCMQ評分中面對呈正相關關系;EMBU評分中拒絕、過度保護與MCMQ評分中回避、屈服評分呈正相關關系,EMBU評分中情感溫暖、RESE評分與MCMQ評分中回避、屈服評分呈負相關關系(P<0.05)。見表5。

表5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家庭教養、自我效能的相關性
2.6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影響因素分析
Logistic多元回歸方程分析結果顯示,EMBU評分中拒絕、過度保護是MCMQ評分中面對評分的保護因素,EMBU評分中情感溫暖、RESE評分是MCMQ評分中面對評分的獨立危險因素;EMBU評分中拒絕、過度保護是MCMQ評分中回避、屈服評分的獨立危險因素,EMBU評分中情感溫暖、RESE評分是MCMQ評分中回避、屈服評分的保護因素(P<0.05)。見表6、表7、表8。

表6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MCMQ評分中面對評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7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MCMQ評分中回避評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8 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MCMQ評分中屈服評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調查結果說明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與健康人群存在明顯差異,在面對挫折、生活事件時更傾向于消極應對,而減少積極面對,提示臨床應重視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心理問題,引導其以積極方式面對生活及挫折。物質依賴患者身心健康受到明顯危害,促使其在面對問題、理解問題、看待問題的角度存在一定程度偏差,表現為采取消極的、不恰當的應對方式處理或解決問題〔6-7〕。物質依賴會使患者逐漸孤僻,使其逐漸遠離健康人群、家人及朋友,減少積極心理能量,同時物質依賴患者群體接觸較為緊密,積極面對生活的榜樣減少,內在應對的積極模式逐漸趨于弱小,而消極應對方式逐漸強化,導致物質依賴患者逐漸傾向于以消極應對方式面對生活〔8〕。物質依賴患者在經治療有所好轉后,仍存在較高的復發風險,通過改善其應對方式,使其積極面對生活、調節心理狀態對降低復發風險有積極作用〔9〕。因此,通過分析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并進行針對性干預有重要意義。
調查顯示,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明顯較健康人群更低。情緒調節自我效能術一般自我效能范疇,是個體在調節日常生活能力及管理過程中自信程度及自我把握感,一般而言,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水平較高的個體在理解他人感受能力、識別自身情緒狀態、管理積極與消極情緒等方面均有較高的自信程度〔10-11〕。但物質依賴對患者情緒存在直接影響,促使患者失去自我調節控制能力、情緒管理能力,使患者在調節自身情緒方面陷入無力感,具體表現為難以控制自身情緒,對自身情緒狀態存在模糊感,導致無法清晰辨別自身情緒狀態,從而降低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12-13〕。同時由于物質依賴的影響,患者理解他人情緒狀態的能力有所降低,逐漸變得以自我為中心,具體表現為對外界漠不關心。因此,通過積極提高患者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促使患者增強對自我情緒狀態、對他人情緒狀態的辨別能力,對促進以積極應對方式面對生活有積極作用。
調查結果顯示,物質依賴者家庭教養方式與健康人群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父母拒絕、過度保護明顯高于常規家庭,而情感溫暖略低。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是非辨別能力存在直接影響,不正確的家庭教養會降低子女是非辨別能力,正確的家庭教養則有助于促使子女形成積極的人格特征〔14-15〕。若家長過度保護,則促使子女對家長過分依賴,缺乏獨立自主性,難以控制自身沖動,最終由于外界及自身因素而形成物質依賴。
根據相關性調查結果顯示,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積極面對與自我效能感、家庭教養中情感溫暖呈正相關關系,與家庭教養中過度保護、拒絕呈負相關關系。家庭教養與子女應對方式密切相關,父母的情感溫暖可給予子女積極的心理能量,受到父母的認同與理解會逐漸培養子女認同他人、理解他人的能力,并逐漸擁有理解別人感受的同理心、管理自身情緒的能力,從而具有高水平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且更易以積極方式面對生活。而高水平情緒調節自我效能可促使個體以積極狀態面對困難及挫折,加強對消極情緒的管理,明顯提高自身情緒管理能力。因此,通過調節家庭教養方式、增強情緒調節自我效能,可明顯改善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
綜上所述,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受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自我效能影響明顯,臨床可通過多途徑、多形式健康宣教調節家庭教養方式、增強情緒調節自我效能,以達到改善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的目的。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精神科物質依賴患者與健康人群應對方式、家庭教養方式、情緒調節自我效能的差異,進一步揭示三者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得出物質依賴患者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在目前國內研究中相對較少,有助于為物質依賴患者家庭心理治療提供借鑒,對患者心理康復治療方案有一定指導作用。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