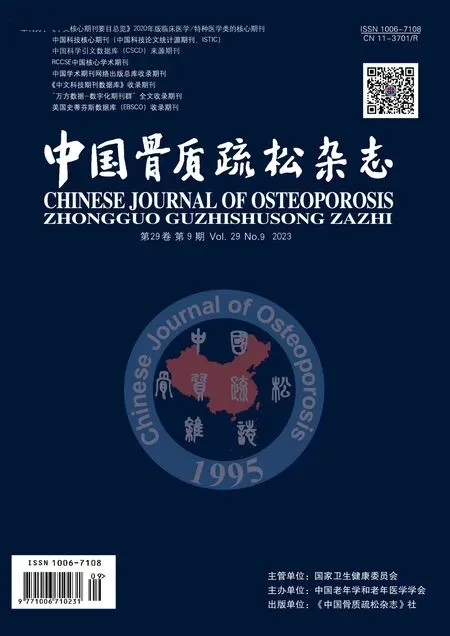絕經后女性骨折風險與肌源性因子及骨代謝指標的相關性研究
彭竑程 李雨真 華臻 王建偉 陳浩 梁杰*
1.錫山區人民醫院東亭分院,江蘇 無錫 214101
2.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
3.南京中醫藥大學無錫附院,江蘇 無錫 214071
骨質疏松癥是絕經后女性高發的一種骨代謝疾病,易致腰髖橈等骨折的發生。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中國50歲以上女性骨質疏松患病率高達20.7 %,60歲以上患病人群中女性占比急劇增加[1]。中國女性比其他人群更容易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估約40 %女性在絕經后會經歷骨質疏松性骨折[2]。我國絕經后女性常常伴隨著骨量減少和肌肉減少這兩大癥狀,這種混合性因素被認為是絕經后女性發生骨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代研究表明骨骼與肌肉密不可分,在生理、解剖、遺傳及功能上相互依存,形成“肌骨單位復合體”概念,兩者之間存在同步力-機械感受效應以及偶聯肌骨內環境的調控因子,這兩種模式雖然機制不盡相同,但最終都是通過信號傳遞共同調控骨代謝,維持骨骼之間成骨與破骨的動態平衡[3-4]。近年來,越多研究證實了肌肉通過內分泌及旁分泌等肌源性因子參與對骨骼的調控,并且已然確定其與骨密度、骨骼肌肌力、肌肉質量及功能存在相關性。肌肉分泌因子如irisin、MSTN等以及肌骨界面間調控因子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和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FGF-2)等促使肌骨間信號串擾,形成調控肌肉質量與骨骼間分子網絡調控骨代謝平衡[5-7]。目前關于骨折風險預測模型的研究逐漸展開,然而這些肌骨代謝物是否能與骨折風險有關尚未見研究。因此,筆者就此探究絕經后女性人群肌骨代謝指標、BMI及BS與FRAX評估骨折風險間的關系,為后續優化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預測模型提供依據,以期為絕經后女性早期篩查及預防骨質疏松及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發生提供更經濟簡便的參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于江蘇省無錫市南京中醫藥大學無錫附屬醫院門診就診絕經性女性患者215例,受試者來源于無錫本地社區鄉鎮,年齡48~81歲,平均年齡為63.6歲。納入標準:自然絕經1年以上,絕經年齡45歲以上的健康婦女。排除標準:既往骨折病史、自身免疫性疾病、繼發性骨質疏松癥、甲狀腺相關病變、糖尿病、骨軟化癥、肝腎功能不全、腫瘤艾滋等影響生存的嚴重疾病、精神意識障礙、骨代謝異常病變及半年內服用過影響骨代謝藥物者。經篩查后共有184例絕經后女性符合參與研究,所有受試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且本研究通過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審查受理號:YKT2021032905)。
1.2 方法
1.2.1基線資料:由無錫市中醫醫院骨傷科醫生收集受試者身高、體重、既往骨折史、吸煙飲酒史、激素使用史、父母骨折史等,以用于進行計算BMI、BS及FRAX評分。BMI=體重(kg)/身高2(m2);體表面積(女)=0.007 3×身高(m)+0.012 7×體重(kg)-0.210 6。
1.2.2骨密度測定:由無錫市中醫醫院放射科醫生采用美國GE-LUNAR Prodigy公司的雙能X線骨密度儀(型號:YM0070330)檢查184例絕經后女性腰椎及股骨頸骨密度。
1.2.3肌骨代謝指標:由無錫市中醫醫院中心實驗室采用比色法測定鈣磷指標,固定時間法測定肌酐,酶動力法測定ALP,ELISA檢測P1NP、irisin、MSTN、IGF-1和FGF-2。
1.2.4骨折風險:采用FRAX評估骨折風險,數據經3人輸入核對,保證數據完整準確。登錄FRAX骨折風險評估軟件(https://www.sheffield.ac.uk/FRAX/),測評系統中采用Asia-china,輸入“股骨頸BMD”預測10年內骨質疏松性骨折發生的風險(the probability of major osteoporptic fracture,PMOF)及髖部骨折風險(probability of hip fracture,PHF)。根據文獻確定骨折風險干預閾值[8-9],依據干預閾值分為低風險組(PMOF<4 %)、高風險組(PMOF≥4 %或PHF≥1.3 %)。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統計軟件分析數據,符合正態性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極小值~極大值)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齡、骨量組間各指標差異及變化趨勢,若組間存在差異,進一步采用LSD法進行兩兩比較,t檢驗比較不同風險組間各指標差異;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線性分析肌骨代謝指標、BMI、BS與骨折風險之間的相關性。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骨折風險概率與相關變量間的關系。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
184例絕經后女性受試者中骨質疏松88例,骨量減少65例,正常骨量31例。全部受試者平均年齡(63.6±7.0)歲,平均BMI(23.30±2.76)kg/m2,平均BS(1.77±0.12)m2,平均股骨頸BMD(0.80±0.13)g/cm2,全身主要骨折FRAX及髖部骨折FRAX概率平均為6.07 %和2.69 %,見表1。

表1 患者的一般基線資料表
2.2 各肌骨代謝指標、BMI及BS間的差異分析
按年齡、骨量、骨折風險分組分析各肌骨代謝指標、BMI及BS間的差異。年齡組間BMD、PMOF及PHF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SCr在55歲年齡段以上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Ca在高年齡段與較低年齡組間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余指標之間差異不明顯(見表2);骨量組間BMI、BS、ALP、PMOF及PHF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SCr、Ca、P等肌骨代謝指標差異均未見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FRAX不同風險組年齡、BS、BMD、Ca、ALP、PINP、irisin及MSTN

表2 年齡分組間的各項指標比較

表3 骨量分組間的各項指標的比較
之間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BMI、SCr、P、IGF-1、FGF-2及鈣磷乘積差異未見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FRAX不同風險組間的各項指標的比較
2.3 FRAX骨折風險概率及BMD與各指標間的相關性分析
FRAX骨折概率與年齡、PINP、MSTN成正相關(P<0.05),與BMI、BS、BMD及irisin成負相關(P<0.05),BMD與年齡、BMI、BS、Ca、ALP、PINP、irisin及MSTN存在相關性(P<0.05),相關性絕對值由大到小分別為PMOF、PHF、年齡、BS、BMI、PINP、irisin、MSTN、ALP和Ca,本研究中FRAX骨折風險概率、BMD與SCr、P、IGF-1及FGF-2均未見明顯相關性。見表5。

表5 骨密度、骨折風險與各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2.4 FRAX骨折風險與肌骨代謝指標、BMI及BS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在排除骨密度對FRAX骨折概率的高度影響下,相關性分析顯示骨折風險與年齡、PINP、MSTN、BMI、BS及irisin相關,以此為自變量,以FRAX低風險或高風險作因變量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PINP與irisin仍在回歸方程,因此這3個變量可以被看作骨折風險的重要相關因素,見圖1。

圖1 骨折風險多因素Logistic分析
3 討論
骨質疏松癥已然成為全球嚴重影響中老年人群身心健康的重大衛生問題,其中女性人群發病率占70 %左右,因此絕經后女性需要格外關注自身骨質情況[10]。目前,大量研究證實肌肉減少與骨質疏松之間關系緊密,肌痿則骨廢,骨痿則肌弱。密切關注肌肉情況可能是早期有效預防及治療絕經后骨質疏松、降低骨折發生率的重要途徑,雖然相關研究也證明肌肉量、肌力和肌肉功能與MOF、HF呈負相關,是骨折發生的保護性因素,但臨床上全身肌肉含量較難得以評估和計算,因此通過肌骨代謝指標測定、體質指數及體表面積評估能有效針對肌肉因素對骨折風險的影響。現階段研究認為骨密度僅僅作為評價骨質疏松而并不能全部反映骨折風險以及作為預防骨折發生的金標準,因此,筆者通過納入蘇南地區絕經后女性人群,分析臨床肌骨代謝指標、體質指數及體表面積隨年齡、骨量、骨折風險間變化差異,及與骨折風險及骨密度間的相關性,探究除骨密度之外對骨折風險影響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選擇肌肉骨骼相關因素研究,常規指標包括體質指數、體表面積,二者粗略反映人群的營養狀態,不同的營養狀態對骨重建平衡的影響不同[11]。骨代謝指標主要涉及血鈣、血磷、鈣磷乘積、ALP及PINP,鈣磷作為無機成分,含量減少會致使骨骼脆弱,骨折易于發生,調節鈣磷平衡,將使骨鹽沉積與溶解速率正常,此外間接也反映出經濟較發達地區人群的營養狀況;ALP作為重要的骨代謝調節標志,一般認為在骨折后會出現相應變化;PINP是重要骨轉換標志物,可以反映體內骨形成的狀態,常被推薦用于骨松骨折風險的評估。肌肉相關指標涉及SCr、irisin、MSTN、IGF-1及FGF-2,研究表明血清肌酐與肌肉相關,能簡易估算肌肉含量;irisin于2012年由Bostrom研究發現,大量研究表明其對骨骼及多種骨細胞的影響,主要通過促成骨及抑制破骨細胞活性參與對骨骼的調控[6];MSTN是作為骨骼生長發育的負調節因子,Elkasrawy等[12]證明其直接作用于骨祖細胞的增殖分化,其拮抗劑可增加肌肉質量,增強骨強度;IGF-1和FGF-2定位于肌骨交界面,是通過肌肉與骨膜表面的旁分泌串擾實現肌骨間生化通訊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肌骨代謝情況[7]。目前國內外專家和指南均推薦FRAX評估工具作為骨折風險篩檢的方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FRAX風險評估工具在各國家應用時具有不同的評估及干預閾值,例如,美國將FRAX-MOF≥20 %或FRAX-HF≥3 %作為高低風險分級標準,英國將FRAX-MOF≥7 %作為干預治療的評定界限,也有存在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特定閾值不同[13-15]。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大樣本統計分析確立中國的FRAX-MOF≥4 %或FRAX-HF≥1.3 %作為高風險的干預閾值進行研究[8-9],為更好地研究該地區骨折風險的因素提供依據。
國內外文獻報道不同國家地區絕經后女性影響骨折風險的主要因素存在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絕經后女性FRAX不同風險組年齡、BS、BMD、Ca、ALP、PINP、irisin及MSTN間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BMI、SCr、P、IGF-1、FGF-2及鈣磷乘積差異未見統計學意義,并且FRAX骨折概率與年齡、BMI、BS、PINP、MSTN、irisin及BMD存在相關性(P<0.05),相關性絕對值除BMD外均在0.4以下,屬于輕度相關,但考慮到骨密度對PMOF及PHF的強相關與FRAX工具計算有關,予以排除后以FRAX低風險或高風險作因變量,相關因素做為協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初步結論示年齡、PINP與irisin 3個變量可以被看作骨折風險的重要相關因素,本研究反映出一些肌骨代謝指標可以作為骨折風險的可參考因素,有效為建立骨質疏松骨折風險預測模型提供依據。PINP作為臨床常見骨轉換標志物,反映骨形成能力強弱,多數研究表明PINP水平升高與骨折發生風險的增加相關,PINP作為獨立危險因素在骨折風險程度預測和骨量丟失率檢測中有較好的適用性[16-17],這與我們的研究相符。同時,本研究也證實陳巧聰等[18]有關肌肉質量、肌力等因素作為骨折風險評價因素的可靠性,肌肉含量減少、肌力下降等因素可能會增加骨折風險概率。因此,通過肌骨代謝指標測定可以通過定量評估驗證骨折風險程度高低,肌源性因子以及骨代謝指標在一定程度下能反映肌肉及骨骼的質量和功能。
雖然研究已證實年齡、irisin及PINP是骨折風險的可參考因素,但卻無法定義一個明確的骨折閾值來衡量,上述研究的FRAX干預閾值也只是通過文獻檢索最適合亞洲地區人群的,研究證實在FRAX-MOF≥4 %或FRAX-HF≥1.3 %時進行干預時取得的經濟學效應最大[19]。因此,我們仍需要通過進一步研究來確定符合該地區干預閾值來進行風險因素驗證,這是制定風險預測模型前的重要一步。因此對于本研究中與骨折風險因素有關但未能留在多因素回歸方程中的指標,如MSTN、BS、Ca及ALP,這些考慮到干預閾值選擇的差異影響,因此后續研究需要更多關注。此外,血磷及肌酐在本研究中變化不明顯,血清肌酐僅表現出隨年齡升高有上升趨勢,但在不同骨量組間卻未見顯著差異,因此通過肌酐評估肌肉含量可能性需要進一步確認,抑或通過尿肌酐水平評估更為可靠。血磷在絕經后女性人群中會因雌激素下降、生長激素增加而升高,而本研究中未見這種趨勢,可能與本地飲食習慣、營養程度相關,通過本研究顯示絕經后女性鈣磷乘積值基本上穩定在35~40 mg2/dL2之間,說明骨鹽沉積與骨鹽溶解均正常范圍內影響成骨作用,間接也反映出經濟較發達地區人群的營養狀況[20-22]。因此,影響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因素需要綜合考慮年齡、肌肉情況、營養以及疾病藥物等條件及自身閾值的選擇。
綜上所述,肌源性因子可以作為骨折風險考慮的可靠因素,骨骼與肌肉作為相互依存的統一體,以及現階段對肌骨單位復合體分子層面研究的深入,進一步證實增強肌肉健康、改善肌肉質量及肌源性因子分泌能降低骨折風險。因此在參考FRAX工具評估骨折風險的同時還可以選擇一些與肌肉有關的指標進行評估,這可以大大提高骨折風險的準確性。本研究受制樣本量偏小、FRAX干預閾值的靈敏度和特異性以及對肌骨代謝指標檢測的誤差,在此后研究中需要補足,進一步關注肌肉相關因素有助于更精確評估骨折風險,為后續優化骨折風險預測模型堅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