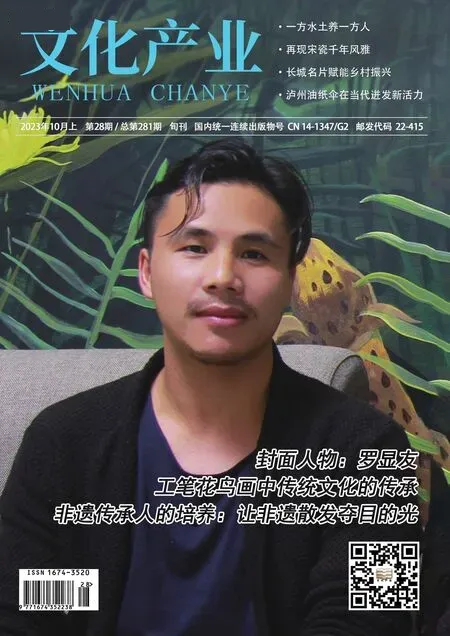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shè)導(dǎo)向下山東省沿黃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
◎陸 忱

我國學(xué)者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模式進(jìn)行了諸多探討。賈鴻雁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走向大眾這一問題切入,分析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靜態(tài)、活態(tài)、綜合、異地四種旅游開發(fā)模式,并由此提出法律制度等五種保護(hù)機(jī)制。雷蓉、胡北明通過對不同類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開發(fā)模式進(jìn)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旅游發(fā)展建議。田寶龍、喻曉玲使用TSP數(shù)學(xué)模型分析,對塔里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主題旅游線路方案進(jìn)行了規(guī)劃。章牧從文旅融合的視角,指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旅游中呈現(xiàn)出的原真性、可體驗(yàn)性、可持續(xù)性和不可模仿性等非物質(zhì)特性,從文化認(rèn)同與原真性、文化再生產(chǎn)、價值共創(chuàng)三方面提出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旅游中的活化路徑。李淥、李晨宇、徐珊珊基于貴州織金古城的實(shí)證,構(gòu)建文化記憶與文化空間關(guān)聯(lián)視角下古城非遺活化的框架,提出文化記憶、空間實(shí)踐、地方感共同構(gòu)成歷史城鎮(zhèn)非遺活化的多維動力。林琰、李惠芬在分析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價值的基礎(chǔ)上,指出非遺保護(hù)有著檔案式、被動式問題,應(yīng)建立動態(tài)化非遺考核評估機(jī)制。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活化利用展開了研究,他們的研究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更重視讓非遺“活起來”,從實(shí)際出發(fā)把非遺活化利用落到實(shí)處。由于非遺形態(tài)、類型多樣,隨著現(xiàn)代化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模式更具研究意義。
■研究背景
工業(yè)革命以來,全球經(jīng)濟(jì)迅猛發(fā)展,生態(tài)保護(hù)、環(huán)境承載力、文化遺產(chǎn)等問題隨之而來。“國家文化公園”是一個新概念,2017年,《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首次提出“規(guī)劃建設(shè)一批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文化重要標(biāo)識”;2019年,《長城、大運(yùn)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shè)方案》提出,建設(shè)長城、大運(yùn)河、長征三大國家文化公園;2020年,“十四五”規(guī)劃綱要中增加了建設(sh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內(nèi)容。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意義深遠(yuǎn)。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座談會上表示,要推進(jìn)黃河文化遺產(chǎn)的系統(tǒng)保護(hù),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chǎn),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yùn)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xù)歷史文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提出,要完善黃河流域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名錄體系,大力保護(hù)黃河流域戲曲、武術(shù)、民俗、傳統(tǒng)技藝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山東省把落實(shí)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國家戰(zhàn)略作為重大使命和重大機(jī)遇,也愈加重視對黃河流域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和利用。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shè)背景下,深入研究山東省沿黃地區(qū)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能夠保護(hù)和傳承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打造山東黃河文化品牌,深化區(qū)域聯(lián)動共建,加強(qiáng)山東省與其他沿黃省區(qū)文化、旅游、教育等領(lǐng)域的合作,搭建山東省與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文化交流平臺。
■山東省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況
黃河從菏澤市東明縣進(jìn)入山東,流經(jīng)菏澤、濟(jì)寧、泰安、聊城、濟(jì)南、德州、濱州、淄博、東營9市25個縣(市、區(qū)),在東營市的河口區(qū)入海。境內(nèi)河道全長628千米,流域面積1.83萬平方千米。
根據(jù)我國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2021年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名錄,選取山東省沿黃城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xiàng)目進(jìn)行類別梳理和地區(qū)梳理。當(dāng)前,山東省沿黃城市共有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126項(xiàng)(詳見下表,由于原萊蕪市于2019年劃入濟(jì)南,統(tǒng)計(jì)時,將原萊蕪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納入濟(jì)南市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占山東省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xiàng)目總數(shù)的68%。山東省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豐富,菏澤31項(xiàng)、濟(jì)寧19項(xiàng)、泰安12項(xiàng)、聊城12項(xiàng)、濟(jì)南20項(xiàng)、德州4項(xiàng)、濱州7項(xiàng)、淄博18項(xiàng)、東營3項(xiàng)。其中菏澤、濟(jì)南、濟(jì)寧、淄博市的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xiàng)目總量相對較多,德州市和東營市的較少。濟(jì)南的皮影戲、濱州的民間剪紙、菏澤的皮影戲和泰安的皮影戲列入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此外,山東省沿黃城市擁有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619項(xiàng),市級2491項(xiàng),縣級7015項(xiàng),分別占全省各級非遺項(xiàng)目總數(shù)的58%、60%、54%。由此可見,山東省沿黃9市的非遺資源十分豐富。

山東省沿黃城市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一覽表
■山東省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和利用存在的困境
文化遺產(chǎn)家底不清,缺乏代表性傳承人
許多非遺資源由于保護(hù)對象和保護(hù)范圍不明確,尚未形成成熟的非遺保護(hù)機(jī)制,導(dǎo)致部分?jǐn)?shù)據(jù)和信息缺失,非遺資源的調(diào)查和梳理工作缺乏系統(tǒng)性,目前仍需要對非遺項(xiàng)目進(jìn)行進(jìn)一步發(fā)掘和整理。部分傳統(tǒng)藝術(shù)如秧歌、山東梆子、魯西南鼓吹樂等生存空間小,即使在傳統(tǒng)節(jié)日也難以見到傳統(tǒng)藝術(shù)表演。一方面,人們追求新事物、科技產(chǎn)物,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喜愛程度降低;另一方面,傳統(tǒng)藝術(shù)傳承人漸少,甚至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困境。
保護(hù)理念和模式傳統(tǒng),非遺活化途徑和手段單一
現(xiàn)階段對沿黃地區(qū)非遺的保護(hù)利用主要集中在對非遺物質(zhì)載體的保存和外在形態(tài)的展示方面,保護(hù)方式仍以行政保護(hù)為主,通過文獻(xiàn)資料或?qū)嵨镄问綄⒎俏镔|(zhì)文化遺產(chǎn)保存在當(dāng)?shù)夭┪镳^、檔案館和文化館,對現(xiàn)代化技術(shù)運(yùn)用不足,數(shù)字化程度較低;利用手段單一,主要是博物館展示、非遺展演、旅游紀(jì)念品開發(fā)等,仍停留在靜態(tài)層面,產(chǎn)品同質(zhì)化現(xiàn)象嚴(yán)重,缺乏創(chuàng)新型產(chǎn)品,給大眾帶來的參與感、互動感和體驗(yàn)感不足。
非遺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率低,知名度較低
山東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豐富,但知名度較低。民間文學(xué)作品多以文字資料形式保存與陳列展示,缺乏知名度,部分家喻戶曉的故事如梁祝傳說、牛郎織女傳說、孟姜女傳說等以表演的形式在旅游景區(qū)內(nèi)進(jìn)行呈現(xiàn),但尚未形成品牌效應(yīng)。傳統(tǒng)民俗活動如燈會、廟會、書會、節(jié)日慶典等規(guī)模較小,影響力有限。傳統(tǒng)美術(shù)和傳統(tǒng)技藝主要以工藝品的形式呈現(xiàn),尚未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非遺文化認(rèn)同感不足,缺乏對當(dāng)代價值的挖掘和闡釋
黃河沿線特有的社會風(fēng)俗、生活方式、精神信仰都是寶貴的文化資源,但現(xiàn)階段對其精神內(nèi)涵缺乏深入研究和生動呈現(xiàn)。在非遺資源的開發(fā)過程中,尚未對其內(nèi)在價值進(jìn)行深度挖掘,且未提煉出具有地域獨(dú)特性的文化符號,缺乏對多種非遺及相關(guān)文化資源的組合配置與整合利用。
■山東省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路徑
立足于政策支持,充分發(fā)揮政府引領(lǐng)作用
依托當(dāng)前建設(sh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戰(zhàn)略,弘揚(yáng)山東沿黃地區(qū)非遺的精神內(nèi)涵,講好新時代“黃河山東故事”。繼續(xù)發(fā)揮政府的引導(dǎo)作用,深入挖掘沿黃地區(qū)非遺蘊(yùn)含的黃河文化的獨(dú)特基因,闡釋沿黃地區(qū)非遺的當(dāng)代價值,不斷豐富和更新非遺的文化內(nèi)涵,增強(qiáng)人們的文化認(rèn)同感。提煉出最具核心價值與地域特征的黃河文化符號,對相關(guān)文化資源進(jìn)行整合利用。從政府層面開展專項(xiàng)宣傳、營銷工作,實(shí)施融媒體精準(zhǔn)化、品牌化營銷策略,圍繞形象宣傳、主題活動、品牌拓展、區(qū)域合作和沿黃區(qū)域聯(lián)動開展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利用。此外,政府應(yīng)根據(jù)不同非遺項(xiàng)目的特點(diǎn),建設(sh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庫,建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搶救性調(diào)查及保護(hù)項(xiàng)目,有針對性地提供經(jīng)費(fèi)支持。
落實(shí)基礎(chǔ)工作,加強(qiáng)非遺傳承人才培養(yǎng)
完善沿黃地區(qū)非遺的保護(hù)、傳承與發(fā)展機(jī)制,摸清山東沿黃地區(qū)非遺家底,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山東特色的沿黃地區(qū)非遺保護(hù)體系。重視非遺傳承人培養(yǎng),既要培養(yǎng)技能型人才,也要培養(yǎng)能夠從事跨領(lǐng)域管理的復(fù)合型文旅人才,建立與學(xué)校、社區(qū)的聯(lián)動機(jī)制,基于校企合作模式培養(yǎng)非遺傳承人,嘗試以新型學(xué)徒制模式培養(yǎng)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師帶徒,傳技術(shù)”,共同打造大師工作室與非遺傳承工作室。同時,推動非遺進(jìn)校園,進(jìn)社區(qū),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jié)合的方式培養(yǎng)非遺傳承人。
轉(zhuǎn)變保護(hù)理念,構(gòu)建數(shù)字化保護(hù)體系
將非遺與數(shù)字技術(shù)、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相融合,利用數(shù)字技術(shù)創(chuàng)新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展示形式,運(yùn)用3D技術(shù)、VR技術(shù)、多媒體互動等展現(xiàn)黃河景象、黃河故事,增強(qiáng)觀眾的感官體驗(yàn),如聲音、氣味、觸感等,強(qiáng)調(diào)動靜結(jié)合,通過人機(jī)交互技術(shù)給觀眾帶來沉浸式體驗(yàn),保持真實(shí)性。建設(shè)非遺數(shù)字化展示平臺,建立動態(tài)的資源數(shù)據(jù)庫和現(xiàn)代化管理服務(wù)體系,將新媒體技術(shù)應(yīng)用于沿黃地區(qū)非遺保護(hù)、傳承中,更好地實(shí)現(xiàn)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活化利用。

創(chuàng)新特色項(xiàng)目,增強(qiáng)非遺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率
創(chuàng)新特色項(xiàng)目,加大非遺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力度,依托文旅融合、非遺創(chuàng)新、非遺營銷等方式,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與旅游、演藝、動漫、藝術(shù)設(shè)計(jì)等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相結(jié)合,打造智慧非遺體驗(yàn)館和購物空間,滿足當(dāng)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非遺文化資源轉(zhuǎn)化率和利用效率,提高非遺文化資源的經(jīng)濟(jì)效益。將沿黃地區(q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化與研學(xué)市場深度融合,結(jié)合周邊地區(qū)研學(xué)旅游受眾的特點(diǎn),設(shè)計(jì)、開展不同主題、不同深度的研學(xué)項(xiàng)目。同時加強(qiáng)與市場上各類開展研學(xué)活動的企業(yè)合作,如旅行社、酒店、文創(chuàng)園、工業(yè)基地等。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黃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著黃河文明的基因。基于當(dāng)前建設(shè)國家文化公園的戰(zhàn)略部署,山東省應(yīng)在不破壞非遺真實(shí)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對非遺資源進(jìn)行合理的開發(fā)利用,充分挖掘、利用其文化元素,從而釋放非遺活力,延續(xù)非遺的生命力。
——山東省濟(jì)寧市老年大學(xué)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