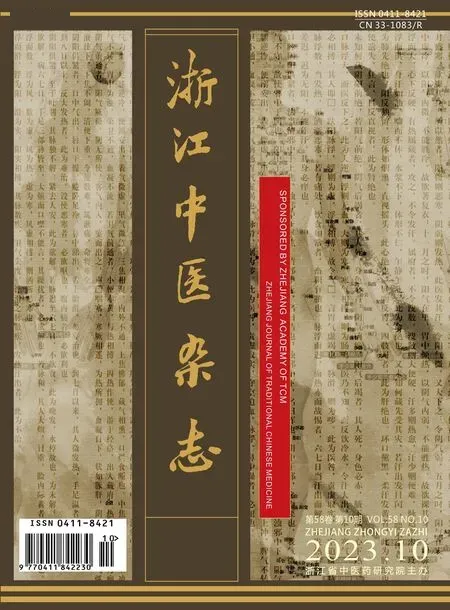基于“肝虛生風”探討單純舒張期高血壓中醫證治*
常銘熙 張 健 蘇金峰 李富震 張福利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脂肪供能占比的遞增,我國居民的肥胖率有顯著增長,多種慢性病也隨之早發、多發,高血壓多被視為是一種與肥胖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病”[1]。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為一種中青年群體多發的亞型,其診斷標準為收縮壓<140mmHg 和舒張壓≥90mmHg。不良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肥胖是誘發此病發生的高危因素[2],體質量指數(BMI)≥28 的人群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發病率較BMI<22人群增加3.13倍,其發病率在BMI較高時達至峰值[3]。
“高血壓”屬中醫學“肝風”“風眩”“頭痛”等范疇,其辨治多從“肝風內生”立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風之為病多為陽氣之異,“內風”多因肝木疏陽失和所致,故張錫純言“肝木失和,風自肝起”[4]299,“肝過盛生風,肝虛極亦可生風”[4]304。筆者結合古今相關文獻的研究及臨床實際效驗得出,單純舒張期高血壓屬“肝虛生風”,此病多因濕熱內積所致,進而“肝木委和,疏陽不及”,“眩暈、頭部昏沉、困倦、精神萎靡”等證候可歸咎為疏陽不及所引發的“虛風”。故本文從“肝虛生風”的角度對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的因機證治進行闡述,以求豐富此病的臨床辨治思路。
1 從氣化角度論“肝木”對“動脈血壓”的調控
張錫純于《醫學衷中參西錄》中首次闡明了中醫視角下的“動脈血壓”,張氏常從氣化觀解讀現代醫學中的生理、病理機制,開啟了衡氣機“升降”之常變以辨治高血壓的法門。雖然張氏并未對血壓的機制及生理意義作更詳解釋,但我們可循血壓高亢的因機來推敲臟腑氣化與血壓間的關聯,正所謂“反者道之動”。張氏根據“頭痛、眩暈、目脹耳鳴、脈弦長有力”等脈證表現,得出高血壓應屬“內中風(即西人所謂腦充血證)”,提出“脈弦長有力(即西醫所謂血壓過高)”等論[4]298。張氏所論的腦充血證實則包含現代醫學中的腦出血與高血壓,高血壓多為腦出血發生的前兆,因二者證機相從,故張氏統稱為“腦充血證”。張氏據“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提出高血壓的形成在于“肝木失和,風自肝起。又加以肺氣不降,腎氣不攝,沖氣胃氣又復上逆,于斯,臟腑之氣化皆上升太過”[4]299,參其所論“肝木失和,風自肝起”即為“高血壓”形成的關鍵,而臟腑氣機的升降逆亂皆以“肝風內動”為引。
肝木為陰體屬“厥陰”,張景岳于《類經》中進行解釋:“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5]厥陰為陰陽二者間的交界,其頗具陰極陽生之勢。厥陰當是調節陰陽轉化、出入的樞機,樞機的作用在于調節對立關系的平衡,故“初陽萌生”“陽從陰出”當決之于厥陰,這即為肝木“體陰而用陽”的本意。《素問·五常政大論》曰:“木德周行,陽舒陰布。”肝木“用陽”之意于此可更得詳論。肝、腎乙癸同源,二者皆從陰化,同為陰體,秘藏在腎中的生陽之氣(即生理之相火)舒展外用多由肝木司權,諸臟腑氣機的升降出入源于相火的推動,如《四圣心源》中言“風者,厥陰木氣之所化也……冬水閉藏,一得春風鼓動,陽從地起,生意乃萌”[6]21,故肝木的疏布作用調控著臟腑氣機的升降。肝木疏陽太過可使臟腑氣機逆升,肝木疏陽不及可使臟腑氣機下陷。張氏且言:“蓋血不自升,必隨氣而上升……蓋氣反而下行,血即隨之下行。”[4]300故“肝木失和”勢必導致諸臟腑氣機升降錯亂,血液流動也將隨之變化,血壓隨之波動,動脈血壓值處于正常值則為“肝木調和”“臟腑氣機沖和”的重要外在參證。
2 單純舒張期高血壓之因機著眼點——“濕熱久踞”所致的“肝木委和”
舒張壓的升高多因外周阻力增大所致,肥胖及糖脂代謝紊亂多為外周阻力增高的主要因素。外周阻力主要來源于血管壁彈性回縮和血液本身疊加的阻力,結合舒張壓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降低的規律,可看出舒張壓主要反映了血液本身引起的血流阻力,這與血容量及血液黏性密切相關。肥胖、久臥不動可導致皮下脂肪多、組織間隙水液潴留,進而擠壓外周血管導致血容量相對過多,長期嗜鹽及高脂高糖飲食引起黏稠度的增加導致血容量絕對過多[7]。朱丹溪于《格致余論》中提出“肥人濕多”[8],肥甘之品的攝入亦可引起濕熱的內聚,濕熱內積可為此病的源頭。
單純舒張期高血壓患病群體多超重、肥胖或合并糖、脂等代謝的異常,平素多為濕熱壅積且伴生陽不足之體,氣化功能處于低下狀態。張氏曾提出“肝過盛生風,肝虛極亦可生風”[4]304,肝木失和的虛實二分正符合《易經·系辭》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亢實過盛則為陽,委和虛餒則為陰,從“肝風”辨治高血壓當從虛實別論。“眩暈、頭部昏沉、困倦、精神萎靡”等證候,屬《靈樞·口問》所言“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此為“濕熱久踞,肝木委和”所引起的“虛風”。章虛谷言“濕土之氣,同類相召”,濕熱易襲中焦,在初始肝木可因濕熱困聚中焦而代償性亢旺,增加疏陽之功以助脾土運行,從而蒸逐濕熱轉散。隨著濕熱盤踞中焦日久,脾胃可漸失其樞轉之力,“肝木”也因濕郁久漬而疏布無力,漸久而現“委和”,失其代償。張氏提出“蓋人之元氣,根基于腎,萌芽于肝,培養于脾,積貯于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4]179,腎所藏相火可因濕熱困遏肝木而外疏不利,亦可因肝木前期代償性疏泄而虛耗,氣化功能可因生陽外疏不足而處于低下狀態。濕熱久踞墜積,肝木不得生發、疏散,生陽之氣不得暢運,胸中所積大氣漸則不足,周身氣機不得斡旋,臟腑氣機呈現出“清陽不升,濁陰不降”的虛陷狀態。因此,濕熱久踞為肝虛生風的驅使,肝虛生風為單純舒張期高血壓形成的關鍵。
3 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的治法——旁通于李東垣對“氣虛生風”的施治
張氏提出肝虛生風的施治立足于李東垣治“氣虛生風”之法,其曾言“東垣之論內中風,由于氣虛邪湊,原與腦充血者之中風無關,而實為腦貧血者之中風,開其治法也”[4]301,“腦貧血者之中風”正為生陽外疏不及的“虛風”。張氏提出“重用黃芪為主,而少佐以理氣之品”[4]397補肝氣之虛,也正是取法于東垣用“辛溫味薄”之風藥的補升肝木之法。《周易·系辭》中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旁通取法之意正是在于引前人之法,并結合實際情形而做相應地調整,故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的治法可循張氏之意,從李東垣所立之法及方藥探尋。
3.1 “氣虛生風”的施治立法及方藥應用:《脾胃論》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9]31,東垣所處時代及行醫環境下人們體質普遍薄弱,脾胃內傷多為“中氣虛耗,寒濕內積”。東垣生活于南宋偏安,金元戰亂時期,處于第“六十六”個甲子周期(公元1204~1263年),大司天為“太陽寒水”,大在泉為“太陰濕土”,此周期主“寒濕運”,基于運氣的影響脾胃內傷之機多偏于寒濕損及。從社會層面來看,戰亂之下民不聊生,百姓多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內外傷辨惑論》中描述了多數人病死之因,闡明了脾胃內傷的主要病機:“計受病之人,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中氣虛耗,飽食過甚引起食滯的內停,故寒濕內生而積。《醫學發明》言“故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過四旬,氣衰者多有此疾,狀歲之際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形盛氣衰如此”[9]188,故中氣虛耗為此虛風的基礎,寒濕內積是氣虛生風形成的關鍵,肝木因寒濕的內漬而無力疏陽外出,“氣虛生風”于此得成。
東垣多將“補升肝木、溫散寒濕、溫補中下二元”作為氣虛生風的治法,針對寒濕內積這一主要因素,其提出“諸風藥皆是風能勝濕也,及諸甘溫藥亦可”。多用“麻黃、桂枝、柴胡、葛根、羌活、防風”等辛散之風藥以破除寒濕對肝木的困侮,主以風藥補升肝木,如《素問·臟氣法時論》言:“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結合體質薄弱、脾胃虛寒這一特點,東垣常用“人參、白術、黃芪”等甘溫之品以培植中氣,復脾胃之氣耗,并多合以大辛大熱之附子、芳香溫燥之砂仁或辛溫益陽之益智仁以暖下元、復生陽。
3.2 “肝虛生風”的施治立法:《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言:“故此一時,彼一時,奈五運六氣有所更,世態居民有所變。”[10]單純舒張期高血壓患者的體質及脾胃內傷之機與東垣所處的時期大相徑庭。當今時代處于第七十九個甲子周期(公元1984~2043年),大司天為“厥陰風木”,大在泉為“少陽相火”,主“風火運”,病多偏于熱化,濕多合于熱,脾胃偏于“濕熱”所傷。時代更迭人民生活品質穩步提升,迥同于饑寒交迫的生活狀態。單純舒張期高血壓患者平素多靜少動、嗜食肥甘,故肥胖居多,體質多偏濕熱質,脾胃內傷之機多為“中氣壅滯,濕熱內積”。
《內外傷辨惑論》言“補之以辛甘溫熱之劑,及味之薄者,諸風藥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9]46,治療時故取風藥以培肝木、復委和。“肝虛生風”的脾胃內傷重在“濕熱久踞”,而“氣虛生風”的脾胃內傷重在“寒濕內積”,同為濕濁困侮肝木內耗里氣而成,但有寒熱偏向之不同。單純舒張期高血壓的治法可旁通于“氣虛生風”的治法,主以風藥補升肝木,并合以“清消濕熱、培復生陽”的復合治法以調復氣化治療此病。
3.3 “肝虛生風”方藥應用:治療單純舒張期高血壓,可以補中益氣湯、李氏清暑益氣湯及其類方為基礎進行加減。可選“柴胡、升麻、葛根、白芷”等具備辛散升提的風藥補升肝木,以破土濕之困而升散,可除因“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的虛風之候。同時還當取“黃芪、太子參”等益氣之品,以補太陰之脾氣進而助肝木之升,即黃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所言“太陰主升,己土升則癸水與乙木皆升”[6]25。此外,“桔梗、杏仁”之宣氣化濕之品可更助肝木升散。
除用以上諸藥助肝木舒展,臨床中還須多藥相合以使得氣機升降有序,進而氣化得以調復。如取“竹茹、茵陳”之性輕宣散之品,既可除痰濕郁熱,又可合風藥升散之性以培植肝木;取“山梔、黃連”之苦清之品,既可內消濕熱,又可防風藥過燥生熱;取“黃柏、澤瀉”相伍以清泄中下焦間郁積之濕熱;取“白芍、麥冬、生地”等養營涼血之品,既可防風藥辛燥太過而傷及陰血,又可起斂降之功而防肝木過升;取“生姜、陳皮、茯神、甘草、白術”健運中氣之品可除脾胃濕積,同時“陳皮、生姜”的辛散之性可助風藥上行;取“桑寄生、杜仲、砂仁、益智仁”等溫陽化濕之品,既可除中下二焦久積之濕,還可充暖腎中所藏“生陽”,如《四圣心源》中言“肝木即腎水之溫升者也”[6]4,故腎水得溫、肝木得升。人身氣機當以回環為序,若諸藥皆以升散、外疏為主,一則有內耗腎元之弊,再則可引起氣化失和,故配以“龍骨、牡蠣”等斂降之品,既可壯腎強下,又可引氣歸元,合諸風藥并行,使得氣機回環有序。通過上述治法及諸藥的并用,可復肝木于和、氣化得以沖和,調復舒張壓至正常值。
4 結語
中醫學注重對形而上理念及方法導向的研究,正如《易經·系辭》中所言“形而上謂之道”,這其中所言之“道”正為“自然而然”的運行法則,中醫學對人體的認識多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出發。《中藏經·人法于天地論》曰“天地順則人氣泰,天地逆則人氣否”,從運氣的變化規律以探求人體氣機的變化情況為中醫學認識人體生理及病理機制的重要蹊徑。中醫學多認為血流動力源于人體氣機的推動,血壓的變化與人體氣機的升降運動密切相關,而這其中肝木的疏陽運升之功調控著諸臟腑氣機的運動之勢,血壓則應肝木的調節而隨氣機的變化波動。張載云“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蕩、勝負、屈伸之始”[11],故“肝木亢實,升之太過”可為失和,“肝木委和,升之不及”亦為失和,而通過方藥的施治以“升其不升”“降其不降”正為求肝木于“和”的方法。“風藥”在此病中的應用及對“氣虛生風”治法上的旁通皆為中醫學重視以“沖和”為要的體現,氣血沖和則百病不生[12],這是中醫學調節機體內穩態的重要思維方式。從“肝虛生風”論治單純舒張期高血壓正是求機體于“和”的重要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