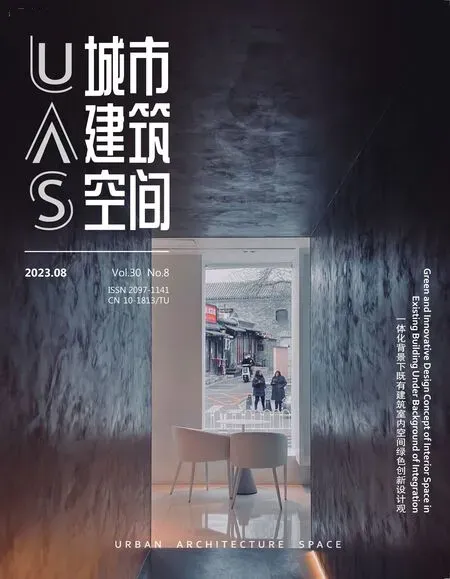佛羅倫薩城市精神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傳承與延續*
彭諶 楊霞
1 佛羅倫薩的城市精神
每座擁有悠久歷史的城市都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氣質,這種氣質體現在城市風貌和形態上,也體現在居民的共同性格特征上。城市氣質是一種外在的表達,而城市精神則是內涵。追溯城市歷史,總能從歷史脈絡中找到城市精神形成的原因。
1.1 佛羅倫薩人的性格
1)對自由的崇尚 獅子是15世紀佛羅倫薩的標志,象征著自由。如市中心維奇奧宮門口的“紋章獅子”復制品,由文藝復興早期的雕塑大師多納泰羅創作,其原作收藏在巴杰羅美術館中。獅子被雕刻得威猛雄壯,表現出威嚴的儀態和貴族的氣質,手持百合花徽章。佛羅倫薩人崇尚自由還體現在政治上追求獨立與共和自治。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由于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逐漸強大繼而建立了共和國。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而貴族則被排除在權力之外。同時建立了官員任期制和選舉制,使民眾關心政治生活,關心來之不易的“自由”。
2)對藝術的包容 佛羅倫薩地處意大利中部,財富大部分來自與許多地區的國際貿易,由此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同時作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在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下,這里培養和吸引了大量藝術家,留下了數不勝數的經典傳世之作。一座城市對藝術的接納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能夠反映這座城市的包容度。佛羅倫薩和這里的人民以高度的包容接受藝術家們在這里“創作”。在人文主義浪潮的推動下,藝術家們也對這樣的包容進行了“回饋”,無論是樸實大方的建筑設計作品,還是以人為中心、弘揚人性的繪畫雕塑作品,藝術都更貼近現實,一反文藝復興前的“神性”創作,激發了人們的審美意識,促進了整個城市對美的追求。
3)對美感的追求 “為了推動教育發展和文化傳播,佛羅倫薩對才學之士采取獎勵機制,最顯赫的是授予其政府官職、大學教職或擔當藝術工程”[1]。由此可見,藝術相關從業人員的地位與政府官員、大學教師不相上下,受到全社會的尊重。人們信任“才學之士”,也從側面反映了佛羅倫薩人對美感的追求。著名雕塑《大衛》反映了佛羅倫薩人對美的執著。如此一尊有諸多創新且標新立異的藝術作品,被佛羅倫薩人以獨到的眼光選中,作為城市的精神象征最初放置于市中心維奇奧宮的門口,其后為更好保存,才移入佛羅倫薩學院美術館室內展廳。
自由、包容、尚美是佛羅倫薩人性格的關鍵詞。這樣的性格特征在文藝復興時期扎根,經歷數百年的歷史變遷,一直延續至今,雖被現代化城市的節奏和喧囂所掩蓋,但如果在城市中漫步體味,仍能從點滴之中感受到其對城市的種種影響。
1.2 人文主義對佛羅倫薩的影響
人文主義的核心是高度重視人和人的價值,以人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張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人權取代神權,以自由平等取代特權和等級制度,崇尚理性,提倡科學,重視古典知識與學術[2]。這種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個性與精神的思想,成為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思想淵源,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城市各個領域得到發展,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人們的風俗習慣也發生變化,世俗生活變得文明化,藝術表現變得現實化,婚姻生活和宗教生活變得世俗化,每個城市居民似乎都在特定的領域找到了某種“主人意識”,對生活充滿希望和目標,使整個城市充滿活力,對外來文化和思想也充滿包容。
2 城市公共空間發展趨勢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關注效率和功能性的居民聚集地——城市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而城市公共空間作為緩解這些問題的場所被眾多城市規劃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注。城市公共空間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同時展示和傳承城市精神。
城市公共空間是城市中人們進行功能性或儀式性活動的共同場所,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周期性節日中,其使人們聯合成社會[3]。關于公共空間營造的思想和做法,一直以來存在兩種觀念,一種是“創造形象”,一種是“創造場所”[4]。“創造形象”是將空間的視覺因素置于支配地位,而忽視社會、文化、經濟等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空間有一定歷史后會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觀賞和旅游價值。后期,西方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的主流觀念逐漸從“創造形象”轉移到“創造場所”,核心思想是“服務社會和人”,關注人對空間的需求。在當今信息時代和商品社會,世界主流思想和文化有大融合的趨勢,世俗生活越來越碎片化和現實化,人們越來越關注實實在在的社會需求。城市公共空間的發展也有逐漸從城市形象塑造領域脫離的趨勢,更加關注人的需求、本土文化和城市精神,城市公共空間的營造更加關注“公共”二字。
3 在城市公共空間中傳承與延續的佛羅倫薩城市精神
3.1 融入現代生活的歷史街區
佛羅倫薩的歷史街區風貌成型于文藝復興時期,有些古老的建筑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4—5世紀,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直至今日仍然基本保留著最初的紅屋頂碉樓樣式,城里隨處可見雕塑古跡、石砌雕刻。1982年,佛羅倫薩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那些耳熟能詳的著名歷史建筑,一部分是宗教類建筑被完整保留,建筑功能都未曾改變,如圣母百花大教堂等。另外一部分,如皮蒂宮等,則由私人空間轉變而來,由家族捐贈,開放后成為博物館。這些久負盛名的歷史建筑在佛羅倫薩城里不會給人帶來太過壓抑的感覺,恰恰相反,建筑不設圍欄圈地,門前的道路就是城市交通道路,人們每天的生活與歷史的遺存完美融合在一起,毫無違和感。美第奇宮高聳的建筑外墻上,砌筑了長長的石椅(見圖1),最初是美第奇家族專門為城內平民設置的休息之地,經過數百年,無論市民還是游客,依然在此休息,這里成為城市公共空間,并且傳承了人文主義精神,沒有任何外力干預,自然而然地延續了下來。

1 美第奇宮建筑外墻上的石椅
如果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來看待佛羅倫薩,這里也許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整個歷史街區道路狹窄,為適應現代人的交通需求,佛羅倫薩人發揚科學理性的人文主義精神,通過劃定機動交通限制區、單向交通組織、街道步行化改造、打造旅游小巴系統等策略來緩解[5]。但是人車混流,部分狹窄的路段人行道只有40~50cm寬,車輛飛馳而過時,行人需要側身才能確保不被汽車的后視鏡剮蹭。但佛羅倫薩人似乎十分接受這樣的狀況,并沒有因此而抱怨,對佛羅倫薩人來說,保留城市歷史的美勝過便利的生活。但佛羅倫薩也不是一個失敗的規劃案例,在人們易于聚集的公共建筑門前,往往留有大面積的開敞空間。幾百年間,無論廣場鋪裝和設施如何更替,這里總是承擔著同樣的城市功能:不同種族、性別、年齡的人在此聚集停留,或休息或玩賞,或交談或靜默。陌生人之間友善和睦,偶爾聊聊天氣與眼前著名建筑的美。在這里,自由、包容、尚美的人文主義城市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3.2 延續城市精神的當代藝術
佛羅倫薩有著璀璨的歷史文化,有始建于14世紀的世界第一所美術學院——佛羅倫薩美術學院。但從現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三面環山,可利用的平坦土地面積不大,也非港口城市,并沒有天然的優勢。但佛羅倫薩商業高度專業化,珠寶行業享譽世界,旅游業更是為其不斷注入新鮮血液。在城市邊界無法大面積擴張的前提下,仍保持著活力。不發達的交通讓佛羅倫薩歷史街區被完好保存下來,人們也自得其樂地享受著這片天地。
佛羅倫薩是藝術之都,不僅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氣質,同樣因為這里的人們熱愛藝術,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前來定居或尋找靈感。佛羅倫薩人對藝術家們秉持了一貫的包容態度,街頭藝術家Clet Abraham在這里留下的作品便很好說明了佛羅倫薩城市精神得以延續。
Clet Abraham生于法國,后移居到佛羅倫薩。定居期間,在城市中陸續展開“創作”。用調侃的方式“裝飾”了一個又一個歷史街區中的交通指示牌(見圖2),每一處都能讓人駐足品味,體現了無窮的生命力和可能性。Clet Abraham并不是替換整塊交通牌,而是在原來的牌子的基礎上貼一張貼紙,可方便撕下恢復原貌。而佛羅倫薩政府部門和市民包容上述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還樂在其中,就如同文藝復興時期一樣,被人文精神和包容性原汁原味傳承了下來。

2 Clet Abraham“裝飾”的交通指示牌
佛羅倫薩歷史街區公共空間稀缺,更沒有多余空間去建設城市綠化,但街道上隨處可見各種藝術家們留下的作品,從知名的到無名的,從繪畫到現代藝術,城市以極大的包容性保留上述作品,使其軟化各個碎片化的公共空間,讓藝術灑滿每個角落,讓公共空間煥發生命力,讓佛羅倫薩延續百年前的城市精神。
4 結語
城市存在的最基本內容是人的活動,人活動的集中場所是公共空間,公共空間離開了人的使用,將變得無意義,其功能應滿足使用者的需求,而其內涵應傳承和延續城市精神——一種烙印在城市和市民血液中的不滅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