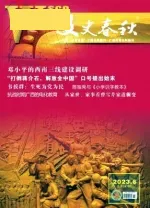漫談“師爺”
李學樸
師爺,是舊時對幕友的尊稱,指受各級官吏聘請幫助處理政務的人。清徐珂《清稗類鈔》說:“仆人稱官員為老爺,稱幕友為師爺。”師爺一詞的稱呼,始于清代,從事此業者多為浙江紹興人。
古代師爺的職責,主要在于協助判案、管理錢糧、起草文書、整理檔案等。與此相應,師爺也分為五大類:刑名、錢谷、掛號、征比、書記。在州縣以刑名、錢谷二者責任最為重大,地位也較其他師爺為尊。延幕入席,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時的幕府,到清代,更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幕友制度。
師爺一行,多與文書案牘打交道,只有讀書人才能勝任這一職業。終清一代,師爺的名聲并不太好。有人曾以“紹”字作諷刺:“搞來搞去,終是小人,一張苦嘴,一把筆刀。”因此,在清朝前期,一般士子是恥于從事此業的。汪輝祖就談到其父曾依人幕下,但不到兩年便辭職回家,原因即在“懼損吾德也”。汪輝祖本人欲習幕時,其母和其祖母還極力阻攔。到晚清,這種以習幕為恥的觀念有了相當的轉變。許多士子潛心于習幕之道,燕集于權臣之家。曾國藩幕中曾有“=圣七賢之目”,幕府人才,一時稱盛。
中國人安土重遷,但師爺卻是特殊的一群。由于他們不屬于國家官僚系統,沒有俸祿,其收入主要來源是主人定期奉送的東倏(亦稱館谷),這就決定了他們寄人籬下的生涯。雖然清政府官員有遷任或離任,幕僚無需變更之規定,但許多幕友,特別是與本官交誼匪淺的,往往都愿意隨本官遷移;如遇官員離任,有的也會另謀出路。對于師爺來說,四處漂泊、居無定所便成尋常之事。
師爺們游幕日方,多有失館不如意者,有的競至客死他鄉。龔未齋說:“宦游異地,最凄涼兩袖清風;客死他鄉,最悲慘一棺暴露。”因此,蕭山師爺何慶成游幕保定頗有資財時,就首倡浙紹會館,以便落魄的紹興師爺有個落腳之地。還有各種同鄉會、公會等,其作用是聯絡鄉誼,互相照應。但這些會館、幫會總是逆旅客途,終非故鄉,“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回鄉是師爺們時刻縈繞在心頭的愿望。
師爺這個龐大的社會集團,其地位也有上中下之分。一些督撫倚重的幕僚,在決定軍政大事時往往比該省的司道大員所起的作用還大,以至于“名滿天下”。有些士子把游幕當作入仕前的熱身練習,而多數州縣官員的師爺是終生以此為業的。大多數師爺走上習幕一途,還是出于生計的壓迫。汪輝祖在《佐治藥言》中說:對于未進舉的讀書人來說,最經常的職業,不外乎教書和游幕兩種,而“寒士課徒者,數月之倏,少止數金,多亦不過數十金”。相比起來,做師爺就好得多。
入幕得勢的師爺往往成為營利之徒,甚至聲色犬馬,飲酒狎妓。萬維翰在其《幕學舉要》就感嘆過:“幕中之流品,最為錯雜,有宦轍覆車,借人酒杯,自澆塊壘;有貴胄飄零,摒擋紈绔入幕效顰;又有以鐵硯難靡,青氈冷淡,變業謀生……”
既然師爺群體成分復雜,品行不端者就在所難免。當然,并不是所有師爺都是貪財好利之輩,其中也有不少正直之士。如師爺中講究“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原則,便是對官場黑暗、官吏腐敗的一種抗議。魯迅也曾說過:“我們紹興師爺箱子里總放著回家的盤纏。”這大概也反映了師爺的一種氣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