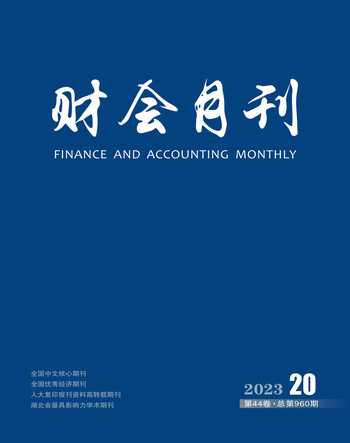新《證券法》下投服中心持股行權與中小投資者保護
馬德水 李雪晴 靳芷昕



【摘要】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一直是我國資本市場制度建設的核心。本文以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為例, 分析新《證券法》實施背景下投服中心在特別代表人訴訟中作用發揮的機理及溢出效應。研究發現: 投服中心參與特別代表人訴訟改善了個人投資者提起訴訟的不足, 主要體現為相關材料和證據搜集的便捷性、 受害者人數以及損失金額計算的快捷性、 參加庭審團隊的專業性; 投服中心具有“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性質, 通過發揮持股行權職能, 在形成對公司經營治理活動軟監管的同時強化投資者保護; 投服中心參與特別代表人訴訟能夠激發中小投資者行權維權的積極性, 推動股東積極主義興起, 促進資本市場法治化建設。
【關鍵詞】《證券法》;投服中心;中小投資者保護;特別代表人訴訟;康美藥業
【中圖分類號】F830.91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20-0118-8
一、 引言
加強投資者權益保護, 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一直是各國資本市場建設的焦點問題, 也是金融市場繁榮和企業發展的根本。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程較短, 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仍以“小散”為主。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者統計數據顯示, 2022年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數量突破2億, 自然人投資者占99.76%, 非自然人投資者僅占0.24%, 中小投資者無疑是我國證券市場的主力軍。中小投資者作為我國證券市場主要參與者, 由于信息獲取和自我保護能力不足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 其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此外, 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逐漸呈現涉案金額及舞弊程度加大、 舞弊手段愈發隱蔽、 舞弊的“謀利”性動機愈發明顯、 “看門人”失職等特點(劉啟亮等,2023)。繼2019年康美藥業、 康得新、 新城控股、 獐子島、 昊華能源等財務造假事件之后, 2021年再現巨額財務造假, 永煤控股虛增貨幣資金近900億元。“黑天鵝”事件頻發造成上市公司股價劇烈波動, 給中小投資者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嚴重危及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可見, 在“新興+轉軌”的制度背景下探索健全完善中小投資者保護機制尤為重要。
針對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 究竟是采取公共實施機制還是私人實施機制一直是爭議的焦點。前者實施主體為政府代理人, 后者則依靠市場機制執行《證券法》。在實踐中, 美國等成熟資本市場是以股東訴訟和股東參與投票等依靠市場力量的私人實施機制為主, 新興資本市場多以通過政府代理人揭露并懲罰違法者的公共實施機制為主(陳運森等,2021)。考慮到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和特點, 我國采用以中國證監會行政監管為主的公共實施機制。2013年以來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逐漸興起, 我國私人實施機制尚處于發展階段, 上市公司訴訟仲裁案件數量隨之不斷增加。但是, 資本市場頻發的“黑天鵝”事件表明, 我國公共實施機制的處罰力度太小, 監管覆蓋面太窄, 而私人實施機制的推進效果也不容樂觀, 公共實施機制和私人實施機制的效率亟待進一步提升(陳運森等,2019)。2014年12月5日, 由中國證監會批準設立和直接管理的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投服中心”)成立。投服中心作為投資者保護公益組織, 其行權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力量發揮作用, 具有政府彈性監管的色彩,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辛宇等,2020;陳運森等,2021)。這一創新性的監管模式對中小投資者權益的保護效果有待理論與實踐檢驗, 而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作為新《證券法》實施后首例集體訴訟案, 為檢驗投服中心在中小投資者保護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場景。
建設法治化國家, 需要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2021年3月1日起新修訂的《證券法》(簡稱“新《證券法》”)正式實施, 其中變化最大、 影響最大的內容, 均圍繞投資者保護展開。新《證券法》回應市場的呼聲, 制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制度——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 并確立了“默示加入、 明示退出”代表人訴訟原則。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標志著我國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正式拉開帷幕, 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模式開辟了中小投資者維權的新渠道。本文基于新《證券法》實施的制度背景, 以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為例, 研究投服中心持股行權對中小投資者保護的作用機理及其所產生的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 可為加強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 彌補證券民事賠償救濟乏力的基礎制度短板, 改善資本市場生態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提供啟示。
二、 文獻綜述
(一)中小投資者保護問題的產生
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問題源于委托代理問題。兩權分離引發了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代理問題(Jensen和Meckling,1976)。隨著股權集中度的提升, 特別是在大型上市公司, 控股股東利用自身控制權攫取公司資源, 侵害中小股東利益, 引發了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Chen等,2013)。代理沖突在新興市場中廣泛存在, 特別是在投資者保護薄弱的國家(Athari, 2022)。東亞新興資本市場上多為家族控制企業, 家族成員在企業管理和治理層面占主導地位, 控股股東現金流權和控制權的嚴重分離, 加劇了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的代理沖突(Wang等,2021)。我國股票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 同樣面臨法律和治理框架薄弱、 股權高度集中、 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引發的代理問題(Firth等,2019)。
股東積極主義是投資者應對代理沖突與利益侵害、 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一種自救機制(辛宇等,2020)。股東積極主義始于個人投資者, 隨著資本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增多, 20世紀80年代在美英等國逐漸興起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浪潮, 即機構股東積極主義(伊志宏和李艷麗, 2013)。在發展中國家, 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的增加以及地位的提升, 繼續“用腳投票”無法增加自身利益, 因此, 機構投資者不得不積極參與公司經營(Buchanan等,2012)。機構股東積極主義行為能夠對企業形成有效監督(Kang等,2018), 并加強對中小投資者權益的保護(Solomon,2017)。由于我國中小股東持股比例偏低, 無法對股東大會中決策過程和結果產生重大影響(Solomon,2017), 以及普遍存在中小股東行權收益難以彌補過高的行權成本的現象, 導致股東積極主義在我國未能興起。
(二)中小投資者在股東訴訟中面臨的困境
股東訴訟制度是投資者權益保護不可或缺的司法機制。股東訴訟對管理者形成直接約束作用的同時間接影響公司治理(Bourveau等,2018)。在其他治理機制失效時, 通過股東訴訟能夠有效約束管理層的過度投資、 外部融資行為, 提高公司治理質量(Chung等,2020)。但在實踐中, 股東訴訟制度仍存在法律針對相關事項規定不具體、 立法司法缺乏靈活性(劉詩瑤,2018)、 上市公司拒絕直接向證監會提供審計文件和相關證據資料(Feng和Fuerman,2019)等問題, 這些問題導致股東訴訟制度不能有效實施。另外, 股東訴訟的提起需要承擔一定費用, 包括法院收取的訴訟費和律師費(耿利航,2013)。當前大部分國家實行“敗訴方”承擔費用的原則, 個人投資者提起訴訟時就需權衡預期收益與成本, 當訴訟收益難以彌補訴訟成本時, 個人投資者就會放棄起訴, 由此造成個人投資者訴訟動力不足、 對侵權人威懾力不足以及“集體行動困境”等實踐難題。
在實踐中, 不同國家和地區探索通過不同途徑化解股東訴訟中的“集體行動困境”。美國制定了“聲明退出”規則和“勝訴酬金”制度, 中國臺灣地區則建立了以非營利部門為主導的證券訴訟模式(薛永慧,2016)。由于我國中小股東素有“厭訴”心理, 并且中小股東在訴訟過程面臨較多障礙, 即便提起訴訟也面臨訴訟成本高、 審理效率低等問題(劉裕輝和沈梁軍,2017), 由此導致我國中小投資者發起訴訟率較低, “集體行動困境”未能有效解決。
(三)投資者保護公益組織在股東訴訟中的作用
法律的威懾及懲罰力度不足、 投資者權益保護機制不完善是導致資本市場造假欺詐等惡性違法行為層出不窮的重要因素。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是懲治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 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有效機制(Hopkins,2018)。鑒于法律制度體系、 文化環境等宏觀因素, 以及中小投資者“集體行動困境”和訴訟程序的阻礙, 東亞地區形成了一種以非營利組織為主導的訴訟模式。在證券集體訴訟中, 機構投資者相比個人投資者通常具有更有力的訴訟支持、 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及更高的公眾知名度, 機構投資者擔任主要原告能夠提高集體訴訟的成功率(Cheng等,2010)。經過多年探索, 我國于2014年由中 國證監會正式批準設立投服中心, 其可以作為股東廣泛發起公益性股東代表訴訟, 并通過參加股東大會、 上市公司重組說明會、 網上行權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 同時借助專業公益律師團隊為中小投資者提供法律援助、 化解糾紛, 以及作為訴訟代理人對涉嫌違法的上市公司提起訴訟(郭靂,2019)。投服中心的行政監管背景及行權手段能產生較強的監管效應(任鶴和顏逢,2022), 迫使企業規范經營行為和信息披露行為(湯旭東等,2023), 通過對大股東的威懾和約束作用以及對中小股東的示范引領, 有效抑制上市公司違規行為(周卉和譚躍,2023)。
三、 制度背景與案例引入
(一)制度背景
1. 新《證券法》中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我國早期對于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不主張采用集體訴訟的形式, 且法律規定投資者及其代表需承擔舉證責任, 判決結果采取“登記生效”方式, 降低了投資者勝訴率(胡明霞,2021)。而國外集體訴訟制度已被運用多年, 目前集體訴訟的方式主要有以美國為代表的“退出制”集體訴訟制度、 以英國為代表的“加入制”集體訴訟制度, 以及以德國為代表的團體訴訟制度等(王琳,2019)。我國證券虛假陳述案件頻發, 導致中小投資者權益嚴重受損是推動我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是基于我國國情以及證券資本市場情況, 借鑒吸收西方主流集體訴訟制度發展而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制度, 適用于證券市場中因虛假陳述、 操縱市場、 內幕交易等證券欺詐行為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案件。新《證券法》第95條第3款規定: “投資者保護機構受五十名以上投資者委托, 可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 并為經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確認的權利人依照前款規定向人民法院登記, 但投資者明確表示不愿意參加該訴訟的除外。”并且設立“默示加入、 明示退出”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涵蓋受損失投資者, 可產生“聚沙成塔”的賠償效應。
特別代表人訴訟與普通代表人訴訟同屬代表人訴訟, 但兩者的起訴主體和制度模式不同。在起訴主體方面, 普通代表人訴訟由受損失投資者提起訴訟, 而特別代表人訴訟是投資者保護機構在接受受損失投資者委托后, 作為代表人提起訴訟。在制度模式方面, 普通代表人訴訟為“加入制”, 而特別代表人訴訟為“退出制”(Wan等,2019)。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以投資者保護機構為主導, 以投資者權益保護為核心。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啟動程序大致可以分為三步: 滿足普通代表人訴訟相關條件→投服中心內部決策→權利人的特別授權(郭文旭,2021)。
2. 投服中心性質與持股行權機制。投服中心體現了我國“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的特色。投服中心作為中國證監會直接管理的非營利組織, 官方背景是公共實施機制特性的一個重要體現, 證券監管機構可以通過公共實施機制為投資者獲取補償(Wan等,2019)。而通過搜集整合上市公司相關資料、 梳理中小投資者反饋事項、 積極關注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 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公司提出質詢和建議(陳運森等, 2021)等職能, 則是私人實施機制的體現。持股行權是投服中心發揮投資者保護職能的重要機制, 可以有效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股東身份參與公司治理的引領示范作用、 訴訟維權以及監督上市公司治理三個方面。投服中心通過加強中小投資者教育、 提供訴訟維權服務等手段, 有效彌補中小投資者因專業知識和能力不足而導致權益受損的缺陷。
(二)案例引入
2018年10月15日, 網絡上出現一篇自媒體發布的文章質疑康美藥業財務造假。至此, 康美藥業存貸雙高、 大股東股票質押比例過高等問題引發強烈的市場反應。2018年10月16日, 康美藥業股價閃崩, “康美藥業”搜索量急劇上升。2018年12月底, 中國證監會正式介入調查。2019年4月29日, 康美藥業發布《關于前期會計差錯更正的公告》, 對2017年財務報告作出重大調整。2019年5月17日, 中國證監會發布公告, 證實康美藥業2016 ~ 2018年重大財務造假屬實。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康美藥業之所以實施財務造假, 從舞弊三角理論分析其動因主要有: ①沉重的債務壓力和企業盲目擴張導致凈利潤大幅縮水帶來的退市風險。②股權高度集中、 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失職、 法律對企業財務造假處罰力度不足為其財務造假提供機會。③面對外界質疑, 馬興田聲稱是由于公司發展過快, 加之內部控制和財務管理機制不健全導致的會計差錯并非財務造假, 將借口自我合理化。
2020年12月31日, 黃梅香等11名康美藥業案受害投資者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簡稱“廣州中院”)提起普通代表人訴訟。2021年2月10日, 廣州中院經審查決定適用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2021年3月1日, 新《證券法》正式實施, 同年3月26日廣州中院發布康美藥業案普通代表人訴訟權利登記公告, 投服中心公開接受投資者委托。2021年4月8日, 在完成相關材料審核后, 投服中心向廣州中院提交56名投資者提供的證據材料, 并申請轉換為特別代表人訴訟, 同年4月16日廣州中院正式發布特別代表人訴訟權利登記公告。2021年11月12日廣州中院對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作出一審判決。
四、 投服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 基于訴訟效率與訴訟效果的視角
從立案時間、 審理時長、 判決時間等訴訟時點來看, 早期的虛假陳述案大部分存在訴訟時間過長、 效率低下的問題。隨著新《證券法》的實施特別是投服中心的加入, 上述問題均得到有效改善。此部分將運用案例分析法重點分析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 并通過與湖南爾康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爾康制藥”)證券支持訴訟案對比, 基于訴訟效率和效果視角研究新《證券法》下投服中心持股行權機制在中小投資者保護中的作用發揮機理。
(一)賠償責任主體的認定
以往證券虛假陳述案的原告通常將起訴對象鎖定為上市公司, 但上市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行為往往是在實際控制人授意和控制下進行的。伴隨著案件審理時間的推移, 上市公司可能會因為經營困境而不能承擔相應的賠償金額, 僅將賠償責任主體范圍鎖定在上市公司過于狹隘, 并不能真正實現對投資者的賠償, 如表1所示。因此, 新《證券法》針對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訴訟案件中的賠償責任主體范圍進行了調整, 除了發行人的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 董監高等人員, 范圍擴大至保薦人、 承銷的證券公司、 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專業證券服務機構。
鑒于中小投資者薄弱的法律知識, 其在實際提起訴訟時未必能夠厘清賠償責任主體范圍, 在此過程中需專業人士幫助。根據有關法律規定, 投服中心接受投資者委托可作為訴訟代表人提起訴訟, 并組建專業律師團隊參加庭審。在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中, 賠償主體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 涉嫌參與虛假陳述的公司董監高人員、 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 簽字會計師。而爾康制藥證券支持訴訟案發生于2019年, 新《證券法》尚未實施, 此案賠償主體為爾康制藥、 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帥放文和劉愛軍、 副總經理王向峰、 總工程師楊海明及其余12名相關高管人員, 具體對比如表2所示。總體來看, 投服中心在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依據法律規定堅持追究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的首要賠償責任, 極大程度保障了中小投資者的權益, 并對實施證券虛假陳述的上市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 以及相關中介機構形成震懾。
(二)賠償范圍的認定: 關鍵時點認定及市場反應檢驗
此部分重點分析訴訟賠償范圍認定的兩個關鍵時間節點, 即虛假陳述實施日以及虛假陳述揭露日, 在此基礎上判定受害投資者人數以及賠償金額。
1. 虛假陳述實施日。根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簡稱《規定》)第20條: “本規定所指的虛假陳述實施日是指作出虛假陳述或者發生虛假陳述之日。”康美藥業于2017年4月30日披露2016年財務報告, 這是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最早的一份財報, 即2017年4月30日起, 虛假財務信息進入證券資本市場, 因此認定2017年4月30日為虛假陳述實施日, 爾康制藥為2016年4月6日。
2. 虛假陳述揭露日。虛假陳述揭露日并非一成不變。《規定》對于虛假陳述揭露日的界定總體遵循以下原則: 在全國范圍內首次公開揭露虛假陳述行為; 虛假陳述行為被揭露后是否對投資者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 具體表現為揭露日后的一定期間公司股價通常呈現下降趨勢, 該公司股價是否與該變動趨勢相符合。在具體司法實踐中, 多以《立案調查通知》《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行政處罰決定》等文件的公告日、 媒體揭露報道日作為虛假陳述揭露日。
在康美藥業案中, 將2018年10月16日定為虛假陳述揭露日, 理由為: 該日自媒體發布質疑康美藥業財務造假的報道后被多家權威媒體報道、 轉載; 自媒體揭露內容引發了巨大的市場反應。康美藥業股價在2018年10月16日之后閃崩, 其走勢與上證指數、 行業指數存在較大背離, 可以認定市場對于自媒體的揭露行為作出了強烈反應, 同時證明了自媒體揭露行為的警示作用。投服中心一方律師團隊提交的百度搜索指數、 百度資訊指數也證明了自媒體轉載后導致康美藥業成為輿論關注中心。因此將該日定為虛假陳述揭露日是合理的。
爾康制藥案中, 將2017年8月10日定為虛假陳述揭露日, 理由為: 中國證監會于2017年8月10日發布《調查通知書》, 向股票市場發出“謹慎投資”的警示信號引起投資者的關注; 《調查通知書》發布的前提是, 在信息披露義務人出現信息披露違規端倪的情況下, 中國證監會通過初步立案調查從側面證實信息披露義務人存在證券虛假陳述的風險; 爾康制藥在巨潮資訊官網進行信息披露, 符合“全國范圍發行或播放的報刊、 電臺、 電視臺等媒體”要求。綜合上述條件, 其將2017年8月10日定為虛假陳述揭露日是合理的。康美藥業案與爾康制藥案虛假陳述關鍵時點如表3所示。
本部分運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康美藥業揭露日前后股價的變化。將2018年10月16日定為事件研究基準日, 窗口期定為(-5,5), 估計期定為120天, 選擇上證綜合指數作為市場收益率, 運用市場模型估計期望收益率, 進而計算超額收益率(AR)和累計超額收益率(CAR)。其中, ARi,t=Ri,t-[R]i,t, [R]i,t=[α]+ ? ? ?×Rm,t, [R]i,t為股票在時點t的期望收益率, Ri,t為實際收益率。將窗口期內康美藥業的超額收益率進行累積得到: CARi,(t1,t2)= ? ? ? ? ? ARi,t。由圖1、 圖2可知, 虛假陳述揭露日及其后三天市場對康美藥業財務造假事件呈現較高的關注度, 投資者在收到康美藥業財務造假的相關消息后, 對公司持強烈的消極態度, 進而導致康美藥業股價大幅下跌。圖3反映了康美藥業一審判決公布前后的市場關注度, 可以看到在一審判決發布后一日引起強烈的市場關注。可見, 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的關注和討論, 增強了“投資者參與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具有溢出效應”結論的可靠性。
3. 受損失投資者人數。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的受損失投資者人數的確定主要依據訴訟賠償范圍認定相關原則: 虛假陳述實施日至揭露日前一天期間仍持有康美藥業股票的投資者總數扣除未受到損失的投資者人數, 共計52037名。爾康制藥證券支持訴訟一案根據有關規定索賠區間為2016年4月6日 ~ 2017年8月10日買入該公司股票并于2017年8月11日之后賣出或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且因此產生虧損的投資者, 共計818名。
4. 賠償金額的計算。計算賠償金額時, 選定系統性風險扣除比例存在一定困難。系統性風險往往是被告方作為抗辯理由阻卻因果關系判斷的有力“法寶”, 當法院認定被告方提交的材料證明了投資者損失與虛假陳述行為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時, 將會在計算時扣除此部分。但由于在司法解釋中并未對系統性風險的認定做具體劃分, 在選擇扣除比例時存在較大的主觀隨意性。
在康美藥業案中, 關于系統性風險的認定原告方與被告方產生了爭議。被告方主張由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進行測算, 而投服中心則主張由深圳價值在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測算。由于測算方式不同, 系統性風險扣除比例的選擇也不同, 雙方一直未形成統一意見。廣州中院最終委托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責任公司進行損失測算, 選取醫藥生物(申萬)指數作為系統風險扣除的參考指數, 采用“個體相對比例法”測算系統性風險, 最終測算受損失投資者共計52037名, 金額總計2458928544元。
在爾康制藥案中, 依據《規定》相關條款, 確認2019年1月23日為基準日, 爾康制藥2016年4月6日(實施日)至2017年8月10日(揭露日)的股價走勢與漲跌幅和大盤基本一致, 但在揭露日至基準日期間, 大盤呈上升趨勢時, 爾康制藥股價卻呈現暴跌狀態, 因此判定爾康制藥在揭露日至基準日期間, 股票不存在系統風險影響因素。本案主要借助投服中心已有的計算機數據模型, 采用移動加權平均法計算出最終受損失投資者共計818名, 賠償金額合計70306009.43元。
5. 訴訟效率。作為首例特別代表人訴訟案, 在康美藥業案中, 關于關鍵時點和系統性風險剔除比例的確認雙方存在分歧, 因此整體審理時長較爾康制藥證券支持訴訟案長。從訴訟時長來看, 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明顯優于爾康制藥證券支持訴訟案, 如表4所示。
(三)賠償金額的判決與執行
在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中, 康美藥業于2021年6申請破產重整, 2021年8月召開第一次債權人會議, 投服中心作為債權人代表積極行使提議權、 表決權等股東權利, 以最大限度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2021年12月20日, 康美藥業破產重整計劃通過并開始執行。2021年12月21日, 有部分投資者在相關網絡論壇反映已收到康美藥業的賠償款。2021年12月29日, 經廣東省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 康美藥業全部債務已通過現金、 股份、 信托權益等方式實現100%清償。爾康制藥在2018年度已就有關訴訟事項計提預計負債6610萬元, 2019年度補提950萬元預計負債。在2020年12月底, 爾康制藥根據判決與調解結果, 已向原告賠償相應損失金額, 賠付已全部完成。由此可見, 在新《證券法》規定下, 投服中心可更加積極行使股東權利, 提升了案件執行效率和效果, 始終站在中小投資者一方為中小投資者爭取更大的利益。
五、 投服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作用發揮的實現機理與溢出效應
(一)投服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作用發揮的機理
1. 聚焦受害投資者維權, 積極發揮自身職能優勢。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 凸顯了投服中心在投資者訴訟維權中的重要作用。投服中心是由中國證監會設立并管理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其官方背景使得康美藥業案審理過程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促進公眾監督案件審理, 提升案件審判的公正性。與此同時, 投服中心在信息獲取和資源整合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憑借自身專業優勢, 利用互聯網全面高效地搜集證據資料, 加速推動立案進程。投服中心積極與各類相關機構溝通協作, 通過組建專業律師團隊參加庭審, 提升案件獲勝幾率, 并督促判決結果有效執行。
2. 組建專業公益性律師團隊, 積極為中小投資者提供訴訟維權服務。投服中心作為具有公益性質的中國證監會直屬機構, 其機構整體包括行業專家、 專業律師團隊、 專業監管人員等, 通過面向中小投資者開展公益性宣傳教育, 加強中小投資者對相關專業知識業務流程的了解, 通過專業團隊為中小投資者提供公益性訴訟、 糾紛調解等服務。由于證券虛假訴訟案件涉及大量訴前準備, 加之高昂的訴訟成本, 阻礙了中小投資者訴訟維權。針對這些問題, 投服中心通過組建公益性律師團隊及時與投資者互動溝通, 并委托專業律師團隊參加庭審, 同時律師費、 案件受理費等相關費用也無需中小投資者承擔, 能夠積極為中小投資者訴訟維權服務。
3. 針對重點內容提出訴辯, 爭取投資者利益最大化。投服中心以保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針對賠償金額的具體認定和計算, 投服中心爭取利益最大化; 針對投資者損失金額的計算, 主張采用更符合客觀事實的移動加權平均法, 該主張也得到法院認可。同時, 針對康美藥業在申萬一級行業指數占比較大、 扣除系統性風險比例過高提出申訴。可見, 投服中心在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中將“投資者保護”這一理念貫穿始終, 為投資者爭取了利益賠償最大化。
(二)投服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的溢出效應
1. 投服中心示范引領, 喚醒中小投資者訴訟維權意識。鑒于中小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的弱勢地位以及訴訟困境, 我國絕大多數中小投資者在權益受損時選擇觀望甚至放棄訴訟, 最終錯過了訴訟的最佳時機而蒙受損失。針對這些情況, 新《證券法》進一步對股東權利、 先行賠付、 證券糾紛等投資者保護制度作出規定。在新的制度背景下, 投服中心職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如開展公益性專業講座, 以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向中小投資者普及訴訟維權相關的專業知識。并且, 投服中心參與訴訟案件的相關內容均會通過網絡公開, 有利于中小投資者快速了解最新案件內容并加深對訴訟制度和流程的理解。投服中心發揮自身的引領示范作用能夠喚醒中小投資者知權、 行權、 維權的意識, 同時又能減少中小投資者訴訟維權時的憂慮, 提升中小投資者訴訟維權積極性。
2. 投服中心持股行權, 規范上市公司經營活動。投服中心通過持股行權的方式參與公司治理, 通過現場行權為上市公司經營章程提供意見和建議。如通過發送股東質詢建議函的方式對公司提出相關合理建議, 針對公司資金占用事項、 子公司失控、 董事監事缺席股東大會提出質詢, 針對上市公司重組存在的不確定因素、 估值是否合理、 經營是否可持續等提出相關問題等。截至2023年2月底, 投服中心持有5075家上市公司股票, 共計行權3488場, 累計行使包括建議權、 質詢權、 表決權、 臨時股東大會召集權等在內的股東權利4413次, 取得較好的行權效果。投服中心持股行權職能的履行能夠促進我國證券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規范上市公司治理與運營。
3. 督促獨立董事勤勉盡責,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引發了獨立董事辭職以及董監高責任保險購買的熱潮, 這一現象也引發了人們關于獨立董事制度的思考。獨立董事制度設立的目的是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 監督公司管理者。但在后期發展中, 關于獨立董事角色的假設與其實際功能的發揮產生了矛盾, 出現獨立董事獨立性下降、 監督效應不強等現象。此外, 風險和收益不對等也是導致獨立董事職能發揮不充分的一項重要原因。如何督促獨立董事履職盡責, 激勵獨立董事積極履行義務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點之一。法律是規范各主體行為的有效手段, 新《證券法》對獨立董事有了更加嚴格的約束, 負有責任的獨立董事所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風險加大。配合投服中心持股行權職能, 通過強化法律責任來促進獨立董事職能發揮, 督促獨立董事勤勉盡責, 從而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六、 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為例, 分析新《證券法》實施背景下投服中心在特別代表人訴訟中作用發揮的機理及溢出效應。研究發現: 其一, 投服中心作為代表人參與的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訴訟的效率和效果。投服中心利用互聯網技術收集受害投資者信息、 訴訟所需材料與證據, 作為代表人提起訴訟, 并組建專業律師團隊參加庭審, 最大化發揮自身職能, 幫助中小投資者獲得賠償。其二, 投服中心具有“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性質, 通過發揮持股行權職能, 形成對公司經營治理活動軟監管的同時強化投資者保護。新《證券法》實施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 通過投服中心的參與有利于提升訴訟的效率和效果, 投服中心的“官方”性質對上市公司起到震懾作用的同時也能夠及時為投資者追回相應賠償。其三, 投服中心參與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具有溢出效應。通過自身示范效應提升中小投資者行權維權的積極性, 多種渠道普及維權相關的專業知識, 公開相關案件進展幫助廣大投資者理解新《證券法》相關條款及其實施流程, 喚醒中小投資者維權意識; 其持股行權作用的發揮能夠有效規范上市公司經營活動, 保障證券市場活動健康有序開展。
本文主要研究貢獻在于: 一是基于新《證券法》背景, 以投服中心為代表的特別代表人訴訟為切入點, 拓展了我國中小投資者保護理論, 豐富了現有文獻; 二是從投服中心持股行權視角分析“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在我國中小投資者保護中的作用實現機理及其產生的后續效果, 為中小投資者保護機制的后續完善提供經驗證據; 三是基于賠償認定視角對新《證券法》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實施進行相應解讀, 深入分析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實施及其效果, 這對于我國今后繼續實施和完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具有啟示作用。
(二)研究啟示
新《證券法》的實施, 進一步明確和強化了投服中心的職能和地位。“半公共—半私人”實施機制有利于強化投服中心對證券市場的監管, 提升中小投資者行權維權積極性, 同時也可強化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 有助于推動我國股東積極主義的興起。除了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 截至2021年9月底, 投服中心共提起支持訴訟案件45件、 股東直接訴訟案件1件、 股東代位訴訟案件1件, 股民申請維權數量逐漸增加。此外, 訴訟還需要專業律師團隊的參與, 股東訴訟的興起也將提升民間律師團隊的活躍程度。
對于投資者而言, 應充分意識到新的法律制度環境帶來的積極效應, 不斷加強維權意識, 提高主動維權的積極性, 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及時向投資者保護機構尋求幫助。對于民間律師團隊而言, 應強化社會責任意識, 關注投服中心與股東訴訟的動態, 及時為中小投資者提供援助。對于投服中心而言, 應進一步規范職能作用的發揮, 強化投資者保護服務, 積極發布相關動態特別是重大訴訟案件, 宣傳專業知識, 及時解決投資者在維權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幫助投資者樹立成功維權的信心。
由于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作為新《證券法》實施后首例特別代表人訴訟案, 尚未發生同類性質案件, 樣本數量有限, 無法進行同類型多案例比較, 存在一定不足。但隨著新《證券法》的逐漸落實完善。股東訴訟興起以及中小投資者行權維權積極性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未來相關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陳運森,鄧祎璐,李哲.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財務報告問詢函的證據[ J].管理世界,2019(3):169 ~ 185+208.
陳運森,袁薇,蘭天琪.法律基礎建設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基于新《證券法》的事件研究[ J].財經研究,2020(10):79 ~ 92.
陳運森,袁薇,李哲.監管型小股東行權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投服中心的經驗證據[ J].管理世界,2021(6):142 ~ 158+9+160 ~ 162.
郭靂.作為積極股東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以投服中心為例的分析[ J].法學,2019(8):148 ~ 159.
耿利航.論我國股東派生訴訟的成本承擔和司法許可[ 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3(1):170 ~ 182.
郭文旭.新《證券法》實施下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啟動程序——規則解讀、制度構思和完善建議[ J].南方金融,2021(6):90 ~ 100.
胡明霞.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下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探析[ J].財會月刊,2021(7):133 ~ 137.
劉啟亮,鄧瑤,陳惠霞,李洋洋,俞浩嵐.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演變:1990~2022——基于典型個案的研究[ J].財會月刊,2023(1):122 ~ 130.
劉詩瑤.我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完善進路研究——以《〈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為切入點[ J].河北法學,2018(11):181 ~ 190.
劉裕輝,沈梁軍.境內外證券市場投資者賠償補償機制比較研究[ J].證券市場導報,2017(8):13 ~ 19.
任鶴,顏逢.監管型小股東與股價崩盤風險——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權的經驗證據[ 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22(6):91 ~ 100.
沈偉,林大山.激勵約束視角下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以新《證券法》為背景[ J].證券法苑,2021(1):360 ~ 387.
湯旭東,常海暇,任保增等.監管型小股東與股價崩盤風險——來自投服中心行權的證據[ 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23(6):1610 ~ 1629.
王琳.投資者權益保護與證券支持訴訟:以法經濟學為視角[ 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47 ~ 155.
薛永慧.臺灣證券團體訴訟制度:規范與借鑒[ J].臺灣研究集刊,2016(3):9 ~ 16.
辛宇,黃欣怡,紀蓓蓓.投資者保護公益組織與股東訴訟在中國的實踐——基于中證投服證券支持訴訟的多案例研究[ J].管理世界,2020(1):69 ~ 87+235.
伊志宏,李艷麗.機構投資者的公司治理角色:一個文獻綜述[ J].管理評論,2013(5):60 ~ 71.
Athari S. A.. Does investor protection affect corporate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Asian markets[ 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22(2):579 ~ 598.
Bourveau T., Lou Y., Wang R.. 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derivative lawsuit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8(3):797 ~ 842.
Chen Z., Ke B., Yang Z.. Minority shareholders' control rights and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decisions in weak investor protection countries: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hina[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3(4):1211 ~ 1238.
Cheng C. S. A., Huang H. H., Li Y., et al..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through shareholder litigation[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3):356 ~ 383.
Chung C. Y., Kim I., Rabarison M. K., et al.. Shareholder litigation rights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s[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20(62):101599.
Firth M., Lin C., Wong S. M., et al.. Hello, is anybody there? Corporate accessibility for outside shareholders as a signal of agency problems[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9(4):1317 ~ 1358.
Feng Nancy C., Fuerman R. D..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in the US and Canada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ir auditor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Journal of Forensic and Investigative Accounting,2019(1):103 ~ 137.
Hopkins J.. Do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deter misreporting?[ 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8(4):2030 ~ 2057.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4):305 ~ 360.
Kang J. K., Luo J., Na H. S.. A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ith multiple blockholdings effective monitor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8(3):576 ~ 602.
Solomon D.. The voice: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perspective[ J].Nevada Law Journal,2017(17):739 ~ 772.
Wan W. Y., Chen C., Goo S. H.. Public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of corporate and securities laws: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J].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2019(2):319 ~ 361.
Wang K. T., Kartika F., Wang W. W.,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the cost of equity: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21(47):1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