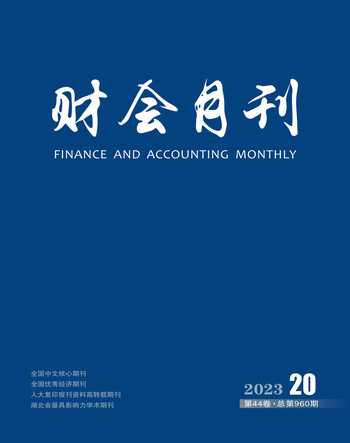基金綠化影響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效應及機制:文獻回顧與展望
夏燁 馬文超



【摘要】碳達峰、 碳中和(“雙碳”)目標的實現, 生態(tài)文明建設新進步的取得, 都要求資本市場在資金的有效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 同時需要企業(yè)致力于可持續(xù)的發(fā)展。研究關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的綠化現象, 首先, 聚焦資本資產定價、 所有權積極主義和同群效應等研究, 梳理與基金綠化相關的市場績效、 企業(yè)效應以及效應擴散方面的文獻; 其次, 基于經驗結論和多中心治理理論, 構建基金綠化對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效應影響的理論分析框架, 并展望該框架下值得進一步考察的主要命題; 最后, 圍繞政治經濟領域相關文獻的結論, 指出紓解環(huán)境管制困境, 探索綠色基金治理效應的理論邏輯, 以及相關研究在環(huán)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基金綠化;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同群效應;環(huán)境績效;公共治理
【中圖分類號】F832.51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20-0135-8
一、 引言
聚焦“雙碳”目標, 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huán)發(fā)展經濟體系, 實現經濟社會發(fā)展全面綠色轉型成為“十四五”和未來十年中國綠色發(fā)展的重大任務。正如2020年12月26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要利用市場手段和管控措施, 實現減污降碳協(xié)同效應。如何利用市場手段解決綠色發(fā)展困境?這是經濟理論與實踐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基本問題。充分發(fā)揮市場主體積極性, 堅持系統(tǒng)觀念, 實現環(huán)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環(huán)境污染治理和環(huán)保產業(yè)發(fā)展中尤為緊迫。盡管改革初期國有企業(yè)自治、 1993年工業(yè)污染防治會議后政府集中治理以及近年來主管部門約談責任官員等開展督政式治理, 政府大幅提升了環(huán)境治理效率, 但是這些治理方式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何“堅持問題導向、 堅持系統(tǒng)觀念”①, 改進環(huán)境治理具體實踐中的不足值得進一步探索。
按照奧斯特羅姆(2000)的公共治理理論, 環(huán)境治理不僅需要發(fā)揮政府、 排污企業(yè)對環(huán)境治理的主導、 主體作用, 還需要其他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陳潭,2017;沈洪濤和黃楠,2018)。目前中央和地方錨定“雙碳”目標, 我國已經全面開展碳排放權交易工作, 理論研究也如火如荼。事實上, 基金在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影響中也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理論探析較少。實踐中, 近十年來中國機構投資經歷了跨越式發(fā)展, 已占到中國資本市場的40%多, 重要行業(yè)超過60%(Qi等,2020)。其中, 綠色基金發(fā)展成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馬駿,2015)②。就新興市場國家而言, 中國綠色投向的公募基金, 其收益、 市場擇機、 波動識別等均好于巴西、 印度和南非等(Ji等,2021)。但是, 目前針對中國的有關探討主要聚焦于國家綠色發(fā)展基金等, 對于資本市場公募基金推動環(huán)境治理的考察并不多見。
回顧已有文獻, 發(fā)現存在大量與基金綠化相關的市場績效、 企業(yè)效應以及效應擴散方面的研究。考察基金投資策略變化對基金業(yè)績的影響, 對象包括新設的綠色基金和將投資策略變更為綠色的基金, 張強等(2023)發(fā)現綠色基金整體上未獲得超額收益, 梁鑫鑫和危平(2019)則發(fā)現主動型綠色投資與被動型綠色指數組合投資的財務績效相近。國內研究的結論表明, 采用積極的綠色投資策略不會給基金在市場上帶來超額收益。就近期的國外證據而言, Hall(2018)、 Ghoul和Karoui(2021)具體論證了綠色策略被采用后對基金的資金流、 周轉率和業(yè)績等的影響, 他們發(fā)現綠色基金并未獲得超額回報。但是, Chen等(2020)認為基金的綠色投資提高了基金的超額收益, 然而回報的正向增加存在于采用消極策略的樣本中。Cooper等(2005)、 Espenlaub等(2017)檢驗了基金名稱和策略變化的原因, 指出與熱門投資類型相關的策略變更主要是為了吸引投資者進而增加資金流入, 而不是真正為了投資者去提高基金的回報。
如果基金綠化只是為了迎合市場投資者的偏好, 而不能通過組合投資給可持續(xù)性投資人帶來收益, 其發(fā)展就難以實現政府和社會公眾的初心。值得關注的是, 國外大量研究發(fā)現, 基于投資者積極治理主義(Investor activism), ESG標準下“股東方案”的實現、 機構持股對企業(yè)社會責任績效的促進成了一種普遍現象(Dimson等,2015;Dyck等,2019;Chen等,2020)。Baloria等(2018)、 Deshpande等(2020)指出, 當私下參與動機與投資者利益不一致時, 股東方案的提交成為一種普遍的可觀測的治理行為。還有研究也表明, 不同時期、 不同的投資主體會通過股東方案推動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Proffitt和Spicer,2006;Grewal和Serafeim,2020)。就企業(yè)的社會責任績效而言, 機構持股作為治理變量, 其與較高的公司社會責任得分相關(Harjoto和Hojejo,2011), 單一機構投資者私下參與及其ESG行為會影響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Dimson等,2015;Chen等,2020)。此外, 國家間的社會規(guī)范差異也會影響機構投資者和公司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Dyck等,2019)。
作為機構投資者的一員, 如果綠色基金可以促進企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 那么這一促進是否僅僅限于機構或者基金所投資的這一企業(yè)?已有文獻顯示, 由于社會網絡和同群效應的作用, 這種效應可能會溢出到被持股企業(yè)所屬的行業(yè)。Ozsoylev等(2014)、 Pool等(2015)發(fā)現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會使機構投資者獲得超額回報, Qi等(2020)則進一步發(fā)現中國機構投資者利用他們在社會網絡中所具有的信息優(yōu)勢, 會顯著影響企業(yè)社會責任投資的決策。同群效應在個人和組織的財務決策中的廣泛存在, 得到了充分的論證(Kaustia和Knüpfer,2012;Bailey等,2018), 包括資本結構選擇、 預防性現金持有、 分配政策、 兼并和IPOs等關鍵事件的市場反應(Leary和Roberts,2014;Grennan,2018)。Serafeim(2018)指出通過多元化組合、 聚焦行業(yè)的多家企業(yè), 可使企業(yè)層面遵循ESG標準的“搭便車”行為公開化, 有助于行業(yè)整體的可持續(xù)性。Cao等(2019)發(fā)現一家企業(yè)社會責任方案的通過, 會引起同群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業(yè)績提升。
由于國內外重點考察綠色基金持股效應的文獻較少, 中國有關積極股權對社會責任影響的具體考察也比較缺乏。本文在回顧以上三類相關文獻的基礎上, 進一步梳理了綠色基金推動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概念和邏輯框架, 并對可能需要進行經驗分析的命題進行了具體論述。對有關理論檢驗的展望包括: 基金綠化內涵界定, 基金綠化的市場動因, 基金綠化的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效應, 基金綠化的擴散機制以及基金綠化與多中心環(huán)境治理的主體策略五個方面。
以基金綠化的方式推動我國環(huán)境治理可能是充分發(fā)揮市場作用的有效途徑之一。目前綠色基金數量大幅增加, 按照投資策略計算, 近年來基金市場上的綠色基金也由2010的2只增加到2020的200多只③。但是相關研究卻十分缺乏, 只有梁鑫鑫和危平(2019)進行了綠色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的特征和收益比較。因此, 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和未來研究展望, 將有助于借鑒國外的前期相關研究進一步考察中國基金綠化的效果。
二、 基金綠化的市場績效
基金綠化的市場績效是指基金目標、 策略調整為綠色之后, 其業(yè)績相對于調整之前或相對于傳統(tǒng)基金的增減。本文主要關注基金投資策略變化和所采用投資風格變化后的市場表現, 以及綠色或社會責任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的業(yè)績比較。
(一)基金投資策略和風格的變化
已有研究關注了綠色基金投資策略和技術變化對基金業(yè)績的影響。相關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一是綠色投資策略的采用, 聚焦那些圍繞環(huán)境治理的大背景調整投資目標、 投資策略的基金, 考察基金投資策略綠色取向及其效果, 其中包括將基金名變更為綠色的基金, 具體論證“綠色策略”被采用后對基金的資金流、 周轉率和業(yè)績等的影響(Hall,2018;Ghoul和Karoui,2021)。二是綠色基金投資風格的變化, 聚焦綠色基金樣本, 考察基金在公司市值、 成長性、 盈利性選擇上的變化, 以及基金經理的擇時能力、 選股能力對資金流、 交易量、 風險暴露和業(yè)績的影響(Climent和Soriano,2011;張強等,2023)。其中, 張強等(2023)聚焦綠色基金投資風格變化, 發(fā)現基金經理會通過盈利風格的改變影響基金的長期業(yè)績, 但擇時能力和選股能力不會對業(yè)績產生影響。
(二)綠色或社會責任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的業(yè)績比較
聚焦社會責任基金, 學者們的研究充分考察了采用不同稱謂的基金在業(yè)績表現上的不同。Bauer等(2005)、 Statman(2011)較早發(fā)現社會責任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在各個市場上存在的差異。我國也有研究考察了綠色基金、 社會責任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在收益上的不同(孔東民和林之陽,2018;危平等,2018)。除了Statman(2011)發(fā)現1990 ~ 1998年社會責任基金的業(yè)績好于市場指數(S&P 500 Index)和傳統(tǒng)基金, 以及Chen等(2021)發(fā)現基金的綠色投資提高了基金的超額收益, 其他比較研究的結論較為一致, 即認為社會責任基金的收益并不比傳統(tǒng)基金高。
以上兩類證據表明, 對于動態(tài)的縱向的基金投資策略變化以及所采用投資風格變化, 以及靜態(tài)的橫向的綠色或社會責任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比較, 均沒有體現出綠色、 社會責任投資的優(yōu)勢。是否真的像Cooper等(2005)、 Espenlaub等(2017)所發(fā)現的, 基金名稱變更為流行的稱呼(或與熱門投資類型相關)只會引起投資者的積極響應, 吸引額外的資金流, 而不會帶來基金回報的增加。但是, 基金綠化的效應可能不只會伴隨個體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和基金管理者的擇機行為。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是: 雖然綠色或社會責任基金的收益與傳統(tǒng)基金相同, 但是其風險分散、 聲譽構建、 社會效應等更大, 是否就可以認為綠色基金的市場表現好于傳統(tǒng)基金。
三、 基金綠化的企業(yè)效應
基金綠化的企業(yè)效應是指上文提及的基金公司設立的綠色基金或由傳統(tǒng)基金變更后的綠色基金, 在踐行綠色投資策略時對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前期通過考察基金資產配置的動機、 基金參與股東方案的狀況、 基金對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等對相關內容進行了一系列考察。
(一)風險與聲譽選擇
基金為什么會將投資人的資金配置到特定企業(yè)?本文通過分析基金股東的利益來回答④。隨著金融市場分工的細化, 在社會公眾環(huán)境關心的促進下, 資本市場投資機構的綠色投資等變得十分必要(Heinkel等,2001;Riedl和Smeets,2017;星焱,2017)。基金作為企業(yè)股東之一處于“代理沖突應對”“風險分散考量”和“自身聲譽構建”事務中。有證據表明, 基金股東通過推動社會責任投資, 可以抑制企業(yè)管理者的代理問題(Harjoto和Hojejo,2011)。為了防止投資組合收益的過度波動, 在資金配置時基金會分散投資于多家企業(yè)并選擇一些履行了社會責任的企業(yè)(Chakravarthy等,2014;Krüger,2015;Kecskes等,2016)。特別是, 為了體現其環(huán)境關心、 凸顯其環(huán)境治理擔當、 維護其良好的聲譽(如社會責任業(yè)績排名等)進而吸引社會公眾的資金, 機構投資者會推動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投資(Riedl和Smeets,2017)。此類研究表明, 基金為緩解企業(yè)代理沖突、 降低投資風險、 維持自身聲譽而配置資產, 有動機參與到被持股企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中。總之, 對社會公眾環(huán)境關心的回應, 以及出于自身動機的權衡, 使得基金傾向于推動企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
(二)積極所有權與環(huán)境績效
關于組織如何促進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 投資者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投資者影響而言, 相關研究基于投資者積極治理主義(Investor activism)對ESG標準下股東方案的實現狀況、 基金持股對企業(yè)社會責任績效的影響進行了論證。
當企業(yè)行動與投資者利益不一致時, 股東方案的提交往往成為可觀測的投資者治理行為(Dimson等,2015;Baloria等,2018;Deshpande等,2020), 因此研究者便將股東方案作為考察投資者努力程度, 及其推動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工具⑤。研究也表明, 不同時期的投資主體是不同的。例如, 在20世紀90年代, 許多ESG協(xié)定由小投資者推動, 包括社會責任基金、 NGO組織和宗教組織等(Proffitt和Spicer,2006); 又如, 2019年大部分聚焦可持續(xù)問題的股東方案由養(yǎng)老基金推動(Grewal和Serafeim,2020)。同時, 描述性的研究表明, ESG方案的支持率處于6% ~ 8%的較低范圍內(Campbell等,1999;Monks等,2004;Tkac,2006)。關于聚焦方案的效應, 有研究發(fā)現: 一方面, 方案提出與績效是無關或負相關的, 環(huán)境、 社會方案影響了企業(yè)的環(huán)境、 社會業(yè)績, 但方案上的資源消耗會使企業(yè)的可持續(xù)業(yè)績下降, 管理上的認同更多是表面的(Barber,2007;David等,2007;Clark等,2008); 另一方面, 與方案相關的披露效應明顯, 尋求更多ESG披露的股東方案引起了更透明的企業(yè)ESG披露和更多的整合報告實踐(Serafeim,2015;Baloria等,2018)。
就社會責任業(yè)績整體而言⑥, 機構持股作為治理變量, 其與較高的公司社會責任得分相關(Harjoto和Hojejo,2011); 單一機構投資者私下參與及其ESG行為會影響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Dimson等,2015;Chen等,2020); 國家間的社會規(guī)范差異會影響機構投資者與公司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Dyck等,2019)。
(三)綠色投資與研發(fā)
在我國研究基金綠化的企業(yè)效應的文獻較少, 相關研究主要結合政府實施的環(huán)境管制, 考察了機構投資者對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和研發(fā)的推動情況。前期針對環(huán)保投資的研究, 主要圍繞制度背景、 環(huán)境管制等的效果進行檢驗(唐國平等,2013;馬文超和唐勇軍,2018)。圍繞機構持股與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 祝敏等(2019)發(fā)現, 機構投資者整體持股能夠促進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其中, 壓力抵制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會促進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 而且環(huán)境規(guī)制對該關系具有強化作用。對于機構投資與綠色創(chuàng)新的關系, 方先明和那晉領(2020)發(fā)現, 綠色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越多的企業(yè)其股票超額收益率越高, 前者通過價值增長和市場關注雙重機制產生溢酬, 而后者僅通過市場關注機制產生溢酬。總之, 企業(yè)綠色創(chuàng)新獲得了機構投資者的關注。楊鳴京等(2018)進一步發(fā)現, 機構投資者關注企業(yè)的實質性創(chuàng)新, 他們通過調研等方式促進了企業(yè)創(chuàng)新績效的提升⑦。
以上研究表明, 社會公眾的環(huán)境關心、 基金公司的聲譽維持等均會讓基金參與到企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中, 并通過股東方案推動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 提高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水平。結合政府管制考察機構持股與企業(yè)環(huán)保決策的關系, 來自中國的證據表明, 與財務決策影響企業(yè)價值的路徑分析與檢驗相一致, 在機構投資者的推動下環(huán)境績效的提升往往會依賴企業(yè)的環(huán)保投資和研發(fā)工作。然而, 其中有關機構投資者的分析邏輯是否嚴恰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檢驗。
四、 基金綠化的同群效應
考察基金綠化的企業(yè)效應不僅涉及單一企業(yè), 還應包括細分行業(yè)內的企業(yè)或同群企業(yè), 已有研究圍繞基金網絡檢驗了其對企業(yè)社會責任的影響, 相關研究還考察了基金或機構投資者對行業(yè)ESG標準的提升、 企業(yè)社會責任方案通過對于同群企業(yè)的影響。
(一)基金網絡
基金網絡是指由被持股企業(yè)的基金股東們形成的網絡關系, 屬于社會網絡的一種形式⑧。基金網絡會通過信息共享提升機構投資者對被持股企業(yè)的治理效應, 其中也包括社會責任方面的效應。聚焦公募基金網絡(Mutual fund network), 計量網絡中心度(Network centrality), 檢驗基金股權資本和社會資本推動被持股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效果, Ozsoylev等(2014)、 Pool等(2015)發(fā)現基金網絡會使機構投資者獲得超額回報, Qi等(2020)則進一步發(fā)現中國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優(yōu)勢會影響企業(yè)社會責任投資的決策, 機構投資者通過社會網絡分享擴散了被投資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信息, 起到了金融中介信息傳播的作用。
(二)同群效應
機構投資者對被持股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影響還會進一步導致行業(yè)或同群效應。同群效應在個人和組織的財務決策中的廣泛存在, 得到了充分的論證(Kaustia和Knüpfer,2012;Leary和Roberts,2014;Bailey等,2018;Grennan,2018)。關于機構投資的同群效應, Serafeim(2018)指出, 雖然企業(yè)提升可持續(xù)性業(yè)績有助于行業(yè)價值增加, 但“搭便車”導致個體企業(yè)缺乏提升可持續(xù)性業(yè)績的激勵。此時, 機構投資者聚焦行業(yè)的多家企業(yè), 可使企業(yè)層面的“搭便車”行為公開化, 有助于行業(yè)整體的可持續(xù)性。聚焦企業(yè)社會責任的同群效應⑨, Cao等(2019)考察了一家企業(yè)社會責任方案的通過對產品市場中存在同群競爭的其他企業(yè)的影響, 發(fā)現方案的通過不僅會引起積極的短期市場反應和社會責任業(yè)績提升, 而且同群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業(yè)績也會隨之提升。
以上研究表明, 基金會通過社會網絡獲得超額收益, 而且會對被持股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產生正向的推動。同時, 同群效應也會影響到被持股企業(yè)及其所處行業(yè)的其他企業(yè), 影響他們的社會責任履行。然而, 相關研究對社會責任履行中環(huán)境治理的具體考察較少,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這一角度的基金治理效應。
五、 基金綠化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 一個理論框架
(一)分析框架的構建
上文對已有研究的理論梳理顯示, 與基金綠化相關的社會責任研究確實存在兩個主要方面的論證: 一是直接效應考察, 對比分析基金的社會責任投資與傳統(tǒng)投資的“風險—收益”差異; 二是間接效應論證, 實證檢驗基金持股對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但是, 正如前文各部分的評述指出, 已有研究雖然全面考察了機構持股的環(huán)境、 社會效應, 但對基金綠化過程, 特別是對基金持股參與環(huán)境治理的研究存在不足。
秉持綠色發(fā)展理念, 聚焦“生態(tài)文明建設中綠色金融發(fā)展”這一主題, 切實領會黨和中央關于“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精神, 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本文認為需進一步考察金融細分市場——基金市場的基金綠化過程及其對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影響, 構建相應的研究框架, 如圖1所示。
圖1中, 圍繞中國金融市場快速增加的基金綠化, 參照國外經驗研究方法和上文的相關結論, 進一步研究需要考慮的基本問題如下:
1. 基金綠化的內涵是什么。在其投資策略發(fā)生轉變之后, 在基金市場上組合投資的收益是否會提升, 投資組合中被持股企業(yè)的環(huán)境業(yè)績是否會提升。這些綠化引起的市場績效和環(huán)境績效需要分別通過市場交易數據和環(huán)境報告文本進行描述和分析。特別值得進一步明確的是哪些基金是綠色的, 這需要通過對基金市場上每只基金的投資原則進行深度比較和判斷。
2. 基金綠化的市場動機是什么。對于綠化動機的具體分析, 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將綠色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進行比較, 考察基金年齡、 規(guī)模、 經理人特征等引起的投資風格差異、 市場回報差異。由于基金經理人的業(yè)績和收益依賴于基金資金流的增加, 因此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檢驗綠色基金相對于傳統(tǒng)基金在資金流吸引上的優(yōu)勢。
3. 基金綠化會引起怎樣的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效應。首先, 進一步研究需要關注綠色基金或投資原則為綠色的基金對于被持股企業(yè)的影響水平, 不同的持股水平或者其對管理者、 其他股東的監(jiān)督差異將決定基金影響企業(yè)決策的水平。其次, 受基金影響的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需要合理界定, 既可以是針對環(huán)境管理和環(huán)境經營兩方面計量的水平層次, 也可以是將財務投入與環(huán)境產出結合的效率層次。
4. 基金綠化對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影響是如何擴散的。分析基金綠化對于被持股企業(yè)和其他相關企業(yè)的影響, 需要關注基金在企業(yè)股東中的地位, 特別是基金所具有的信息優(yōu)勢, 此時, 需要考察企業(yè)的治理結構和與企業(yè)相關聯(lián)的基金網絡。同時, 當同一類企業(yè)中的一員受到綠色基金的影響或其網絡的影響時, 同群企業(yè)的反應需要進行充分的考察, 這里將包括與環(huán)境績效提升相關的具體措施, 如技術創(chuàng)新、 融資約束、 環(huán)保投資等。
5. 基金綠化情境下多個相關主體如何進行行動策略的選擇。在中國企業(yè)受環(huán)境管制的實踐中, 企業(yè)基于成本考量的自主治理水平如何, 排放權交易市場運行對于減排的促進效果如何, 市場化的綠色基金參與和推動程度如何, 三種治理方式的邊界確定是有效提升中國基金綠化效果的根本保證。
(二)有待進一步檢驗的內容概述
1. 基金綠化內涵界定。隨著基金市場上社會投資者的綠色意識的增強, 基金為了滿足投資者的環(huán)境關心、 吸引額外的資金流(Cooper等,2005;Espenlaub等,2017), 基金“目標、 策略及名稱的綠化”將會增加。如圖2所示, 基金綠化(由傳統(tǒng)T到綠色G)伴隨著基金市場績效的變化; 在政府監(jiān)管要求和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訴求下, 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會引導并加速基金綠化。正如機構持股與社會責任投資領域的兩類文獻所指出, 機構投資者促進了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 同時機構投資者也會傾向于持有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的企業(yè)的股票(Dyck等,2019;Chen等,2020)。進一步研究如下: 第一, 需要采用“網絡爬蟲、 文本閱讀”方法考察近年來中國基金市場上基金綠化的樣本分布、 綠色類型和綠色程度。第二, 需要采用符合中國投資者訴求表達的環(huán)境關心量表⑩等問卷調研綠化機理涉及的一個基本問題, 即此類綠色基金的出現是為了迎合資本市場上的非理性投資者嗎?第三, 需要通過案例描述基金的市場、 環(huán)境績效。在此類綠色基金出現的不同時期、 不同階段, 通過案例進行具體分析: 綠色基金(G)的資金流、 周轉率和異常回報等是否不同于傳統(tǒng)基金(T)?(Ghoul和Karoui, 2021)?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受兩類基金的影響是否不同?
2. 基金綠化的市場動因。理論分析指出, 基金管理者會出于風險分散(規(guī)避收益波動)、 聲譽維持(追求業(yè)績排名)目的特別是為了應對社會公眾的環(huán)境關心, 參與基金綠化, 中國也存在相關的研究(張方方和陳峰,2018)?。但是, 關于基金的產生,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是基于克服信息不對稱的需要, 而產業(yè)經濟學則認為是基于規(guī)模經濟和規(guī)模效應的需要, 由大量資金組成的投資組合可有效降低管理費用, 提高投資組合效益, 并通過多樣化的投資降低投資風險。然而, 對于基金綠化或綠色基金而言, 除了信息功能和資產配置優(yōu)勢使其發(fā)揮了社會公眾與企業(yè)之間的金融中介作用, 正如內涵界定部分所提到的, 基金綠化是否迎合了市場投資者還需進一步實證考察。一是需要識別綠色基金與傳統(tǒng)基金在總凈值、 費用率和周轉率等基金特征上的差異, 明確基金經理綠化基金的具體動機; 二是需要識別綠色基金相對傳統(tǒng)基金在“超額資金流”上的不同, 判斷基金綠化對投資者的吸引水平。
3. 基金綠化的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效應。考察基金綠化的間接效應, 即綠色基金參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效應, 其中內生性問題的解決是經驗分析的關鍵。正如對機構持股與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的研究發(fā)現, 機構持股會影響被持股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履行, 同時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履行狀況又會引起機構投資者對該企業(yè)的遴選。對應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分析, 該問題同樣存在。黎文靖和路曉燕(2015)發(fā)現, 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對機構持股有正向影響; Dimson等(2015)、 Chen等(2020)也發(fā)現單一機構投資者私下參與及其ESG行為會影響企業(yè)社會責任履行中的環(huán)境得分。在以上雙向因果關系中, 基金參與企業(yè)的治理可能并不以推動環(huán)境責任履行為目標, 環(huán)境績效好的企業(yè)只是在其他方面對基金產生了吸引。考慮不可觀測的企業(yè)異質性(Hete-
rogeneity)可能會同時影響綠色基金持股和企業(yè)環(huán)境責任履行, 如何將綠色基金持股視作或設定為外生的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動因顯得特別重要。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在考察中國機構持股抑制企業(yè)避稅及其效應時發(fā)現, 機構投資者與被投資上市公司之間的空間距離是較好的機構持股工具變量; Chen等(2020)則在考察美國機構持股與企業(yè)社會責任時發(fā)現, 被持股企業(yè)是否納入股指清單是較好的機構持股工具變量。顯然, 在以上內生性問題的解決中, 聚焦于中國的地理距離、 納入指數狀況就值得進一步探索。
在對綠色基金參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這一間接效應考察中, 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的測度顯得尤其關鍵, 應具體檢驗綠色基金(含綠色與傳統(tǒng)基金比較)對被持股企業(yè)環(huán)境業(yè)績和生態(tài)效率的影響。什么是環(huán)境業(yè)績?什么是生態(tài)效率?如上文分析中所指出, 依據《ISO14031環(huán)境管理環(huán)境表現評價指南》評估“環(huán)境管理控制—EMP”和“環(huán)境經營結果—EOP”, 將過程績效與結果績效相結合, 可以有效界定企業(yè)的環(huán)境業(yè)績指標要素。同時, 考慮到中國會計準則自2000年以來與國際的趨同, 在進一步研究中采用國際會計與報告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組(ISAR)2000年提出的“環(huán)境效益—EEI”評估方法, 將財務績效與環(huán)境績效相結合, 協(xié)同考察單位增加值的環(huán)境影響, 將可能合理界定生態(tài)效率的指標要素。最后, 便可采用極差標準化的無量綱方法或熵值法等排序, 獲取觀測對象得分, 進行比較分析。
4. 基金綠化的擴散機制。理論上, 綠色基金介入企業(yè), 通過優(yōu)化治理結構加強環(huán)境管理控制, 進而促進企業(yè)環(huán)境管理業(yè)績(EMP)和節(jié)能減排投入, 從而提升企業(yè)環(huán)境經營業(yè)績(EOP)。正如市場動因分析中指出, 綠色基金優(yōu)化治理結構的動機應與一般公募基金選擇社會責任履行較好的企業(yè)一樣, 這些綠色基金的管理者出于風險分散、 聲譽維持等動機, 可能會參與到企業(yè)的股東方案選擇或者“用腳投票”促進企業(yè)決策的優(yōu)化, 這種社會責任傳遞的邏輯也會引起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的提升。特別是, 出于對社會合法性的構建?, 社會公眾的環(huán)境關心、 基金公司的聲譽維持也會是他們參與治理時著重考慮的問題。
但就治理參與的邏輯而言, 除了關注“從綠色方案執(zhí)行到環(huán)境績效提升”, 進一步研究還需考察決策情境的影響。關注股權資本和社會資本共同對被持股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影響, 考察網絡治理和同群效應的作用, 這在分析綠色基金促進企業(yè)環(huán)境效應提升的路徑時變得尤其關鍵。根據陳運森和謝德仁(2011)、 ?Qi等(2020)的網絡分析, 獨立董事網絡、 機構投資者網絡確實會影響企業(yè)的投資決策、 社會責任履行。在客觀存在的綠色基金網絡中, 處于網絡中心的基金自然會在信息共享、 決策影響上具有優(yōu)勢, 進而對影響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的技術創(chuàng)新、 融資緩解和環(huán)保投資提升產生積極效應。依據Cao等(2019)的檢驗, 同群效應會影響行業(yè)內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履行, 一個企業(yè)方案的通過會使得處于競爭狀態(tài)的同群企業(yè)提升其社會責任履行, 這一邏輯在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方面自然會存在。此時, 當提升環(huán)境治理的各個路徑(技術創(chuàng)新等環(huán)節(jié))受到綠色基金網絡的影響時, 由于理性羊群效應(Leary和Roberts,2014), 環(huán)境績效將加速溢出到同群或行業(yè)內企業(yè)?。然而, 是因為同群企業(yè)之間的產品競爭發(fā)揮作用, 還是因為具有網絡信息優(yōu)勢的綠色基金起了作用, 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考察。
5. 基金綠化與多中心環(huán)境治理的主體策略。依據奧斯特羅姆(2000)的多中心治理分析, 借鑒Williamson(1985)的比較靜態(tài)分析框架, 本文考察基金等主體參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現實情境, 如圖3所示。基金的綠化程度受環(huán)境管制強度、 企業(yè)自治能力、 市場替代性治理程度, 特別是企業(yè)污染水平的影響。按照前文分析, 基金會參與企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 其效應也會溢出到相關行業(yè)。在環(huán)境管制、 企業(yè)自治和市場替代的實踐中, 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當市場替代企業(yè)解決環(huán)境問題出現失靈時, 基金作為市場中的特定主體, 其如何加速或干擾管制約束下的企業(yè)與市場的替代或合作。基于環(huán)境污染的企業(yè)自治?和市場替代(排放權交易等?)狀況, 需要根據中國近年來企業(yè)污染水平(Ki)和環(huán)境管制強度(Ri)的變化, 調整環(huán)境管制和企業(yè)污染參數, 比較新、 舊均衡狀態(tài)下基金參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不同。結合前文分析, 本文提出基金、 企業(yè)、 政府在基金綠化進程中參與環(huán)境治理的方式和程度, 如基金為了資產配置而評價企業(yè)綠色水平時所采用的方法、 計算模型等。以上正是環(huán)境多中心治理實踐中, 基金、 企業(yè)、 政府和市場其他主體可能參與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基本邏輯。
六、 結論
企業(yè)是經濟社會體系的細胞, 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水平決定著環(huán)境治理的總體成效。來自我國的政治經濟分析和檢驗表明, 不同的政治、 行政制度、 法規(guī)政策引起的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效果不同(唐國平等,2013;Ward等,2014;沈洪濤和馮杰,2012)。環(huán)境經濟分析表明, 測度環(huán)境物品價格并權衡經濟收益與環(huán)境成本, 合理選擇政策可以緩解環(huán)境負外部性。命令控制型、 經濟激勵型等環(huán)境政策給予地區(qū)或企業(yè)在技術創(chuàng)新、 投融資和減排上的約束或激勵(Greenstone等,2012;包群等,2013;李青原和肖澤華,2020)。但是, 上述文獻也指出, 管制成本過大導致了環(huán)境管制對對象、 強度選擇的困境。考慮到以政府為主體的環(huán)保投資及環(huán)境治理將無法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Ward等,2014), 重新審視市場主體的自生能力(林毅夫,2008)、 探尋市場解決方案就顯得尤其重要, 如科斯協(xié)商模式(Coasian bargain)下中國近年來碳排放交易的實踐和發(fā)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進一步關注環(huán)境社會理論中“環(huán)境關心”“生態(tài)現代化”對社會主體環(huán)境意識的強調(Dunlap和Van Liere,1978;Buttel,1987;洪大用,2012), 市場層面的專業(yè)化投資及環(huán)境技術創(chuàng)新所帶來的效率提升, 會從一個企業(yè)到企業(yè)所處的行業(yè), 再擴散到整個社會, 將打破環(huán)境治理的“政府—企業(yè)”二元模式, 轉向“政府、 企業(yè)和社會投資者”多中心模式。基金銜接了社會投資者和企業(yè), 因此考察基金對社會投資者的引導、 綠色基金在資源配置中的能動作用也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
鑒于我國目前社會公眾特別是對公募基金的綠色關注普遍增加, 以及他們參與企業(yè)治理已成為環(huán)境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 因此需要進一步思考基金市場綠化過程中環(huán)境公共治理的現實路徑和意義。中國基金綠化的現狀和動因是什么?基金綠化在中國如何促進企業(yè)的環(huán)境績效?綠色基金網絡對于企業(yè)、 行業(yè)環(huán)境決策的信息提供具有怎樣的優(yōu)勢?相關市場主體和政府在基金綠化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未來針對相關問題的回答將為中國綠色基金的規(guī)范化成長、 政府部門科學引導綠色基金的發(fā)展提供有效的借鑒。
【 注 釋 】
① 習近平總書記于2022年10月16日做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時,首次提出了“六個必須堅持”,即: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tǒng)觀念,堅持胸懷天下。這“六個必須堅持”系統(tǒng)闡明了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世界觀、立場觀點方法。對于“新發(fā)展理念”中的“綠色”發(fā)展,同樣需要結合我國環(huán)境治理中的問題,結合我國實踐經驗系統(tǒng)地進行思考和解答。
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生態(tài)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提出“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確立了中國發(fā)展綠色金融的政策框架。
③ 本文所指的綠色基金,從其轉變?yōu)樵摲N基金的過程來講又可稱為“基金綠化”。按照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yè)協(xié)會的《綠色投資指引(試行)》(2018),基金綠化是傳統(tǒng)公募基金調整投資目標和策略的現象,以及公募基金成立時名稱中含有綠色、環(huán)保、節(jié)能、新能源、循環(huán)經濟等字樣的狀況。
④ 總體而言,企業(yè)利益相關者的壓力、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獲取引起了企業(yè)對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視和解決,環(huán)境績效提升進而帶來財務業(yè)績的提高。當然,有財務實力的企業(yè)更容易進行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
⑤ 在研究中,即使不考察股東方案的情況,也可以通過基金持股的水平或類型對基金的監(jiān)督作用進行考察,如李青原和時夢雪(2018)考察監(jiān)督型基金對盈余質量影響時采用Fich等(2015)的思路,取基金投資組合中排前10%的企業(yè)樣本,將其定義為監(jiān)督型基金。
⑥ 早期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在企業(yè)社會責任業(yè)績提升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Graves和Waddock,1992;Greening,1999)。
⑦ 機構投資者會支持與社會責任投資相關的創(chuàng)新活動,助推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Chen等,2006;Butler和Lamb,2018)。
⑧ 社會網絡是一種包含大量行動者并由他們相互關聯(lián)而形成的社會結構,組織、個人往往內嵌于這種覆蓋廣、層級多的多重關聯(lián)之中。
⑨ 除了本文所關注的與決策相關的同群效應,學者們同樣發(fā)現環(huán)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同群效應。Tomar(2019)指出,當企業(yè)的披露存在較多的同群企業(yè)的影響時,企業(yè)管理者會將同群企業(yè)的披露作為學習的標桿,披露管制下該企業(yè)的溫室氣體的排放會有更大幅度的減少。
⑩ 環(huán)境關心量表(NEP),是一種針對環(huán)境社會問題面向社會公眾的調查工具,通過市場調查,基于問卷數據,可以有效揭示社會投資者的需求,特別是他們的環(huán)境關心狀況(肖晨陽和洪大用,2007)。
? 基于外生市場收益CAPM的Jensen Alpha估值、基于內生競爭對手的“業(yè)績排名”(前期業(yè)績低于該基金的基金數占所有基金的比例)均可用于對基金異常回報的測度。
? 對于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的評估,已有研究通常采用ISO 14031框架、“環(huán)境效益—EEI”方法進行計算。
? 張方方和陳峰(2018)采用基金歷史業(yè)績和12個主流財經網站對基金經理的正面報道作為聲譽變量,研究發(fā)現基金經理的聲譽越高,為基金帶來的資金流量越大,資金流量對前期業(yè)績的敏感性也越強。
? 合法性是指在一個由社會建構的規(guī)范、價值和信念體系中,一個實體的行為被認為是可取的、恰當的一般性感知和假定。按照Suchman(1995)的分類,合法化過程涉及意向性的和實質性的,在實體環(huán)境聲譽的維持方面,意向合法性的解釋被我國的研究者所認可,強調實體為了迎合社會需要而構建其合法性。
? 按照Cao等(2019)的研究,可以通過計量存在共同持股基金的樣本企業(yè)的環(huán)境業(yè)績(或生態(tài)效率)的均值(或被持股企業(yè)所在行業(yè)的均值)測度同群環(huán)境壓力,并進一步檢驗不同壓力分組下基金持股、基金網絡中心度對被持股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的效應。
? 我國歷來重視央企、國企引導下的企業(yè)自治。改革初期我國普遍采用國有企業(yè)自治的方式,1993年工業(yè)污染防治會議后采用了政府集中治理的方式。
? 近兩年,我國試行并成功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僅2020年12月29日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發(fā)布《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總量設定與分配實施方案(發(fā)電行業(yè))》《納入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名單》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以來,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和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發(fā)布了10多項方案、辦法或通知。按照中央的總體部署,自2020年12月29日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出臺的《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總量設定與分配實施方案(發(fā)電行業(yè))》《企業(yè)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核查指南(試行)》《碳排放權登記管理規(guī)則(試行)》《關于開展重點行業(yè)建設項目碳排放環(huán)境影響評價試點的通知》等陸續(xù)發(fā)布,對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的推進、排放報告、排放核算、環(huán)境影響評價、數據質量監(jiān)督等工作做出規(guī)范。與此同時,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等部門也通過節(jié)能降碳相關規(guī)章,助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huán)的經濟體系、推動新型儲能快速發(fā)展、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嚴格能效約束推動重點行業(yè)節(jié)能降碳等。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奧斯特羅姆著.余遜達,陳旭東譯.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
包群,邵敏,楊大利.環(huán)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嗎?[ J].經濟研究,2013(12):42 ~ 54.
蔡宏標,饒品貴.機構投資者、稅收征管與企業(yè)避稅[ J].會計研究,2015(10):59 ~ 65.
陳潭.第三方治理:理論范式與實踐邏輯[ J].政治學研究,2017(1):90 ~ 98.
陳運森,謝德仁.網絡位置、獨立董事治理與投資效率[ J].管理世界,2011(7):113 ~ 127.
方先明,那晉領.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公司綠色創(chuàng)新溢酬研究[ J].經濟研究,2020(10):106 ~ 123.
洪大用.經濟增長、環(huán)境保護與生態(tài)現代化——以環(huán)境社會學為視角[ J].中國社會科學,2012(9):82 ~ 99.
孔東民,林之陽.企業(yè)社會責任、公司價值和基金業(yè)績[ 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62 ~ 72.
李青原,時夢雪.監(jiān)督型基金與盈余質量——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南開管理評論,2018(1):172 ~ 181.
黎文靖,路曉燕.機構投資者關注企業(yè)的環(huán)境績效嗎?——來自中國重污染行業(yè)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金融研究,2015(12):97 ~ 112.
林毅夫.經濟發(fā)展與轉型—思潮、戰(zhàn)略與自生能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梁鑫鑫,危平.中國股票市場“綠化”投資組合的策略選擇研究[ 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49 ~ 62.
馬駿.論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 J].金融論壇,2015(5):18 ~ 27.
馬文超,唐勇軍.省域環(huán)境競爭、環(huán)境污染水平與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 J].會計研究,2018(8):72 ~ 79.
沈洪濤,馮杰.輿論監(jiān)督、政府監(jiān)管與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 J].會計研究,2012(2):72 ~ 78.
沈洪濤,黃楠.政府、企業(yè)與公眾:環(huán)境共治的經濟學分析與機制構建研究[ 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8 ~ 26.
唐國平,李龍會,吳德軍.環(huán)境管制、行業(yè)屬性與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 J].會計研究,2013(6):83 ~ 89.
肖晨陽,洪大用.環(huán)境關心量表(NEP)在中國應用的再分析[ J].社會科學輯刊,2007(1):55 ~ 63.
星焱.責任投資的理論構架、國際動向與中國對策[ J].經濟學家,2017(9):44 ~ 54.
楊鳴京,程小可,李昊洋.機構投資者調研,公司特征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績效[ J].當代財經,2018(2):84 ~ 93.
張方方,陳峰.基金經理聲譽與資金流量——基于基金歷史業(yè)績與互聯(lián)網媒體報道的研究[ J].南方金融,2018(12):41 ~ 52.
張強,董佳,劉善存.綠色基金投資風格漂移與基金業(yè)績評價[ 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157 ~ 167.
祝敏,寧金輝,苑澤明.機構投資者異質性、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環(huán)保投資[ J].金融發(fā)展研究,2019(7):12 ~ 20.
Bailey M., Cao R., Kuchler T., Stroebel J..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8(6):2224 ~ 2276.
Baloria V. P., Klassen K., Wiedman C. I.. Shareholder Activism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Initiation: The Case of Political Spending[ 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8(2):904 ~ 933.
Barber B. M.. Monitoring the Monitor: Evaluating Calpers' Activism[ J].Journal of Investing,2007(4):66 ~ 80.
Bauer R., Koedijk K., Otten R..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Ethical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and Investment Style[ 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5(7):1751 ~ 1767.
Butler F. C., Lamb N. H..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rms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J].Business and Society,2018(7):1374 ~ 1406.
Buttel F. H.. New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7(13):465 ~ 488.
Campbell C. J., Gillian S. L., Niden C. M..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Shareholder Proposals: Lessons from the 1997 Proxy Season[ J].Financial Management,1999(1):89 ~ 98.
Cao J., Liang H., Zhan X.. Peer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Management Science,2019(65):1 ~ 17.
Chakravarthy J., DeHaan E., Rajgopal S.. Reputation Repair after a Serious Restatement[ J].Accounting Review,2014(4):1329 ~ 1363.
Chen T., Dong H., Lin C..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0(2):483 ~ 504.
Chen Y. S., Lai S. B., Wen C. T.. The Influence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n Corporate Advantage in Taiwan[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4):331 ~ 339.
Clark G. L., Salo J., Hebb 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hareholder Acti-
vism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US Corporate Annual Meetings, Campaign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2001-04[ 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2008(6):1370 ~ 1390.
Climent F., Soriano P.. Green and Good?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US Environmental Mutual Fund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2):275 ~ 287.
Cooper M. J., Gulen M., Rau P. R.. Changing Names with Style: Mutual Fund Name Changes and Their Effects on Fund Flow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2825 ~ 2858.
David P., Bloom M., Hillman A.. Investor Activism, Managerial Responsiveness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1):91 ~ 100.
Dimson E., Karakas O., Li X.. Active Ownership[ 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5(12):3225 ~ 3268.
Dunlap R. E., Van Liere K. D.. 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78(4):10 ~ 19.
Dyck A., Lins K. V., Roth L., Wagner H. F.. 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Dr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9(3):693 ~ 714.
Espenlaub S., Haq I. U., Khurshed A.. It's All in the Name: Mutual Fund Name Changes after SEC Rule 35d-1[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7(84):123 ~ 134.
Fich E. M., Harford J., Tran A.. Motivated Monitor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ortfolio Weight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21 ~ 48.
Graves S. B., Waddock S. A.. Response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s Proceedings,1992(1):338 ~ 342.
Greening J..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Type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5):564 ~ 576.
Grennan J. P.. Dividend Payments as a Response to Peer Influe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8(3):549 ~ 570.
Grewal J., Serafeim G.. Research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Foundations and Trends(R) in Accounting,2020(2):73 ~ 127.
Harjoto M., Hojejo 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SR Nexu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45 ~ 67.
Heinkel R., Kraus A., Zechner J.. The Effect of Green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Behavior[ 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1(4):431 ~ 449.
Ji X., Zhang Y., Mirza N., et al.. The Impact of Carbon Neutrality on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Equity Mutual Funds in BRIC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1):113228.
Kaustia M., Knüpfer S.. Peer Performance and Stock Market Entr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2):321 ~ 338.
Krüger P.. Corporate Goodness and Shareholder Wealth[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5):304 ~ 329.
Leary M. T., Roberts M. R.. Do Peer Firms Affect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4(1):139 ~ 178.
Monks R., Miller A., Cook J.. Shareholder Activism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 Study of Proposals at Large US Corporations[ J].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04(2-4):317 ~ 330.
Ozsoylev H. N., Johan W., DeNiz Y. M., et al.. Investor Networks in the Stock Market[ 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5):1323 ~ 1366.
Pool V. K., Stoffman ?N., Yonker S. E.. The People in Your Neighborhoo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Fund Portfolio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5(6):2679 ~ 2732.
Proffitt W. T., Spicer A.. Shaping the Shareholder Activism Agenda: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Global Social Issues[ J].Strategic Organization,2006(2):165 ~ 190.
Qi L., Wang L., Li W.. Do Mutual Fund Networks Affe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0(2):1040 ~ 1050.
Serafeim G.. 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Investor Clientele[ 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5(2):34 ~ 51.
Serafeim G.. Investors as Stewards of the Commons?[ 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8(2):8 ~ 17.
Suchman M. C.. Management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3):571 ~ 610.
Tkac P.. One Proxy at a Time: Pursu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Sharehol-
der proposals[ J].Economic Review,2006(91):1 ~ 20.
Ward H., Cao X., Mukherjee B.. State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Gap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4(3):309 ~ 343.
Williamson O. E.. Assessing Contract[ 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85(1):177 ~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