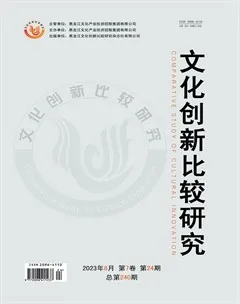文化自信視域下英語視聽說教材的文化呈現分析
賀紅艷,陳秋麗,謝夢羽
(1.中原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河南鄭州 450007;2.廣州新華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 510000;3.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廣東廣州 510420)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上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做貢獻的中國’。”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以及國際交流合作的不斷增多,外語教育擔負著“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神圣使命。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教材是課堂教學的重要載體,是外語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的外語教材須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呈現,以強化學生文化自信,了解中外文化差異,增強文化素養,不斷提升學生“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國際傳播能力。鑒于此,本研究依據張虹、李曉楠研制的《英語教材文化呈現分析框架》,對我國出版的一套英語視聽說教程1—4 冊的文化內容呈現進行標注統計,通過統計結果分析探討,為該套教材的后期修訂及教師合理化使用該套教材提供建議思路。
1 相關文獻回顧
1.1 英語教材相關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英語教材研究主要分為理論研究、實證研究和綜述研究3 類,其中以理論研究最多。實證研究主要圍繞教材編寫、教材建設與研發、教材使用、教材內容分析、教材評估等方面展開,其中教材內容分析在實證研究占比最大,分為語言類內容和非語言類內容分析。孫有中等從課程思政視角下探討高校外語教材設計的思政融入路徑[1-2]。徐錦芬、劉文波從國家安全視角探究外語教材建設的具體路徑,并圍繞目標設定、教材選材、活動設計三大環節探討外語教材建設如何完成服務于國家安全的重要使命[3];兩位學者又從教材使用取向、教材使用策略及行為和教材使用影響因素3 個方面評述外語教材使用的分析框架,并提煉相關研究主題[4]。徐鷹等依托具體教材具體闡述教材編寫理念與特點[5]、外語教材建設和教學設計中的文化認同[6]、外語教材編寫中的課程思政元素融入[7]等。程曉堂、趙笑飛指出我國外語專業語言類教材存在語言輸入量不足、語言素材質量不高、重語言知識輕語篇內容、練習多語言實踐活動少等問題,進而探討編寫外語專業語言類教材的方式與路徑[8]。
總體來說,雖然我國外語教材研究不斷發展,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但是論文數量整體偏少,研究視角單一、片面,研究內容不夠系統,研究范式以科學實證范式較多,人文理解研究范式較少[9]。
1.2 英語教材文化呈現分析研究
教材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使學生更好履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的時代責任,外語教材是關鍵要素。梳理和評析外語教材的文化呈現對文化教學至關重要。目前,針對英語教材中文化內容的分析主要從文化類型、文化內容的呈現方式和教材評價理論3 個視角展開。吳曉威等基于Cortazzi &Jin 的文化地域維度,具體闡述了人教版高中英語教科書母語文化內容缺失的表現,即英語課程標準中“文化意識培養目標”制定偏向性嚴重,教科書中母語文化內容比例嚴重不足,母語文化內容呈現系統性缺失和時代性缺失,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母語文化的輸入缺失[10]。張虹、于睿選取4 套大學英語教材的第一冊對之文本內容分析,發現4 冊教材均不同程度地呈現了中華文化,主要涵蓋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呈現方式以隱性呈現為主[11]。王熔熔、李晨通過對比中西方文化在大學英語教材中的呈現方式發現,教材中呈現中國文化內容的欄目數量少,中國文化內容呈現的模態形式較為單一。中西方文化內容在呈現方式上的不同確實導致了兩者在學習效果上的不同,加劇了“中國文化失語”現象[12]。
綜上所述,英語教材中的文化呈現研究缺乏系統性和時代性。英語教材尤其是高等階段的英語教材對中華文化的呈現較為匱乏,且存在中華文化呈現不夠全面、碎片化的特點,多以隱形方式呈現[13]。
2 研究思路與流程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出版的一套英語視聽說教程為研究對象。該教程共包括4 冊,每冊圍繞自然、生命、科技、未來、文學、藝術、哲學、神話、價值觀、電影、節日、家庭、婚姻、性別、環境保護、網絡生活、史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學、新聞學等不同主題展開。該教程每冊包含10 個單元,每單元分為Session One 和Session Two 兩節,每節含有Part I、Part II 和Part III3 個部分。Part I 和Part II 均為根據相應的視聽輸入材料完成指定的聽力或口語任務;Part III 通過呈現一定的情境、背景知識或視聽素材使學生完成相應的討論或口頭匯報,側重學生的口語輸出。因為部分單元的Part III 并未提供視聽材料,本研究主要分析各單元每節的Part I 和Part II 兩部分,共計320條視聽材料。
2.2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兩個問題展開:
(1)該教程中不同地域文化的呈現比例如何?
(2)該教程中不同類型文化的呈現比例如何?
2.3 研究框架
張虹、李曉楠借鑒國內外英語教材中的文化呈現研究,通過對我國4 套大學英語教材和3 套高中英語教材的多元文化教學項目進行標注統計,圍繞文化呈現內容和呈現方式兩個維度,研制了《英語教材文化呈現分析框架》(以下簡稱《框架》)[14]。該《框架》將文化呈現內容按地域分為:(1)學習者的母語文化;(2)目標語國家文化;(3)國際文化;(4)共有文化。具體來說,母語文化指“中華文化”;目標語國家文化即“內圈國家文化”,指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文化(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愛爾蘭);國際文化指“所有外圈、延展圈國家即其他不將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的文化”;共有文化指“不存在較為顯著的國家或民族背景、沒有明顯地域差異的文化”。就文化類型而言,該《框架》從英語教材主題內容出發,嘗試兼顧國內外分類方式的不同特點,將文化分為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s)、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文化觀念(cultural perspectives)、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ies)和文化人物(cultural persons)5 個類型(如表1)。其中,文化產品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所創造的產品,是最容易認知的文化的物質形態,包括物質產品、建筑和藝術形態,是文化教學最直接的內容”;文化實踐指“人類生活和行為方式,包含節日習俗、行為準則等”;文化觀念包括感知、信仰、價值和態度,決定了文化產品和文化實踐,比如儒家思想、名人名言等;文化社群指“根據民族、語言、性別、種族、宗教、社會經濟階層等不同群體劃分的文化,是國家/民族等層面的文化”;文化人物指“某一文化群體的知名人物”。
此外,《框架》依據文化出現在教材中的位置將文化呈現方式界定為顯性和隱性。其中,顯性方式指文化內容在語言輸入材料部分呈現; 隱性方式指文化內容在練習中呈現。《框架》為呈現方式賦予1 到10 分不等的權重,用權重與頻次相乘的方式來看文化呈現的強度。因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英語視聽說教材,該教材以輸入材料為主,沒有專門的輸出練習部分,故本研究僅采用本框架的“文化地域”與“文化類型”分類來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
2.4 數據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3 位成員按照《框架》的文化地域和文化類型兩方面對教材進行編碼。為確保不同編碼者對相同文本獨立編碼的一致性,3 位研究員首先對第三冊Unit One 進行獨立編碼,隨后對比三者的編碼結果。對不一致的編碼,邀請另外兩位同行進行編碼,完成后與三位成員的結果對比,并討論協商至結論一致。試編碼后,本研究的3 位研究員共同完成該教程1—4 冊各單元的正式編碼,并由負責人對編碼進行最終審閱。如有不認同的編碼,3 個首先協商達成一致;不能達成一致的,再邀請同行進行編碼、協商直至一致。
編碼結束后,研究者使用Excel 對文化地域和文化類型進行頻率與占比統計,從而獲得該教程的整體文化呈現情況及各冊文化呈現情況。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不同地域文化的呈現:共同文化占比最大,母語文化占比最小
該教程(1—4 冊)共320 條輸入材料,不同地域的文化呈不均衡呈現,如表2所示。其中,涉及共同文化的內容最多,共152 條,占比47.50%;目標語國家文化次之,共103 條,占比32.20%;涉及國際文化和母語文化的內容較少,其中涉及母語文化的內容僅24 條,占比7.50%。由此可見,4 冊教材側重共同文化和目標語國家文化的呈現,對母語文化的關注較低。

表2 教程(1—4 冊)不同地域文化的呈現情況
每冊教材不同地域文化的呈現也各有不同,如表3所示。4 冊書中,第一、三、四冊教材中文化地域的分布一致,均是共同文化占比最多,目標語國家文化次之,母語文化最少,分別為1 條、3 條和0 條,存在明顯的母語文化呈現缺失; 第二冊中各區域文化的呈現較為均衡,呈現的母語文化在四冊中也最多,共20 條,占該教程“母語文化”出現頻率(24 條)的83.33%。第二冊以“文化”為主題,對中西方文學、藝術、哲學、神話、價值觀等進行探討,每單元都有中國文化的呈現。

表3 每冊教材不同地域文化的呈現情況
3.2 不同類型文化的呈現:文化觀念占比最大,文化社群占比最小
在4 冊教材的320 條輸入材料中,涉及文化觀念的材料共131 條,占比40.94%;文化實踐的次之,共105 條,占比32.81%;文化社群的占比最少,僅有8 條,占比2.50%,如表4所示。

表4 教程(1—4 冊)不同類型文化的呈現情況
分冊來看,如表5所示。第一、二、四冊不同文化類型的呈現較為一致,占比最高的均為文化觀念(33.75%,40.00%,57.5%); 文化社群占比最小(6.25%,0%,3.75%)。第三冊教材中文化實踐的占比最大(61.25%),約為文化觀念(32.50%)的二倍,占該教程“文化實踐”出現頻率(105 條)的46.67%。這與該冊教材的主題有關:本冊書以“觀察社會”為主題,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處理婚姻、性別、危機、環保、網絡等的具體實踐。就“文化產品”而言,第二冊書涉及“文化產品”的材料最多,共28 條,占該教程“文化產品”出現頻率(51 條)的54.90%。這也與該冊教材的主題“品鑒文化”有關,該冊教材通過介紹不同文化的文化、藝術、哲學等具體文化產品,引導學生進行跨文化思辨和批判性品鑒。就“文化觀念”而言,第四冊教材涉及該類型的材料最多,有46條,占該教程 “文化觀念” 出現頻率(131 條)的35.11%。這與第四冊教材的主題“走進學術”有關,側重呈現不同文化下人們在史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領域的不同文化觀念。第一冊教材的各文化類型呈現相對平衡,5 種類型均有不同比例的涉及,較好地契合了該冊教材的主題“聆聽生活”。

表5 每冊教材不同類型文化的呈現情況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該教程側重共同文化及目標語國家文化的呈現,呈現的主要文化類型為文化觀念及文化實踐,存在一定程度的母語文化呈現缺失,在“文化社群”的呈現上也偏少。此外,不同地域和不同類型的文化在該教程中的呈現與每冊教材的主題緊密相關。第二冊以“品鑒文化”為主題,故而較大比重地呈現了我國藝術、文學、神話等具體的文化產品;第三冊以“觀察社會”為主題,著眼點和側重點落在了“社會實踐”上;第四冊圍繞“走進學術”這一主題,著重呈現不同文化背景下對人文社科核心問題的文化觀念。
教材價值的實現離不開教材的使用過程。然而沒有一本教材是完美的。教師作為教材的主要使用者,要避免“過度依賴教材”和“完全拋開教材”兩種極端做法。教師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遵循“選、調、改、增”的操作策略對現有教材進行重構;以“促進教學目標達成”為原則,從共享慕課資源和海量網絡資源中甄選與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匹配度高且優質的教學材料,或錄制微課等形成課程獨有的教學材料包,與現有教材形成互補,從而讓教學材料更有效地服務于學生綜合運用英語能力的提高,更有力地促進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讓教學材料重構助力課堂教學質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