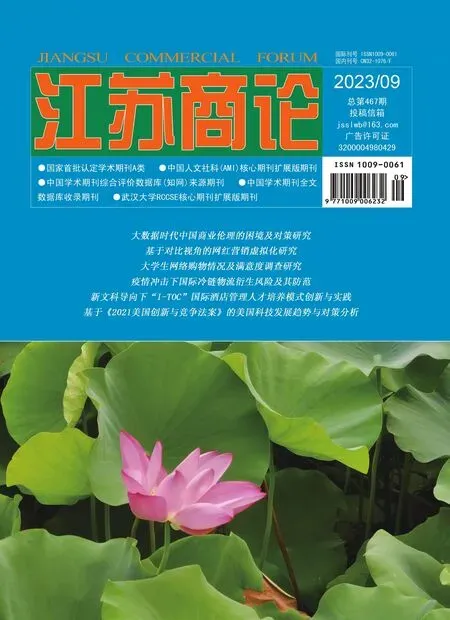基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高等教育學科調整的實證研究
劉運生
(湖北工業大學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68)
一、引言
在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 如何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需要,并通過與區域互動發展, 實現21 世紀中葉中國經濟社會綜合實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跨越式發展,是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知識經濟的到來給高等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 具體而言,包括培養創新人才、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擴大培養規模、提高勞動力整體素質、變革人才培養模式、優化創新教育環境和科學研究的挑戰等①。 鑒于現階段中國同一省市間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并且不少地區存在區域產業結構嚴重失調的現象。 因此,如何利用高等教育的學科調整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促進發達省市落后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解決人口輸送問題,從而促進中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仍然是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過運用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應用統計學和教育經濟學等學科的知識,以江蘇區域高等教育作為研究對象,以系統模型為基礎,研究內部系統與發展激勵的互動系統,設計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高等教育實施系統,實現中國發達省市落后區域的跨越性發展,從而促進發達省市落后區域的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二、相關理論概述
(一)相關理論基礎
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系統培養人才的最后環節,完成此階段的學習就可以直接進入市場參與高品質生產,創造財富,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②。 按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接受教育的層次越高,勞動所能創造產品價值就越大,隨之就需要更多具有較高素質各類人才駕馭生產力③。 20 世紀60 年代初,丹尼森在分析影響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運用統計法對各種因素進行分析時指出使經濟發展波動的因素有很多,但影響程度最深的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在此他將從業者的教育程度本質劃歸為人力資本的投入。 著名學者Cobb 和Pual Doulas 聯合討論經濟投入和產出關系時締造的生產函數,被稱之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公式④。
(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與高等教育學科調整的關系
中國學者謝泗薪、李曉陽在研究中闡述了高等教育學科調整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他指出,高等教育學科調整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他認為,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中國各地高校應該加強校際交流,構建多元化學科體系。 在保持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多樣性的過程中,不同形式和層次的高等教育都有相應的質量控制形式,必須滿足一定的質量標準⑤。 蔣華林認為,高校作為人才發展領域變革和發展的推動者,通過調整學科結構,可以加速區域經濟增長和地方實力。 他還指出,事實上,特定區域的高校學科結構并不直接與當地經濟掛鉤;特定區域的高校無法保障區域經濟的發展⑥。 然而,區域高等教育學科的調整是當地企業發展的參謀點與推動劑,能夠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創造巨大價值。
三、江蘇省高等教育學科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
(一)指標選取
本文構建了反映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相關指標,遵循指標科學性、互操作性、系統性以及中介性的基本原則,構建高等教育學科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相關性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高等教育學科調整體系由6 項組成,包括:專利申請許可證人數(人)、普通教育機構數(高校)、畢業生數(人)、高等教育專職教師數(人)、專家技術人員數(人)以及高校學生數(人,學科調整后。 而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由9 個指標組成,即: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均GDP(元)、衍生產業占GDP 的比重(%)、人均消費支出(元)、高等教育占GDP 的比重(%)、人均財政收入(元)、農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以及固定資本比率(%)。
(二)因子分析
首先對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進行因子分析,要確定此數據集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必須首先對數據運行進行kmo 和Bartlett-ball 測試⑦。 經過運用spss19.0 統計分析軟件對數據加以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1、2 所示:三個kmo 值均大于0.5。 通常認為變量之間的偏相關很強,Bartlett 球形概率檢驗為0.000,低于顯著性水平0.07。同時,綜合方差損失系數較小,說明該數據集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表1 KMO 以及Bartlett 的檢驗

表2 公因子方差
然后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因子,用最大偏差法進行比較分析⑧。結果如表3、4 所示。表3 顯示了初始自我貢獻、 分配貢獻系數和累積貢獻率的偏差,反映了高等教育水平,并區分了公允價值大于3 的兩個因素。累積貢獻偏差的兩個分量之比為96.668%,即總變異量的96.668%,提取F3 和F4 的第一個公共元素。 表4 顯示,這些變量對該區域高校水平有影響。該因子的貢獻率為89.495%,是影響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主要評價指標。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高校畢業生數量和專利申請面臨較大壓力,這反映了特定區域的教育質量。 該因子的偏離貢獻率為46.973%,也是影響特定區域高校發展的重要指標。

表3 解釋的總方差

表4 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圖
最后,計算因子得分。 根據系數指數,將比率轉換成方程式,計算江蘇省35 個區域的高等教育總水平,如表5。 為得到各區域三級水平的綜合評價,利用各因素的主要貢獻度計算各區域三級水平的綜合水平,即第一資本的權重,F3 系數為89.835%,第二大權重系數為46.973%, 高等教育綜合類的計算公式為:高等教育總水平=89.835%xf3-i-46.973%xf4。

表5 2020 年江蘇省高等教育水平綜合得分及排序
(三)研究結果
綜合上面的模型模擬及實證檢驗,再用同樣的模型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因子分析。 江蘇省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可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次的差異為0,稱為“高度同質化”;第二層的差異是[-3,-3],定義為“協調”;第三級的差異在[-5,-5]之間,定義為“基本協調”;第四級的差異在[-7,-7]之間,定義為“不協調”;第五級差異大于7 或小于-7,定義為“非常不協調”。 在表6 中,我們可以看到,2020 年江蘇省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有多個層次。 參考科學家此前的研究,將評價中的負差定義為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將正差定義為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

表6 江蘇省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程度
四、江蘇省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產業結構協調的實證分析
根據新西蘭經濟學家費雪的產業分類方式,產業結構分為初級產業、衍生產業和高校產業。 中國普遍反映為標準產業的產業結構⑨。 其中,學科發展分為理學、工學、文學、經濟學、哲學、教育學以及農學等33 個門類。
(一)第一產業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的協整性檢驗
1.變量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運用的樣本數據為2016—2020 年,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局網站。 本研究為消除經濟波動的數據影響,對江蘇省工業總產值(GDP)的初步數據進行了統一。同時,為避免數據波動的影響,原始數據的對數值分別為3nGDP 和3nT,其中一階差表示為D3nGDP 和D3nT;二階差表示為DD3nGDP 和DD3nT 和DD3n, 初步數據如表7 所示。 本次采用EV Industrial EWS8.0 統計軟件版本進行數據處理。

表7 2016—2020 年農業在校生數與第一產業產值及其指數
2.單位根檢驗。要消除邏輯錯誤和回歸問題,首先要測試靜態變量。 單位根檢驗是統計檢驗中最常用的檢驗方式, 通常是檢驗階數穩定性較好的方式。 一般而言,雖然字符串不穩定,但是經過一階或二階差分后可以轉換為平穩的字符串。 EV EWS 軟件中有三層選項:單位根檢驗的等級、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 如果檢驗水平沒有被拒絕,而是根據一階差分拒絕原假設,那么這個序列可以認為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就是單位根。 如果一階差分后仍然拒絕原假設,那么就有必要執行二階差分,因此需要多次嘗試執行單位根測試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檢驗結果表明,DD3nGDP 在3%的顯著性水平和常數DD3nT,這表明3nGDP 和3nT 是I(4),那么可以進一步測試。
3.變量的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整合關系是一種穩定、長期的關系,然而這種關系不一定是因果關系。Granger 因果檢驗主要是剔除時間序列3 和4 的演化。 如果用序列3 和4 之前的值來聯合預測序列4, 預測結果比用序列4 之前的值準確。 表中顯示,在30%的顯著性水平上, 格蘭杰商品產值的增加是由于農業學生人數增加。如今,高校畢業生較少參與核心行業, 大多數在畢業后攻讀研究生。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較多。 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村的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高校研究生數量得到提高, 同時農業學生數量有可能相應減少。再分別對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高等教育學科結構作類似的協整性檢驗,可得到相應的結論。
(二)實證結果
從回歸方程結果可以看出,基于三大產業的格蘭杰因果關系,理工科等學科的學生人數正在帶動相應的產業價值上升。 然而農業學科專業和學生數量的增加,對于促進第一產業生產價值發展的效果并不顯著。 理工科學生畢業后通常都具有一定的技術技能, 所以他們涉及的行業更多與第二產業有關, 同時也可以為其他產業的發展增加附加價值。然而,文科學科不同于理工科,文科生價值的創造具有不顯著的特征,文科學科創造的價值一般是間接的。 由于在技能掌握等方面的不同,文科生大多從事服務業,或者選擇自主創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第三產業的創新與發展。 而對于農業學科學生而言,他們往往不愿意參與第一產業的勞作。 因此,諸多畢業生從事第三方產業的勞作,無法有效為農業的發展提供相應價值(表8)。

表8 產業結構與學科結構協整回歸結果
綜上,學科結構調整要充分發揮對經濟發展的服務作用。 首先要尊重市場規律,以社會投資與辦學效益的最優對接為導向, 運用最佳決策的可能性,順應行業結構,構建科學的預測體系。 預測產業的發展,并為高校的學科結構安排提供參考。
綜上所述, 作為近年來發展迅速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具有良好的經濟實力與區位優勢,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創造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也是高等教育始終走在全國前列的重要原因。 江蘇省一直將“科教興省”作為戰略發展目標之一。 核心使命是加快教育發展,壯大江蘇教育體系,強化當地人力資源的建設。 然而,由于發展時間較短,區位間發展差距較大。 為此,在新時期,江蘇省需要對高等教育學科進行調整,使之與區域經濟發展協調。
注釋:
①鄭鳴,朱懷鎮.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7(4):6-7.
②張瑜,李書華.金融開放度與宏觀經濟波動——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實證研究[J].財經論叢,2012,160(5):52-57.
③李鋒,朱燕空,張偉良.河北省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中國成人教育,2011(13):3-5.
④鄭鳴,朱懷鎮.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7(04):76-81.
⑤謝泗薪,李曉陽.生產性服務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區的實證[J].商業經濟研究,2019(8):3-6.
⑥蔣華林.區域教育科學研究競爭力實證研究——基于2001—2011年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的統計分析[J].教育發展研究,2013(5):6.
⑦孫虹,魏海麗.基于VAR 模型的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工業技術經濟,2015(10):8-11.
⑧高耀,顧劍秀,方鵬.中國十大城市群主要城市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綜合評價研究——基于107 個城市2000 年和2010 年的橫截面數據[J].教育科學,2013(3):11-13.
⑨郭慶然,丁翠翠.中國“三化”協調發展的區域格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38(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