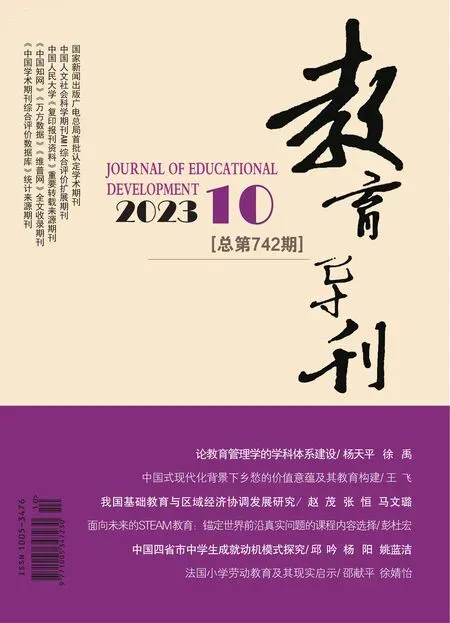我國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趙 茂 張 恒 馬文璐
(1.云南師范大學 泛亞商學院,云南昆明 650091;2.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楊凌 712100)
一、引言
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關系是涉及到基礎教育公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在基礎教育已演化為基本公共服務產品背景下,教育財政成為推動基礎教育發展核心一環,但當前我國城鄉二元化結構特征顯著,經濟發展多級化特征明顯,導致基礎教育財政投入地區差異顯著,這對基礎教育區域均衡化發展形成重大挑戰。現有研究表明:教育賦能下的人力資本邊際收益遞增特征明顯〔1〕,這進一步強化了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動耦合性,即:基礎教育發展提升勞動者素質,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憑借其邊際收益遞增特性,釋放區域經濟發展潛力,增強區域經濟發展動能,這又進一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保障基礎教育財政支出,反哺基礎教育進步,周而復始,教育與經濟的互動耦合作用不斷增強。
國家教育財政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的政策背景下,中西部地區基礎教育失衡是否有效緩解?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二元互動耦合協調發展能力如何?是關系到地區教育、經濟政策制定,基礎教育公平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為此,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利用綜合評價、耦合協調度等模型實證檢驗基礎教育、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二者互動耦合協調發展能力,以期為政府編制基礎教育財政預算,制定地區經濟發展政策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教育與區域經濟“二元化”關系是學術界關注熱點。早期經濟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動因歸結為: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但這不足以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現實情況。隨著經濟理論的發展,人力資本理論應運而生,教育從人力資本維度進入經濟學家的研究視角,這推動了教育經濟學形成與發展,至此,教育經濟理論從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方面不斷推動教育與經濟研究向縱深發展。
研究方法方面,大量學者通過丹尼森法、柯布道格拉斯函數、超越生產函數、盧卡斯學校教育模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GMM與門檻模型、灰色斜率關聯模型等多種實證技術手段,多角度檢驗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研究發現:一方面教育提升人力資本,帶動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教育提供物質基礎,拉動教育進步。研究內容方面,一是教育推動經濟發展方式上,Schultz認為,教育直接推動經濟發展,即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質量,增加人力資本等方式推動區域經濟發展〔2〕;Lucas和杜育紅等指出,教育間接推動經濟發展,即教育通過技術積累、激發創新活力、制度完善等途徑推動區域經濟發展〔3〕〔4〕。二是各教育層次下教育基礎對經濟增長貢獻差異顯著。黃維海等基于中國70年教育數據,實證研究發現:中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相對較高,但下降趨勢明顯,而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步提升〔5〕;王云多以教育人力資本的獨特視角研究發現:經濟越落后地區,基礎教育(含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越大〔6〕。經濟越發達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越大,如:我國中西部地區基礎教育對經濟發展貢獻率顯著高于高等教育。三是不同國家相對發展優勢下,教育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差異顯著。曹淑江指出:擁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其次為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7〕;Baldwin and Borrelli、Ilon和Marquez and Mourelle分別基于美國、韓國和西班牙等發達國家數據的實證研究均發現,教育對推動經濟發展貢獻顯著〔8-10〕。另一部分學者基于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證明,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存在顯著差異,如:南非教育對經濟發展拉動作用小,相反印度教育對經濟發展貢獻顯著〔11〕。
綜上,各教育層次對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差異顯著,且我國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逐步提高,但當前教育與經濟的相關研究成果側重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鮮見。鑒于此,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構建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指標體系,利用綜合評價模型測度二者發展現狀,引入耦合協調度、收斂模型繞開“中介變量”黑匣子,探究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挖掘二者協調發展內在特征,推動二者協調發展,以期拓展教育經濟理論成果,為相關學者提供參考,幫助政府合理編制教育財政預算,為制定經濟、基礎教育相關政策提供支持。
三、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機理分析
基礎教育系統與區域經濟系統互動耦合特征顯著,即:基礎教育供給驅動區域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需求反向拉動基礎教育進步(見圖1)。

圖1 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機理
(一)基礎教育供給驅動區域經濟發展
基礎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增加人力資本的內部機制,激發經濟增長潛力,驅動區域經濟發展〔12〕。如Schultz以人力資本視角切入,研究發現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質量,增加人力資本,提升勞動要素生產率等方式直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13〕。杜育紅等的研究也發現,教育有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引致內外部兩類效應機制作用于經濟增長,一是通過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機制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即:教育提升勞動力知識技能水平,提高勞動效率,增強經濟發展動力;二是教育的外部協調效應機制提升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即:教育通過人力資本機制,促進多生產要素協調作用能力提升,扭轉人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趨勢,這增強了教育、人力資本對經濟運行效率的促進作用,提升了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14〕。陳晉玲等基于教育層次新視角,將教育劃分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大層級,探究教育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發現:中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對較高,但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各層級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差異顯著,經濟越滯后的地區,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高,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明顯,即:我國中西部地區,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高于高等教育;東部地區,高等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基礎教育,這與曹淑江的研究結論保持高度一致〔15〕〔16〕。
(二)區域經濟發展需求拉動基礎教育進步
一是基礎教育逐步演化為一種重要的公共服務,在教育財政體制下,教育財政投入是基礎教育進步的物質基礎。區域經濟發展提升地方財政收入,保障了基礎教育財政投入,進而確保區域經濟穩定發展。朱耘嬋等考慮到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正外部性,繞開人力資本、技術等“中介”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教育財政投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與物質資本投入相比,教育財政投入對區域經濟發展效率的提升更為顯著;與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相比,基礎教育投入對經濟發展貢獻率更大〔17〕。劉玉君等以教育財政投入與經濟增長的動態視角切入,利用系統GMM回歸模型,試圖探究地區教育財政支出與區域經濟增長的二元聯系時發現,教育財政支出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之一,教育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1.135,即:財政教育經費每提升1%,促進區域經濟增長13.5%〔18〕。二是區域經濟增長加速教育領域現代信息技術應用,推動基礎教育發展的結構性優化、地區性優化。閻光才以教育信息技術的視角切入,探究技術革命對教育變革影響時發現:技術革新與技術的加速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教育變革,提升了教育效率,促進了教育模式與方法的優化〔19〕。誠如:早期造紙技術的產生,加速了教育體系化的形成;印刷術的出現變革了教育囿于少部分權貴階層的狀況;現代信息技術的出現,打破了優質教育資源的地域限制、時間限制,加速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均等化進程。周子荷也指出經濟發展帶動信息技術變革與加速技術的普及應用,為教育變革提供契機。三是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生產方式變革(自動化技術普及),轉變了經濟發展對勞動的需求,進而影響基礎教育發展方向〔20〕。袁玉芝和杜育紅考慮到人工智能技術全面應用,將對勞動力技能的需求數量與結構帶來重大變革,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與美國職業信息網絡數據,利用明瑟方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實證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對非程序化技能需求上升,對程序化技能需求下降,這與我國現行“程序化”的認知型教育教學體系相悖,這必然加速“認知型”教育教學體系向“問題型”教育教學體系轉變,將在很大程度上強化學生非程序化技能,增強問題解決能力,提升教育效率〔21〕。Carnoy and Levin也指出:經濟發展加速生產方式變革,推動技術革新,為新技術的普及性運用奠定物質基礎,引發工作崗位與技能要求變化,提升異質性技術需求,造成結構性失業,推進教育變革〔22〕。
上述理論分析可以發現,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雙向關系明顯。一方面,基礎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借助人力資本內部機制,激發經濟增長潛力,驅動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利用基礎教育外部協調機制,增強多生產要素協調作用能力,提升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穩定發展為基礎教育奠定物質基礎,拉動基礎教育進步。同時,其加速了教育領域現代信息技術應用,推動基礎教育發展的結構性優化、地區性優化。更為關鍵的是,區域經濟發展也帶來了生產方式變革(自動化技術普及),轉變了經濟發展對勞動需求,進而影響基礎教育發展方向。綜上,基礎教育供給驅動區域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需求拉動基礎教育進步,二者良性循環實現雙向協調發展。
四、指標體系及模型構建
(一)指標構建及權重賦值研究
基礎教育水平指標體系構建是參考王淑芬等、龔春燕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高中、初中、小學三層面,從教育規模、教育質量等維度,綜合反映基礎教育水平情況〔23〕〔24〕。進一步考慮到我國于2001年正式開始“撤點并校”大量中小學被撤除、合并,以整合基礎教育資源的政策背景結合學齡人口基數的區域差異,確定以每十萬人在校生數衡量教育規模;同時考慮到教師在基礎教育質量提升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5〕,將師生比納入指標體系以測度基礎教育質量。進一步考慮到教育經費的基礎性作用,將生均財政教育經費納入指標體系。區域經濟水平指標體系構建是在參考張芷若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考慮到區域人口基數、區劃面積等因素,將總量指標人均化,從經濟水平、經濟結構、消費水平等三方面共計10指標反映區域經濟綜合發展狀況〔26〕(見表1)。
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以來,黨中央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體系,深化教育綜合改革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為更好分析教育政策實施的成效,本文選取政策推行之前的2012年至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探究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狀況。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3-2020)、《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13-2020)、《各省市區統計年鑒》(2013-2020)、《國民社會經濟發展統計公報》(2013-2020),教育部《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2013-2020)其中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得出。
(二)模型構建
1.綜合評價模型

(1)
為合理確定指標權重,引入熵權法。遵循客觀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合理性等原則,綜合考量層次分析法、優序圖法、專家咨詢法、熵值賦權法、CRITIC、獨立性權重和信息量權重等權重計算法,為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朱喜安等,2015),確定以熵權法對指標賦權。正向指標表示值越大時整體優化效果越好,負向指標反之〔27〕。Pijn表示i項指標j省n年的貢獻度,ei表示指標i的信息熵,Wi為權重,經測度公式(2)(3)得各指標權重(見表1)。
(2)
(3)
2.耦合協調度模型
測度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Cjn、Bjn、Djn分別表示j省n年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的協調度、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α、β為待定系數,由于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同等重要,令α=β=0.5,進一步,結合我國發展實際狀況,遵循科學性、系統性、連貫性等原則,參考楊勝蘇等(2020)的耦合協調度指數測度量表(見表2),為進一步分析、判斷各區域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狀況提供參考〔28〕。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量表
(4)
3.收斂模型

(5)
五、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的實證分析
基于2012-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利用歸一函數(2)、熵值賦權法(3)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并賦權重,進一步利用綜合評價模型(1)測度出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綜合指數,最后利用耦合協調度指數模型(4)度量2012-2019年各區域二者耦合協調發展能力(見表3)。(由于版面問題2013-2018年數據略去)。

表3 2012年與2019年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數
(一)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總體分析
1.時間軸縱向分析
2012-2019年,基礎教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協調發展能力均呈上升態勢,基礎教育水平不斷提升、區域經濟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二者耦合協調發展能力不斷提升(見圖2)。2012年以來,基礎教育水平指數凈增幅約40%,年均增速約為5.5%;區域經濟指數凈增幅約45%,年均增速約為6.5%,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指數凈增幅約為20%,年均增速約為3%,當前已處于優良協調發展階段,二者協調發展能力較強,基本實現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目標,二者間良性循環基本形成。但基礎教育整體水平仍偏低,著力提升基礎教育水平的任務仍任重道遠。

圖2 2012-2019年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指數及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數
2.描述性數據橫向分析
利用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指數及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數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分析近十年來三指數內在變化特征(見表4)。相較2012年,2019年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呈三點新變化。一是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耦合協調指數均顯著增長,這表明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水平進一步提高,二者協調發展能力顯著增強。二是基礎教育水平指數、區域經濟指數及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數的均值大于中位數,表明三者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空間;三指數的標準差、極差均擴大,這表明基礎教育、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的區域絕對差距逐漸擴大。三是基礎教育水平指數與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數的變異系數擴大,區域經濟指數的變異系數縮小,表明基礎教育水平與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的區域相對差距擴大,而區域經濟相對差距縮小,存在地區收斂特征。

表4 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發展指數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3.地區收斂性探析
為進一步檢驗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的收斂特征,引入收斂系數模型(5)對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的地區收斂性特征進行交叉驗證(見圖3)。

圖3 2012-2019年三指數變異系數(左)、σ收斂系數(右)表
可以發現,基礎教育水平指數的變異系數、σ收斂系數均保持上升走勢,驗證了基礎教育水平的區域相對差距擴大,不存在收斂性特征的結論,這與周遠翔等(2019)學者的研究結論高度一致〔29〕。特別地,2016-2018年基礎教育水平的變異系數、σ收斂系數,增速較快,基礎教育水平的區域相對差距明顯擴大。同時,區域經濟指數的變異系數、σ收斂系數均顯著降低,這表明區域經濟的相對差距縮小,地區收斂性顯著,區域經濟暫時落后的地區存在趕超頭部區域的可能。更為關鍵的是,耦合協調度指數的變異系數、σ收斂系數維持在較低水平,這表明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的區域相對差距較小。
(二)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時空探析
1.基礎教育水平時空探析
2012-2019年,我國31省份基礎教育水平穩步提升,但仍保持較低水平,增速區域差異顯著。2012年,天津基礎教育水平全國領先,其余30省份基礎教育水平低,2019年,北京、上海、西藏等17省域基礎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其中,北京基礎教育水平最高,年均增速約為27%,上海、西藏基礎教育水平次之,年均增速約為16%,其余28省年均增速不到5.5%,增速差距顯著,進一步證實了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相對差距擴大的結論。
其原因可能是,北京、上海分別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區域經濟發達,區位優勢明顯、吸引力強,師資力量雄厚,而西藏雖地處西部邊疆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組團式”教育援藏、“西藏班”等模式下,使得西藏可以共享北上廣等沿海地區優質基礎教育資源〔30〕。如西藏生均教育經費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全國第三位,遠高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且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十五年免費教育,入學率大幅提升〔31〕。
2.區域經濟時空探析
近十年來,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絕對差距依然較大,表現出明顯的沿海、沿江(長江)集聚性發展特征。2019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沿海地區率先跨入高水平發展階段,但西藏、甘肅區域經濟依然滯后,水平低;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天津沿海省份與江西、安徽、湖北、重慶沿江省份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由2012年的沿海集聚式發展延伸為沿海、沿江集聚式發展。
3.二者耦合協調度時空探析
2012-2019年,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持續增強,總體跨入優良協調發展階段,協調發展能力強。2019年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等12省域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指數超過0.65,處于優良協調發展階段,協調發展能力強,其余19省份協調發展能力相對較弱(見表5)。

表5 2012年與2019年耦合協調度指數
可見,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呈明顯的空間集聚特性。2012年,僅西藏、云南、貴州、廣西4省處于瀕臨失調發展階段。2019年,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等沿海9省域與新疆、西藏、青海邊疆3省基礎教育水平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強,表現出明顯的沿海,邊疆集聚性特征。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利用綜合評價、耦合協調度、收斂系數等模型測度我國基礎教育水平、區域經濟及二者協調發展能力狀況。
研究發現,一是我國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快速發展,二者協調發展能力不斷增強,但基礎教育水平偏低,區域增速差距持續擴大。傳統基礎教育水平滯后的西藏地區基礎教育發展較快,當前處于較高發展水平。二是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區域間絕對差距擴大、相對差距縮小,地區收斂性顯著,呈明顯的沿海、沿江集聚性發展特征。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沿海省份與江西、安徽、湖北、重慶沿江省份區域經濟水平全國領先。三是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持續增強,總體跨入優良協調發展階段,空間集聚特性顯著。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浙江、江蘇、福建、廣東、海南沿海省域與新疆、西藏、青海邊疆省份,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強,進入優良協調發展階段,并表現出明顯的沿海、邊疆集聚性特征。
(二)建議
一是注重基礎教育公平,扭轉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失衡趨勢。近年來,我國基礎教育快速發展,基礎教育水平明顯提升,但基礎教育水平差距逐漸增大,如:云南、廣西、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區,基礎教育水平低,增速慢,與北京、江蘇、上海、廣東、福建等沿海教育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水平差距持續擴大。由此提出:創新教育幫扶模式,跨區域整合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即:總結現有西藏、新疆的基礎教育成功模式,將現代信息技術與沿海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結合,探索“信息技術+沿海優質教育資源”幫扶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跨區域優勢,整合基礎教育資源,縮小區域間教育資源差異,扭轉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失衡趨勢。
二是加強省際經濟合作,努力形成優勢互補,產業共進,共同繁榮的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物質生產力極大提高,區域經濟相對差距顯著降低,有效緩解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根本矛盾;同時,經濟發展頭部地區逐步由沿海向內陸擴張,表現出明顯的沿海、沿江集聚性發展特征,顯示出區域經濟間的強正向相互作用。由此提出:加強省際經濟合作,充分利用沿江、沿海經濟強省的優勢產業結合中西部地區獨特自然條件與勞動力資源優勢,加快形成優勢互補,產業共進,共同繁榮新局面。
三是打造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示范區,發揮示范區“明星”效應,提升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效能。現階段,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能力顯著強于內陸地區,表現出明顯的沿海、邊疆集聚性。充分利用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集聚性特征,打造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特色示范區,這有助于發揮示范區“明星”效應,增強廣東、上海、江蘇等沿海能力強省的領頭示范作用,探索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新模式,提升基礎教育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效能,增強二者協調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