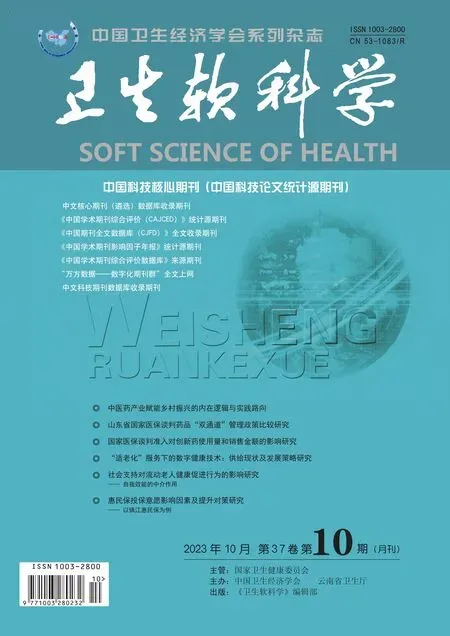2015-2021年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分析
秦曉強(qiáng),王秀麗,王翠平,郭豐勇,何曉晴
(山東省立第三醫(yī)院,山東 濟(jì)南 250000)
近年來,人民群眾的醫(yī)藥費(fèi)用增長明顯,根據(jù)《中國衛(wèi)生健康統(tǒng)計年鑒》數(shù)據(jù),2015-2021年我國公立醫(yī)院門診次均醫(yī)藥費(fèi)用增加36.4%,住院次均醫(yī)藥費(fèi)用上漲32.2%。為控制醫(yī)藥費(fèi)用不合理增加,國家提出了“騰空間、調(diào)結(jié)構(gòu)、保銜接”的醫(yī)療服務(wù)價格改革,2015年10月,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等五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關(guān)于控制公立醫(yī)院醫(yī)療費(fèi)用不合理增長的若干意見》[1](以下簡稱《意見》),提出“總量控制、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控制醫(yī)療費(fèi)用總量增長速度,合理調(diào)整醫(yī)療服務(wù)價格”的目標(biāo)。《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三級公立醫(yī)院績效考核工作的意見》(國辦發(fā)〔2019〕4號)以及《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推動公立醫(yī)院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意見》(國辦發(fā)〔2021〕18號)中,均提出要提高醫(yī)療服務(wù)收入,控制藥占比等指標(biāo)。因此本研究利用結(jié)構(gòu)變動度,運(yùn)用《中國衛(wèi)生健康統(tǒng)計年鑒》中的數(shù)據(jù),結(jié)合《控費(fèi)意見》中提出的部分監(jiān)測指標(biāo),對2015-2021年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收入結(jié)構(gòu)的變化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分析,探索政策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問題,為進(jìn)一步控制公立醫(yī)院醫(yī)療費(fèi)用不合理增長,優(yōu)化收入結(jié)構(gòu)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自2016-2022年《中國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衛(wèi)生健康統(tǒng)計年鑒》。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獻(xiàn)研究法,從2016-2022年的《中國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統(tǒng)計年鑒》《中國衛(wèi)生健康統(tǒng)計年鑒》中提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并對同類文獻(xiàn)進(jìn)行梳理。以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為研究對象,參考《關(guān)于控制公立醫(yī)院醫(yī)療費(fèi)用不合理增長的若干意見》(國衛(wèi)體改發(fā)〔2015〕89號)中提出的控制醫(yī)療費(fèi)用不合理增長的部分監(jiān)測指標(biāo),選取統(tǒng)計年鑒中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門診醫(yī)療收入以及住院收入結(jié)構(gòu)中相關(guān)指標(biāo)進(jìn)行結(jié)構(gòu)變動度分析。
1.3 結(jié)構(gòu)變動分析法
結(jié)構(gòu)變動分析法作為一種動態(tài)數(shù)據(jù)處理的方法,可以綜合表達(dá)費(fèi)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構(gòu)成變化,反映醫(yī)療費(fèi)用結(jié)構(gòu)變化的總體特征[2]。結(jié)構(gòu)變動分析法包括3個評價指標(biāo)[3,4]。
1.3.1 結(jié)構(gòu)變動值(Value of Structure Variation,VSV)
VSV是事物內(nèi)部各項(xiàng)目構(gòu)成比在一定時期內(nèi)期末值和期初值的差,為正值表明某項(xiàng)目比重增加,反之比重減少。VSV=Xi1-Xi0,i表示收入項(xiàng)目序列號,0表示期初,1表示期末。Xi0表示第i項(xiàng)收入在初期占總費(fèi)用的比重,Xi1表示第i項(xiàng)收入在期末占總費(fèi)用的比重。
1.3.2 結(jié)構(gòu)變動度(Degree of Structure Variation,DSV)
DSV反映某事物內(nèi)部各項(xiàng)目構(gòu)成比在該時期內(nèi)的綜合變化。DSV=∑|Xi1-Xi0|。
1.3.3 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
即各項(xiàng)目變動值的絕對值在結(jié)構(gòu)變動度中占的比重,用來表示某項(xiàng)目變化對總結(jié)構(gòu)變動的影響大小。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Xi1-Xi0|/DSV×100%(i=1,2,3…)。
2 結(jié)果
2.1 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基本情況
2015-2021年全國三級公立醫(yī)院的醫(yī)療收入由64,040.4萬元增加至84,636.8萬元,增長32.16%,其中藥品收入下降5.92%,檢查和化驗(yàn)收入增長52.79%,衛(wèi)生材料收入增長55.88%,掛號、診察、床位、治療、手術(shù)和護(hù)理收入增長57.37%。見表1。
2015-2021年全國三級公立醫(yī)院的門診醫(yī)療收入由21,266.9萬元增加至28,640.5萬元,增長34.67%,其中掛號收入下降13.21%,檢查收入增長52.52%,治療收入增長66.65%,手術(shù)收入增長102.90%,衛(wèi)生材料收入增長48.32%,藥品收入增加5.56%。見表2。

表2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門診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情況 單位:萬元
2015-2021年全國三級公立醫(yī)院的住院醫(yī)療收入由42,773.6萬元增加至55,224.1萬元,增長29.11%,其他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中,手術(shù)收入增幅最明顯,為93.49%,其次為護(hù)理收入,增幅為93.01%,藥品收入出現(xiàn)下降,降幅為13.55%。見表3。

表3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住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情況 單位:萬元
2.2 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情況
2.2.1 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情況
根據(jù)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醫(yī)療收入的數(shù)據(jù),將2015-2021年劃分為6個區(qū)間,分別為2015-2016年、2016-2017年、2017-2018年、2018-2019年、2019-2020年和2020-2021年。計算各區(qū)間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結(jié)構(gòu)變動度,見表4。

表4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變動度
2015-2021年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醫(yī)療收入的總結(jié)構(gòu)變動度為19.81%,其中2016-2017年結(jié)構(gòu)變動度最大,為6.31%;其次為2017-2018年,為4.77%。在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中,藥品收入在6個區(qū)間內(nèi)均為負(fù)向,提示藥品收入占比不斷下降;檢查收入,衛(wèi)生材料收入,掛號、床位、治療等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均為正向,提示占比不斷上升;其中醫(yī)療服務(wù)收入的增長幅度高于檢查收入、衛(wèi)生材料收入。見表4。
2.2.2 三級公立醫(yī)院門診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情況
分析門診收入結(jié)構(gòu)中的6項(xiàng)收入,發(fā)現(xiàn)2015-2021年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門診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度為17.64%,低于總醫(yī)療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度,其中2016-2017年的結(jié)構(gòu)變動度最大,為4.64%;2018-2019年結(jié)構(gòu)變動度最小,僅為1.01%。藥品收入在6個區(qū)間均為負(fù)向,對總體結(jié)構(gòu)度的影響最明顯;檢查收入、治療收入、手術(shù)收入在5個區(qū)間內(nèi)均為正向,其中檢查收入的增幅相對較大。見表5。

表5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門診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變動度
2.2.3 三級公立醫(yī)院住院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情況
分析住院收入結(jié)構(gòu)中的7項(xiàng)收入,發(fā)現(xiàn)2015-2021年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住院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度為23.32%,高于總醫(yī)療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度,可見住院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化較明顯。2016-2017年住院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度最大,為7.22%;2018-2019年結(jié)構(gòu)變動度最小,僅為1.96%。藥品收入在6個區(qū)間均為負(fù)向,總結(jié)構(gòu)變動值為-12.17,其次結(jié)構(gòu)變動較大的是衛(wèi)生材料收入,為3.99。見表6。

表6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住院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變動度
2.3 我國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
分析各醫(yī)療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發(fā)現(xiàn)在6個區(qū)間內(nèi)貢獻(xiàn)率最大的均為藥品收入。2015-2021年藥品收入貢獻(xiàn)率為59.57%,其次掛號、床位、手術(shù)等醫(yī)療服務(wù)收入,貢獻(xiàn)率為18.88%,兩者合計為78.45%。見表7。

表7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 單位:%
分析門診醫(yī)療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2015-2021年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最大的分別為藥品收入(60.38%)、檢查收入(13.52%)和治療收入(13.25%),三者累計貢獻(xiàn)率87.15%。在不同區(qū)間內(nèi),各貢獻(xiàn)率略有差異,但藥品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在各區(qū)間內(nèi)均為最高。見表8。

表8 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門診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 單位:%
分析住院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2015-2021年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最大的分別為藥品收入(52.20%)、衛(wèi)生材料收入(17.11%)、手術(shù)收入(12.38%),三者累計貢獻(xiàn)率81.69%。在5個不同區(qū)間內(nèi),結(jié)構(gòu)貢獻(xiàn)率最大的均為藥品收入,在2018-2019年出現(xiàn)明顯下降。見表9。

表9 2015-2020年三級公立醫(yī)院住院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 單位:%
3 討論與建議
3.1 藥品收入占比下降,控費(fèi)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以藥補(bǔ)醫(yī)機(jī)制有所改善
本研究發(fā)現(xiàn),2015-2021年全國三級公立醫(yī)院藥品收入下降5.92%,住院藥品收入下降明顯,為13.55%,藥品收入占醫(yī)療收入的比重由40.97%下降至29.17%,減少11.8個百分點(diǎn),達(dá)到《控費(fèi)意見》中要求藥占比控制在30%以下的目標(biāo),控費(fèi)效果較好。同時在6個區(qū)間中,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中藥品收入在各區(qū)間內(nèi)均為負(fù)向,表明藥品收入占比不斷下降。另外,藥品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貢獻(xiàn)率最大,提示藥占比下降變化最為顯著,符合《公立醫(yī)院醫(yī)療費(fèi)用控制主要監(jiān)測指標(biāo)》中“藥占比逐步降低”的要求,控費(fèi)政策取得一定效果,收入結(jié)構(gòu)發(fā)生明顯變化,以藥補(bǔ)醫(yī)機(jī)制得以改善,與其他相關(guān)研究具有一致性[5,6]。深入分析三級公立醫(yī)院藥占比出現(xiàn)下降的原因,得益于衛(wèi)生政策“組合拳”的實(shí)施,包括落實(shí)藥品集中采購機(jī)制;不斷規(guī)范醫(yī)務(wù)人員診療行為,落實(shí)處方點(diǎn)評、抗生素使用等制度,加強(qiáng)對醫(yī)務(wù)人員用藥行為的監(jiān)管;推行DRG醫(y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等。
3.2 檢查收入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占比有所增加,形成新的增長點(diǎn),需加強(qiáng)管控
本研究表明,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檢查收入增長52.79%、衛(wèi)生材料收入增長55.88%,在6個變動區(qū)間內(nèi),檢查收入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基本為正向,顯示檢查收入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的占比不斷增加,與《控費(fèi)意見》中該指標(biāo)“逐漸下降”的要求不符。通過進(jìn)一步分析門診與住院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發(fā)現(xiàn)除藥品收入外,門診醫(yī)療收入中檢查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貢獻(xiàn)率最大,住院醫(yī)療收入中衛(wèi)生材料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和貢獻(xiàn)率最大,提示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逐漸由藥品收入向檢查收入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占比傾斜,藥品收入騰出的空間部分轉(zhuǎn)化為檢查化驗(yàn)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存在“以藥補(bǔ)醫(yī)”轉(zhuǎn)向“以械養(yǎng)醫(yī)”的風(fēng)險,其他相關(guān)研究也得出相同結(jié)論[7]。究其原因,除了合理性因素外,也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取消藥品加成后,政府的財政補(bǔ)助不到位,醫(yī)院的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壓力增大,存在逐利行為,逐漸增加檢查化驗(yàn)、衛(wèi)生材料收入代替藥品收入;再者由于衛(wèi)生行政部門對耗材的監(jiān)管不到位,醫(yī)患信息不對稱等原因?qū)е聶z查化驗(yàn)、衛(wèi)生材料收入增加,不符合國家公立醫(yī)院改革、降低人民群眾醫(yī)藥負(fù)擔(dān)的政策導(dǎo)向。
3.3 醫(yī)療服務(wù)收入占比略有增加,醫(yī)務(wù)人員勞動價值部分得以體現(xiàn),結(jié)構(gòu)需進(jìn)一步優(yōu)化
治療、手術(shù)、護(hù)理等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醫(yī)務(wù)人員技術(shù)勞動價值的體現(xiàn)[8]。本研究顯示,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中,體現(xiàn)醫(yī)務(wù)人員價值的醫(yī)療服務(wù)收入增加57.37%,在6個變動區(qū)間內(nèi),醫(yī)療服務(wù)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值基本為正向,表明醫(yī)療服務(wù)收入占比有所增加,勞動價值得以體現(xiàn),符合掛號、手術(shù)、治療等收入占醫(yī)療服務(wù)收入“逐步提高”的要求,“騰空間、調(diào)結(jié)構(gòu)”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醫(yī)療服務(wù)收入結(jié)構(gòu)變動的貢獻(xiàn)率不高,尤其在住院醫(yī)療收入中床位收入和護(hù)理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較小,價格調(diào)整效果不明顯,需進(jìn)一步采取相關(guān)措施增加醫(yī)療服務(wù)收入,優(yōu)化收入結(jié)構(gòu),這一結(jié)果與其他研究一致[9]。
對2015-2021年三級公立醫(yī)院各項(xiàng)醫(yī)療服務(wù)收入結(jié)構(gòu)變化情況進(jìn)行深入分析,發(fā)現(xiàn)自《控費(fèi)意見》實(shí)施后,2015-2018年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優(yōu)化比較明顯,尤其是2016-2017年,結(jié)構(gòu)變動度在6個區(qū)間內(nèi)最大,政策效果最顯著。2018-2019年各項(xiàng)醫(yī)療收入的結(jié)構(gòu)變動度在6個區(qū)間內(nèi)最小,僅為0.9%,門診收入及住院收入均呈現(xiàn)此趨勢,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優(yōu)化不明顯,效果出現(xiàn)反彈,2019年后趨勢逐漸好轉(zhuǎn),收入結(jié)構(gòu)不斷優(yōu)化。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主要受衛(wèi)生政策實(shí)施的影響,《控費(fèi)意見》實(shí)施后,衛(wèi)生行政部門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受政策時效性影響在2016年后效果逐漸凸顯,同時由于政策具有周期性,2018年政策效果出現(xiàn)反彈。2019年后受國家三級公立醫(yī)院績效考核、醫(yī)療價格政策調(diào)整、推動公立醫(yī)院高質(zhì)量發(fā)展以及DRG支付等多項(xiàng)政策文件的影響,三級公立醫(yī)院醫(yī)療費(fèi)用結(jié)構(gòu)進(jìn)一步優(yōu)化。
3.4 多措并舉控制醫(yī)療費(fèi)用不合理增長,優(yōu)化醫(yī)療收入結(jié)構(gòu),維護(hù)醫(yī)患雙方合法權(quán)益
綜上所述,控費(fèi)政策實(shí)施后,藥品收入占比下降,收入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但藥品收入下降帶來的增長空間大部分被檢查收入和衛(wèi)生材料收入的不合理增長所替代,體現(xiàn)醫(yī)務(wù)人員價值的醫(yī)療服務(wù)收入占比略有增加,收入結(jié)構(gòu)存在進(jìn)一步優(yōu)化的空間,同時存在政策效果波動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需采取多項(xiàng)措施:一是實(shí)施高值醫(yī)用耗材集中采購和陽光采購,在保證質(zhì)量的前提下鼓勵采購國產(chǎn)高值醫(yī)用耗材,加強(qiáng)對醫(yī)用耗材的監(jiān)管。二是不斷落實(shí)醫(yī)療服務(wù)價格調(diào)整政策,降低大型醫(yī)用設(shè)備檢查治療價格,適當(dāng)提高治療、手術(shù)、護(hù)理等費(fèi)用價格,體現(xiàn)醫(yī)務(wù)人員技術(shù)勞動價值。同時不斷完善補(bǔ)償機(jī)制和激勵約束機(jī)制,避免醫(yī)務(wù)人員過度用藥、過度檢查的行為,維護(hù)醫(yī)務(wù)人員的合理利益收入,不斷提高積極性。三是在各項(xiàng)衛(wèi)生政策的實(shí)施過程中要保持連續(xù)性和綜合性,強(qiáng)化政府責(zé)任,確保對公立醫(yī)院的虧損補(bǔ)助及時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