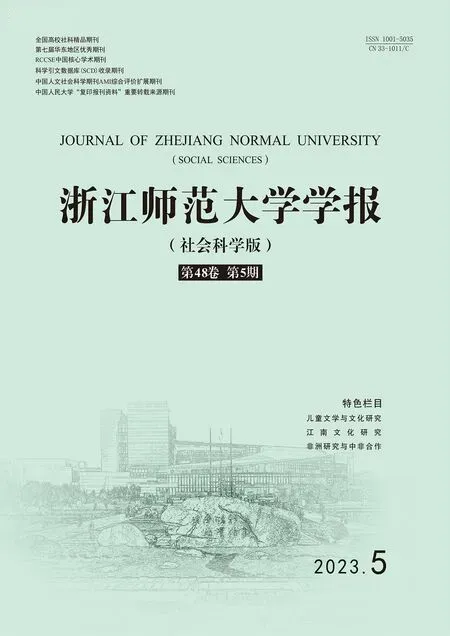圖像的“出位之思”
——《小朋友畫報》的圖像敘事與新民期待
吳翔宇, 趙哲宇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圖畫一直在兒童的文學閱讀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直接參與了兒童文學的文體建構。對于圖畫、插畫之于兒童文學的關系,黎正甫認為,圖畫本身不是兒童文學,但連續的圖畫構成故事,如連環故事圖畫可以說是一種兒童文學。[1]葛承訓與黎正甫的觀點完全一致:“如以圖畫表示一個故事,圖畫就成為文學的一種了。”[2]14然而,檢視清末民初的“連環畫”,無論是故事、圖畫質量,還是圖文的組合關系,都不太適合兒童。對此,魯迅認為此類畫只是彌補文學不足的“宣傳的連環圖畫”。[3]在他看來,民間的《智燈難字》《日用雜字》可以幫助兒童識字,《圣諭像解》和《二十四孝圖》都是借圖畫以啟蒙。之所以要附上圖畫,魯迅將其歸因于“中國文字太難”。他認為既然要啟蒙,還是要讓兒童能懂,而“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癡,但應該著眼于一般的大眾”。[4]同時,圖文并置的圖畫書,對畫家的要求也很高,“倘不是對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5]與魯迅否定舊式的連環畫不同,茅盾一方面認為其文字只是類似舊書“眉批”的“說明”,另一方面又認為其尚有可取之處:“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在那些‘連環圖畫小說’的形式——六分之四的地位是附加簡單說明的圖畫,而六分之二的地位卻是與那些連續的圖畫相吻合的自己可以獨立的小說節本,——確是很可以采用。因為那連環圖畫的部分不但可以引誘識字不多的讀者,并且可以作為幫助那識字不多的讀者漸漸‘自習’的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階梯。”[6]有感于粗制濫造的“連環圖畫書小說”的無孔不入,茅盾也憂慮這會擠壓純兒童文學讀物的發展空間,并提醒新書業以及兒童讀物的作者應該“痛自反省”。茅盾并不否定此類讀物圖文并茂的形式,而是擔憂其質量低下,“內容輾轉抄襲,缺乏新鮮的題材”。[7]
兒童報刊是現代兒童文學文體實踐的重要載體。畫報類讀物因其圖文并置的特殊性,在現代圖畫書的文體生成中作用更為突出。1926年,中華書局創辦了兒童刊物《小朋友畫報》。與《小朋友》相比,《小朋友畫報》更關注幼兒群體,在報刊的版面設計中,圖畫的比重更大,繪制更加精細,多為彩印,且出現了具有現代圖畫書特點的“故事畫”。在《兒童讀物的研究》中,王人路談及1930年代廣泛閱讀的兒童刊物,認為《小朋友》《兒童世界》《小朋友畫報》《兒童畫報》“這四種刊物,比較的在中國的兒童群眾里占很大的位置”。[8]可見在當時,《小朋友畫報》與《小朋友》《兒童世界》一樣,都廣受小朋友們的歡迎。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的書寫中,《小朋友》《兒童世界》廣受重視,例如蔣風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中提到“我國第一個純文學的兒童周刊——《兒童世界》”,[9]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中又提到“《小朋友》和《兒童世界》創辦于1920年代,屬于‘老牌’的兒童定期刊物,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極受小讀者的歡迎”。[10]王泉根提到《兒童世界》是“中國現代最有影響的兒童刊物”,[11]并多次列舉在《小朋友》和《兒童世界》中刊登的兒童文學作品。但在兒童報刊的研究中,學界的研究重心多在《小朋友》和《兒童世界》上,而對畫報類的兒童讀物研究不足。通過研究《小朋友畫報》中服飾、游戲、教育等圖像敘事內容的現代內涵,以及故事畫中圖文結合方式的形式特點,可以從意義與形式兩方面發掘其圖像藝術的現代訊息,從而為現代圖畫書文體的歷史發展提供諸多新的材料和研究思路。
一、《小朋友畫報》概況及發刊時間考述
圖與文的并置有助于兒童接受,孫毓修所編《童話》叢書正是采用了“加圖畫,以益其趣”[12]的方式,成為深受當時兒童歡迎的讀物。在《兒童的文學》中,周作人就曾感嘆:“要尋能夠為兒童書作插畫的,自然更不易得了,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13]在閱讀了陳和祥的《圖繪童謠大觀》后,周作人對其“繡像式的插畫”表示不滿:“我所看了最不愉快的是那繡像式的插畫,這不如沒有倒還清爽些。說起這樣插畫的起源也很早了,許多小學教科書里都插著這樣不中不西,毫無生氣的傀儡畫,還有許多的‘教育畫’也是如此。”[14]在《兒童世界》的創刊號的十個欄目中,就有“插圖”和“滑稽畫”兩種。此后,還刊載了鄭振鐸的《兩個小猴子的冒險記》 (連載六期)等長篇圖畫故事,這些內容成為最早圖畫書的樣態。此外,鄭振鐸還在“封面畫”上精益求精,“封面畫”與每一期的風格、基調、主題相呼應,其功能不局限在宣傳與廣告的層面,而且構成了《兒童世界》雜志生命的一個部分。
同為面向兒童的雜志,《小朋友畫報》的突出特色體現在“圖畫藝術”上。它創刊于上海,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其創刊對于中國圖畫書的文體自覺有著重要的意義。該刊選材范圍很廣,將“幼稚教育”中涉及的文學門類,包括各種兒童容易體驗的故事,用簡明的圖畫來表達,輔以淺近的文字。在刊載欄目方面,設有童謠、謎語、笑話、畫圖(單幅和多幅)、故事畫、剪貼、拼圖游戲、涂色、數數、填字、手工、兒童自由畫、照片等。在刊載內容方面,《小朋友畫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類:識物的科普類,如1935年第1卷第13期①的《冬眠的動物》;識字寫字算數類,如1935年第1卷第14期的《象》;文學意味較強的故事畫,如1937年第3卷第62期的《天氣好,向外跑》;描述兒童生活、民俗風貌的童謠類,如1935年第1卷第14期的《做湯圓》;宣揚政治思想的紀念日圖畫,如1934年第1卷第1期的《七月九日》;培養兒童動手能力的游戲類,如1934年第1卷第6期的《紙風車》。這些刊載內容蘊含著將兒童培養成為知識健全、熱愛學習、講究衛生、體魄健康的新國民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小朋友畫報》專設了一個特別的欄目——“獻給讀者的父母和教師”。在這個欄目中,編輯部介紹了此刊的主要內容、編者的設計理念、建議的閱讀方式等。在復刊(1934年)的第1期中,該欄目提供了不同年齡兒童閱讀此刊的方法:“一、對于未曾上學的兒童,請將圖意釋給他們聽。二、對于已經上學的兒童,請指導他們誦讀圖上的文字。三、對于已經能夠自動誦讀文字的兒童,請把本期中所列的材料,一一歸納起來,組成一個單元,解釋給他們聽。”[15]這一欄目很像現代圖畫書的導讀手冊,不僅告訴讀者“寫了什么”,還告訴讀者“怎么閱讀”。它不再將閱讀圖畫當成一種個人的娛樂活動,而是注重親子共讀中父母對孩子知識的引導。該刊發行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讀者在翻閱圖畫,誦讀文字之余,能夠更進一步而追求知識”。[15]“獻給讀者的父母和老師”專欄更是彰明了編者啟發兒童“新知”的訴求。例如,在1935年第1卷第20期中,編者強調,詩歌《梨花淡白柳深青》應該誦讀,并將“梨花之形態,柳樹之習性,以及柳絮何以會飛揚的理由”講解給兒童聽。其余的內容,如與小蝌蚪有關的“青蛙生長之情形”,與萬里長城有關的“建筑時之用意”,與釣魚有關的“練習計數”,均強調兒童應該補充知識,學習應該習得的材料。而故事、圖畫和游戲則處于輔助兒童理解知識的從屬地位。《小朋友畫報》的編者特別注重與兒童的交流。前述“獻給讀者的父母和老師”欄目就是編輯與讀者溝通交流的平臺。除此之外,報刊還積極向兒童約稿,約稿內容包括自由畫、筆記、故事、兒歌、勞作、攝影等。可見,《小朋友畫報》不僅將兒童視為讀者,而且把他們視作創作的主體。換言之,兒童不僅可以是生活材料的搜集者和記錄者,還可以是自由寫作、繪畫的創作者。這種行為固然是銷售和宣傳策略的體現,但也肯定了兒童的能力,彰顯了兒童的獨立品格。
正是基于注重圖畫藝術之于兒童文學閱讀的關聯,《小朋友畫報》與同時期的《兒童世界》《小朋友》等雜志一道成為推動圖畫書文體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不過,關于《小朋友畫報》的辦刊和停刊日期,學界也存在著分歧。在《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中,張梅的說法是:“《小朋友畫報》:1926年8月由中華書局在上海創刊,半月刊。由王人路、吳啟瑞編輯。1930年因政治原因停刊。1934年7月復刊……1937年抗戰爆發停刊。”[16]在《中國現代幼兒文學的發生》中,杜傳坤的觀點則是:“1934年中華書局創刊的《小朋友畫報》。”[17]在吳永貴的《中華書局對我國學術文化的貢獻》中,有這樣的記載:“《小朋友畫報》半月刊(1926年8月創刊)。”[18]在《論少兒出版發端期重要出版物及其文化影響》中,李勇這樣說道:“1926年8月,《小朋友畫報》創刊。”[19]由此可見,對于《小朋友畫報》的辦刊日期,主要有1926年和1934年兩種說法,而停刊日期,僅在張梅的《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中表述為“1930年因政治原因停刊”“1934年7月復刊”“1937年抗戰爆發停刊”。[16]
從學理上看,從原始史料中找取發刊日期的線索更為準確。民國時期報刊業的發展進入一個黃金時期,為了擴大宣傳,不同的刊物之間往往相互刊登廣告信息,甚至有專門刊發各類廣告的報刊,如《申報》。1926年8月8日,《申報》曾刊載過《小朋友畫報》的廣告信息(圖1)。按其信息,該畫報已在1926年8月1日出版了第1期,此后每月1日和16日各出1期。

圖1 《小朋友畫報》廣告信息②
同一出版社的刊物之間也會相互打廣告,這也是了解該畫報創刊日期的線索。中華書局發刊的《小朋友》第230期(1926年9月出版)有這樣的記載:“近來我們接到許多訂閱《小朋友畫報》的信和匯款”;[20]第252期(1927年2月出版)中記錄過如下文字:“從前送給小朋友們的《小朋友畫報》,有些人寫信來說沒有收到……決定將219—225期的懸賞獎品,改送《小朋友畫報》第一期到第六期。”[21]由此可知,《小朋友畫報》自從在1926年8月《申報》刊發廣告信息到1927年2月,確實已經出版了至少6期,并且被用作《小朋友》的附贈品和獎勵品。
據張梅統計,《小朋友畫報》在“1930年因政治原因停刊”,并在腳注中注明這一信息來源于王人路的《兒童讀物的研究》。[16]查詢王人路的《兒童讀物的研究》,他卻只提及了“《小朋友畫報》曾因為政治的關系已停刊未續”,[8]并未提及具體年份。《小朋友》第259期(1927年4月出版)有如下記載:“《小朋友畫報》只出到第八期就停止了……已請一位姓唐的先生接編。”[22]但在同年的《小朋友》第278期(1927年9月出版)中,卻與第259期的表述有出入:“《小朋友畫報》自從原編輯人走后,一時找不到相當的人接手辦理,以致不能按期出版,時常勞諸位寫信來催問……現在決定暫不繼續出版。”[23]可以確定的是,在1927年《小朋友畫報》停刊前就至少出版了8期。至于在第8期(1926年12月發行)之后,到《小朋友畫報》確定停刊的日期(1927年9月)之前,是否有真如吳翰云所說有“姓唐的先生接編”,就不得而知了。
尋繹同一時期不同雜志的記載及研究者的觀點,容易得出如下看法:《小朋友畫報》在1926年8月1日發行了第1期,此后至少發行8期。1927年王人路離職停刊,1934年7月復刊。復刊后出版的刊物內容,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均有記載,但1926—1927年的《小朋友畫報》現已無跡可尋。考證發刊時間,并不僅僅是錯誤信息的糾正,它還意味著對那一時期歷史面貌的還原。考證的過程不僅可以折射出版者是如何以文學為資本,介入“啟蒙”與“生意”的知識結構,而且能洞見那一時期不同刊物、不同出版社之間的密切聯系。這種研究思路,可以幫助我們突破只聚焦研究對象內部的思維偏狹,將它與動態的歷史語境聯系起來,從而獲得一種更為深刻的、進入到歷史場景中去思考的理性認知。
二、圖文的語法關系與價值預設
利用圖畫來傳達現代觀念及信息的方式,在《兒童世界》《小朋友》等兒童專業雜志中已大量存在。這體現了辦刊者及兒童雜志“圖畫現代性”的觀念,與文字所蘊含的“思想現代性”相互補充,合力推動兒童文學的現代化進程。[24]不過,在兒童文學發生期的研究中,圖像常常處于被忽視的狀態。魯迅曾說:“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25]在《兒童的書》中,周作人提及了“童話繪”的概念,他認為“童話繪”比“歷史繪”更為有趣。然而即使兒童喜歡“線畫”,中國的寫意畫等古美術技法也并不適合兒童。為兒童考慮,周作人甚至將“為兒童的美的畫本或故事書”與兒童文學創作的意義相提并論,[26]由此可見其對于創制圖畫書的先鋒意識。考察發生期兒童文學的圖畫故事,不難發現,圖畫比文字更為直觀,更為具象。它以明顯直接的視覺印象給予讀者形象的、感性的認識,借助身體形象、活動空間、視覺器物等將圖畫隱喻的兒童期待、新舊圖景、救國想象等以近乎“無意識的形式”施之于接受者,潤物無聲地催化了現代觀念的生成。
(一)滑稽的兒童相——教訓與娛樂之間
“喜劇的摹仿對象是比一般人較差的人物。所謂‘較差’,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壞’,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種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東西是一種對旁人無傷,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訛。”[27]在《小朋友畫報》的故事畫中,“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兒童(有時也表現為調皮的小狗、小貓等動物)時常成為圖像的主人公,他們常常犯些無傷大雅的錯誤,惹人發笑。這種類型并不是《小朋友畫報》的首創,它來源于清末民初流行的諧畫、時畫、漫畫等,并以“滑稽畫”的命名方式,第一次在兒童期刊《兒童教育畫》中運用。
在以往的故事類型中,頑童犯錯誤往往是因為他們有著某些方面的不良習慣,例如“不講文明”(《兒童教育畫》1916年第71期),“偷吸紙煙”(《兒童教育畫》1915年第67期),而滑稽效果常常表現為兒童自食惡果,得到了懲戒,如亂扔瓜皮反踩瓜皮,自己摔倒;偷吸紙煙反被紙煙燒了衣服。在這些滑稽的圖像后面,經常會跟上一段說教的文字。例如在《兒童畫報》里《哪一個敢去做》的故事畫中,原本講述了一個“老鼠歡歡喜喜討論如何對付老貓,卻不料這一切早被老貓知曉”的滑稽故事,但在文章最后,鄭振鐸卻附上了一個訓誡的結尾——“這是一個教訓:凡事,說說是很容易的,做到就難了!”[28]在這種故事的敘述邏輯中,圖像的“滑稽”雖然具有愉悅的功能,但仍然只是一個糖衣,真正重要的是文字所表達的訓誡意義。圖像和文字指向的維度是相互背離的,當圖像強調“趣味”時,文字卻對“趣味”不斷壓抑和規訓,使之成為文字的附庸。
在《小朋友畫報》中,這種訓誡依然存在。《小呆子的故事》描述了小呆子借桌子回家,卻丟失了桌子的滑稽故事。造成滑稽效果的是兒童特有的思維方式:小呆子看見一匹馬有四條腿,跑得很快,所以認為桌子有四條腿,也會自己走路,于是把桌子丟在半路獨自回家,當發現問題再趕回去時,桌子已經不見了。作者用成人的眼光來觀察兒童的思維邏輯,并將兒童的這一行為放置到一個特定的生活場景中,加以夸張和放大,從而造成滑稽的故事效果。這種滑稽雖“不致引起痛苦或傷害”,[29]但也隱含了這樣一個道理:兒童思維是幼稚的,是亟待完善和成熟的,如果不被成人教導,就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在《小朋友畫報》的一些故事畫里,這種“幼稚的”兒童思維卻讓事情峰回路轉,反而給人一種意外之感。1936年第2卷第39期的《媽媽!我們出去買些好東西給你吃!》(圖2)描寫了一對兄妹突發奇想去搖栗子,然后被栗子砸頭的滑稽場面。但被栗子砸頭卻并沒有帶來不幸,兄妹倆反而拾得了一筐栗子,抬給了媽媽作禮物。與此類似的是1934年第1卷第9期的故事畫《捉迷藏》(圖3),雖然在捉迷藏的過程中哥哥撞了個大包,但卻獲得了一張雖然滑稽但是很有紀念意義的照片。小錯誤不僅無傷大雅,反而意外獲得了很多美好的收獲。在這種滑稽敘事中,訓誡退場了,隨之出場的是對兒童的寬容、理解和接受。將兒童所犯的小錯誤用一種文學的方式處理,得到一種滑稽的審美愉悅,這種敘述方式體現了兒童觀念的進步。

圖2 《媽媽!我們出去買些好東西給你吃!》

圖3 《捉迷藏》
但不論是“訓誡”還是“娛樂”,這些滑稽的兒童始終缺乏主體性,無法掙脫成人觀察和審判的目光。這種滑稽故事,更像是成人為了心中的“頑童”觀念,截取了兒童生活中極其微小的片段,組成一個動態短片式的情節。其中的兒童既沒有多樣的、可發展變化的性格,在圖像上也沒有獨具特色的肖像描繪,反而千篇一律,面目模糊。在“訓誡”和“娛樂”之間生存的兒童,無法擺脫時代和現實的束縛,他們的“滑稽相”更像是一種傀儡式的表演,可以惹得臺下的眾人發笑,卻缺乏自主的靈魂。
(二)凝視的風景——傳統與現代之間
柄谷行人認為,“風景”早就存在,但它需要通過文學家或畫家的命名,才能夠被發現。在此之前,畫家觀察到的不是“事物”,而是某種先驗的概念。[30]在《小朋友畫報》中所呈現的風景圖像,呈現出傳統和現代新舊交雜的文化特質。和同時期畫報中明顯的政治訴求和軍事隱喻不同,《小朋友畫報》的空間場景呈現出一種近乎“田園牧歌”的理想狀態,獨樹一幟地在救國救民的夾縫中舉起兒童風景和風俗的旗幟。
不同于《小朋友》報刊圖像中偏向現代西方的空間場景,《小朋友畫報》中兒童的活動場所與當時孩子的生活更為貼近。池塘、磨坊、田野、山水、花鳥……他們雖選取了傳統繪畫中的意象,卻并不注重寫意,而是更重視這些景物的真實性,將這些物象作為普及兒童知識,展現兒童景觀的工具。例如,在1934年第1卷第3期的《牽牛花》(圖4)中,畫者用黑色勾線,彩色著色,將原本藝術性較強的國畫意象用兒童更容易欣賞的方式,描繪得更為清晰,色彩更為濃郁,既保留了我們傳統繪畫的意蘊,又能達到教兒童知識的目的。

圖4 《牽牛花》
民風民俗是《小朋友畫報》傳統風景的重要呈現內容。由于畫報具有時效性,編者常常依據時令,編排給兒童特定的圖像內容,例如夏至、黃梅、五月雨水、春季桃花……除此之外,畫報中還刊登了元宵節、端午節、兒童節、除夕、新年等節日的圖像景觀,頗具“風俗畫”的意味。這些畫面中所描繪的場景帶有新舊交雜的時代特征。例如,1935年第1卷第16期的《元宵節》(圖5),描繪了一群穿著新式服裝的兒童,手拿著各種各樣造型的燈籠,在老師的帶領下成群結隊玩耍的場景。這里,兒童的服裝和游玩方式都發生了現代的轉變。

圖5 《元宵節》
“土地”在《小朋友畫報》中反復出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土地代表著祖先,是祖先傳承下來的財富和精神遺產。由于祖先在人們心中的特殊位置,土地也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意蘊。人們可以在土地上祭祀、勞作和生活,維持穩定而熟悉的血緣和宗族關系。在《小朋友畫報》中,土地與祭祀的關系被有意忽略了,留下了其中與培養現代兒童密切相關的內容——勞動。
編者選擇了許多與勞作有關的畫面,教導兒童要懂得勞動的辛苦。在1934年第1卷第1期《踏車》中,畫面中有兩位農民在烈日下勞作,并配以文字“田干稻枯,忙殺農夫”。此外還有1936年第2卷第44期《上古時候的人是這樣過活的》,通過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人民生活方式的對比,說明勞動使人進步的道理;同期的《農工商兵》,告訴兒童每一類人民都在努力工作,都值得尊敬。此外,在土地上耕作的牛、土里長出來的蔬菜……這些與土地密切相關的生活常識,也以“圖說”的形式出現在畫報中。
土地也是兒童游戲的重要場所。兒童在土地上自在玩耍,體現了一種和諧自然的“田園牧歌”的氛圍。在《騎驢》中,女孩騎在一頭溫順的驢子身上,低下頭和牽著這頭驢的男孩商量接下來去哪玩。這種畫面的呈現是詩化的,在救國救民的時代浪潮中顯得獨樹一幟。
在民國時期,鄉村早已不再是封閉的系統,現代工業快速地侵入原本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中。在《小朋友畫報》1934年第1卷第9期的《秋天的野外》(圖6)中,除了挑著扁擔的賣貨郎,郁郁蔥蔥的樹木,連綿起伏的山峰,還有讓人無法忽視的山腳下冒著黑煙的火車和黑色的電線桿。火車和電,這兩項現代社會的標志性內容,逐漸成為畫報中現代性的視覺表征,以不可阻擋的態勢進入人們的視野。

圖6 《秋天的野外》
(三)改變時空觀的現代產品——救國與想象之間
隨著“科學救國”浪潮的興起,科技產品承載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內涵,“飛機”“火車”等交通工具的引入帶來了人們時空觀的革新。這些在畫報中重復出現的現代產品,逐漸成為一種視覺符號,寄托了人們對科技救國的想象。飛機,作為工業革命的成果和產物,見證了科技的巨大力量,人們可以借由飛機超越空間翱翔天際。“人之欲飛,其思想絕不始于今日也。”[31]從古到今,對于翱翔天際的期待綿綿不絕。不同于文學作品中人們對“飛”的烏托邦想象,現代科技的發展帶來了飛機的發明,這種基于科學和實踐的飛翔體現為一種“視覺現代性”的價值沖擊。
在《小朋友畫報》中,飛機這個圖像出現了很多次。有知識普及類的《飛機有許多用處你可曾知道》《水上飛機》《飛機、火車、輪船》;有幻想類的《乘飛機去見月公公》;有手工類的《小朋友,做飛機》《只要心思巧,用些竹簽用些豆,一架飛機做成了!》。在1936年第3卷第52期的《乘飛機去見月公公》(圖7)這幅幻想圖景中,“看”是畫中人物的主要動作。小朋友們在機翼上或站或坐,興奮不已。孩子們看的對象既不是太陽,也不是云朵,而是從古至今寄托無限情思的月亮。飛機自然不可能飛得比月亮還高,但它卻讓人們擺脫地面的束縛,打破物理空間的桎梏,到達想象的頂端。“看”也是觀看這幅畫的人的動作。畫中人俯視著月亮,畫外人俯視著畫中人。一些坐在機尾的孩子和畫外的閱讀者對視,仿佛完成了一次超越時空的對話。

圖7 《乘飛機去見月公公》
在《倫敦新聞畫報》中也有很多想象坐在飛行器上俯視的圖像,但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想象的俯視圖景更加清晰、更加具象,他們以鳥瞰的視角獲得盡可能多的觀察細節。而中國的這幅圖,雖然作者也采用了俯視的視角,但顯然更加虛幻。這里體現了中西不同的想象方式。西方的想象更偏向于科學,他們以理性的方式得出結論;而中國的想象更偏向于哲學,用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實現理想的圓滿。
身處內憂外患的時代,飛機所隱含的浪漫意味只能退居一旁,借助飛機興國救民才是更應該實現的事。在《飛機有許多用處你可曾知道》中,明確了飛機“放煙幕”“投炸彈”“載旅客”“載郵件”的作用。飛機肩負了民用和軍事兩大重任,承擔了無數仁人志士科技救國的想象。除了飛機之外,火車也是《小朋友畫報》現代圖像的重要內容。火車或飛機都更像是一個符號,它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念,改變了人們溝通和交流的方式。在內憂外患之時,這些現代符號和救國聯系起來,變成一種積極的意象,一項應該努力發展和推動的事業。
三、圖畫現代性與圖畫書文體的萌芽
在啟蒙語境下,借助視角的“看”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圖畫”也就成為一種現代性形式。在《小朋友畫報》的眾多欄目中,有一種類型最為特殊,那就是“故事畫”。故事畫用連續的多幅圖畫共同敘述一個故事,且單個場景的篇幅比一般的連環圖畫大,多為兩個場景占一頁篇幅。這種敘述方式與現代圖畫書頗為相似。但故事畫對兒童的態度更為包容,更能理解兒童犯的無傷大雅的小錯誤,更符合現代兒童觀念。
(一)從“視覺游戲”到故事性的嘗試
故事性是圖畫故事成為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以往的滑稽畫和圖畫故事中,雖然有著生動有趣的動作,卻很難有情節完整的故事內容。這種片段性的畫面呈現更像是一種“視覺游戲”,通過主人公某些關鍵動作的定幀,填補某一段連續動作的留白。為滑稽而滑稽的動作片段,初讀起來或許有趣,但讀多了卻感覺是一種敘述裝置,只有技巧性的內容,而無實在可感的情節。
在《小朋友畫報》的故事畫中,這種“視覺游戲”依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不同的是,畫報中出現了幾個頗有情節趣味的故事樣式。例如,1935年第1卷第21期的《小狗變青蛙》(圖8),就敘述了一個具有反轉意味的故事:兄妹倆去郊外玩,把準備好的點心放在帽子里,開心地一起吃。沒注意來了一只小狗,連著帽子把點心拖走了。兄妹倆發現后,拿著手杖,追著帽子往樹林里趕。小狗趁亂從帽子里出來,在灌木叢后面偷吃點心。可惜兄妹倆沒有發現,還一直用手杖往樹林里攪。樹林里的青蛙被攪得很煩惱,呱呱叫著跳出來,嚇了兄妹倆一跳。

圖8 《小狗變青蛙》
在這個故事畫里,小狗、妹妹、哥哥、青蛙行為的“錯位”造成故事情節的滑稽效果。兄妹倆和小狗像是分屬于兩個不同的聲部,小狗與兄妹倆的斗智斗勇使情節變得引人入勝,青蛙角色是一個意外的合音,它的突然加入使整個故事的演奏變得更加精彩。這個故事畫中最具張力的是這樣一幅畫面——哥哥在樹叢里攪,想要找到點心,殊不知小狗早已偷梁換柱,把點心拖到一旁快樂地享用了。在上下這兩幅圖中,兄妹倆和小狗處于同一時間,但因聚焦場景的不同而顯示成了兩幅畫面。這種處理方式已經和現代圖畫書“同時異構”的畫面表達頗為相似。
與此故事類似,圖畫故事《老鼠釣金魚》也具有這種情節的反轉性。故事講了一只灰老鼠想要吃魚缸里的金魚,找黑老鼠幫忙。黑老鼠提議用尾巴把金魚釣上來,灰老鼠照做,終于釣上來一條魚。可是他倆都認為魚應該是自己的,誰也不讓誰。正在扭打間,一只貓過來把魚吃掉了。這個故事在敘述連續性動態場景的同時,逐步引入角色,使得故事的矛盾從如何把魚釣上來的問題變為魚的分配問題,結尾貓的加入使得激烈的矛盾戛然而止,引發故事的喜劇效果。雖然總體來說,這兩個故事畫還是以“滑稽”為敘述的核心來設置故事框架,但它們已具備了“雙線并置”這樣從不同視角敘述的故事情節和“多次反轉”的故事邏輯。在故事的篇幅上,出現了六幅圖、八幅圖這樣的長故事;在角色設置上,也有兒童、成人、動物等多個角色共同參與,這些嘗試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從“以圖釋意”到“圖文合奏”
在兒童文學的發生期,圖像常常作為激發兒童興趣,幫助兒童理解的工具。茅盾認可連環圖畫的作用,認為它“不但可以引誘識字不多的讀者,并且可以作為幫助那識字不多的讀者漸漸‘自習’的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階梯”。[6]葛承訓在《新兒童文學》中指出:“文字與圖,務必符合。文字要確切地說明圖畫的要義,及故事情節的主點。”[2]17圖像在這一時期往往作為闡發文字的工具,幫助兒童進入文字閱讀的大門。
萊辛認為,畫面善于表現靜態的、空間性的內容,而語言善于表現動作的、時間性的內容。[32]在發生期兒童報刊的圖畫故事中,繪者常常把一些富有動感的故事片段截取出來,利用視覺的補充效果,將連續性的故事內容闡發出來。如《兒童世界》1922年第3卷第6期的《汽車歷險記》,就把汽車一路的行進路程描繪得跌宕起伏。但在這種情況下,圖像依然只是文字的二次敘述,它的作用是促進文字故事的理解,并沒有自己獨立的圖像意義。
饒有意味的是,《小朋友畫報》中出現了一些圖和文承擔不同意義的故事畫。在1935年第1卷第14期的《捉小鳥》(圖9)中,畫面表述了與文字不同的內容。愛姑想要把籠子里的小鳥拿下來,卻因為不夠高,小鳥沒拿到,自己反而跌了一跤。這時愛姑道:“有志者,事竟成;想個好方法,我一定要拿來玩玩。”[33]在文字中,作者并沒有寫明這個好方法是什么,但在圖畫中我們知道,這個好辦法是踩到哥哥的背上,把鳥籠拿下來。顯然,這個故事畫的作繪者了解,如果將這個好辦法以文字的方式說明,不僅內容冗雜,而且并不會帶來迅速閱讀圖像后,對這種所謂“好辦法”的會心一笑。在這里,圖畫不僅僅是作為文字故事的解釋說明,而是和文字一起,參與到故事的敘事中來。

圖9 《捉小鳥》
圖和文之間形成良好的藝術感染力也是圖文合奏的另一種形式。在《天氣好,向外跑》的故事畫中,極富有韻律感的童謠和質樸童趣的水墨繪畫相互配合,獲得了單一圖像或單一文字都不能取得的效果。現代圖畫書的重要標準就是圖畫和文字配合之后,能夠取得“圖×文”的效果。而《小朋友畫報》中一些故事畫的藝術實踐,給予了轉型時期的圖像敘事以更多的可能性。
結 語
促進兒童文學現代化進程的,不是只有文字,還包括在兒童報紙、雜志中廣為流傳的圖像內容。圖像因其表述方式的特殊性,在畫面內容中會展示更為具象、更為直觀的歷史遺留信息,這即是美學術語“出位之思”的真實意涵。當圖像參與敘事,并與文字相互結合時,不同的圖文組合方式會引發文學內部的文體實驗。處在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的滑稽畫、故事畫、小畫報、圖畫故事等種種實驗形態,都是圖畫向現代化邁進的體現,是兒童文學文體自覺的表征。從概念上看,文體是“文之體”與“文和體”的語義融合。[34]圖像敘事在向現代轉型時所呈現出的種種傾向——對幼兒游戲天性的寬容和理解、對傳統繪畫技法的吸收和創新、對塑造新國民的意義訴求、對趣味和滑稽的張揚等——在圖畫書藝術高度繁榮的當下仍有諸多借鑒的意義。簡言之,探索《小朋友畫報》中的圖像歷史,有助于我們理解彼時的圖像敘事是如何塑造現代文化,影響成人社會對兒童的認知,并改變兒童的閱讀和生活方式的。不過,需要提出的是,“故事畫”是否是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需要深入研究。同時,《小朋友畫報》的圖文合奏是否代表著現代圖畫書的端倪,應放置于圖畫書文體現代化的整體結構中考察,而這則是一個具有寬度和深度的研究議題。
注釋:
①1934年7月1日,《小朋友畫報》復刊,并將當期期刊設為創刊號。這里的“1935年第1卷第13期”為復刊后《小朋友畫報》的期數。此后的期數,均按照復刊后計算。
②文中圖片均來源于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