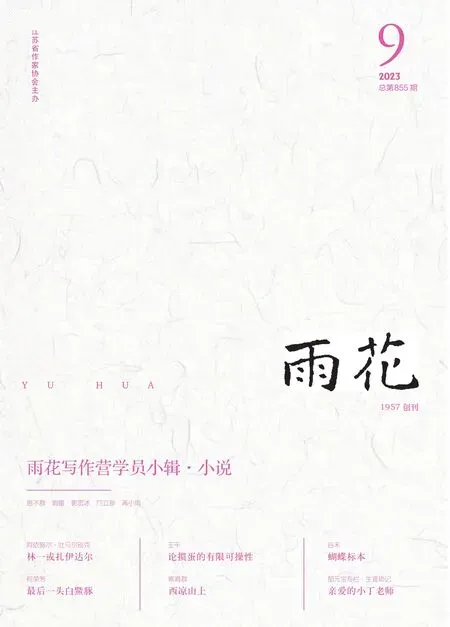滿天星
徐曉華
大年夜放鞭炮,河東河西就數四爺爺家動靜大。
上歲數的人不以為奇。四爺爺綽號滿天星,是個搟匠,幾十年熬硝兌藥,搟的大爆竹最有名,人稱子母雷,足有虎口粗,放的時候點燃引線,“嗚嗚”叫喚著躥上天,母雷迸裂,“轟隆”一聲噴出兩道紫焰,看的人叫好聲未落,又是兩聲巨響,子雷炸開,驚得滿河雪浪滾。
子母雷霸氣,不唯絢麗養眼,更在那摧山震谷的聲響。四奶奶說,當年被子母雷震蒙了,才糊里糊涂嫁過河來。本是上山砍柴下河摸魚的伴,哪曉得四奶奶的爹娘就是不松口。不是嫌家里窮,也不是嫌人口多負擔重。四爺爺雙親早逝,無藤無蔓獨苗一根。論長相,五尺多高,不胖不瘦不聾不瘸,站那里像塊水打浪磨的拴船石。相克呢!四奶奶家祖輩在河邊開草紙坊,搟匠恰好要用草紙搟鞭炮筒子,鞭炮一炸,紙筒不碎成瓜瓤子么。做父母的擔心在情在理。媒人臉厚嘴巧,順著話頭往攏捏,打草紙的遇到搟鞭炮的,好比種稻子的遇到煮米酒的,織布的遇到開裁縫鋪的,順溜溜的好緣分,不是百里無雙,也是十里少有。克不克是個由頭,不放心四爺爺搟鞭炮的營生,那是個忤孽藝,猛藥烈火,不曉得毀了好多人,拆散了好多家庭。河里人操辦婚姻大事,不講風光不求富貴,圖個穩當長遠。
八九歲上,我常去看四爺爺搟鞭炮。家里五間石板屋,兩間廂房當了作坊,屋里屋外一股火藥味。搟鞭炮的人家,忌諱細娃串門,說得的說,說不得的也說。比如兌藥時來一句會不會燃,打引時問一聲炸了怎么辦。口舌不利凈,怕觸了霉頭。細娃又愛動,腳不停手不住,曬的土硝兌的火藥,動得不好會惹大禍。大人們立下規矩,哪個敢去四爺爺家,回來頂著太陽跪沙壩。偏偏四爺爺要試引線快慢,試藥力軟硬,早早晚晚響鞭炸炮,那聲音走山轉水,直往耳朵鉆。不許去,一群細娃就相約到四爺爺屋后的嶺上聽,邊聽邊數,看是二十四響的“草鞋板”,還是六十四響的“過山龍”。饞得心里發癢,就去林子里撿干柴,荒地上架大火,砍水竹桿、白蠟葉丟火里燒,炸得“噼噼啪啪”,但那聲響哪比得四爺爺的鞭炮,過把干癮還行。
我能去四爺爺家玩,得益于家門口那片棗林。茶杯粗的米棗樹,疏疏密密長了四十幾棵,一年能收三百多斤干棗,蜜甜的米棗不曉得甜了多少河里人的嘴。四爺爺倒不貪吃棗子,也不愛喝棗子酒,他記掛的是棗樹干,那是做搟凳的上好木料。砍回去晾干,裁二尺來長的兩塊拉板,刨成月牙狀,下陰上陽,形似弓背,俗稱月牙扣。搟鞭炮筒子時,用鐵桿裹紙塞進拉板,加木楔調松緊,一推一拉,出來就是拇指長的空心筒子,與和面時搟面杖來去碾壓差不多,這大致是河里人把做鞭炮叫搟鞭炮的來歷。拉板用得勤,要光滑有韌性,普通木材做的搟半個月就起槽,搟出的紙筒厚薄不均勻,跑氣走火,炸的聲響“噗嗤噗嗤”,空蕩軟綿。棗樹木紋細,木質堅韌耐磨,面上起了毛邊,夜間噴口水上去次日又平復如初,搟的紙筒堅實緊密,炸裂聲勁爆。棗木,就成了搟匠的神木。
秋來棗熟,收過棗子,棗葉枯干飄落,樹身收了木水,四爺爺便提著一掛六百六十六響的鞭炮,一大早踏著霜花來我家求棗木。棗與早諧音,求棗木的人得起早,不怕凍雨洗面,不怕霜風刮骨,我母親才會把棗木相送。四爺爺是本族幺房的后人,年紀不大輩分高,是母親看著長大的,為人處世、品行舉止還信得過。四爺爺每次來,母親都爽快地答應,要他去棗園選,看好哪根砍哪根。我心里卻打著小算盤,扯著他的褲腰帶跟到棗園,四爺爺掄起斧頭,我便抱住要砍的棗樹,好說歹說都不放手。四爺爺有絕招,眨眉眨眼哄我,聽話,讓爺爺砍了,給你把大爆竹,沖得比天高。小心思被四爺爺拿捏準了,我便放了手。四爺爺繞樹三匝,手舞足蹈,念念有詞:“畫個平安符,求根發財樹;搟的筒子緊,炸到凌霄云。”樣子像在菩薩面前求福。砍倒棗樹,斬頭去尾,剔枝削皮,脫了衣的米色樹干,摸上去比我臉蛋還滑爽。四爺爺一把好力氣,抓起樹干甩上肩,大腳板踩過結滿霜牙子的荒草,“嚓嚓、嚓嚓”出了棗園,又回頭喊我,想要爆竹,哪天放早學了來家里拿。荒草中散落的木渣,似鞭炮炸裂后的碎紙,淡淡木香,聞起來跟棗子一樣甜。
棗樹肯生發,四爺爺隔年來求一根,棗林卻沒見稀疏。一到開春,風酥雨潤,老蔸上萌三四苗新芽,不出半年就綠茵茵地蓋住了樹兜上的疤。嫩葉搖花,老枝孕果,棗子一年比一年結得厚。母親逢人便夸,搟匠是個旺財的人。
怪不得四爺爺搟的爆竹聲響大,從四奶奶進門,搟鞭炮一色改用書紙,廂房里堆了一大堆。和草紙比,書紙薄、性脆、硬度大,不像草紙綿軟、厚實,雖比草紙價錢貴,搟的鞭炮卻不容易受潮,存半年后燃放,響聲還是脆蹦蹦的,有紅白喜事的人家格外喜歡。河里人從娘肚子落地,活到埋進岸邊的砂土堆,鞭炮聲里接生,鞭炮聲里成家立業,鞭炮聲里入土,一生周周轉轉,總離不得鬧熱的鞭炮聲。也難怪,清江河撞峽沖灘,轟轟嘩嘩的浪濤聲灌滿了日子,生死都愛熱鬧。熱鬧熱鬧,熱的是人心齊,鬧的是動靜大,若沒鞭炮助威,或者鞭炮聲疲沓,熱鬧就像大人穿肚兜,短了一截。
這與講排場不沾邊。清江河邊山大峽深,人戶稀朗,走人家放掛鞭炮,是放個信號,知會主人家有客登門,免得迎客時頭沒梳臉沒洗,手慌腳亂,禮數不周。上河下河的人,聽鞭炮聲疏密,就曉得主人家人緣好壞,聽響聲長短,就明白來人與主人家的親疏。挑在一丈二尺長竹竿上放的“千字頭”,多半是至親。提在手上放的“蜈蚣腿”,響聲跑不過河就落了,那是邊近的鄉鄰。娶媳婦、嫁姑娘、華堂落成、賀壽星、添丁口、開孝門,執事單上少不了一個幫忙放鞭炮的。大門外候著,見客人來,老遠奔去接過鞭炮,朝禮房吆喝一聲:舅舅人家,禮炮三千響!河那邊的大姑爺,禮炮兩千八百響!賬房先生要一一上賬,主人家往后好還人情。同燒一山柴,共飲一河水,少不得你來我往,姑送草帽遮太陽,嫂還斗笠擋風雨,人情世故就如河水奔灘,綿綿不絕。
過事的人家鞭炮聲起,四爺爺就跑到嶺上,豎起耳朵聽。遠親近戚,有放本地鞭炮的,有放瀏陽花炮的,憑聲響,還是自家搟的土鞭炮鎮場子。不是自夸,是熬的土硝藥力威猛。“硝多響,磺多炸,火蝕多了煙子大。”硝是橫力,硫磺是直力,火蝕是助燃的,分量搭配不同,炸的聲響氣勢不同。按師傅傳下來的口訣,耍不得奸猾取不得巧,搟匠的飯碗端在四方四鄰的嘴巴上。鞭炮是響器,會開口發聲,河東響河西聽,婆家放娘家聽,主家放旁人聽,好壞都擺在明處。一場事辦下來,賓客聊得最多的是鞭炮。嘴乖巧的說,嘿,劈天一炸雷,雷公推的霹靂車巡河來了。藏不住話的說,“噗噗噗噗”,王母娘娘蟠桃宴上吃壞了肚子,憋出幾個悶屁。說話愛轉彎的,就打比方,是吹火筒呢,這頭吹氣那頭冒煙。挖苦鞭炮師傅填藥時手緊,盡是空心筒子,缺斤又少兩。
“三八火蝕二八磺,土硝十分聲嗓壯。”祖師爺傳的火藥配方,一斤硝兌三兩八錢木炭灰、二兩八錢硫磺粉。劑量是死的,人是活的,好搟匠懂得隨季節變化斟酌加減。三伏帶秋,天干物燥,藥要減半分,太足,炸成一鍋粥,失了節奏,千字頭的只當得五百響,買家不劃算。寒天冷凍,梅雨季連陰天,引線易潮,結火慢,響聲前后脫節,半天“哽”一聲,聽起來差勁。過喜事的走引藥要加幾錢,炸起來“噼里啪啦”,一聲抓著一聲,又順暢又喜慶。過白事的要多加木炭灰,煙火氣繚繞,隱了孝棚靈堂,罩住白綾祭幡,哭爹喊娘的場面淡了,逝去的人走得從容。看似易得的木炭灰,講究還多,深山里砍回五倍子樹,挖土坑悶燒,燒到樹皮卷出一浪浪的花,退火冷卻,拿木槌捶成細末,羅篩篩出來,抓手里比月光還柔和,兌的火藥發火穩,爆發力均勻,聲響宏闊。圖省事,火塘里燒的杉木炭灰也可用,只是聲響碎,跟吹破嗩吶差不多,缺了陽氣。搟出這樣的鞭炮,搟匠把臉塞褲子里才敢見人。
四爺爺最怕聽到斷魂鞭。尤其在夜里,“噼啪噼啪”地爆響,像密林的老鴉叫,一聲聲扎得心里發慌。叫什么呢?十歲是一生,百歲是一死,變一世人就躲不開生門進死門出,凡人又沒吃仙丹,哪有長生不老。船破要靠岸,竹老要回頭,窩囊也好風光也好,一把揉進硝煙里,風一吹就干凈了,剩天寬地闊,水清沙白。斷魂鞭是分割陰陽的,不可提早編好,搟匠哪能望人死。有老父老母病體沉重的,家人臨時來訂,四爺爺不談價錢,只悶聲問要單還是雙。單送男子雙送女,搞錯不得。編的時候,以引線為準,送男仙的第一顆從陽面編起,送女仙的第一顆從陰面編入。這樣的規矩一整套。鞭炮筒子搟好后,打捆成餅,送亡人的要捆“飽角”,辦喜事的要捆“餓角”。鞭餅為六邊形,又叫蜂窩餅,飽餓之分,無非飽角每邊捆十九顆,餓角捆十八顆。十八之數,亡人最忌,十八層地獄,哪個愿去哪個敢去?再者,飽含圓滿、充盈之意,是對亡人的褒獎;餓具殘破、缺憾之狀,告誡活人不可貪多求全。生人不免死人意,一口氣不來了,凡事死者為大,苦難丟開,快活帶走,幾掛鞭炮,是灑淚送別也是真心祝福。十九為奇數,十八為偶數,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男主陽,女主陰;以陽滋陰,以陰壯陽,陰陽互濟,正應了古話,“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陰陽錯位,對死者是大不敬。人窮骨頭重,在生不論功過悲苦,卻在乎死后的聲名,編得若有差池,搟匠會夢見討債鬼。
記不清斷魂鞭里,送走了多少村人族眾,有兒孫滿堂走順頭路的,也有歲不滿十的化生子。做人一世,在生各有定分,各有辛勞,耕田耙泥頂天立地,孕兒育女日辛月苦,掉氣那一刻,聽不到親人哭喊,卻聽得到斷魂鞭響。不在乎長短多少,要的是順溜響堂。鞭炮聲腳頭快,會把生前走過的路,再走一回;到過的地方,再看一次;還要翻山過嶺去呼親喚友。送走一個,四爺爺的心里就棗木兜一樣結一個疤。逢冬春換季,疫年災月,聽斷魂鞭響得密,就無邊無際地想,要是黃泉路上的人一起喊一聲,比子母雷更霸氣吧?峽口的老巖會不會喊塌?清江河水會不會倒流?那一頭,閻王爺會不會派牛頭馬面放一掛引魂鞭,在奈何橋上接一程。生也有涯,死也無涯,有斷魂鞭壯行,帶著人間煙火,總不懼那忘川河扎骨的冷氣。
怕歸怕,有人上門,生意要做,還得提起精神。軋一刀新買的皮紙,拿起竹引尺,把火藥倒入引槽,按下開關,漏一線引藥到裁好的紙上,左手牽紙右手捻引,一口氣捻好七七四十九根引線,從鞭餅上選飽滿干爽的鞭,一個壓一個、一線串一線排齊編緊,不能讓斷魂鞭為死者惹口舌。遇到連陰天,濕氣潤了鞭引,響得斷斷續續,會有人說,看嘛,做人不耿直。偶爾有一兩顆啞鞭,又有話說,哪件事后人沒安排妥帖,還在記掛著,走得一步三回頭。做齋的掌堂法師,講得更神秘,硝煙騰空起,后人百事順遂;煙塵貼地走,后人多少要受些磋磨。四爺爺當然不信,他試過多少次,季節不同,陰晴不同,煙氣跑下坡、沖上坡,東飄西蕩,那是跟風走。風是煙騎的一匹快馬,過得懸崖,穿得密林,爬得天梯,鉆得地縫,和死者的德行操守無瓜無葛。人有善惡勤懶,灑多少汗、流多少血、淌多少淚,一點一滴都滲進了河邊的土里,前人墾荒,后人耕種,種花花開,育苗苗壯。說長道短的,倒不是嘴賤,是借鞭炮聲為幌子,點醒活著的人:做事要踏實,做人莫虧心。曉得卻不解釋不爭辯,人各有悟性;到死還不通透的人,跟一顆啞鞭有何分別?啞鞭也不是真啞,引線被炸斷了,小孩子撿起來剝開紙筒,把火藥倒在紙上,拿柴火頭點燃,“噓”的一聲,亮光四射。那亮光里,吃過的虧、享過的福、慪過的氣眨眼間就沉入了黑夜,計較來計較去,還不如爽爽快快走,有鞭炮聲開路,來生就不會迷失。
直聽到斷魂鞭落,河風送過來呼天喊地的哀號,四爺爺才閉起眼睛,哼起了送亡人的挽歌:
噼噼啪啪起煙塵,
人生好比一陣風;
風來風去風還在,
可憐人死不回來。
遇到村人新婚大吉,新郎官來買接親的鞭炮,四爺爺是要討喜錢的。編個雙鳳朝陽,總計一千二百響,兩頭各編四百響后,就停了手,望著新郎官說,哎呀,這幾天時晴時雨,坐久了腰桿發癆。懂事的新郎官就掏出準備好的紅包遞過去。四爺爺推辭說,又不是外人,不興這么客套。新郎官說,勞累您家了,表示個心意,千萬莫推了,再推,就是看不起人。那時的紅包,也就一塊二毛錢,家境寬裕的頂多包兩塊四。幾番推辭,四爺爺才笑瞇瞇地接了,說,好嘛好嘛,沾點年輕人的喜氣。連忙把中間的四百顆編了,又格外送十二顆子母雷,一起用紅紙包好,雙手寄給新郎官,邊恭喜邊說,我也沒得別的賀禮,幾顆大爆竹還響亮,湊個熱鬧。等新郎官告辭,四奶奶就笑四爺爺,看你這要喜錢的,子母雷賣二毛五一顆,十二顆是三塊錢,還倒貼呢。四爺爺說,貼錢沾一身喜氣,賺一村人氣,心里得了爽快,哪里虧呢。
熬硝舂藥,打引編鞭,四爺爺跳起腳忙,四奶奶是搭不上手的。不讓干,說毛手毛腳,做不好細活路。沒話找話說,四奶奶竹繃子上刺繡,針去鳥兒有聲,線走蟲兒會吟,手巧著呢。原是疼四奶奶,怕有個萬一,要命只要一條,要殘只殘一個。四爺爺真想偏了,進了一家門,就是一家人,一鍋熱飯舀兩碗,一床破絮蓋一雙,雨水落在井水里,分得出你我嗎?四奶奶故意抱怨,唉,哪有說的那么兇險,你是怕我學會了把手藝帶回娘家!一個大男人,心沒針眼大,吃一河水長大的,不曉得河里人的本事,下水能擒龍捉鱉,進山敢打虎獵豹,最差也會犁田打耙播谷種豆,老天爺不厚一個薄一個,還在出氣的,各有各的養活,誰稀罕一個搟匠!
四爺爺不吱聲,聽煩了,就找個空日子拉著四奶奶去趕場,不買東賣西,偏去賣鞭炮的攤子上湊熱鬧。一排七八個搟匠,有的半邊手掌麻利地捻鞭引,有的剩兩根指頭拿竹篾捆鞭餅;有的一臉血痂,笑比哭還難看;還有的一張陰陽臉,白斑套黑點,大白天看起來都嚇人。有個搟匠,下嘴唇缺了一塊,把不住風的嘴說的話卻好聽:嘿,難怪四師傅無災無難,順順遂遂,原來屋里有個觀音菩薩保佑。四爺爺臉上就堆了笑,連連點頭,是呢是呢,托福托福。你是托祖師爺的福哦,會搟幾顆子母雷,硬是把觀音菩薩哄到了懷里。那缺嘴笑著補了一句。搟匠們說笑,四奶奶一句都沒聽進去,眼睛盯著案板上的鞭炮,生怕太陽曬熱了,它們會猛然炸起來。
回來的路上,四奶奶走得搖搖晃晃,渾身上下的骨頭像被誰抽走了,最愛聊白的人,一路半句話不說。四爺爺覺得怪,去的時候爬上坡腳快身輕的,回來走下坡卻拖不動腳,肯定是被幾個搟匠的樣子嚇到了。可嫁了搟匠,哪能不在驚嚇里過日子。按道理,結婚十幾年,日日擔心夜夜怕,早就是槍桿上的麻雀——嚇大膽了,還有什么好怕的。便說笑話,有個搟匠愛喝酒,酒醉了插鞭引,把媳婦繡花的絲線當引線剪了,插得五顏六色,歪歪扭扭,第二天買鞭炮的人看到了,笑得岔氣。四奶奶根本不搭腔,喘著氣問,那些人缺這缺那的,哪門還在做搟匠?四爺爺望著天說,唉,做一天搟匠就是一輩子的搟匠,缺這缺那就不活了?殘手殘腳還能搞別的嗎?熟門熟路將就著找口飯吃,天天和火藥硝石打交道,心氣熏烈了的,不到爬不動的時候,搟匠不能拖累人。這些話,是不是早就想說?是心里話吧?四奶奶紅著眼睛問四爺爺。四爺爺不敢看四奶奶,扭頭看著路邊的荒草,平平和和地說,又不是故意唬你的,你都看到了,不讓你沾手,為你好呢。四奶奶嘆口長氣,慢吞吞地說,唬我有用嗎,你就不怕?好幾回夢里喊跑啊、跑啊,要不,停了搟凳吧,種田也能生活。四爺爺說,好手好腳的不愁找不到飯吃,十五六歲學的手藝,做了快二十年,不是我想停就停得住的。對河兩岸的人家沒人搟鞭炮,逢年過節,大事小事,半點響動沒有,死氣沉沉的,村不像村,戶不像戶,過啞巴日子會把人悶死的。有個雞叫狗咬,有幾聲鞭炮響,人家才曉得屋里有活人,就像清江河,春不起波夏不滾浪,還叫河嗎?四奶奶說,你不做天底下就沒鞭炮賣了?硬是要做,我也攔不住,求天老爺保佑吧,你也不要逞英雄,一個人做不過來的事,喊我搭個幫手,多只眼睛看,周全些。四爺爺搖了搖頭說,天老爺唯獨保佑我么,想開了,小命是天老爺給的,要取走也留不住,要哪樣是哪樣,該來的躲不掉,躲得掉的不是禍,怕,就不得做搟匠。
那以后,收書紙的活路落在四奶奶頭上。一擔竹筐一桿秤,到學校收,也到有學生的人家收。多半收的是舊報紙、用過的作業本,極少有舊書賣。四奶奶會親近人,到學校去,摘點當季的菜蔬、瓜果送給食堂做飯的師傅,一來二去熟了,就放點零錢委托幫忙收,過十天半月去結一次賬,少跑好多路,還不打空回轉。有時手頭不方便,就拿鞭炮換,一個“千字頭”折合八斤書紙。學校用得著,到期末考試后,總分前一、二、三名的學生,老師要登門給家長報喜,窮得請不起鑼鼓班子,總要響響亮亮炸一掛鞭炮。于河邊人家,這是天大的喜事,后人肯讀書、成績好,比桃花魚撞網還高興。鞭炮聲里,幾家歡喜幾家愁,有的家長拿著娃兒不及格的成績單慪氣,好多娃兒挨訓、挨竹片抽,卻也激起了更多娃兒發奮用功。人們盼著來年,報喜的鞭炮會從村口一直炸到自家場壩里,炸得火樹銀花,炸得五子登科。
那樣的鞭炮聲,四爺爺聽得滿臉泛光,忍不住拿幾顆子母雷,跑到嶺上放,騰地而起又從天而降的轟隆聲,交織、回旋在清江河的上空。恭喜、恭喜、恭喜啊。送喜報的一路人馬,順風聽到四爺爺扯開嗓門喊的恭喜聲,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唉,四師傅的手藝真是一絕,人又熱心,要是膝下有個一兒半女,喜報肯定往他屋里送。
書紙收回來,要鋪在石場壩曬幾天,除霉除濕。四奶奶就搬個板凳坐階檐上,拿把響篙趕雞子,有時也隨手挑幾本書看。到底是老高中生,懂得多,我去玩的時候,常給我擺古。她最喜歡講《西游記》,講孫猴子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鬧,講過火焰山偷芭蕉扇,講唐僧師徒經九九八十一難取到真經。有回還考我,問四大發明,哪個跟搟鞭炮有關。我想都不用想,說,火藥唦。又問,火藥是哪個發明的?我想了想說,老師講是古時候煉丹的道士。四奶奶笑著說,不對,是你四爺爺的祖師爺發明的。廂房里正在捶炭灰的四爺爺聽到了,放下手里的活路走到門邊說,吔,難得你說一回搟鞭炮的好話,是的呢,我們搟鞭炮的祖師爺有兩個,一個叫李畂,一個是藥王孫思邈,弄不清誰是老師傅,一個發明了拿竹筒裝火藥,以煙火氣驅邪魔瘴氣,一個發明了卷紙筒子做鞭炮,把天下的日子炸得熱熱鬧鬧的。
四爺爺怎么兌鞭炮藥,從沒讓我看過。一道門檻攔著,廂房里藏著什么稀奇,外人來了不讓進,門里門外說話。四奶奶進去拿東西,也是前腳進后腳出,多停一會兒,就被四爺爺推出來了。只有在石碓窩里舂硫磺粉、舂炭灰時,才讓我站在他身后瞄幾眼。小心得很,撕一塊軟和的舊衣服布,包住了鐵碓頭,舂的力度極柔和,碓頭抬得很低,動作像演木偶戲的。每次我去四爺爺家,母親都要再三囑咐,不要亂說話,最好當啞巴,更不要隨便動東西。我嘴里答應,心里卻不服氣,難道一句話能把火藥點燃嗎。看四爺爺篩灰、拌粉,大氣都不敢出,憋得難受。四爺爺忙一陣,歇氣喝茶時,我想問他,鞭炮到底怎么搟成的,又怕說錯話。四爺爺可能猜到我想問什么,就講,搟鞭炮手腳多,從開工理紙到編好,一起是“七十二道半,點火還不算”,半道是什么?在筒子上打孔裝鞭孔是一下打兩個,只算半道;點火是放鞭炮時的事,所以不算。我心里想,真麻煩,比解方程的步驟還多。終于憋到要回家吃晚飯了,才喊一聲,四爺爺,我回去了,今天我一句話都沒說,要是你的火藥炸了,莫怪我啊。四爺爺嘴里嘀咕著,這娃娃,讀書讀成個憨家伙了。
很多年后見面,四爺爺還會笑話我,每次都說,憨家伙回來了。大了,我才明白忌口何止是河里人的風俗。不論哪個地域哪個行當,做什么事,誰不想圖個吉利?好比開車出門,要是門衛來一句,慢點開,莫撞車,鬼才樂意聽呢。何況搟鞭炮的,手工兌藥,是極危險的,稍微分神或者心有波瀾,火候、力道差之毫厘,都可能引發不可收拾的禍事,忌口,就不是會不會說話的小節了。不過,四爺爺出事,跟我小時候不會說話沒半點牽扯,倒是跟我參加工作后,托母親給他傳的一個口信,是有牽連的。事隔二十年,想起來心尖都疼。
那時我在老家相鄰的鄉鎮當派出所長,在市里開完治爆緝槍工作會后,順道回去了一趟。跟父母親聊到工作,說馬上要禁止小作坊生產鞭炮,一刀切的政策,以后說不定鄉鎮農村都要禁鞭。父親聽說后,一口一個好,說那東西早就該禁,好幾個學生家長做鞭炮出了事,有一家慘得很,房子炸塌了,兩個大人走了,萬幸孩子在上學,逃過一劫,好端端的一家人,剩個孤兒,慘呢。母親就和父親斗嘴,指著屋頂說,下這么大雨,你在全村轉一下,看有幾家漏雨?漏雨的都是懶家伙,平素不撿瓦,倒怪雨下大了。世上一天死那么多人,未必都是搟鞭炮炸死的。遠的不說,就說我四叔搟了半輩子鞭炮,活得好好的。父親嘴巴也不笨,反問,你要不怕,怎么反對老大去給四叔當學徒,還把娃娃打一頓。母親惱火地說,故意吵是不是?老大那火爆脾氣,做得細活路嗎?那行,等你百年歸山了,要后人們不聲不響把你拖出去埋了。父母一輩子都愛斗嘴,我也勸不住,只好說,你們說的都有理,但是,小作坊肯定是不能搞了,確實不安全。
我能理解父親,一個教書匠,只愛看書寫字,一輩子樹葉落下怕砸腦殼的人,那些年,不管我們多么羨慕別人家放爆竹,父親總是不肯買的,他清楚,這么個家庭,經不起任何驚嚇,但最終卻拗不過母親,總會從四爺爺家買些回來,氣呼呼地喊我們攢勁放,放完了再買。我也理解母親,村頭村尾坡上坎下,大事小事哪有不放鞭炸炮的,祖祖輩輩養成的風俗,說丟就丟,比割肉還疼。
斗嘴歸斗嘴。母親連夜就去了四爺爺家。去說了什么,我也沒問。等我去單位的第二天傍晚,父親打來電話,催我趕到鎮上醫院去,說四爺爺出事了。想問一聲人怎么樣,四奶奶呢?還沒問,父親就掛了電話。
一路上想著種種情景。顛簸幾十里路趕到老家鎮上的醫院,從開著的病房門一眼看到站在病床前的四奶奶,懸起的心稍微平緩了些。人還在病床上,四奶奶還能伺候病人,就不是最壞的結局。剛踏進病房門,紗條裹住的四爺爺就開口了,憨家伙回來了啊?沒事沒事,就是把汗毛燒掉了幾根。說話氣局還足,只是嘴巴裹住了,聲音有些悶,像筒子沒搟緊的爆竹聲。安慰了四爺爺幾句,四奶奶就喊我出去。在門口,才跟我說,聽你媽說馬上要關作坊,他就想趕緊搟些子母雷存放著,一輩子就這手藝長臉,怕以后搞不成了。哪曉得心里急,炒藥時多加了一根柴,火猛了些,鍋里轟的一聲燃了,等我跑過去,人都被沖滾了,倒在地上抓頭發上的火苗子。天呢,幸好是燃,不是炸。
正說話,鎮上派出所的一位老同志來問情況。我心里明白,事故是要處理的,得給社會一個交待。沒等他開口,我先說了,等傷者治愈了再處理吧,搟了半輩子鞭炮,靠這個養活,又傷了,肯定想不通,盡量多做做工作,是我的四爺爺,我就不便多說了。老同志點了點頭,說,兩難呢,這幾天下鄉,都在關鞭炮小作坊,村里的多數人還是不理解,有人開玩笑,以后過年過節是不是學祖宗,燒竹子燒白蠟葉炸?可一起起的事故,人命關天,不下重手管又怎么行呢?彼此是同行,沒有挑明的話,大家都懂。我只盼著四爺爺能早些恢復,也盼著辦案的,體諒搟匠的艱難辛苦,從輕發落。
三個多月后的一天,我去拘留所,接拘留滿期的四爺爺。他體質好,二十幾天就出院了,那陣我在外地出差,沒幾天回老家去看他,路上我一直在想,四爺爺的一張臉是不是丑得怕看了。
“哐當”一聲兩扇鐵門打開,四爺爺抱床被子,小跑著出來了。那時陽光正好升上山梁,亮悠悠的光柱迎面照在四爺爺方正的臉上,瘢痕像一層雪白的霜牙子,上面撒了一顆顆黑芝麻。
我喊了聲四爺爺。他笑嘻嘻地說,憨家伙,還認得我嗎?猜猜看,里面的人怎么叫我的?
面對一張泛白的肉皮上布滿黑點的臉,能怎么叫?叫麻子?或者更缺德的叫癩蛤蟆?我這樣想,沒說出聲,怕四爺爺受不了。
想不到子丑寅卯吧,叫我滿天星呢。四爺爺竟擠出了滿臉喜氣。
滿天星!
取這外號的人,一定放過子母雷,記得那沖天而起爆出的紫焰,記得那漫天繁星一樣的閃閃爍爍。
取得真好,雖是玩笑,卻又體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