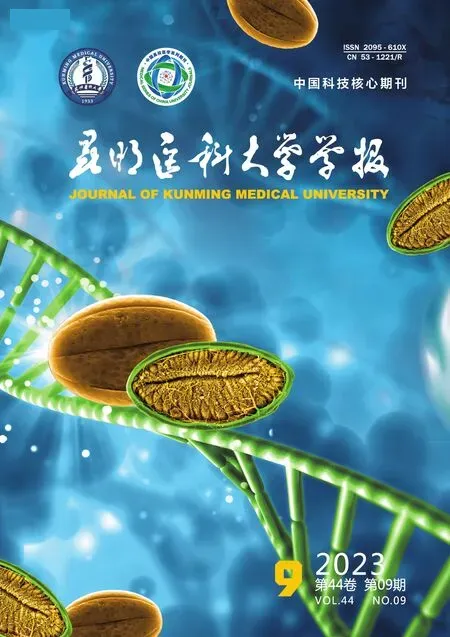腹腔鏡與開腹完全結腸系膜切除術對結腸癌患者血小板活化、并發癥發生率及腫瘤復發的影響
張權昌,吳喬聯,劉 宇,趙 欣
(昆明市第二人民醫院普外科,云南 昆明 650000)
結腸癌是中老年群體多發惡性腫瘤,隨著飲食結構及生活習慣變化,在年輕群體中發生率越來越高[1]。該病早期無特異性癥狀,多數患者確診即為中晚期,且有較強的轉移性,治療難度較大,預后效果差[2]。完整結腸系膜切除術(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作為結腸癌近年新型治療手段,在改善免疫功能、延長患者生存期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且經多項研究[3-4]證實。既往CME 采用的開放手術,創傷較大,術后恢復時間長,并發癥較多[5]。隨著腹腔鏡技術的發展,腹腔鏡輔助下CME 在臨床應用愈加廣泛,其創傷輕微、可促進術后早期病情恢復[6]。有研究[7]顯示,手術操作會導致血小板活性變化,進而影響凝血功能,不利于患者預后。目前,臨床上關于血小板活性在腹腔鏡CME 術后的變化情況,臨床鮮有報道。本研究進行對照分析,旨在進一步探究腹腔鏡輔助下CME 治療結腸癌的臨床優勢,以為后續患者治療提供依據,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遵循《世界醫學會赫爾辛基宣言》[8]進行前瞻性對照分析,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后實施。選取2020 年1 月至2022 年1 月昆明市第二人民醫院80 例結腸癌患者,參照《中國結直腸癌診療規范》[9]相關標準,并經影像檢查、實驗室檢查確診。入選條件:均為右側結腸癌患者;具備手術指征;均為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10](AJCC)Ⅱ~Ⅲ期;無結直腸手術史;患者或家屬簽署同意書。排除條件:臟器功能不全患者;遠端轉移患者;凝血功能、免疫功能缺陷者;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患者。以電腦隨機法分為觀察組(n=40)和對照組(n=40)。
1.2 手術方式
患者入院后完成血常規、影像、病理、生命體征等相關檢查,并給予對癥支持干預,待生命體征符合手術標準后實施手術操作。對照組行CME,患者仰臥予以全身麻醉,于腹正中做切口建立工作通道。探查腹腔及腫瘤情況,清掃可疑的腫瘤轉移組織,分離內結腸系膜及血管,清掃血管根部淋巴結,夾閉并切斷腸系膜下血管,根據情況行結腸切除或斷端吻合。觀察組行腹腔鏡CME,患者取位、麻醉同對照組。于臍上緣行切口穿刺建立13~16 kPa CO2氣腹,置入腹腔鏡探查腹腔。分別于左腋與臍水平線焦點、下腹中線恥骨上2 cm、劍突下2 cm 分別做操作孔與輔助操作孔。采用常規中間入路,分離并切斷腸系膜使腸系膜靜脈暴露,清掃周圍淋巴結,結扎血管根部,依次將回結腸、右結腸與中結腸血管右支分離,繼續行淋巴結清掃。對Toldts 間隙進行拓展,使腎前筋膜、十二指腸與胰頭位置暴露,切除大網膜,避開回盲部分離腸系膜及肝曲至升結腸,使內側回腸貫通,游離遠端回腸,于右腹部小切口切除病灶。
1.3 觀察指標
(1)圍術期情況:手術時長、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肛門排便時間、肛門排氣時間及住院天數;(2)淋巴結清掃情況:記錄2 組各期淋巴結清掃數量及陽性、左右半結腸淋巴結清掃數量;(3)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記錄2 組切口感染、吻合口瘺、淋巴瘺、不完全性腸梗阻、下肢深靜脈血栓等發生率;(4)血清炎性指標:采集患者術前及術后1 d、5 d 外周靜脈血5 mL,離心15 min 分離血清低溫冷藏。以ELISA 測定白細胞介素-6(IL-6)、C 反應蛋白(CRP)水平,試劑盒購自Siemens Healthcare Diagnostics Products Limited;(5)血小板活化指標:以流式細胞儀(碧迪生物科學,型號:BD FACSCanto)檢測術前及術后1 d、5 d 血小板-中性粒細胞聚集體(PNA)、血小板-淋巴細胞聚集體(PlyA)、血小板-單核細胞聚集體(PMA)、血小板-白細胞聚集體(PLA);(6)術后隨訪1 a,觀察2 組患者復發與無復發生存情況。
1.4 統計學處理
以EXCEL 校驗,采用SPSS25.0 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描述,以t檢驗,多時點比較以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當理論頻數T≥1 且 < 5 時,采用校正χ2檢驗,當理論頻數T≥5 時,采用未校正χ2檢驗。均為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2 組基線資料
2 組年齡、性別、體重指數、位置、AJCC 分期及合并疾病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
表1 2 組基線資料比較[()/n(%)]Tab.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n(%)]

表1 2 組基線資料比較[()/n(%)]Tab.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n(%)]
2.2 2 組手術相關指標
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術中出血量與術后引流量較低,肛門排氣、排便時間及住院天數較短(P< 0.05);2 組手術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 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Tab.2 Comparison of surgery-related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2 2 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Tab.2 Comparison of surgery-related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2.3 2 組淋巴結清掃情況
2 組Ⅰ期、Ⅱ期淋巴結清掃數量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Ⅲ期淋巴結清掃數量及陽性、左右半結腸淋巴結清掃數量較高(P< 0.05),見表3。
表3 2 組淋巴結清掃情況比較[(),個]Tab.3 Comparison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ach]

表3 2 組淋巴結清掃情況比較[(),個]Tab.3 Comparison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ach]
*P < 0.05。
2.4 術后并發癥發生率
觀察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2 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n(%)]Tab.4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2.5 血清炎性指標
2 組術前血清IL-6、CRP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術后1 d 至5 d,2 組血清IL-6、CRP 先升高后下降(P< 0.05),觀察組術后1 d 血清IL-6、CRP 均低于對照組(P< 0.05),2 組術后5 d 血清IL-6、CRP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5。
表5 2 組血清炎性指標比較()Tab.5 Comparison of serum inflammatory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5 2 組血清炎性指標比較()Tab.5 Comparison of serum inflammatory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與術前比較,#P < 0.05;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5。
2.6 血小板活化指標
2 組術前PLA、PlyA、PMA、PNA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術后1 d 至5 d,2 組PLA、PlyA、PMA、PNA 先升高后下降(P< 0.05),觀察組術后1 d PLA、PlyA、PMA、PNA 均低于對照組(P< 0.05),2 組術后5 d PLA、PlyA、PMA、PNA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6。
表6 2 組血小板活化指標比較[(),%](1)Tab.6 Comparis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

表6 2 組血小板活化指標比較[(),%](1)Tab.6 Comparis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
與術前比較,#P < 0.05;△P < 0.05。
表6 2 組血小板活化指標比較[(),%](2)Tab.6 Comparis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ˉ±s),%](2)

表6 2 組血小板活化指標比較[(),%](1)Tab.6 Comparis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
與術前比較,#P < 0.05;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5。
2.7 腫瘤復發與生存情況
2 組均未出現脫落病例。觀察組術后1 a 復發1 例,無復發生存率97.50%(39/40);對照組復發7 例,無復發生存率為82.50%(33/40)。觀察組術后1 a 無復發生存率低于對照組(P< 0.05),見圖1。

圖1 術后1 a 無復發生存曲線Fig.1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curve 1 year after surgery
3 討論
隨著診斷技術發展,結腸癌早期診出率不斷升高,為結腸癌早期治療提供了有利條件。手術作為結腸癌主要治療方案,其主要目的是盡可能切除病灶,延長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質量,部分患者及時接受治療可獲得治愈可能[11]。CME 是結腸癌現階段常用治療方案,其以胚胎可解剖學為基礎,盡可能減輕損傷,抑制腫瘤細胞轉移。而Sica GS 等[12]研究顯示,傳統CME 忽略升降結腸系膜存在,易導致淋巴結殘留,增加復發風險,同時術中切口較大,腹腔感染風險較高。
近年腹腔鏡技術迅速發展,推動了CME 應用進程。腹腔鏡技術將微創技術與快速恢復理念有機結合,可有效彌補開放CME 的不足,促進預后改善。腹腔鏡CME 較開放CME 具有以下優勢[13-14]:(1)腹腔鏡直視下操作,可清晰辨別腫瘤邊界,同時銳性分離組織,無撕裂情況,有助于腫瘤徹底切除,預防術后復發;(2)切口直徑較小,組織損傷輕微,能降低出血量,減輕對微循環的破壞,提高安全性。本研究中,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術中出血量與術后引流量較低,肛門排氣、排便時間及住院天數較短,淋巴結清掃數量較高(P< 0.05),這與陸峰等[15]研究基本一致,而手術時間與陸峰等[15]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與樣本量有關。外科手術會對機體造成損傷,影響患者預后。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較對照組降低(P< 0.05),這可能與觀察組手術創傷輕微、術后病情恢復較快有關。為進一步證實腹腔鏡CME 的近期療效,本研究術后隨訪1a 表明,觀察組復發率低于對照組,無復發生存時間長于對照組(P< 0.05),由此可見,腹腔鏡CME 在預防術后復發和延長患者生存期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筆者認為:該術式可清晰術野,降低腫瘤邊界辨別難度,從而使腫瘤徹底切除。但該術式存在局限性,腹腔鏡CME 中結扎腸系膜血管、清掃周圍淋巴結、顯露腸系膜上靜脈和胰頭被認為是極為復雜的操作步驟,因此,對醫生的技術要求較高。
外科手術雖能有效治療結腸癌,但同時也會引起機體損傷,增加一定治療風險[16]。受圍術期多種因素影響,機體應激反應被激活,促使IL-6、CRP 等炎性因子釋放,加劇機體局部炎癥級聯反應,從而導致組織損傷加重[17]。因此,監測機體炎癥指標濃度變化情況,不僅能掌握機體損傷程度,還能作為評估預后效果的重要指標。本研究經動態監測可知,術后1 d 2 組血清IL-6、CRP水平均較術前升高,但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5),表明相比開腹CME,腹腔鏡CME 具有操作精準、創傷輕微等多種優勢,而2 組術后5 d上述炎癥指標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與病灶切除、術后病情逐漸恢復相關。另外,血小板作為血液重要組成部分,在維持毛細血管壁完整方面起著重要作用[18-19]。Ren J 等[20]研究指出,血小板活性增強會影響機體凝血功能,促使血栓堵塞血管,進而影響患者預后。本研究中,術后1 d 2 組PLA、PlyA、PMA、PNA 均較術前升高,說明2 種手術方式均會促使血小板活化,而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 0.05),考慮原因可能是:(1)腹腔鏡手術組織損傷輕,可減少術中失血量,有助于恢復術后血流灌注,改善血液微循環,進而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表達;(2)切口小,操作基本處于密閉狀態,能降低感染對局部組織影響,也是減緩血小板活化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2 種方式行CME 治療結腸癌手術難度相當,但腹腔鏡CME 術中出血量較低,能抑制血小板活化,減輕炎癥反應,促進病情恢復,同時淋巴結清除率高,降低復發風險,延長生存期,且能減少并發癥發生。但本研究隨訪時間較短,遠期療效尚未明確,有待延長隨訪時間作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