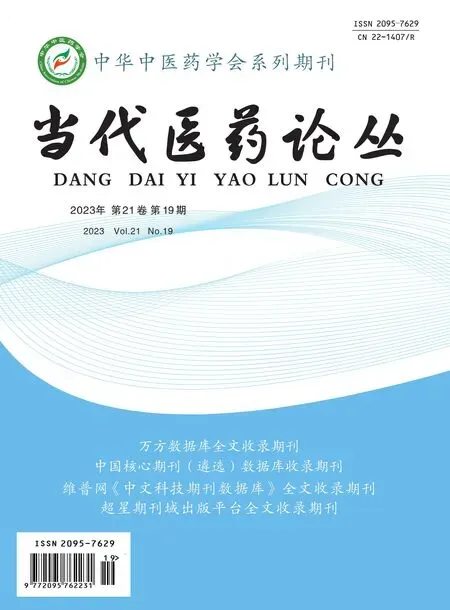BAG.1蛋白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表達及與患者預后關系的研究
李元明,郝 娟,伊斯拉木江?吐爾遜,陳家驊
(1.新疆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63;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當前全球發病率、致死率最高的惡性腫瘤即肺癌,且近年來其發病率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約有80%的肺癌為非小細胞肺癌。目前,多學科聯合治療已取得長足進展,但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5 年生存率僅為15% 左右。肺癌發生的主要原因為細胞凋亡[1],但非小細胞肺癌的整體發病機制較為復雜,涉及多種基因、蛋白。研究表明,BAG.1 作為一種多功能的蛋白,能夠與多種基因及蛋白進行相互作用,調節細胞增殖。在正常組織中,BAG.1 蛋白一般不表達或呈弱表達,同時其表達情況在不同種類惡性腫瘤中也不盡相同。在一些惡性腫瘤中,BAG.1 蛋白陽性表達的意義及與患者預后的關系尚未完全明確。當前,關于BAG.1蛋白在惡性腫瘤中陽性表達的意義已成為臨床研究的熱點。本文就BAG.1 蛋白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表達及與患者預后的關系進行探討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 年1 月至2018 年1 月我院胸外科收治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共計100 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非小細胞肺癌的診斷標準;接受外科手術及術后病理學檢查;自愿參與本研究。在這些患者中,有男性60 例,女性40 例,年齡范圍30 ~78 歲,平均年齡(56.20±1.24)歲;病理類型:腺癌50 例(其中TNM 分期為Ⅰ期、Ⅱ期、Ⅲ期的患者分別有23 例、16 例、11 例),鱗狀細胞癌50 例(其中TNM 分期為Ⅰ期、Ⅱ期、Ⅲ期的患者分別有12 例、11 例、27 例)。
1.2 方法
術后采用免疫組化二步法對組織切片進行檢測,觀察檢測結果,并對BAG.1 蛋白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表達及與患者預后的關系進行分析。免疫組化試劑:免疫抗人BAG.1 多克隆抗體(SC.939 工作濃度)、即用型PV 二步法免疫組化試劑盒、檸檬酸抗原修復液。免疫組化染色方法:采用免疫組化二步法,對染色體進行處理,在處理過程中,將已知的BAG.1 蛋白為陽性對照,以PBS 代謝一抗為陰性對照,檢測過程中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術后通過電話隨訪、門診隨訪等方式了解患者術后腫瘤復發、轉移等情況,并明確其總生存期、中位生存期等。本研究的中位隨訪時間為60 個月左右,門診隨訪時需對患者進行胸部CT 檢查,完善隨訪資料。
1.3 觀察指標
(1)觀察100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BAG.1 蛋白的表達情況。(2)分析BAG.1 蛋白與非小細胞肺癌中患者預后的關系。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 表示,用χ2 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 標準差(±s)表示,用t 檢驗,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BAG.1 蛋白的表達情況
對BAG.1 蛋白在100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的表達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其中BAG.1 蛋白(+)患者有63 例,占63.00%,BAG.1 蛋白(.)患者有37 例,占37.00%。對BAG.1 蛋白的表達、組織學分級等情況進行分析表明,組織學分級越高者BAG.1 蛋白的陽性表達率越低(P <0.05),而BAG.1 蛋白的陽性表達率與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理類型及TNM 分期等無明顯相關性(P >0.05)。詳見表1。進一步分析表明,BAG.1 蛋白在胞漿中陽性率越高,患者的死亡率越低,生存時間越長。

表1 BAG.1 蛋白陽性及陰性患者一般情況及腫瘤病理特征的對比分析[例(%)]
2.2 BAG.1 蛋白與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關系的分析
通過對相關因素與非小細胞肺癌中患者預后的關系進行分析表明,BAG.1 蛋白、TNM 分期及組織學分級均是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P=0.023、0.015、0.023。詳見表2。

表2 BAG.1 蛋白與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關系的分析
3 討論
肺癌是一種常見的惡性腫瘤,其發病率和致死均較高。研究表明,肺癌的發生、發展具有遺傳學基礎,是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及微衛星不穩定性等多因素、多步驟參與的過程。近年來,隨著細胞凋亡(apoptosis) 概念的確立,人們對腫瘤發生發展有了新認識,認為細胞凋亡的缺陷或受阻是腫瘤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其中找到對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有幫助的特異性高、敏感性高的基因,有助于腫瘤的早期診斷、判斷預后及個體化治療。
相關研究表明,80% 的肺癌為非小細胞肺癌[1]。針對非小細胞肺癌,臨床最常用的治療方法是手術切除病灶,對改善患者的預后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則不能采取手術治療,只能進行化療、放療及免疫治療等保守治療[2]。研究表明,miRNA與非小細胞肺癌的發生、轉移及患者預后等具有密切的關系。let.7 家族是最早發現的miRNA 之一,在很多腫瘤細胞中影響基因的表達。Let.7 的表達能夠影響肺癌的分型,其低表達提示患者預后相對較差。RAS 家族、HMGA2 均受到Let.7 的調控[3],因此可認為Let.7 通過直接調控RAS、HMGA2 影響腫瘤的發生、發展及患者預后。調查顯示,miRNA 在有效抑制腫瘤因子表達的同時,能夠對相應的癌基因產生負調控作用,當miRNA 表達降低時,能夠起到抑制腫瘤細胞生長的作用。在腫瘤的早期階段,通過檢測血清腫瘤標志物進行診斷的敏感度、特異性不高。系列研究表明,miRNA 穩定存在于血液中,同時在不同人群中的表達存在一定的差異。肺癌患者體內的miRNA 存在缺失情況,研究表明肺癌患者體內的miRNA 表達譜與人體的血細胞表達譜具有一定的差別。正常人體的血細胞、血清表達譜作用相似,在血清學檢測中能夠有效實現腫瘤標志物的檢測。研究發現,對肺癌患者進行唾液細胞學檢查的敏感度、特異性分別為47.82%、100.00%,而miR.21 對于診斷肺癌敏感性較高[4]。部分學者在對癌癥靶向基因的研究中發現miRNA 與肺癌耐藥性明顯相關[5]。但在腫瘤的治療中引入miRNA 尚有一定困難,如何做好調控、確保安全有效還需繼續進行研究[6]。
BAG.1 是一種抗凋亡基因,其表達的蛋白是一種已經被確認的多功能結合蛋白,與bc.2 形成復合物,發揮抗細胞凋亡的作用。BAG.1 也有助于抵抗熱休克、生長因子缺失、凋亡、缺氧、細胞毒性藥物、放射線、內質網小體等多重應激,還可影響腫瘤對化療的反應。BAG.1 可作用于熱休克蛋白、絲氨酸/ 蘇氨酸蛋白激酶(Raf.1)、肝素結合表皮生長因子樣生長因子、肝細胞生長因子受體(HGF)、血小板生長因子受體(PDGF)、蛋白酶體、Hsc70 C 端反應蛋白(CHIP)和一些核激素受體,調節細胞凋亡、分化、增殖、轉錄、轉移和活力,從而影響腫瘤的發生發展。目前,多個臨床研究發現BAG.1 基因在肺癌、乳腺癌、食管癌、前列腺癌、肺癌等治療方面發揮著關鍵性作用。BAG.1 基因根據翻譯起始位點的不同主要編碼4 種不同的異構蛋白。BAG.1 是抗凋亡基因,理論上BAG.1 蛋白高表達的患者其生存期及預后較差,而一些研究結論恰恰相反,這似乎存在矛盾[7]。至少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研究中直接證明了這一觀點。有研究團隊在一項75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回顧性分析中表明,那些凋亡指數增加的患者死亡風險增加1.9倍。這種表面上凋亡活動和生存之間相矛盾的關系在BCL.2 的抗凋亡活動中同樣存在[8]。而不清楚的是抗凋亡活動是如何改善患者生存的,這需要通過進一步的研究來發現。BAG.1 調節途徑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般與腫瘤形成、化療耐藥具有相關性,并為多種腫瘤的預后評估、治療靶點選擇提供了可能。BAG.1 蛋白在肺癌中的表達與患者預后的關系存在一定爭議[9]。同時,根據我國前期的研究發現,BAG.1 蛋白與Stathmin 基因在非小細胞肺癌中均有高表達,提示BAG.1 蛋白與Stathmin 基因在非小細胞肺癌的進展中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此外,Stathmin 基因還與腫瘤的遠端轉移密切相關,并可能影響患者的預后。因此,BAG.1 蛋白與Stathmin基因可能成為預測非小細胞肺癌惡性程度及患者預后的指標,并能為肺癌的治療提供一定參考[10]。對非小細胞肺癌及小細胞肺癌患者進行個體化診療是當前研究的重點和難點[11]。尋找與肺癌發生密切相關的特異性易感基因,可為本病的早期診斷、治療及預后評估等奠定基礎。BAG.1 分泌的多功能蛋白可通過多種途徑來實現抗凋亡的作用,但其中的一些具體機理尚不明確,且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沖突[12]。
綜上所述,BAG.1 蛋白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陽性表達率較高,且與患者的預后有關,有望成為臨床預測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