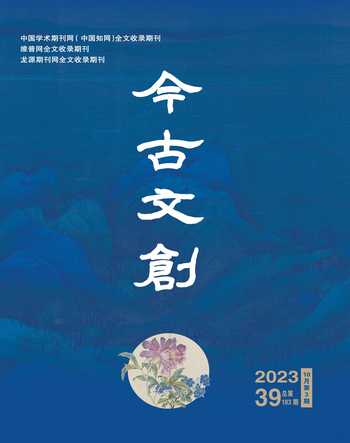《東北叢刊》研究綜述
趙聰聰
【摘要】創辦于20世紀30年代的《東北叢刊》,作為東北學社創辦、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發行的大型文史類綜合刊物,其所刊載文章內容豐富,涉及文史、經學等類別,主要收錄東北籍學者的著作和非東北籍學者有關東北研究的論著,極具地域特色。叢刊刊載的大量東北史研究論著,較早關注了東北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地理范圍、主權歸屬、民族屬性等問題,有力地回擊了俄國尤其日本“滿洲學”混淆視聽的言論,為后世東北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東北叢刊》;東北史;綜述
【中圖分類號】K2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9-01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9.038
近代日俄履侵東北,除政治、軍事等手段外,還企圖通過文化侵略之先導,以“學術研究”來證明“滿蒙非中國論”,以實現吞并東北的目的。尤其日本,組建體制健全的各種“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進行所謂研究,大肆宣揚“滿蒙非中國”的謬論。為抗衡此局面,金毓黻等愛國學人產生了組建研究東北學術團體的想法。1929年,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開會時,金毓黻提出組建此學會,獲一致通過。1930年,東北學社正式成立。學社以發揚東北文化,倡導學術研究,促進思想交流為旨歸,定期進行講演會及旅行。
學社發行會刊《東北叢刊》,第一期出版于1930年1月,共發行二十期,“九一八”事變后停刊。該刊設有學術、文苑、插圖等多個欄目,刊發了史學家吳廷燮、金毓黻、卞宗孟,古文字學家黃侃,經學家王樹楠、高亨等人的文章,極具地域特色。叢刊刊載的大量東北史研究論著,內容豐富,涉及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及地方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等領域,為后世東北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對于《東北叢刊》,時人已有所介紹,但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有以《東北叢刊》的內容作專題研究的論著和學術論文。這對于一個反映20世紀30年代東北歷史文化面貌,促使東北地區的史學界形成共同體并推動東北史地研究的刊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下面,就目前學術界對《東北叢刊》及其關涉問題的研究狀況進行一番梳理,以期為《東北叢刊》的深入研究準備條件。
一、收藏情況
《東北叢刊》被多處圖書館收藏。其中,大連圖書館藏第2—6,9—11,13—20各期,精裝合訂本三冊。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第1—19期,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第1—20期。另外,新刊《中國少數民族舊期刊集成》(中華書局影印,2006)76至78冊收錄了《東北叢刊》1—4,9—11,13—17各期。最全的是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其收錄了《東北叢刊》第1—19期,這些為研究該雜志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二、對《東北叢刊》創辦機構東北學社的研究
關于東北學社,目前學界主要圍繞著其創辦背景、過程、宗旨、學術活動進行研究。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1]對東北學社有所涉及,記載了學社的創辦背景、規章制度、創辦宗旨、定期舉行的活動等內容。
趙太和的《東北學的興起——東北學社的史學研究》[2]以東北學社作為專題,全面分析其產生背景、活動、學術成績及其會刊《東北叢刊》。文章指出學社以會刊《東北叢刊》為園地,在東北學之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等領域發表了大量論著,促使各分支學科的形成和發展,取得頗多成績,力圖與日本“滿洲學”相拮抗。
霍明琨在《20世紀上半葉的東北學術團體》[3]中,闡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后成立的東北學社、東北青年學社、東北研究社、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等東北學術團體及其創辦的刊物。其中,詳細敘述了東北學社的創辦背景、創辦過程、創辦人員、學社宗旨、學社活動、學社影響等內容,認為東北學社的成立和所進行的活動,加強了東北地區的學術交流,堪稱20世紀上半葉東北史地研究的重鎮。
趙太和在《1911年至1945年間的東北史學研究》[4]一文中,從學術史的角度考察當時從事史學活動較多、影響較大的東北學社,評論其成就、得失和影響,并用表格詳細列舉了學社的歷次演講和《東北叢刊》的撰文者,進而分析史學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及對史學近代化的影響。他認為,東北學社具有鮮明宗旨、章程、固定的會所和穩定的經費來源,定期舉行講演會及旅行,又發行會刊,具備近代學術團體的基本要素。截止1930年,以東北學社的組建為標志,東北史學團體基本實現制度化。
20世紀20年代,為對抗日人“滿蒙研究”的文化侵略,以金毓黻為代表的東北學人挺身而出,創辦東北學社,發揚東北文化。姚洋洋在《金毓黻的家國情懷與東北史研究》[5]一文中指出,東北學社定期組織活動,邀請上海學者陳彬龢進行演講。陳彬龢在演講中,揭露了日本文化侵略的本質,認為日人試圖從歪曲的文化層面將東北地區從中國領土中割裂。東北學社的一系列活動,使得人們對東北局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激發了國人的愛國愛鄉之情。
三、對《東北叢刊》作者群的研究
《東北叢刊》主要收錄東北籍學者之著作和非東北籍學者有關東北研究的論著,其作者多為東北學社成員,成分復雜。從職業看,囊括當時東北學界、教育界、政界及軍界等。主要有史學家金毓黻、吳廷燮、卞鴻儒、方國瑜等;文學家吳闿生、高步瀛等;古文學家黃侃;經學家王樹楠、高亨等。本文主要對涉及論文內容的史學家進行綜述。
(一)金毓黻
金毓黻,亦稱毓紱,原名金毓璽,字謹庵,后改為靜庵,號千華山民,遼寧省遼陽市燈塔縣人,東北學社的發起人,《東北叢刊》的編輯,是近現代東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精通史學、文學、文獻學,一生致力于東北史地研究,著述豐富,編撰史學專著16部,叢書和史料書共八部,在期刊雜志上發表了百余篇史學論文,是東北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國史學史草創時期的代表人物,被贊譽為“遼東文人之冠”。
李春光的《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6]探討1936年金毓黻在日本訪問學者、進行訪書活動的收獲,提出三點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他看到了許多在國內罕見或已亡佚的地圖和輿地典籍,如《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方輿紀要圖》《盛京程站圖》《圣朝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大元一統志》殘本二冊寫本;其二,看到了一些元明時期北部邊防和北方少數民族的典籍,如:《籌邊篆議》八卷、《名臣寧攘要編》《殘元世系考》,這些典籍因被清朝統治者禁毀所以國內沒有保存下來,是金毓黻東北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其三,搜集到了關于遼東史事的珍稀書籍,如《柵中日錄》《遼海丹忠錄》,還發現了比國內董氏刊本更加精良的《乘軺錄》。
朱慈恩的《金毓黻與〈東北通史〉》[7]以《東北通史》為例探析金毓黻研究東北史的特色,認為金毓黻的史學研究雖然并沒有跳出傳統的方法與路徑,但是也受到了新史學的影響。《東北通史》的編纂,繼承了晚清學人對史實考證校勘的傳統,他將具體的史實考證成果加以融合,成為一部通史,同時金毓黻全面地收集各種史料,包括正史、雜史等地上材料和出土文物這樣的地下材料乃至于域外史料。
姚洋洋的《金毓黻的家國情懷與東北史研究》通過論述金毓黻的求學和入仕途背景,以及介紹他的東北史三部代表作,認為在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中帶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并總結出金毓黻東北史研究的三個特點:愛鄉重邦之情、學術報國之意、博彩其他民族之長的開放性。
賈紅霞的《金毓黻東北史研究中的日本因素與學術訴求》[8]闡述了金毓黻在面對“滿蒙學”愈發緊逼的壓迫之下,與日本學術界從初步接觸到深受影響再到構建起本土化的東北學的三段發展,作者認為其客觀汲取“滿洲學”部分成果以為己用,駁斥了日本“滿洲學”歪曲東北地區分屬與民族的歷史事實,同時也應看到為和日本學者爭奪學術領地,金毓黻重點關注的焦點多局限在政治、史地領域,也存在有成書過快稍顯粗糙的不足,但總的來說,金毓黻東北史研究這一行為,寄寓了歷史學家發展本國史學的愛國情懷。
(二)卞鴻儒
卞鴻儒,字宗孟,遼寧蓋平(今蓋州)縣人,東北著名歷史學者,與金毓黻共同創建了“東北學社”,并在《東北叢刊》中發表《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日本刊行滿蒙叢書敘錄》《寫本明實錄提要》等文章,在東北文獻、東北史地、東北民族、文物考古及遼慶陵石刻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閆海、閆雅涵的《卞鴻儒與中國東北歷史考古研究》[9],該文作者多次踏訪卞鴻儒的家鄉故里,在掌握了許多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對卞鴻儒在東北史研究、東北文獻、東北史地及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了詳細介紹。作者認為卞鴻儒提出的“三大族系”理論梳理清晰了復雜的東北古代民族,對學術界做出了重大貢獻。
李俊義、李彥樸的《卞鴻儒對遼慶陵石刻研究的學術貢獻》[10]主要闡釋了卞鴻儒對遼慶陵石刻研究的學術貢獻。文中指出,1930年,任東三省博物館常務委員的卞鴻儒與梁思永聯合赴熱河林東、林西等處,進行學術考察。他在提交的《考察熱河古物報告書》中《遼代遺跡之聞見》的部分,記述了新發現的遼慶陵石刻。后又撰寫文章介紹了在林西獲得的出土于慶陵的契丹字哀冊文拓片的始末。在卞鴻儒等人的推動下,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遼慶陵石刻。
(三)吳廷燮
吳廷燮,近代史學家,原名承榮,字向之,號次夔,又號景牧。吳廷燮一生篤好史學,著述活動延續達半個多世紀。他參與了近代幾次重大文化活動,如修清史、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修纂民國史等,貢獻頗多。在《東北叢刊》中刊載《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唐方鎮年表卷一之一》等文章。
楊書元的《吳廷燮寫本〈明實錄〉》[11]對吳廷燮寫本《明實錄》做了簡要介紹,并敘述了吳本《明實錄》的確認及收藏經過,指明吳本《明實錄》多數抄自清內閣明清檔案,是一部近于內閣原本一體完整罕見珍本。
吳振清的《吳廷燮及其在補史表上的成就》[12]中,以時間為線,將吳廷燮的生平分青少年、北京任職、沈陽講學、“九一八”事變后留居北京和南京家居五個時期,并分別介紹。作者將其史表編纂的成就概括為補舊、創新、編撰方志表三個方面。最后介紹了吳氏推崇南宋史家李燾和李心傳,史學上深受二李的影響,著述力求翔實,撰述《清十三朝紀年要錄》和《明通鑒長編》的情況。
李新鈺在《吳廷燮〈新疆大記補編〉研究》[13]一文中,對吳廷燮《新疆大記補編》一書的成書過程、內容及體例、史料來源和價值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在第二章中,詳細敘述了吳廷燮的生平著述和學術活動,并闡釋了吳廷燮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想。
四、對《東北叢刊》內容的研究
《東北叢刊》是大型文史綜合刊物,其較早注意到對中國東北史的研究,其內容有關東北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及地方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等,刊載了30多篇東北史的論文。較早關注東北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地理范圍、主權歸屬、民族屬性等問題,開創性地彌補了傳統史地學“多詳于中原而略于邊省”的遺憾。《叢刊》對東北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故本文主要對《東北叢刊》所涉及的東北民族史內容進行綜述。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著、楊成能譯的《滿洲發達史》[14],運用大量史料,從所謂的學術角度,歪曲中原與東北的關系,企圖證明漢人是未經滿洲人邀請而來的入侵者,主張“東北與中原本土分離論”。此外,又闡述了“東北諸民族”同日本民族的關系,主張“滿蒙不可分離”,從日本國防的角度“經營滿蒙”,強調對東北的“支配權”。以此來蠱惑民眾,煽動輿論,為日本吞并東北做準備。為駁斥日本滿蒙學派的謬論,卞宗孟在《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按照東北古代各民族的源流及分合,把東北民族劃分為東胡、貉及肅慎三大族系,每個族系又包括若干部族,對東北民族理論進行了梳理,明確東北民族屬性,有力地回擊了各種歪曲事實的言論。
金毓黻的《東北通史》中,在繼承卞宗孟劃分的東北族系的基礎上,又補入漢族(華夏族),構成東北四大族系,即東胡族系、濊貊族系、肅慎族系和華夏—漢族族系,比較完整的劃分了東北族系,為后世研究東北民族史奠定了基礎。
佟冬主編的《中國東北史》一書中,基本沿襲了金毓黻在《東北通史》中將東北古代民族分為“四系”的觀點。他在書中將東北地區的古民族分為遼西古商族(燕族、孤竹與古朝鮮)、西部的山戎(東胡)、南貊與北穢、東北部的肅慎四系。
五、研究的評述
綜上所述,筆者將從以下兩個方面表達對《東北叢刊》研究的看法:從《東北叢刊》刊物自身研究來看,學界研究較少,主要是金毓黻在《靜晤室日記》中對《叢刊》創辦宗旨、文章來源等內容的闡述。其次是趙太和對東北學社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并簡略提及《東北叢刊》。由此可見,學界對《東北叢刊》的發掘和利用,仍處于起步階段,只有一些零星的、點式的研究。從《東北叢刊》刊物價值來看,《叢刊》呈現了許多史學家早年的思想文化,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東北歷史文化面貌,極具地域特色和歷史價值。但就目前學界研究成果來看,這與《東北叢刊》刊載了多篇東北民族、文化研究論文,其對東北史研究的開創性的地位并不相符。因此,需要更多學者的加入,開拓新視角,結合新的研究方法,進一步完善研究。
參考文獻:
[1]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小組校點.靜晤室日記(全十冊)[M].沈陽:遼沈出版社,1993.
[2]趙太和.東北學的興起——東北學社的史學研究[J].歷史教學問題,2017,(05).
[3]霍明琨.20世紀上半葉的東北學術團體[N].光明日報,2010-07-04.
[4]趙太和.1911年至1945年間的東北史學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17.
[5]姚洋洋.金毓黻的家國情懷與東北史研究[D].長春師范大學,2017.
[6]李春光.金毓黻赴日搜求東北史地文獻考略[J].遼寧大學學報,2007,(06).
[7]朱慈恩.金毓黻與《東北通史》[J].蘭州學刊,2008, (11).
[8]賈紅霞.金毓黻東北史研究中的日本因素與學術訴求[J].歷史教學問題,2020,(06).
[9]閆海,閆雅涵.卞鴻儒與中國東北歷史考古研究[J].東北史地,2016,(03).
[10]李俊義.卞鴻儒對遼慶陵石刻研究的學術貢獻[J].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10).
[11]楊書元.吳廷燮寫本《明實錄》[J].社會科學輯刊,1984,(04).
[12]吳振清.吳廷燮及其在補史表上的成就[J].史學史研究,1998,(03).
[13]李新鈺.吳廷燮《新疆大記補編》研究[D].新疆師范大學碩,2014.
[14]稻葉巖吉.滿洲發達史[M].東亞印刷株式會社,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