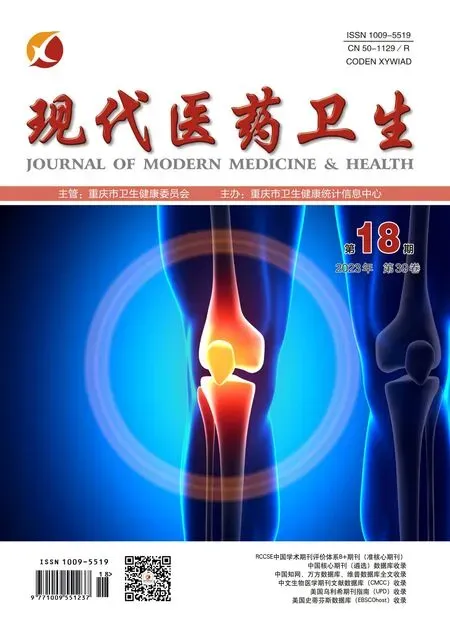ELANE突變相關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癥診治進展
肖于凡 綜述,張志勇 審校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風濕免疫科/國家兒童健康與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兒童發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兒童感染免疫重慶市重慶重點實驗室,重慶400014)
重度先天性中性粒細胞減少癥(SCN)的致病基因有ELANE、 GFI1、HAX1、SBDS等,其中最常見的致病基因是ELANE突變,稱為SCN1型,遺傳方式為單基因常染色體顯性遺傳。骨髓細胞分化都在早期階段停止,不能產生正常功能或數量的成熟中性粒細胞,表現為中性粒細胞數量的絕對缺乏,根據中性粒細胞絕對計數(ANC)變化規律不同和臨床癥狀的差異,ELANE突變的表型為SCN和周期性中性粒細胞減少癥(CyN),目前報道的SCN患者遠多于CyN患者[1-3]。ELANE突變通過影響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NE)的結構或功能,最終致中性粒細胞減少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最常見的是未折疊蛋白反應(UPR)理論。無論SCN或CyN患者,都表現為早發、反復的呼吸道感染、皮膚黏膜感染,嚴重感染者可危及生命、惡性轉化為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DS)或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ML)是預后不良的重要原因[2-3]。此病臨床的治療方式少且局限,盡早使用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是目前改善臨床癥狀的一線選擇和終身治療方式[4],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是目前唯一根治手段[2,5],基因編輯是未來根治的方向[5]。
1 發病機制
1.1ELANE基因突變 ELANE基因位于染色體19p13.3上,含有5個外顯子和6個內含子。目前,ClinVar數據庫中有超過200個ELANE基因突變,包括錯義突變、無義突變、同義突變、移碼突變、內含子剪切等多種形式,以錯義突變為主[1,3,6-7],散發突變病例和家族遺傳病例在目前已有的報道中無明顯數量差異。突變位點不僅包括成熟酶的編碼區,還包括酶原區和啟動子區,突變部位傾向于酶活性位點附近(外顯子3、4、5和內含子3、4)[5-6]。A57V、G97P、S126L、P139L、V190_F199del、W241X在文獻中既有SCN也有CyN病例報道[1,8-10],同一基因型有2種不同的臨床表型,目前尚不清楚具體機制。ELANE突變如V65del、N116D、C151Y、G185R、P205R、G214R、G214V,無論SCN還是CyN,都傾向表現出更嚴重的臨床癥狀,發展為MDS/AML或死亡的風險更高[3,6]。CyN病例中的雙位點突變傾向于表現出更嚴重的臨床癥狀,如A233P合并V235WfsX突變、G192A合并193_195del突變[11-12]。
研究發現,少數SCN患者父母的外周血有ELANE基因突變,但未表現出相應的臨床癥狀,提示存在體細胞嵌合體或不完全外顯遺傳的可能性[13-14],或親代生殖系嵌合的可能[13]。反映了ELANE基因突變的遺傳不穩定性,ELANE突變本身可能并不是完全導致中性粒細胞減少的原因,或許需要合并其他遺傳事件才能發生,需要進一步研究,并且在進行遺傳咨詢時引起重視。
1.2中性粒細胞彈性酶 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是由ELANE基因編碼的267個氨基酸翻譯為N-、單個前二肽、C-前肽,經過4次蛋白修飾為具有催化活性的酶(PDB:1HNEE,RefSeq 30-247),成熟的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含有218個氨基酸,主要功能是水解蛋白質底物和參與細胞外誘捕功能。有研究認為,ELANE突變是功能缺失型突變(LOF),翻譯修飾不完全導致蛋白質結構缺失,不能正確折疊、加工、分泌或降解[15]。也有研究認為,ELANE突變與NE結構破壞無關,而與NE功能障礙有關[16],但都不能完全解釋NE的結構和功能障礙是如何導致中性粒細胞分化成熟停滯。目前,相關的假說較多,歸納為以下幾類:(1)ELANE基因無義突變會影響NE肽鏈的C-端,致NE不易被銜接蛋白3(AP-3)識別,進而錯誤定位影響早幼粒細胞發育[6,16]。(2)內質網管控蛋白質折疊,ELANE突變產生結構或功能異常的NE,過多異常NE累積可促發內質網應激,啟動未折疊蛋白反應(UPR)促進早幼粒細胞凋亡[17]。(3)有學者發現,未發生UPR的情況下,NE錯誤折疊會產生早幼粒細胞核體(PML-NB),進而致活性氧(ROS)水平升高,ROS誘導突變NE降解[7,18]。(4)Wnt3a與CSF3R聯合刺激造血細胞中中性粒細胞的成熟,研究發現SCN患者中淋巴樣增強子結合因子1(LEF-1)顯著下降,LEF-1表達下降中斷WNT3a信號通路,影響NE成熟[16]。
2 臨床特征
2.1臨床特點 中性粒細胞組成人體抗感染的固有免疫系統,嚴重中性粒細胞減少癥容易引起嚴重的反復細菌或真菌感染,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和大腸桿菌最常見[4,7,9,11,15]。ELANE突變相關的SCN患者起病年齡常在生后6個月以內,CyN患者常在1歲以內。2020年法國嚴重慢性中性粒細胞減少癥登記處(FSCNR)研究表明SCN和CyN診斷年齡中位數分別為0.19、0.8歲(95例SCN,49例CyN)[2];2004年BELLANNE-CHANTELOT等[6]研究中SCN或CyN診斷年齡中位數分別為2.8、16月齡(54例SCN,27例CyN)。
SCN患者常以臍炎、口炎或肺炎起病[4],CyN多數以口炎為首發臨床癥狀[18]。SCN患者大多遭受終身反復感染,CyN比SCN發病率低,表現為周期性的中性粒細胞數量減少,周期為14~36 d(多數21 d左右),持續約3~7 d,臨床癥狀也呈周期性變化[3,8,19]。兩者均以呼吸系統、皮膚黏膜為最常見的感染部位,2015年MAKARYAN 等[3]研究報道,307例ELANE突變相關中性粒細胞減少的患者中,常見的感染分別為口腔潰瘍(80%)、肺炎(49%)、膿腫(19%)、敗血癥(17%)、蜂窩織炎(12%)和腹膜炎(3%)[3]。CyN患者呼吸系統的感染多數集中在口咽部,周期性出現口腔潰瘍是最主要的癥狀,SCN患者口咽部感染更多表現為牙周炎,包含牙齦炎、牙齒松動、牙齦紅腫、牙齦出血、牙槽骨吸收等,慢性損傷可能導致早期齒齦壞死、牙齒脫落[8,20]。SCN出現下呼吸道感染的頻率比CyN更高,肺部感染起病早、易反復,部分患者出現氣管、支氣管發育不良或肺纖維化[1,13]。MAKARYAN等[3]研究報道,97例SCN患者63%發生了肺炎,相比之下26例CyN發生肺炎的比率僅有19%。嚴重感染時可出現呼吸衰竭,需要吸氧甚至氣管插管維持氧飽和度[2,19,21]。兩者皮膚黏膜感染常表現為無或少膿液的膿腫,SCN常見的感染部位是肛周和臍部[15],嚴重時需要外科手術治療[7,21]。除此之外,中耳炎、乳突炎、淋巴結炎、骨量下降、貧血也常有報道[7-8,15,22]。2021年有1例SCN患者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相關報道,患者為20月齡的男嬰,因肺炎入院,病程中因銅綠假單胞菌感染出現典型的腮腺潰瘍、肛周膿腫,中性粒細胞數量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后進一步下降,呼吸道癥狀整體不重,可解釋為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NETs)的形成減少[21]。
CyN患者的臨床癥狀相比SCN普遍更輕,少數患者直到其子代確診后才被發現,部分患者隨著年齡增長臨床癥狀明顯改善,僅表現為口炎、不再出現感染癥狀或不出現任何癥狀[23]。少部分CyN患者表現出嚴重的臨床癥狀,呼吸衰竭需要氣管插管支持,或出現膿毒血癥、顱內感染、急性壞死性筋膜炎[13,19],僅2016年報道了1例CyN惡性轉化為急性白血病的病例,A233P合并V235WfsX雙位點突變的女性患者,4周時首次出現銅綠假單胞菌膿毒血癥,17歲時發展為急性髓細胞白血病,需接受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11]。
普遍認為ELANE突變導致的SCN比CyN患者的臨床癥狀更嚴重,部分患者惡性轉化為MDS、AML或更罕見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尤其G-CSF普遍應用后,雖延長了SCN患者的生存時間,但SCN惡性轉化率也隨之增加。2006年國際嚴重慢性粒細胞減少癥登記(SCNIR)確認了高劑量G-CSF暴露與白血病轉化之間的關系[24],同年相繼提出了SCN惡性轉化的累積發生率超過25%[6,24]。2010年ROSENBERG等[25]研究表明,使用G-CSF 15年后,MDS/AML死亡的累積發生率為22%,因膿毒血癥死亡的累積發生率為10%;2020年FSCNR研究提示MDS/AML的10年累積發生率為4.4%,20年累積發生率為5.5%[2]。除了惡性轉化外,膿毒血癥、呼吸衰竭、顱內感染或移植失敗都會導致SCN死亡[2,13-15,21,23,25]。
2.2輔助檢查 血常規是首次發現和監測中性粒細胞減少癥的重要檢查,重癥中性粒細胞減少癥患者長期維持中性粒細胞計數降低,至少3次出現中性粒細胞水平低于0.5×109L-1有助于診斷[15]。CyN患者中性粒細胞數量呈周期性減少,潛在患者建議3~4個月血常規連續監測,每周至少3次,連續計數超過2個周期[11],少部分CyN患者成年后中性粒細胞數量周期性改變會消失[23]。
骨髓細胞學檢查是協助診斷的重要檢查,無論是SCN還是CyN,骨髓涂片中成熟中性粒細胞均罕見,粒細胞左移,停滯在早幼粒細胞/中幼粒細胞階段,髓樣細胞數量顯著減少,成髓細胞和早幼粒細胞水平低,單核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水平較高[13,15,21-22],定期的骨髓細胞學檢查也有利于早期發現患者是否惡化為骨髓增生綜合征或急性白血病。
基因檢測是診斷的“金標準”,對患者及潛在攜帶者的ELANE基因組DNA和cDNA序列進行分析,測序包括啟動子區域、外顯子和內含子-外顯子邊界,有助于臨床癥狀及預后的預測[3,15]。
鑒于ELANE突變與MDS/AML的相關性,建議每年進行血常規監測和骨髓細胞學檢查,尤其出現不典型癥狀或體征時,臨床醫生更應進行積極的檢查。
3 治 療
3.1感染管理 預防和控制感染對患者生存質量至關重要。盡管G-CSF治療可以改善中性粒細胞計數,但仍存在感染的風險,尤其是口腔感染,定期監測血常規和口腔科隨訪,保持個人口腔衛生、定期牙齒檢查,有助于改善患者預后[7,15,20]。目前少見報道SCN或CyN患者使用滅活或減毒活疫苗免疫后出現不良反應。
3.2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 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作為一線治療方法,通過代償機制糾正中性粒細胞水平及降低發生膿毒血癥的風險,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改善生活質量。2006年PHILIP等[24]研究的374例SCN患者在G-CSF使用后SCN患者膿毒血癥死亡率下降到每年0.9%。
幾乎所有ELANE突變相關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癥患者對G-CSF治療有反應,但每例患者使用劑量差異非常大,2004年BELLANNE-CHANTELOT 等[6]研究表明,SCN使用G-CSF劑量的中位數高于CyN。2020年FSCNR隨訪研究表示,112例ELANE突變患者使用G-CSF治療的患者平均劑量為9.8 μg/(kg·d)[2]。普遍推薦(包括ISCNR)治療的初始劑量為5 μg/(kg·d)[15,24],根據患者臨床癥狀增減劑量,中性粒細胞絕對計數超過1.0×109~1.5×109L-1為治療目標,且<25 μg/(kg·d)的G-CSF用量可明顯改善大多數患者的臨床癥狀[14]。G-CSF難治性患者需要大劑量G-CSF治療來控制頻繁和嚴重的感染,最大用量可高達300 μg/(kg·d)[22]。
隨著生存時間的延長,SCN患者惡性轉化風險成為日益關注的問題。有研究指出長期使用G-CSF治療的患者發生MDS/AML的風險較高[15,24-25]。2015年MAKARYAN等[3]研究報道的307例患者中,SCN或CyN使用G-CSF 20年后發生MDS/AML、移植或死亡的累計發生率分別為46%、7%。80%發展為AML的SCN患者被發現有集落刺激因子3受體(CSF3R)的獲得性體細胞突變,且大劑量G-CSF治療(>8 μg/(kg·d))或累積劑量超過10 000 μg/kg的患者會增加惡性轉化的風險[3,11,26]。
3.3造血干細胞移植 造血干細胞移植仍是目前唯一根治方法,移植供體來源多為無關供者,其中臍帶血和骨髓干細胞較為常用。目前,關于移植指針總結為以下幾點:(1)G-CSF治療效果差:①<1歲開始使用G-CSF[1];②中性粒細胞數量無法上升至0.5×109/L或仍繼續下降[24],G-CSF使用后,仍有反復或嚴重感染[1,7];③大劑量G-CSF(>8 μg/(kg·d))治療后粒細胞無升高的難治性SCN[2,6,25];(2)隨訪過程中發現CSF3R基因突變[2];(3)嚴重膿毒血癥或惡性轉化MDS/AML/ALL[1-2,7]。
從理論上來講,移植后最理想的情況是完全嵌合體,因此預處理方案十分重要,優先選擇清髓的預處理方案,比如白消安(Bu)、環磷酰胺(Cy)、抗人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ATG)組成的Bu-Cy-ATG(MAC)預處理方案[2,4]和氟達拉濱(Fu)、白消安(Bu)、抗人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ATG)組成的Fu-Bu-ATG(MAC)預處理方案[4]。56%的SCN患者移植后中性粒細胞計數穩定,不再出現反復感染,無需G-CSF治療。目前,預防GvHD常用的藥物有環孢霉素(CSA)、霉酚酸酯(MMF)、甲氨蝶呤(MTX)、氟達拉濱(Fu)、他克莫司(Fk)、強的松(Pred)等藥物[2]。FSCNR提出ELANE相關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癥患者的HSCT預后良好,移植后5年生存率為87.5%,移植生存率為95.0%,長期生存率為90.0%[2],目前GvHD是患者移植后預后差和死亡的主要原因[1-2]。
3.4其他 目前,治療方式少且局限性多,因此一些基于CRISPR/Cas9 ELANE基因編輯[5]、NE抑制或增強G-CSF功能的新治療方法可能在未來應用于臨床。2021年EKATERINA等[9]研究提出煙酰胺與G-CSF協同治療可改善療效,2017年MAKARYAN等[27]提到一些內源性重組或合成的NE抑制劑已進入臨床前階段,如K562、MEG-01、MK0339等藥物,抑制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可能是未來的一種治療選擇,2020年有研究提到CRISPR/Cas9 介導的ELANE基因熱源性校正編輯或突變的等位基因敲除治療在ELANE突變患兒中的潛在應用,開發了一種基于CRISPR-Cas9-AAV6的基因修復方法[26]。2022年MAKARYAN又將NE抑制劑和基因編輯兩種治療方法通過人早幼粒細胞HL60進行實驗比較,2種方法對SCN和CyN的療效都有巨大潛力,但NE抑制劑作為口服藥物似乎是更好的治療方式[28]。
4 小 結
ELANE突變導致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癥有SCN和CyN 2種表現型,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是罕見的原發性免疫缺陷病,突變位點多,以雜合錯義突變為主。目前,發病機制研究不清,臨床特征為起病早、感染反復、部位多,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和大腸桿菌感染最常見,呼吸系統、皮膚黏膜為最常見的感染部位,SCN比CyN的臨床表現更加嚴重,部分患者惡性轉化為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或急性白血病,甚至死亡。血常規、骨髓涂片有利于早期發現,基因分析不僅是診斷的“金標準”,還有助于預測臨床表現,如V65del、N116D、C151Y、G185R、P205R、G214R、G214V突變、A233P合并V235WfsX、G192A合并193_195del都傾向于表現出更嚴重的癥狀,因此同一基因型表現為不同表型、基因型與臨床癥狀的關系亟待研究。預防感染有助于患者的長期管理,G-CSF藥物治療有助于改善臨床癥狀,HSCT是目前應用于根治此病的唯一治療手段。NE抑制劑作為G-CSF的替代治療藥物仍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基因編輯也是未來治療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