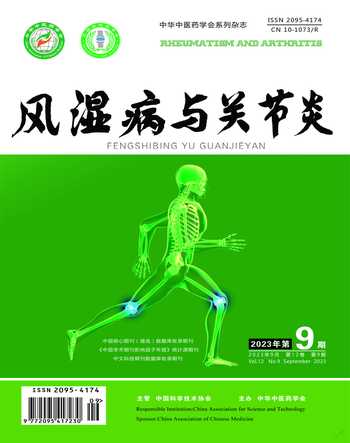古代旴江醫家痹病證治思想初探
喻建平 羅文花 危安瀾 石垚 吳桐 李潤洲
【摘 要】 旴江醫學作為具有地域特色的醫學流派,旴江醫家對痹病有較為全面系統的認識。在治療上遵循經典,立足實際,注重審證論治,祛邪止痛同時不忘補氣養血。在用藥上能依據不同證型,靈活選方,并深諳藥性,不一味見癥施藥,能圓機活法,在通絡止痛基礎上兼用補益、燥濕等藥物,巧妙地使諸藥相輔相成。同時,對藥物劑型選擇有獨到見解,展現了靈活思變,匠心炮制的用藥方式。還在痹病的外治領域積累豐富的經驗,活用蒸洗、外貼、涂擦等諸多特色外治法,使藥力直達病所,內外合治痹病。旴江醫家提出的痹病病因病機和治法方藥對后世影響深遠,故對旴江醫家痹病的診治思想進行梳理提煉,望能給現代風濕病診療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關鍵詞】 痹病;旴江醫家;辨證論治;學術思想
痹病又稱痹證,西醫學風濕病中的類風濕關節炎、骨關節炎等均屬中醫學“痹病”范疇[1]。風濕病學作為多學科交叉的新興學科,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門領域,采用中醫藥治療有其特色和優勢[2]。旴江醫學是我國著名的古代四大地方醫學流派之一,在中國醫學發展歷程中占據重要地位。旴江醫學源遠流長,歷代名醫輩出,臨證經驗豐富,著作涵蓋臨床基礎理論和臨床各學科[3]。諸多旴江醫著中都散落記載著具有旴江醫學特色的痹病辨證思想和治療方法。本文對旴江醫著中有關痹病病因病機的認識和治療方法,以及用藥特點加以歸納整理,深入發掘旴江醫家在痹病證治方面的臨床經驗,使其古為今用,為現代中醫治療痹病的發展貢獻力量。
1 病因病機
中醫學對痹病的認識最早見于《黃帝內經》,按病因分為行痹、痛痹和著痹等,隨著時代的演變,東漢張仲景稱痹病為“濕痹”和“歷節”,唐代王燾稱其為“白虎病”或“白虎歷節風”,后在金元時期朱丹溪又提出了“痛風”之說,而到了清代,王清任認為:“凡肩痛、臂痛、腰痛、腿痛,或周身疼痛,總名曰痹證。”至此,痹病的完整病名才首次被記載下來[4]。
在對痹病病因病機的認識方面,旴江醫家既遵從《素問·痹論篇》中“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理論,同時又有新的認識,既指出外邪致病,也強調體虛對痹病發生的重要性。明代旴江醫家龔信纂輯、龔廷賢續編的《古今醫鑒》中記載:“夫痹者,手足痛而不仁也。蓋由元精內虛,而為風寒濕三氣所襲不能隨時祛散,流注經絡,入而為痹。”[5]明確指出體虛是痹病發病的前提條件,體內元氣虧虛,風寒濕三氣趁虛而入,流注經絡而致痹。旴江醫家李梃在《醫學入門》中言:“痹屬風寒濕三氣侵入而成,然外邪非氣血虛則不入。”[6]357旴江醫家喻昌《醫門法律》認為:“故知胸痹者,陽不主事,陰氣在上之候也。”[7]135“四肢痹,四肢為諸陽之本,本根之地,陽氣先已不用,況周身經絡之末乎。”[7]133“筋痹,必因血不榮養。”[7]136
“肝痹,厥陰肝臟,所生者血也,所藏者魂也,血痹不行,其魂自亂。”[7]138喻昌認為,體內氣血乃人之根本,氣血不足無以御邪于外,外感風寒濕諸邪乘虛而入,則為痹病,總屬本虛標實證。旴江醫家張三錫在《醫學六要》提出:“痛風,即《黃帝內經素問》痛痹……古云三氣合而為痹。今人多內傷,氣血虧損,濕痰陰火,流滯經絡,或在四肢,或客腰背,痛不可當,一名白虎歷節風是也。”[8]張三錫不僅指出機體內傷外邪乘虛而入,同時認為致病不局限于風寒濕三氣,還有濕痰陰火之邪侵入機體皮膚,濕痰流注,火邪郁閉經絡,而成痹病。而龔廷賢在《壽世保元》同樣指出:“夫痛風者,皆因氣體虛弱,調理失宜,受風、寒、暑、濕之毒,而四肢之內,肉色不變。”[9]可見旴江醫家不僅繼承《黃帝內經》論痹之旨要,還立足實際,結合自身臨證經驗,對痹病病因病機有所創見,進一步深化了對痹病的認識。
2 辨證論治
《黃帝內經》按病因不同分為“風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濕氣勝者為著痹”,并依據部位之不同,詳分五體痹,還將久病不愈,內侵臟腑之不同,分為五臟痹和六腑痹等。旴江醫家大多都是根據《黃帝內經》中對痹證的論述辨證論治。
李梃在臨證中針對致病邪氣的差異,遵循風寒濕三邪的特性,如寒多者,則用五積散加天麻、附子或蠲痹湯;濕多者,采用川芎茯苓湯、當歸拈痛湯、防己黃芪湯等;寒痹之甚者,則用三痹湯和三五七散;風寒濕熱痹者,則用二妙蒼柏散等分,加虎脛骨、防風減半。李梃同時注重機體氣血虛實和痰瘀程度的不同,辨明不同病證特征,由此施以相應的治法。如氣虛痹者,陽虛陰盛也,多用四君湯加肉桂、生附子或川附丸;血虛痹肌膚不仁者,多用濟生防風湯或黃芪建中湯去飴糖加桂枝;夾痰手足痹麻、多睡眩暈者,多用濟生茯苓湯或二陳湯加竹瀝、姜汁。李梃還強調痹病初起不宜用補益之品,以防止邪郁經絡,《醫學入門·痹風篇》記載:“初病驟用參、芪、歸、地,則氣血滯而邪郁經絡不散。”[6]358
龔廷賢認為,痹病不能依例而治,臨證當審證辨因,不但從風寒、痰濕諸邪不同性質考慮,如遍身疼痛,風寒者宜散寒解表,濕痰者宜除濕化痰;也從氣血經絡進行分析,如遍身走痛如刺、日輕夜重者宜疏經活血行濕,如肢節腫痛、痹阻經絡者宜清熱除濕通絡;還從疼痛部位進行論治,如雙手疼痛麻痹者宜祛風化痰,如兩足疼痛麻木者宜清熱除濕。龔廷賢在《萬病回春》言:“凡治痛風,用蒼術、羌活、酒芩三味散風行濕之妙藥耳。”[10]311其治痛風基本方“羌活湯”散風行濕,補血行氣,使全身血行氣通,外邪祛除,祛濕止痛。龔廷賢治療以祛邪固本為特點,治法靈活,補虛以養肝補腎、益氣補血為主,配以解表散寒、溫散、除濕、化痰、清熱等攻邪治法。
喻昌辨治痹病注重扶正固本、益氣養血,在臨證辨治中強調:“凡治病者,必求于本,或本于陰,或本于陽,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乃為善治,若不知求本,則茫如望洋,無可問津矣。”喻昌《醫門法律》記載“附痹證諸方”共21首,其中首推《婦人良方》三痹湯,方中人參、黃芪、當歸、川芎、白芍滋養氣血,續斷、杜仲、牛膝補腎強骨,全方補益之品占很大比例,既可以補氣血固根本,又可以除風寒濕之痹痛,虛實同治,標本兼收,可謂良方。喻昌對于三痹湯評價之高,足以體現其治痹崇尚扶正培本之意。
3 用藥特點
喻昌治療痹病強調益氣養血,這種用藥方法與他辨治重視扶正固本的理念相吻合。如治在脈,用人參丸,《黃帝內經》曰:“脈痹不已,復傳于心。”方中人參、黃芪、當歸補心血溫陽益氣,以安心神護其脈。如治肝痹,用人參散,此乃喻昌自創,《醫門法律》中記載:“昌嘗制一方,以人參為君,黃芪、肉桂、當歸、川芎為臣,以代赭石之專通肝血者,佐參芪之不逮,少加羌活為使。”[7]138正所謂肝藏血,血不足則肝臟失調,方中人參、黃芪、肉桂、當歸均是養血益氣之品,以補氣血助肝平。喻昌雖主張治痹重在扶正固本,然不可一味補氣血,臨證當審辨。如治在腸,用吳茱萸湯,宜“辛辣開之”,是故方中以散寒止痛的吳茱萸為君;治在皮,用羌活湯,宜清肺氣,以祛風散邪為重;如痹在手足、濕流關節,用薏苡仁湯,則舒筋除濕為要。可見喻昌治痹知常達變,選方恰當。同時,喻昌治痹不論寒熱,臨證喜用祛風之品。如治療熱痹,用升麻湯,方中還搭配羌活、防風辛溫解表之藥,以增宣痹通絡之功;如治療冷痹,用巴戟天湯,方中亦有防風、防己辛散之品,用以宣通脈絡散邪于外。但喻昌也指出,治痹不可單用風藥,其在《醫門法律》評曰:“凡治痹證,不明其理,以風門諸通套藥施之者,醫之罪也。”[7]110正如喻昌治療熱痹時雖加以羌活、防風,但特意將羌活、防風用量減半,防其過燥,體現出其治痹圓機活法,用藥巧妙。
龔廷賢治痛風基本方(羌活湯):羌活、蒼術、黃芩、當歸、芍藥、茯苓、半夏、香附各一錢半,木香、陳皮各七分,甘草三分。方中羌活祛風勝濕,通利關節,能升太陽經和督脈的陽氣,為治太陽風寒濕邪之要藥;蒼術散寒除濕,為祛太陰寒濕的主要藥物。兩者共奏燥濕止痛之功。配伍性寒之黃芩清熱燥濕,以防溫燥傷陰;當歸、芍藥養血活血;茯苓利水滲濕;半夏燥濕化痰;香附、木香、陳皮行氣止痛。縱觀全方諸藥,燥濕類藥物居多。再如龔廷賢以靈仙除痛飲治骨節腫痛、濕熱流注遍身痛風者,此方用羌活、獨活、蒼術、威靈仙、黃芩等藥燥濕,配合防風、枳實、川芎等藥行氣,當歸尾、赤芍養血活血,共行祛濕止痛之效。通過龔廷賢用藥可知,其治療痛風注重在方中加燥濕類藥物,足見其深諳藥性,在明辨病性的基礎上,使燥濕藥和祛風清熱、活血通經、養血滋陰等藥相輔相成,增強臨床療效。同時,龔廷賢臨證治療痛風,不拘泥于普通的湯劑,其擅長根據病性、病位靈活運用不同的劑型。如內服丸劑乳香定痛丸(蒼術、川烏、當歸、川芎、乳香、沒藥、丁香),《萬病回春》提到:“上為細末,棗肉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黃酒送下。”[10]312全方合用,共奏散寒除濕、活血止痛之功。然方中川烏有毒,且諸藥偏辛燥,易傷脾胃,故龔廷賢用棗肉為丸,以緩解毒性,顧護脾胃,再以黃酒引藥入經,此舉體現其用藥巧思所在。
4 特色外治法
旴江醫家治痹承前賢之長,同時又獨具創見,還在痹病的外治領域積累豐富的經驗,從外用方藥具體組成、制備到適用證型皆著述鑿鑿,堪為借鑒。旴江醫家治痹外治方藥包括蒸洗、外貼、涂擦等諸多施治方法,同時遵循“辨證論治”原則,據病因病機不同,方藥性味各有側重。如《萬病回春·痛風門》中“神應膏”先將生姜汁以砂鍋內煎數沸,入皮膠化開,將鍋取下坐灰上,放入乳香、沒藥末,攪勻成膏后,熨熱貼于患處。方中雖僅乳香、沒藥這兩味活血止痛之藥,看似簡單,但龔廷賢將其攪勻成膏,再以熨法,施于患處,使藥性透皮毛,達腠理,療效斐然,是治血瘀痹痛;如《醫學六要·治法匯·痛風門》中“外貼方”以蕓薹子、安息香、川花椒、附子為重,溫陽散瘀,消腫止痛,是治寒痹;再如《醫學入門·外集卷六》中“千金單蓖麻湯”秋夏用蓖麻葉,春冬用蓖麻子,蒸半熟敷患處,溫度下降后再換,以患者汗出為度,再輔以疏風活血之品內服,以治風濕痹病。
而且,旴江醫家認識到,實邪痹病乃頑癥痼疾,根深蒂固,纏綿難愈,必須內外合治,才能發揮療效。如清代旴江醫家謝星煥在《得心集醫案》[11]中記錄王氏婦四肢腫痛(痛風)一案,案中以龍膽瀉肝湯清肝瀉火,加桃仁、澤蘭清火逐瘀,更入竹瀝、姜汁通經入絡的同時,外將澤蘭兜搗敷腫處以活血化瘀為主,即內服的同時配以外敷,使藥力直達病所,藥透效佳。
5 小 結
旴江醫學人才輩出,眾多旴江名醫傳承了歷代前賢學術精華,加之自己的獨到見解,在各種疾病治療上取得較高的成就。而旴江醫家對痹病有較為全面系統的認識,其治痹遵循經典,立足實際,審證論治,認為痹病既有外邪致病之因,還強調體虛對痹病發生的重要性,而且認為致病不局限于風寒濕三氣,還有濕痰陰火之邪侵入機體皮膚,濕痰流注,火邪郁閉經絡,而成痹病。在臨證中針對致病邪氣的差異,遵循風寒濕三邪的特性,辨明不同病證特征,同時注重扶正固本,益氣養血,體現了不受前人思想制約,圓機活法臨證知變的創新思想。在用藥特點上,旴江醫家依據不同證型,靈活選方,并深諳藥性,不一味見癥施藥,不遠溫熱,施以辛散之品,以增強宣痹通絡之功;并圓機活法,在通絡止痛基礎上兼用補益、燥濕等藥物,巧妙地使諸藥相輔相成;同時,對藥物劑型選擇有獨到見解,展現了靈活思變,匠心炮制的用藥方式;還在痹病的外治領域積累豐富的經驗,巧妙運用蒸洗、外貼、涂擦等諸多特色外用方法,使藥力直達病所,內外合治痹病。筆者對旴江醫家痹病的診治思想進行梳理提煉,望能為后世醫家在痹病的治療中起到投礫引珠的作用,對旴江醫學有更深挖掘,為現代風濕病診療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參考文獻
[1] 楊越,李露,王慎,等.中醫導引在痹病治療中的應用探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21,27(6):918-920.
[2] 婁玉鈐.風濕病命名與分類的規范化研究[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8,23(9):840-844.
[3] 周步高,何曉暉,潘源樂,等.試論旴江醫學對中醫學發展的貢獻和價值[J].中華中醫藥雜志,2022,37(3):1254-1257.
[4] 王敏,張景明.痹證淵源及現代醫家論治經驗[J].現代中醫藥,2018,38(5):82-85.
[5] 龔信,龔廷賢.古今醫鑒[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310.
[6] 李梃.醫學入門[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357-358.
[7] 喻昌.醫門法律[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2:110-138.
[8] 張三錫.醫學六要[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216.
[9] 龔廷賢.壽世保元[M].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345.
[10] 龔廷賢.萬病回春[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311-312.
[11] 謝星煥.得心集醫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163.
收稿日期:2023-05-06;修回日期:2023-06-22
作者單位:1.江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西 南昌 330006;2.九江市第三人民醫院,江西 九江 332099;3.江西中醫藥大學,江西 南昌 330006
通信作者:李潤洲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陽明路56號,8497519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