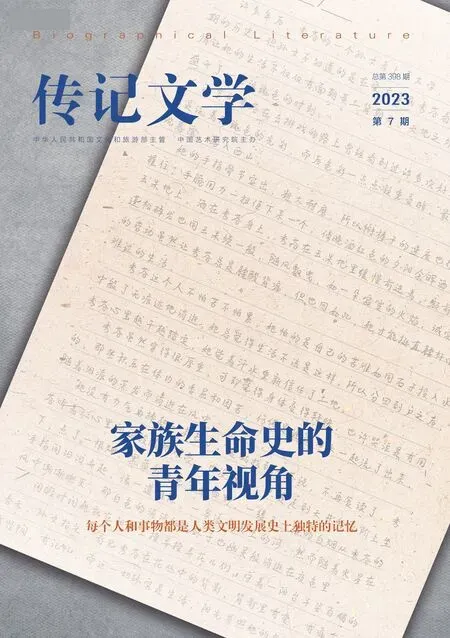當時只道是尋常
——以三位“知青”祖輩為中心的家族史
裴昭遠
前記
疫情期間,風傳我姥爺居住的小區可能會被封閉。姥爺二話不說,帶著保姆直奔農貿市場,買了未來一段時間的糧食物資。從小經歷饑荒年代留下的本能和經驗,讓他能做出比我們更迅速、準確的判斷。于是,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我要記錄下家族的歷史,記錄下我們祖輩經歷過的事情,讓這些經驗留下來,教育我們,也讓我們知道自己究竟出身于一個什么樣的家庭,了解我們自己。了解身邊祖輩們親身經歷過的歷史,是我們的責任之一。
在一次次的家庭聚會中,我采訪了很多長輩,留下了錄音筆差點存不下的錄音。長輩們聚在一起,互相填補記憶中的遺忘的部分,糾正記憶中的錯誤,還原出了一個大概的家族歷史。我又根據錄音一點點整理,將家族的歷史記錄下來。
限于篇幅,我只選取了1950 年至1956 年出生的三位“知識青年”:我姥姥的弟弟、妹妹和妹夫的故事。
1950 年出生的姨姥爺本應1966 年初中畢業,是“老三屆”的一員,卻因為成分問題成為不了“紅衛兵”;1953 年出生的姨姥姥是“老三屆”后的第一屆,考初中的考試被一張大字報攔腰折斷;1956 年出生的舅姥爺沒能接受完整的小學教育,在學生時代的拉練和畢業后的插隊中傷了胃,從事過工人、農民、商人、教師、司機等多種職業……
他們在童年時經歷了“大躍進”,少年時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本來暢想的人生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他們有夢想,卻在宏觀的時代壓力和微觀的家庭壓力下被步步緊逼;他們有激情,都開著汽車跑遍了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城……
在20 世紀50 年代至90 年代的時光中拼搏的他們,是一個北京普通家庭的生活點滴,能讓我們從一個側面,對那段歷史有更深刻、更準確的記憶。
祖輩的父親與母親
我家的先祖,我姥姥的爺爺的爺爺從安徽販絲綢進京,后在北京立足。我的這位先人經營有方,在北京置辦了四合院房產七八處,郊區還有田地。如此大的產業,自然是有家譜傳家。只可惜姨姥姥在“文革”時為避禍將家譜焚毀。好在姨姥姥和舅姥爺在小時候當故事看過家譜,回憶出了家里進京的過程。
正所謂富不過三代,隨著一代代的分家和經營不善,家業逐漸敗光。傳至我姥姥的爺爺的時候,已經只剩幾處房產,開始為別人記賬、做小工為生,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妻子依靠剩余幾處房產的房租過活。周轉不濟時,便賣掉一處房產渡過難關。時過境遷,便只留下了一處位于德勝門的房產,與三個兒子共居其中。
她的二兒子,便是我姥姥的父親,我的太姥爺。太姥爺的父親家業已經敗落,自己還需要為別人記賬做工,自然享受不到闊少爺的待遇,自幼便在古玩店學徒。然而1916 年出生的太姥爺,少年時期處在一個軍閥混戰的年代,有錢有閑擺弄古玩的老爺們不多,古玩行的小伙計們也就難以繼續在這行討飯吃,只好自謀生路。
北洋政府籌辦的北京有軌電車公司就成了太姥爺的去處。在那里,他成為一名售票員。大約在1937 年前后,他經人介紹,娶了一位小他一歲、出身京郊的姑娘為妻,那便是我的太姥姥。
我的太姥姥一輩子操勞。在娘家做姑娘時,母親身體多病,便一直代替母親操持家務。一日梳頭時,母親向太姥姥說道:“別梳頭了,收拾一下窗臺,等會兒人多了你忙不過來。”太姥姥不解其意,等回過神來才發現,母親已經撒手人寰,剛剛那話的意思是,自己馬上就要走了,因此才會有不少人上門。
母親去世后,太姥姥更是辛苦,就連兄長的婚事也要自己主持操辦。為兄長娶親后,本以為自己能輕松些許,沒承想剛過門的嫂子卻去找未曾謀面的婆婆去了。太姥姥只好再為自己娶來第二位嫂子。
她的命便是如此,一刻不得閑,腦子里便不存在偷懶的想法。嫁給太姥爺時,太姥爺的親兄弟三人還和母親住在一起,三位兒媳婦中另外兩位妯娌則和太姥姥完全不同,滿腦子是如何躲過差事的主意,于是依舊是太姥姥撐著家里絕大多數的家務事,卻得不到自己婆婆的喜歡。太姥姥換了個家,身上的擔子卻是一點不輕。想吃一個純棒子面的窩窩頭,卻也得不到自己婆婆的許可。
太姥爺的母親周轉不靈的次數終于快要追上房產的數量,便直接將三個兒子趕出了家門,自己繼續吃房租過日子。太姥姥對此毫無怨言,反而因為不用再受婆婆的氣,再操持一大家子的家務而開心。太姥爺和太姥姥搬到了新街口租房住,等電車公司分了宿舍后,他們又搬到了位于桃園東里的住所。他們在那里一直住到自己生命的終點,就連我的母親也是在那里長大的。
最初只是售票員的太姥爺,在1949 年后成為坐辦公室的調度,還擔任工會和互助會的干事。所謂互助會,就是電車公司的職工互相接濟的一個平臺。太姥爺時常兜里揣著現錢,如果有人有難,不等打報告申請,自己便直接掏錢相助。由于住在電車公司分配的房子里,自己的鄰居也是自己的同事。單位有一早班車司機常常睡過頭,太姥爺則常常早起,常在路過時敲門,將對方叫起后離開。憑借著自己的勤勉和人緣,1962 年太姥爺被評為北京市先進職工代表,還因此獲得去北戴河療養的機會。
我的太姥姥則一直時運不濟,甚至連一份正經的工作都沒有。上天似乎并不眷顧這樣一個操勞的人,太姥姥打的幾份零工,都陰差陽錯錯過了轉正的機會。她干的最長的一份工作是在果品公司負責挑水果,從34 歲做到42 歲,卻得到了一個40 歲以下職工轉正的消息,超齡的她不但沒能轉正,連工作都丟了,只好回家成為了街道居委會的主任,調節鄰里雞毛蒜皮的小事。家里絡繹不絕地來人,某家的婆婆和媳婦吵架,往往是婆婆先來訴一通苦,指責媳婦諸多不是,第二天媳婦又來說自己的難處。連給無業青年介紹工作,也是她的職責所在。

太姥爺和太姥姥,攝于桃園東里
這讓一天天辛苦操勞的太姥爺連最后的清靜也失去了,家里待不住,只能出門散心。太姥姥做零活補貼家用時,卻發現自己把好的工作都介紹給了別人,自己只能去永定河挖河泥,搬運數十斤的大石磚。這份力工的工作即將轉正之時,太姥姥卻又傷了自己的腳,再次錯過了轉正的機會。等自己傷好后,又干了一段時間,當快能轉正之時,尾椎骨再次受傷,又錯過了轉正。直到街道為方便居民購物,設置了一個小賣部,太姥姥才開始代管小賣部,不用拖著自己年過半百的身體去做力工了。
在為生計奔波,為家務操勞之余,太姥姥還一直在生育。1939 年,18 歲的太姥姥便生下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姥姥。太姥姥一共生下了八個孩子,有一半意外夭折。我的姨姥姥和舅姥爺,連同姥姥和大舅姥爺,便是我太姥姥八個孩子中活到成人的四個。
祖輩們自述的童年
姨姥姥和舅姥爺只差三歲,舅姥爺和自己的大姐(我的姥姥)之間差了17 歲,而即使姥姥和太姥姥之間也只差18歲而已。年齡的差距,使得我的姨姥姥和舅姥爺更像一個一家四口的核心家庭,而姥姥和大舅姥爺則有一層若有若無的疏離。
1956 年剛剛出生時,舅姥爺就患上了病,家里人一度以為他死了,將他放到了地上。當時只有三歲的姨姥姥蹲在一旁觀察著這個弟弟,看見他微微動了一下,趕緊提醒自己的父母,這才將舅姥爺重新撿起,撫養成人。

2021 年的桃園東里
1958 年,困難時期開始。太姥爺和太姥姥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撫養兩個孩子。大舅姥爺此時正在讀中學,放學時間較早,便操持起家務,后來中學畢業在家待業,更是連家里的做飯也負責了起來。
那時候北京每月24 日放糧,23日晚上往往就沒糧食吃了。到24 日早上,人們會擠著搶糧。有的家庭實在挨不到24 日,只能向鄰居借糧。計劃經濟之下,家里也要自己計劃,每天做飯都要稱量著做,不然很難挨到月底。
奔波操勞的太姥爺要吃一張大餅,同樣辛苦的太姥姥要吃一張小餅,嗷嗷待哺的姨姥姥和舅姥爺還要吃一份,自己做飯的大舅姥爺便只能吃一小口。即使這樣,糧食還是不夠。姨姥姥還記得,自己在某月的23 日晚上問太姥姥吃什么,太姥姥回答說吃粥。一大鍋清水,放幾棵野菜、幾粒米,便是粥了。雖然每個月總會餓上一天,但是相較于其他要扛上幾天饑餓的人家,這個桃園東里的小家還不算太慘。只是這里的男孩子仿佛天生就要承受委屈,大舅姥爺如此,舅姥爺也如此,女孩子卻往往得到偏愛。
舅姥爺的學習成績一般,非常想和同學交好,但是不知道為什么,常常被同學欺負,難以交到朋友。每次在外打架,不管是打人還是被打,在父母的眼里就是“惹事”,回家又會挨一頓打。
直到二十多歲,參加工作之后,舅姥爺給家里做了一個沙發,太姥爺看到后說:“你還有點用。”這句話舅姥爺記了一輩子,因為這是舅姥爺第一次得到父親的肯定。此后,家里的家具很多都是舅姥爺親手做的。
三年困難時期過去后,生活逐漸好轉,不再有吃不飽的日子,平時可以吃上大白菜和自己曬的菠菜干,逢年過節還能吃上韭菜炒豬肉。家里的相對寬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孩子數量較少,年齡差距又較大,即使是姨姥姥和舅姥爺也差了三歲。相比之下,姨姥姥未來的丈夫,姨姥爺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人,日子就要困難得多。

太姥姥、太姥爺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大舅姥爺(后排左一)、姥姥(后排右一)、舅姥爺(前排左)、姨姥姥(前排右),1962 年4 月攝于北京頤和園
1950 年出生于河北的姨姥爺比姨姥姥大三歲,不滿周歲時就被母親抱到北京找自己的父親。其時姨姥爺的父親在北京做學徒學織布,出師后自購了一臺腳踏織布機,夫妻二人一起織布販布為生。1956 年公私合營,成立合作社時,各家的生產資料必須合伙,姨姥爺家的織布機也被迫上交。按照當時的標準,雇過一個人,有生產資料的就是“小業主”,若是雇過三個人則會被定性為“資本家”。因此,雇人打過線的姨姥爺一家被定為小業主。不過合作社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個體戶們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各個單位上班。成立人民公社時,街道以姨姥爺等兄弟姐妹年齡太小為理由,要求姨姥爺的父親讓出一間平房,名義上是做托兒所,實際上又安排了一戶人家。
姨姥爺常常幫家中干活,但想看五分錢的電影,父親卻不許可。若是求得兇了,往往會被父親按在炕上用鞋底子暴打一頓,姨姥爺挨完打起來繼續干活,然而心思卻已經飛到電影院去了。姨姥爺在小學時是小隊長,學校組織春游時,家長大多會給五角錢,唯獨姨姥爺家里不給。因此中隊長小隊長們合影時常常會少了姨姥爺。上學帶飯時,姨姥爺常年只有咸菜窩頭。用票證購買糧食布匹等物時,要用手中的票證交換對方手中質量較差但數量較多的票證。生活的細節讓姨姥爺從小便深刻體會了缺錢的感覺。
姨姥爺小學學習十分努力,考初中前經常凌晨四五點鐘起床背課文,做算術題,然而天資有限,作文將模范文一字不差地默寫了一遍,考試完又接到了要補考的通知。補習三四天后,校長單獨告訴姨姥爺不用再來了,回家等通知吧。姨姥爺猜測,這是因為老師看他能一字不差地將模范文背下來,可憐他辛苦。小學畢業之后,姨姥爺分到了最差的九十中。
祖輩們的“中學”
1966 年,姨姥姥本應小學畢業,參加升學考試,但沒想到突然老師頭一天就把卷子發下來了。姨姥姥疑惑問:“怎么回事?”老師回答說:“今年不考了,回家當習題做。”原來是“文革”爆發了。一夜之間,仿佛世界變了。
姨姥姥看到習題后,覺得最難的應用題都很簡單,認為自己肯定能上一個好學校。前一年大院街坊家的閨女考上了女十五中,姨姥姥很想上這樣男女分校的學校,一直以此為目標,只可惜考試沒了。舅姥爺此時則剛剛小學四年級畢業,兩人停課半年,一直在家里待著。
在家的姐弟二人里,年歲稍大的姨姥姥成了太姥姥口里的“當家人”。家里有一副麻將牌,姨姥姥怕是“四舊”,于是每天燒火的時候偷偷燒掉幾塊,直到一塊不剩。現在姨姥姥還記得那副牛骨的麻將牌,手感極佳,質量上乘,每次焚燒的時候煙灰都很大,燒不干凈的骨灰只能混著煤渣倒掉。太姥爺心愛的京劇書也不敢留著,一并撕掉點火燒了,那本先祖留下的家譜也在此時付之一炬。
半年后,姨姥姥被分到了九十中,和姨姥爺成了同學,卻還因為差著三屆的緣故并不認識。姨姥爺的父親在工廠工作,卻不希望姨姥爺也成為工人,叮囑他好好學習:“你要是到了工廠,關在車間里頭,一天八個小時不得自由。”
在父親的考慮中,姨姥爺的目標應該是鐵飯碗的鐵路和郵局,因為這些不在室內工作,可以坐火車或者騎車到處轉。父親的希冀成了姨姥爺的目標。姨姥姥錯過了考初中的機會,姨姥爺則錯過了初中畢業考技校的機會,鐵路和郵局自然也成了泡影,組織關系只能留在九十中里。這段時期,課業自然就放下了。在學校本身也學不到太多東西,更何況在學校里的時間也不多,經常需要去學工學農,進入工廠勞動,往往一年只能上一個月課。有時冬天凌晨四點要啟程出發去學農,也有時是半夜出發。機靈的借口自己有病或者來例假可以跟老師坐車走,老實些的只能徒步幾十公里走到大興。
舅姥爺還經歷過好幾次拉練。拉練時最早是兩個女生負責做飯,經常在飯點無法準時提供伙食,最終飯菜還是夾生的。因此伙食工作后來讓舅姥爺和另一個男生負責,舅姥爺當管理員,統籌規劃全班三十多人的伙食,包括做飯用的煤炭等。每個人每月八元的伙食費,如何使用全部由舅姥爺負責,另一個男生只負責做飯。炊事班和其他人都要拉練,但是只有炊事班需要背著鍋碗瓢盆。到目的地后別人可以休息,炊事班卻要生火做飯,因而辛苦很多。舅姥爺在拉練中的經歷讓他在后來的插隊中得以進入食堂工作。
未曾“上山下鄉”
隨著“文革”高潮的結束,“上山下鄉”成為了中學生們的新熱潮。然而,有兩個人做出不同的選擇:一個是出身農村(北京郊區)的太姥姥,一個是小時候離開農村但常去河北老家的姨姥爺。
太姥姥對自己的孩子看得很緊。大舅姥爺準備去參軍的時候,先考慮的是洋氣的空軍。經過體檢等一系列步驟,連軍裝都領到手了,太姥姥卻怕他從天上掉下來,堅決不放大舅姥爺走。后來大舅姥爺又有了當陸軍的機會,偷偷去檢查身體,合格后拿著軍裝回家,太姥姥說陸軍可以,這才把兒子放走。
而對于姨姥姥,太姥姥則是咬緊牙關,絕不松口。她說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沒過過一天好日子,那個累姨姥姥受不了。來家里動員的人嚇唬她,說不走就沒工作,只能在家待著。太姥姥則對姨姥姥說:“我豁出去養你十年,找人家嫁了,我也不讓你去!”
姨姥姥則很向往所謂的軍事化管理和集體生活。太姥姥反對道:“那么老遠,怎么回家啊?”姨姥姥卻說不考慮那個,認為在那里發工資,吃得又很好。軍代表來家里介紹過情況,還發了她一身軍裝,更讓她向往,為此常常和太姥姥慪氣。
學校常常召集同學們開會,宣傳上山下鄉的好處。姨姥姥從一年級就是旗手,一直當到六年級中隊主席,中學當班長,此時經常需要動員同學們上山下鄉,自己也想去卻又不敢違背太姥姥的意思偷偷溜走,常常為此苦惱。
自己不去,如何拉得下臉動員同學們呢?此時,她的姐夫(我的姥爺)——當時全北京都不多見的大學生——出了個主意。姨姥姥從小就非常容易緊張,凡事只要可能都讓舅姥爺出面。即使打醬油,臨到她那里都會讓她心跳加速。學校會演大合唱時,她往往緊張得一句都唱不出來。姥爺據此讓姨姥姥去看病,還囑咐她當天早上起來不要吃飯。測心率時姨姥姥因為饑餓和緊張心率極高,穩定在120,最終得到了個“心動過速,懷疑甲亢”的診斷。靠著這個單子,姨姥姥有了不走的借口。
絕大多數人都走了之后,姨姥姥在家正常生活了一年半,幾乎每天都在玩,有一次買了張兩塊錢的月票在北京城到處找便宜菜買,但是轉來轉去發現自己只認識鼓樓。
這段時間,她只偶爾去學校一趟開會,開會接著動員,目的地是云南。姨姥姥還是想去,太姥姥說:“太遠了,坐火車得三天!”后來又說去通縣插隊,姨姥姥又想去,說這個離著近。太姥姥說:“你要是男孩子,我就不攔著。”
太姥姥不是說笑。作為男孩子的舅姥爺就去插隊了。從初中畢業后,舅姥爺覺得終于不用考試了,自己解脫了,心里充滿著無論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的自信,插隊到了通縣種地,在那里學會了抽煙。一個月后,因為拉練時的炊事班經歷,舅姥爺被調到了食堂工作。
與被母親禁止上山下鄉的姨姥姥不同,姨姥爺是自己堅決不肯去上山下鄉。“文革”期間,姨姥爺作為“老三屆”中的一員,因為出身小業主成為不了紅衛兵,還時常因害怕打砸到自己家里惶惶不安。
從1966 年開始到1970 年的五年時間,姨姥爺都在家里待業,有時在學校的安排下,一起參加游行、學習班等各種活動,每年都會回河北老家農村。由于見過農村的真實景象,姨姥爺對農村的印象是:一片漆黑,點小煤油燈,起早貪晚;冬天挖大渠淘大糞,夏天割麥子汗流浹背,喝涼水吃窩窩頭;農村的水需要從水井里打上來,得混著秸稈和灰塵喝。姨姥爺的父親也說:“離了北京,你就別想找北京!”在北京習慣了一百多個公園和自來水的姨姥爺比起其他同學都更清楚農村的真實情況,因此堅定了不去上山下鄉的想法。

大舅姥爺參軍后寄回的照片
然而出身不好的小業主如何能夠拒絕號召,這是一個不小的問題。姨姥爺給自己制定的策略是:裝慫。無論外界如何鼓動如何打擊,心里一定要有一根主心骨——不能去上山下鄉。在事態實在緊張的時候,姨姥爺就會跑回河北老家躲一個月。一次從老家回來時,姨姥爺發現班里五十幾個同學已經全部被送去上山下鄉,只剩下姨姥爺和一個身體有殘疾的同學。
身體健全的姨姥爺因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在意向登記冊上,姨姥爺把四個選項(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工廠去;到企業去)全部選上。工人宣傳隊的人說:“你要選那個‘到農村去’!”但無論宣傳隊再說什么,姨姥爺都一句話不再說了。
在對抗上山下鄉的壓力之外,姨姥爺在這段時間又開始面對一個熟悉的老對手——饑餓。在家吃閑飯的姨姥爺此時已經不是當初的小孩子,找到了解決全家糧食問題的方法——撿白薯。
當時農村大都是生產隊,秋冬季生產隊刨完白薯后,姨姥爺就會沖進地里重新刨一遍地,將較深處的、刨漏的白薯撿回家。一到秋冬季白薯放秧的時候,每天凌晨五點多,姨姥爺就會裹著破棉襖,懷揣著兩張家里烙的小烙餅和啤酒瓶子裝的涼水,掛著大麻袋,騎幾十公里的自行車到鄉下,晚上八九點鐘回家時能扛回滿滿一大麻袋的白薯。若是能在生產隊刨完白薯,允許外人來撿的“頭茬”進入白薯地,姨姥爺就能撿到足夠的白薯。可若是沒能趕上,土地在生產隊刨過又經過幾撥人“撿”,實在是不剩什么了,便只能“間接偷”一部分來填肚子。生產隊收上來的白薯用麻袋堆在一旁,總會有一個蜷在軍大衣里的老頭看著。姨姥爺便拉住當地的孩子,從一包七分錢香煙里抽出一根,或者拿一小塊水果糖,用這些東西賄賂他們,讓這些孩子利用他們本地人可以拿白薯的優勢給他偷幾塊白薯,隨后再去別的地方如法炮制。
姨姥爺每天從家里出發,各個生產隊哪天幾點“放茬”,哪里用的是機器收不干凈,仿佛腦子里有一張完整的地圖一樣門兒清。姨姥爺每年從十月開始,連續一個多月的時間,憑借這一手“撿白薯”的技能,解決了全家的糧食問題。
除了秋冬季的這一個多月以外,姨姥爺還常常需要去學農,收麥子。一去便又是一個月,由于不愿意吃苦和戀家,即使是學農時姨姥爺也會偷偷跑回家。學校要求進企業勞動時,在父親“鐵路和郵局”的影響下,姨姥爺自己找到了北京飯店和霞公府附近的北京列車站工作。列車站很樂意接受這樣一個學工來的不要工錢的臨時工,將姨姥爺分到了永定門到秦皇島的鐵路做列車員,一路途經豐臺、黃土坡、黃村、魏善莊、安定……工作幾天就能休息幾天,姨姥爺感覺十分瀟灑,只可惜不能留下。
到1971 年,姨姥爺全校上下兩千多名學生中只剩下58 個因各種原因不去上山下鄉的學生,其中就包括姨姥爺和低姨姥爺三屆的姨姥姥。
祖輩們的工作和愛情
在擔驚受怕些許時日后,沒有上山下鄉的姨姥姥和姨姥爺依舊得到了組織分配的工作。
姨姥姥和姨姥爺由于組織關系同在九十中,作為全校上下兩千多人中最后的58 人被一起分配到了北京的汽車配件工廠。也就是在那時,沒有特殊原因,但沒有上山下鄉的姨姥姥和姨姥爺相識了。
在家里受父母疼愛,在學校招老師喜歡的姨姥姥,在工作時毫不意外地獲得了領導的照顧。其他人都分了機加工、組裝等臟活累活,姨姥爺先在磁電機工作了兩個月,后被分到了倉庫做管理員。姨姥姥則和另一個女孩被分到了樓上的組裝調節器的單間,穿著白大褂,有師傅領著,工作不累,環境也好。
有一天車間新來了一個銑床,大家都起哄說:“新床啊!讓我去多好!”姨姥姥也跟著起哄,結果被車間主任聽見了,因此被調到了銑床工作。工作一周后,姨姥姥撂了挑子,跟主任說:“這活又累,潤滑油又黑又臟,還到處都是,我干不了。”主任就將她調去了區里的宣傳隊,會演了一個月。回來時車間多了個新的鑄造車間,于是姨姥姥就轉去了那里。
鑄造車間里就兩個女學員,剩下的連班長都是男的。車間處于實驗階段,沒有太多工作要求,男的又多,姨姥姥幾乎什么累活都不用干,每天幾乎就是玩沙子,身材都開始發胖了,這期間還加入了共青團。
一年之后,工廠配了輛貨車,領導讓她去開車。姨姥姥一開始不想去,但是架不住領導多次請求,最后還是去開車了。工廠提供了學費和機會,姨姥姥在駕校花半年時間學會了開車。全工廠只有姨姥姥一個司機,所以她又可以以此為憑“吊腰子”(以自己的特殊和別人討價還價),甚至還有一間單獨的休息室。
有一回姨姥姥腰有些不舒服,又不愿意請病假,就在工廠休息。新來的廠長看不過去,訓斥道:“你為什么不出車?”姨姥姥說自己腰疼。新廠長繼續訓斥:“腰疼開病假去!你干得了干,干不了別干!”姨姥姥被激怒,把駕駛本甩給新廠長:“我不干了!”原來的老廠長趕緊過來哄:“他說不干就不干了,他算老幾啊?你這本是公安局發的,他說的沒用。”這才把姨姥姥安撫下來。
姨姥爺當倉庫管理員的時候,姨姥姥的貨車就停在姨姥爺工作的倉庫里。姨姥爺并不甘于做一個倉庫管理員,憑借自己堂堂的相貌和出色的口才,終于得到了廠長和書記的賞識,從倉庫管理員變成了外協銷售。當時的農村大隊時常派人來城里“趟路子”,找活掙外快,工廠就會把不愿意干的糙活累活都轉交給農村大隊。姨姥爺作為外協銷售,聯系的便是這些“業務”,可以到各地“享受”農村大隊的招待和饋贈。農村大隊為了掙外快,通過各種途徑搞來車床,無論什么活都愿意沒日沒夜地干,還要給司機和業務員各種好處。姨姥爺一直記著父親的教導,對于工廠工作非常抵觸,因此對在70 年代就能全國各地到處跑業務順便旅游,非常滿意。
跑了一陣子外協后,姨姥爺又開始向往當司機,覺得會開車是一個技術活,掌握開車這門技術就有了一技傍身,為此又去找廠長,軟磨硬泡拿到了學車的許可。當時廠中姨姥姥是唯一的司機,姨姥爺常常跟著姨姥姥一起跑業務,學開車。隨著姨姥姥買的兩張電影票,兩人相戀,1977 年結婚。由于姨姥爺的車技是姨姥姥教的,兩人的“師徒”關系在廠里成為笑談。
1975 年,25 歲的姨姥爺得到了成為工農兵大學生,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當時他正在外地出差,已經是團員的姨姥姥幫他張羅著火速入團,然而回到北京后此事卻再無下文。姨姥爺知道這個機會被人頂替了,但當時他卻不知道自己究竟錯過了多么寶貴的一個機會。
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姨姥爺總有自己的辦法。結婚之前,姨姥爺想給姨姥姥弄到新婚房,想起了自己小時候被街道分走一間平房的往事,決定以此為借口搞到一間新房。然而時過境遷,當時要走那一間平房的領導早就去世了,其他領導不愿意承擔自己分外的責任,這個問題因此被高高掛起。
姨姥爺卻準確地判斷出這件事不歸房產所管,死死抓住了街道辦事處。他很清楚,沒有人敢明說不給他解決問題,因為自己結婚要房住的理由是正當的。占住這一點,姨姥爺每天都會跑到街道領導的辦公室,要求解決問題,無論怎么推脫都不聽,最后終于磨出來了他和姨姥姥的新婚房。
學生時代被考試折磨,插隊被務農折騰的舅姥爺最渴望的工作是能夠不考試、不下地勞動,還有寒暑假待遇的工作。等到插隊結束時,他被分配成為小學體育老師,這完美地符合舅姥爺的要求,為此他常常得意道:“我是二十四級國家干部!”
1976 年,舅姥爺所在小學的教導主任應去“五七干校”勞動,但其不愿意去,因此舅姥爺被推出代替其進入位于天宮院的“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勞動期間,學員都是各個學校的老師,其中有一位精通古詩和音樂的學員,常常在聊天中提及古詩,勾起了舅姥爺的興趣。在半年的勞動過程中,舅姥爺學會了大量古詩古文。母親從小一直生活在太姥姥家里,舅舅帶著背古詩的事情一直印在她的腦海中。
1979 年,舅姥爺認為自己沒有學歷,同時非常希望學一門手藝,有一技傍身,認為有手藝才算有能耐。同時也考慮到老師工資太低,只有23 元工資,轉正后也只有32 元,離開學校,經大舅姥爺介紹,進入東郊鑄造廠成為鑄造工人,工資超過了40 元。
鑄造工人只是舅姥爺的一個過渡,他希望借此證明自己有能力養活一個家,并從小學老師的工作中擺脫出來,獲得了一個工人的身份。1980 年,大舅姥爺幫舅姥爺找到了通用機械公司新成立的空調銷售工作,舅姥爺立刻跳槽。機械公司此后合并為機械研究所,舅姥爺就在機械研究所工作,負責調試,后來又擔任通訊員,同時和上游的甲方和下游的乙方接觸。
1982 年左右,被派到廣東工地的舅姥爺非常上心,一直努力鉆研技術。當地的總工程師在風道設計中犯了一個錯誤,舅姥爺立刻發現了這個問題,并當眾指出了這個錯誤,因此得罪了總工程師,但自己卻渾然不知,反而得意洋洋。后來舅姥爺的領導詢問舅姥爺怎么得罪那位總工程師了,告訴他被人在背后說了不少壞話,舅姥爺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因為什么。直到多年后,舅姥爺才回過味兒來。
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舅姥爺一直沒有穩定的對象。在當小學老師時,舅姥爺曾有一個曖昧的對象,當時沒有挑明。在鑄造工廠工作時,有一個化驗室的姑娘對舅姥爺有意,兩人相處半年后分手。直到1981 年,才在太姥姥的介紹下和舅姥姥相識。
1980 年,舅姥姥還在學車,學車的地點則和太姥姥的小賣部很近,因此經常光顧。太姥姥則用起了當街道主任調節婆媳關系時鍛煉出來的語言能力,旁敲側擊打聽出了舅姥姥沒有對象。舅姥姥當時只有21 歲,別人介紹對象時,常常因為自己年紀太小而拒絕。太姥姥這時給舅姥姥介紹了舅姥爺,但是隱瞞了舅姥爺是自己兒子這件事,只說是自己的街坊,家里條件很好,在通用公司上班,還有1 米78 的大高個兒。舅姥姥還是有些猶豫,但是太姥姥堅持不懈地推銷這個“街坊”。長時間的努力終于打動了舅姥姥,答應出來和舅姥爺見面。

姨姥姥和姨姥爺,攝于桃園東里
太姥姥將舅姥姥帶到了蒲黃榆的一座橋邊,和舅姥爺隔橋相望。舅姥爺一眼就認定了舅姥姥是“自己家里人”。兩人很快相戀。后因瑣事二人吵架,舅姥爺急中不小心說漏了那個介紹對象的“老太太”是自己母親的事,舅姥姥這才知道太姥姥和舅姥爺的關系。舅姥姥每次和舅姥爺吵架,不理舅姥爺的時候,舅姥爺就會跑到舅姥姥單位門口守著。舅姥姥下班時看到舅姥爺堆著一臉笑的樣子,便也會笑起來,這一篇就算揭過了。
大舅姥爺的媳婦也是太姥姥介紹的。無論大事小事,太姥姥都操碎了心。1984 年,舅姥爺和舅姥姥結婚后,夫妻兩口子一起住在桃園東里,伺候太姥爺。太姥姥卻永遠沒有閑下來的命,一直是家里的“總指揮”。

舅姥姥
祖輩們的父母及子女
太姥姥對舅姥爺的苛刻要求,有些類似皇帝對太子的磨礪。她非常寵愛女兒,卻一直認為女兒遲早是要嫁人的,內心深處將小兒子看作自己年老時的寄托。
舅姥爺特別敬畏自己的父母,唯父母命是從。一次過年時,舅姥爺曾允諾去接舅姥姥,但臨出門時太姥姥突然派他去買面。舅姥爺甚至不敢告訴母親自己還要去接女朋友,把舅姥姥晾了一個多小時,后來再去接舅姥姥時也有些畏畏縮縮,看見舅姥姥與大舅姥姥等人正在說話,安慰自己說舅姥姥會和他們一起來,沒想到舅姥姥告別后依舊在原地等他。舅姥姥非常生氣,將準備好的禮物放在舅姥爺家門口就回家了,后來舅姥爺和大舅姥爺上門賠罪才算了結。
然而太姥姥沒有享受哪怕一天的福。
1986 年9 月1 日,一直在太姥姥家居住生活的母親考上了北京大學,這是這個工人大院多少年沒有的事情。全家人簇擁著她進了北大,在宿舍安頓下來,太姥姥也去了。但當周末母親回家時,她的大舅媽卻告訴了她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太姥姥走了。
原來太姥爺突然因為腦梗住院,已經操勞了半個世紀的太姥姥奔前忙后,最后一根稻草終于落下。醫院里的太姥爺被照顧得無微不至,醫院外的太姥姥卻被壓垮了。舅姥爺將太姥姥背到醫院,但是為時已晚,這具受過太多傷、太多苦的身體已經走不下去了。
臨終時,太姥姥將一切都托付給了舅姥爺,包括自己多年來攢下的幾十塊錢,偷偷藏在正房對面小煤屋的墻洞里。老太太省吃儉用,但是一定要有點錢壓在手里,無論是丈夫、兒女還是孫女,絕對不能在面兒上少了一點光彩,絕不向人開口借錢。這點壓箱底的積蓄交給兒子時,想必她已經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不知道她有沒有想起當初自己的母親讓自己收拾窗臺的往事。

舅姥爺抱著小表姨
1986 年9 月6 日,太姥姥病逝,享年69 歲。
舅姥爺向往開車,渴望有速度有激情的工作。舅姥姥在認識舅姥爺時就正在學開車,與交通隊的警察交好,在舅姥姥的幫助下舅姥爺拿到了學車的資格,一邊工作一邊學車。1986 年,舅姥爺辭去通用機械公司的工作。經大舅姥爺的朋友介紹,獲得了臨時的司機工作。數月后,又經大舅姥爺介紹進入了天倫服務公司。
然而舅姥爺辭去通用公司的工作時,沒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面對母親的離去以及腦梗的父親,還有嗷嗷待哺的女兒和整個家的責任。即使是數十年后,談起這段歲月時,舅姥爺也不禁流淚。
1981 年時,姨姥姥工作的零件加工廠合并。到90 年代,車隊要承包出去,變成計件工作。姨姥姥因此不再開車,改去車間干裝配工,每天只干晚班,從晚上九、十點鐘干到十二點回家,工作效率比同事們都高,依舊受到領導喜愛,一直到2000 年,姨姥姥退休。
太姥姥去世后,“總指揮”沒了,舅姥爺和舅姥姥背負起了家里的一切。工作稍清閑些了的姨姥姥也常常回到娘家,帶來錢和水果等物,幫著洗衣,做家務,共同撐起了這個曾經庇佑他們的家。
太姥爺出院后喪失了部分記憶,為了不讓他的身體進一步惡化,舅姥爺聯合家里人向他隱瞞了太姥姥已經去世的消息。直到太姥爺去世,舅姥爺等人也沒有向他挑明太姥姥去世的消息。
但太姥爺始終在尋找,在詢問,他要搞清楚老伴究竟去了哪里。舅姥爺等人騙他說太姥姥住院了,太姥爺就堅持要去醫院看望太姥姥,讓夾在中間的舅姥爺非常為難,只好一次次編新的謊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太姥爺可能漸漸糊涂了,更可能是猜到了答案,終于不再追問。
舅姥爺工作的天倫公司是改革開放時期,北京市政協與北京貝迪克集團共同組建成立的。在政企分離時期,北京市政協又開始與天倫公司切割,將一部分股份無償給予北京信托經營。
政企分離后,新來的經理打算甩開舅姥爺這些公司的老人們,自己單干。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舅姥爺等人一起到政協交涉,終于驚動了上層領導,此事被迫中止,舅姥爺也得以一直在天倫公司工作到2004 年,隨后開始經營自己的飯店。
姨姥爺和姨姥姥的女兒,我的四表姨于1978 年出生;舅姥爺和舅姥姥的女兒,我的小表姨則于1985年出生。限于政策,他們沒有像自己的父母一樣生育許多子女,而是都只有一個女兒。
我姨姥姥、舅姥爺的子女這一輩,共有姐妹五人,每一位都在各自的領域內干得不錯。我的四表姨與四表姨父結婚,生下了我的表妹。在我小時候,我羨慕媽媽有舅舅而我沒有,因此很長時間里都不喊四表姨父而是喊“舅舅”。小表姨現在在街道工作,就像我太姥姥曾經一樣。而與太姥姥不同的是,小表姨的工作是正式的。我的母親,也是這一輩最年長的大姐在大學中結識了我的父親,兩人相戀結婚。

姥爺、姥姥抱著我和小姨、姨父合影

我和姥姥、姥爺,攝于回龍觀
尾聲
1999年10月4日,我出生。2000年1月,我第一次見到了上文中的每一個人,除了太姥姥。
太姥爺一直和舅姥爺生活在一起。由于腦梗,他的語言和行動能力受限,但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愿和愛。他永遠最寵愛家族中最小的女孩,從姨姥姥開始,到我的母親、我的四表姨、我的小表姨。只有她們才能夠得到糖拌西紅柿盤底的甜湯,其他人都不行。每次被舅姥爺帶到任何一個兄弟姐妹家做客,臨到要走時他總會伸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大衣,隨時準備起身和舅姥爺一起離開,仿佛在說別想把我丟在這里。
后來,我見到了太姥爺,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春節和一個元宵節。
2000 年2 月23 日,見到了重孫子,還偷偷在重孫子手里塞了50 元錢的太姥爺去世,走得非常安詳,享年84 歲。家里人都說,我是唯一一個有可能打破“糖拌西紅柿甜湯歸屬女孩”這個定律的人,然而卻沒有驗證的機會。
我的姥姥和姥爺有兩位女兒。他們把大女兒(我的母親)送到了我的太姥姥家,二女兒(我的小姨)則在姥姥和姥爺家長大。我的母親一直在她的姥姥家長大,我則在我的姥姥家長大。那時姥姥和姥爺剛好退休,他們把我養到四歲時才送回家里。隨著年歲漸長,姥姥和姥爺搬到了回龍觀,和我的小姨住在一個小區。此后的每個周末,我都會去在姥姥和姥爺家里住兩個晚上。

我和小姨的合影,攝于2022 年北京冬奧會期間的國際轉播中心
我也因此經常見到我的小姨和姨父。小姨的工作在我印象里一直和體育有關,2008 年的北京奧運會和2022 年的冬奧會她都在第一線工作。因為她,我在8 歲時就得到了現場看奧運會的機會,在冬奧會時能夠和她一起參與工作。姨父則無論是歷史、科技還是游戲、體育,所有小男孩喜歡的東西他好像都懂。他們沒有孩子,因此在我身上傾注了很多的愛。
每個周末,我常常和小區里的孩子們一起玩。隨著孩子們一點點長大,出來玩的孩子越來越少,補習班里的孩子越來越多。當我的周末逐漸被補習班吞噬時,我見到姥姥、姥爺的時間也就越來越少了。
2019 年,我剛好獲得了一筆獎學金,用這筆錢帶姥姥去了她想去的莫斯科餐廳,辦了一場八十大壽辰。同年9 月12 日,姥姥病逝。她幸運地躲過了新冠時代,卻也讓我永遠失去了采訪她的機會。
我很想念她。
姥爺已經快90 歲了,他自然沒有了帶兩三歲的我上公園玩時那樣敏捷強壯,但是他靜靜地坐在那里時,滿頭茂密帶黑的頭發會讓你以為時光是不是沒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跡。
大舅姥爺曾經是家里的大哥,是家里最有路子的人,舅姥爺和姨姥爺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介紹的。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他不再是那個能夠呼風喚雨的老大哥,親戚們遇到的問題逐漸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大舅姥爺選擇了離開這個大家庭。在我有記憶之后,我經常聽到長輩們談起這位大舅姥爺,卻再也沒有見過這位祖輩,即使是太姥爺的百年冥壽和他的大姐、我的姥姥去世時他也沒有出現。
姨姥爺、姨姥姥和舅姥爺、舅姥姥的生活一直都很幸福,他們還在繼續書寫屬于自己的人生。
(因篇幅有限,本文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