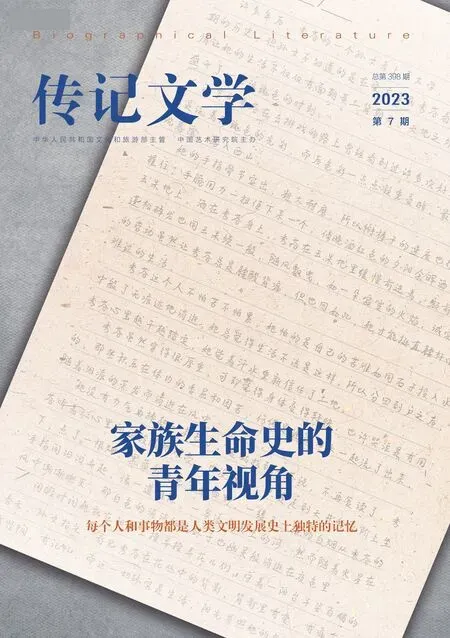沙礫下的白銀
翟子涵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荒涼的角落,或許誰也不會在意,可是從來都有人默默耕耘,哪怕銷聲匿跡,終日潛行。陽光總是親吻它忠實的大地、石塊和沙礫。那些石塊和沙礫之下的,是彎曲的背影,和被石塊沙礫掩埋的——白銀。
1964 年春天,老翟第一次踏上這片黃土地,雙腳踩在鋒利的石塊和沙礫之上,“不平坦”——是他對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作為建設此地的第一代人,他們從遠方而來,帶著來自五湖四海的身與心,將汗水與背影鋪滿大地,用這青春與光陰融化鋒利的石塊,創建出一個新的家園。他們望著不平坦的黃土地,上面布滿了石塊與沙礫,他們看到的不是絕望,而是深埋于地下的白銀與希望。這是屬于第一代人的故事,也是屬于我們的故事。
這是一篇埋頭苦干的故事。
這篇故事由我的外公為我講述。
一
當時的老翟還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澀小翟。
小翟的家境清貧,姊妹兄弟眾多。碰巧當時國家號召發展經濟,各大工廠開始到全國各地招收畢業生,于是高中未畢業的小翟休去學籍,報名招工。成功被選入后,小翟的母親為兒子收拾好了人生的第一份行囊,小翟拎著簡易的布袋子,從那個降生的地方出發,與母親告別,徑直地登上了公交車。簡陋的公交車在彎彎繞繞的土路上搖搖晃晃,年輕的小翟和這左右搖擺的公交車一樣,迷茫,彷徨。
些許期待,是終于走出生活了十幾年的小城,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更多迷茫,是不知要到何處、做何事,如同抓起一把沙子隨意撒出去那般。
不知過了多久,車子停了下來。
“跟著隊,往前走!”
沒有停留,無需詢問,只是告訴你跟著隊伍,往前走。
下了汽車,上了火車。舊時代的綠皮火車帶有別樣的哐當聲,“哐當哐當”,同行的友人早已疲憊,倚著車座打起瞌睡來,但是小翟卻睡不著,他看著窗外的天,那是灰蒙蒙的天,路邊沒有樹,偶爾看見一兩株灌木叢,車窗的玻璃上蒙著一層臟東西,細細一看,是一層薄薄的黃土,綠皮車越走越荒,逐漸連一絲綠色都沒有了,只有無盡的黃色,路邊所生長的也只有稀稀幾棵枯草,沒有像家鄉臨洮那樣,有一條洮河,帶來流水的歡快與生機。看著窗外,小翟的思緒來到了自己的童年時光。炎炎夏日,常常與伙伴們來到洮河附近,裸身跳進清涼的河水之中,散去一身燥熱,時而抱著棵圓木,優哉游哉,隨波逐流;時而伙伴間相互比拼,逆著水流,憑著少年蠻力,奮力爭出個一二。再看看窗外的干涸,小翟首先想到的是今年的夏天會和以往不一樣,沒有了洮水,沒有了朋友,更是遠離了家,內心突然升起一絲難過、悲傷和想念,以及后悔為什么剛才不和母親多說幾句,好好告個別。這種感覺就像綠皮車的“哐當”聲一樣,聽起來是普普通通,但經不住認真聽,認真了,滿耳便是離家的悲泣聲。小翟呆呆地望著窗外,這種難過從內心慢慢來到鼻腔,干澀的空氣再也擋不住眼角的濕潤。“哐當”聲一路駛向黃土地的深處,這條綠皮車成為荒漠里唯一的綠色。
終于,一陣嘈雜聲吵醒了眾人,火車到站了。小小的站臺上擠滿了人,每個人都像是被黃沙籠罩的雕塑,在往后長期的風吹日曬下,每個人的面孔都變得如同這里的大地一樣布滿溝壑,粗糙干涸。小翟看著他們,心中嘆口長氣,原來這里就是白銀啊。
“出門有輛面包車啊,上車,上車。”
下了火車,坐麻了的雙腳還未來得及伸一伸,就又坐上了汽車。一發動就感覺要散架了的面包車已經駛離了火車站。小翟坐在窗邊,本想好好看看這究竟是一座怎樣的城市,但是外面狂風呼嘯,揚起沙子,如同一塊紗布把這個城市包裹起來,生怕別人看到了它的真面目。簡易的面包車如同勇闖天涯的勇士,開著微弱的車燈,在漫天黃沙中行駛,它不必穿透黃沙,它仿佛已是沙塵暴中的一部分,盡管坐在車里,黃土鉆過縫隙彌漫在車廂的各個角落,小翟第一次體會到呼吸間都是黃土的滋味。
下了車,小翟就被呼呼刮來的西北風所驚到,雖然剛剛在車內已發覺這風與以前所感受到的不同,但是真正接觸它的一剎那,小翟才感受到真正的西北風的威力——強勁的風裹著礫石,迎面吹到人的臉上,硬生生地發疼,同時還有塵土,彌漫在各個地方,避無可避,一張嘴,一口土。小翟下車站定后伸展伸展發麻的雙腿,順便環顧四周,看看這究竟是什么地方。可是一眼望去除了遠處幾間小平房,就是黃土、就是荒山!這是一個看一眼很難喜歡上的地方。沙塵暴、西北風、無盡的黃土、干旱的大地,沒有哪一個景象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好地方,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難以生活的地方。
和小翟來自同一個地方的同伴有九人,他們九人最初站在幾乎是一無所有的黃土坡上,迎著狂風,伴著日落,彼此素不相識,但“老鄉”的稱號讓他們惺惺相惜,也是這九人在之后的日子里一步步見證了一個工廠的誕生,陪著這個工廠同甘共苦,同時他們是那批為后代掃除石塊與沙礫的人。雖然初到白銀時,一切都是那么的艱難困苦,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難以保證,可是每個人都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希望,每個人都對這個名為“白銀”的城市充滿期望。
他們相信黃土之下必現“真金白銀”。
1964 年3 月8 日,是小翟來到這里的第二天,小翟與同行的八位同伴前去工廠報到。天灰蒙蒙的,就算打著手電,前方的路也很難看清,一行人緩慢地走在去工廠的砂石地上。不久,老天突然發威刮起了大風,小翟雖然身高馬大,也被這西北風吹得站不穩腳跟,只好與同伴緊緊靠在一起,才不至于被風吹跑,大家一步步地挪,頂著狂風,足足兩個小時,才來到了廠房。說是廠房,不過是個磚瓦搭建起的平房。簡單登記名字、簡單分配部門、簡單分配住處……那一天,小翟拿著借來的15 塊錢,到小賣部為自己購置了第一份家當:一床席子、一床被褥、一個暖壺、一個臉盆、一個搪瓷杯、一支牙刷、兩塊肥皂,還有一個編織袋。一切收拾妥當,小翟來到了人生中第一間宿舍——宿舍樓里的男廁所。小翟就在這特殊的“單間”生活了半年時間。
雖說和別人講起住在廁所里是件很尷尬的事情,但是生活永遠不缺少趣味。比如,從廁所的窗戶往外看,會發現夜晚的天空很美,不過確實出于環境原因,很難看到星星,連本該泛著深藍的天空也是一種霧蒙蒙的朦朧美;又比如,和隔間的同事晚上睡不著時可以暢談人生,也不用擔心打擾到旁人;再比如,可以聽到來自五湖四海的各種各樣有趣的故事,一幫人在小小的廁所里談天說地,人到老年回憶起來也是別樣的人生體驗。盡管在新環境有諸多不適,小翟依然樂觀地面對,努力調整自己融入新生活。
1964 年的白銀是蘭州市的一個區,屬于黃河上游甘肅省中部干旱地區。20 世紀50 年代,從1953 年到1957 年“一五”期間,蘇聯對中國工業領域援建了156 項計劃,憑借著礦產資源的優勢,在白銀境內只有十幾戶人家的郝家川地區就有兩個項目的開展,一個是化工廠,一個是全國最大的銅、白銀等有色金屬冶煉廠,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上出現了“白銀區”三個字。
初到工廠的小翟被劃分到了下屬的廠子上班,這里的每一位工人都來自全國各地,一些是來自東北老廠房的老工人,一些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中專畢業生,一些是軍隊的轉業人員,還有一些來自沿海發達地區。當時工廠的工作從基建開始,而像小翟一樣沒有知識背景的高中畢業生則要從頭開始惡補各類知識。于是,小翟開始了緊張的學習過程,在老廠工和來自沿海地區技術人員的幫助下,他逐漸了解工藝技術。半年時間內,小翟白天學習新東西,學習機器,學習流程,學習圖紙。夜晚,他拿起筆桿,將所見所聞所獲記錄下來。半年后,小翟成功通過考核,參與了工廠的第一條生產線的第一次投產。小翟記得很清楚這一天是1964 年8 月2 日,自這一天起,小翟成為了這條生產線上的一名倒班工人。
他們這代人拾起石塊,防風治沙。
他們是這樣的第一代人:不問來路,不問浮名,將彎曲的背影散在大地上,未來,又要將自己的骨肉葬于這片土地。
他們這一代人不僅僅是拾起石塊的一代人,更是建起高樓的一代人,建起圍墻的一代人。
20 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國家戰略部署下,小翟所在的工廠也迎來了艱巨的國防建設的任務。
面對突如其來的任務,廠里人手有些緊張,經過商議,決定土建部分由工廠共青團團員和共產黨黨員在晚上的業余時間里加班進行。于是小翟與工友們在北方天寒地凍的12 月里,身著單衣,舉著榔頭,在零攝氏度以下的室外挖土方,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每天從早上七點開始干活,中午吃頓飯休息一下,一連干到深夜。在這期間,廠里免費發放糧票,提供二兩面條的供應。午飯時間一到,工友們圍成一圈,捧著飯盒,“哧溜”的響聲,證明這二兩面條有多好吃。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快樂的笑容,彼此互相看看,也是止不住地笑。兩個月的時間里,小翟和工友們超額完成了任務。
將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外公說,他認為吃過最好吃的面條就是當年挖土方時每天吃的那二兩面條子,其實也沒啥特別之處,就是手工拉出來的白面拉條子舀了一勺素菜和一勺臊子湯,配菜少得可憐,可能記憶中最寶貴的味道是屬于那個年代沒有任何添加劑的糧食香。當時的記憶與味道一直留在外公的腦海里,面條成為了回憶那段充滿力量和奮斗精神的青年時光的標志食物。哪怕之后的生活條件好了,外公最喜歡的食物依舊是面條。
國防建設任務的艱巨最終轉化為二兩面條的甜美。他們真的很渺小,但星星之火之所以可以燎原,偏居中華大地一角上的他們,哪怕是做著挖土方的工作,也是勝利背后的原因吧。
二
小翟在工作中勤勤懇懇,橡膠鞋底踏過車間的每個角落,匆匆的步伐、忙碌的身影并沒有辜負小翟的努力,在這座白銀小城中,小翟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塊“白銀”。這份禮物充滿愛意,陪伴小翟走過人生往后多少個春秋;這份禮物是份福氣,多少個冬暖夏涼都有愛人的陪伴。這是一份可貴的愛情,一塊沉甸甸的白銀。
在這片黃土地上,暗藏著許多白銀,小翟與同齡的伙伴們用真心與勤勞挖掘深埋于地下的白銀,待這些白銀浮現后,正是那一代人愛情的出現,彼此短短相視一望,便是跨越幾十年間的相濡以沫。
1976 年的夏天,是小翟與小劉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小劉第一次來到白銀這座城市,從此以后,小劉將余生都留在了這片黃土地上。
小劉的老家在甘肅省天水市,年紀輕輕的她于1965 年就開始參加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蘭州第一毛紡廠擔任擋車工,自從入廠起,小劉就是每年的“先進生產者”,當時的擋車工一人最多只能擋四臺紡車,而小劉可以擋六臺,她的事跡和照片還登上了《甘肅日報》。1976 年,小劉為了支持小翟工作,辭去了“蘭毛廠”的工作,離開了生活條件在那個年代相對較好的省城,只身來到白銀,和小翟一樣,加入到這片土地的建設工作中。小劉調來后,單位給小翟分了一間18 平米的土坯房,在這個小房子里,小翟用一個月的工資置辦了一整套新家當,這是屬于小翟的人生第二套家當。小翟掏出單身時節省下來的錢請人打了一套木制家具,還請匠人筑起了新灶臺,小劉和小翟一同去公社購置了一些生活用品,日子,就這樣開始了。
雖然我從小生活的家中已不是當年那間小屋子,但一些20 世紀的老物件卻又存在于屋內的各個角落,比如,家中的洗臉架子就是一個很古老的刷漆木凳。外公告訴我,這個木凳是當年他與外婆結婚時專門找人做的。直至今天,這個木凳的質量依舊很結實,乳白的油漆掉了不少,露出了它內層的木頭,木頭的顏色很深,好似歲月的痕跡。雖然木凳看起來老舊了不少,可是在如今的房子里,哪怕增添了再多的現代家具,木凳的存在對于外公外婆而言就意味著這個家還是當年的模樣。外公外婆的愛情,宛若那個刷漆木凳,深褐色的木材之間,喘息著的是交織的生命。
生活,是鍋碗瓢盆的平淡,也是不時閃現著的一個又一個小驚喜。
1972 年,小翟的第一個女兒小秦降生在天水。
為什么要叫小秦呢?
秦字,形如舉杵舂禾,象征著成熟的莊稼,并且小秦降生于天水,這里古稱秦州,小翟以秦字命名女兒,希望女兒可以茁壯成長,學有所成,成為一棵稻谷,豐富人生。
由于小劉和小翟的工作都很忙碌,根本沒有能力照顧女兒,所以小秦自出生起,就被留在了天水,由小劉的母親看養,小劉不在女兒的身邊,小秦只好從小喝奶粉長大。小秦是由外婆抱著長大的,外婆陪著小秦學會了走路,學會了說話,學會了一個人吃飯,學會了自己去上幼兒園,學會了在小小年紀可以基本照顧自己。而此時的小劉和小翟都在艱難生活的平原上如陀螺般轉著。
這樣的日子稱不上是苦難,但隨處可見生活的酸澀。外公與外婆年輕時候的奮斗生活史像一部寫實電影,反映的是那個年代的工人們的普遍生活,這樣馬不停蹄的“陀螺生活”對外人講起來可能是無聊的、無趣的、塵土般的、干澀的。但也正是這樣的生活,讓一個家、一座廠、一座城轉動了起來。
1977 年,小翟與小劉的第二個女兒降生了,小翟給她起名為小銀。
為什么要叫小銀呢?
小女兒出生在白銀,這個因有色金屬而生的城市。銀,與其他黑色金屬不同,它自身反射著一種耀眼的光澤,這種細膩的金屬不同于黃金的高調奪目,也不同于黃銅般的暗沉無光,它是這般內斂穩重的同時又可以刻畫出別樣的輕巧歡快。
小女兒出生不久,大女兒由于要上學的緣故也被接回了白銀,當時小翟當上了工長,大家都稱他為翟公,要開始上長白班,早上早早地去到工地,傍晚才回到家中。于是,小女兒又被送到了天水,到外婆身邊,小銀的外婆再次從頭看著一個小女孩長大。
每一個小孩子的長大都很不容易,不過幸好有外婆在。
這段時間里,小翟在日常的工作中,跟來自不同地方的同事們進行學習和討論,在專業知識上學習了不少內容,在思想覺悟上也得到了提升。此時,小翟的人生中有了一個重要的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工廠的工作與生活,讓小翟意識到了人生的選擇有很多種,而敢于奉獻,勇于擔當,忠于信仰,是一個了不起的選擇。生命中無意被白銀選擇,事業上無意被工廠選擇,此時的他感謝這份選擇,來到白銀的小翟通過自己的努力有能力去選擇、去保護、去擁有、去奉獻。于是,1977 年的秋天,小翟經過深思熟慮后寫下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
據外公回憶,對于那份申請書的原稿,他一字未改,下筆那一刻,寫下的都是真情實感,讀了再多遍,依舊是那份熱血澎湃的感受!
1981 年9 月1 日,經黨組織批準,小翟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三
20 世紀80 年代,白銀市有色金屬公司主體礦山進入開采后期,銅資源大幅度減少,工廠計劃任務減少,有色金屬工業進入困境。白銀小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時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小翟作為工廠第二梯隊的后備干部,于1984 年被廠里推薦,考入甘肅廣播電視大學,進行“全脫產二年制黨政干部基礎理論必修課”的學習,當年的小翟已經有38 歲了,再次進入校園,當起學生,學習新的領域的知識,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挑戰。雖然生活壓力和學業壓力重重,但是小翟成功拿到了學位證書。
1986 年8 月,小翟被指派了一項緊急任務——和當年一起來白銀的八位同伴到廠志辦公室編撰《廠志》。一連幾個月的搜查資料、翻閱書籍、尋訪見證人,小翟與其他八位同事編寫出了第一部廠志,當時這本不太厚的油印書中所記錄的不僅僅是短短二十多年間,一個位處祖國內陸深處的工廠的發展史,更包含了像小翟這樣二十年前背井離鄉來到這片荒漠,通過一點一滴努力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的企業工人所留下的心血,以及他們留在這里的青春和生命。廠志編寫快收尾那幾天,小翟和同事們從白銀火車站包了一輛面包車,重新走了一遍進廠路。小翟望向窗外,白銀市區的街道上有一排剛種植一兩年的柳樹,街邊是新修建的綠化帶,里面種著一些矮小的灌木和淺色的小花,微風吹進車廂,帶著獨有的暖意。
二十年,足夠和狂風告別,也足夠掃凈塵土。
再后來,公司為了更好地建設分廠,聘請了德國外賓。小翟被調到對外招待所擔任主要負責人。小翟第一次負責這種行政上的接待工作,在此之前全廠從沒有人正式有過相關工作經驗,小翟只能自己摸索,盡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不能讓外國人看低了中國人。小翟開始到處查詢資料該如何接待外賓,有了一定相關知識后,開始計劃這項任務,對吃住行,一一進行了規劃和安排。
那年,外賓成功入住到了賓館,小翟的任務也圓滿完成。
1992 年,小翟被提升至公司動力廠黨支部副書記。在這段時間里,小翟逐漸深入了解如何研究安排黨支部工作,召集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大會,了解掌握黨員的思想、工作和學習情況,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做好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公的工作筆記,我未曾細細閱讀,但墨藍色的鋼筆字跡在句讀之間讓我仿佛看到了當年外公深夜伏案工作的身影,窗外月明,窗前風攢,而窗下人心靜,將歷史與時間記錄在案,將來路之艱辛化成筆墨留在書扉,將自己融進工作,伴隨工廠的成長而成長,伴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在時代的長河中默默耕耘,哪怕銷聲匿跡,也要終日潛行。
秋天是收獲的季節。小翟在工廠的不同部門之間學習、收獲,從基層基礎機械運行,到人為控制機械運行流程;從坐在大學教室學習一門新的課程,到將所學所思應用到工作崗位的實踐中;從一個勞力工作者,到執起筆桿寫下工廠的過往;從一個群眾走向資深的老黨員。當年的小翟怕也是沒想到自己可以在這片土地上收獲這么多吧。
四
從廠門口進入后有一條筆直的馬路,馬路兩側長著高大的柏樹。從小銀也就是我的母親回到白銀時,那道路兩旁的樹就生長在兩側。
它們被第一代人播種,與第二代人一同成長。
沒有了石塊與沙礫的白銀,更適合新一代的成長。
1983 年的冬天,小銀被接回白銀,希望可以在白銀上小學,受到更好的教育。于是來年里,小銀與姐姐小秦一起在小學上學。
1985 年,小學學制進行改革,為了不影響小秦的學習,小劉決定讓小秦到天水去讀住宿高中。于是,小秦再次離家,來到天水,一年才回白銀一趟,過年也是大家在天水團聚。之后,小秦又回到白銀參加了中考。小翟與小劉為了可以讓小秦早些上班,讓她參加了提前招生考試,小秦自小成績優異,提前被東北的一所五年制大專院校錄取。收到通知書后,大家并未因為優異的成績而高興,反而陷入了猶豫不決當中。家里沉默了幾天,終究還是沒讓小秦去那所學校,而是上了技校,想著學有所用,可以直接入廠。
1990 年,小秦正式參加工作,分配到了公司動力廠工作,上長白班。再后來小秦又通過自學考上了公司職工大學,學習的是化工機械專業。翟家的小女兒高中畢業后考上了蘭州市一所不錯的中專院校,學習分析化學專業。畢業后本想留在外地,但是小翟和小劉堅持叫她回來,回到工廠工作,最后小銀分配至公司科研所理化分析室上班。
小秦與小銀成為了建設工廠的第二代人。
小翟一家四口,都成為了當地建設中的一分子。
我出生于2004 年的8 月,而外公退休于同年的9 月。我一出生,外公便每一天都陪在我的身邊,不曾看見外公身著藍色工作服的模樣,但外公總是帶我在下班的時候守在大馬路旁,等著媽媽回家。在那條筆直的大馬路上,廠里的人們大都騎著自行車或者電瓶車,他們一律穿著深藍色的工作服,對于兒時的我而言,很難從他們之中分辨出誰是媽媽,但現在回想起來,他們其實都是外公的模樣,是年輕的外公的樣子。
廠里有個特點是會在上下班的時候響起廣播聲,陪伴著每一位上班或歸家的人,這熟悉的廣播聲也陪伴了我18 年的光景。在那片柏樹樹蔭下,外公外婆教會了我如何喊媽媽,如何走路,他們看著我長大,陪著我成長,成為我的庇護,成為我的靠山,我因為有了他們的照顧而不需要像我的媽媽和大姨一樣被送到遠方,在遠離父母的地方學會獨立。我因為有了他們而可以隨時撒嬌,隨時告狀,隨時投入一個溫暖的懷抱。我,成為了很榮幸的,也是最幸福的第三代人!
工人們都很在乎子女的學習,因為作為二代,他們將一生都留在了工廠,留在了白銀,對于外面的世界,希望子女能代他們去瞧一瞧。我的媽媽與大姨也很在意這件事情,可能是因為她們對沒能去到更遠的地方抱有遺憾吧。
我與表哥都是在市里上的小學、初中和高中。為了我們,全家人都很努力。
綁在自行車座上的海綿、買的超大的雙人傘,可以不用著急趕公交車,而是坐在后座上甩著兩條腿優哉游哉,有時會因為暴風雨而顯得很狼狽,但更多的時候可以比別人多收獲一份夕陽的禮物。雙腿漸漸不能隨意擺放,于是有了自制腳蹬子……再之后,我上了市里不錯的初中,外公也老了,風里來雨里去的那輛自行車閑置在了家里的角落處。我常常是坐著那趟唯一來往于市中心與工廠的2 路公交車往返外公外婆家。
2022 年的春天,我迎來了人生大考,高考過后就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選擇,但是作為我這一代人,和當年的媽媽與大姨面臨選擇時所考慮的問題已截然不同,全家人都支持我去國內的一二線城市上大學,走出去,看看祖國的繁榮大都市究竟是什么樣子。
外公想到,當年的他聽從家里人的安排,高中沒畢業就休了學,跟著一群陌生的同伴,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被安排到廠里上班,接著每一步的發展自己好像從來沒有作過太多選擇,一切都是廠里安排,自己要做的只是努力做到最好就可以了。而如今,孫子輩的我晃眼間,已經到了當年外公來到白銀討生活的年齡,與外公不同的是,我對人生有了更多的選擇,未來是一道充滿未知的探索題,答案究竟該如何寫,看的是我自己每一步的人生是如何選擇。
我是最幸福的第三代人。在這座被祖輩們建設得如此溫馨的小城中無憂成長,在外公外婆的照顧下健健康康長大成人,在父母輩的努力下,受到好的教育,擁有好的條件,可以去選擇,可以去嘗試,可以去經歷他們不曾經歷的人生,可以去邁向更廣闊的世界。
第三代人成為了第一代人的驕傲;第三代人成為了第二代人夢想中的樣子。
五
寫到這里,外公的故事好像已經進入了結尾。因為我意識到,我與外公的生命軌跡好像越走越遠了。年邁的外公精力已不再像年輕時那么充足,每天在做的事情也不過是打掃打掃衛生,看看電視,琢磨一下手機,當然,他還是那么愛看新聞。與外公的交流也不再多,在外讀書讓相見都變得很難。外婆家窗前有幾棵柳樹,兒時外婆帶著我搬著板凳,坐在樹蔭下,躲過酷暑的炎熱。那惱人的柳絮、吵人的知了、來自外婆扇子下的微風、伴我入睡的第一首童謠……與外婆一起度過的童年時光成為一種記憶,總是在一個人的時候被喚起。而從今往后的寒冬里,干枯柳枝的窗下,只剩一對背影。
第一代的他們陸陸續續將身與心交付給了這片土地,他們像當年來到這里一樣,不曾帶走什么,可留下的是今天發展尚好的工廠,是位于祖國內陸但風景宜人的白銀,是懷揣著夢想與希望的我們。屬于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屬于我們的時代才剛剛開始。
難道故事就結束了嗎?可是,我們不就是曾經的他們嗎?
我,就是當年的外公,來到一個新的城市學習與生活,探索知識,學習技能,投入到建設祖國的工作中。在未來,通過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白銀”,在忙碌的生活節奏里,從未放棄,從未停止。我在奮斗的人生中繼續書寫著我們全家人共同的故事。
六
這篇故事由我的外公為我講述。
此后,將由我來講述。
我想告訴世人這是怎樣的三代人。
《澎湃新聞》中有一篇關于白銀的報道是這樣描述的:“這個因廠礦而設立,以重金屬命名的城市里,祖輩們拋棄了根,隔斷親緣,來到這里。二代們將終生奉獻于此,第三代又如候鳥般飛離。等到第四代出生的時候,多半又將重歸五湖四海,并把二代們的身和心再次帶離。”
而我對三代人的講述是:
他們的第一代,默默耕耘,終日潛行,拾起那鋒利的石塊,清除磨人的沙礫;他們防風治沙,種下綠植,鋪上柏油馬路,建起高樓,建起屏障;他們選擇在這片土地上生兒育女,繁衍后代,建立新的根基,建立新的家園;他們撫育兒女成長,并教育他們學成歸來,繼續建設這個家園;他們將生命從遠方帶來,播種于黃土地,生命頑強生長,繁衍不息;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埋藏于黃土之下,以骨肉化為養料,滋潤大地,呵護萬物生長,讓這片黃土地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歷史故事。
他們的二代自小長于這片土地,家對他們而言就是這里,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鄉語怎么說,故鄉的概念對他們而言或許已經模糊,但是一到外地,大家都會一致介紹自己為白銀人——“銅城”白銀。作為二代的他們,自小看著父母早出晚歸,問起什么工作,都會說“進廠上班去”。廠子,成為大家幼時的向往之地,隨著年齡增長,課本中外面的世界或許更加誘人,他們努力學習想著出去看看,但是大多數人又因為各種原因,回到廠子,往日的同學成為同事,一起建設從老一輩手中接過的工廠,看著它隨著科技進步變得更加智能,無人操作成了工廠發展的主線。他們這代人一生都與這個廠子緊密聯系,也正是他們這代人,見證了祖國發展的蓬勃時期,創新精神的發展、科技人才的引入、管理政策的改善,等等。變得越來越好,是這代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每個二代人心中,或許都埋藏有一個小小的遺憾,這遺憾如同一抔黃沙,風過沙散盡,指尖仍殘留那綿綿細土。雖有遺憾,二代人仍為這片黃土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的故事不盡相同,卻各有各的精彩。
他們的第三代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出去看看,是每個第三代人刻苦讀書的目標。因為他們的父母自小教育他們一定要好好學,努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三代人的故事如同一股泉水,發于山澗。第一代人呵護他們成長,緩緩流淌,帶著二代人的心,卷著細沙,流向各處,追著夢,追著心,看遍世間美好,尋找新的家園。
我想講述的正是這樣一段故事:
在祖國的西北有一座名為“白銀”的小城,在這座小城中有一個工廠,最初它埋藏于鋒利的石塊與沙礫之下,有這樣的一代人,他們默默耕耘,哪怕銷聲匿跡,也終日潛行;他們從遠方走來,將青春與生命奉獻于此;他們為后人掃除了石塊和沙礫,建設了新的家園。在這些石塊與沙礫之下,他們最終也收獲了屬于自己的“白銀”。
在市中心的公園中有一座獻給他們的雕塑,上面刻著“獻給銅城的開拓者”,“開拓者”是對他們最大的贊美。
再后來,他們將自己的身與心留在了這片土地,這里不是他們的故土,但對他們而言,這里就是他們的家園。
努力為國家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創造新的輝煌——這是第一代的他們期待的人生圖景。
而我的故鄉——白銀,從最初的黃土坡變成了如今令人向往的模樣:
歡聲笑語充盈于晴空
萬家燈火照亮著歸路
驚蟄是草長鶯飛
大暑是花紅柳綠
秋分是落葉飛舞
冬至是銀裝素裹
新春而至
萬家團圓
張紅燃爆
這是一座同呼吸共命運的北方小城
往日時光,匆匆流水
腳下萬水千山
卻遠止不住對你們的思念
微風拂起,花草清香
雙眸望眼欲穿
遠方的家又是否無恙
在那祖國的內陸
雖燈光昏暗
但無數次照亮我的夢鄉
無時無刻
不在思念
外公外婆已經年老
不能伴你們身邊左右
唯愿
攜著你們的眼
奔向遠方
看遍世間萬紫千紅
看遍世間花紅柳綠
看遍世間一切 一切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