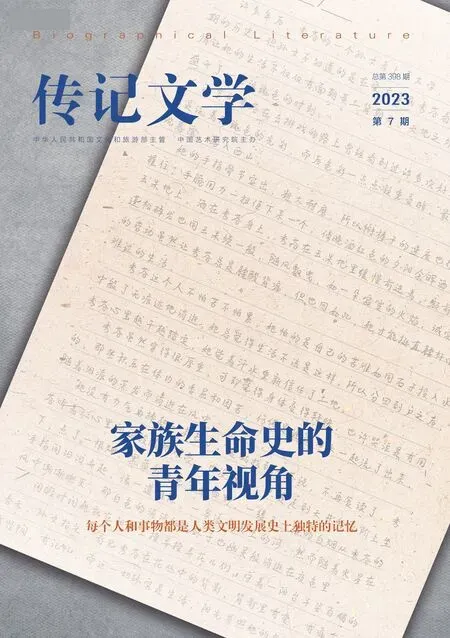歷史的回望與還原:論漫畫回憶錄中的記憶
徐 萌
漫畫回憶錄的初始功能就是對個人記憶與時代記憶的記錄。歷史作為記憶的官方形式,常常被認為具有極高的可靠性。人們通常認為,歷史學家極力摒棄記憶的夸張和偏頗之處,公正地、批判性地呈現出客觀的集體記憶。記憶作為原始材料,其多視角的補充對歷史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漫畫回憶錄作為對記憶圖像式的追溯與還原,進一步豐富了歷史資料的形態,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全新形式的歷史檔案。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伯克認為:“圖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證詞一樣,也是歷史證據的一種重要形式。”[1]在彼得對“圖像”的寬泛定義中,漫畫就是其中之一,它可以讓我們更加生動地想象過去、重塑過去。不同于傳統的文字回憶錄對讀者想象構造的依賴,漫畫回憶錄在創作時就基本完成了這一工作的絕大部分,但回憶錄的主體顯然對創作者提出了至高的要求——這些圖像必須無限接近歷史環境。漫畫回憶錄的作者當然不是在作單純的還原,那不過是一部描摹畫的集合,無疑限制了這一媒介的效用。顯然,抽象化的漫畫語言對真實的展示有著更為特殊的混合屬性——漫畫對特征的高度抽象化和現實主義畫風對細節的無限具象化往往被視作是背道而馳的,漫畫回憶錄要在這種矛盾中達成和諧。因此,在一部漫畫回憶錄里,圖標中往往被著重處理的是那些具有時代特殊性與顯著影響的因子,這使得非現實主義的圖像同樣也能抵達真實。不單單是圖境的接近,語境和視角的還原對合理性的達成也至關重要。圖像或許擅長彌補沒有留下影像記錄的部分,但那些可能從未被言說或被忽略的歷史通常更依賴于講述者的記憶視角。
記憶時空:個體視角下的歷史群像
雅克·塔蒂在創作《戰俘營回憶錄:1680 天》之初,就希望將其作為二戰期間戰俘群體的珍貴歷史檔案公之于世,以此來記錄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對抗時間的流逝和遺忘。塔蒂的妻子多米·妮克在為此書作序時如是說,“或許有成千上萬的人和他一樣,不同于那些戰壕英雄,他們沒有耀眼的勝利和功績來炫耀……當時幾乎沒有人試圖了解年輕的他們如何在眾多的戰俘營里熬過了受盡屈辱折磨的幾年”,“這部作品是勒內的證詞”[2]。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懷著戰爭的創傷,大屠殺文學蓬勃發展,人們渴望展現歷史的真相,幸存者文學以其唯一在場性(這里主要指每個幸存者獨有的歷史參與性和個體視角)成為重要的研究視角,主要代表作品有馬克斯·蘇薩克的《偷書賊》[3]、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4]、伊恩·麥克尤恩的《黑犬》[5]等。與此同時,幸存者的自傳、回憶錄也成為重要的歷史資料,如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6]、迪克·溫特斯的《親歷兄弟連——溫特斯少校回憶錄》[7]等。關于這段歷史記憶,關注點基本都落在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對戰爭的反思和幸存者戰后創傷的延續。顯而易見,在文學史上,無論是小說還是傳記,戰俘群體本就被長期忽視并逐漸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群體,尤其隨著時間流逝,其中許多當事者早已經將這些故事帶進了墳墓。《戰俘營回憶錄》無疑還原了一些被人們所忽略的、即將“逝去”的記憶,尤顯珍貴。
不得不承認,這樣一份宏大的“歷史檔案”是來之不易的。我們知道,根據創作者身份與記憶主體的關系,回憶錄通常也被分為自傳式和他傳式。后者在實際操作上其實更為困難,這是較于自傳來說更艱難的還原,更何況是將大量的記憶素材可視化,如何呈現細節也許比細節本身更為重要。很多人會把這種漫畫回憶錄的創作過程想得非常簡單,然而雅克·塔蒂曾回憶自己的創作經歷:妻子研究了眾多照片幫助明確故事背景,兒子花費許多時間去研究文獻資料……而實際的創作過程要遠比我們想象的創作過程還要艱辛得多。為了精確地重現歷史,塔蒂特意重走了父親所到之處,實地考察,詳細核實,最終還原了當時的軍事地圖和父親長達四個月的行軍路線,這為整個回憶錄作出了堅實的地理注釋,幾乎每一處都有著明確的地標對照,證據翔實。而作品中還原的許多畫面,例如圖1 所示,也令人印象深刻[8],尤其是呈現了某些超出日常認知范圍的情景,都是那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如果沒有當事者的記憶,這些經歷難以想象,震撼人心又令人忍俊不禁。戰俘營環境艱苦,為了活下去,人們逐漸放下尊嚴和榮辱,只為生理服務。

圖1
私人的記憶不僅作為官方記憶的補充,還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雷吉斯·德布雷認為,圖像源于喪葬,正是為了延續死者的“生命”,才制作出雕像、塑像、畫像等一系列的圖像,將珍愛的、易朽的對象永遠保存下來,這是人類的普遍要求[9]。漫畫回憶錄也逐漸成為紀念的媒介之一。莎塔碧說道:“我也不希望人們忘記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在獄中失去生命、在兩伊戰爭中喪生、在各種暴政統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離開親人和祖國的伊朗人。”[10]她的《我在伊朗長大》記錄了這些英雄和眾多無名的堅持者,同時也向人們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伊朗。一方面,不同于伊朗人對他們國家歷史的回顧式書寫,瑪贊一家代表了這片土地上較少一部分人的目光——他們雖是純粹的皇室后人,但從出生起便接受西方現代教育,身在家國,靈魂卻格格不入,這種混雜文化背景的視域中對伊朗國家歷史的展現具有獨特的價值;另一方面,作品中講述者瑪贊的獨特視角——童稚到少年時期寄居他國的經歷,又為這段歷史摻雜了一種置身事外的懵懂和認知變化過程。
《鼠族》對記憶的表達呈現出多維度交融的特征,這首先體現于其典型的雙敘事模式:一邊展示自己和父親現在的生活狀況——以收集父親的口述記憶素材為由,一邊斷斷續續進入父親的記憶。在拉彼得·漢德克的代表作《無欲的悲歌》[11]中,記憶主體重疊交互的敘述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作為一部擬回憶錄小說,他在回顧母親的一生時,同時記述自己糾結的創作過程,展示了人在面對記憶時難以把握真實的諸多不確定感。《鼠族》亦是如此,再現了人與記憶的連結,記憶被重啟、重現時的心理流動。它的雙線模式通常被認為是為了更全面地展示父親戰后的生活,以闡釋戰爭帶來的持續性創傷,然而同《無欲的悲歌》一樣,其雙線敘述強調著多空間的記憶——首先側重講述父親二戰間幸存的記憶,第二層則再現阿特收集父親的素材期間的記憶,再者又展現了父親在此期間的部分生活片段。對父與子的生活和記憶的多時空、全方位還原,使得父親的幸存史也豐滿立體了許多——父親當時曾經怎樣看待自己,后來又怎樣重新看待曾經的自己;阿特曾經怎樣理解戰爭中的父親,再到創作中又如何重新審視這一切。這其中包含了不同個體對那個時代的凝視,展現了自身對他人的注視,以及某種意義上的自我審視。
近年來,漫畫回憶錄能獲得學術認可并逐漸走向經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透過個體視角對時代的忠實反映。20 世紀70 年代,漫畫回憶錄從地下漫畫中獨立出來之時,恰逢人類文明最動蕩革新時期——戰后世界支離破碎,秩序亟待重建,科技革命迅速發展,一切價值重估,人們緬懷過去,困惑于當下。時代的需求自然而然地為這些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時空跨度較大的重大題材的書寫即意味著宏大敘事。麥克勞德曾在《理解漫畫》中對漫畫作出了明確的定義:“經過有意識排列的并置圖像及其他圖像,用來傳遞信息和激發欣賞者接受美學。”[12]其中,圖像的“并置”起到關鍵性作用。不同于其他基于視覺的靜態媒介,漫畫獨有的連續性使得宏大敘事得以可能。這些繪畫形式獨立的時空特點使得敘述內容十分有限,即使有些單幅作品篇幅很長,內容廣泛,甚至帶有情節(如《清明上河圖》),但場景的合一性仍有很大的制約。而漫畫的連續性將不同的時空在畫格之間連接起來,中間的空隙注入我們的想象力,借助知覺封閉的力量、可見與不可見的配合,使我們可以將并置的圖像轉換成完整連續的、統一的現實世界。時空連續性不僅可以作出長篇敘事,并且極大程度上調動讀者的參與感,于是真實在場感不言而喻,這和回憶錄對真實的追求不謀而合。
在漫畫回憶錄中,畫格本身作為一種重要的圖標,也是一種敘述語言。畫格之間的連接承載著時空的變化,是漫畫可以進行長篇敘事的重要依托。畫格本身雖不會改變內容,卻能改變閱讀體驗。
在《鼠族》的雙線敘事中,兩個時空之間常伴有插敘,阿特進行了特殊化的處理作以區分,使讀者更容易辨認。例如在回憶的故事中插入講述者當下的評論和想法時,非過去時空部分的圖像都是沒有畫格邊框的[13],如圖2 中右上角的阿特和中部左方的父親。去邊框處理是《鼠族》中獨有的畫面敘述手法,它讓頻繁的雙時空插敘秩序井然。

圖2
畫格中一些巧妙的圖形分布隱藏著因果與聯系。如圖3 所示,《鼠族》開篇有一頁的畫格分布十分有趣[14],三個分散的畫格中的部分圖形可以連接起來,在頁面中央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物動態圖——年邁的父親一邊踩著自行車康復訓練,一邊和“我”提起這段歷史,他的眼睛受傷、視力受損,需要戴著眼鏡,集中營的編碼仍留存在他的胳膊上。而頁面的右下角用圓形畫格呈現出父親年輕時候的形象特寫——年輕挺拔,衣著得體講究,充滿活力。這種視覺對比在故事之初就隱藏了諸多信息。

圖3
正如我們所熟知的,漫畫回憶錄中每一個畫格通常展現某一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事物,當進行到下一格時,情況必然會發生變化。正是這樣的閱讀“潛規則”使我們默許時間的推進,將單獨的行為串聯起來,形成情節。那么,單獨畫格里可不可能容納多種時空呢?答案幾乎是肯定的,《鼠族》的插敘手法在圖像上就表現為多時空并置。事實上,相比時間,空間的多重化更具靈活性,畢竟時間轉瞬而逝,但空間可以被有意切割,允許被同時放置。貝克德爾在她的家族回憶錄《悲喜交家》中,為了表達家庭中的距離和隔閡,就采取了這種方式,如圖4 所示,即在同一畫格中制造空間矛盾[15]——同一個家庭里,大家各有自己的小空間,幾乎毫無關聯。相比設列不同的畫格來一一展現,一個畫格中的多空間并置突出同一中的非同一感,割裂感更加強烈。

圖4
不止同一畫格中的多空間并置,不同畫格之間也可以在時間的行進中并列同一空間,兼顧完整的視覺效果。如圖5《鼠族》中繪奧斯維辛中每天排隊領湯的場景[16],從上到下的四個畫格在分別敘述吃飯的細節和領湯的技巧,圖畫細節則相互銜接,共同組成了一幅全景。值得注意的是,下方吃飯的場景中,右側的角落就橫著幾具或許是被餓死的猶太人的尸體,仿佛意指死亡距離他們如此之近,隨時都有可能因饑餓喪命。然而,如此強烈的視覺對比被刻畫得隱秘而平靜,讓人心悸的同時又無限接近了那種切身的無望之感——奧斯維辛中的每個猶太人或許早就習慣了身邊人的死亡,只能想盡一切辦法努力存活。

圖5
心理真實:視覺中的變形與“虛構”
毋庸置疑,直觀的視覺沖擊力是漫畫回憶錄最有力的武器。當作者想要對讀者強調某些信息時,常常直接突出對象,鋪滿視線,讓你不得不去注意它。如果一篇文章想要突出信息,長篇幅的描寫是基礎途徑之一,漫畫回憶錄異曲同工,其經典形式就是類似于電影的“特寫鏡頭”,出現時常常占據較大的畫格。不論是電影還是漫畫,特寫最擅長的就是內心活動的傳達,它放大細節,通過線條和形象刺激感官,從而產生極強的感染力和共情性。如圖6 所示,戴維在《縫不起來的童年》中,就呈現了許多臉部特寫,其中在表現家人對自己的心理壓迫時,畫面中的人物面部陰影濃重[17],充滿窒息感,俯視的角度、高高在上的姿態和憤怒冷酷的表情更是讓人心悸。

圖6
突出的另一種方式就是重復/重疊。圖像重復類似于敘事作品中的頻率,即某一動作或形象反復出現,例如戴維的回憶錄中不斷出現的“小人”、阿特的《在沒有雙塔的陰影下》中多次閃現的“熊熊燃燒的北塔”;圖像重疊也有類似的效果。重疊,是指將相同或相似的圖形并列疊加使用。如圖7 所示,瑪贊的《我在伊朗長大》中對重疊的運用簡直爐火純青,常常用來描述宏大的、群體性的事件[18],如革命、屠殺和慶祝,但同時又充滿趣味性,十分符合敘述者的視角。首先,疊加帶來的數量優勢會造成視覺密集感,給人以直觀的沖擊力,喚醒感官;其次,重疊常常將復雜的事物簡單化、規律化,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讀者的理解;再次,在這種疊加中,圖形的同一化也更容易凸顯時代變革中的某種統一性和普遍性,天然地增添了漫畫回憶錄獨立的宏大敘事能力。

圖7
顯而易見,相較于其他靜態圖畫(如素描、油畫等),漫畫的畫風本身就偏向于極簡。但回憶錄對細節的要求又更翔實一點。所以,當一部漫畫回憶錄在此基礎之上出現不尋常的簡化之時,往往屬于有意為之。簡化也是一種強調,創作者刻意隱藏某些信息,以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增強參與度,從而達到心理層面的沉浸和融入。如圖8《縫不起來的童年》中“缺失的眼睛”,戴維在作品中作為講述者,他的眼睛自始至終都是清晰的,刻意被隱去眼睛的似乎都是戴眼鏡的人——父親、母親和外婆。麥克勞德曾在他的漫畫理論三部曲中描繪自己的形象時,就僅僅畫了一副鏡框,以簡單塑造一個“講述者”,因為畢竟不作為故事的參與者,圖像功能單一,不需要留有細節化的解讀空間。但《縫不起來的童年》中隱去眼睛的鏡框明顯不屬于這種情況,眼睛的缺失不是從一而終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又會回歸正常化。作品中的父親、母親和外婆都是戴維成長陰影的主要來源,眼睛的缺失象征著漠視,他們都自私冷漠,看不到戴維的需求[19],無視親人的苦楚。而當涉及到極端情況,或觸碰到他們在意之處時,情況才會發生改變。例如圖9 所示,戴維無意間發現自己患了癌癥而家人一直向自己隱瞞之時[20],他輕聲質問,而父母卻怒氣騰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被侵犯,這時他們的眼睛浮現,傳達出壓制、恐嚇、毫無歉意等種種訊息。還有,當母親以為戴維瀕臨死亡時,終于愿意對他作出最終的關懷,這時她的眼睛回歸正常。

圖8

圖9
另外,在處理一些特殊情況時,也會作必要的簡化。通常源于視覺上的緩沖和心理上的回避。例如《鼠族》中描繪納粹殘害兒童的畫面[21],為了避免血腥,只再現了尸體的下半部分,并且用對話框對墻上的血跡加以覆蓋,這抑或是出于對創傷的某種遮蔽——不忍回想,回避傷痛的再現。
即使在典型的現實主義小說中,“看起來真實”也僅僅是淺層的需求,在畫面的敘述引導之下最終抵達內心真實才是使用漫畫這一媒介的終極奧義。毋庸置疑,漫畫回憶錄一定是忠于心理真實的,即使漫畫一直給人留下夸張化、戲謔化的固定印象,但這兩者并非對立。相反,漫畫語言的某些“虛擬”方式能夠達成更好的效果。
《戰俘營》就在通篇敘事結構中采用了典型的虛擬場景,塔蒂將自己直接帶入,在時間上也順應了過去時,化身為少年時的自己,父與子共同置身于那段記憶中,對話模式也貫穿始終。奇妙的是,少年塔蒂作為雙敘述聲音之一,其身份又不全然虛擬,他模擬了那個不可能的肉身,但思想顯示出混雜的屬性,既包含假設的童年視角,又帶有明顯的作者的成人眼光。且不同于《鼠族》,《戰俘營》完全無意于區分時空,盡可能將虛擬場景完美融入,刻意打破了虛實的界限。鑒于少年塔蒂身上多重的組織因素,除了服務于形式上的時空統一外,其形象的建立明顯有著更深刻的考量——他懵懂、無知、單純,就像我們這些置身于這段經歷之外的每個讀者,我們可以跟隨“父親”去重現歷史的細節,但是終究無法感同身受。就像塔蒂在故事中不止一次對“父親”的發問:“你不是要逃跑嗎?你的計劃呢?”在我們的意識里,這一切似乎沒有那么艱難,然而就像他的不理解,僅僅身為讀者的非親歷者仍無法切身體會他們的饑餓、恐懼、絕望和無奈;而他身上的現代屬性和成人眼光,體現著作為創作者的塔蒂在了解事實之后對父親的關懷與悲憫,進一步說,更像是再現了當今這個時代和那段鮮為人知的戰俘歷史的對話。我們難以經歷歷史,但至少可以接近,可以發問,可以讓真實顯現。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映射了情感的難以共通性,但是盡管預設了非親歷者的理解限制,講述這段記憶仍然意義重大,揭露那些不為人知的真實,才有可能喚起回聲、穿越歷史的迷霧。
奈德爾曾一再強調,傳記是重組的藝術,這種重組不單單是指材料的組合重構,更強調創作者頗有助益的自我投射對抵達傳主心理真實的意義。薩特一生曾為多個作家立傳,如以福樓拜為傳主的《家庭的白癡》、以熱內為傳主的《圣熱內》等,許多歷史學家努力在他的自傳和傳記中解開謎題,最終卻在這些作品中尋找到了某些真相。每一部傳記都深藏傳記家本身的人格縮影,甚至更多信息,尤其是在一部他傳中,我們幸運地擁有了“兩部傳記”。
對話式敘述在《戰俘營》中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在于,它是兩種聲音的共同發聲。他傳式的回憶錄本身就包含兩種人格的顯現——傳記家和傳主。而對話式的雙重敘述使其更加凸現。對話意味著更加明確的意指,一人說話一人承接,一人發問一人回答,它使信息更加明確。話語信息的明確進一步塑造著對話雙方的人格和情感。如《戰俘營》中的父親,他是一個合格的戰士,盡管法軍的軍事安排如此糟糕,但他始終恪守命令,堅持到最后一刻。在少年塔蒂身上,我們看到他對父親的理解,他讓自己陪伴父親一路顛沛流離,見證著父親的孤獨與憤怒,以孩子的單純去關懷。我們在塔蒂的筆下可以看到父親對戰爭、對自己的理解,而塔蒂在重組父親經歷的同時,既是對父親的理解,也是在對自己作出新的解讀。
漫畫總是帶有天馬行空的特質,同樣作為虛擬手法,聯想(或想象)世界的圖像還原為回憶錄創造了更加豐富的表達空間,尤其是在表現感覺和情緒時,相比文字,漫畫的表達要直觀震撼得多。戴維·斯摩爾的泣血之作《縫不起來的童年》十分像一部心理小說,故事是主線,但氣氛、情緒、感覺、情感似乎才是他著重刻畫的。這是一部鮮有的文字極少的漫畫回憶錄,敘事和抒情幾乎都依賴于圖像,但效果令人驚嘆。作品中戴維在經歷兩次手術之后,他第一次鼓起勇氣,看到了那條碩大的、丑陋無比、觸目驚心的傷疤。如圖10 所示,那個夜晚,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22]:夢里有一只瘦弱的兔子,它正經歷著狂風暴雨,恐懼而絕望。沮喪中,它看到墻邊有一把傘,于是滿懷希望,將其緊緊抱在懷里,正當它奮力打開企圖獲得庇佑之時,卻驚懼而絕望地發現,這把傘是壞的!這段畫面僅有的文字,就是“媽媽”。戴維在深受苦痛和漠視之后,展現了這個預示著他不幸的真相的夢境,讓人悲痛不已!相似的聯想表達在這部作品中的還有很多,比如戴維觀察自己的囊腫時,聯想到他在醫院里看到的那些神秘的“小人”,覺得他們似乎就寄存在自己的脖子中,十分準確地展現了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懵懂好奇但又恐懼不安的心理狀態。在被所有人嘲笑為變態、娘娘腔之后,他覺得不被世界所接受,十分沮喪,幻想自己鉆進畫中的一個新世界,那里有許多小伙伴熱情地歡迎著自己……

圖10
人類生活與歷史緊密糾纏難以分割,漫畫回憶錄對歷史圖像式的追溯與還原,將種種記憶喚醒并可視化,生動地書寫著個體的生命軌跡,甚至是記憶本身的軌跡。記憶中那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都被漫畫這一載體分解變形、并置重組,形成了一種新的回望歷史的方式。這也是當代傳記多媒介化、多元化的表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