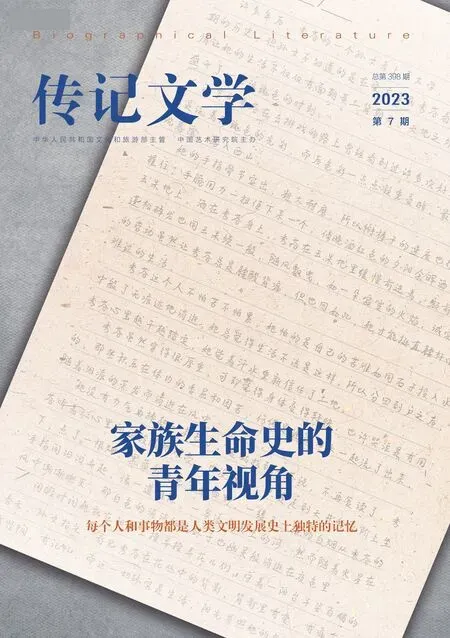夏菊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雜技藝術家
田潤民

1965 年,夏菊花在法國演出《頂碗》
夏菊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雜技藝術家,她的代表作《頂碗》于1957 年獲得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雜技比賽金質獎章,從此被譽為“頂碗皇后”。1979 年,她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在擔任中國雜技家協會主席的近三十年間,她提出建立國家馬戲院、創辦國家級雜技學校等建議,持續推動雜技教育、雜技理論創新,引領中國雜技走向世界。中國雜協授予她“終身成就獎”。2017 年12 月28 日,夏菊花入選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推薦名單;2019 年1 月13 日,入選2018“中國非遺年度人物”;2019 年9 月25 日,獲得“最美奮斗者”個人稱號。
夏菊花始終思考著如何讓雜技更好地走近人民、服務大眾,至今依然為傳承弘揚中國雜技而不辭辛勞。
“夏天哪有菊花?”
1959 年,李先念同志第一次見到夏菊花時,和她開玩笑說:“你這個‘頂碗皇后’,名字真怪,夏天哪有菊花?”
一句玩笑話揭開了她悲慘的身世。
夏菊花本不姓夏,也并非在夏天出生,當時身在武漢雜技團的她,湖北卻并非她的出生地。夏菊花本姓徐,1937 年9 月出生于安徽省潛山縣雙峰柳林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5 歲那一年,因生活所迫,父母忍痛將她送到一個馬戲班子混口飯吃。這個馬戲班班主姓夏,膝下無子,算命先生說,收個養女作“押子”,可改變無子命運。“小菊花”就這樣認夏老板為養父,從此改姓為夏,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賣藝生涯。
夏菊花跟著夏家班,走遍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她表演的節目是“空中飛人”,老板用一根粗繩子系住她的辮子,升吊在空中蕩秋千,這個節目又叫“吊辮子”。每一場演下來,用手搓頭發,大把大把地掉,人像昏死過去一樣。她想哭,卻不敢出聲,只能任憑眼淚默默地流淌;想痛痛快快睡一覺,又怕挨打不敢睡。有一次演“爬高梯”,她不慎從梯頂上掉下來,當場摔斷鎖骨,險些丟掉了性命。
那個年代,像眾多的雜技藝人一樣,夏菊花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
為上前線苦練《柔術》
1950 年年初,13 歲的夏菊花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隨夏家班從湖南衡陽來到武漢漢口的民眾樂園。民眾樂園是當時漢口最繁華的娛樂場所,戲曲、說唱、雜耍等各種表演藝術在這里百花齊放、爭奇斗艷。進入武漢雜技團的夏菊花第一次登上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舞臺。
朝鮮戰爭爆發后,武漢的文藝工作者紛紛報名上前線演出,夏菊花也報了名,卻沒有被選上,原因是年紀小,且沒有自己的絕活兒。這次“落選”,深深刺痛了夏菊花,她下定決心要練出自己的節目來。
1952 年,夏菊花在民眾樂園觀看了一部蘇聯大馬戲團的紀錄片電影,影片中一位女演員表演的“叼花柔術”引起了她極大的興趣。只見那位姑娘身體隨意伸展、卷曲、翻轉,將女性身體的柔軟度表現得淋漓盡致。生性好強的夏菊花想:“外國人能演柔術,難道中國人就不能演嗎?”
她把自己的想法講給養父聽,養父說:“孩子,這個節目好是好,但練起來很苦,首先要練牙齒的功夫,你能吃得了這份苦嗎?”
“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夏菊花點了點頭。
于是,養父在地板上挖了個洞,將一個彎曲的鐵桿插入其中,指著鐵桿頂端對夏菊花說:“這鐵頭就是將來演出的絹花,你必須用牙齒咬住天天練,一直練到能自如地做出各種動作為止!”
用牙齒和鐵較勁,多么痛苦的訓練!夏菊花天天練牙咬鐵頭,練得牙齒出血,還要練習下腰、掰腿等一系列高難度動作。舞臺上驚險度高、觀賞度強的優秀雜技節目,無不滲透著臺下演員日復一日無盡的汗水、淚水甚至鮮血。半年之后,夏菊花表演的《柔術咬花》終于和觀眾見面了。1954 年,《柔術咬花》被收錄進電影紀錄片《中國雜技藝術表演》,夏菊花在全國雜技界有了一定名聲。這一年,她如愿以償奔赴朝鮮,為“最可愛的人”慰問演出。

夏菊花創演《柔術咬花》
《頂碗》轟動歐洲
夏菊花真正的代表作是表演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雜技節目《頂碗》。
1956 年5 月5 日,法國巴黎文學藝術社社長、法國共產黨黨員索利亞與該社資方代表隆布羅索訪華。巴黎文學藝術社以促進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為宗旨,曾邀請蘇聯和東歐國家藝術團以商演形式到歐美國家演出。這次訪華,隆布羅索擬邀請一個50 人的雜技團于是年8 月初參加英國愛丁堡國際藝術節,10 月初在法國演出5 周,然后去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等國演出。
當時中法兩國尚未建交,這是對外宣傳新中國的好機會。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索利亞和隆布羅索的來訪十分重視。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批準雜技團出訪。
為了把中國最好的雜技呈現給歐洲人民,文化部從全國雜技團挑選節目,指定多次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中國雜技團演員金業勤擔任隊長,負責排練。武漢雜技團夏菊花的《柔術咬花》被選中。早在1954 年拍攝雜技紀錄片時,金業勤就結識了夏菊花,這次出國排練,他發現夏菊花的《柔術咬花》又有了進步,尤其是在表演方面。時年19 歲的夏菊花,散發著一股青春活力,尤其是她那雙大眼睛像會說話一樣,金業勤想讓她在舞臺上多亮亮相,問她:“你除了《柔術咬花》以外,還會演什么節目?”夏菊花回答:“還會演《頂碗》。”金業勤看后覺得節目很美,但技巧太少,只有“頂碗倒立”“右臥魚”“左含水”三個動作,構不成一個完整的節目。就在取舍兩難之際,金業勤突然想起一件怪事:幾年前在世界青年聯歡節演出期間,每當中國女演員出場時,很多“老外”不注意看演員的臉,而是前后轉著看她們的腳。金業勤問翻譯:“這些外國人是什么毛病,看表演不看臉,光看腳?”翻譯告訴他,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婦女都是小腳。金業勤吃了一驚,心想:“都什么年月了,這些外國人怎么還認為中國婦女纏小腳!”
他不由得把這件怪事和夏菊花的《頂碗》聯系起來。夏菊花的《頂碗》主要動作是拿大頂,頭上頂著一大摞碗,用手支撐身體倒立起來,兩條腿從頭上那一摞碗的兩側伸向前方,這不就是展示兩只腳嗎?如果這個節目能上演,就是正面宣傳新中國婦女的形象。想到這里,他下決心要促成這個節目上演。
為了把這個尚不成熟的《頂碗》變成一個完整的節目,金業勤設計了一個“啞劇”情節:他請年僅15歲的小演員陳臘本以助演的身份和夏菊花扮成姐弟倆,夏菊花扮演姐姐,陳臘本扮演弟弟。調皮的弟弟無意中發現了一摞碗,想把這一摞碗頂在自己頭上,卻怎么也頂不住,他想讓姐姐試一試,遂把12 只大花碗一個接一個地摞在姐姐頭上。當弟弟的手脫離那一摞碗的剎那間,只見姐姐前后左右晃動(演員故意而為),最終憑借高超的平衡力將一大摞碗穩穩地立在頭上。這時,弟弟既高興,又有點兒不服氣,給姐姐出了一道難題:頭頂著碗,在舞臺上走、跑、轉、跳、踢腿。姐姐迎接挑戰,頭頂寶塔似的一大摞碗,在舞臺上走、跑、轉、跳、踢腿。弟弟為姐姐的勇氣和智慧高興,但還不甘心,似乎有意要難倒她。他搬來一個板凳,在上面來了一個倒立,心里的潛臺詞是:如果頭頂一大摞碗的姐姐也在板凳上倒立,那摞碗會不會掉下來?只見姐姐兩手摁著凳子猶豫了一下,然后漸漸抬起兩只腳,從頭上那高高聳立的一大摞碗兩側伸向前方。夏菊花在表演過程中,身姿輕盈自如,臉上始終浮現著甜美的笑容。
在赴歐洲演出的節目審查中,夏菊花演完她的《柔術咬花》后,接著表演由金業勤臨時編排的《頂碗》。負責審查的領導表態:可以作為備份節目。所謂“備份節目”,即非正式節目,可以演,也可以不演,往往是在正式節目因故不能演的情況下的替換節目。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備份節目竟然在此次出國演出中震撼了歐洲各國。每當夏菊花頭頂寶塔狀的一大摞碗把雙腳從頭上伸向前方時,觀眾席里就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頂碗》由“備份節目”變成每場必演的主要節目,成為整臺雜技晚會的最大亮點。
就這樣,夏菊花在國際舞臺上有了名字。赴歐洲演出一直持續到1957年2月。同年6月,夏菊花主演、陳臘本助演的《頂碗》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并贏得金質獎章,這是我國雜技藝術在國際舞臺上首次獲得最高榮譽。
練功三年攀高峰
《頂碗》在歐洲演火了之后,夏菊花在武漢一下子變得家喻戶曉,但她并沒有陶醉和滿足。她心里明白,金業勤導演的《頂碗》是針對“中國女人都是小腳”這個偏見而來的,陳臘本當助演,是以表演來彌補技巧上的不足。夏菊花認為,這個節目本身還有潛力可挖,她決心繼續鉆研,把中國雜技“險、難、奇、美”四大特點展現在《頂碗》中:“險”即驚險,“難”指技巧難度,“奇”指奇特和想象不到的效果,“美”即好看。她從技巧的難度開始,從低到高、從靜到動、從雙手到單手。她站在凳子上練功,一個上午四個小時不下來,兩只手磨出厚厚一層老繭。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枯燥的練功中,夏菊花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
1957 年出國演出歸來的夏菊花年方20 歲,正是女孩子談情說愛的美好年華,集美麗與榮譽于一身的夏菊花不乏追求者,但為了攀登《頂碗》的高峰,夏菊花關上了感情的閘門,全身心撲在練功上,以碗做伴,道具碗成了她的最愛。回憶起那三年的“臺上幾分鐘,臺下千日功”,夏菊花說:“那個年代的我,根本不知道別的,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琢磨,一門心思要練出新動作,一上去就是四個小時。”“我體會最深的是,功夫是摻不得半點兒假的,也偷不得一絲巧。一天不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對手知道,三天不練觀眾知道。”
三年以后,還是在民眾樂園,夏菊花帶著48 只大碗和觀眾見面了,她展現給觀眾的是《頂碗》的新技巧——“拐子頂腳面夾碗”:在由方桌、板凳、三層長凳疊起的“牌樓”上,支起兩根拐子。夏菊花雙手支撐在拐子上起頂,身體輕盈地懸空,接著反曲身體,雙腿越過雙肩,向前伸出,形似春燕展翅,凌空飛翔。這一造型集“險、難、奇、美”于一體,成為《頂碗》節目的經典動作。夏菊花還打破了《頂碗》歷來固定于頭部的傳統,創造出“腳面夾碗”的高難動作,充分展示了中國雜技演員腰、腿、頂的功夫。這一高難動作被陳毅同志贊為“絕技”。
在表演藝術領域,電影有“腕兒”,戲曲有“角兒”,雜技因為沒有自己的明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人瞧不起,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有人認為雜技不算是藝術。然而,一個節目改變了人們對雜技的偏見,《頂碗》不僅展現了雜技的高難技巧,同時展現了雜技獨特的美。夏菊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雜技的第一代明星。
周恩來同志曾經說過“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指的是《十五貫》和昆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夏菊花的《頂碗》提升了雜技在中國表演藝術領域的地位,聞名于全國,走向了世界。
黃金時代
1965 年9 月,夏菊花隨武漢雜技團赴法國演出,這是中法建交后兩國政府文化交流的第一個藝術團隊。出國前夕,李先念同志特意在家里接待夏菊花等部分演員,叮囑道:“法國是第一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西方大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你們出國演出要體現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要通過演出宣傳中國的進步,為國家爭光。”
9 月30 日,武漢雜技團在巴黎塞納河對岸的夏樂宮拉開了首演的帷幕,這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夕,夏樂宮是巴黎有名的劇場,在這樣的時間和地點演出,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當晚,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等前來觀看演出。法國報紙不無幽默地稱:“出席觀看演出的部長們可以開一次部長會議。”演出結束后,馬爾羅特意接見夏菊花,稱贊“演出是詩一般的技藝,表現出中國人民勇敢勤勞、不怕困難的精神”,“看了你們的演出,說明沒有中國人辦不到的事情”。熱情的法國媒體還給夏菊花戴上了“頂碗皇后”“雜技女皇”的桂冠。
1966 年12 月,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周恩來同志和陳毅同志親自批準武漢雜技團赴柬埔寨,為亞新會祝賀和慰問演出。西哈努克親王稱贊:“武漢雜技團為在這里舉行的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增添了不少光彩。”他還把一枚“友誼獎章”親自佩戴在夏菊花胸前。
領軍雜技
改革開放以后,夏菊花已進入不惑之年,她離開了心愛的舞臺,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培養新人和藝術管理上。她的學生——武漢雜技團第四代《頂碗》演員李莉萍,繼承和發展了她的節目《柔術咬花》和《頂碗》,創造出“咬花腳底頂碗”技巧,將《頂碗》推向了一個新水平。1983 年,李莉萍的《柔術頂碗》在第九屆蒙特卡洛國際比賽中為中國奪得首座“金小丑”獎。夏菊花激動地說:“那一刻啊,我太高興了,比自己獲得金牌還要高興!因為《頂碗》后繼有人了,因為這是零的突破,是中國雜技發展的里程碑時刻!”

2018 年,本文作者與夏菊花(左)合影
1981 年,夏菊花當選為首屆中國雜技家協會主席,接著連任四屆,時間長達29 年,成為中國雜技界最具代表性的領軍人物。在雜協主席任上,夏菊花不圖虛名,辦實事,為建設武漢雜技廳、創辦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立下了汗馬功勞。她帶頭踐行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用行動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以扎實的專業知識、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贏得雜技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尊敬,中國雜協授予她“終身成就獎”,并推舉她擔任中國雜協名譽主席。
夏菊花自1963 年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后,又被選為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并連任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縱觀夏菊花的一生,她獲得無數的榮譽,擔任多項職務,但她從不擺名人的架子。走下舞臺和主席臺的夏菊花,為人謙虛,行事低調,把名和利看得很淡。她常說:“我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給予的,我要為人民為雜技事業做點兒實事!”“沒有國家的強大,我夏菊花哪能走向國際舞臺!每當我出國演出,參加比賽,我首先想到的是偉大的祖國!”
如今已經86 歲高齡的夏菊花老人,依然心系雜技,獻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希望能把雜技的美好傳給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